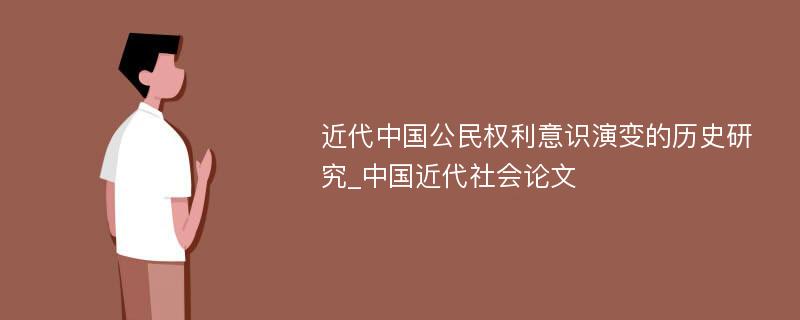
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权利论文,意识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8—0043—06
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 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 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 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 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 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 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 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 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 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 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 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 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 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 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 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 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 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 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 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 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 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们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具体深化的。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缺憾。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探讨明显不足。虽然人们认为财产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将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张知本一方面认为身体、居住、言论、结社等自由应绝对化,一方面认为对私有财产应严格限制。张知本说:“与社会生计有重大关系的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我以为无妨使之社会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加以严格的限制。本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绝对个人主义时代,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个人意志自由不能干涉’,是不容许法律对于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加以任何限制的。但个人本位法律观念一变而为社会本位后,此种有关社会生计之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已是要在维持社会福利的范围内,才得受到保护。”[28] 应该说,类似观点在当时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这自然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收稿日期 2006—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