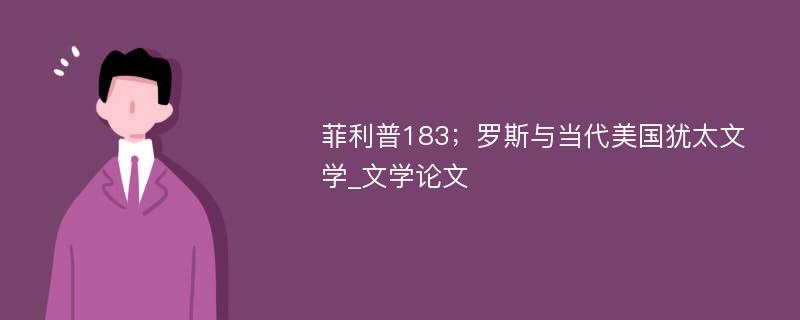
菲利普#183;罗思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菲利普论文,犹太论文,美国论文,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犹太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呈现出了一种复杂难解的状态,即对其定义很难进行严格的界定,以致目前学术界对哪些是和哪些不是犹太文学仍存有分歧。同样,提起美国犹太文学,任何同一或连贯的文化和宗教模式都不能成为衡量它的尺码,因为在美国,社会结构的熔炉性特征、经济的高速发展、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不断更新,使犹太作家从创作主题到风格上都颇具特色。随着19世纪大量犹太移民进入美国,描写犹太移民生活的美国犹太文学逐渐兴起,并在美国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二战以后,在美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和各种思潮中,涌现出一大批有代表性的犹太裔作家,象贝娄、辛格、马拉默德、梅勒等,这些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文化熏陶和历史命运写出了战后的一些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来解说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并一定程度地昭示了当代美国文学的走向。菲利普·罗思(Philip Roth,1933— )就是素有“神童”之称的最年轻的一位美国犹太裔作家。
罗思1933年3月19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独生子,家境颇差,父亲薪水较低,曾在家开鞋铺也遭破产。幸运的是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他在一家保险公司谋到了一个推销员的职位,从此家境好转。13岁时,罗思就读于威克高中,他天资聪颖,喜好读书。1950年,他入鲁特哥斯大学纽瓦克学院学习,次年转至巴克内尔大学并于1954年毕业,1955年又获得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在美国陆军服役一年,后因伤退役回到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讲师,教授英语。罗思在成名之际与马格丽特·威廉姆斯结婚,3年后婚姻破裂。威廉姆斯后来死于车祸。晚年他一直同一名叫克莱尔·布卢姆的英国女演员同居。罗思在任教期间便开始为各种杂志撰写短篇小说。19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成名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Goodbye,Columbus”),成为当时美国文学界评论的热门话题。《新闻周刊》赞扬这本小说集立意独特,富于创新,是“时代的杰作”,罗思也因此于1960年获“国家图书奖”和美国犹太书籍委员会颁发的“达洛夫奖”;同年,又获“古根海姆奖学金”和“美国文学艺术院奖学金”。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他的奖状中说:“……为了他所写的祖国国土的风景及人民具有趣味性及人情味……他的《再见吧,哥伦布》标志着一个青年文学家的成熟,他才华焕发、精湛,具有奋斗不息的勇气。”[①a]1968年,这部作品又被搬上银幕,对美国小说家来说这是少有的殊荣,罗思随后又被列入美国当代一流的小说家之列。
罗思的创作主要是长、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分别收集在1956、1959和1960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中。60年代,罗思发表了3部长篇小说:《放手》(Letting Go,1962)、《当她顺利的时候》(When She Was Good,1967)和《波特诺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1969)。这3部作品都以处在家庭矛盾关系中受压抑的年轻人为主人公来反映当代犹太人希图摆脱传统的桎梏,而又无法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的矛盾。6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骚乱狂躁的社会氛围中,“越战”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种族冲突不断升级,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前两部作品几乎以同一基调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阴郁沮丧的时代背景,而最后一部作品却是一个彻底的转折,一部“突破性”小说;其中的精神分析得到了最成功的运用,原先受压抑的愿望和情感被释放出来,获得充分的表达,堪称一部壮观的弗洛伊德小说,但也由于内容猥亵而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责难。总之,《波特诺的怨诉》的问世把罗思的创作推向了高潮,至此罗思完成了他在早期作品中对美国犹太家庭问题的探讨。
在《波特诺的怨诉》以后的作品中,突破传统压抑、解放情感的因素或强或弱,但始终对准某个焦点:《我们这一伙》(Our Gang,1971)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是两部政治性讽刺作品。前者以模仿总统演说、电视声明和记者招待会等闹剧式手法,揭露和讽刺尼克松政府的虚伪,是针砭时弊之作;后者以棒球和反共产主义为主题展开漫长的自由联想,开头与结尾套用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的章法,中间则有意穿插各种不同的手法和风格以形成强烈对比,产生讽刺效果,反映了稀奇古怪的当代美国社会。《乳房》(The Breast,1972)和《情欲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1977)是卡夫卡式的寓言,写一个英语教授陷入情欲困境后的心路历程。前者是罗思在大学执教“欧洲现代派文学”期间,直接受他所崇拜的奥地利犹太血统作家卡夫卡影响而创作的一部象征性小说;后者则以主人公凯佩希致力于一系列富有情欲主题的小说的研究为契机,反映当代犹太知识分子在情欲与事业之间的内心困惑,揭示生活和艺术、人的阅历和人的性格之间的关系。罗思花了7年的时间写成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1974)是继《放手》之后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其中最精采的部分就是他对自己多年思考过的“女性当权、男性服从”在主题上的高度概括。文学论文集《读我自己及其他》(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1975)阐明了罗思对现代生活以及包括他自己创作在内的犹太小说的复杂情感。
“朱克曼三部曲”——《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1979)、《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1981)、《解剖学课》(The Anatomy Lessons,1983)和《对立的生活》(The Counterlife,1987)从小说背景、人物经历乃至许多细节都与罗思60年代成名以来的文学生涯相同,带有文学自传性质。用罗思的话说,这几部作品“是虚构的传记文学,是受我自己的生活体验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①b]罗思每一部作品的问世,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评论界的非难以至嘲讽:如《鬼作家》中朱克曼因其一部短篇小说受到反犹指控;《解放了的朱克曼》所说的文学成就给他造成种种的误解以及结束语中朱克曼对布拉格的访问;《解剖学课》中他对评论家攻击的反驳以及《对立的生活》所叙述的与英国女人同居等等,都是他在小说创作上真我假我、亦真亦幻的一种革新探索,也是当代美国犹太人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自我身份异化的写照。
步入暮年以后,罗思仍笔耕不辍,但感情基调趋于平稳,大有向犹太传统道德回归之势。1988年出版的《诸多事实:一个小说家自传》以朱克曼同自己书信问答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阐明了罗思各个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亲自经历,讨论了是以小说形式还是事实形式表现罗思身世更为妥当的问题。他声称该书的出版表明他“已疲于用面具、伪装、歪曲和谎言来创作小说或描述自己”。在写到父子关系和父亲形象时,罗思一反过去过于激动的嘲弄语气,相反却充满了关爱与怜悯,表现出了深厚的挚爱亲情。《欺骗》(The Deception,1990)回归传统道德的倾向更加突出。小说中心就是一个名叫菲利普的主人公,51岁、已婚、客居英国。他同情妇每次做爱前后总要进行一番交谈。虽然小说的背景是性爱,但谈话的内容大多是反映作者本人向传统道德回归的意识。过去罗思对别人指责他“反犹”“叛逆”充耳不闻,但在这里他处处为自己的犹太本性辩解。
罗思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犹太人,主要描述这些人物在不断变化的美国社会中的自我意识或他们所起的作用。这些人中有的出身低微,有的是新生的中产阶层的典型,但都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缺陷。他们厌恶犹太人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犹太教规,斗争的目标是要冲破传统的束缚,结果造成父子不和、爱情失败,只得以淫乱的性生活或求助于心理医生来解脱内心痛苦和精神的空虚,由此引出精神危机这一主题。这里,我们不妨从3个方面来分析罗思创作的思想主题。
一、两代人的冲突
罗思认为“代沟”是犹太民族文化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犹太人生活中一个永恒的因素。作为一名从美国犹太居民区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深深懂得如何才能将自身的体验赋予“代沟”主题以深层的含义。他的第一部成名作《再见吧,哥伦布》起点就很高。小说以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揭示了美国犹太青年要摆脱父母的束缚、寻求自我发展的强烈愿望。新泽西州纽瓦克青年尼尔·克卢格曼与回家度暑假的女大学生布伦达·佩廷金在游泳池偶然相识并一见钟情。书中的“我”(即尼尔)虽出身低微,但心地善良,并怀着未婚男子初入社会的热情来探求人生必经之路。他不顾犹太传统规范和摩西十戒,在美国这块自由的文化环境里整日与布伦达寻欢作乐。而这对于象尼尔的舅母裴莱德(小说中充当尼尔父母的角色)这样传统道德极强的犹太女人来说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情。她强烈反对尼尔与布伦达的爱情,以致尼尔不得不去布伦达家里躲避舅母的管束。在布伦达家里尼尔看到了长辈们压抑人性的传统观念的虚伪,他带着讥讽的语气描述挤进富裕的中产阶层的佩廷金夫妇。老佩廷金不善言辞,但教诲下辈时说起创业的艰苦却振振有辞:“一个人只有艰苦工作才会有所得,坐着你就甭想。”商业上的成功使他(她)们变得富有,对女儿的感情也就更多地表现在满足她物质上的需要。小说结尾,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与尼尔在家做爱用的避孕物时,都惊得不知所措,想到的只是从物质利益上说服布伦达。母亲给她的信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把你送进最好的学校,给你买最好的东西……你知道吗?你伤透了父母的心。难首你就这样报答我们为你付出的一切吗?”[①c]字里行间突出了两代人之间的物质交易关系。
《鬼作家》更为严肃地反映了“代沟”主题。男主人公纳尔逊·朱克曼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作家,因写了一篇揭露某犹太家庭丑闻的短篇小说而与父亲发生争执。道克先生(朱克曼的父亲)无法容忍小说中对犹太人贪婪、自私、浅薄的“污辱性”描写,指责儿子有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因此极力要求朱克曼声明自己不是小说的作者。“你是个好孩子,”道克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讲:
你不是写这种小说的人,而且还谎称这是事实……你是在犹太人的环境中长大的,你不知道非犹太人读了你的小说是怎么想的,这不是你的过错。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不考虑什么伟大的作品艺术,他们不懂艺术,也许我也不懂。但我要说的是,人们不是看艺术,他们看的是你书中的人。他们将怎样评价你书中的人呢?你想过没有?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真正明白这世上对犹太人的友爱是何等地少啊?[①d]
对道克来说,对犹太人生活的任何批评对自己的民族都是不利的。这会进一步招致美国白人的歧视,使犹太人在这里难以立足。但是,朱克曼坚持“文学取材于生活就要反映生活的实质”这一主张。这样,父子发生争吵而大伤感情,以致最后道克不得不求助于赫赫有名的犹太法官奥非特先生来劝说朱克曼。朱克曼一气之下离开父亲,找到著名犹太作家朗诺夫,登门求教,寻求创作艺术的真谛。
这类作品还有《放手》、《当她顺利的时候》等,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代沟”对犹太家庭的影响:《再见吧,哥伦布》是一部恋爱的悲剧;《波特诺的怨诉》展示了青年人的病态发展;《鬼作家》反映了青年作家的苦恼。罗思作品如此突出两代人的冲突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语文学是犹太文学的经典部分,而“代沟”正是《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以色列(Isreal)一名本身便包含着“与神角力”之意。《旧约》第一章提到上帝6天创造世界万物,从一片混沌中造出天地、江河、鸟兽、树木花草等,在第六天造出亚当和夏娃。上帝即为“天父”——人类的始祖。对犹太人来说仅次于《圣经》的第二经典《塔木德》曾记载,当人类变得桀骜不驯时,“天父”大怒,训斥道:“即使跳蚤也比你们生得早。”很多《圣经》典故都隐含着“父与子”的思想主题。比如,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上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他们不仅同遭世俗的各种苦难,亚当还要受劳役之苦,夏娃须忍生育之痛。这种“父与子”的冲突首先表现为“原罪”。但是,犹太人从未认真对待过“原罪”,相反却认为,人要亲自品尝生活的味道,才可真正成熟起来;而这只有在摆脱上帝的“惠顾”、恢复人的本来的自由时才有希望做到。亚当在犹太人心目中已不是“堕落”的象征;他成为人类原始的纯洁的体现者。尽管亚当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仍活了9百多年,而且繁衍了无数后代。
上帝与人立约更深化了“父与子”的主题。《旧约》中的“约”字就是“契约”之意。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说讲道:亚伯是以色列的先祖,娶撒莱为妻。受神的启示,他去哈兰(Harran)。后来,上帝令他离开家园,寻求新土地,并许给他荣誉、土地、子孙后代。亚伯遵从“父意”移居迦南(Canaan)。他以自己的虔诚赢得了上帝许给他的一切,成为“以色列之父”。上帝同亚伯立约确定了犹太人的“选民”地位。后来,上帝又同摩西立约,即西奈契约,具体为“十戒”。它显示出神与人的双重关系:犹太人要对上帝笃信不移,上帝赐给他们土地,使他们能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逐步堕落,开始崇拜偶像,上帝震怒,使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灾难,以示惩戒,“父与子”终于反目成仇。上帝与“选民”的斗争成为《旧约》的主旋律。上帝抱怨说:“我把孩子们养大,他们却起来反对我。”对此,评论界认为“选民”与上帝反目为仇是犹太民族不幸的根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罗思作品中的母子冲突多于父子冲突,母亲在家庭中居主导地位。犹太问题专家哈洛德·费斯认为,在传统的犹太家庭里,父权是犹太教信仰的象征,但后来随着犹太教让位于基督教,父权便逐渐由母亲取而代之。在《旧约》“创世纪”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亚伯因妻子撒莱久无身孕就爱上了他的一个女佣夏甲并和她有了孩子。撒莱于是对夏甲怀恨在心,尽管亚伯把上帝赐予他的一切同撒莱分享也不能满足她。以后,撒莱90岁时生了儿子以撒,便要求亚伯赶走夏甲和她的儿子以确保以撒的继承权。亚伯对她的要求一一照允。这成为母亲涉足父权的典型例子。在当代美国犹太家庭里,父亲往往把家里的一切,包括子女的教育权都交给了母亲,母亲却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权利。这样,母亲就成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被讽刺的对象。
父亲变成了母亲!母亲又变成了父亲!在我家里性别角色混淆到了何种程度啊!谁应该管教我,谁应该袒护我;谁该是软弱的,而不该咒骂、责备、批评、挑剔……[①e]
二、异化带来的困惑
在历史上,古希伯来人虽历经与迦南、非利士、米甸、巴比伦等民族的冲突而几度沉浮,但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仍保持了大体一致的生存空间,呈现出相对统一的文化特征。公元66年与135年两次犹太战争的失败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上有着关键意义,它标志着犹太人正式开始了流散世界各地的历史,从而导致了犹太文化的分散状况。犹太移民最初集中在欧洲各地,从1654年开始陆续有小批被迫改宗的犹太人来到北美洲,但因人数甚少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接触。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从1870年开始,大量的德国及东欧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犹太文化才真正开始了与美国文化具有决定意义的碰撞。据《美国犹太年鉴》统计,1900年美国犹太人已从1830年时的6,000人猛增至100万人,到20世纪上半叶已达到350万人。此后美国政府虽然限制移民运动,但由于二战期间纳粹分子在欧洲残杀了600万犹太人(约占当时犹太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导致幸存者陆续涌向美国,以致二战时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美国的犹太移民来自四面八方,社会、经济背景各异,甚至移民内部也有矛盾,但共同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种族身份,使得犹太移民文化在美国主体社会中以相对统一的亚文化体系出现,与美国社会发生着文化接触,从而也实现了犹太文化的美国演变。这种演变一方面以犹太传统为文化之根本,另一方面又融进了美国文化的若干内容,因而美国犹太文化一定程度地整合了两种文化的双重特性。在犹太移民演变为美国犹太人的文化过程中,移民们呈现出种种困惑的文化心态。
在文学主题上,犹太作家特别发挥了那些根植于犹太传统而又与当代社会相契合的思想。几千年来犹太民族作为客民生活在异邦文化的夹缝之中,始终处于边缘人的地位,面临着一种被同化的危险。罗思正是以描写被美国社会同化的犹太人而著名的作家。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窥见到当代美国社会中年轻一代犹太人的变态心理,他们一方面厌恶犹太人的家教观念和教规,拼命想挣脱传统的桎梏,另一方面又难于在现代美国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乐园。对于这种夹在古老传统和现代文明缝隙间的矛盾心理,别的犹太裔作家虽然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描绘,但谁也不及罗思写得那样深刻鲜明。罗思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描写他认为是“疯狂”了的世界,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世界不是那么疯狂,我早就改写其它重大题材了。”
罗思借助性问题来表达自己对异化本质的思考。性问题成为主人公异化后失却自我、孤独无援的症结。对性的思考在本世纪初的文学作品中就早已有所体现。D·H·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儿子与情人》已经向世人发出了性自由的呼唤,而对犹太作家来说,对性的探讨只是在本世纪中叶,这大多由于犹太家庭对性行为相对轻视,以致子女不得不以一种冒险的方式来体验性的奥秘。犹太人的性欲渴求和压抑在贝娄和马拉默德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罗思在作品中却是把它作为研究课题并用精神分析法来探讨主人公的性困扰。罗思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从《波特诺的怨诉》到《欺骗》直接以性来展示主人公的精神空虚并把性行为当作摆脱压抑、争得自由的武器。
《波特诺的怨诉》就是一部曾因露骨的性描写和暴露犹太人的隐私而毁誉参半的作品。主人公波特诺不堪忍受传统的桎梏,用无节制的手淫和纵欲来发泄内心的苦闷。波特诺从小困惑于自己的犹太本性:一方面父母的关爱使他内心良知上要作一个“犹太式”的好孩子——聪明、自尊、有责任感;另一方面他要作“男子汉”的愿望要求他必须打破那些阻碍个性发展的家长制禁忌。这样,他就陷入了代表犹太传统的父母社会文化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之中。作为犹太血统的他要融合到富有吸引力的美国文化中去,就必须消除犹太出身这个隔阂。他想以性征服的方式,得到安格鲁·撒克逊等非犹太血统的纯美国人角色认同。于是他便同各种纯美国女人发生性行为。这种性行为与手淫有着同样的功效,在他看来再也没有比这更使父母生气的了,而他这样做也正是要向父母显示自己生命的独立存在。他把这些纯美国女人都冠以“Monkey”、“Pumpkin”、“Pilgrim”之类的绰号,使之在自己的心目中成为没有人性的东西,成为他消除身份隔阂、消除心里不平衡的机器。书中写到:
大夫,我所讲的,与其说是我想跟这些美国姑娘们搞,不如说我想跟她们的背景搞——通过做爱,我会发现美国,征服美国——也许更恰当。哥伦布、史密斯船长、温斯诺普总督、华盛顿将军——现在是我,波特诺,好象我明确的使命就是从48个洲各勾引出一个姑娘来。[①f]
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波特诺想冲出犹太家庭及其传统,在竞争激烈的陌生环境中参与进取的强烈欲望。而实际上,波特诺根本不可能通过性行为来“征服美国”,因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美国人,他必须摆脱犹太本性,彻底异化,而这一点他却做不到。虽然他尽了力,但儿时父母的声音始终在他潜意识中回响。
《乳房》和《情欲教授》直接以性的苦闷来夸张地表现人性的变异。《乳房》类似卡夫卡的《变形记》,书中照旧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由教授戴维·凯佩希夜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150多磅重的女性乳房开头,接着通过这个会说话的乳房荒诞不经的功能行为的展现,描写了许多变态现象。乍看起来似混乱不堪,但内里则体现了作家对美国商业性文化压力下个人异化的忧虑和关注。如果说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是由于生活的重负与现代社会中人们职能单一、彼此冷漠所致,那么《乳房》中凯佩希的变形可归于美国性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冲突所起的知识分子的惊恐。
《情欲教授》描写主人公变形前的痛苦,延续了《乳房》的旧主题。戴维·凯佩希是个既有情欲又讲授情欲的教授。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周围人物对他双重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年轻时,他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要求十分严格,而电影中滑稽演员的低俗表演却时常对他产生诱惑。长大后,他追求爱情,但总被爱情所困扰。在经历了凄凉的婚姻冲突后,便陷入了深不可测的自我怀疑之中。与海伦离婚后,他幸运地找到了克莱尔·奥文顿这样肉体丰满、性情安详的妇人。他如此迷恋这个女人,以致他的怀着卡夫卡梦魇的头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在事业上,凯佩希讲授一系列有关情欲小说的课程,对契诃夫和卡夫卡的研究使他的想象力离不开灾难,习惯于为失败而伤感,难于爆发出欢天喜地的感情。罗思在此展示了凯佩希在情欲强烈和能力低下的冲突中的困惑。他的双重性格始终使他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情欲与负罪感、自由与压抑、幻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
罗思的作品体现了当代美国文学最明显的特点:无根基的感受和空虚。这是他对当代美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对美国犹太人表现出的困惑和荒唐行径,罗思采取冷眼观察的态度,加以嘲弄和攻击。他曾振振有词地说:只有昏沉肤浅的作家,才认为能对改变事物发生作用,才能自觉地处理矛盾和争论。这样,他的主人公在纷繁杂乱的世事面前总是流露出一种“永久的困惑”。
三、在传统中寻找自我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表现出一种向犹太传统回归的倾向,这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二战前,美国犹太移民同其它少数民族一样,生活在被异化的阴影之下而被迫放弃本民族的传统习俗,以获得美国主流文化的接纳。四五十年代期间,多元文化观念开始为社会接受,然而这一代犹太移民后裔已经为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主流文化同化,他们的民族群体意识已变得十分淡薄。60年代末期以来,多元论开始深入人心,加上美国这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又不能提供一个有凝聚力的文化特征来取代移民已基本放弃的种族特征,于是许多群体和个人开始重新寻找和恢复自己的种族文化,以取得群体感和认同感的立足点。“这对于生活在现代工业化和官僚化社会的文化沙漠中所面对的冷漠、孤独和无聊心态来说,确是一种解脱。”[①g]民族群体意识重新抬头这一趋势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十分自然地表现为返回犹太家园、重温犹太价值观念、继承和发扬犹太文化传统。这一倾向在罗思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异化导致了犹太身份的丧失与自我本质的危机。罗思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异化的痛苦后,并没有彻底地消极退让,相反,在小说结尾处,读者时而发现主人公返回犹太家园,希图实现自我的倾向。
《再见吧,哥伦布》中的尼尔由于美国文化的影响,既想与布伦达纵欲,又不愿承担责任,于是一再要求她避孕。任性的布伦达虽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不想受到牵制,暑假一结束,便将避孕物扔在家里返回学校。由于布伦达母亲的斥责与反对,两人只好分手,在分手后的结尾部分,书中写道:
对着玻璃上反照出的我的形象,我觉得自己仅仅是玻璃上能看到的那张脸、那双手、那对脚的物件而已。外表并未反映内心。是什么东西把我内心的追求和向往变为爱,然后又将其变为欲释放出来?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赢得变成失去,使失去变成赢得呢?使我对布伦达产生爱情的东西,难道也会使我产生跟她睡的淫欲吗?[②g]
尼尔的反思表现了他对人性与自由的关注。他开始想自己是否真爱布伦达,并怀疑失去她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是输还是赢的问题。尼尔没有找到自我,但却作出了回归犹太性的表示。小说最后两句写到尼尔并未迟疑多久,及时地赶上了去家乡纽瓦克的火车,并在新年的第一天,又回到从前的图书馆开始了新的工作。这似乎是向读者暗示主人公将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波特诺的怨诉》的主人公在“征服”各种美国女人的过程中被打败,于是便把眼光投向犹太家园——以色列,期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尝试到一种正常的性行为。小说结尾大肆渲染他处身于犹太人世界的激动之情。可笑的是,以色列也并非他的最终归属。他和一个以色列女人初次相遇便发生冲突,以致自己的性功能彻底丧失。他向往已久的家园竟成为注定他失败的坟墓。在以色列这块犹太人享有自由的土地上,波特诺却成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鬼作家》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两个犹太青年回归传统的过程。女主人公蓓蕾特是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孤女。二战期间,她偷偷地记下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暴行。后来,纳粹分子洗劫了她全家,从此她便同家人断绝了音讯往来,孤身来到美国避难。战后,她的生父听说她已丧生,就把她在战争中写的日记公诸于世,一下子轰动了西方社会。蓓蕾特无意中读到父亲全文发表自己日记的消息,悲喜交集,感慨万分。一方面她急于与父亲相认,另一方面又不愿让人知道日记的作者还在人间,为了使那些非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眼泪象犹太人的血那样流下来”,她便毅然放弃与父相认的机会,充当日记的“鬼作家”。同时,蓓蕾特对养父兼教师朗诺夫有感激爱戴之情,一天夜里,她要求同朗诺夫结婚,一块儿移居佛罗伦萨,老作家慑于社会舆论和道德观念,婉言拒绝了她,由此造成两人的暧昧局面。这一切都被初涉文坛的朱克曼发现。仰慕已久的精神父亲与这位犹太姑娘的种种尴尬场面、老作家摆弄拼凑句子而不是面对现实的小说创作方式,使朱克曼一贯视为极神圣的东西遭到破灭,乃至想到与生身父亲的关系。朱克曼得知蓓蕾特的日记之事后,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敬仰和爱慕之情。小说结尾描写朱克曼曾梦见自己与蓓蕾特在家里定婚的场面,以此向父母证实自己的犹太本性和回归犹太传统生活的决心。
《对立的生活》描写了犹太作家朱克曼(《鬼作家》中的主人公再次出场)和他那位当牙医的弟弟亨利的非凡际遇。朱克曼和亨利都已人到中年,却发现自己不但同现实生活对立,而且兄弟俩的生活也惊人地彼此对立。39岁的亨利已颇有名气,家庭生活也安定舒适。他既有娇妻爱子,又有情妇,甚至还得到一位瑞士血统的德国金发女郎的垂青。但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犹太人,他不辞而别,独自一人到以色列,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追求犹太人的自我更新。在《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中,罗思以朱克曼作为叙述者曾告诉读者,亨利性功能失调,并患有心绞痛,可他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为了继续寻欢,上了手术台,终于死亡。朱克曼本人虽然结过3次婚,但因身患心脏病和不治之症,所以一直无子。而在这部作品里,罗思又转而叙述朱克曼到以色列劝已经复活的亨利回美国,他自己则在手术台上死去,还举行了葬礼。故事情节如此扑朔迷离,两兄弟的生命仿佛互相交替,朱克曼在一封给亨利的信中就说过“咱们俩的位置在互相交换变形”。这里,罗思借用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经历道出了什么是“犹太特性”以及犹太人与犹太精神文化中心以色列的情感联系。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作为犹太文化在美国演变的生动写照,体现了古老的犹太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交融,呈现了非凡的文化景观、文学实绩,并多方面地表现出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性意义。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众多流派思潮中,象贝娄、马拉默德、梅勒、辛格、罗思等犹太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先锋角色,在主题思想、创作方式、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一定程度地领导了当代美国文学的趋势。犹太作家的成功以及犹太文学在当代美国文坛的显要地位已经引起了美国文学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美国评论家格里布斯坦曾这样说过:
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的更深刻了解,有谁能比犹太人更好地教育我们呢?这些最有经验、最老练的受苦的人……我们美国人在美国的国土上没有经受过最残酷的战争恐怖。我们应该了解遍地血腥、陈尸累累的惨境。无论是由于内疚,还是由于病态的好奇,犹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西方人心目中一向扮演巫师、秘诀掌握者角色的犹太人,在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遭受的折磨,已使他们从令人憎恨、恐惧、取笑的人物转化为引人注目的受苦人。[①h]
罗思堪称犹太作家的典范。他的小说文风坦率,情节清楚,人物栩栩如生。尽管有时情节发展显得突然,故事结构有些松散,但这决不会使他充满活力的作品有所逊色。他的作品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均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美国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在创作手法上,他比较善于吸收各家之长。《伟大的美国小说》就是模仿马拉默德的《呆头呆脑的人》(1952)写成。而他作品中轮廓分明的地方背景、对美国文化中的夸张事例的爱好以及他的诙谐有趣,又与贝娄十分相似。他很欣赏梅勒的漫画式的人物描写,认为这就象“在实验时往实验品上滴上一滴染料一样,可使肉眼难以发现的某些物质显得清晰可见”。罗思的优秀作品至今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注释:
①a 杨为珍、张永昊编:《外国文学家小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9页。
①b 谢为群译:“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采访录”,《外国文学报道》,1988年,第41页。
①c 菲利普·罗思:《再见吧,哥伦布》,1959,第90-92页。
①d 菲利普·罗思:《鬼作家》,1979,第95页。
①e 菲利普·罗思:《波特诺的怨诉》,第59页,第234页。
①f 菲利普·罗思:《波特诺的怨诉》,第59页、第234页。
①g Michael W.Hughey and Arthur J.Vidich,"The New American Pluralish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Human Sciences Press,1992),P.102).
②g菲利普·罗思:《再见吧,哥伦布》,第96页。
①h 《世界文学》编辑部译:《当代美国文学》(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