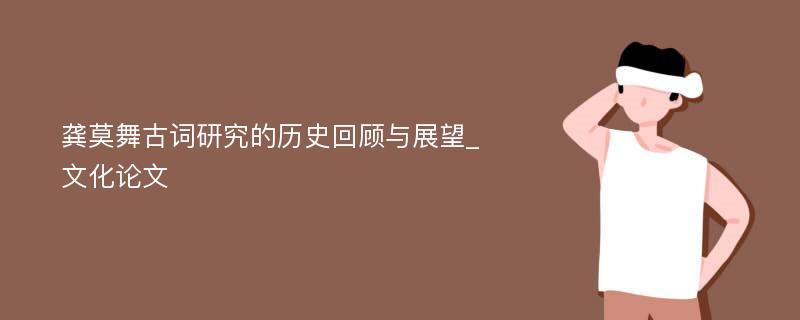
《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回顾论文,公莫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6-0034-05
《公莫舞》古辞最早见于《宋书》卷二十二《乐志》四,称《巾舞歌诗》,或称《公莫巾舞歌行》,共308字。《南齐书》卷十一《乐志》载其歌辞开头15字,结尾25字,并与《宋书》略异。《乐府诗集》卷五十四亦载其全文,比《宋书》少“海何来婴”一叠句,共304字。因《公莫舞》声辞杂写,东晋后已不可句读,遂成千古之谜。本不得其解“似不必强作解人”[1](P105),但又因它与《铎舞歌·圣人制礼乐篇》是迄今仅存的两篇诗、乐、舞并录的作品,乃是研究汉代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的宝贵文献,所以,一千多年来,研究者不乏其人。大致说来,20世纪前主要是讨论外围问题,20世纪后则重在解读原文本身。
为便于回顾,依《宋书》照录原辞如下:
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哺声何为茂时为来婴当思吾明月之上转起吾何婴土来婴转去吾哺声何为土转南来婴当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婴下来吾食草吾哺声汝何三年针缩何来婴吾亦老吾平平门淫涕下吾何婴何来婴涕下吾哺声昔结吾马客来婴吾当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婴海何来婴海何来婴四海吾哺声熇西马头香来婴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谁当求儿母何意零邪钱健步哺谁当吾求儿母何吾哺声三针一发交时还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遥来婴弩心哺声复相头巾意何零何邪相哺头巾相吾来婴头巾母何何吾复来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来婴推非母何吾复车轮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转轮吾来婴转母何吾使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使群去时使来婴去时母何吾思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时思来婴吾去时母何何吾吾。
20世纪前的《公莫舞》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关于名称来源及歌辞内容。沈约在《宋书》卷十九《乐志一》中称:“《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俗云项伯,非也。”这段记载说明沈约对《公莫舞》有三点认识:其一,它是以“巾”为道具的巾舞,晋宋时仍在演出;其二,名字来源于所谓“鸿门故事”的传说不可信;其三,《公莫舞》其声腔就是《公莫渡河曲》。今天看来,沈约关于《公莫舞》以巾为道具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其等同于“今之巾舞”似表述不够严密,它只是“巾舞”中的一个剧目;他对附会“鸿门故事”的否定很有见地,该作确与“鸿门故事”无涉;“传唱已久”的判断为今人研究该作的产生时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将《公莫舞》与《公莫渡河曲》混而为一却是一种误会。《南齐书》卷十一《乐志》将《公莫舞》视作晋代作品,更是误解。云:“晋《公莫舞歌》二十章,章无定句,前是第一解,后是十九、二十解,杂有三句,并不可晓解。建武初,明帝奏乐至此曲,言是似《永明乐》,流涕忆世祖云。”从两正史记载说明,《公莫舞》的来源及内容东晋后已发生误会和不可复解;不过,《南齐书》从音乐角度分二十解并称为致明帝“流涕”的悲调,却启迪了今人。之后,传为陈智匠著的《古今乐录》否定了沈约《公莫舞》即《公莫渡河曲》的看法。云:“今三调中自有《公无渡河》,其声哀切,故入瑟调,不容以瑟调离(杂)于舞曲。惟《公无渡河》,古有歌有弦,无舞也。”[2](P787)其理由是《公莫舞》有歌有舞,而《公无渡河曲》乃入瑟调,而瑟调不是舞曲,故有歌又有音乐伴奏而无舞,只唱而不舞的《公无渡河曲》与有唱有舞的《公莫舞》不可能是同一篇作品。《古今乐录》的看法颇具说服力。至唐宋时期,人们对《公莫舞》名称来源和内容的认识更模糊了。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三《乐志》下,综合《宋书》所载及沈约按语而述之,自当视为沈约观点的照录。此前魏征等《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之后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却皆信从《宋书》载“鸿门故事”传说,而删除沈约“俗云项伯,非也”的否定性按语,肯定此舞与项伯有关。中唐李贺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公莫舞歌序》云:“《公莫舞歌》者,咏项伯翼蔽刘沛公也。会中壮士,灼灼于人,故无复书,且南北乐府,率有歌引。贺陋诸家,今重作《公莫舞》云。”[3](P4409)不仅认为《公莫舞》的舞名源于“鸿门故事”,且演唱内容就是“鸿门故事”,他自己的重作表现的同样是此内容。《乐府诗集》晚出,卷五十四不仅收录了《公莫舞》歌辞,还征引了《宋书》、《南齐书》、《古今乐录》、《旧唐书》等书中的相关文献,为今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郭茂倩征引而不按断,说明其在《公莫舞》来源问题上无所适从。综上可见,沈约《公莫舞》与“鸿门故事”无关之说并未被唐宋人普遍接受,这一时期对《公莫舞》名称来源的认识从总体上反比沈约倒退了。不过,《隋书》与《旧唐书》指出《公莫舞》“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也对后人研究“巾”之形状有所启示。《隋志》所引齐人王僧虔“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4](P377)之语也为今人确定《公莫舞》乃汉时民间俗舞提供了佐证。
第二,关于《公莫舞》歌辞难解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当推沈约贡献最大。他在《宋书》卷二十二《乐志》四《今鼓吹铙歌词》题下加注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依笔者理解,其意为,乐人演唱歌辞,只凭口耳相传,所以只重声音而不重辞意,这便指出《公莫舞》歌辞原本就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因是文字只记其音,难免出现用同音而不同义的别字;其二,因记音不确,有些地方可能误用了读音相近的错字。《古今乐录》征引沈约的另一段话更切中问题要害:“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尔。”[2](P285)古代记录乐府的书籍,都将歌辞和声字一起记录,原本歌辞用大字书写,声字用小字书写,传抄中大小字逐渐相混,遂致歌辞与声字难以区别,歌辞的意思也就自难明白了。相比之下,晚出的智匠所谓“《巾舞》古有歌辞,讹异不可解”[2](P787)之说反逊色不少。称不可解的原因是歌辞“讹异”,却未言明“讹异”之因,更未及关键的“声辞合写”。细审“讹异”,当为记音误用错别字和传抄讹误两端。至北宋,《景祐广乐记》综合沈约和智匠之说而从之。云:“《巾舞歌辞》一篇,字讹谬,声辞杂书,不复可分。”[5](P666)惜也未能对“字讹谬”原因作具体解释。到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则将“讹异”、“字讹谬”之因的一端说明白了。云:“古词之不可读者,莫如《巾舞歌》,文义漫不可解。……岂非岁久文字舛讹而然耶?”即《公莫舞》之所以难解,盖因时代久远传抄讹误所致。严羽此说虽亦忽视了最根本的两因,却是沈约之说的重要补充。至此,古人将《公莫舞》难解之因归结为三点:声辞杂写、用错别字记音、传抄讹误。笔者以为,此三解可谓准确而全面,为后人恢复《公莫舞》本辞真貌并解读其文意提供了一把钥匙。唐宋以后,随着《公莫舞》音乐的失传,论述《公莫舞》歌辞者渐趋衰微。
进入20世纪,《公莫舞》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终获突破性进展。首发其端者是陆侃如、冯沅君两先生。他们撰写于1925年至1930年修订于1937年的《中国诗史》,在《公莫舞》研究上取得两点成果。一、依据对自认为可解的“城上羊,下食草”数句原文的断句,将作品主题推测为“或者是写游牧生活的。”[6](P187)惜两先生未将声字与歌辞分开,故断句不确,仅依错断之句推测主题,自然亦很难准确。但“游牧生活”之说不仅摆脱了旧说的束缚,客观上还将《公莫舞》确定为产生于北方并反映北方生活的作品,此对杨公骥先生确定该作品产生地提供了启示。二、校正了古文献中“莫”、“离”、“舞”三字之误。两先生认为,《公莫舞》“与《公无渡河》(《宋书》误“无”为“莫”)却显然无涉。”[6](P186)此处校《宋书》“莫”为“无”,为否定沈约误说提供了旁证,因沈说的主要依据即两题目都有“公莫”二字。又,引录《古今乐录》云:“不容以瑟调离(杂)于舞曲”。[6](P187)校“离”为“杂”,则为否定沈约上说提供了确证。作“杂”,则指出入于瑟调的《公莫(无)渡河曲》有歌而不可能有舞,故与有歌有舞的《公莫舞》绝非同作,若作“离”,则结论正相反。再有,引录《古今乐录》云:“(《巾舞》)江左以来,有歌舞(無)辞”。校“舞”为“无”,遂释《公莫舞》歌辞六朝时既已不可解何以还能演出之疑。其时演奏的仅是《公莫舞》音乐舞曲而已不含歌辞。确切地说,陆、冯两先生的成果还算不上对《公莫舞》歌辞有实质性研究。
对该作实质性研究是从逯钦立先生开始的。逯先生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其1945年撰写的《汉诗别录》中。一、在系统研究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声辞杂写”致难解读的过程作了较科学的揭示。云:“考汉乐旧谱,名曰(声曲折),与歌诗分立,本不相混。惟降至魏、晋,旧谱不存。乐人以音声相传,无形中曲歌合流,而声辞以杂,然本身之分辞分声以及曲折,彼此限界,固未尝泯也。更以大字、细字,混而不分,歌诗之辞义,亦濒于不解。此其升沈离合之大凡也。”[1](P97)其说甚详确。二、依“声辞杂写”之例,首次将《公莫舞》歌辞和声字试作分离。从研究现存与魏晋乐谱旧式相类的六朝道曲乐谱入手,分道曲声字为甲、乙两类,甲类为乐谱用字,乙类为指示该字演唱时拖腔之用字。进而类推析出《公莫舞》中的声字“吾何婴”,“意何零”、“子以邪”等。在此基础上,对《公莫舞》歌辞作了点校。因声字判定不精,更因逯先生尚未发现原辞中有舞蹈术语等,致使标点后的歌辞仍难通读。尽管如此,其研究方法确为后人昭示了解决问题的门径,功不可没。三、对部分字句作了训释。如,释“公莫”为“公姥”,“汉人舅姑之谓”,揭示出《公莫舞》本名当作《公姥舞》:释“城上羊下食草”与鲍照诗“踯躅城上羊,攀隅食玄草”义同;释“行度四州洛四海”之“洛”为“略”之借字。皆为确解,并成定论。四、把主题解为“弃妇之辞”,后又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发展为“西汉人形容寡妇之舞诗”[7](P278),其说虽不确当,然亦启迪了部分学者。此外,将《公莫舞》断为西汉作品,虽立论依据不可取,其结论却至确。
在逯先生研究之基础上,杨公骥先生的研究获得重要突破。杨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确认《公莫舞》中除声字外尚杂有舞蹈动作术语等。他先于1950年发表了《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光明日报》1950年7月19日),35年后又作了较大修改和增订,题为《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第二文文末注:“一九五零年四月四日草毕于长春,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增订”,作者自视后文为前文的定稿,故我们总结杨先生的成果亦以后文为代表。其成果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全面区分并解释了原文中的歌辞、和声,语助词、舞蹈动作、角色名称等。1.歌辞(略)。2.和声有:“哺声”,就是“辅声”即“一人倡,三人和”的和声;“相哺”,即“相和”;“哺”即“辅”之假借字。3.语助词有:“吾”,读如“乌、啊、吁”;“何”,音同“荷”即悲叹声;“邪”,同“牙”,犹如今日“呀”字。4.舞蹈动作有:“转起”、“转”、“转南”、“健步”、“三针一发”、“弩心”,“相头巾”“头巾”、“推排”、“转轮”等。5.角色名称为“母”与“子”。可见杨先生对原文的研究比逯先生细致系统许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他将“和声”和“语助词”相混皆视作“声字”,仍值得商榷;对各具体词语的归类颇有不正确处,已被后来学者陆续指出。二、从歌舞剧角度对原文作了句读校点。依“大字写辞,小字写声”先例,用不同字体标出歌辞、和声、动作、角色;校改原文错讹;指出歌辞韵脚和反复句章法。尽管杨先生完成的校本存在不少问题,有待后人逐步完善,然毕竟首次使《公莫舞》成了一篇大体可以通读的文学作品,实乃功泽后学。三、在点校原文基础上,对歌辞内容、表演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作品的性质和意义。1.将内容主题归结为“一场表现母子分离的‘小舞剧’”,儿子离家的原因是外出经商谋生。将全剧分为五节。杨先生的“经商”说,今已被多数学者所否定,但其对作品内容的描述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2.分节描述了两位扮演母子的演员从跪坐演唱到起身而舞的表演过程。3.确认《公莫舞》的性质和意义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四、大体考证了《公莫舞》产生的时限与最初流行地区。认为其产生的时间下限不会晚于公元25年;其最初流行的地区是冀州(今河北省)中山、常山、邯郸一带。杨公骥先生对《公莫舞》研究的贡献颇大,以致于被有的学者视为《公莫舞》研究的草创者。
杨先生之后,白平先生也对《公莫舞》研究作出了贡献,惜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白先生在刊发其《汉〈公莫舞〉歌词试断》(《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1期)一文时似未见过杨文,故称“这篇古诗词虽载录至今,却未能断句和得到解释。”他的主要贡献是:一、提供了新的断句思路和依据。认为《公莫舞》难以解读的原因之一是后之好事者在正文之外插入了“标注文字”,即“哺声”(7见)和“哺”(5见)二词,只是未标注到底。由此判定,其歌辞由主句(即辞句)和辅句(即声句)两部分组成,凡辅句都是主句的部分(或全部)的复唱,并在末尾用“哺声”或“哺”字标注之。“吾”(33见)多是煞尾字。白先生的思路可使复杂问题简明化。二、受《南齐书》启发。将歌辞分为二十个段落。此种划分虽将音乐之解误作歌辞之章,但仍是补前人之阙。三、概括出更切文意的主题。称“表现的是一个出外征戍服役的男子与老母在悲痛决别之后的互相思念之情。”显然,“征戍”说胜于“经商”说,其已为赵逵夫先生的严密论证所证实。四、对部分词语的训释颇有价值。如释“城上羊,下食草”句源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句。笔者愚见,此解似比类比鲍照诗句更合取证规范,因鲍诗晚于《公莫舞》。释“针缩”当作“征戍”,“平门”当作“凭门”,“五丈”为“五丈河”,“汲水”当作“淇水”,“交时还”当作“几时还”,“思君”当作“思吾”等,亦似比前人之校解为胜。不过,白先生的结论多直断所得,失引文献依据,缺少严密论证,乃大遗憾。同时从汉乐府角度而非戏剧角度体认《公莫舞》,亦憾不如杨先生得其正解。
之后,赵逵夫先生将此项研究推向了全面深入。其成果见《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1辑)和《三场歌舞剧〈公莫舞〉与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现实》(《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5期)两文。赵先生的重要贡献有六个方面。一、从理论高度探讨了歌辞、复唱、声词、语助词、表演术语、辅声提示词的特征及相互关系,字词分类更趋精细1.认为语意连贯者乃是歌辞。2.重复部分乃为复唱,复唱也是歌辞。3.声词由演员自唱而不是杨、白所说由场外人“相和”;声词是固定词组而不会是单字,杨先生以单字作声词有不确处:声词独立于歌辞之外而不像语助词粘着于歌辞之上,杨先生将二者相混乃为分类不精。4.与歌辞不相连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是舞蹈术语。5.“辅声”,“辅”为辅声提示之辞,提示场外演员据曲调和声。在此基础上,对各字词归类:“来婴”、“何婴”、“何来婴”、“吾噫邪”、“何邪”是声词”;“头巾”、“相”,“复相”、“遥”(摇)”“转”、“转轮”、“弩心”、“推排”是舞蹈术语;句末“吾”、“邪”、“以邪”、“何”、“何吾”是语助词。赵先生如上区分未必尽当,确比前贤完善许多。二、确认《公莫舞》通篇为代言体。代言体乃戏剧的标志,是否通篇代言体乃判定作品体制性质的关键。杨先生未论代言体问题,其校本仅从最后第五节歌辞中析出“母”、“子”作为角色标识以示代言,还不能作为确认该作品为歌舞剧的充分依据。赵先生则设专节讨论代言体问题,确认《公莫舞》通篇为公、姥、儿三角色对话体制,并取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的漆樽画印证之。又对该作原无角色标识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同时更正了杨先生析歌辞呼唤语“母”、“子”为角色标识字的误会。从理论上支持补证了“戏剧”说。三、通过考证《公莫舞》的历史背景,阐释歌辞,重新解说脚本内容和主题。释“茂”为“屯戌”形讹,“三年针缩”为“三年征戍”之记音,并取证歌辞,经商之别不当有死别之悲,亦不当有“三年”期限,“三年”之期当为无法抗拒之外力决定。校“三针一发”为“三正一发”,依《汉书》、《汉仪住》细论西汉兵制,施政常规,释为每次在三个够征遣年龄的人中抽调一人应征。释“马头香”为“马头杳”即码头茫远,“治五丈”指瓠子口,以考出歌辞写武帝时马邑设伏与黄河塞瓠子口前后事。由此归纳歌辞主题为:儿子因外出服役屯戌所造成的家庭离合悲欢。“大体内容是说儿要到远方去戍守3年,公(父)、姥(母)悲伤不忍分离。数年后儿子回来,母子相见,悲痛万分”。四、根据《南齐书·乐志》残篇与王僧虔《古今乐录》“伧歌以一句为一解”[2](P376),从音乐上将其分为二十解,对其音乐结构进行了划分。同时指出,本篇一解一章相合,但划分角度不同,澄清了白先生与解相混的误会。五、对《公莫舞》进行了校勘与更为科学的复原。根据剧情所表现的时间段和人物上下场情况确定为“三场歌舞剧”。六、通过文物资料,论定了《公莫舞》产生的时间下限。考证了武威磨嘴子出土的汉代漆樽画为《公莫舞》剧的写真画,又据考古界对48号墓的研究结果断定该画“至迟是西汉末期的作品”,使《公莫舞》产生年代有了可靠实证。并据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等实物说明《公莫舞》只是巾舞的一个剧目,而不是古人误解的巾舞就是《公莫舞》。赵先生的研究成果引起较大反响及争论。
最近几年,参与《公莫舞》研究的还有姚小鸥先生。他在1998年和1999年集中刊发了4篇相关文章,依发表时间和注解看,其撰写顺序当为:《〈巾舞歌辞〉校释》(《文献》1998年4期)、《公莫巾舞歌行考》(《历史研究》1998年6期)、《〈公莫舞〉与王国维中国戏剧成因外来说》(《文艺研究》1998年6期)、《〈巾舞歌辞〉与中国早期戏剧的剧本形态研究》(收入胡忌主编《戏史辨》,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篇文章主要是对杨公骥先生观点的申述与修补。一,为杨说增补新证。如,杨承逯说释“公莫”为“公姥”,姚释“公”(父亲)时举《广雅·释亲》、《战国策·魏策》、《风俗通义》文献为证;释“姥”(母亲)时举郭璞《山海经图赞》为证。杨释三个“时”字“指示歌者在‘这时’加和声”,姚举元杂剧示意“开场”的“开”,《张协状元》指示“接着唱”的“接”为旁证。杨释“转”为舞蹈术语“转身”,姚举《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沈钦韩《补注》、《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裴注》引《吴书》为证等等。二、修正杨说。如,杨校改“马头香”为“马蹄香”,说明母子分离的季节,姚从赵逵夫说改为“马头杳”,并从赵释“马头”为“码头”,增《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二年》之《胡注》为证。杨释“相头巾”为“使用头巾”,姚从叶桂桐说释“相”为乐器名,征引文献亦从叶。惜用赵、叶两说均未注明。杨释“头巾”为“今之包头巾”,赵、叶释为舞者手中所持丈余长之舞巾,姚释系于带上之佩巾等。另其校本亦对杨校本有几处修正。三、补充杨说。如,“针缩”,杨未解,姚补释为“用力以脚顿地”,“针”乃“振”之借字。“三针一发”,杨称“详不可解”,姚释为重复三次的“针缩”动作,“针”乃“针缩”之省。后三篇文章与第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
但是,在对《公莫舞》文体性质的判定上一直存在着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不是代言体的戏剧,而是乐府歌辞、单人舞。持这种观点的除白平先生外,主要是叶桂桐先生。叶先生为此专门刊发了两篇商榷性文章,一篇是交稿于1985年迟刊于1994年《文史》第三十九辑的《汉〈巾舞歌诗〉试解》,一篇是刊于《文艺研究》1999年6期的《论〈公莫舞〉非歌舞剧演出脚本——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前文是针对杨先生进行商榷,后文则主要是针对赵先生进行商榷。叶先生研究《公莫舞》走的是逯钦立先生的路子,即从考察汉魏六朝的记谱方法“声曲折”入手,并将《公莫舞》的研究与《铎舞歌诗·圣人制礼乐篇》、汉铙歌《石留曲》以及刘宋鼓吹铙歌三首等“声辞杂写”歌辞的研究同时进行。在声词分类上,将其分作记谱方法用字、行腔时用字、语气用词三大类,比逯先生的甲、乙两分法更细。在声词的具体辨析过程中,将杨先生作为角色标识的“母”与“子”二字解作声词,即语气词。认为母与子两个人物并不存在。继而,又以赵先生未从作品原文中析出角色标识字为由,否定了其公、姥、儿“三个人物”说。亦即否定了《公莫舞》的代言体性质。认为《公莫舞》是单人舞,表现“妻子思念远戍的丈夫”。很显然,叶先生判定是否代言体主要是以能否从原辞中析出角色标识字为唯一根据的,未从“一问一答,显然非一人所说”的歌辞内容本身去体认。
随着《公莫舞》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总结其成绩、回顾其研究历程的文章也应运而生。《文学遗产》1990年4期所刊张宏洪先生《〈公莫舞〉研究述评》一文,对逯钦立、杨公骥、赵逵夫三位先生的贡献作了评述。叶挂桐先生《论〈公莫舞〉非歌舞剧演出脚本》、马世年先生《对〈《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商榷〉的再商榷》(《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4期)两文中亦有简略回顾文字。《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6期所刊马先生《20世纪〈公莫舞〉研究回顾》短文,系统简明,颇具参考价值。
无庸讳言,在《公莫舞》研究过程中,近年也出现了某些偏差。有学者曾在其研究成果中对某前辈学者的观点提出过完全合乎学术规范的商榷性意见(注:参见《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1辑。),十多年后则另有学者借题刊发了两篇反批评文章,(注:参见《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3期和《学术界》2001年4期。)然其重点不在辨析哪种观点更近情理,而是“借端炒作”学术之外的东西,致使《公莫舞》研究在非学术问题上纠缠不休,影响了正常研究的深入。此种不良学风在今后的《公莫舞》研究中当引以为戒。
通过对《公莫舞》研究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已初步揭示了《公莫舞》的真貌。若要将其面目彻底廓清,还需同仁付出艰辛的努力。首先,关于文体性质的体认。存在着“歌舞剧”说和“非歌舞剧”说的分歧。在分歧中,尽管由杨公骥先生开创的从戏剧角度审视、校点作品的研究思路经赵逵夫先生的推进和姚小鸥先生的宣传,影响较大,但由逯钦立先生开辟的从乐谱和乐府歌辞角度考察、点校作品的研究思路经白平、叶桂桐先生的发扬光大,同样有不可忽视的理由。各部戏剧史对其略而不论,亦说明了“歌舞剧”说被认可的程度。同时,在确认其为“我国最早的歌舞剧演出脚本”的学者内部,对两个人物还是三个人物,五段还是三场的分歧目前也尚无统一趋势。其次,关于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存在着“征戍”、“经商”、“怀远”等说。尽管“征戍”说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但“经商”说的支持者仍不改初衷。再次,关于字词的具体阐释。虽然所有学者都完全赞同并遵循析出歌辞之外广义的“声词”以疏通原文的点校原则,但在对具体字词性质归类、意义、作用、位置的确认和研究中,不仅分歧颇大,且众说纷纭。仅从诸家校本对原文字词见仁见智的改动即可见一斑。除逯先生研究尚浅,原文大意还未疏通,故仅校改5字外,后来者皆改字颇多,杨先生校改20字,白先生校改增补30字,赵先生校改24字,叶先生校改13字,姚先生校改14字。虽各家校改之字互有交叉重复,但互不相同者人人皆有,可见认识差异之大。对同一字的意义阐释,歧见迭出,更不待举。这一切都说明,《公莫舞》的研究离认识的统一还有相当距离。
未来的研究应如何继续深入呢?笔者不揣固陋,略陈愚见。其一,联系西汉社会大背景考察作品文体性质内容。既然学界对《公莫舞》产生西汉说已无异议,系统考察西汉尤其汉武帝时期是否具备歌舞剧这种综合性艺术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文化土壤,对判定《公莫舞》的文体性质颇为重要。若能开掘出此戏剧产生的强有力实证,《公莫舞》为我国最早的戏剧演出脚本的结论将会更大程度地被认同。其内容解析也会更趋完善。这方面赵先生已发其端,颇具启示意义。其二,加强地上文字文献研究与地下出土文物研究的结合,以澄清《公莫舞》的体制和表演情况。赵先生借助对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漆樽画的研究不只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有说服力的实证,更重要的是这种“二重证据法”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门径,具有普遍意义。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认识,著名音舞史专家何昌林先生才建议叶桂桐先生研究汉代画像砖石以解决问题。这种研究十分重要,必须继续下去。进而,赵、姚两先生对此漆樽画性质判定上的差异(赵认为是《公莫舞》写真画,姚认为画面表演的是“拂舞”而非“巾舞”),又给我们以启示,即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公莫舞》的性质体制,仅靠古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受专业局限,他们对出土文物的确认难免不确,若望研究继续深入,还需舞蹈史、戏剧史、音乐史专家和考古学家等的介入。只有通力合作,各展其长,才能得出更具权威性的结论。当然,我们更期待着能有直接说明问题的文献、文物出现。其三,加强文学史家与文字学史、艺术史、民俗史等专家的跨学科合作,以推进《公莫舞》原辞阐释的深入。因其课题狭小,其研究至今仍在少数人的小圈子中进行,未能引起广泛关注和参与。但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又亟需跨学科横向联合。《公莫舞》不仅是迄今仅存的诗、乐、舞并录的两篇书面作品之一,还涉及到汉代的生活俗语等,其原辞极为复杂,唯有音韵、文字、训诂、戏剧、音乐、舞蹈、历史、民俗等各科专家共同努力,逐字甄别研究,才能作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圆通阐释,使分歧降至最低限度。其四,在未来的研究中,端正态度,改进学风亦颇为重要。《公莫舞》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着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单独彻底解决问题,因此它不是哪个门户的专利,需要众人共同参与。所有参与者的终极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争高低,因此,在共同的研究中应发扬平等切磋、互相学习的精神,既不应借商榷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更不能将学术之争演变为学术排诋。那样,将会使该项研究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不仅不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反会给研究添乱。我们相信,只要学界同仁密切合作,共襄此举,《公莫舞》的真面目被彻底廓清,是很有希望的。
收稿日期:2002-05-08
标签:文化论文; 中华文史论丛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宋书论文; 戏剧论文; 公无渡河论文; 南齐书论文; 歌舞论文; 旧唐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