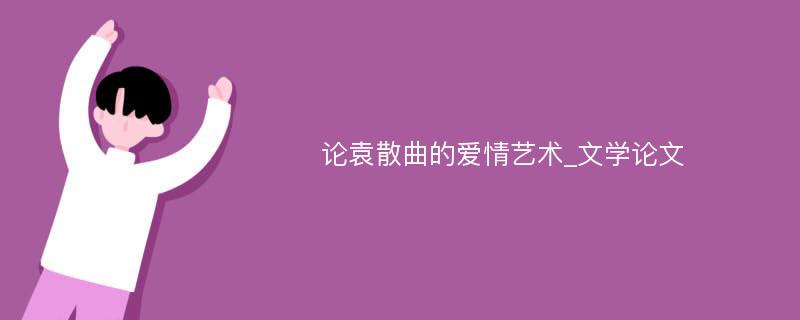
挚情率直假亦真——论元散曲的言情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曲论文,率直论文,亦真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不同体式的作品又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本文探讨了元代散曲言情的艺术特征,指出元散曲言情多采用“奔迸法”的表现方式,其突出特点是真诚,有时撒谎也是真诚的表现。并分析了这种言情艺术的特殊原因。
关键词 元散曲 言情艺术 真诚 撒谎 爱情观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1〕这一论述也基本符合元散曲的实际情况。 元散曲产生和流行在1264年—1368年之间,属于“最近八百年”之内。散曲是“歌”的一种,也是“诗”(广义)的一种。而“性爱”又确是曲家笔下的常题。
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自人类有文字以来,爱情便在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诗经》的开卷第一篇《关关睢鸠》便是情诗。爱情这一根红线,贯穿在各种式样的文学作品之中。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体式的作品,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本文专就元散曲言情艺术的特征作些粗略地探讨。
一、多采用“奔迸法”表现方式
梁启超在《中国古代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中指出,中国古代韵文的情感表现有三种方式:㈠“奔迸法”,㈡“回荡法”,㈢“含蓄蕴藉法”。(梁启超所言的“情感”,含义十分广泛,本文只就其中的“恋情”作些研究。)作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一代之文学——元曲,其言情方式是以第一法为主导,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所谓第一法——“奔迸法”,照梁启超的解释,是指“有一类感情,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遗的。”“在这个时候,含蓄蕴借,一点也用不着。”〔2〕任讷在《散曲概论》中也说:“同一话也, 词与曲之所以说者,其途径与态度亦各异。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驰,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节、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3〕诗词常以含蓄蕴藉为工, 而曲则以直露显明为特色。且看贯云石《中吕·红绣鞋》: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
——贯云石《中吕·红绣鞋》
喜又惊,笑相迎,倚湖山露华罗袖需冷。谁惯私行,怕负深盟,偷步锦香亭。寻寻觅觅风声,潜潜等等芳情。粉墙边花弄影,朱帘下月笼明。轻,吹灭短檠灯。
——张可久《越调·寒儿令·春思》
前首小令着意刻画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人聚短别长,相倚相守,怕分离而珍惜每一刻的欢爱,彻夜不眠。后首小令对偷情、幽会中的少女情态和心理,都作了极致的刻画。这个女子爱得是何等热烈而大胆!“私行”、“偷步”,这不是对封建礼教的毫不顾忌的蔑视么!同样,男子对女子的爱也是真挚而大胆的:
长江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当记得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诗,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
——贾因《中吕·醉高歌红绣鞋·寄金莺儿》
像这样歌咏男女恋情的作品,元散曲中不是个别的,其胆大直露明白而毫无蕴藉的程度,可以说为历代诗作之冠。
描写幽会如此,描写相思、闺怨也毫不逊色。比如马致远《双调·寿阳春》:
相思病,怎地医?只除是有情人调理。相偎相抱诊脉息,不服药自然圆备。
——马致远《双调·寿阳春》
害的是相思病,灵丹妙药怎地医?害的是珊瑚枕上丁香寐,害的是鸾凤被里鸳鸯会,害的是鲛绡帐里成憔悴。害的是敲才相见又别离,害的是神前共设山盟誓。
——元·无名氏《仙吕·寄生草》
此二曲把历代文人难以启齿之情如此直率大胆地道出,不用任何景物和比兴婉转之法,而是以极其通俗甚至十分口语化的语言抒发其内心之情,因此感情的流露显得直率大胆,恐怕唯元曲能如此。像无名氏的《神吕·快乐三过朝天子》也是一样:“若得我病可,除非是见他,药引子舌尖上唾。”再如徐琰的《双调·蟾宫曲·青楼十咏》等都描写得十分直率而大胆。如是诗、词作品,往往是“情感正在很强的时候,他却用很有节制的样子去表现他。……令人在极平淡之中,慢慢的领略出极渊永的情趣。”〔4〕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以水喻愁。“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通过多种景物的描写,喻愁无处不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以景物衬托愁绪,更是名句。说明诗词多是婉转、蕴藉的。
散曲不但不“节制”其情,不蕴藉其感,而惟恐其情不烈,其意不显。散曲中的情感表现越显露、越直接、越急切、越透辟、越“极情尽致”,似乎曲“味”就越浓,越能显示散曲的特性。
这种理论总结,大致符合元散曲的创作实践,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走极端,“应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奔迸法”用过了头,也就出现了一些淫词媟语、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元妓张氏的《南吕·青衲袄·偷期》、无名氏《中吕·红绣鞋》、乔吉的《仙吕·赏花时·风情》等,就不堪入目。
二、真诚,是言情作品的共同特点
读元代散曲,无数个文学形象常激动人们的心灵,虽然他们大多没有名字,但你绝对不能否定他们的存在。
元曲作家们塑造的一个个主人公,各有独树一帜的鲜明性格:有的刚强,有的温柔,有的机警,有的冲动,有的玩世不恭,有的勇猛顽强。尽管他们的性格迥然不同,但一个共同点却使我们自然地把他们联想和并列在一起。这个共同点就是真诚。
所谓“真诚”,按现在人们的解释,就是真实诚恳,诚心诚意,没有一点虚假,是虚、假的反义词。在元散曲的言情作品中,当然找不到抽象解释,但我们在那一个个具体形象中,可以强烈地体会、感受到其含义:
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
——无名氏《越调·小桃红·情》
曲中使用了“真诚”,在这里大致和曲中的“志诚”、“有情”同义。当然,“真诚”不是一般的“有情”,而是男女双方毫无保留地倾心相爱,生死不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永不变心。“真诚”,就是“解不开同心扣,摘不脱倒须钩,糖和蜜搅酥油。活摆布千条计,死安排一处休。恁两个忒风流,死共活休要放手。”(无名氏《商调·梧叶儿·题情》)在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中表现出的真诚,是内在的,深沉的,使读者对曲中主人公感到一种促膝谈心、触手可及一般的亲切。
别来宽褪缕金衣,粉悴烟憔减玉肌。泪点儿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儿才干一半儿湿。
这是王和卿的《仙吕·一半儿·题情》。读者不知道曲中的女主人公是谁(这无关紧要),但她那因思念心上人而日惭憔悴的面容,那因伤离别而日渐消瘦的身影,不是活脱脱地站立在读者面前吗?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读者心灵的圣殿中,这个泪流满面的思妇形象,一定占据着一席地位。
她是真诚的,没有半点虚假。因为她的流泪,她的消瘦,她的悲伤,她的痛苦不是有意做给任何人看的,“泪点儿只除衫袖知”。在外的情人不知,也不能让家里人知。真诚思念的痛苦化作无穷的泪水,滚到衣衫上,只有衫袖才是自己的知己。马致远的《双调·寿阳曲》(有十多首言情的作品)、白朴的《中吕·阳春曲·题情》、关汉卿的《仙吕·山坡羊·闺思》等都是这一类型的作品。在元散曲中,此类作品有相当多的数量,实在难以罗列。
对真情实意的赞扬和歌颂,另一面就是对虚情假意的批判和鞭挞,这也是“真诚”表达的一种方式。
锦绣围,翠红堆,当初有心直到底。双宿双飞,无是无非,不许外人知。眼睁睁指甚为题,意悬悬为你著迷。有情窥宋玉,没兴撞王魁。呸!骂你个负心贼。
——张可久《越调·寨儿令·闺怨》
无须咀嚼,曲中女主人公认真率直的个性便跃然纸上,无须寻绎,她那火炽的感情已从字里行间洋溢而出。心里纵然情如火炽,但是多情反被无情弃,其怨其恨,可想而知。诚挚真切的爱恋、缠绵幽怨、“有心直到底”的密约深盟、“双宿双飞”的美好愿望、“无是无非”的幸福憧憬,最后因“撞王魁”而化成一句话:“呸!骂你个负心贼。”王魁是典型的负心汉的形象。他未达时受桂英资助,与桂英盟誓不相负,后王魁得中高官,转娶崔氏女。桂英自刎,化为鬼魂,迫死王魁。这里女主人公把无情无义的负心汉比作王魁,正是包含着对薄情寡义之人的批评与否定,对无情无义之人的控诉与鞭挞,对虚情假义之人的宣判与惩罚。
对负心人批判谴责最为严厉的大概要算元人的另一支小令了:
鸳帐里,梦初回,见狞神几尊恶象仪。手执金槌,鬼使跟随,打着面独脚皂纛旗,犯由牌写得精细。疋先里拿下王魁,省会了陈殿直,李勉那斯也听着:奉帝敕来斩你伙负心贼。
——无名氏《寨儿令·恨负心贼》
这里以梦境的形式,对弄虚作假的负心人进行报仇泄恨。女主人公对负心人是恨之入骨的,她希望:负心贼不仅不得好死,就是死了以后,其灵魂也要受到审判,受到制裁!永远不得超生,叫他世世代代轮番做牛做马。当然,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里,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是不可能实现自己愿望的,所以这里只能通过梦境来达到目的,借上帝的正义之剑,来扫荡人间的所有负心贼。
卢挚的《双调·蟾宫曲·咏别》写一女子受骗上当,觉醒后发出悲叹:“劣心肠作弄难拿。到了偏咱,到底亏他,不信情杂,忘了人那。”侯克中的套曲《黄钟·醒花阴》有十三支小令叙述一女子对虚情假义之人的怨恨,当她无力改变这一骗局时,只好借助神明来实现她对负心人的惩罚:“瞒不过天地神明,说来的咒誓终朝应,亏心神鬼还灵圣。”周天质的《越调·寨儿令》写出了女主人公发现自己受骗之后的怨愤和决绝,她认清了对方是“假题情绝句诗,虚写恨断肠词”,其决裂是异常果断的:“嗤!都扯做纸条儿!”那些虚假绝句诗、断肠词连同男子的虚情假意都在这“嗤”的一声中被撕成碎片。王和卿的套数《大石调·暮山溪·闺题》,写一个男子深夜醉酒归家,等候已久的妻子怒火中烧,于是对丈夫又逼问,又打骂:“问着时节只办的摆手,骂着时节永不开口,我将你耳朵儿揪。你可也共谁人两个欢偶?我将你锦片也似前程,花朵儿身躯,遥望着梅梢上月牙儿咒。”这里的“问”、“骂”、“揪”、“咒”等一系列动作,是女主人公愤怒的发泄。她愤怒的原因只有一个:怀疑丈夫“共谁人两个欢偶”,也就是怀疑男人的“真诚”。好在她只是怀疑,证据不充分,所以惩罚不重,只揪耳朵,没有判处死刑。可见在感情问题上,人们是不允许对“真诚”有半点折扣,来不得半点含糊。用元人的话说,就是“山盟共设,不许暂时少撇,若有个负心的教他随灯儿便灭”(无名氏《双调·珍珠马·情》)。
真诚,作为一种个人的道德力量和道德情感,它是具有那种品质的人对自己内心状态的一种体验和反省。真诚,它好比是人内心深处潜藏的火种,在平时,它只是静悄悄地蕴含着,然而,在黑暗、空虚、彷徨的时刻,在遭受巨大打击而深感痛苦的时刻,它却会情不自禁地猛烈燃烧起来,给人以勇气、力量和光明,使人不畏逆境,勇往直前,直至焚毁自己的生命。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中的女主人公窦娥,就是最光辉的典范。流氓泼皮的哄吓诈骗,贪官酷吏的严刑拷打,整个黑暗势力的强大压力,都丝毫不能挫折她的真诚。
在散曲作品中,因篇幅的限制,一般很难表现曲折复杂的情节,不可能反映人生的过程,只能表现生活的某一个片断,思想波澜的某一朵浪花。因此散曲作品很难塑造窦娥那样的形象。但是仍然可以窥探到艺术形象的真诚品质。“我共你,莫相离,肉铁索更粘如胶共漆。系着眉毛,结着鬀髻,硬顶着头皮,熬一个心先退”(曾瑞《中吕·迎仙客·风情》)。这里除了对爱情如醉如痴的憧憬、如火如荼的燃烧之外,什么都不复存在,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其真诚是感人肺腑的。
王国维说:“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5〕其实不止诗词,散曲何尝不是如此? 这些脍炙人口、盛传不衰的散曲作品,除了表现技巧的独特以外,不正是其中饱含离愁别恨之苦吗?不正是抒发社会黑暗、男尊女卑的不平之声吗?
三、撒谎也可能是情感真诚的表现
真诚,并不止是指通常意义上的“不撒谎”。通常说的“不撒谎”,往往只表现了一种低层次的道德力量上的真诚,是一种幼稚、天真的真诚,是一种单纯的真诚,这些当然是可爱的,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可惜现实生活并不那么单纯,也并非十分美好,因此,撒谎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这里且不说敌对斗争的“瞒天过海”,或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不说医生为控制病人情绪的波动而对病人隐瞒病情,就是在情感活动中,撒谎也是常见的现象。比如恋爱中的情人,如果一方得知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为不连累对方,往往不明说病情,而谎说不再爱对方而断绝关系。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当沙威追捕冉阿让时,散普丽斯姆姆“一连两次,一句接着一句,毫不踌躇,直截了当地说着假话,把她自己忘了似的”,掩护了冉阿让。小说中的散普丽斯姆姆是一个以诚实著称的人物,但她此时撒谎,读者只会赞叹她的聪明机智、泰然自若,谁会对她有半点谴责呢?因为她的撒谎,是出于一种高尚的责任和动机。
在元散曲中,此类作品也不乏其例。关汉卿的《仙吕·一半儿·题情》(共四首)有这样一支: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女主人公对情人的求爱举动,在语言上有“骂”有“嗔”,在行动上又加以“推辞”。但是,她骂了之后紧接着就是“回转身”;“嗔”的前面还用了个带有转折意义的连词“虽”,说明“嗔”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而心里是愿意、喜欢、爱恋;“推辞”也只是“一半”,另一半是“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定:“骂”、“嗔”、“推辞”是假,说的是谎话,做的是虚伪;“肯”才是真,心里面是爱恋,骨子里是真情实意。女主人公“推辞”与“肯”的矛盾心理,表里不一的复杂感情,一方面是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那种封建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考验情人是否“真诚”的一种方法,是维护永久真诚的一种措施。试想: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见面就结交的男女,那种不动心、不动情的苟合,与牲畜的行为又有多大差别?又有什么“爱情”可言?因此,这里的撒谎作假,也是“真诚”的表现,甚至是更深切的表现。从散曲艺术角度说,女主人公的矛盾动作与复杂心理,把一个女子对爱情的真诚执着,心潮的波动起伏,仅只在37个字的小令中,就有层次地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最大程度的丰富了散曲作品的表现力,增强了作品感人的艺术力量。
歌妓真氏写有一首小令[仙吕·解三酲]:
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那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
很明显,这里的“娇模样”是女主人公“乔做作”出来的,是假,是外表,是生活环境逼出来的,假模假样当然没有什么“真诚”可言。实际上她是痛苦的,所以她才有“泪千行”。而这种痛苦偏又不能公开,是“背地里”的,这就更增添了痛苦的份量;本是痛苦的心情,却偏被逼着在人前强颜欢笑,又使痛苦的份量翻了一番。但是,我们在她那“乔做作”的假模假样的形象中,分明感觉到她的真诚。这种真诚,就是她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就是她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因此可以说,她的痛苦越深,她的真诚就显露得越充分。在这里,作假(“娇做作”)、痛苦、真诚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作假=痛苦=真诚
进一步说:三者之间又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作假越逼真,包含的痛苦就越深沉,表现的真诚就充分。如果上列公式可以成立,那么就可得出:作假(“娇做作”)=真诚。
类似的散曲还有不少。“骂玉郎有上梢没末尾。……捱这等相思会”(王仲元套数《中吕·粉蝶儿·集曲名题秋怨》)。“做意儿将人不采。”(吕止庵《越调·天净沙·为董针姑作》)。“眉尖上眼挫侧,先留下几分恩爱,怕人知得地佯不采”(无名氏套数《双调·夜行船·忆所见》)。“羞,见人推病酒”(徐再思《南吕·阅金经·闺情》)。“粉郎前,一半儿支吾一半儿软”(查德卿《仙吕·一半儿·拟美人八咏·春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撒谎作假=真诚”这一公式。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撒谎作假=真诚”这个公式绝不能乱套滥用,它只能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有条件地成立,即使在“言情”的活动中也是一样。一方(不论男女)向另一方声称是出自善良动机而撒谎作假,这还不能肯定具有“真诚”,只有当他(或她)把这种善良动机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时,才能确定他(或她)的“真诚”,这公式才能成立。当然,这种判断只能由后人(或旁人)去作,当事人是难以表白的。因为她(或他)并不能把自己的撒谎作假告诉对方,擢穿了的谎言当然不成其为谎言,而且也不符合生活逻辑。
四、言情散曲中的爱情观
元散曲描写纯洁忠贞的爱情和对婚姻自由追求的言情之作是相当多的。即使是一些卓有建树的大家,也不能免俗,写了不少男女情事的作品。
我们读元散曲中的言情作品,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元人的爱情是那样的直率,那样的坦露!是那样的粗犷,那样的热烈!又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纯洁!
我为你吃娘打骂,你为我弃业抛家。我为你胭脂不曾搽,你为我休了媳妇,我为你剪了头发。咱两个一般的憔悴煞。
——无名氏《中吕·红绣鞋》
这里除了爱,就只有情,其它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都可以弃而不顾。真是爱得真切,爱得纯洁,爱得死去活来。
那么,元代青年男女相爱是否有标准或条件呢?还是用元人的散曲来回答:
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
——兰楚芳《南吕·四块玉·风情》
历来世俗的婚姻匹配标准(特别是文学作品中张扬的理想匹配标准)是郎才女貌,或才子佳人,或政治、经济方面的门当户对,这里却一样都不具备,双方都是缺项。他们所具有的一个是“心儿真”,一个是“情儿厚”。他们相爱的唯一的标准就是“意相投”。这便是主人公爱的宣言,爱的追求。有了这种心心相印,有了这种意气相投,才会有真心和谐美满的姻缘,才能化“丑”为美,化“村”为善,使爱情得到升华,也就有了更高层次的美。这大概是作者敢于高举反叛世俗观念的旗帜,把“丑”、“村”加以炫耀的原因吧。
再看无名氏的《中吕·普天乐·失题》:
他生的脸儿峥,庞儿正。诸余里耍俏,所事里聪明。忒可憎,没薄幸。行里坐里茶里饭里相随定,恰便似纸幡儿引了人魂灵。想那个滋滋味味,风风韵韵,老老成成。
前一首是男人眼里的女人,此一首是女人眼里的男人。此女主人公的标准似乎比前首中男主人公的标准要高一些,条件也似乎多一些,涉及到外貌(“脸峥”、“庞正”、“风韵”)、内才(“聪明”)和品质(“老成”)。但仔细品味,和前首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她并没有提及男人的地位和钱财,强调的还是相亲相爱,强调的是“没薄幸”,强调的是不仅行动上的“相随定”,而且精神、思想、魂灵、情感上也要相一致,不能有半点差异。因此,这里突出的还是一个“爱”字。
我们虽不能说元人的爱情观一概如此,但此两首散曲确有极大的代表性,至少在散曲作品中是如此,这在前三节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这种求“爱”重“情”的纯洁的爱情观。就是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是相当进步的。言情散曲中所反映的爱情观及以这种观念创作的言情作品,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即使在那样黑暗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也并不全是冷漠无情、尔虞我诈的,心灵与心灵之间,也还有用真诚架设的桥梁,交流着真挚地情感;心灵与心灵的撞击,飞溅出爱的火花。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爱抚,正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润滑剂,所以,读这类作品,特别容易动情。通过研究言情散曲,我们可以感到蕴藏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中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问题是,元散曲中反映的爱情观符不符合元代的实际?或者说,那种观念指导下的爱情能不能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 ”〔6〕恩格斯根据其共产主义的理论推断:只有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社会里,才会有“现代的性爱”。在“金钱”社会,黄灿灿的金钱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也可以使“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在消灭私有制之后才能普遍地实现“现代的性爱”,“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7〕
恩格斯的论断是无可辩驳的。元人纯洁的爱情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爱情观也是超时代的。本文第一节录贾固的《红绣鞋》,其对爱情的忠贞执着,一往情深,确实感人至深。但据《青楼集》记载:贾固(字伯坚)任山东佥宪时,属意于歌妓金莺儿,二人情意缠绵。后调任西台御史,无日不思念情人,于是作此小令寄赠之。正因为此小令而被弹劾罢官,后不知所终。贾固与金莺儿之间的爱情是不庸置疑的,而最终不能实现也是现实。
真正的爱情难以如愿,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黑暗社会的,有封建家庭的,有礼教思想的,加上“薄幸”的“情人”也屡见不鲜。正因为这样,爱情的夭折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倾诉相思之苦、谴责对方薄幸的言情散曲数量相当多。
既然纯洁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实现,曲家们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歌颂纯情的男女、留下那么多言情散曲呢?我认为原因有五:
一是歌咏爱情是人们的理想追求和对幸福的憧憬。曲家们同作梦的人一样,常设计出一个理想、虚构的世界,建立乌托邦、乐园及天国。它代表曲家们愿望的实现,或者记录了无法实现愿望的哀叹。这虚构的世界由曲家们过去心灵生活的残屑所构成,再加上最近事件或心像的润饰。这是文学创作中常有的现象。
二是歌咏美好爱情是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否定。言情散曲特别是那些描写爱情毁灭后倾诉相思之苦的哀伤、怨恨之作,往往是和揭露世情险恶结合在一起的,其社会意义,当然也就远远超出爱情本身了。
三是曲家们才华的发泄。钟嗣成把元代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类是“读万卷书,作三场文,上取巍科,首登黄甲者”。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是极少数,因为元代大半时间不兴科举。二类是“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即隐居。三类是“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素为戏玩者”。〔8〕这一类就是杂剧与散曲作者。他们流落勾栏瓦肆,“向烟花中儿上走”,与歌儿妓女交结其密,在人身自由和爱情自由都谈不上的情况下,很多曲家却在青楼之中找到短暂的真正的爱情。这样,他们一方面有才华而无处使,另一方面勾栏瓦肆青楼妓院的生活提供了创作的素材,燃起了创作的冲动,找到了施展才华的突破口,于是,言情之作大量涌现。元散曲中的言情之作,也主要由这一类知识分子所为。
四是元代入籍的市井妓女——市妓的大量增加。据夏庭芝《青楼集志》载:“我朝(指元代)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可见元代市妓兴旺发达之盛况。他们活跃于瓦舍勾栏、酒馆妓院之间,以色相侍人,以歌舞侑酒,以演唱挣钱。其中不乏色艺兼优的杂剧演员、歌星、舞星、诗人。她们表演的杂剧和歌唱的散曲就是受时人的激赏的艺术形式。她们的生活需要社会的承认,渴望时人的欣赏,更需要文人的理解和支持,为她们的演唱提供脚本和歌词。这样,一大批文人就走进了她们的生活,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亲密无间的情感,并且相互以散曲形式赠答唱和。言情散曲的繁荣,也就理所当然了。
五是元蒙统治者原来生活在边远塞地,性爱观念原本比较自由,较少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入主中原后,礼教思想统治相对宋代要宽松一些,文人创作较少限制,这也是言情散曲得以增多的原因之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0卷229页
〔2〕〔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三十八《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3〕《散曲概论》
〔5〕《人间词话·删稿》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第90页。
〔7〕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8页。
〔8〕元·钟嗣成《录鬼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