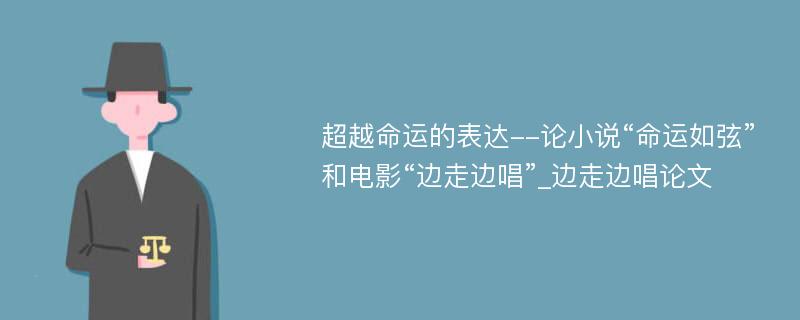
超越宿命的表达——关于小说《命若琴弦》和电影《边走边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琴弦论文,边走边论文,宿命论文,电影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有着特别情感担当的作家,他的特殊经历使他比常人更能体会人生的悲剧感、存在感和命运的残酷,在他平静的文字之下,我们感到的是顽强的生命气息和非常人的自我超越,并且他的文字没有丝毫的焦虑和错位感地表达出存在的景观。陈凯歌是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中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影片饱含对人文精神的自觉追求以及文以载道的使命感,他的自省精神和忧患意识使他的影片呈现出浓厚的哲思品格。史铁生和陈凯歌同属一代,在同样的社会大动荡的激流中走过,经历了历史的冷调幽默,承受了命运的考验与锤炼,他们身上有着当下青年所无法体会的深重、诚挚、复杂的感情,他们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信念的坚守在本质上是同源的,这种对人生的观照与思考在当下变得弥足珍贵。这里,将这两位不同领域的大家联系起来的介质,源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和陈凯歌在1991年由此改编的影片《边走边唱》。我们发现,陈凯歌在影片中的镜语表现并未忠实于原著,他在拍摄中摒弃了文学的影像化复制从而对故事本身进行了再创作,影片只是借用了小说的故事框架,并以强烈的主观意图对原著进行改编,显然,导演本人对于意义和理念的追求远远大于影片形象或故事的本身,对于视觉造型的强化和物象象征的指认也使得影片的内蕴超过了故事的讲述,他用电影特有的光影声画语言颂扬着如歌的生命,以“人心”为本位,对人性进行深刻的解析,对人在命运面前的抗争与无奈进行了智性的思考。我们感到,这两个不同体式的艺术文本似乎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美学趣味和哲学品质,他们都本然地调动自己的艺术元素和表现手段,努力探究生命与存在及其终极理想与价值。
作家史铁生在《命若琴弦》中为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盲歌手的师父为他留下一张可以让其重见光明的药方,前提是要以弹断一千根琴弦作为药引,然而“千弦断”后,盲歌手不但没有实现“一辈子的愿望”,还被告知这张他守护了一生的药方不过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这使得盲歌手陷入绝望和荒诞的深渊,但是盲歌手并没有被虚无与绝望彻底击垮,归于平静之后,他彻悟了虚设目的的重要性,带着徒弟重新回归“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生活。史铁生通过盲歌手的命运遭际揭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困境和宿命。导演陈凯歌在呈现《边走边唱》的时候,盲歌手已成为深受尊重的“神神”,电影不但展现了他的内心冲突和矛盾的煎熬,更加重了盲歌手徒弟石头的分量,影片在神神与石头的矛盾和冲突中进一步展现了人类情感的波动和欲望的压抑,形成了影片特有的张力,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命运面前的双重选择及其可能性。
小说《命若琴弦》讲述了人的奋斗的过程与失落的悲哀,命运的沉浮,旨在揭示人生的复杂内涵,然而小说的主题绝对不仅仅是关于目的和过程的随机解说,史铁生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出人生的寓言:命运在人的能力和欲望之间投注了一个永恒的距离,怎样使人在这种无法超越中获得超越,在绝境中获得自救才是他真正的关注点。在这里,史铁生的解决办法是让处于绝境状态中的人发生生存欲望的转移。当盲歌手领悟到他所付出的努力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他在命运的悬崖边回撤了一步,并且为自己寻到了一个新的生存目的——为徒弟的生命给予新的重量,前提是让徒弟永远也不知道希望只是一纸空白。史铁生的理智在于他承认虚无,肯定虚无的价值,他以虚无为背景,却又智慧地超越了虚无,他表达出人在荒诞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可以也完全有能力通过抗争荒诞来获取生存的意义。作家显然对这种抗争深信不疑,他在一吞一吐中触及了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拷问,对目的的诱惑和过程的美妙进行了新的梳理,他用这种自为的救赎方式欣赏着抗争过程的美好与壮观,凸显着个体生命在遭际命运的毁灭性打击后仍具有的伟大与顽强,同时,也体现出“西绪弗斯神话”中推石人的气度。
陈凯歌的电影《边走边唱》,同样涉及到人与命运的关系以及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导演有意模糊了故事发生的年代,故意呈现一种亘古、蛮荒的气氛,以此营构影片的寓言氛围和情境。影片中的神神已不再是小说中浪迹天涯的民间歌手,盲歌手出入乡村的朴素故事,平民性的动作和身份也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陈凯歌对其哲人化和理想化的艺术处理,“人”与“神”的双重身份亦使他比小说中的盲歌手更加丰富。作为人的一面:他在自己对于欲望的付出与欲望能否实现中反复的自问自省,对自己的行为有着强烈的质疑;他极力的想“看一眼”世界的本来面目以体味作为正常人的快乐;他对石头和兰秀的爱情以自己的价值尺度进行野蛮干涉,行使着父权。作为神:他的歌声又让人屏气凝息;他像一个布道者一般被人簇拥跟随;他在广阔的空间内用琴声训导众生,用“人之歌”阻止村民的荒蛮械斗,他奇迹般的唤醒众生并使他个人对于光明的追寻转换成整个族群的追求,他的歌声使整个族群的身心得到了洗礼和超脱,鸟群在天空中人字形的排列完美地展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他具有了盲人本身所不具备的异乎寻常的神性,陈凯歌式的理想主义在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中的盲歌手在希望落空之后正视了自己是瞎子这一无法更改的命运,在心弦绷断之后仍然坚韧地选择了生活,命运的玩笑虽然让他身心疲惫,却没有将他彻底击垮,他仍旧和徒弟行走在路上,他身上传达出的是无奈之后的一种大勇与大智。影片中神神的结局比起盲歌手多少有些悲哀,同样发现了那张无字的白纸,盲歌手选择让自己继续走下去,神神却很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神神在“看一眼”的欲望驱使下,对不可能发生的一切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他仿佛就是追日的夸父,五百年的追求也难逃渴死海边的命运,他对空白所带给自己的绝望,唯一能做的是砸碎了先师的墓碑,他所表现的是被骗后的愤恨,这一无力的反抗显然毫无意义可言。当神神再次面临村民的械斗时,他已无力弹唱“人之歌”,他拣起脚下的石头投向村民的械斗,这一刻,他神性尽失,成为野蛮械斗的一分子。此时,一个表面被奉为“神神”的盲人,实质上却是作为命运的受难体出现的,他对于整个族群神智的启迪无疑具有极大的反讽性。悲剧之后,老人仍旧在族群的围绕中高歌,歌声中透露出他对于自身神性消解的认知,表达出对于光明世界的神往。老人的歌声中还暗含着人的“心盲”,一个族群的盲,实际上指出无论怎样人都看不见人生的真谛。这使得老人在神性与人性中不断摇摆,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陈凯歌经常把老人放在自然景观与人物的比例超常失衡的画面中,使得他在庞大的背景中显得孤立无援,老人最终在失落、绝望中死去:他被安置于一叶小舟之上,以一袭白衣,在流水中回归黄河。死亡是他必须的归宿,亦是他最好的解脱,正如兰秀所说:“死是换个地方更好的活着”。
具体地讲,影片中石头这一代歌者的精神分量远远重于小说中的小瞎子,他是导演重笔描摹的人物,如果说师父的追求是对于神性、对于终极目的的追求,那么石头的身上表现出更为真实的人性化选择,陈凯歌在石头身上完成了人性对神性的颠覆,展现了神性到人性的回归。小说中的小瞎子是钟情于“电匣子”那个未知世界中的对一切都充满新鲜感的年轻人,“电匣子”里的声音成就了小瞎子对世界的全部想象和延伸,他的问题也仅限于“什么是绿色的长椅?”、“什么是曲折的游廊?”,以小瞎子的能力和阅历,他所思考的问题也只能是这样具象的,小说中的小瞎子虽然看不见世界,但比起电影中的石头,他无疑是获得了有限幸福的一个。影片中的石头被导演加入了太多的东西,石头在影片开始的发问就几乎触及到终极概念,“什么是蔚蓝色的大海?”“空白是白的吗?”“什么是天上的星星?”一个个问题有如天问,这绝不是石头这样一个少年所能应对的,其中无疑透露着导演个人执拗的存在性人文追求。影片中的石头绝不是小说中那个师父的忠实追随者,他对于师父的关爱大于对师父信仰选择的尊敬,他对于师父的了解也大大超过师父对他的了解,从本质上说,石头是作为师父——上一代价值观的对立体出现的。石头的言行和选择不断地怀疑着师父所信奉的一切,与其说他是师父人生信条的传承者,不如说他是师父人生信条的控诉人。他在大吼“空白怎么是白的呢!”这一刻起,就注定了他选择了与师父别样的道路。石头从未想过要弹断一千根琴弦,他对兰秀说:“我不一样,弹断多少是多少”,这表明石头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药方充满了不信任;在师父让他远离兰秀的时候,他说:“师父,你哄自己哩,琴不是女人哩”;在师父怒斥他跟兰秀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你馋了……我说你馋了”;在师父兴致勃勃地拿起药方去抓药的时候,他又这样说:“琴弦是被太阳晒断的……晒断地和弹断的一样”。陈凯歌曾说“人,能够超越环境的人叫做圣人,不能超越环境的人是凡人”。[1] (P205)就这一点来看,石头没有迷失在对于空白药方的纯粹追求中,而是确立了自己命运的走向,尊重自己的本能,他的选择不同于师父对于终极目标的追寻,他所认定的路就在脚下,“边走边唱”的幸福恰恰是在这个少年身上体现出来的,石头才是陈凯歌真正设置的启蒙者。
还有一点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边走边唱》对于情爱的描摹也更加彻骨。小说中的兰秀因为被小瞎子的“电匣子”吸引,而主动与他靠近,在同样对“电匣子”里的世界产生好奇的同时渐渐与小瞎子产生单纯的情感,兰秀的出嫁只是更加激发了小瞎子想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欲望。影片中石头的爱欲比起小瞎子的爱情要更为辛酸,他和兰秀的爱欲几乎成为他生命的另一个支点,石头心中,有爱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睁眼看世界只能算是他心目中幸福的一部分。石头爱上的兰秀是一个敢爱敢恨、性格刚烈的少女,面对父亲的强势她可以选择不嫁给石头。但也不会让外来的压力在自己身上得逞,她选择的方式是非常极端和彻底的——用自己的死亡来抗拒妥协。兰秀留给石头深深一吻,然后纵身跳下悬崖,这一刻也是石头的至爱理想幻为泡影的一刻,兰秀的死也让石头陷入了生的绝境。某种程度上,石头成了和师父一样的可怜人。这里,师父和兰秀的死使得石头身上的两个生命支点全部坍塌,石头在这种境况下对于自己人生的认知异常的冷静与清醒,他拒绝成为新的神神,拒绝成为族群中新的神性代言,同时也抛弃了师父所传递的宿命,在石头身上,到底是对命运进行抗争还是臣服都显得过于奢侈,他的路就在脚下,他的生命价值在于边走边唱,因此他选择了肃然离去。
影片结束于蝴蝶风筝在空中的飘飞,这无疑是导演留给观者的希望,这标志着新一代的歌者已经决定不再重复过去,而是选择重新上路。然而这放飞的风筝终究是纸扎成的蝴蝶,在如此浩大的天空中它的力量有多大,它又能随风飘多远,这种放飞与其说是一种解脱,不如说是另一种困惑的开始,风筝放飞的一刻,我们陷入了真正的沉默,因为谁也无法为一只纸风筝的命运作出完满的解答,这脱离了束缚的纸蝴蝶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是值得人们怀疑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史铁生和陈凯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和艺术表达的可能性,寻找和呈现人的抒情诗般的内核,他的隐形的或裸露的真实,他的可见的以及无所知的命运的奥秘。
史铁生的小说从向人们反复传递切身体验渐渐过渡到行而上的思考与探究,这种精神视域的扩展让他的《命若琴弦》呈现出清朗、温馨、内敛、豁达的气韵。在《命若琴弦》中,无论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师徒关系的展现都透射出一种朴素的、醇厚的、达观的情致,字里行间都有一股温情、简素蕴含其中。对于注定失败的命运所作出的抗争被他处理的如此简单、美妙,流畅的叙述中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忧伤。《边走边唱》唱出的则是一首基调沉重、情感浓烈的人性哀歌,“只要扫一眼,就让人能感到这是一部意义深远、教训丰富、气度雄浑而手法庄重的影片”。[2] (P152)影片远没有史铁生笔下大彻大悟之后的平静,更找不到那种尘埃落定后的安然与沉寂,小说中所透露的清虚与温爱全部被陈凯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打破。陈凯歌没有以故事情节作为结构影片的主线,他把创作重心偏向于影像之外的哲理表达,在电影《黄土地》之后的创作惯性使他依然钟情于黄土高原的景象和奇美的空间表现,并突出了影调、造型、音响的运用,力求一种博大的气势与奇诡的视觉冲击力,这种追求在影片中随处可见,比如影片初始的镜头,蓝色顶光从画面上方直射而下,到画面底部渐渐过滤成黑色,长长的帷幔飘荡在云层起伏的画面中,道具化的摆设和飘进画面的铃铛声使得师爷的死宛若神仙的飞升,在这样一个鸿蒙初始、天地渐开的时空中师父接收到指导其毕生命运的一纸药方。这里舞台效果般的精心设计和具象的繁复运用更加了强化了象征与寓言的启蒙效果。
在表现影片的史诗色彩和寓言基调的同时,除了采用自然景观与人物的失常比例以表现人物内心的压抑与冲突外,还吸收了一些后现代的笔法来制造诡异的气氛。比如在黄河渡口的面铺中,陈凯歌设立的人物形象就颇为匠心,老板娘被过分的虚化,她仅仅是盲歌手寄托情欲的一个符码;形如罗汉的老板形象就更加模糊与神秘;面铺的伙计总是发出令人悚然的声音。还有陈凯歌所钟情的仪式化表演:黄河渡口边众人对于师父和石头的簇拥,沙漠中少女们对师父表示欢迎的方式,师父每次宛如在圣坛中的吟唱。具体物象也在影片中纷繁出现,浩远的沙漠、壮美的戈壁、怒吼的黄河、奇诡的渡口、风化的鱼骨、燃烧的火把等等,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元素是小说所不具备的,也只有电影才能给人这样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就视效来讲,“影像的意旨系统更易于解读”[3] (P333),也可以“出其不意地使话语得到了一个情境”[3] (P334),这一点,文字在表述上可能不及画面来得直观,然而,文字的间隙所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却不是影像画面能够填充完整的,文字本身所蕴含的张力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别样体验也是电影难以企及的。
陈凯歌堪称中国电影界的“银幕诗人”,显然,他试图在《边走边唱》中为今人的精神枯井注入一汪清水,可以说这部影片是陈凯歌保持个人诗情风格及其创作理想所做的一次悲壮的努力,他曾说“我们现在对物质的狂热追求表现在精神上的负增长——精神的贫乏、茫然和无所求……对于我们国家文化上的这种严重危机,我是非常忧虑的”。[4] (P176)这里,我们像对史铁生一样,对他的结构能力和精神气度深信不疑。然而,其创作意图却受到读者的误解,影片中的镜像传达方式也很少被人体悟,这一点上,陈凯歌更像是影片中的盲歌手,有时肯定自己“神神”的身份,坚守自己的终极目标,舍弃一切凡尘俗世的纠葛,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有时又不断地对自己的信念进行怀疑、生出悬浮和游离,这使得他在执着艺术的过程中获得外界肯定的同时,又无法排遣内心的苦闷,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呈现在他的电影中就使得影片的表意系统略显紊乱,应该说这种混乱是文化转型期所有复杂性的必然表现,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甚至不是由他个人所决定的。陈凯歌标明将这部影片献给母亲,这种近乎成人礼的献祭本身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子代对于母体的告别,同时也暗示着子代人踏上新的征程,迎接别样的选择,途中,答案在哪儿并不重要,行走与寻找本身才是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