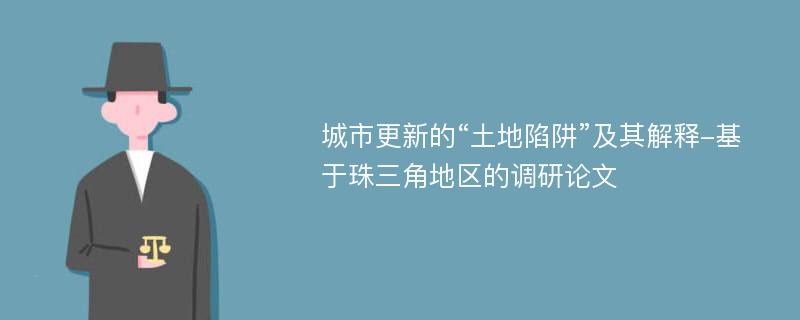
·公共管理 ·
城市更新的 “土地陷阱 ”及其解释
——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研
刘 超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基于珠三角地区的调研,城市更新面临细碎化地权与统一规划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经济成本与交易成本双高的难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乡村特殊工业化路径中形成了制度化的土地利益群体对于国家权力在土地开发与空间规划上的阻碍。一方面,在“三来一补”的工业化路径中,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成为该地区通行做法,造就了大量的土地利益;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巨大收益分配不均衡和监管难的困境,地方政府开始了以股权量化与政经分离为主要内容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在法律制度意义上强化了这一群体,形成了“团体—共有”式的集体产权秩序。现行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改变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由此疏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带来基层治理的困境。
关键词 :城市更新;土地陷阱;土地利益群体;产权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1978—2017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7.8%快速上升到58.52%,年均提高约1.4个百分点[1]。当城市增长主义逐步走向终结,城市发展也转向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存量开发。城市更新是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核心内容是对城市中老旧或衰落区域进行拆迁改造的再开发和再建设,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的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由于各大城市普遍存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问题,社会各界对土地资源短缺认识逐渐提高,城市发展逐渐从“增量扩张”转型为“存量优化”[2],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合理有效利用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
(一)城市更新的困境研究
已有的城市更新的困境研究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行土地制度不正当论。这种观点认为,城市更新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是因为土地发展权集中在政府手中,侵蚀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具有社会公正性,城市更新陷入了土地合法性困境,主张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这些学者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认为应将那些在历史中形成的违法建筑纳入合法框架,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扩大农民收益[3],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是解决现有的小产权房现象的关键[4]。二是利益博弈论。城市更新困境的实质是国家权力介入集体土地产权利益分配,形成国家和集体之间的产权博弈[5];空间资源错配,开发主体和土地权利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局部高强度开发共同导致困境[6]。因此,主张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出发,建立合理的、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因此,需要在土地资源配置和土地利益格局重构间找到根本平衡,重新整合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模式,借助于市场化途径,通过利益博弈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打造利益共同体模式[7]。
法律不正当论认识到了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对于城市化的影响,但却将历史遗留问题当作反对现行城市更新政策的主张。殊不知,恰恰是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为主要特征的农民自主城市化模式带来了如今城市更新所面临的困境[8],而通过征地制度完成土地城市化实现了土地“涨价归公”,符合宪法秩序[9]。利益博弈论则是在遵从现状合理的情况下,认识到了巨大土地利益分配带来的困境,但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作为一个技术问题,强调借助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回避了现行的土地制度的合法性安排及土地利益群体的特征。更为关键的是,以上研究的理论共识是保障特殊地区的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权利,其核心目标是保护这些地区农民的利益。但是二者并没有关注到城市更新面临的深刻经济社会背景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制度困境,反而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政策安排上升为全国性的安排。这就需要重新回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理解现阶段复杂的利益构成来源,进一步解释地方性土地制度形成的政治经济根源及其背后折射的公共政策执行的困境。
(二)研究路径
在珠三角地区,由于乡村工业发展和城市不断扩张,城市和农村边界日益模糊,大量工商业建立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由此,珠三角形成的土地利用结构特征表现为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为大量“城中村”所切割,或者为大量农村包围,又有“村中城”的说法,“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目前,土地开发需要更高规模的统筹以便合理优化配置紧缺资源,但是土地掌握在分散的村集体手中,实现土地再次开发的成本巨大。因此,珠三角核心地区的城市更新主要表现为在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的土地再开发利用问题。
本文的目标是解释现阶段城市更新困境面临的经济社会根源及其背后折射的制度运转困境。在以“三来一补”企业为中心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中,农民直接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及增值收益分配,其直接后果是经济发展模式牢牢地和农民集体土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内在地驱动集体经济组织不断通过“经营”土地获利,并且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把长期经营的利益分配关系合法化,形成了制度化的“土地利益群体”。因此,城市更新面临强大的阻碍。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笔者及所在团队在珠三角核心地区的中山、深圳与东莞的基层调研。
二、城市更新的“土地陷阱”表现
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斯图加特大学教授哈肯(Hermann Haken)1971年提出协同(synergy)的概念,并在1976年发表的《协同学导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协同理论[2]。协同理论认为,某个主体作为一个系统,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以及系统与系统外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序架构、沟通合作使得整个系统创造出新的价值,获得原来分散个体简单汇总所无法达成的效果[7]。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协同过程的本身就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协同的结果就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因此,“协同”与生俱来就是与“创新”紧密相联的。
(一)产权细碎化的困境
城市更新的首要条件是通过高层次的统一规划清除附着在土地上的既得利益,实现土地的整合,完成功能区布局。改革开放以来,规划由单向落实计划需求的工具,到城市空间发展管控的重要工具,再到实现多元协调发展目标的公共政策[11]20-21。规划的本质涉及对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也是国家专断意志的体现、国家强制能力的重要表现。
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封闭性。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资格是因出生、婚姻等自动成为集体成员的方式而获得,无须支付任何代价,死亡便自动退出,不可继承。通过股权的量化固化,成员权转化为股权,股权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交易,只能通过继承获得,新出生人口和嫁进来的媳妇不能拥有股权,享受不到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处。集体经济的收益集中于某一特定时间形成的利益群体,这一集团超越了血缘和地缘等社会关系,成为封闭性的利益群体。二是利益一致性。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依照“按份共有”的方式平等地分给每个股民,股民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联系具有直接性。并且,集体收益来源于地租,地租具有稳定性、无风险、易监督的特征,农民之间借助股份合作社建立起了一致性的共同利益。三是排斥性。通过政经分离,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收入难以转化为基层的公共服务能力,基层治理能力下降。因其建立起的股份合作社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性质,村民与股份合作社便建立起直接的利益联系,股份合作社就必须代表股民利益最大化而行动,作为股民的村民也因此可以借助股份合作社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利益。当遇到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公共政策时,便产生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由此提高,国家基础性能力下降。
(二)经济成本高昂的困境
由于集体土地上覆盖了大量的物业,厂房出租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形成了大量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些土地虽然在性质上属于集体土地,但是其功能、市场价格与国有土地并没有差别。这些土地是在土地管理不严的情况下形成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虽然深圳市在2004年土地改革时,对关外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国有化”,这只是在土地性质上做出了法律界定,实际上农村集体依然掌握土地的实际权力。目前,城市更新遇到了巨大的一致的土地利益群体的阻碍,城市更新要完成土地开发权的进一步上收,政府面对巨大的利益群体,协调谈判对象众多,并且在众多的利益群体之间形成了模仿效应,一个项目改造成功意味着接下来的项目改造需要同样多的经济成本。目前城市更新中开发商介入的每亩平均改造成本达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因此,只有具有高价值的商住地块才能承担。比如2017年,中山市大力推进以“三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有8个镇(区)的10个项目入选全市“三旧”改造连片试点项目,涉及用地面积3 120亩,计划总投资228亿元[12],每亩平均改造成本为730万元。这样大的成本只可能由商住用地开发商承担,更多的未规划为商住的土地不可避免地被开发商所弃用,成为城市洼地。
(三)交易成本巨大的困境
厂房出租获得的收入性质属于集体经济,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集体厂房出租获得的收入是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有的一份分红收益。当项目涉及多个集体经济组织和众多分散农户时,政府规划的大量城市更新项目常常陷入困境,陷入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局面,交易成本高昂,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多个村集体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主要是利益主体多,协调成本很高,各村就土地股份量化方式、控股权、收益风险分担等难以形成共识。S镇是中山市西郊的一个工业小城镇,以服装制造业为主,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大量引入外来“三来一补”企业。到2016年底,全镇约有400家服装企业及6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从业人员约有8万人,全镇服装产业产值170亿元,约占全镇工业产值的70%。该镇土地细碎化状况很惊人。S镇总面积为55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强度为40%,建设用地约有3万亩,其中主要部分是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工业用地和农民宅基地,这些土地分散在15个行政村、50个集体经济组织单位,其中7个行政村、43个村民小组,形成土地利用高度细碎化的格局[注] 见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广东中山市S镇土地利用报告》 。 。这种格局是珠三角很少有跨集体经济组织的城市更新项目成功的原因,由此形成了珠三角地区在土地利用上典型的制度劣势。
面对如此巨大的困境,深圳市最终结合广大城市更新地区土地权属特点建立了“20—15”利益分享机制,具体为:城市更新范围合法用地和原农村历史违建用地比例控制在7∶3以内,针对30%违建用地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其中20%由政府收回纳入储备,80%由市场主体开发,且80%用地中,须另外贡献15%土地优先用于建设公共基础设施[13]。但即使如此,在2010—2016年期间,深圳市累计列入更新计划的项目约600个,而这些列入计划的项目中真正完成用地供应的仅为20%左右,已完成开发建设进入市场的更加屈指可数[14]。这表明在珠三角地区,尽管政府掌握着土地规划权,然而农民集体实际掌握着土地,在土地利用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集体和政府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必须清楚的是,这种政策是政府面对巨大的土地利益不得不做出的妥协,突破了现有的土地宪法秩序。地方政府即使提供优惠的政策条件,激励相关利益主体合作投入城市更新,由于村民有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想象,也不能解决问题。在集体土地入市的制度框架中,现有土地细碎化格局背后附着的大量既得利益,政府要限制、取消这一利益,需要付出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在外来企业大量涌入珠三角农村的背景下,集体土地制度在过去30多年成为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如今,城市发展面临转型,经济发展单元提升,珠三角主要城市可用建设用地消耗殆尽。目前深圳市、东莞市的国土开发强度已超过45%,珠海、佛山在35%左右,广州、中山开发强度亦逐渐逼近30%,可开发土地与用地需求的矛盾十分尖锐[10]。地方政府转而强调盘活存量用地的重要性。但是,珠三角以村镇为主导的农村工业化是建立在集体土地基础之上的,农地违规转用带来土地利用粗放、高度分散和碎片化的问题,不利于城市产业优化和各项城市规划的落实。
三、地租经济与地利分配的制度化
之所以形成如此庞大的细碎化地权,与珠三角地区特有的乡村工业化路径密切相关。在早期的“三来一补”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推动“四个轮子”一起转,村集体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厂房,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企业租用厂房获得物业收入。农民突破已有的宅基地管制,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设高层建筑用于出租,获得高额的地租收入,农民极其不愿意退出土地。集体土地的收益具备公共利益的属性,通过分红分配到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一致性的制度化的土地分利群体。
(一)乡村工业化中的地租经济
20世纪80年代,在“三来一补”的乡村工业化发展模式中,厂房建设需要土地集中统一使用,因而面临着土地分散在农民手中的矛盾。由此,地方政府的默许与村集体强大的土地管理能力使得土地自发由分散走向集中,村集体依靠统一上收土地开发权作统一规划利用,一般将集体土地划成农业保护区、工业开发区、行政住宅区。通过招商引资,在集体土地上建设了大量的物业厂房,村集体经济得以发展。厂房物业建立在集体土地上,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农民也因此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收益。在20世纪90年代,广东南海推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便是直接将农民的土地折算成股份,农民由此获取收入。以中山市Y村为例,2015年村集体总收入为5 321万元,其中村一级的总收入为4 158万元,各村民小组总收入1 163万元。到2015年12月31日止,村一级固定资产达1.89亿元,经营性物业的面积达15.6万平方米,村集体经营性的厂房、宿舍、商铺基本全部出租[注] 见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广东中山市S镇土地利用报告》。 。
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农地按照“公有私用”的方式处理,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由此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珠三角地区,由于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随着国家产业布局与世界产业格局的大调整,乡村工业化迅速发展,土地增值收益巨大,带来了农地非农化的问题。工业化要求改变个体分散控制土地的局面,土地由个体转向团体控制,按照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因为,村集体经济来源于土地,农民相信该收益是由自己土地入股获得的,由此,产生了强大的分红冲动,并反对政府提取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区域性的公共服务。农民与土地的利益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结纽带,并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制度化的联系。
(二)地利分配秩序
随着集体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社会利益主体的诉求也日趋多元化,出现了农村基层争权夺利、身份竞争和利益分配纠纷、权利差异与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不断加剧[15]。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成员权的界定问题,表现为户籍与村籍的矛盾、成员权与地权的矛盾等,特别是庞大的外嫁女群体的上访问题[16],迫使地方政府通过清产核资、股份量化和固化来明晰集体收益分配边界,防范因此发生的各种矛盾。广东省各地在2002年之后陆续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核心内容是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通过实施股份合作制,促进农村集体“三资”的有效管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该地区通行的做法是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股份化,由村民委员会占有集体股,组织成员占有个人股;并且实行“生不增,死不减”的固化股权措施,即股权配置完毕后,成员的股东权固定不变,既不因股东死亡而消灭,也不因村民增加而增加成员股权。
在婚姻的过程中,得到婚姻滋养的岸田俊子得出“男女互相怜爱”之相处之道;而秋瑾由于经济问题,留学艰辛而更加坚定经济的重要作用,更加坚信女子只能靠自己。
(三)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征
珠三角地区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集体经济组织改造为“股份公司”,建立董事会-职业经理人的治理结构,这样就把集体土地的利益和一家一户的利益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致的共同利益。政府在征地拆迁时不仅会遇到少数个别的钉子户,还会遇到整体的有共同利益而且能够形成行动能力的钉子群。
另一方面,由于农地非农化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村干部出现普遍的贿选行为。为了防止村干部以权谋私的寻租行为,强化村民对集体资产的监督积极性,一些地区开展了“政经分离”的改革,将村民委员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开,从而分离了基层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两种职能,村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公共服务,股份合作社按照现代的股份制公司结构运行。深圳市在2016年开始了“政经分离”的改革,其具体内容包括:党组织的一把手和村(居)委会成员不能担任经济联合社社长一职,村党组织负责党务监督;村委会负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经济联合社负责经济建设和股份分红,经济联合社由年满18岁有选举权的股民选举。由此,村社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经济发展规划分离,经济收入不再转化为基层的公共服务能力,这也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的去政治化。
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土地开发而言,土地的统筹层次越高,土地开发的成本越低,城市的规划更加能够落实下去,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政府就越能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高密度的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可持续的城市化要求土地的非农发展应该在超越村庄的更大尺度之上进行协调,以使土地相对集中开发和有效利用。由此,城市发展的正外部性能够通过再分配的机制惠及更多人,做到土地“涨价归公,地利共享”。若土地统筹层次比较低,土地产权单位比较小,土地利用中就会遇到“细碎化”困境,政府即使是征地用于公益事业,成本也极高。政府若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城市功能规划,并进行拆迁,难度就会非常大,与握有细小琐碎的土地产权的个体打交道,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钉子户,提高政府开发土地的总成本。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完成之后,集体经济组织经由简单互助劳动性质的临时互助组,演变为在共同劳动基础上的常年互助组,再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转变到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62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集体成员共同参与生产和劳动的农业经营模式和土地权利结构。集体经济的运作原则是在公有产权秩序下,集体是个体的集合,土地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是国家介入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工具,集体产权制度高度政治化。
随着土地的非农化和土地级差收入的不断提高,整个村社变成了一个以经营土地为目的、以分配土地收益为纽带的实体[17]。强大的地租经济进一步刺激了农民对于土地利益的渴望,为了扩大村集体收入,股份合作社和政府讨价还价,力图使利益最大化。这也意味着经过股份合作制改革之后,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大私”的原则运行,无法实现与国家的有效对接,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群体,政府的城市更新政策无法落地。
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治效应
珠三角地区的农村成立合作社的目的是进行土地集中开发,开发土地和经营集体经济的目的是实现量化后形成的股民利益。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取消个体化控制产权的同时,又通过股份化产生被量化、固化和可内部处置的股权,由此形成了“团体-共有”式的产权秩序,土地保持团体控制的产权格局,利益分配遵循“按份共有”的基本规则。在股份制改革之前,通过分红制度,农民和集体土地收益的联系已经事实上建立起来;股份制改革后,农民和集体土地收益的联系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个体化的地权意识进一步强化。
(一)从公有产权秩序向共有产权秩序转化
关于农村产权实践,张小军提出“复合产权”的概念,强调经济产权、社会产权、文化产权、政治产权和象征产权的复合存在[18]。这反映了产权观念的塑造一方面源自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源自国家的制度塑造。中国农村的集体产权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制度的安排,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界,珠三角地区的集体产权实践发生了重要的变迁,逐渐从公有产权秩序向共有产权秩序转化。
动态造价管理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动态造价管理的调控有着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定额的特点,这个特点就使动态管理调控具有了指导性的特点,与传统的调控方式对比,动态管理调控方式有定额性、指导性和动态性的特点,这些特点能够更好地去平衡多方面的因素,所以在建造的工作当中应该采用动态管理的方式去管理造价。
企业的成功落地引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员,珠三角一些地区本地人与外来人员的比例甚至达到1∶20。庞大的流动人口需要生活居住场所,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并没有能力为庞大的外来人口提供完善的公共居住条件,在出租屋市场的刺激下,当地村民突破宅基地限制,超标建设房屋,形成了大量的违法建筑,这些房屋出租收入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家庭收入。
建筑企业要考虑到建筑整体设计方案、使用方案、项目特点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合理招投标。在招投标时,设置一定的额度标准,对造价成本进行控制,从中选择最合理的方案。另外,还需要相关的管理部门积极参与,将经济方案与建筑方案相结合,选择出最经济实惠的方案,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明确资金流向。与此同时,建筑企业在对设计公司的选择时,需要询问专家意见,确保设计公司的选择的正确性,避免设计方面出现的不合理,造成建筑企业的经济损失。设计公司的正确选择,可以有助于顺利完成招投标,对建筑工程造价进行诸多方面的监控,有效控制建筑造价的成本控制。
现在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私有产权认识。其直接后果是,将集体权利按照份额划分到个体私人,集体控制的资产减少,个体农户控制的资源增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收益分配问题,避免了为增加分红而采取的各种策略行为。但是,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实质是将集体资产从公有变成“按份共有”,将集体变成共有性质的团体组织。股份制本质上代表了“成员所有、成员控制和成员收益”的一种治理模式,按份共有的股份合作社是由个体权利集合而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私化的原则运作。
多么短暂而悲哀的人生!我总是对自己说,要活着,你还有儿子,还有老母亲。对于这个世界,你已经没有了贡献的能力,但你是人子和人父,必须要尽到责任。这是天命,也是义务。在漫长而焦灼的求医问药过程中,多亏了几位医生朋友的指点,他们借助微信,通过观看我发过去的图片和诊断影像,指引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做。他们是我认识很久或者相识很短的朋友,而且极其普通,我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从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言行上,我觉到的,是一种无上的善意,乃至基于对生命和人本身怜悯、爱护的热情与耐心。
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模型是一个4层剪力墙结构,层高均为3 600 mm,总高度14.4 m,梁和剪力墙平面见图1和图2,图中LL2截面尺寸为200 mm×500 mm,LL1的截面宽度为200 mm,截面高度在400~1 600 mm之间变化。不考虑楼板的影响,墙厚均为20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Ⅱ类场地,设计地震分组为第1组,抗震等级设为二级。
中新生代时期,特提斯洋壳和次洋壳依次向北运移,龙首山拱断带遭受强烈挤压,发生以垂直升降运动为主的构造变形,将龙首山拱断带切成菱形,形成菱形断块的构造格局。
(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迁
基于集体产权公有秩序,集体公有制经济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农民认为土地是国家的,村集体是代表国家管理土地的基本单位。集体经济和集体所有制是农村自治的根本,集体土地具有公共利益属性,成为激活村民自治运转的经济基础[19]。集体产权本质是一种社会合约性产权,它是特定行动关系协调的产物,其法律属性看似模糊,实则各当事人对于以某种原则和共识而形成的权利分配格局异常清晰[20]。集体经济组织是“小公”,国家是“大公”,二者能够有效地结合,国家的政策意志能够通过政经合一的集体组织渗透到基层,这也意味着国家的基础性能力很强。国家与农民发生深刻的共振,其关系越加紧密。
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集体产权秩序转变为共有产权秩序。因而,从制度上强化了农民和集体经济收入的关系,由农民私人利益集合形成的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对外排斥性,强化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在“共有”产权秩序下,集体经济按照共有规则运行时,集体资产属于私有产权的叠加,集体收入按照私有产权份额分配,集体利益分配格局提前锁定,强化了村民小组的大私性质。共有制已经确认每个人的私有权利,任何集体利益调整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私利,这部分人就成为集体行动中的合法反对者。股权量化之后,村民在集体资产上具备私有产权意义,认为所有集体收入都应该分给个体,村庄公共治理成本应当由政府承担,政府因此承担着巨大的公共产品供给压力。集体经济组织仅仅成为按照固有的股权分配利益的组织,村组干部失去了解决矛盾的权力与能力,基层治理从动员型治理转化为分配型治理。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越高,集体收益越高,农民集体行动能力越强,集体经济组织与国家权力的疏离越大,公共政策的执行因而受到巨大的阻力。国家试图从制度层面消除基层的问题,却最终消解了基层内部化解矛盾的能力。
五、结 语
本文论证了珠三角地区土地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困境,该地区特殊的工业化路径形成了巨大的“土地利益群体”,且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合法化,该利益群体具有封闭性与排斥性的特征,其背后的运行规则遵循“团体-共有”式产权秩序。由此导致城市更新政策执行面临细碎化地权、经济成本与交易成本巨大的困境。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就可能陷入规划继续无序、项目无法落地、土地资源无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在此种土地制度安排下,国家意志难以有效传达到基层,国家基础性能力由此变弱,国家与农民关系疏离。中国目前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键时刻,涉及重大的经济社会利益的调整,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应当避免落入珠三角地区的土地陷阱,保持公有产权秩序,维护弹性的、可调整的产权结构极为关键。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EB/OL].(2018-09-10) [2018-09-19].http://www.gov.cn/shuju/2018-09/10/content_5320844.htm.
[2] 邹兵.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转型的动因与路径[J].规划师,2013(5):5-10.
[3] 周其仁.土地制度改革有四方面值得关注[J].理论学习,2014(10):36-37.
[4] 曲苏闽.对小产权房问题的法律思考[J].中国土地科学,2011(12):22-27.
[5] 万举.国家权力下的土地产权博弈——城中村问题的实质[J].财经问题研究,2008(5):11-16.
[6] 林强.城市更新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反思——以深圳为例[J].城市规划,2017(11):52-55,71.
[7] 王桢桢.城市更新的利益共同体模式[J].城市问题,2010(6):85-90.
[8] 朱介鸣.城乡统筹发展:城市整体规划与乡村自治发展[J].城市规划学刊,2013(1):10-17.
[9] 桂华.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制度合法性辨析——兼论我国土地宪法秩序[J].法学评论,2016(1):31-41.
[10] 合富研究院.佛莞深珠4市开发强度超30%警戒线 面临土地局限[EB/OL]. (2017-09-27) [2018-09-19]. https://www.sohu.com/a/194970817_118671.
[11] 张京祥,罗震东.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12] 中山日报.“三旧”改造助力城市新发展[EB/OL]. (2017-11-24) [2018-09-19]. http://www.zs.gov.cn/main/zwgk/newsview/index.action?id=213304.
[13] 刘芳,张宇.深圳市城市更新制度解析——基于产权重构和利益共享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5-30.
[14] 冯少文.城市更新如何提速[EB/OL]. (2017-11-17) [2018-09-19].http://epaper.oeeee.com/epaper/H/html/2017-11/17/content_87676.htm.
[15] 郑佳斯,张文杰.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J].岭南学刊,2016(5):16-22.
[16] 桂华.论法治剩余的行政吸纳——关于“外嫁女”上访的体制解释[J].开放时代,2017(2):164-183,8-9.
[17] 蒋省三,刘守英.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发展调查[J].管理世界,2003(11):87-97.
[18] 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23-50.
[19] 桂华.农村土地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关联分析——兼论村级治理的经济基础[J].政治学研究,2017(1):99-110,128.
[20] 折晓叶,陈婴婴.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J].社会学研究,2005(4):1-43.
The “Land Trap ”of Urban Renewal and Its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LIU Chao
(Center for Rural China Governanc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430074, Hubei, China )
Abstract : Urban renew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urban renewal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ine ground rights and the unified planning,which is a problem of high economic cost and high transaction cos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ed land interest group formed in the rural special industrialization path hinders the land development and space planning of the state power. On the one hand, in the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direct entry of collective land into the market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thus creating a large number of land value-added benefits.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solve issues such as disequilibriu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added income and dilemma of supervis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reformed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system with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stock right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strengthened this “division group” in the sense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formed a group-shared style. The order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come an antecedent disadvantage of the land system. Therefore,the current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will chang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operation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alie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farmers,which may bring serious consequences.
Key words :urban renewal; land trap; land interest group; property order
中图分类号 ::F12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9)02-0066-07
doi: 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2.007
收稿日期 :2018-09-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ID030)。
作者简介 :刘超(1990—),男,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与城乡基层治理。
标签:城市更新论文; 土地陷阱论文; 土地利益群体论文; 产权秩序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