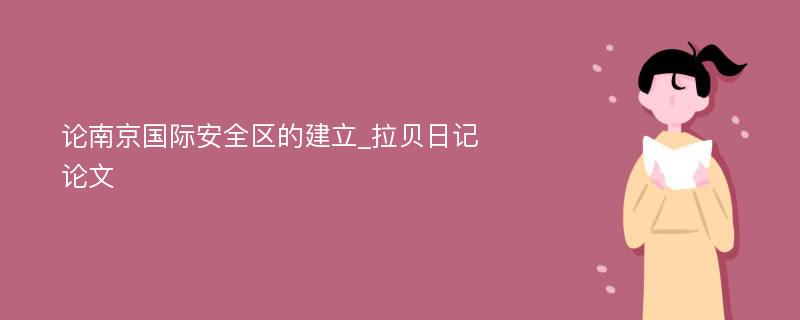
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区论文,南京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11月,正当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之时,仍留在南京的一些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人,不顾自身安危,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在南京沦陷后保护了大批无辜平民。目前,在国内外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人们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即使有关南京安全区的论著,也大多注重安全区的功能和作用,而对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背景和经过却很少论及。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南京安全区成立的背景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机对南京进行了疯狂的轰炸。8月15日,日机20架,轰炸了南京明故宫机场、大校场机场等目标。这是日机首次空袭南京。此后,日机对南京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野蛮轰炸,使南京军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机轰炸的目标主要为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以及电力和通讯部门。但是,南京城南的人口稠密区、医院及学校亦遭日机的轰炸与扫射。8月27日,日机轰炸了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省立第三医院、宪兵团驻地、东郊遗族学校、卫生署等处。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称:“查近日敌机不时来侵袭我首都,本署以邻近军事区域,致昨日(八月二十六日)夜十二时,敌机飞经本署上空时,投落炸弹数枚,其中二枚落于本署,当命中制药厂后部,炸毁及烧毁厂房五十余[平]方,制药仪器及材料伤损半数,自来水管亦由地中爆出,煤气管及电线均被毁损,职员宿舍亦受震荡,裂痕多处,幸未伤人,制药厂被炸后旋即起火,由本署消防班及警察厅消防队施救,延烧至一小时始告扑灭,统计房屋、药品、设备等各项损失,约值四五万元之谱。”(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邻近卫生署的中央医院也多次遭到轰炸。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拉贝记述说:“中央医院里落下了15枚炸弹。这很难说是否就是把医院当作轰炸目标。但看上去很像是这样。”(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魏特琳在9月26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下午5点。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带吴博士、格蕾斯·鲍尔和我去中央医院查看了昨天中午遭轰炸的后果。尽管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中央医院和卫生署所在的院落里……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位于爆炸现场北面,离现场有一段距离的卫生署大楼的窗户玻璃也全部震碎了。”(注:[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美国驻日本大使C·格鲁也记录了日机对南京的若干次轰炸情况:“8月26—27日,江苏南京。南京的贫民区遭到轰炸,约100名平民死亡,其中有50人被烧死……这是8月15日以来对南京连续轰炸中最猛烈最惨酷的一次”,“9月25日,江苏南京(9月19—29日也一样)。对街道进行猛烈轰炸,在攻击政府建筑物目标的同时,中央大学、中央医院也包括在内。这些地区与军用机场、武器库、兵营并没有关系。数百名非军事人员被炸死,数千人受伤。”“11月24日,江苏南京。日机20架轰炸了中央商场地区,炸弹落入国立博物馆附近,法国教会,以及小商摊密集的商业街,约40名平民被炸死。”(注:《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编》,(东京)青木书店1992年版,第26—27页。)
日机的野蛮轰炸,使许多市民无家可归,沦为难民。然而日军连难民也不放过。9月22日,日机对南京进行了多次空袭,轰炸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市政府、下关火车站等地,位于下关的难民收容所亦遭轰炸。下关难民收容所系用芦席搭起的临时性建筑,日机轰炸使收容所燃起大火,“致死难民在百余人以上”。(注:《申报》1937年9月23日。)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目睹了这一惨状:“轰炸后我去下关难民收容所看了看,那情景真是触目惊心,轰炸现场到处是遇难者的遗体。大多数难民居住的简陋小屋被炸弹点燃,燃起了熊熊大火,从烈火中冒出的浓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烟柱矗立在空中,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见。”(注:[日]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南京大屠杀事件资料集——第2卷英文资料编》,第85页,转引自[日]笠原十九司:《南京难民区的百日》,(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7页。)
拉贝看到日机轰炸下的穷苦平民,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次响起警报声时,一大批穷苦的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奔跑着经过我的房子到五台山去,那里的山丘下挖有一些较大的防空洞。这是一种灾难。我真不愿意看到这种痛苦的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39页。)在南京的许多外籍人士都认为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南京人民一些帮助。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1—13页。)
从拉贝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有着自己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这种道德准则促使他决定留在南京。
与拉贝一样,当时在南京的许多外籍人士都具有这种道德准则。魏特琳也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我不能走,因为我要是走了,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8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14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注:[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第18页。)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拉贝、魏特琳、米尔斯、贝茨、马吉等西方人士不忍心看到南京平民遭受的苦难,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毅然留在南京,为拯救遭受苦难的人民尽一份道义上的责任。除了这一因素之外,应该说宗教信仰也是促使他们留在南京的重要原因。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福斯特在致家人的信中写道:“金陵大学医院为数不多的几位工作人员正英勇地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多这儿亟需的专业人员都撤走了。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了许多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的英勇行为。我们意识到基督关于被雇者与好牧羊人的故事是多么真实可信,我们更加理解了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含义。”(注: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四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32页。)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在致妻子的信中也写道:“我们南京安全区是靠充分的勇气建立的,或是如你所爱说的,靠信仰,或是靠某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无畏精神。”(注: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四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220页。)作为一名传教士,米尔斯所说的信仰,显然是指他们所皈依的基督教精神。
以往,人们往往把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说成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背地里尽干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这一评价未免有失公允。尽管历史上确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还是有许多传教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慈善事业作出了贡献。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自凇沪抗战以来,大批平民家破业毁,沦为难民。据1937年9月底的调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难民不下130万人。(注:《立报》1937年10月1日。)有鉴于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决定发起组织南市难民区,以收容、救济饱受战火蹂躏的难民,其发起人是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
饶家驹是法国天主教神甫、震旦大学教授、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部主任兼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凇沪抗战爆发后,饶家驹发起组织上海国际救济会,在震旦大学等处创设了一批难民收容所。
当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后,饶家驹意识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重,遂提出在南市设立难民收容所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日军当局也表示原则同意。(注:《密勒氏评论报》编印:《中国抗战》第一集,第94页。转引自罗义俊:《南市难民区述略》,见《抗日风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175页。)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划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已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注:转引自罗义俊:《南市难民区述略》,见《抗日风云录》,第175页。)
南市难民区设立后,难民收容工作进展顺利。至11月中旬,已安置难民十几万人。(注:《救亡日报》1937年11月18日。)虽然日军在难民区周围经常施暴,但由于难民区是经中日双方同意设立的,因此,日军未敢轻易地进入难民区,使大批难民避免了日军的蹂躏和战火的摧残。
由于上海各报对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作了大量报道,南京的外籍人士对此早有所闻,并以此为榜样。米尔斯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我称之为饶神父区,正是由于他的名字辉煌地与它联结在一起。”(注: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四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220页。)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也说明了这一点:“我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个创建成员。”“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11月底,预料日军将要进攻南京。以饶家驹神甫建立的国际委员会的榜样,这个委员会对那里大量的平民提供了相当的帮助,我们试图在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在南京做相同的事。”(注:Martha Lund Smally( edit.)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Documentation of the Nanking Massacre,P.44,Yale Divinity.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因此,可以说上海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为南京安全区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二、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酝酿
11月下旬,当日军向南京进逼时,国民政府即着手迁都的准备工作。11月16日,政府各机关开始大规模迁移。11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政府的西迁,对南京的平民来说无异于失去保护。有鉴于此,11月中旬,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先生提出了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难民区的设想。据杭立武回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南京看到报纸上报导上海有个饶神父,在上海设难民区,容纳很多妇女和小孩。我忽然动脑筋,觉得日本将来进攻南京了,我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设立一个难民区。那时我是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认得金陵大学的许多美国人,同时我也是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和许多英国人、德国人有来往。我约集了一二十个外国人,我说我们要设一个难民区,他们都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为人道的事情,应该赞同。我们这个难民区很自然的就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划进去,一直到鼓楼、新街口。划好后,我们就写信给上海饶神父,请他把地图给日本的司令看,请他同意我们成立难民区,并且答应不要骚扰难民区。”(注:杭立武:《筹组南京沦陷后难民区的经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3期。)
杭立武并没有说明他是哪一天提出设立安全区的,但我们可以从其他资料中找到答案。魏特琳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说:“在今天我们非正式的宣传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听说了成立‘安全区’的计划。这个想法仅仅是两天前提出来的,现在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真是了不起。”(注:[美]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第155页。)由此可见,杭立武是在11月16日提出这一设想的。
11月17日,魏特琳在并不知道杭立武提出设立安全区的情况下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W·R·派克,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安全区域。信件全文如下:
亲爱的派克先生:
在日军逼近南京前,我认为预先为那些无法避难的贫苦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市民设立一个对他们来说较为安全的场所(类似“安全中心”或“安全地区”)为好,并期望能事先就此事进行商讨。
正如您所知,这样的事情在上海已经实行了,但为时已晚。毫无疑问,如果能及早着手进行周密的准备,将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当然,我知道这件事并不那么容易,即使是相对安全,也必须事先征得交战双方的同意。另外,不仅只是(向交战双方)提出建议,为了获得军方的同意,还必须由有影响的中立国人士出面。
我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的目的,那些出资捐助者们(指美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始者委员会的出资者—引者注)也一定会很乐意的。若本校被指定为(安全)中心,我们准备立即腾出楼下的房屋,准备好大房间,以备万一。
上述事情,恳请您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并请尽快商讨,我希望及早看到商讨的结果。(注:魏特琳致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W·R·派克的信,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派克收到魏特琳的信后,立即报告了大使,并于当天给魏特琳回了信,回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魏特琳女士:
你1937年11月17日的来信已经给大使看了。信中建议,将非武装的平民集中起来,提供一个“安全中心”,以尽可能避免战争的伤害,并应当将这一情况告知交战双方的军事当局。
如果设立这样的中心,大使馆是欢迎的,并打算代为向日军当局转达。(注:美国驻华大使馆W·R·派克致魏特琳的信,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同日下午5时30分,金陵大学的外籍教师米尔斯、贝茨、斯迈思三人相约来到美国大使馆官员派克家,就设立安全区问题与派克商谈。米尔斯等向派克提出了设立安全区的设想。他们认为,首先,一旦南京附近及市内发生战事,为了让一般平民躲避战火,应当设立一个安全区、难民区或非战斗区域,以保障平民的安全。其次,安全区设在市内西部较为适宜。因为战事将发生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而中国军队在西部地区并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中国军方可能会同意将西部地区划为非军事区。(注:《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编》,第122页。)米尔斯还表示,一旦安全区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希望美国大使馆能代为向日本当局转达这一信息。对此,贝克表示,“对这件事,今天大使馆已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因为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女士关于设立安全区的来信,已有明确的答复,大使馆很乐意代向日本当局转达。”(注:《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编》,第122页。)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看出,成立安全区的设想并不是某一个人提出的,而是中外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设想。
11月17日晚,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及使馆官员派克与孙科等共进晚餐,张群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也在座。席间,派克向中方人士说明了下午与米尔斯等人交谈的主要内容。约翰逊也表示,这不是美国官方的建议,而是一些民间人士的设想,目前还处于商讨阶段,如果这一建议进入实质性阶段,美国大使馆可代为向日本当局转达这一信息。(注:《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编》,第123页。)对此,张群表示,现在考虑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而马超俊市长看来是第一次听到设立安全区的构想,他没有表明个人的态度。(注:《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编》,第122页。)
米尔斯等人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安全区能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获得各方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中日交战双方的同意。当米尔斯等人向美国大使馆官员表达了设立安全区的建议后,中国方面至11月29日以前,始终没有给予正式的肯定答复。
从11月17日至28日,中国方面虽然没有正式明确的答复,但拉贝等外籍人士仍然间接地了解到中国方面对此举的肯定态度。11月26日,当拉贝向杭立武询问中国方面是否同意设立安全区时,杭立武表示:“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已经表示赞同。”(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08页。)11月29日,中方正式同意设立南京国际安全区。
除了中国方面外,美、英、德等国驻华大使馆均对设立国际安全区表示赞同。11月17日,魏特琳向美国大使馆官员派克先生提出建立安全区的设想后,美国大使约翰逊即表示赞同。英国大使馆对此也表示同意。(注:参见[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97页。)德国虽然是日本的盟友,但德国大使对此亦表示赞同。拉贝在日记中记述道:11月22日,“德国大使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们的介绍,认识了斯迈思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97页。)另外,德国大使馆官员罗森将张群的官邸借给拉贝作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也说明了德国大使馆的态度。罗森在12月24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12月9日,日本向所有大使馆发出了要求,要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这时我同领事馆的秘书许尔特尔先生一起再次坐车进城,以便把留在那里的帝国德意志人接到长江上去——可惜没有成功。无论如何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此之前我把一家中国银行供我支配的一所房子交给了拉贝先生,这所房子有一个由德国顾问建造的,不怕轰炸的地下大掩体。”(注:《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载《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第152页。)这里罗森有误,该房屋并非中国银行所有,而是张群位于宁海路5号的官邸。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日本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安全区的命运。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向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美国政府和国务卿发出了关于设立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电报,并希望尽快将电文转送日本方面。
电报发出三天后,仍未得到日本方面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十分焦急。11月27日,国际委员会再次通过美国大使馆向驻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出电报,希望日方对设立安全区给予友善的考虑,并希望立即得到答复。(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12页。)
12月2日,国际委员会终于收到由上海饶神甫转来的日本当局的复电,电文中称:“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本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24页。)
从上述电文来看,日军当局虽然否决了设立安全区的建议,但同时又表示:“只要与日本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对于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各方反应不一。英国认为这是断然拒绝。(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25页。)国际委员会对这样的答复已感满意,并认为这毕竟比完全拒绝要好。(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25页。)
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方的态度,国际委员会随即发电给饶神甫,要求日方直接给国际委员会一个明确的答复,并希望饶神甫将这一意见转达给日本方面。(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25页。)
12月5日,美国大使馆转来了日本方面的正式答复,答复全文如下:
日本当局仔细考虑了南京国际区的建议,日本大使现通过总领事馆将下列通告通知美国大使:
1、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有必要给安全区领导层提供足够的物资材料或其他特别权力,以便安全区附近发生战斗时,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2、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
3、鉴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即使该建议受到中国当局的欢迎,但仍然不能保证做到在南京发生战斗时,能够完全阻挡住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并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4、尽管日本政府完全承认对此建议负责的领导层高尚动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担在未来对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保证义务。
5、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34—135页。)
这个答复仍然模棱两可,而且日方不相信国际委员会有能力阻止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因此日本“不承担在未来对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保证义务。”日方的这一答复,为日后日军进入安全区,并滥施暴行埋下了伏笔。
杭立武先生曾回忆说:“因为日本军方的人和饶神父有来往,饶神父就把地图给日本司令,后来饶神父回信给我,只讲日本司令说:‘我们知道这件事了’,并且接受了地图。后来在进入南京城的日本兵身上发现这种地图,是有难民区的。”(注:杭立武:《筹组南京沦陷后的难民区的经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3期。)杭立武于12月2日夜奉命将藏于南京朝天宫库内的一万余箱文物用船转移到汉口,他本人也随船离开南京,显然,以后发生的事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回忆未必准确。笔者至今仍未发现能够证明日军地图标有安全区的资料。当时能够与日军联系和交涉者,只有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而在国际委员会委员大量的日记和书信中均无此记载。恰恰相反,大量资料证明,在日军的地图上并没有标明安全区。米尔斯记述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约100人的分遣队。他们坐在马路南面,对面是一大群中国平民。我们试图向军官解释安全区的概念,并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发现他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安全区。”(注: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四册)—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30页。)此外,金陵大学教授斯迈思在记述这一情况时也说:“在战斗期间我们就睡在平时的床上,愚蠢地相信日本人会指示他们的大炮尊重安全区。12月13日下午,当我们在城中和他们的先头部队接触时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在其地图上标出安全区,我的头发都惊得几乎竖了起来。”(注:Martha Lund Smally( edit.)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1937-1938,March 8,circular letter from Lewis S.C.Smythe,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ccasional Publication No.9.)由于日本当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承认安全区,因此也不可能将安全区标明在军用地图上。
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国际安全区的成立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酝酿期间,只有米尔斯、贝茨、斯迈思等少数几个外国人(主要为美国人),拉贝是在11月19日才得知此事的。拉贝在日记中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92页。)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召开了一个会议,着重讨论了成立国际安全区的有关事宜。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推举约翰·拉贝为委员会主席。拉贝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推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97页。)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委员会还发表了一项筹备设立安全区的声明,并通过美国大使馆将该声明转告中日交战双方。(注:《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编》,第125—126页。)此后,国际委员会又确定斯迈思为委员会秘书、杭立武为中方总干事、费奇为外方总干事。(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33页。)
当时委员会中有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和英国人等,为什么大家推举拉贝为主席呢?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的主任,同时又是德国纳粹党南京支部的组长。早在1936年,德国与日本即签订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一年后,即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又形成了轴心国集团。因此,由日本的盟国——德国人出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有利于国际委员会开展工作。第二,拉贝对中国十分熟悉,且具有相当的组织领导能力。早在1908年,年轻的拉贝即来到中国,先后担任过德国西门子公司北平、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0年,他又担任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经理。从1908年算起,他在中国已工作生活了近30年,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民间风俗相当了解。由于他在中国一直担任经理之职,因此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由拉贝出任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较为合适的人选。
关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的日期,以往的论著均没有论及。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际委员会认为其成立的时间为11月22日。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8年2月18日易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中称:“难民区——若干在南京之人士,鉴于饶神甫与其同志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所获之成功,遂欲步其后尘,在南京设一类似之区域。经五、六日之筹备,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组成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这正是筹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外国人士举行会议,并确定拉贝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那一天。但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是一些外国人自发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而不是现代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此它对主权国家并不具约束力,而且,它在日军攻打南京及占领南京之初,将代行某些市政职能。因此它的成立必须得到中国方面,尤其是南京市政当局的认可。
中国方面正式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在11月29日。拉贝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下午4时,委员会内部会议召开,我们讨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例会,市长当众宣布了国际委员会成立。”由此可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自身成立于1937年11月22日,而中国方面正式认可是在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宣布国际委员会成立之时,即11月29日。
为了配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中方表示将给委员会拨款10万元。(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17页。)至12月7日止,国际委员会已收到4万元。(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44页。)后来国际委员会又陆续收到8万元拨款。中国方面还答应调拨2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后来由于运输困难,国际委员会实际收到了9067袋大米、1000袋面粉和350袋食盐。(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此外,马超俊还表示让国际委员会负起安全区内的全部责任。为了协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维持区内秩序,马超俊还向委员会派去了400名警察,以“看守安全区的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54页。)
12月2日,国际委员会迁入宁海路5号办公,这里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参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区标,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会标确定为白底红色圆圈中套一个红十字,同时划定了安全区的范围:“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98页。)总面积为8.6平方公里。
国际委员会划定上述区域为安全区,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一旦日军进攻南京,由于日军的进攻方向主要在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等处,因此中日双方的交战区域主要集中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而安全区位于市区的西部,距交战区域较远。
第二,安全区中包括了南京市的“新住宅区”。所谓“新住宅区”,即二三十年代建设的高级别墅区。在这一区域内居住的主要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以及有显赫社会地位的人,而这些人大多随着政府的西迁而撤离。因此该区域空置住宅较多,便于安置难民。《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报告书》记载:“新住宅区亦在难民区内,其中官吏阶级所住之广厦,业已搬空,其他新式房屋,曾为知识阶级及中产阶级所居者,其住户均已西迁。此等私人产业,有时仅有佣仆或戚属留守其中。”(注:《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书》,《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第三,在安全区内,外国使馆林立,包括日本大使馆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都设在这一区域内。此外,在安全区内,外国财产也较为集中,其中重要的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鼓楼医院、中英文化协会等等。这些外国财产的存在,不仅使日军在轰炸和炮击时不得不有所收敛,而且国际委员会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些财产的安全。
第四,在安全区内,中国军事设施较少。当时除安全区边缘地带和五台山等地有少数中国军队的高射炮阵地外,没有其他军事设施。这便于中国军队的撤离,对保证安全区的“非军事性”也是十分有利的。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成立之初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在安全区内,不允许有任何一方的武装人员进入,当然也不允许有任何军事设施存在,这是安全区存在的前提。中国方面虽然同意设立安全区,但区内的军事设施还没有全部撤出,而且国际委员会与中国军方对安全区的边界还存有分歧,甚至军方的一些人不赞成设立安全区。(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39页。)为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断与中国军方接洽,中国军方也答应给予积极配合。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于12月3日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发了一份函件,表示他“原则上完全赞同成立这么一个区域的想法”,并表示“我会尽快敦促军事人员不得在区域内居住或穿越该区域。……关于从安全区撤出所有军事组织和交通设施一事,我已经下达命令”。(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17页。)
尽管在短期内从安全区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有许多困难,但12月7日当国际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巡视安全区时,他确认高射炮阵地已经从五台山撤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其他一系列军事设施正准备运走。”(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46页。)虽然直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安全区内仍有中国士兵存在,但从总体上说,唐生智的命令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至少撤出了部分军事设施。
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之初,由于日本方面还没有给予正式答复,国际委员会不敢贸然宣布安全区的正式设立。拉贝在12月1日的日记中记述说:“晚上7时30分,在首都饭店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开展建立难民区的工作,因为我们始终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如果我们要求在南京的市民搬进中立区,之后却又遭到日本人断然拒绝,那么我们将负有很大的责任。表决的结果,大多数委员赞成我们继续工作下去。”(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23页。)此后,国际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将存于安全区外的粮食和燃料等运进安全区。然而这项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国际委员会“很难找到运输工具去拉我们的大米和面粉。其中一部分存放在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无人看管。”(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26页。)为此,国际委员会通过新闻媒体请求广大市民提供运输工具,以便尽可能地多运送一些物资进入安全区。
12月5日,当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方面的正式答复后,决定立即开始工作,将标有国际委员会标志的旗帜插在安全区的边界上,以便市民能辨识安全区的范围。12月7日,位于安全区东北边界的山西路交叉路口处已经插上了界旗,同时国际委员会还向报界公布了安全区的行为守则。同时披露了安全区启用时间:“(1)一旦中国军方撤出全部军事设施,委员会将向双方(中方和日方)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2)公共建筑物和学校将尽快开放,安置最贫穷的人,开放事宜将另行公布。(3)安全区的最终开放还将通过报纸的专版予以公布。”(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47页。)
12月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布了《告南京市民书》,此后大批难民开始涌入安全区。拉贝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些难民的悲惨情景:“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这个所谓‘安全区’,街道上比和平时期活跃了许多。看着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流浪,真是催人泪下。那些还没有找到落脚处的人们,在寒冷的黑夜来临时,一家老小就躺在房子的角落里睡觉,还有一些人甚至就躺在露天大马路上。”(注:[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150页。)
至南京沦陷时,虽然国际委员会始终没有向中日双方正式宣布安全区的启用,但随着《告南京市民书》的公布和大量难民进入安全区避难,安全区实际上已开始启用。日军占领南京后,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和他们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在保护与救济难民、向日方抗议、与日军交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