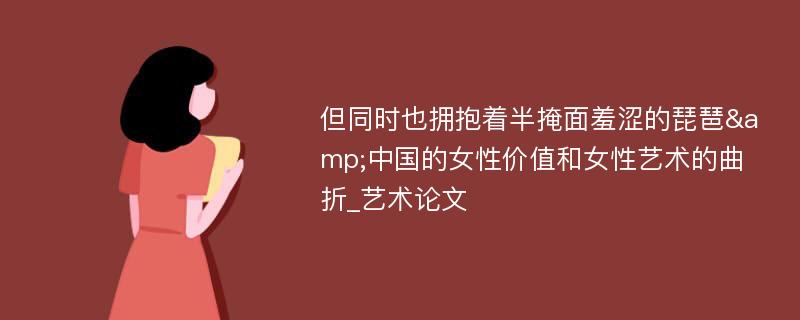
犹抱琵琶半遮面——中国的女性价值与女性艺术一波三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犹抱琵琶半遮面论文,一波论文,中国论文,三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艺术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问题,它甚至首先是一个“女性价值”的问题。
我之所以使用“女性价值”而不是“女性主义”,是因为使用“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在目前我们的艺术批评话语中面临危险。这不仅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多重的男性化气质依然是主导,而更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女性主义”的认知都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而只约化为一个概念,一个标签,一种僵硬的界定,而因为这种误解造成的本能的反感,往往会使女性艺术问题失去心平气和的学术对待,甚至从讨论的前提中就被歪曲和拿掉。事实上,“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化的问题。“女性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中,对应着一个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学,历史、文学、艺术甚至科学等众多领域的观念变革,一系列流派纷呈、庞杂松散的思想体系,1960至1970年代达到了高潮,并随着那个时代成为了历史的一页。有些遗憾的是,由于许多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女性主义”在其后的时代被沾染上一些并不令人乐观的气息,并逐渐凝固成一个带有固定色彩的“标签”。但女性主义关注的根本问题——“女性价值”,在当代西方文化中一直深入发展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如果我们把“东、西方”视作一种时间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的话,西方从女性主义延伸下来的关于“女性价值”的探索,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代表了国际当代女性文化的一种进步的方向。这种情形,与整个西方当代文化一样,给中国当代文化以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大前提下,中国女性艺术成为西方女性艺术冲击和影响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里我使用“女性价值”和“女性艺术”这个概念,就是基于我对这种现实的认同。但另一个现实是,中国女性艺术面对的古代闺阁艺术传统和近现代的革命艺术传统,与西方完全不同,这些来自历史和社会因素,构成了中国女性艺术特殊的存在语境。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脉络,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无法一伸腿就跨过去,或假装自己不是从这种文化中生长出来的。
基于这样的批评立场,我关心的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绘画”,而是女性艺术在当代艺术中作为一种新的问题的存在价值,简单地说,我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女性艺术而不是从女人绘画的角度来看女性艺术。这样一来,我既不能拐弯抹角地回避至今依然对女性艺术发生作用的敏感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也无法一头扎进具体的作品里去,鸵鸟一样只把一个没有上下文的大屁股对着观者。
一、通过男性标准的女性价值与闺阁画艺术
20世纪以前,中国封建时代强大的父权制话语体系,使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独立和完整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女性几乎只能通过男性标准,作为“被看对象”和“欲望对象”才有价值。因此,在艺术作品中,女人往往被处理在被消费的位置。中国10-19世纪产生和发达的仕女画中的女人形象,可谓女人作为“被看对象”、“欲望对象”,即观看、赏玩对象,也即男性对女性消费性审美的集中体现。
由女性创作的作品则是凤毛麟角。有可能拥有绘画”特权”的妇女只有两种,即闺阁名嫒和风尘名妓。前者一般都出自绘画世家,深锁闺阁又身处绘画氛围,使她们不仅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有优越的条件接触绘画。后者的处境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如果不是能诗善画的风流文人成为她们重要的“服务对象”,她们可能永远都没有靠近绘画的机会。因此,绘画对于女性只是一种教养和技能训练,与琴、棋、书,乃至歌舞、刺绣没有本质的区别,或消闲自娱或应对谴怀,所画的也只是些花花草草、闺阁生活等,所以被称之为“闺阁画”(附图2)。少数优秀者,能够以绘画写意抒情而使其作品具有艺术性(附图3),但风格、手法等语言方式上,都不可能超越文人画的男性审美尺度,而且,最能体现文人士大夫退而“寄情山水”的“避世”心态,也即最能体现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的山水画,在闺阁绘画中几乎见不到。
二、通过革命标准的女性价值与半边天艺术
19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的现代艺术潮流中有几个女画家,凭着自己的特殊背景和才情,得以与少数海外归来的男性画家一样,接受并学习西画。尽管她们的艺术尝试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所画的题材虽未能超出花花草草的闺阁绘画范畴(附图5),在当时已属十分难得。
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始终被“革命”的主线贯穿着。无论是前半个世纪的“拯救民族危亡”,还是后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都是围绕着不同的革命需要,女性价值当然也必须通过革命标准才能得以体现,妇女解放都是为革命的而不是为妇女的。这种妇女解放,即“妇女能顶半边天”,依据的是一种绝对平等的无性别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即是以这种完全男性化的标准要求自己,摈弃一切女性化的因素,从外表到灵魂,从言行方式到衣著打扮,“革命女性”没有自己的标准可依,只有一切都向革命的男性看齐,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男人、女人都必须走入革命化模式。革命的妇女艺术同样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强调“革命性”内涵和强调男性化审美特征。我们可以从不同革命时期女性的形象及其她们的艺术作品中(1920-1930年代民主革命时期:附图1;1940-177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附图6,8),看到这种半边天艺术模式的一致性和联贯性。
三、女性价值的重新陷落与闺阁绘画的现代翻版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首先山现的社会背景即是“人性复归”。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绝对平等的“无性别”原则规范下,以牺牲自己女性本性为代价,吃力地顶着“半边天”的妇女,不用任何的宣传和运动,也没有任何的口号和说法,就本能地渴望把自己还原成为“女人”。然而,除了传统的女人模式,她们依然是没有别的标准可依,所以,这一“还原”在观念上又几乎回到了女人的传统规范角色中。女性价值重新陷落。1979年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几乎把中西方古代艺术传统、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各种流派和样式都翻用和尝试了一遍。然而,摆脱了革命现实主义男性标准的同化,她们依然找不到可以泊靠的女性堤岸,对功利主义的避之如虎,使她们连社会题材都害怕触及;更加无样可依、无家可归的状态,使她们在艺术观念上又几乎自觉不自觉地回归到传统艺术的家园,几乎是闺阁绘画的现代翻版。这种“新闺阁画”有着千篇一律的共同特点:题材上强调画生活——花花草草,纯情少女、温馨母子;观念上视纯情纯真为最高的审美境界——阳光灿烂、优越闲散、美梦甜腻(附图4、7、9)。看不到女性意识的突破和对当代女性生存状况、当下女性问题的追问、个体生命感觉的反映,总而言之,与中国当代文化尤其女性文化无关。语言模式尽管使用的手法看上去“多种多样”,但既没有逃离各种公共化的传统语言模式的藩篱,也很少同期男性艺术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段的模仿性尝试,以至于整个1980年代中国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思潮中,几乎见不到女性的身影。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新闺阁画”的观念,如同畸形的遗传基因,一直延伸给了下一代乃至几代女艺术家。如今大多数至今依然在这种观念下创作和生活。
四、女性价值的重新追问与女性方式的个人化
无论是在古代的艺术传统,还是在近、现代的革命艺术传统中,中国妇女艺术的观念始终围绕着男性话语的圈圈打转。妇女艺术创造对男性话语的习惯和依赖,也使得女画家们对自己的处境和自我意识无知无觉,“从男性话语模式中分离”的观念往往是她们感到恐慌,她们担心这样做会完全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长期以来,她们的价值只有通过男性话语体系得以体现,一旦离开了这种价值体系,她们甚至会变得手足无措,这使得她们在探索自我发现、自我表达的道路上裹足不前。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不断发展和西方女性艺术信息的断断续续的流入,一些女艺术家感到不满足,在作品中尝试一些改变,但重新寻找女性“自我”的路,她们走得并不容易。一些女艺术家借他人的外衣暖自己的身体,在驾轻就熟的写实主义技巧基础上,做一些特别的处理,以表达作为生存在现代社会女性的内心感觉和自我意识;另一些女艺术家则接受了有限的西方女性主义艺术信息的影响,凭借自身的直觉和才能,关注女性自身的体验和经验,并探索超越公共语言模式的表达方式。19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艺术作品出现了更为主动的探索迹象,女性艺术问题也在整个当代艺术潮流中日趋重要。一些女性艺术家,开始摆脱类同的女性特质的困扰,更深层地寻找自我,并在寻找个人方式的道路上逐渐成熟起来。1990年代后期,更年轻的女艺术家逐渐成长起来,幸运的是,她们从一开始就懂得寻找个人的或女性的触点思考和创作,很快进入“角色”,但能否成为出色的艺术家,还有待于今后在更漫长的创作道路上的不懈努力。这些1970年代山生的“新新人类”女孩,既没受到过多传统的男女不同的规范暗示,也没受到太多“文革”时的男女绝对平等的阴影笼罩,她们的成长于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成熟于日趋国际化的信息时代,不仅重视个人化的美丽、享乐成为可能,而且强调个人化的意识、成功也是必然。正视自身的存在,不再刻意强调和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对她们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一些带有不言而喻的“冒险”色彩的禁区:如以女性身体为媒介和符号,对性心理和感觉的表现等,也被她们大胆闯入。一些更为年轻的女艺术家,则以看似轻松的“游戏”化方式,表达出她们对现代生存的特殊感受,如甜蜜的伤害感等。(附图10、11、11,13、14)
女性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出现大约十年了,但在我的印象里,我们这个自诩前卫的当代艺术批评的圈子,还从来没有过关于女性问题的正面讨论。女性艺术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车面的状态。我个人的双重的女性身份——女的、女性艺术的批评家,使我成了这个圈子里的“稀有动物”,也使我必须遭遇和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我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一直很孤独。当然,如我前面所说的,女性艺术从来不是—个单纯的艺术问题,它甚至首先是—个“女性价值”的问题,而关于女性的题目从来都是有争议的,没有结论的,不可能说出真理来的,但这种争议性正是女性问题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年来,我—直期待当代艺术中女性问题的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