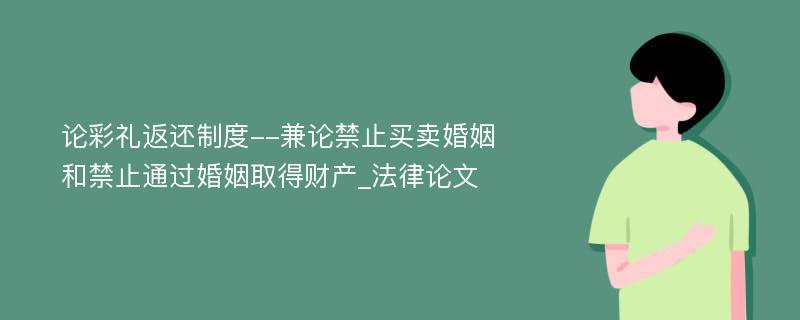
彩礼返还制度研究——兼论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婚姻论文,彩礼论文,财物论文,买卖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婚姻案件中聘金或聘礼处理原则的指示》(1951年10月8日)(以下简称为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聘金或聘礼的几个疑义和早婚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51年12月3日)(以下简称为1951年《聘金或聘礼的复函》)第3条之规定,“男女双方均以婚姻为目的”①而给付的“聘金或聘礼”,依其性质可分为以下三类:①“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②“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②③“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依据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在婚姻法施行后给付的聘金或聘礼具有以下法律效力:①对于“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原则上均应将其因此所得财物没收,并得酌情处罚”(第3条)。就何谓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1979年2月2日)(以下简称为1979年《民事意见》)“(三)买卖婚姻问题”第4段规定了以下两项:1)“对尚未结婚或者结婚时间不久,情节较轻的,其财物可不予没收。其中确因买卖婚姻造成了男方生产、生活上的严重困难,可让收受财物的人酌情返还一部。但不能因返还财物妨碍婚姻自由,或者再次造成买卖婚姻;”2)“对共同生活多年、生有子女的买卖婚姻,其财物不予没收,也不予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以下简称为1984年《民事意见》)第17条仍然规定,“属于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离婚时,原则上依法收缴”;②对于“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得斟酌具体情况及情节轻重予以没收,并得予当事人以教育或必要的惩处”(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2条)。1979年《民事意见》彻底改变了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2条的立场。它规定,“那种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但女方向男方要了许多财物,或父母从中要了一部分财物的……不要以买卖婚姻对待。如因财物发生纠纷,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1984年《民事意见》第18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1993年11月3日)(以下简称为1993年《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意见》)第19条第1款与之相同。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没收“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和“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的立法理由是:“给付的一方就不单纯是一个受骗的人,而自己也有了违法行为”(1951年《聘金或聘礼的复函》第3条);③对于“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原则上均不许请求返还。但如给付之一方在经济上特别困难而收受之一方又有返还能力者,则在确保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得对给付之一方酌予照顾,判令收受之一方返还全部或一部”(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4条)。1993年《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意见》第19条第2款规定,“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以按赠与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3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为《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第2款规定:“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既然在法律效力方面“彩礼”和“聘金或聘礼”如此地不同,那么《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所称的“彩礼”与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所称的“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是什么关系?返还彩礼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有过错方是否可以请求返还?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彩礼”与相关财物之间的关系
(一)彩礼的解释
按照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所称的“彩礼”应做出以下解释:(1)给付和受领彩礼的主体不限于双方当事人。“就给付人而言,既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也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的亲属……包括其父母兄弟。”“就收受该彩礼方而言,既包括……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也包括其亲属”;③(2)给付彩礼方在主观上是非自愿的。“一般来讲,这种彩礼的给付,都是非自愿的,往往迫于当地行情及社会压力而不得不给。”④因此,这种彩礼的给付“与一般意义上的无条件的赠与行为不同”。如果就后者发生纠纷,“只要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其当初所为的是一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现已经履行完毕的,则是一件普通的赠与纠纷案件;”⑤(3)彩礼主要归女方娘家。彩礼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付给女方的娘家了,真正用于其结婚置办各种物品的反倒很少。”⑥(4)彩礼在数额上往往很大。“给付的彩礼,多为金钱,也有一些贵重物品。由于各地方情况不同、当事人条件的差异等因素,彩礼的数额及价值也不尽相同。但普遍看来,相对于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而言,给付的数额往往很大。有的当事人为了能满足这一要求,不得不全家举债,负担较重。”⑦(5)彩礼尽管在性质上不属于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和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但是有时候有交叉。“彩礼,与借婚姻索取财物、包办买卖婚姻等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⑧尽管“彩礼有时候会成为包办、买卖婚姻或者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这时,对于彩礼问题的处理已经被比其行为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所吸收,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民间风俗,是属于触犯了法律规定,依法要被禁止的行为。对当事人的处理就已经应该作为借婚姻索取财物被禁止、作为包办买卖婚姻被禁止,而不再是简单的彩礼应否返还问题。”⑨
综上所述,彩礼可以定义为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主要指男方)及其亲属依据习俗向对方(主要指女方)及其亲属给付的钱物。依据收受主体的不同,它可以分为“女方获得的彩礼”和“女方亲属获得的彩礼”两类;依据财产的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分为“贵重物品式的彩礼”和“金钱式的彩礼”两类。
(二)彩礼与“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的关系
1.“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解释
按照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应做出以下解释:(1)“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是以立法者或准立法者将“聘娶婚之性质”确定为“买卖婚”为前提的。中国长期以来均实行聘娶婚。“周兴以后,既于礼制上奠定聘娶婚之基础,汉、唐以来,复于法制上保障聘娶婚之程序,故后期型之嫁娶方法,实以聘娶为主……遇有不经聘娶之方法而卖婚者,法律亦大都予以禁止……虽有时于聘娶婚中杂人掠夺或买卖之行为,此不过两种方法之结合,仍以聘娶方法为外壳,亦不得谓其即为掠夺婚或买卖婚也。”⑩“聘娶婚之意义”“即系以媒妁往来传婚姻之言,纳币而为婚约之形成,告鬼神藉示婚姻为两族之事,则父母之命自亦在其中矣。”(11)“聘娶婚之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两面性。“聘娶婚虽以买卖婚为其渊源,且留有买卖婚之痕迹甚强;然既以‘聘’与‘买’分,并依‘礼’而成之,即不得再以买卖关系,解释聘娶婚之性质也……固为契约,契约不限于买卖;斯婚约亦不得即认为买卖。纳征所以证婚约之成立而已,玄熏束帛非身价也……观于唐宋明清各律对于婚姻之请求,以曾否设定婚书或授受聘财是断,而所谓聘财者,并不拘多少,即受绢帛一尺以上亦然,可知其更远于买卖形式,而为纯正的婚约关系矣。故纯正的聘娶婚所异于现代志愿婚者,不过属于两族或两家之契约,非尽以男女两方之意志为主已耳。”(1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一直明确地或默示地将“聘娶婚之性质”确定(“指为”)为买卖婚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1年12月26日)第8条规定,“……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它很可能就是第1条“……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的具体化。“1942年,赤水县政府二届二次议员大会通过‘严禁买卖婚姻’法律议案。但在该法律议案的实施中,政府发现‘暗中偷卖、偷买仍然发生’。赤水县查出几起买卖婚姻案,但买卖婚姻的得款‘是否由公家没收’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故上报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将呈文移边区高等法院。”边区高等法院《对于赤水县询问买卖婚姻价值款应否没收问题的意见》指出:
制度的改善,是要随一般的教育文化生活的提高,方能得到实际的效果,如果文盲生活,尚未达到某一阶段,而骤然绳以严峻的法律,就会发生以下的事态:①公布的法律与隐蔽的事实,有完全处于相反的趋势,结果,不合法的事实,并不能减少,而法律徒成为扰民之具。②尤其是在边区的环境,与顽区相接近,政府取缔检查如果过严,一般无知的人民,容易对政府引起不满,无形中发生一种远心力,离避边区,去到顽区作婚姻买卖行为,所谓为丛驱爵,是值得注意的。③婚姻上的聘礼,在法律上势难予以一定数目的限制,富家多出,贫家少出。目前边币贬值,一万元边币,合之从前现银,不过值得三、四百元,表面数目虽大,实际上不过够办衣物首饰数事,我们如果硬指为是买卖婚姻的代价,是不足以折服人的”,因此,“在审判上关于这类的事件,是采取以下的适应方法:①是以非亲告不理为原则。②如果发生纠纷,成为诉讼,法院只审查他们的婚姻本质上有无瑕疵,如男女婚姻资格,是否重婚,年龄是否相当,女方是否同意,手续是否全事,是否威胁、抢夺、诱骗。如婚姻本质上无瑕疵,聘礼数目虽多,亦是有效。如有瑕疵,即应宣告婚姻无效,聘礼返还不予没收。
该项司法解释尽管出于某些考虑最终未将聘礼作为买卖婚姻的价款予以没收,但是它的确试图将聘娶婚定性为买卖婚姻应该是没有疑问的。“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司法处”在其“总结材料”中指出,“陕北一般婚姻多系旧式的买卖婚姻,一般男子要娶一个女人非花一定的聘礼不可(此话固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事实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是这样办的。”(13)《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1950年4月14日)(以下简称为1950年《婚姻法起草报告》也明确指出,“受旧社会婚姻制度习惯感染的婚姻当事人及其亲属们的关心和负责,往往是……贪图某些眼前小利的。”“中国几千年……男女婚姻关系……是撇开双方本人的黑市交易和以物易物交换。”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1条明确规定,“……所谓买卖婚姻就是婚姻法第2条所禁止的‘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上述文件更加明确地表明,聘娶婚的性质被确定为买卖婚姻,聘金或聘礼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买卖婚姻的”价款。当然,1979年《民事意见》做出缓和性的规定,而不再将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所称的“变相的买卖婚姻”认定为“买卖婚姻”。1980年《婚姻法》和现行《婚姻法》从之。如果不将“聘娶婚”认定为“买卖婚姻”,“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就无从谈起。
(2)获得该项财物是以“索取”而不是“主动”或“自愿”给予为前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第2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最高法院《关于军人婚约和聘礼问题的复函》(1951年6月1日)明确指出,“如聘礼系由订婚人父母或男女双方出于自愿帮助或赠与”,则不属于“公开的买卖婚姻”;反之,如系“索取的财物”则属之。依据1979年《民事意见》之有关规定,“……男女主动互相赠与和赠送对方父母的财物……”与“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具有根本区别。所谓“索取”,就是指“要”,(14),所谓“要”,就是指“因为希望得到……而有所表示”。(15)
(3)“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的真正获得者是女方的父母或寡妇的公婆。在旧中国,“结婚之际,男女两家尤其是男家,要支出巨额的费用……除去仪式本身所消费的,再加上筹办嫁妆即:在男方家则为向女方家交纳的聘财、在女方家则为‘嫁奁’,就构成结婚费用的主要内容。可是,似乎聘财被认为是女方的身价,并屡屡有金钱被交付之事发生;同时因为其数额经媒人数次介入牵线交涉并被约定,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少见。这似乎很容易让人坚信,在中国婚姻制度之中存在着浓厚的买卖婚姻的要素,但是事实绝非是一概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聘财一旦由男方家支出,不久就会变为新娘的随嫁财产,又回到男方家来。以上所说的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聘财变成随嫁财产又回到男家去,即使这样讲,当然它也没有进入男家的财产中,而是作为该夫妇的特有财产留下……总之,其讨价还价的交涉,应该是企图能确保女儿夫妇多分摊一些,绝不是交涉女儿的卖价。”(16)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迫于贫穷而被欲望束缚的父亲将聘财装进自己的腰包,若不让他负担与聘财相抵的、足够的随嫁财产,则此时他才是‘卖女儿’。”(17)可见,聘财的“索取者”不一定就是获得者。依据解放之前的边区高等法院《对于赤水县询问买卖婚姻价值款应否没收问题的意见》之立场,无论聘礼最终归谁所有,都属于买卖婚姻。不过,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做出缓和,而将“以索取对方一定的财物为结婚条件”定性为“变相的买卖婚姻”(第1条)。因此,只有女方父母获得的彩礼方属“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此外,聘礼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即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1条所指的“嫁寡妇要身价”。它是指“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而获得的“财礼”。(18)
2.“彩礼”与“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的关系
由于“彩礼,亦称‘财礼’、‘聘礼’、‘聘金’‘聘财’”(19)因此,“女方亲属获得的彩礼”也可称为“女方亲属获得的聘财(聘礼或聘金)”。由于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将父母嫁女儿获得的聘金或聘礼定性为“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因此“女方亲属获得的彩礼”也就应该定性为“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两者根本不是平面交叉关系。
3.法律漏洞的补充
依据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1条、第3条之规定,“女方父母获得的彩礼”是“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原则上均应将其因此所得财物没收”。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之规定,“女方父母获得的彩礼”在一定条件下应该返还。这构成了法律漏洞。
在此情况下,应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的规定。其理由是:(1)将“聘娶婚之性质”定性为“买卖婚姻”并不正确。“买卖婚姻”是指“以财物购妻”,它与“交易婚”和“劳役婚”共同构成“有偿婚”。(20)“买卖婚姻”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要件:①收受财物的第三人应该享有“主婚”权。“买卖婚”“依主婚人之意思而成立婚姻关系”;(21)其实质是以财物购得“主婚权”,类似于以价款购得所有权;②人口可以合法买卖。“交付”的“财物”“视之为对价”。(22)“男人买得他的妻子,她因此就成了他的财产。这种新妇的购买,在一切条顿人中,蛾特人、诺曼人、丹人(Danes)、萨克逊人(Saxons)、盎格罗萨克逊人(Anglo-Saxons)以及南部高地日耳曼人、佛兰克人、勃艮弟人以及伦巴德人(Lombards)之中,都可看到……我们祖先的婚姻,是一种真正的生意业务,新妇只是一种买来的货物……萨里及伦巴德的法规中的reipus(钱串)即是新郎放在他妻子指上的卖价。所以最古的结婚戒指,就是妇女的肉体、她多产的子宫及她多忙的手脚的价格;”(23)③妇女无论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买卖婚姻起源于野蛮的部落……也是与奴隶制(institution of slavery)联系在一起的”(24)“购买来的新妇,从她父亲势力之下转到丈夫势力之下了。她的丈夫可以打她……可以将她给予另一个人,可以在某种情形下杀死她。”(25)这些条件在新中国已经不复存在:①1950年《婚姻法》第3条、1980年《婚姻法》第4条、现行《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也就是说,家长或寡妇的公婆没有主婚权;②其次,禁止买卖人口。依据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刑法》第141条、现行《刑法》第241条的规定,禁止买卖人口。即使出卖亲生子女,也是违法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3月20日)(以下简称为2000年《打击拐卖的通知》)第4条规定,“……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③1950年《婚姻法》第1条、1980年《婚姻法》第2条第1款和第2款、现行《婚姻法》第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而且,实行“买卖婚姻”的结果就是建立“早婚(child marriage)的习俗”。(26)其理由是“女儿年龄越大,就越不值钱”。(27)而新中国婚姻法禁止早婚。1950年《婚姻法》第4条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1980年《婚姻法》第5条和现行《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其实,在聘娶婚中,“夫对于女家,仍须交付财物,但仅作为礼物,不视之对价,故与有偿婚不同”,(28)根本不应该定性为“买卖婚姻”。而且,如果定性为买卖婚姻,还会带来隐患。由于婚姻法“禁止买卖婚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之规定,女方父母收取彩礼的行为因“违反法律”而无效,并应该依据第61条第1款的规定予以“返还”。(29)这会给夫妻之间、一方与对方的家庭之间、双方的家庭之间埋下纠纷的种子;(2)依据“六礼”(包括给付“彩礼”)这一“礼俗”结婚并不等于违反婚姻自由。1950年《婚姻法起草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的“第一个特点,当然应该是男女婚姻自由。在这种新婚姻制度下,在男女婚姻问题上,任何人出来包办强迫的办法,任何第三者的人或‘神’的干涉行为,都不应有存在的余地。男女结婚,只能是双方本人完全自愿的夫妻关系的自由结合。”建国之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没有理由证明结婚时如果给付彩礼,就会违反婚姻自由。依据1999年对于河北省满城县黄龙寺村的婚姻行为的实地调查,尽管人们依然依据“六礼”礼俗结婚,在结婚问题上,“自己作主”、“自己作主、父母同意”、“父母同意、自己作主”三者合计所占的比例;于“1950-1965”年之间是75%;于“1966-1979”年之间是61.1%;于1980年以后是66.7%。(30)即使是“父母作主”,由于“亲子间自然之爱出于天性”,(31)父母一般不会损害子女的婚嫁利益。总之,孟子所谓的“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32)恐不为过;(3)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不具有可操作性。1950年《婚姻法起草报告》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下,“任何财物的多寡,任何门第的高低,都不应再成为男女结婚关系的基础。任何珍贵之物,都不能作为男女相互爱情的替代物或交换品。基于共同生活(包括共同劳动等)共同事业(包括对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态度等)而引起的相互了解特别友谊所形成的相互爱情,是男女结婚的基础,也是婚后夫妻关系持续的基础。”由于“结婚”的法律性质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因此,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实质是要求结婚“意思的形成”必须受“爱情”这一“考量因素所左右”。(33)它属于对“动机”的要求。(34)由于动机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且在从事法律行为时又无需表示它,因此是很难操作的。更何况建国以后的《婚姻法》只要求“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婚姻登记机关在审查当事人双方的结婚登记申请时,也只审查双方是否自愿(《婚姻登记办法》(1986年3月15日)第6条第2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2月1日发布)第12条第2项、《婚姻登记条例》(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第6条第2项)。(4)女方父母获得彩礼无可厚非且没收会加重女儿的负担。对于“公开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3条规定,“原则上均应将其因此所得财物没收。”1984年《民事意见》第17条规定,“离婚时,原则上依法收缴。”该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村的生活实际。“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决定了农民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并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但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基本也是在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赚钱,由于他们的文化层次较低,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逐年降低,所获收益也会随之减少。等到老年,农村中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晚年生活无法得到保障。”(35)因此,起着将未来债权转化为现实物权作用的聘礼本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0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在老年人死亡时,已经出嫁的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对于所继承的遗产,依据1950年《婚姻法》第10条、198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1984年《民事意见》第12条、现行《婚姻法》第17条第1款第4项之规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依据1950年《婚姻法》第13条第1款、1980年《婚姻法》第15条第1款、现行《婚姻法》第21条第1款之规定,出嫁的女儿对父母仍有“赡养”的义务;依据1980年《婚姻法》第15条第3款、现行《婚姻法》第21条第3款的规定,赡养请求权的发生要件是“父母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如果予以没收,赡养请求权就更容易发生,从而会加重女儿的负担;(5)“索取”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因为“一方索财,如果对方不同意,自然索财不能成功。只有在对方愿意的情况下才可实现。”(36)
4.“禁止买卖婚姻”条款的废除
1980年《婚姻法》和现行《婚姻法》第3条第1款规定,“禁止……买卖婚姻……。”它与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1条所称的“公开的买卖婚姻”相当。依据1950年《婚姻法起草报告》,被定性为“公开的买卖婚姻”的行为除了“嫁女儿”“要身价”和“嫁寡妇要身价”之外,还包括“出财物买妻子”和“贩卖妇女与人为妻等”。作为“聘娶婚”的前两者不应该定性为“买卖婚姻”,已如前述。后两者更不应定性为“买卖婚姻”。“出财物买妻子”无疑地应该是指或至少主要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991年9月4日)(以下简称为1991年《严惩拐卖犯罪分子的决定》)第3条所称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现行《刑法》第241条第1款所称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将其排除的理由是:①收买行为和结婚行为具有本质区别。1991年《严惩拐卖犯罪分子的决定》第3条第2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第3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虐待等犯罪行为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第4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并有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犯罪行为的,依照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现行《刑法》第241条第2、3、4款与之类似。而且,如果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1991年《严惩拐卖犯罪分子的决定》第3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现行《刑法》第241条第6款与之类似。很显然,收买行为不同于结婚行为。其实,只有被买妇女在威逼利诱之下同意办理结婚登记甚或同意为事实婚姻,婚姻才能成立;②被买妇女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公安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通知》(1991年10月5日)第4条规定,“……对其中在拐卖前系成年未婚妇女,按照其本人意愿要求留下的,可依照婚姻法有关规定处理……”。2000年《打击拐卖的通知》第6条第2款规定,“……对于自愿继续留在现住地生活的成年女性,应尊重本人意愿,愿在现住地结婚且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应当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拐卖妇女与买主所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由人民法院裁决……”。依据现行《婚姻法》第11条的规定,被胁迫结婚的法律效力仅仅是可撤销。如果“禁止买卖婚姻”属于强行性的条款,其婚姻就应该是无效的。③《婚姻法》规定禁止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实为越俎代庖。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刑事法律还不完善时由《婚姻法》规定禁止拐卖妇女还无可厚非,那么在1991年《严惩拐卖犯罪分子的决定》第6条第1款就明确规定“拐卖……妇女……的非法所得予以没收”之后,《婚姻法》还继续保留该规定就不能原谅了。
“贩卖妇女与人为妻”无疑应该是指1991年《严惩拐卖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所指的“拐卖妇女”和现行《刑法》第141条所称的“拐卖人口”。所谓“拐卖人口”,依据1984年《办理拐卖人口案件解答》第1条第1款的规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用欺骗、利诱、胁迫等手段主要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84年3月31日)第1条第1款规定,“拐卖人口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用欺骗、利诱、胁迫等手段主要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将其排除的理由是:①收买行为和结婚行为拥有本质区别。依据1991年《严惩拐卖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款4项的规定,拐卖人口的目的还可能是“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现行《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与之相同。拐卖妇女只是为收买人与被拐卖的妇女建立婚姻关系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这一行为相比,拐卖妇女这一行为与婚姻的成立相距更远。既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本身都不能构成买卖婚姻,拐卖妇女本身就更无从构成买卖婚姻。可能是由于这一原因,边区高等法院《对于赤水县询问买卖婚姻价值款应否没收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贩卖妇女与人做妾或婢或操娼妓营业的行为,这不是婚姻问题。”(37)②在司法实践中,即使被拐妇女已经成婚,也没有追究拐卖者之干涉婚姻自由的责任;③《婚姻法》规定禁止拐卖妇女也是越俎代庖。
(三)“彩礼”与“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的关系
1.“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解释
依据文意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应做出以下解释:(1)“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也是以立法者或准立法者将“聘娶婚之性质”确定为“买卖婚”为前提的。如果不将聘娶婚在性质上认定为买卖婚姻,“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也就无从谈起。
(2)获得该项财物也是以“索取”而不是对方“主动”或“自愿”给予为前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第2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最高法院《关于军人婚约和聘礼问题的复函》(1951年6月1日)明确指出,“如聘礼系由订婚人父母或男女双方基于自愿帮助或赠与”,则不属于“变相的买卖婚姻”;反之,如系“索取的财物”则属之。依据1979年《民事意见》之有关规定,“……男女主动互相赠与和赠送对方父母的财物……”与“女方向男方要了许多财物,或父母从中要了一部分财物”具有根本区别。
(3)“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获得者应是女方本人。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1条将“以索取对方一定的财物为结婚条件”认定为“变相的买卖婚姻”。它比较明确地暗示着“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获得者是女方本人。而1979年《民事意见》认为,“女方”的“父母”也可以是获得者。这一规定不妥。其理由是:①它不符合“聘娶婚”的特征。“纯正的聘娶婚所异于现代志愿婚者,不过属于两族或两家之契约,非尽以男女两方之意志为主已耳。”(38)换言之,双方结婚是为当事人双方本人或其家长所不反对的。由于“纳采”(依据现代民法,在性质上应属附卜得吉兆为条件的同意)“问名”、“纳吉”(依据现代民法,在此时“婚约”已经成立)在先,而纳征(即交付聘财)在后,还由于“纳征”只不过起是否“许嫁”,即婚约是否成立的“证明”作用,因此聘财的交付其实是建立在合意基础之上的。只不过由于在聘娶婚中女家向男家“索取”了聘财,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将其定性为“买卖婚姻”;由于在聘娶婚中存在“父母之命”,(39)所以又将其定性为“包办强迫婚姻”。而1979年《民事意见》却认为,只有“买卖婚姻”(即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所称的“公开的买卖婚姻”)才是“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的,才是“包办强迫”婚姻,而“借婚姻索取财物”(即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所称的“变相的买卖婚姻”)是建立在“婚姻基本上自主自愿”基础之上的,显然违反了立法本意;②以“财物数额”为准划分“公开的买卖婚姻”和“变相的买卖婚姻”也不科学。1979年《民事意见》认为,如果财物数额是“大量”的,则构成“公开的买卖婚姻”;如果是“许多”的,则构成“变相的买卖婚姻”。由于从后果上看,国家对前者的责难程度要远高于对后者的,因此“大量”要比“许多”高。而在实践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成婚支出的费用要远远低于男家在正常订婚过程中支出的。(40)③由于婚约在民事上没有法律效力,由于违反妇女意志的性行为构成强奸罪等原因,男方一般不会盲目地、冒险地向女方家给付大量钱财。因此,女方父母先“包办”(41)订婚、然后收取彩礼,如女孩不从则进行强迫恐怕也不多见。
2.“彩礼”与“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的关系
由于“彩礼”与“聘金”或“聘礼”只不过具有名称上的差别,因此女方获得的彩礼也就是女方获得的聘金或聘礼。由于女方获得的聘礼依据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被认定为“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因此,“女方获得的彩礼”之法律性质也就是“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1984年《民事意见》第18条将“女方获得的彩礼”在内的财物统称为“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
3.法律漏洞的补充
在离婚时“女方获得的彩礼”之返还问题上,1984年《民事意见》第18条和1993年《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意见》第19条第1款与《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尽管总体上一致,但还是具有以下细微的区别:(1)返还的条件不同。前者是:①“结婚时间不长”;②“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后者是:①“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②“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2)返还的范围不同。前者只需“酌情返还”,后者没有这一限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女方获得的彩礼”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系平面交叉关系,因此不能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处理,从而构成了法律漏洞。
在此情况下,原则上应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之规定。其理由是:(1)“结婚时间”长和不长忽视了“金钱式的彩礼”在财产形态上的转化。在古代,女方获得的聘财具有“每一代人日用器具更新费的特质”,是用于购买“室内的日用器具、铺盖、盛装使用的衣服等等”的,在“并不富裕的普通家庭”中,“大部分一生只有一次机会来筹办”。(42)今天依然如故。“彩礼所包含的项目:家用电器属于耐用消费品,可以长期消费;日常生活用品和大批量购进的服装也是为留待日后慢慢使用,亦属长期消费,等等。从本质上说,彩礼本身,即是为将来消费所进行的‘储蓄’”。(43)一般而言,当事人应该只有临近“成婚”,才会以“金钱式的彩礼”购置。换言之,只有在“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情况下,“金钱式的彩礼”才没有转化为双方共同生活用的或女方专用的财物,才可能返还。而一旦共同生活,无论长短,其大部甚或全部就已经转化为财物;(2)以“给付人”而不是“对方”生活困难为条件更为科学。因为“彩礼”一般而言,是从“男子”的“家产”(43)——应该主要是男方父母的共同财产——支付的,因此不能以“对方”作为判断标准。不过,在返还时,法院确实应该考虑“金钱式的彩礼”是否消耗、消耗的比例等具体情况。
4.“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条款的废除
尽管1979年《民事意见》、1980年《婚姻法》、现行《婚姻法》不再像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那样,将“女方获得的彩礼”定性为“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而予以没收,但是“变相的买卖婚姻”仍然为1980年《婚姻法》和现行《婚姻法》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种形式保留下来。它应该得到废除。其理由是:(1)它违反了农村的生活实际。1950年《婚姻法起草报告》明确指出,“人民自己”将“结婚”“重视为终身大事”。因此,在结婚之际,购置新生活用品乃是顺理成章的。新生活用品固然可以由夫妻双方购置、日后购置,然而“在农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风险太大,女性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性,决定了她出于日后生活保障这一动因而向男方索要彩礼的行为。”(45)而且,“金钱式的彩礼”购置的财物多“留置”在男家,因此他们一般不会遭受不可预测的损害。(2)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由于支付巨额彩礼的人多为男方父母,因此他们如何安度晚年的确令人担忧。不过,依据《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第2项“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老年人可以撤销赠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该规定可以适用于儿媳和公婆之间;(3)由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与“禁止买卖婚姻”一样,属强制性法律规范,因此它也同样为当事人“带来隐患”。
(四)“彩礼”与“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的关系
1.“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解释
按照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的方法,“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可以作出以下解释:(1)依据1979年《民事意见》之有关规定,获得“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主体既包括双方当事人,也包括“对方父母”。
(2)受赠人获得赠与物是建立在赠与人“主动”赠送的基础之上的。
(3)依据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4条之规定,它既不是附条件,也不是附义务的,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应该返还的。而且,该条件不同于《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撤销赠与的条件。
2.“彩礼”与“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之间的关系
由于“给付彩礼方在主观上是非自愿的”,而不可能是“主动的”,因此,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3.“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制度的法律漏洞
“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制度的法律漏洞是:(1)在法律效力方面,附条件的赠与应该排除而未排除。依据《民法通则》第62条的规定,民事行为可以附条件。因此,赠与合同可以附停止条件或解除条件。而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4条规定,“赠与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原则上均不许请求返还”。很显然,附停止条件或解除条件的赠与应该排除而没有排除;(2)它与《合同法》之有关规定相互矛盾。依据《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无附款的赠与合同一经履行,赠与人便“无偿”取得了“财产”;依据《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第1项、第2项的规定,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情况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依据《合同法》第194条之规定,撤销赠与之后,赠与人可以请求返还。而1951年《聘金或聘礼处理的指示》第4条规定的返还要件是“给付之一方在经济上特别困难而收受之一方又有返还能力”者,返还的范围是“在确保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判令收受之一方返还全部或一部”。
(五)聘金或聘礼制度的应然状态
如果未来的立法放弃将“聘娶婚”定性为公开的或变相的“买卖婚姻”之立场,放弃将聘金或聘礼定性为公开的或变相的“买卖婚姻的代价”之立场,由于获得聘礼的一方属无偿获得,因此就应该依据《合同法》第185条之规定,将聘金或聘礼定性为“赠与物”。依据《民法通则》第62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之规定,聘金或聘礼可以分为附条件的聘金或聘礼和不附条件的聘金或聘礼两类。对于前者,在停止条件或解除成就时,获得者就应该返还;对于后者,按照《合同法》撤销赠与的有关规定返还。
三、返还彩礼的请求权基础
(一)比较法的考察
所谓请求权基础,是指“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请求特定作为或不作为之法律规范。”(46),就返还彩礼的请求权基础,罗马、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的立法可以分为“给付目的不达”之不当得利和“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当得利”两类立法模式。前者建立在“彩礼”之法律性质被确定为附停止条件的赠与之上;后者建立在彩礼之法律性质被确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之上。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将给付彩礼定性为附条件的赠与有“推定”和“拟制”两种途径。“所谓条件,系使法律行为效力之发生系于将来客观上不确定事实成否之附从的意思。条件本身亦为意思表示,而赠与又为契约,当事人必须合意,附条件之赠与始能成立。然而,交付聘金或礼物时,当事人明示约定附以解除条件者,其例绝少,因此此项附解除条件之意思表示,仅能依社会一般观念,认为系属默示意思表示。此种认定原属拟制,未必尽符当事人原意。”(47)
1.“给付目的不达”之不当得利
罗马法认为,彩礼属于“预期结婚而赠与”。如果“其后目的不能实现……为给付之一方得向受领给付之一方请求返还所受之利益”。(48)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之规定,婚约不履行时,关于婚约当事人间之“赠与”或“以为婚约之信证所与之物”,任何一方“得依不当得利返还之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49)此种不当得利在性质上也应该是给付目的不达之不当得利。1928年5月21日,日本京都地方法院认为,聘礼属于“以婚姻之成立为停止条件之赠与”。(50)而且,日本部分地方法院将“结婚”这一条件做了目的性扩张。首先,对于已经办理了结婚申报但持续期间短暂的婚姻,仍然要求受领方返还。1952年8月13日,“鸟取”地方法院在“自结婚时起一方就没有诚实地维持婚姻关系的意思,并应该认识到婚姻关系必定因此而终止”的案件中,认为“依据信义原则,参照婚姻关系不成立加以处理,受领方应负担返还之义务”。1962年8月8日,“柳川”地方法院在“婚姻即使在形式上已经成立,但由于夫妻生活持续期间短暂,事实上的夫妻协同体没有成立的”案件中,“参照婚约不履行加以处理,受领方应负担返还义务。”(51)其次,对于短暂的事实婚姻,仍然要求受领人返还。1928年5月21日,日本京都法院率先做出判决指出,“事实上的夫妻共同生活既然已经开始,交付订婚礼品的目的就已经完全实现。”1928年11月24日,最高法院支持了京都法院的立场,即原则上只要事实婚姻成立,给付方就不得请求返还。(52)1935年10月15日,最高法院修改了自己的立场。它指出,“事实婚姻虽然已经成立,但由于持续期间比较短暂,且双方感情不和,订婚礼品授受之增进双方情谊之目的没有实现,”因此,受领方应该像婚约解除时一样加以返还。(53)“神户”法院在1957年4月23日于事实婚姻只持续一个多月,“弘前”法院在1957年8月13日于事实婚姻只持续一个月的案件中,均支持了返还的请求。在美国,“在聘礼(engagement gift)系期待结婚而给予受赠人的情况下,大多数法院认为,尽管在形式上看是绝对的,但实质上是附条件的。婚约一旦违反,赠与人有资格请求返还。”(54)所附的条件属于停止条件。即“结婚是获得戒指的所有权的前提要件。只有交换结婚誓言,受赠人才能获得它的所有权。”(55)在条件的形式问题上,美国各州分为两类:其一是可以是“默示的条件”(implied condition)。“大多数法院承认以后结婚这一条件在性质上可以是默示的,”(56)“只要有优势证据证明礼物是基于期待结婚而给予的,就足以证明礼物是附条件的。”而且,法院还认为,“要求戒指的赠与人将‘如不结婚即不赠与’的愿望表达出来是过分苛刻的,也是不必要的。”(57)其二是必须是“明示的条件”(express condition)。“有少数法院拒绝将聘礼定性为以结婚为默示条件的聘礼。它们要求请求返还聘礼的赠与人证明聘礼曾经明确地附加结婚这一条件。”当然,依据判例,“明示的条件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来表达,而不是非通过明确的协议表达不可。”(58)
2.“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当得利
日本“神户”、“大阪”法院认为,订婚礼品属于或类似于以婚姻不成立为解除条件的赠与。(59)我国台湾地区1958年台上字第917号判例指出,“凡订立婚约而授受聘金礼物,固为一种赠与。惟此种赠与并非单纯以无偿移转财物为目的,实系预想他日婚约之履行,而以婚约解除或违反为解除条件之赠与,嗣后婚约经解除或违反时,当然失其效力;受赠人依第179条,自应将其所受利益返还于赠与人。”(60)我国台湾地区1958年台上字第1469号判例指出,“婚约之聘金系附有负担之赠与,上诉人既不愿履行婚约,则依第412条第1项、419条第1项,被上诉人自得撤销赠与,请求返还赠与物,纵解除婚约之过失系在被上诉人,亦仅生赔偿之问题,不能为拒绝之论据。”就附条件的赠与和附负担的赠与之间的关系,1966年3月28日,民刑庭总会决议认为,“为订立婚约所付之聘金,究系附有负担之赠与,抑解附有解除条件之赠与,本院1958年台上字第1469号与同年台上字第917号判例见解不同,应否删除,议决:两判例并存”。(61)由于“婚约则依民法第975条规定不得请求强迫履行,故惟有撤销赠与之一途”。(62)因此,附负担之赠与的返还最终同样应该依据“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而且,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结婚”这一条件或负担未做目的性扩张。1954年台上字第158号判例认为,“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恶意遗弃,经第一审判决离婚确定在案,其所收之聘金、饰物及支付之酒水费200元,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被上诉人应负返还之义务。按因离婚而消灭之婚姻关系,并无溯及既往之效力,在离婚前之婚姻关系既已成立,自不发生不当得利问题,上诉人所为不当得利之主张,殊难谓为有据。”1961年台上字第351号判例再次认为,“聘金乃一种赠与,除有解除条件之赠与于条件成就时失其效力,赠与人得依第179条之规定,请求受赠人返还其所受之利益外,不得以此为因判决离婚所受之损害,而依同法第1056条第1项请求赔偿。”(63)
(二)我国的请求权基础
1.彩礼的性质
最高法院认为,彩礼在性质上是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都不容否认和忽视。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如果没有结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64)而且,依据“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这一内容,“条件”在解释上应该包括“默示的条件”。而且,“结婚”这一解除条件也做了目的性扩张。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如果“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离婚时也应该返还。立法理由是:“如果一直没有共同生活的话,也就没有夫妻之间相互协助、共同生活的经历。所以,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虽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活还远没有开始。由于各地方的习惯不一样,农村及一些地方,往往更注重的是举办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婚礼,更注重的是两个人真正走到一个家庭中,开始共同生活。而且许多时候,举办这些仪式与登记结婚要隔很长时间,如果双方尚未共同生活的,也没有过多把双方共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65)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如果“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时也应该返还。立法理由是:“给付彩礼、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在一起后,由于双方性格不合等原因,加之生活困难等因素,结婚时间不长,双方就离婚了的,实践中也大有人在。而且由于给付彩礼,全家已经债台高筑,生活陷于困境,此时这些人也大多要求返还彩礼,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激化矛盾。”(66)
2.请求权基础
由于彩礼的法律性质被确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因此“当事人一方依照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向另一方为给付后,因为附解除条件成就,另一方因受领给付所获得之利益,失去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67)依据比较法的解释,此种不当得利当属“给付目的嗣后不存在”之不当得利。(68)不过,“由于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因此,对于彩礼中的“贵重物品”来说,“不当得利”属获得占有的不当得利,赠与人可以请求返还所有权。(69)对于彩礼中的金钱来说,“货币的所有权因为交付而发生当然移转(货币的持有人视为货币之所有人),此为公理性的原则,给付货币的一方没有请求所有权返还的基础。”(70)不当得利属获得所有权的不当得利,赠与人不能请求返还所有权。(71)
四、返还彩礼与过错
(一)比较法的考察
就返还财礼与过错的关系,即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的一方或由于自己的过错致使对方解除婚约者如系赠与人,能否向无过错的另一方请求返还,罗马、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的立法可以分为返还彩礼不受过错的影响和返还彩礼受过错的影响两类立法模式。
1.返还彩礼不受过错的影响
罗马“帝政”以前,婚约解除时,“对订婚时收受他方的礼物,应行归还”。(72)1967年7月31日,日本大阪法院判决认为,“只要将订婚礼品认定为有目的的赠与,在目的不达到的情况下,就不应该考虑责任的有无,而应认可返还的请求。”(73)依据我国台湾地区1958年台上字第1469号判例,返还彩礼也不受过错的影响。当然,受害人可以依据民法第978、第979条的规定请求损害赔偿。在美国,尽管大多数法院在解决聘礼纠纷时继续采用过错主义,但是“有少数法院追随无过错离婚主义,在解决订婚戒指的纠纷时,也采用无过错主义。”(74)1971年,纽约州在格登诉格登(Gaden v.Gaden)(75)案中率先确立了无过错主义。(76)此后,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堪萨斯州最高法院也采用了无过错主义,(77)宾西法尼亚州也采用了无过错主义。(78)美国少数法院采用无过错主义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男女平等。“过错主义是建立在男女不平等基础上的、过时的。它应该让位于无过错离婚法体现出来的中立主义”;其二是“它可以给负担已经过重的法院提供明确的原则,防止当事人陷入激烈的婚约解除诉讼之中”。(79)
2.返还彩礼受过错的影响
罗马“帝政”以后,“聘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生强制履行的效力,法律视不履行婚约有无正当理由而作不同的规定:男方无正当理由而毁约的,要丧失聘礼,同时应归还女方的全部赠与;如女方无正当理由而毁约,则不得收回赠与,除返还男方的聘礼外,还要另付四倍于聘礼金额的罚金,以后改为与聘礼相等的数额。”“男女一方因正当理由”“而解除婚约,则由双方互退聘礼和赠与”。(80)在婚约因给付方之过错而终止的情况下,日本下级法院的一般立场是对有责方之返还请求持否定态度。所持的理由主要有:首先,过错方请求构成“非礼”。“神户”法院在1952年5月26日判决认为,订婚礼品在性质上属结亲的标志,如果一方面给付方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婚约终止,另一方面又提出返还订婚礼品之请求,属于“非礼”;其次,过错方请求“违反信义原则”。“奈良”法院在1954年4月13日、“小仓”法院在1973年2月26日、“大阪”法院在1968年1月29日判决认为,有责方的返还请求违反信义原则;再次,“过错方应受制裁”。“大阪”法院在1966年1月1日判决认为,有责方应该受到制裁,因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在高级法院中,东京高等法院在1982年4月27日率先判决认为,如果准许有责方的返还请求,则违反了信义原则。(81)在美国,“无过错离婚法确立之前,在赠与方违反婚约(break engagement)的情况下,大多数法院(a majority of urisdiction)均主张或承认受赠人有权保有订婚戒指或请求返还它的价值,”(82)“很多法院(courts)认为,在受赠方违反婚约的情况下,对未婚妻赠与价值不菲且能长期保存的礼物之赠与方可以请求返还礼物。”(83)“目前,在解决戒指的所有权纠纷时,大多数法院仍然坚持过错主义。”(84)
(二)我国采用了无过错主义
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第1款的规定,返还彩礼不受过错的影响。因为“本解释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85)此种立法是正确的。因为彩礼属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不问过错的有无,均应该返还。当然,在婚姻解除损害赔偿制度(《婚姻法》第46条)的基础上,我国应该确立婚约乃至事实婚姻解除的损害赔偿制度。(86)否则,就是不公平的。
注释:
①1951年《聘金或聘礼的复函》第3条规定,“所谓伪装结婚骗取聘金、聘礼等财物的行为,与男女双方均以婚姻为目的之买卖婚姻不同,是以诈骗对方财物为目的,以伪作结婚为得到对方财物的手段,并无与对方有夫妻共同生活的意思。”
②1950年《婚姻法》第2条规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1980年《婚姻法》第3条第1款将其分解为“……禁止……买卖婚姻……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两项。现行《婚姻法》从之。
③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页104。
④同上注,页103。
⑤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0。
⑥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4。
⑦黄松有,见前注③,页90。
⑧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0。
⑨黄松有,见前注③,页99。
⑩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页90。
(11)同上注,页91。
(12)陈顾远,见前注⑩,页92。
(13)强世功:“权利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上)——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网址是:http://www.chinalawedu.com或http://article.chinalawin.cn。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1213。
(15)同上注,页1465。
(16)罗马法的“大法官法”鉴于“已解放和已出嫁的直系卑亲属,和仍处在家长权下的子女等一样享有对其父系血亲尊亲属的继承权,但前者的劳动所得,或者得到的赠与、遗赠以及嫁奁归他们自己所有,而仍在家长权下的子女等,他们的劳动所得和接受的赠与、遗赠等,都要放在家里归家长所有或用益。于是,产生了不公平现象”,而“创设一种‘财产加入’制度……一方面允许脱离家长权的子女等回到生父家继承其父的遗产,另一方面则要求他们将在脱离家长权期间的劳动所得或接受的赠与、继承的遗产等,加入其父的遗产中去,与其他继承人共同分配。可见,‘加入’制度的实质,是将所有直系晚辈血亲的财产都计入遗产的范围之内,让全体继承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分配遗产。”周楠:《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533。中国古代有的朝代似乎没有类似的制度,例如,《唐律·户婚》附《户令》规定,在继承时,“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不过,《宋刑统·户婚律》附《户令》却规定,“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参见孔庆明、胡留元、孙季平编著:《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330、页392-393。如果没有类似的制度或类似的制度落实不好,由于实质上全部或主要来源于男家的女方陪嫁财产不参加继承,于是在结果上就成为“多捞也白捞”。这一结果很可能对订婚过程中的女方父母产生了激励作用。
(17)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412-414。
(18)冯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论述”。文章的网址是:http://ccsh.nankai.edu.cn.。当然,在今天的中国“嫁寡妇要身价”无疑是少之又少的。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前者。
(19)《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页919。
(20)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三民书局1988年版,页40。
(21)同上注,页40。
(22)戴炎辉、戴东雄,见前注(20),页40。
(23)F.Müller-Lyer:《家族论》,王礼锡、胡冬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324-325。
(24)Frances W.Kuchler,Law of Engagement and Marriage,Oceana Publications Inc.1978,p.89.
(25)F.Müller-Lyer,见前注(23),页326。
(26)FrancesW.Kuchler,见前注(24),p.90.
(27)Elizabeth Warner,"Behind the Wedding Veil:Child Marriage as a Form of Trafficking in Girvs",12 Americ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Gender,Social Policy & the Law,2004,p.236.
(28)戴炎辉、戴东雄,见前注(20),页40。
(29)黄松有,见前注③,页93。
(30)黄观鸿、程贵铭:“农村婚姻中的礼俗与法——河北省黄龙寺村婚姻行为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页96。笔者对表中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计算。
(31)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695。
(32)《孟子·滕文公》(下)。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男孩一出生(父母)就希望帮他找房好妻室,女孩一出生(父母)就希望帮她找个好夫家;做父母的心愿,人人都是有的。”韩路主编:《四书五经》(上),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页375。
(33)陈自强:《民法讲义1——契约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91。
(34)同上注,页308。
(35)wwee:“彩礼的经济分析”。网址:http://www.21manager.com。发布时间:2003年10月27日。
(36)周安平:“对我国婚姻法原则的法理学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页168。
(37)强世功,见前注(13)。
(38)陈顾远,见前注⑩,页92。
(39)“父母之命”的立法理由恐怕如孟子所说,如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缺乏许可和使者传达意思表示,当事人双方就会“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孟子·滕文公》(下)。
原文是:“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可是(儿女)不等父母的同意、媒人的说合,就挖墙打洞相互偷看,甚至越墙幽会,那么父母和社会上的人都会轻视他们。”韩路,见前引注(32),页376。
“父母之命”起到了防止当事人双方草率地未婚同居、未婚怀孕,起到了维护当事人双方(应该主要是女方)的尊严之作用。在未婚同居、未婚怀孕越来越常见——其中不乏因某种原因没有结婚而彼此诉讼——的今天,可能需要重新审视“父母之命”的妙用。
(40)黄观鸿、程贵铭,见前引注(30),页98。
(41)所谓“包办”,就是指“不和有关的人商量、合作,独自做主办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见前引注(14),页40。
(42)滋贺秀三,见前引注(17),页414。
(43)wwee,见前引注(35)。
(44)滋贺秀三,见前引注(17),页414。
(45)wwee,见前引注(35)。
(46)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页38。
(4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29-430。
(48)王泽鉴:《债编总论(二)——不当得利》,三民书局1995年版,页4。
(49)Peter Gottwald,Dieter Schwab and Eva Büttner,Family and Succession Law in Germany,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45.
(50)史尚宽,见前引注(31),页158。
(51)松岛由纪子:“结纳の法的性质”,森泉章等人合编《民法基本论集(第7卷)——家族法》,法学书院1993年版,页46。
(52)同上注,页44。
(53)松岛由纪子,见前注(51),页44-45。
(54)Barbara Frazier,"But I cant marry you:Who is Entitled to the Engagement Ring When the Conditional Performance Falls Short of the Altar?",17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ers,2001 p.422.
(55)Brain L.Kruckenberg,"I Don't:Determining Ownership of the Engagement Ring when the Engagement Terminates 〔Heinman v.Parrish,942,P.2d 631 (Kan.1997)〕,37 Washburn Law Jounal,winter 1998,p.426.
(56)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23.
(57)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24.
(58)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25.
(59)松岛由纪子,前引注(51),页42。
(60)王泽鉴,见前注(47),页428。
(61)同上注,页428。
(62)李模:《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兴丰印刷有限公司1989年版,页197。
(63)王泽鉴,见前注(47),页427-428。
(64)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1。
(65)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1。
(66)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3。
(67)邹海林:“我国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1996年版,页32。
(68)同上注,页32。
(69)邹海林,见前注(67),页31。
(70)邹海林,见前注(67),页29。
(71)彩礼返还的当事人是个别给付人和个别受益人。返还的标的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原物存在,返还原物及孳息;如果因受利益的性质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返还的,偿还该利益的价额。为了确保婚姻自由,返还的范围应该是“现存利益”,但是如果有恶意,如在未商定婚期之前盲目购买结婚财物、解除婚约之后返还之前购买财物,则应该返还此前现存的利益。
(72)周楠,见前注(16),页168。
(73)松岛由纪子,见前注(51),页44。
(74)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33.
(75)Gaden v.Gaden,272 N.E.2d 471.
(76)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34.
(77)Brain L.Kruckenberg,见前注(55),p.435.
(78)Property Law-Pennsylvania Supreme Courl Holds That Engagement Rings Must Be Returned Regardless of Who Brokethe Engagement.-Lindh v.Surman,742 A.2d 643 (Pa.1999) ,113 Harvard Law Review,May 2000,p.1877.
(79)同上注,pp.1879-1880。
(80)周楠,见前注(16),页168。
(81)松岛由纪子,见前注(51),页43。
(82)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28.
(83)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31.
(84)Barbara Frazier,见前注(54),p.433.
(85)黄松有,见前注③,页102。
(86)张学军、付翠英:“论我国婚约解除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和学说”,《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页61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