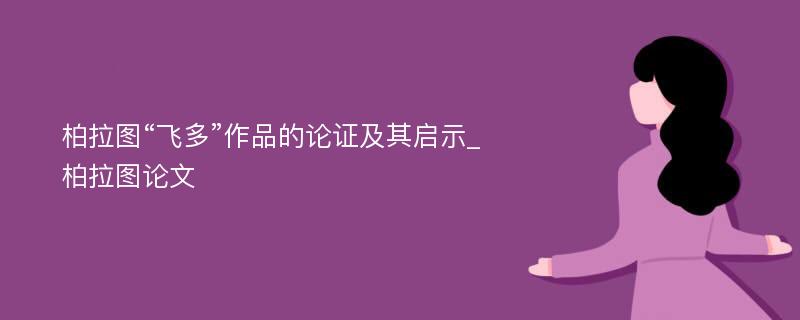
柏拉图《斐多篇》的论证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多篇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斐多篇》是柏拉图中期相论(注:“相论”旧译作“理念论”。因为“相”这个术语,希腊文的'ιδ'εα(idea) 和ε 'ι δos(eidos) 在旧译中作“理念”。这种旧译尽管相沿成习,但问题颇多,很不适当,已有多人指出。参见汪子嵩、范明生等撰写之《希腊哲学史》卷二第653页—661页,该书首版1993年,人民出版社。在陈康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注35中,建议译之为中文的“相”,我们从此。罗念生在《古希腊哲学术语译名管见》(载《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10月第9页)中, 建议分别译作“原型”和“模式”。)的代表篇目之一。在该篇对话中,柏拉图描述了苏格拉底在雅典狱中服毒受刑前,和他的朋友及学生就哲学家如何对待生死问题,从而围绕灵魂不朽进行的一场对话。本篇对话所记事实可信;(注:泰勒《苏格拉底》第一章、导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另见汪子嵩等编撰《希腊哲学史》卷二第334页,第二编、 第六章四节“史料和‘苏格拉底问题’”。人民出版社1993年。)但其中的相论则主要反映了柏拉图思想在中期的发展状况,由于提出了系统的本体思想和认识论思想,在柏拉图全部对话中占有重要地位。
《斐多篇》的主题是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在整个对话中,这一论证从多个角度反复展开进行。然而,如果从逻辑和哲学发展的近现代眼光考察,我们实在会产生这样两个疑问:
这些论证在逻辑上是否可靠?
所要论证的问题是否构成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说纯粹理性范围内的问题?
先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诸多论证中,柏氏采用的论证方式大多是或然性的类比推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简单类比,例如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论证、回忆说的论证、第一个相论论证等;另外,有些论证也不无循环论证之嫌,例如第二个相论论证在最后得出结论时(105D)。尤其是,作为全部论证的最主要部分的相论说,本身尚不成熟,隐含着许多难解的容易引起混乱的问题,概括说有两点:一为“分有”问题,即各类不同的具体事物究竟是如何分有相的?它们分有的到底是怎样的相?比如同一事物是否可分有不同的相,例如某张桌子除分有“桌子”的相外,是否还分有“家具”的相等;不同类别的不同事物是否可分有同一相,例如铁和石头都分有“坚硬”的相,巴特农神庙和荷马史诗都分有“崇高”的相。二为“分离”问题,即相作为一种不同于具体事物的存在,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种存在?相与相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是包含还是全异,不清楚。
再看第二个疑问,我们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灵魂问题在康德,被认为是超出于纯粹理性范围之外的信仰问题或实践问题,而非思想问题;在维特根斯坦,则被认为是超出于语言表达之外的神秘存在,对之必须保持沉默。这些几已成定论和常识。质此,二千五百多年前柏拉图抓住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由此,第一个疑问,即具体论证中的逻辑窘迫,主要还是源于第二个问题,即“灵魂不朽”是不可论证的,其与逻辑无涉,不是作者的逻辑能力欠缺,而是论题对于逻辑本身的超出。
既然《斐多篇》从根本上证明的是一个不可能被证明的问题,而且此证明本身存在且必然会存在的纰漏,那么,将如何解释苏格拉底对于灵魂不朽所抱的坚定信念呢?这一信念,在苏格拉底受审、囚狱和赴死的全过程中,(注:对苏格拉底受审、囚狱和赴死情景的描绘,分别见柏拉图对话之《申辩篇》、《克力同》和《斐多篇》。)有最集中最充分的表现。面对死亡,苏格拉底镇定从容、安详平和,如其所言,他对死亡是有准备的,他相信灵魂不朽,相信自己死后的美好归宿。而且,终其一生,作为公民,作为战士,(注:苏格拉底作为公民和战士所表现出的正直与英勇,分别见色诺芬《回忆录》(第1卷第1章第18节、第1卷第2章第32节、第4卷第4章第3节),柏拉图《会饮篇》(219e -220e、221a-b)、《拉凯斯篇》(181a-b)。)作为哲学家,苏格拉底随时随地都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无比的正直,这一切,无疑与他坚定的内在信仰有关。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不能用哲学和逻辑在发展二千多年后带给我们的眼光去评判古人,而是应该努力进入历史,持一种同情与谦虚的态度。以此观之:一,在苏格拉底所处的哲学的童年时代,在理性的光芒刚刚升起之时,面对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一个人生的根本问题,他能殚精竭虑提供如此充分细密的论证分析,实属难能可贵,尤其在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比如汉民族)的思维水平相比时。(注:见本文后引陈康先生之例举,即《陈康论希腊哲学》前言,商务印书馆1987年。)二、在人类思维尚未充分生长发育的当时,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两个疑问,尤其第二个疑问,对于苏格拉底实在都是潜在的,是未被明确意识到的;相反,他对于自己论证的力量倒是抱有充分信心的。在理性曙光的初照之下,他感到的是逻辑的力量,而非逻辑的无能;理性在加强着他的信念,而不是在侵蚀和削弱着他的信念。
其次,在《斐多篇》主体部分的三个同构而又各自独立的论证中,(注:《斐多篇》64c—115a论证灵魂不朽,为全篇主体部分, 这部分论证,可分成三个结构完整的小论证。即:31(64c—69e),32( 70a—84b),34—37(91d—115a)。三个小论证在结构关系上是同构的,即,每次都是从此岸现世自身生活的贫困窘迫始,论到灵魂的不朽及死后灵魂的归宿可能,再反转回来又论到现世生活中对智慧的热爱,及以之净化自身而为死亡作准备的重要;三个小论证在论述强度上是依次加强的,这不论从篇幅还是从论证的繁密程度上均可见出。整个论证就象三个依次由小到大的同心圆一样,第一个圆基本是提出问题,第二个圆以正面的“立”为主,第三个圆则有“破”有“立”,是先“破”后“立”的。在意思上,这三部分不光是论证了灵魂不朽,它们每次到最后都强调了生前净化的重要性。)除了推理文字,都有关于死后灵魂的各种可能归宿及彼岸世界图景的描述,更有对生前净化的重要性的强调。这方面的内容,在第二尤其第三个论证中有相当篇幅,极尽铺陈。这些文字和纯推理文字形成明显的对比和提示。对于稍微了解当时希腊的奥尔菲教信仰背景、以及毕达哥拉斯教派教义的人,不难发现,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反复陈说的世界图景和人生信条,并非为他所有,实际上只是当时的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熏陶与赐予。这是一些自他出生之日起就覆盖和围绕着他的传统和氛围,是很早便已在他的心灵深处扎下根来,并终其一生为他所持守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首先并不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而是他的宗教、他的信仰,某种意义上,他的哲学和逻辑实在只是这一信仰统摄下的产物。他是先有“灵魂不朽”的信念,然后才尝试对其进行逻辑的论证。整个《斐多篇》对灵魂不朽的论证,可以看作他的宗教神学陈述,就象后世诸多神学家,相对于基督教信仰而建构的神学巴别塔一样。说是“神学”而非神话,是因为他们试图赋予传统宗教观念以理性的形式,从而超越想象与习俗之上,进入思辨的领域;说是“巴别塔”,是因为他们试图以不可能的理性方式去言说信仰,通达信仰。在实际上,他们都是先有信,再才有想、说和作,而非先有思有想有逻辑。具体到《斐多篇》,首先是传统和习俗赋予并支持了“灵魂不朽”的信念,而非逻辑的论证。在《斐多篇》中,大量的论证文字之外,存在大量不假思索的非论证性陈述和描绘,正是这一点的明证。当然,逻辑论证显然充分有力地提升和强化了这一信念本身。
阅读《斐多篇》,至少告诉我们如下事实:在苏格拉底时代,哲学思维远未彻底从宗教信仰中分离出来,宗教是哲学思辨赖以展开的大文化背景甚至前提,宗教为哲学思维的展开,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命题。相比而言,在时代和个人精神生活中占有更深更广影响的,是宗教而不是哲学。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不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是作为执着理性、追求智慧的哲学家终其一生的,他们虽然不可能超脱传统,但他们都试图使传统信仰得到理性的提纯和上升,使之深化和系统,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他们的探索在许多时候往往超出传统信仰领域,而有所创新,比如关于“相”的思想等。虽然他们的这些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但正是通过这些探索,人类才第一次目睹了自我理性的日出,为后世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质此,他们的思想毕竟是哲学,而非神学。
根据以上分析,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尚可对苏格拉底执着论证的精神,有进一步的体认。首先在于“破”,虽然理性不能给予人生问题以根本的论证,不能为信仰提供绝对的保证,不能给予我们一个价值和意义的绝对的“是”,但在一个多元甚至混乱的世界上,在众声喧哗中,它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伪”的与“浅”的信仰观念,使我们能够认清各种“不是”,从而使我们不致落入愚昧与迷信的陷阱中。这是一种“负的方法”,它使我们的心智时刻保持清明与警惕,使我们据有一个批判的立场。读过柏拉图“对话”的人,都会对苏格拉底所声明的那句话,“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与各种人的相互辩难问答中,苏格拉底常常针对许多价值观念,诸如“正义”、“勇敢”、“虔诚”等提问对方,使对方先提出各种正面回答,然后经过一番论辩,让对方陷入进退两难的逻辑困境,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回答。常常在对话结束时,就所涉及的主题,连苏格拉底本人也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正面回答。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对话毫无意义,恰恰相反,这样的没有“结果”,往往比轻率和不假思索的“结果”有力有用得多。至少,它清理了通往真理路途上的各种自以为是的盲信和偏见,把我们领上或者说逼上了真正的思想之路、真理之路。它去除愚昧昏暗的各种教条和偶像,突现出可信者。
其次在于“立”,所谓“正的方法”。《斐多篇》全篇主题是“论灵魂”,但这一主题并非凭空飞来,它是由具体而无法回避的个人当下死亡处境中引出的。由此可见,从起始,西方思想即表现为一种直面人生的努力,正因为这些人生根本处境,如“死亡”、“痛苦”、“罪恶”、“人性的软弱”、“命运的不测”等,才迫使或激发起他们巨大的理论创造热情,使他们去进行艰苦卓绝的思想努力,构造出各式各样宏伟的思想体系,以支撑这有限与多艰的人生,谋求人性的改善,精神的升华和超越。正是这一直面的勇气,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动力源泉,使其得以穷尽人性潜能与人类创造性的一切可能的领域,而焕发出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由此着眼, 我们才能理解诸如 “logos”、“soul”、“idea”、“ real nature”、 “object in itself”、“what itactually is”,包括“理想国”、“天国”以及后来的“基督”、 “太阳城”、“乌托邦”等概念或者说观念的意义所在。它们是人类精神超越死亡、罪恶和有限自我的努力的产物,是人类的创造亦或发现。它们是用来同有限、软弱、不洁和充满罪性的肉身以及纷乱与变动不居的现象界相对立的,正是在这一紧张对峙中,形成了一个生发意义的无穷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他们既深刻体验到人生的罪性与悲剧性一面,又充分经历到人生神圣与伟大性的一面。也就是说,logos、soul、idea 这些中心概念(或观念),以及围绕它们所形成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思想体系产生的根本动因,是由于对人生根本境遇的觉醒。但这具体的境遇只是条件,唯有觉醒的理性在与各式各样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才有可能升华抽象出一些深具活力与穿透性的中心观念和范畴,构建出宏伟的思想体系。在思想的自由竞争中,理性本身也得到了锻炼与强化。
随理性结晶成形的各种范畴概念及其衍生概念和观念,不仅表现为对人类命运之有限性的超越,尤其表现为对人类知识立场的暧昧性和道德立场的游戏性的拒斥,它们使我们在“知”上有所定,在“行”上有所立。它导致知的确定性:定量与定性;和行的确定性;是非、准则、规范和理想维度。它造就一种对真理、生活的严格与严肃的态度,成就一种稳定的、诚实的、有尊严的人格。在理性的王国里,人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万事万物以及人的那个根本的“是之为是”, 即“whatitactually is”、“object in itself”,它必然是确定的。 它先天地排拒无立场的实利主义与机会主义。在这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总之,理性虽然在根本和绝对的意义上不能有所立,但在历史的与相对的意义上,它不但使愚昧和迷信显形,而且在面对存在的虚无、命运的奇诡、历史的黑暗、社会的混乱和人性的脆弱中,有所创造!而这创造,正是理性的正的方法的体现。
综上,一个人“信什么”往往并不靠理性和逻辑决定,它主要是先天被给予的,它与个人生存其中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还有自身的资禀与气质有关;“信不信”也主要不取决于论证和逻辑,因为理性与信仰之间无路可通;然而,“所信”却应尽量受理性的诘问和质询。正是在最后这一点上,中西判然有别。一部中国思想史,是少用逻辑方法的,正如陈康先生所例举的:这中间有“无父无君的杨墨‘是禽兽也’的推论。用于蒙混过关的‘白马非马’的分析。在自己的意见上挂起前人的招牌(‘仲尼墨翟俱道尧舜’)。或用前人的言论来增高自己的意见的价值(‘六经为我注脚’)。用从半空中飞下来的结论作推论的前提(‘道曰式,曰能……’)。打着万应灵丹的旗号,其实是空洞无内容的诊断(‘方有方之理,圆有圆之理’)。”(注:《陈康论希腊哲学》前言,商务印书馆1987年。)陈先生在这里举出的,只限于哲学思辨领域,其实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方法的功用,更多地体现在日常实践领域。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的观念左右和影响的,而许多看似天经地义或习以为常的观念,往往是经不住理性分析的,比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德”,二十四孝里的“孝”,(注:对“二十四孝”的批判,在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已有所涉及,其实这二十四个故事很少有合理常情常理者。)缠脚的“美”(注: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中讲到:“过遍世界,研究过初民社会,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或野蛮的民族把他们的女人的脚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节断折残废,而一千年公认为‘美’的!”。),再比如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注:以诸葛亮的所谓“智慧”,与早他将近千年的苏格拉底们所追求的“智慧”相比,境界与性质与之不同。),宋江的“义”,岳飞的“忠”(注:参阅潘旭澜《岳坟漫想》,《上海文学》1999年第7期第70页。 )等等。阅读《斐多篇》,我们深感苏格拉底对于做人质量的强调,他强调人之为人即在于人有理性,人既不应该停留在贪图饮食的驴子和残暴凶恶的豺狼的动物层次;也不应该象蜜蜂和蚂蚁一样,仅止于具备良好的社会声誉和权威的公民层次;人应尽最大努力发挥理性所赋予自己的力量去求知,并以理性去净化自己的欲望、激情和德行,使自己达到真正的、绝对的和唯一的善,亦即智慧。而这,正是哲学家所追求的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注:柏拉图《斐多篇》81b—84b。本文《斐多篇》引文及标码皆据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sir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通俗点说,就是人必须用reason武装自己, 好人不等于糊里糊涂和老实巴脚,他必须十分清楚,即所谓道德理性。反省和反思是不同的,反省是无条件认同各种道德命令,并以之对照自己的生活与行为,要求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与之相符;反思则不仅检讨自己的生活和行为,首先还要检讨和悬搁各种道德命令,使其经受理性本身的严格分析审查,反思绝不盲目和无条件地承认任何道德伦理学说及它们的要求。质此,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有反省而少或无反思,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的“道德”绝然不同于中国人的“伦理”,它是经过道德理性的严格审察和提纯的产物,而这,正是希腊哲学的真正成果所在,其自觉于苏格拉底时代,完成于希腊化及罗马时期的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注:A.A.Long在其《希腊化哲学》一书的第二版序言(写于1985年)中说,对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开展认真的研究,力图恢复其原貌的工作,只是到新近的十年才有了重大的进展。以前人们总是认为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才是希腊哲学的顶峰,对后来的哲学评价不高。这种情况,到20世纪中期之后看法渐渐有了改变,认识到希腊化哲学有自己独特的重大贡献。A.A.Long本人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个主要成员,他和D.N.Sedley合作编辑了《希腊化哲学家》的资料集, 自己还写了几部著作。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很有研究深度的贡献。
杨适教授在其新著《爱比克泰德》(台湾东大图书公司)中说:“通过芝诺的Politeia,一种新的哲学开始崭露出来。它所关注的,同苏格拉底、犬儒派一样,是人的生活和道德的问题。犬儒派已经看出原来希腊人的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种种缺陷,提出了新的自然的生活哲学。
斯多亚派予以继承,进一步从理论上批判了老的城邦概念,明确提出了新的世界城邦的理念和新的人性观念。它是一个同以往希腊哲学大不相同的新型世界观,有着全新的视野和一种超越特殊的普遍性高度。人们总是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当作希腊哲学最伟大的导师。但是,这个观点是值得重新考察的。至少在从希腊化时代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导师并不是他们,而主要是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第38页))
通过对《斐多篇》的学习,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所谓哲学,根本上应是一种思想方法和思想习惯的养成,这就是逻辑的方法和分析的习惯,哲学尽管不能给予我们关于人生的终极答案,但它却训练我们的思想离弃虚妄和愚昧(负的方法),而“趋近”于合理和真实(正的方法)。哲学是一种训练!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有如下议论,正好用来印证上面的体会:“一个人最坏的毛病就是厌恶论证。厌恶论证是跟厌恶人类出于类似的原因的。厌恶人类是由于并无充分认识就盲目信任某人。你认为这人是完全真实、可靠、可信的,后来却发现他下流、虚伪。然后你又对另外一个人得到同样的认识。这样久而久之,先是把某人看成推心置腹的朋友,然后是连续不断的争吵,于是对人人都发生厌恶,认为人人都没有真心。”(89d)“假定有某种论证是真实、可靠、可以学习的, 如果有人由于见到有些论证似乎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却并不责备自己、责备自己缺乏技能,一生气就把责任干脆归给那些论证,把他们厌恶、辱骂一辈子,放弃认识实在真象的机会——那就糟了。”(90d )“我们首先要谨防这种毛病,别让自己心里以为论证是根本不可靠的,我们应当反过来承认自己还不可靠,必须果断地努力使自己变成可靠的。……我并不热衷于使自己所说的话在听众心目中显得真实,以为那是次要的事,主要的是使我自己相信它。”(90e—91b)苏格拉底在此指出的由于不懂论证技术而导致的论证厌恶症,恰好强调了论证技术的重要性;其次,他强调了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应排除各种外在干扰,一心一意去相信论证的力量,实现论证的力量。
阅读《斐多篇》,我们还可以对哲学家之为哲学家得到一个较为本原深入的理解: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显然认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便是哲学家的人生(80c—84b),因为他们生前最充分地运用了自己的reason去摆脱变动不居的感官印象世界,而达到真正的knowlage,即关于善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运用这些知识去净化自己的灵魂,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和激情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和解放,从而为死亡作了准备,使自己的灵魂在死后能够进入一个远比此世美好的神明世界,进入到不朽者行列,永享神明的福址。也就是说,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人作为哲学家,不仅在于自觉运用神明所赋予人的理性去求取真知,而且在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净化自身,即道德践履。哲学不仅仅是学园里的讲论和书斋里的著述,首要的是哲学地去生活、去实践,只有理性思辨与道德净化并重,才可望达到真正的智慧境界,即善。苏格拉底的一生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生活上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
关于“净化”,在此还可予以申说。《斐多篇》通篇在谈论灵魂问题,谈论天堂和地狱的情况,所有这些谈论,又都是由苏格拉底在狱中的临死情景引发出来的。这样,《斐多篇》似乎旨在表达一种“生死观”。但我们认为,在希腊、在苏格拉底,具体到《斐多篇》中,尽管讲了许多的死,讲到人生如牢狱,肉体是坟墓;讲到灵魂被幽禁在肉体之中,人生是灵魂的忏悔演习,似乎绝对地悲观厌世。实际不然,所有这些关于灵魂及彼岸世界的讲论,最终都反射回到了此岸此在的肉身实际,呈现为一种强烈的净化自身的要求和愿望,它导致的是一种强烈的净化自身的要求和愿望,它导致的是一种最积极的生活状态,它激发出此生的生命激情与创造欲望。这种“生死观”的真正落脚点,并不是此生的“死”,而是此生的“净化”,即“生”。这里实际突现的是一种真正强有力的积极的“人生观”,只不过它是在打通生与死的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呈现的,是以一个睿智的哲人的立场与方式讲说出来的。
标签:柏拉图论文; 斐多篇论文; 哲学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