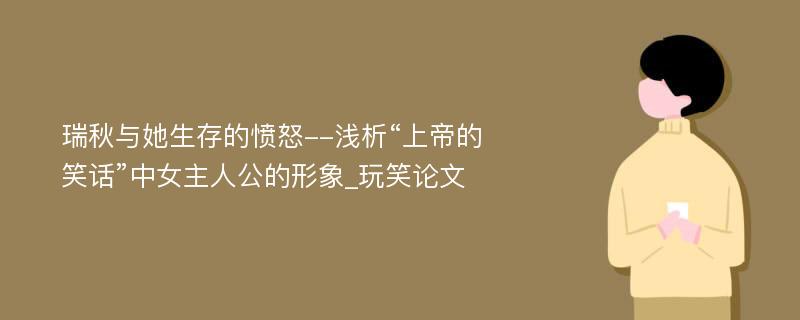
雷切尔及其生存的愤怒——评析《一个上帝的玩笑》的女主人公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主人公论文,玩笑论文,愤怒论文,上帝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是位被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乔治·伍德科克誉为“加拿大的托尔斯泰”的女作家,毫无疑问她是加拿大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她的作品中,不管是以非洲为背景的游记和小说,还是以加拿大为题材的系列小说,都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空间感。她作品中的人物都个性鲜明,并且作品同男作家们所侧重的不一样:不是主人公的个体价值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同,而是关注于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此外,她还赋予笔下的人物独特的宗教背景,穿插进许多意味深长的神话和《圣经》中的典故,使得每位人物都富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玛·劳伦斯以其故乡加拿大一个西部小镇尼帕瓦为原型的“马那瓦卡”系列作品中,每一部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位面临着各自生存的困境而最终得以自我实现的女性:《石头天使》中的哈格、《一个上帝的玩笑》中的雷切尔、《火中人》中的斯达茜、《房中鸟》中的范尼莎以及《占卜者》中的莫拉格。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这一系列作品所描述的,实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层面而已。具体说,讲述的都是一个“朝圣者”终其一生、打破重重枷锁、苦苦探求的心路历程,探求的是关于上帝、关于自我以及关于自由的本真认识。这一母题在这系列的第一部小说《石头天使》(1964)以及获得“总督奖”的第二部小说《一个上帝的玩笑》(1966)中揭示得尤为深刻。关于《石头天使》中女主人公哈格的探求与救赎,请参阅拙文“一个朝圣者的历程”。〔1 〕本文将对《一个上帝的玩笑》(以下简称《玩笑》)中的女主人公雷切尔的形象进行剖析,通过展示其内心的困惑、恐惧和她因严重的人格分离而导致的生存的愤怒,表明每一个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所应体现的独特价值,从而探索玛·劳伦斯作品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一、用两个声音说话的雷切尔
同《石头天使》一样,玛·劳伦斯在《玩笑》一书中也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使读者不由自主地就“介入”了书中的“我”——女主人公雷切尔的矛盾重重、郁闷单调的生活中去:雷切尔·卡麦隆,马那瓦卡镇的小学教师,一位殡葬员的女儿,34岁的她如今仍和孀居已20年的母亲住在一起。在读了本书的第一章之后,读者便会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女主人公一直在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声音是对别人说的,礼貌、冷静、理智而又平和;另一个声音则是对她自己说的,冷酷、刻薄、蛮横而且激愤。在小说的第一页,雷切尔站在教室的窗户旁,看着学生们在操场上和着一首歌跳绳,由这首歌她又走进了童年的幻想:
风低低地吹,/风高高地吹/雪花从天上飘下来/雷切尔·卡麦隆说她宁愿去死/只为得到那座金色城池。/她聪明,她漂亮,/她是金城的女王。〔2〕的确,在雷切尔的梦中,她是一位聪明漂亮又高贵的女王。或者象《旧约·创世纪》中的那位雷切尔一样,“身材匀称,容颜俏丽”,又拥有雅各的真爱。〔3〕但是, 她内心那个残酷的总对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快就提醒她回到现实中来。这里哪儿有什么“女王”?从窗玻璃上映射出的不过是一个34岁的颇令她自卑的女人的孑影,这个声音说:
当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所小学度过我的一生,而我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诚惶诚恐担心自己表现不好的小姑娘了,却变成了一个过高过瘦的庞然大物的“她”……〔4〕继续读下去,读者会发现雷切尔一直沉浮于美丽的幻想和严酷的现实之间。那个向外发出的声音满是克制、压抑的,而且那股压制的力量异常强大,制约着她的一言一行。相反,那个老对她自己说话的声音就象时刻都可能喷发的火山一样,总是不住地打击、责骂她,让她胆颤心惊。读者不难想象同时受这两个声音制约和打击的雷切尔是多么痛苦:一方面,她得依照“别人会怎么想”的前提去做很多她“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如,她应该体谅学生,对他们公正无私;她应该是一位懂事的女儿,优秀的教师;她应该喜欢每一个人,热爱她的母亲,随时乐意为她尽孝;她不应该依赖任何人;从来不应该感到受到别人的伤害;不应该急躁焦虑;她应该清心寡欲而且自然纯朴;她应该严格地控制住自己的情感而且从不说没有考虑清楚的话;她应该总是知道、理解并能预见生活中的一切,尤其是在和尼克的交往中……类似的“应该”和“不应该”在雷切尔的脑海里还有很多,当她与别人相处时,它们就会自动跳出来规范她的言行。另一方面,当她做那些“应该”和“不应该”做的事之后,第二个声音就会毫不留情地责骂她、羞辱她、讽刺她,让她惭愧不已。那么,读者也许会问,雷切尔的两种声音背后是由什么力量支配着的呢?在深入她的内心之后,笔者发现,雷切尔的第一种声音受着一股非常强大的“混合力”的支配:即马那瓦卡镇清教徒的压抑克制的传统和雷切尔的母亲梅·卡麦隆的长期训诫的综合效果。而她的第二种声音却体现出她内心本真自我的挣扎和急于显露的倾向。因此可以说,第二种声音才是雷切尔真实的声音,它急切地渴求替代第一种声音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本我,拥有人的自由、人的完整、人的个性、人的尊严和人的存在的合理性。第一种声音,是女主人公认为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中不得不使用的,它实质上是雷切尔作为客体存在的“第二身份”的表现,换言之,女主人公的痛苦正是由于其存在是“自在”的“在”,而非“自为”的“在”所造成的,这是雷切尔之“存在”的特殊性。
长期以来,雷切尔都以其“第二身份”(心理学中的“人格面具”)来与周围的人交流和生活,而压制着她的“第一身份”,亦即其本真自我:一个母性的、渴望真爱和自由的女性角色。这种“双重身份”的存在,使得她的真实自我和真实感受都被强行压制在她的意识深处。她的本身存在与其表征存在是完全相悖的,所以,对于她的自我身份,她不能肯定地说:“我是自为的在。”(“I am what I do.”)
换个角度看,雷切尔的“双重身份”就是其生存人格的严重分裂,正因为如此,她已濒于歇斯底里的边缘,近乎崩溃。小说几乎每一章节都有雷切尔近乎癔语的独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经宣称:“他人即地狱”。而雷切尔正挣扎在那样一个“地狱”中。她和周围的人没有沟通,又不互相了解,她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无足轻重的“物体”。至于她对于自身存在的任何体验,在她看来都是无用的:
我看起来并不老。我看上去不会超过三十岁。但会不会是我自己看得不准?可我又如何得知别人看我会是什么样?〔5〕这种对自己充满怀疑的感觉时常涌现,尤其是那两次在小镇的饭馆里,她体会得最为深刻。她第一次去的时候,那帮青年人完全没注意她,这使她感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我不喜欢从他们中间穿行过去,因为那样的话,我不得不忍受他们眼里的漫不经心和不屑”。〔6 〕而当她第二次光顾那家饭馆的时候,本来希望那伙青年人忽略她,可是一旦他们真的再一次忽略她了,她又萌生出一股强烈的愿望:盼望从他们眼里看到自己不是一个游荡的影子,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存在:
(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无名之辈,就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现在我并不感觉自己身在此地。如果他们此刻朝我这边看的话,我一点儿都不会介意的,甚至不在乎他们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因为那样的话,至少可以证明点什么。〔7〕在这段内心独白里,雷切尔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体的愿望过于强烈的后果就是使自己沦为“大众”的牺牲品。换言之,雷切尔的问题用存在主义作家昆德拉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就是“媚俗”。他说,只要留心公众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鄙视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结果是使人丧失掉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主体价值,最终被“异化”,成为一个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物体”,类似于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遭遇。在雷切尔的下意识里,她对周围的人,包括同事、邻居、母亲及恋人尼克,都得无条件地服从。她所做的一切必须符合他们的要求。正因为这样,雷切尔从来不可能客观地审视自己,她总是以别人的标准来挑剔和指责自己,自怨自艾、自卑自贱。小说中有几个典型的细节:当学校的教导主任威利尔就她给某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一事提出质疑时,她立即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立刻责备自己当初不该那么做。由此可见,她是怎样地将自己摆在一个客体的位置上,任凭别人评判裁决。她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如此,总是顾虑到公众的存在,哪怕他人或许并不在乎她的所为。在她刚念中学的时候,一次,有位同学想请她看电影,准备为她买一张儿童票,因为儿童票便宜得多,她的年龄也没有超过有关规定。但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怎么面对那个验票员呢?还有那个引座员?”〔8〕有时候, 她甚至还会在没有什么根据的前提下,仅凭自己的想象,就对某件事忧虑不已。如有一次,她在山上散步,遇见了一对中学生情侣,碰巧听到他俩大笑起来,于是她便在心里思忖,想象着不多久全镇的人都在议论古怪的卡麦隆小姐总是一个人散步。她对自己说:“我可以想象自己成年累月都这样独自走在这些铁轨、这些公路上,一英里又一英里,永无止尽。”〔9〕
除了担心自己言辞或举止不当之外,雷切尔看到别人出丑时也会感到不寒而栗。原因很简单,从别人的丑态里她看到了自己可怜的影子,这是她被扭曲变形了的幻像。如,当她在商店的橱窗玻璃里看到自己被折射成怪异的模样时,又开始悲叹起自身的形象来。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雷切尔的痛苦和迷惑都是她自己造成的。她因过于循规蹈矩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公众的也是自我的“囚徒”,这个囚禁她的牢笼实际上就是她自己的想象。再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原本是一个被动折射出的形象却被她当成是真的自我形象来加以接受,这意味着雷切尔缺乏一个主体的“自在”所拥有的自信。
如果说对于“自在”的自信缺乏、对“在”的察觉仅能借助他人来得以实现有什么后果的话,那就是使得个体内部生命活力匮乏,妨碍原初自我的天然显现。比如,当她和尼克同在一辆车上时,虽然她很想靠他近一些,但她害怕会因此出车祸,故而不敢妄动。她在脑海里为自己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如果……人们到时候发现我的头发散乱,嘴上的口红没了,衣冠不整怎么办?”〔10〕在想象中,她可以无拘无束地和尼克在一起,但当尼克近在眼前了,她却马上变得十分拘谨,不能自然地表现自己。即:只有在梦想当中她和尼克才是自然、自由的,而当他本人站在她面前时,她便又落在“客体”的位置上,期冀他对她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对于自己不能流露内心真实感受这一点,她痛苦地发现自己与同事凯拉截然相反:
凯拉把她公寓外间的门另漆了一种颜色。我想他们会允许她那样做,不管他们是谁。但我一想到别人可能会拒绝(我的要求),就不愿去冒险一试了……凯拉做事甚至还可以“先斩后奏”。真希望我也能象她一样。〔11〕这表明雷切尔已经意识到她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她骨子里刻上了“别人会怎么说”的想法。雷切尔曾对尼克提到自己在表达真实想法时存在的障碍。她说,镇上的乌克兰人比她自由得多,那些人“没有被禁锢起来,……更容易直言不讳心中所想。而且那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也很容易为其家人和自己接受”。〔12〕从对乌克兰人的羡慕中,可以看到她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从而失去了自由表达的能力。这就是她为什么总是用与第一种声音完全不同的第二种声音来同自己说话的原因,这样,她的本真自我就被压抑得越来越厉害,自我流露也越来越少。她总是很挑剔地聆听自己与别人说话的声音,随即又用第二种声音责骂自己没有涵养没有气度。即或是同恋人在一起时,她也感到自己“象早期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动作快得象机械,滑稽极了”。〔13〕
雷切尔内心这种不可协调的“双重身份”的存在,导致了严重的人格分裂,使其精神世界矛盾争斗不断。因此剖析一下女主人公“双重身份”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能够充分地理解其生存的恐惧和愤怒。
二、“重重枷锁”下的雷切尔
先来看马那瓦卡镇的清教主义传统。小镇的大部分居民都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一支——加尔文宗。它强调禁欲,突出苦行,认为人类由于原罪而受诅咒,人类是否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这时候的上帝已不同于《新约》中的那个允诺给人们带来希望、仁爱和救赎的上帝;他现在因为动了怒而责罚其子民,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罪恶、死亡和诅咒的人世间。信奉这一宗教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们在生活中压抑,克制,不苟言笑,勤奋工作,而且总是怀着深深的负罪感。所以,这里的人们不可能真正领略到生活的乐趣,他们害怕热烈的情感,对于死后灵魂是否获得拯救也充满着恐惧。作为小镇第三代居民的雷切尔,尽管并不真正信奉上帝,悄悄地对自己说:“上帝死了……我都记不清是多久以前了。……”〔14〕但是一到了危机出现的关头,她仍是忍不住向他祷告。由此可见,周围的信徒们互相告诫的“上帝不允许我们怎样怎样”的话在她的心目中还是很有分量的。这样,她就只好遵照小镇的宗教传统,压抑、克制而且带着极深的负罪感生活着。否则,她就会成为镇上的“怪物”,成为所有人攻击的靶子。
再来看雷切尔的母亲梅·卡麦隆的长期教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雷切尔的性格造成负面影响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这位母亲。这位殡葬员的妻子30多岁便开始守寡,20年来过的是一种纯粹的单调封闭、禁欲克制的生活,她的情感世界一直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伊瑟·哈尔丁曾在“妇女的神话”里提到过象梅这样对情感麻木的女性。她认为,这类妇女总是极少关注或发展感情这一领域,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情感就那么一回事,以前怎么样,一辈子就怎么样。而梅的情感生命不仅没被她自己重视,而且还被牢牢地笼罩在“举止要得当”的面纱之下。〔15〕她从雷切尔还很小的时候就给她灌输“人是很邪恶”的观点,要她随时警惕自己“邪恶”的自我。她告诉女儿,她在骨子里是不可爱的同时也毫无价值可言,只有按照母亲的要求去做,才可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过早失去父亲的雷切尔理所当然地对母亲的教诲言听计从,将她的要求视为“圣旨”。而当女儿做了错事之后,梅的惩戒方式也很特别,正如雷切尔所回忆的那样:
我记不清自己犯了什么错。只记得当时自己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我知道她决不会揍我一顿然后就原谅我。不,她从不那样做。那不是她的方式。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絮叨,说我做的错事是怎样伤透了她的心。〔16〕梅采取的惩罚方式,对于正在成长的需要情感上的关怀的孩子来说的确太残酷了:因为她用的是“情感上冷淡”的方法,这使得孩子的情感生命极大地受到伤害。类似这样的童年创作的结果,就是让年已34岁的雷切尔依然要从母亲那漠然而“客观”的眼神里找出自我的存在。不仅如此,成年以后的雷切尔也从来没有真正与她的母亲沟通过。梅总是扮演出一个“受苦受难”的羸弱的母亲的角色同女儿讲话,这使得她的女儿丝毫不存与她平等交流的幻想。因此,她俩之间的所谓交流每次都以雷切尔的沮丧和负罪感告终。此外,梅无时不在注视着雷切尔的举动,生怕她“出格”。她在偷听了雷切尔的电话之后,满面愁容地对女儿说:“我没有偷听……但我无意中听到你好像提到什么事来着?”〔17〕或者是满怀失望地对女儿说:“不要紧,亲爱的。我想或许每个人都有考虑不周的时候。但我却没想到你会——”〔18〕这种方式的谈话每次都让雷切尔心烦意乱。而当她即将对自己的事做出什么决定时,梅也总是竭尽全力让她感到不应该,然后以一种自我牺牲的语气说:“毕竟是你自己的事呀,亲爱的。”之后,作女儿的必然道歉:“对不起,妈妈。”但梅决不满足于此,她会继续以一个孤苦无助者的身份进一步让雷切尔自责,直到雷切尔为自己的“罪行”深刻反省为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梅其实正是以其“受苦受难”“孤苦无助”的形象来打动雷切尔的心,从而控制她。因为除此之外,她几乎没有别的可以依恃的力量。在女儿做了什么有悖于她的意愿的事之后,她总是忧心忡忡地说:“真的,雷切尔,那可不大好。”〔19〕实际上,在梅的心目中,除了传统,别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该存在,都是“不好”的,其中包括激昂的情绪,婚姻以外的两性关系以及任何形式的欢悦。因为,梅一直生活在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中,一切都有规可循。她深信“上帝爱秩序。”这一信念从她对桥牌的喜好上能得到证明。因为桥牌游戏是极其有序极其理智的,所有的冒险、尝试都被限制在一定的规则之内。梅的两个女儿对她的这项喜好都充满怨愤,斯达茜曾称她母亲的那些牌友是“驼背老婆子们”,“从来看不见比她们的眼镜更远的东西。”〔20〕雷切尔则把她母亲的桥牌会说成是“仲夏夜女巫们的大聚会”〔21〕,这说明梅在她女儿心目中的形象是很可憎的,但她们对她却毫无办法。
除了教训女儿们要在别人面前“循规蹈矩”之外,梅还时常向她们灌输女人应守哪些特别的规矩。她认为女人只有在得到父母的许可之后才能同异性接触,否则则是可耻的;当得知镇上的一位名叫凯茜·斯图亚特的女孩怀孕之后,她叹息着说:“对她妈妈来说太可怕了,那么好的一个女人……斯图亚特太太是个多好的女人哪!……”〔22〕,她借对斯图亚特太太的怜惜加深女儿内心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母亲的怜悯和俯首听命;另一方面是对人言的畏惧和对自己的管束。对于梅和雷切尔这样的母女关系(非公开的社会关系)。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
妇女的形象总是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来刻画的……所以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不在这样的传统之列。这就使得母女关系转变为一种“地下”关系,而这种关系使得母女间的相互情感作用异常强大。〔23〕此外,根据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女儿对于母亲在情感上有着一种献身或曰“牺牲”的倾向,这样一种关系就使得做女儿的一方老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不敢主动地表现自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雷切尔从小就毫无怨言地按照梅认为是“好”的方式去待人接物。可以说,在与其母亲的关系中,雷切尔根本无从确认自我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价值,相反,她必须完全将自己放在一个客体的位置上,等待着母亲来评判她、确认她。
综观雷切尔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由于她一味地顺从于小镇的清教主义传统和母亲严格呆板的训戒,致使其真实自我完全被压制、被扭曲,得不到自然而然的显现。那么,真实的雷切尔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可从她对她姐姐的嫉妒中看出来。这里的雷切尔跟《创世纪》中的雷切尔一样,嫉妒她做了母亲的姐姐。她也曾像那个雷切尔一样对着尼克说:“给我孩子。”是的,34岁的她从心底里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的角色,结婚,然后生好几个孩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她却得守着那位体弱多病又有些神经质的母亲过活,尽她的“职责”。除了羡慕姐姐斯达茜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之外,她还羡慕她住在远离小镇的温哥华。因为离开小镇,就意味着获得自由。可是这一切她现在都没有。但是,雷切尔是否心甘情愿地继续过这种压抑苦闷的生活呢?显然不是。尽管她对这样的生活起初充满了恐惧和迷惑,但当她明白自己究竟想要寻求什么之后,她就对这样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强烈的愤怒,而且渐渐地愤怒越积越多,取代了恐惧,最终变成促使她走出困境的力量。正因为雷切尔在经历了激烈的内心冲突后能够振作起来,走出困境,追求另一种人生,才使她具有巨大的魅力和现代意义。
三、恐惧、愤怒的雷切尔
雷切尔心中一直有个声音在对她说: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这正是过于看重公众的存在的表现,这也必然导致她对周围的人和对自己的恐惧:害怕身边的人认为自己稀奇古怪不接受自己;害怕自己是因为认不清自己,害怕自己出丑,落人耻笑。雷切尔所害怕的,就是年已34岁却仍独身的自己变成一个“怪人”,一个大伙儿眼中的“傻瓜”。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无时无刻不紧跟着她。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这种畏惧是很愚蠢的:“感到害怕,我真蠢。但我确实害怕。我也没办法。一个人怎么可能去面对像我这样愚蠢的脸呢?我可不敢。”〔24〕这几句内心独白可以充分说明她心里存着对周围一切的恐惧。再如,当她因打了班上的一个学生而被教导主任召见的时候,她感到害怕极了。尽管跟她关系还不错的同事凯拉极力安慰她说,威利尔就是那样一个喜欢捉弄人的人:
“如果你某一天走到他面前对他说:给我听着,威利尔,别小题大作了——”雷切尔说:“你可以做得到,但我不能。”
“为什么?”
“我——”我不得不去搜寻一个充足的理由,“我受不了那样的场面。那让我害怕。”〔25〕雷切尔对威利尔的这种恐惧从本质上来讲是对传统和权威的畏惧,而且,每当她一遇到一点事的时候,她就会跑去找凯拉:“显然我就是坚强不起来。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凯拉?我——噢,凯拉,我真害怕极了。”〔2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雷切尔对凯拉的依赖近似于她对母亲梅的依赖,因为凯拉对于雷切尔,不仅是一般同事间的关心,而且有很大程度的长辈对晚辈的呵护和疼爱。这可以从凯拉老是称雷切尔为“孩子”上得到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母爱的凯拉,也同样令雷切尔感到害怕:
我很明白我不必感到害怕。她还是那个我认识了多年的凯拉,我反复这样告诉自己。但是我身体的某一部分却想远远地避开她……〔27〕在分析了雷切尔与其母梅·卡麦隆的关系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雷切尔现在对凯拉的恐惧其实就是源于其对母亲的恐惧。因为凯拉也象她母亲一样,随时随地都关注她的一举一动,也经常告诉雷切尔要怎样怎样。因此,雷切尔想要避开凯拉,实际上就是她内心想要摆脱掉母亲的控制这一愿望的折射。因为她觉得这样生活着“太累、太累了。”〔28〕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怎么想”,而不是出于自愿。每天她面对的都是一些毕业后就再也想不起她的小学生。这样的工作让她感到十分厌烦。更令她烦恼的是住在这个小镇上,拼命赚钱,以支撑母亲和她的这个“家”。她想方设法打发走每一天,熬过一个个长夜,盲目地顺从和迁就她的母亲——但可悲的是,她所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毫无意义。她“觉得浑身冰凉,而且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脱离了”。“我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一丝感情,简直象索然无味的独白。”〔29〕这几句话可以视作雷切尔对自己的生活所作的总结:和所有人都是疏离的,生活陷于一种无序、虚无的状态。对于虚无,存在主义者们将此做为现代人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特征。萨特指出,这种感觉几乎存在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心中,“只不过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太忙了,以致于无暇去顾及这些感觉。”〔30〕归根结底,“这种虚无的感觉起源于对生活的绝望,是‘上帝死了’给现代人造成的幻灭感和绝望感。”〔31〕雷切尔也是如此。那么,陷入绝境的她是否就此沉沦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经过了反复的内心挣扎之后,雷切尔终于积聚起了勇气,不再充当行尸走肉的影子,而是开始反抗。如果说《石头天使》中哈格反抗的方式是她的骄傲的话,那么《玩笑》中的雷切尔反抗的方式就是愤怒。
首先是她对周围的人的愤怒。有一次在咖啡馆里,当她察觉出有位十几岁的姑娘流露出对她的鄙视时,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她怎么想与我无关。为什么有关呢?……她以为她是谁呀”?〔32〕另一次,她的愤怒更是无法扼制。当时她去找雷文医生,告诉他可能她怀孕了。医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象雷切尔这样理智的姑娘是不可能现在怀孕的。这时她忍不住怒火中烧:
我不相信医生在说这话,但这显而易见是事实。对于他所说的,我挑不出一个词来表达我的愤怒或是去刺伤他。我真想用指甲在他道貌岸然的脸上划出些道道来,或者象飞奔的汽车那样狂吼着冲向他。〔33〕在这里,我们不妨把雷切尔的愤怒理解为对于小镇传统的愤怒。正因为这个小镇上的所有人都象这位医生这样,握着一套权衡是非曲直的准则,才使得她长期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当她从心理上走向成熟和独立之后,就必然会反抗这种禁锢人的传统。
其次是她对自己的愤怒。在同上司威利尔谈话时,雷切尔开始对自己生气:“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急切又卑贱。说不定我还会不顾廉耻地跪下来吧。我真恨。恨自己这样说话。”〔34〕这时候,她恨的是那个刻意去迎合别人而丢失自我的雷切尔,而雷切尔此时的愤怒正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在和尼克约会之后回到家里,她怒气冲冲地“坐在床上,抽着烟, 想着这不是做事情的方法——有什么全错了……”〔35〕那么,她冥思苦想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个小镇和她那令人神经崩溃的母亲。因为她母亲老是象她小时候一样地管制她,提醒她:“雷切尔,雷切尔,你以后要变成什么样?”〔36〕所以,在对自己发了怒以后,她意识到如果想获得自由,就必须起来反抗她的母亲。
最后,我们看她对干预她生活最多的母亲的愤怒。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梅象以前那样絮絮叨叨地叫雷切尔不要怎样怎样的时候,雷切尔在心里愤愤地说:“‘当我长大了!’她说话的语气好象我才十二岁。我过的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活啊。……”〔37〕另外,当梅干涉雷切尔和尼克的交往时,雷切尔终于忍不住顶了梅几句,这时候梅说:
“真的,雷切尔,……你没必要对我那样说话。如果你稍加注意的话。”“对不起,对不起。”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抱歉。我的愤怒是孩子气的。(虽然我知道),这不是她的错。……〔38〕的确,在这个夏天与尼克有了交往之后,雷切尔逐渐走向情感上的独立,开始与她的母亲对抗。即使她知道母亲反对她和尼克来往,仍然充满怒火地大胆地和她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在她以为怀上了尼克的孩子之后,就在心里假设她母亲会变成什么样:
伤心?羞愧?歇斯底里?……她一定会说:“雷切尔,……我把你养大,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去做那样的事吗?”或许还会说头发变白了都是因为什么什么。可在所有这些神经质的发作和类似的花招用完之后,她是会真正伤心的,仿佛面临着死亡一样。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想法。〔3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雷切尔已经预见到她母亲的眼泪和歇斯底里,但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这无疑是给梅一个最沉重的打击。而她之所以有了勇气来对抗梅,是因为“我已经是母亲了”〔40〕的感觉让她坚强。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需要有人来管制的小孩。但当她得知她肚子里不过是一个肿瘤的时候,她感到仿佛上帝给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一样。愤怒的她在冷静下来之后毅然决定离开这个小镇,离开她母亲,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时候的她想起了尼克对她说的话,象《圣经》中的雅各一样:“我不是上帝。我不能解决一切问题”。〔41〕是的,尼克不是她的上帝;而她自己呢,也不可能是梅的上帝,不可能代替她母亲解决一切问题。“每个人都得建立自己存在的意义”〔42〕。所以,在医生摘除她体内的那个肿瘤的同时,她也去掉了她的“第二身份”,重新发现了那个完整的、母性的自我,挣脱了那些“应该”和“不应该”的束缚,将自己从想象的牢笼中解救了出来。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时候的雷切尔终于获得了“我在”的经验,不再是一个处于被动状态的“物体”。所以,她终于能够骄傲地对那个所谓的“上帝”说:“上帝同情愚蠢的人。上帝同情上帝自己吧。”〔43〕
在剖析了《一个上帝的玩笑》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之后,笔者在此想要指出的一点是:玛·劳伦斯作品中的人物均是像雷切尔这样陷入生存的困境但都不甘沉沦的反叛者。她们都能冲破束缚自身的樊篱,获得自由。而且,在每一部作品的最后,我们都能听到她们坚定、骄傲的声音:“听着,布拉姆——”,“听着,尼克——”,……“听着,上帝——”。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玛·劳伦斯的作品正是昆德拉所指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他认为,“小说是对于‘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44〕从“马那瓦卡”系列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刻画来看,玛·劳伦斯没有停留于困惑,也不曾终止于悲观;而是从困惑走向思考,从悲观走向人的反抗,从思考与反抗走向人的自觉,也许这才是劳伦斯的含义?
最后,让我用戈登·莱特福特的一首歌中的几句歌词来为玛·劳伦斯对雷切尔的刻画作一结语:
你将会收集梦想呢
还是将聚敛财富?
你怎么能找到财富
假如你找不到自己?〔45〕
注释:
〔1〕《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2〕〔4〕〔5〕〔6〕〔7〕〔8〕〔9〕〔10〕〔11〕〔12〕 〔13〕〔14〕〔16〕〔17〕〔18〕〔19〕〔20〕〔21〕〔22〕〔24〕〔25〕〔26〕〔27〕〔28〕〔29〕〔32〕〔33〕〔34〕〔35〕〔36〕〔37〕〔38〕〔39〕〔40〕〔41〕〔43〕Margaret Laurence:A Jest of God.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96.第 1,1,19,68,203, 82,99,114,214,108,117,39,96~97,97,98,172,239,18,71,43,58,46,57,63,45,69,218,56,121,144,71,81,197,239,148,246页,笔者译。
〔3〕Good News Bible.American Bible Society,1976.Genesis第33~35页,笔者译。
〔15〕〔23〕HelenM.Buss:Mother and Daughter Relationshipsin the Manawaka Works of Margaret Laurence.Victoria:Universityof Victoria,1985.第34、33页,笔者译。
〔30〕〔31〕〔42〕Ed.D.R.Matuz:Contempomary LiteraryCriticism:Sartre.Detroit,Michigan:Cale Research CompanyBook Tower,1988.第474,477,478页,笔者译。
〔44〕转引自仵从巨“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外国文学研究》,人大书报资料中心 1997年第2期,第76页。
〔45〕Gordon Lightfoot,"Sit down Young Stranger",If youcould Read My Mind,Reprise Records,no.6392.笔者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