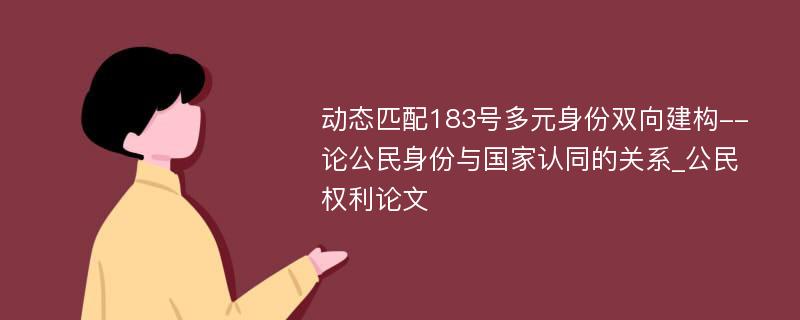
动态匹配#183;多元认同#183;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向论文,公民论文,身份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2-0160-09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g Giddens)曾言,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是特定国家的“公民”,而且也无不注意到国家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多样性角色①。公民在国家中的这种地位一方面形成了个体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另一方面则使个体对国家形成复杂的情感关系,尤其是“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从最简单的角度衡量,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似乎是一种简单对应的关系,即取得了某个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体,他在政治上所认同的也相应地会是这个国家。生理和政治上生活在某个国家而心理上却认同另一个国家的情形似乎是反常的、不合理的。通过对现有相关理论的检视和将它们置于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有着更加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还可以是模糊或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要理解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所了解。按照著名公民身份理论家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的界定,公民身份表示个体在国家中拥有的正式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②。公民身份理论通常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大传统。前者强调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公民责任和公民情感的重要性。由于权利通常是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谈论公民身份的时候,通常把它看作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二是公民的情感与归属。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公民身份“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③。“认同”(identity)则通常表达了三种涵义:一是“同一”、“等同”,指事物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所具有的连贯性;二是“确认”、“归属”,指个体或群体辨识自己的特色,确认归属于哪一类属;三是“赞同”、“同意”,指个体或群体对事物或观点所持的肯定态度④。认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群体认同、政治认同等。国家认同只是各种认同形式当中的一种。它既包括对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运作等的政治认同,也包括对领土主权、民族同胞、象征文化等的文化认同。例如,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他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⑤社群主义者沃尔泽(Michael Walzer)也注意到“国家认同包含政治与文化两个面向”⑥。
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基础。但是,一方面,由于拥有同样身份地位的公民通常归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如民族、种族或者族群,导致他们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经常脱节,甚至是背离,从而使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另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支流四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也被楔入了许多失谐的因子。这表现在,公民身份不仅在范围上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形成欧洲公民身份等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出现性向、生态、文化等其他公民身份类型。公民身份的变化不仅给以国家和权利作为言说对象的传统公民身份造成张力,而且还使公民的政治认同超越国家的层次,表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面对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日益增加的张力,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思考,出现了“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维系论”从国家认同是维系公民身份的最有效手段的角度出发,认为公民身份如果不与国家认同结合在一起,将会使自身变成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维系论”的这种看法与其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公民身份的立场相一致。在它看来,公民身份如果不建立在共同历史、政治文化和共同命运感的基础上,将导致自身变成一种纯粹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简单互惠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不仅将导致公民身份变得虚弱无力,而且还将损害到国家,使之除了能够为其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之外无能为力。在它看来,公民身份倘若要变得富有含义和坚强有力,那就必须与国家的历史、象征、民族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例如,金里卡认为:公民身份涉及在各种选项之中作出选择,而共同体文化则不仅提供了这些选项,而且还使公民身份变得富有意义⑦。德沃金也认为:共同体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用来识别有价值的经验的眼镜”⑧。言下之意,共同体文化构成了公民身份的底色,个体落实其公民身份的能力依赖于其认同和掌握共同体文化的能力⑨。从这种立场出发,“维系论”认为,对于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优先于公民身份。文化认同是公民身份存在的土壤,只有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公民身份才会变得充满意义、才能得到实现。
“切割论”则从对立的立场出发,试图割裂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将公民身份扩展到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外。这一观点认为,国家认同尽管重要,但它并不是公民惟一的认同形式,宗教、阶级、性别、环境等也是公民认同的基本对象。既然公民认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切断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就未必导致前者失去其文化之根和变得空洞无物。更有甚者,以文化差异作为公民身份存在的理由,将导致公民身份更加具有排斥性,使主流民族或种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无法真正享有公民身份。除此之外,“切割论”还从全球化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已不再构成全球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结点,跨国公司组织、全球NGO组织以及大量其他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一起共同编织起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治理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已不再能够单独通过民族国家而得到维持。同时,从公民身份的责任来看,当今环境破坏、全球不平等、全球移民等问题的涌现也要求我们割裂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固定关联,思考自身与其他共同体的责任。以全球移民为例,跨国移民的加速使民族国家的构成明显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倘若要建立平等而有序的社会,那就必须利用公民身份的平等精神,并且将它与民族、国家等观念分离开来”⑩。总之,不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的角度衡量,公民身份都必须割裂与民族国家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公民身份的普遍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排斥性之间的矛盾,划清公民身份与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界限”(11)。
如果说“维系论”和“切割论”代表了两种对立的立场的话,“匹配论”则是一种更加细致的主张。它既不主张将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割裂开来,也不赞同简单地以共同体文化来维系公民身份。在它看来,要理解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首先必须对这两个概念作更细致的分析。不论何者,都存在着不同的种类划分:公民身份可以划分为以权利、义务为导向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以公民文化、心理归属为导向的“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国家认同则可以划分为对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持肯定态度的“赞同性认同”和对领土、主权、人口、历史等持归属态度的“归属性认同”。在划分不同公民身份和不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匹配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的实际上是一种彼此匹配的逻辑关系,即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赞同性国家认同相匹配,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则与归属性国家认同相匹配。前一种国家认同聚焦于国家制度,由此形成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宪政爱国主义;后一种国家认同则专注于对国家领土、国家历史、国家文化和祖国同胞的认同,并由此形成一种深沉的“在家的感觉”和情感投入(12)。通过对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细化和相互搭配,“匹配论”试图超越前两者形成的认识论困境。
从总体来看,三种观点显然都存在其合理之处,面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基础日益为全球化浪潮所消蚀的倾向,“维系论”试图重新夯实公民身份的文化根基。同样面对日益强化的全球趋势,“切割论”则试图彻底割断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使公民身份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匹配论”与“维系论”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但又显得比后者更加细致和深入,它不仅看到了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不可分割性,而且还试图区分出不同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联。三种观点尽管表面上显得差异迥然,但仔细检视它们后面所隐含的各种假设,可以发现,它们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把公民身份看作一种固定的法律地位,都把国家认同看作个体对国家的固定情感指向,都试图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建立起某些固定的关联等。如何审视三种观点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把对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理解推向深入,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在这一核心问题的观照下,本文接下来将依次探讨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与“维系论”和“匹配论”相关联,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是否只是一种或两种清晰而固定的搭配关系?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模糊或者动态的匹配关系?
第二,同样与“维系论”和“匹配论”相关联,国家认同是否只是对制度和文化的认同,国家认同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形式?
第三,与上述三种观点相关联,国家认同是否只是共同体文化的产物或者公民理性地选择的结果,它能否是两者互动的产物?
针对前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承认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某种匹配关系,意味着必须对“切割论”的观点作更细致的分析。“切割论”主张公民身份必须彻底摆脱民族国家以及负载其上的国家认同的羁绊,使公民身份具有容纳全球化所带来的含义复杂化趋势的潜能。但是,在本文看来,无论全球化给当今民族国家带来了何种冲击,任何有关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时代已经结束的断言都为时尚早(13)。毋宁说,当今时代更是一个民族国家日益净化自身而成为普遍化的时代。因为在此之前,民族国家总是与其他政治组织形式(比如大型帝国)等同时存在。在当今时代,随着两极格局所荷载的意识形态争斗的瓦解,“民族国家的观念第一次为每一个人所接纳,他们都试图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14)。既然民族国家没有消失,公民身份很大程度上也就仍将以民族国家作为言说对象,后者也就仍将是形构公民国家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切割论”的反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接受“维系论”和“匹配论”的观点。“维系论”主张公民身份必须以共同体文化为基础,建立起共同体文化与公民认同的单一匹配关系。“匹配论”则更进一步将“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文化—心理公民身份”相区别、“赞同性国家认同”与“归属性国家认同”相剥离,从而表明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匹配关系。“维系论”将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化约成了单一的文化形式。“匹配论”尽管比前者更加细致和深入,但其“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赞同性国家认同”相匹配、“文化—心理公民身份”与“归属性国家认同”相匹配的双线匹配论也存在简单和武断之嫌。从简单的一面来看,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晚期现代性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公民身份也明显超出“匹配论”所归纳的两种形式。如果公民身份不止这两种形式,那么,与之相应的国家认同也就不会是两种,而是多种。基于此,其对于两者关系的概括也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概括。这一点在下一节将会重点论述到。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承认它只存在“赞同性国家认同”和“归属性国家认同”两种形式,“匹配论”所提出的这种双线匹配关系也显得武断,因为它后面表明的是两种相互矛盾甚至是相反的认识论立场:在共同体文化面前,个体只能消极地认同和归属于它(归属性国家认同);在国家的法律制度面前,个体则有充分的主体和理性意识,能够自主决定是否该赞同还是反对它们(赞同性国家认同)。生活在某一文化场域中的个体是否果真如此无能为力,自身的认识只能消极地由前者所形塑?生活于某一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个体是否就果真具有如此高的自主性,能够冷静和理性地决定自身对于它们的态度?实际上,一方面,从两者关系的角度来看,政治法律制度根本无法完全与共同体文化割裂开来,因为前者通常是在后者所提供的土壤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外在制度”、后者主要体现为一种“内在制度”的话,那么,“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内在演变出来的制度互补”(15)。另一方面,从人类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何种场景下,人类认识都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在外在制度的背景下人类就具有充分的认知能力,而在内在制度的背景下则完全被其支配的情形。这也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表明的基本观点:一方面,所有的人都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另一方面,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又总是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既来自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又来自行动的意外后果(16)。如果制度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分类不是如此泾渭分明,那么,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匹配关系也就会变得更加模糊。
另外,“维系论”和“匹配论”都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建立起一种固定的匹配关系,而未看到两者关系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反映了民族与国家之间时而融合、时而紧张的关系。“匹配论”所区分的两种公民身份分别对应于民族和国家两个共同体。实际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至少也包括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两个过程(17)。政权建设使民族国家建立起统一的、排他性的权力体系,民族建设则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了文化和心理的合法性源泉。但是,在当今世界,单一民族国家的情形毕竟少之又少,一个国家拥有多个民族或者一个民族分布在多个国家的情形比比皆是。这对同时兼为两个共同体成员的个体的情感认同会造成何种影响?答案是,如果民族的边界与国家的边界真正吻合,那么,“匹配论”所持的匹配关系或许会是有效的;如果相反,两个共同体的边界并不重合,尤其是发生民族挑战国家的极端情形时——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前南斯拉夫以及当今许多其他国家频频发生的内战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公民的归属性认同所指向的或许更是民族,而与国家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出现极端情形,即公民的归属性认同指向另一个他不生长于其中、但却为其民族所主宰的国家,而其赞同性国家认同则指向自身生长于其中、但不为其民族所主宰的国家,从而形成两种国家认同彼此背道而驰的情形。白鲁恂说“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18),反映了这方面的含义。它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匹配关系并不是那么固定。取得了某个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体,既可能在情感上对这个国家形成归属性认同和赞同性认同的统一,也可能导致两者分道扬镳。当今为民族分离运动所累的许多民族国家至少反映了这方面的因素。撇开这种极端的情形,一个国家新型民族政策的出台、民族关系的变动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等也可能导致两者关系表现出动态性。
不论是“维系论”还是“匹配论”,都只将分析的视野集中在民族国家内部,没有看到当今国际移民浪潮下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转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即从原来个别和偶然性质的移民转化成为群体、永久性质的移民(19)。不仅移民的规模迅猛扩大,而且移民的区域也相对集中,美国、西欧和大洋洲成为国际移民的集中地。相关统计资料表明,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外国移民均超过本国人口的5%,瑞典的比例甚至高达19.9%(20)。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移民的国家认同呢?“维系论”没有把分析的视角扩展到这一领域;“匹配论”则提出,他们可以对移入国持赞同性国家认同,而对母国持归属性国家认同。后一种观点对于刚移入他国的移民来说或许如此,但不能保证在较长时间内同样有效。随着移民在移入国居住时间的推移,他们不仅可以对移入国的政治制度产生赞同性国家认同,而且可以对它形成归属性国家认同,这对移民的后代来说尤其如此。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什么移入国会要求移民在本国居住数年之后再举行入籍和归化宣誓的原因。宣誓本身是移民对移入国产生情感归属的反映。这些情况说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匹配关系并不像“维系论”和“匹配论”所说的那样稳固,国际移民不仅可以改变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匹配关系,甚至可以根本改变公民的国家认同。
上述分析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并不像“维系论”所说的那样,是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单线对应关系,也不是像“匹配论”所说的那样,是两种公民身份与两种国家认同之间的双线对应关系。一方面,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纠结、人类认识能力的特性等因素可以模糊二者的划分,从而使不同国家认同的划分变得模糊。另一方面,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国际移民等因素则可以使二者的关系表现出动态性。概言之,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匹配关系,两者的关系通常是模糊的和动态的。
“维系论”和“匹配论”都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建立起某种强固性关联,这使它们看不到国家认同的其他形式,从而忽略了“切割论”所具有的长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切割论”主张拆散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之间关联的做法有什么可取,而是说其从全球化的立场理解公民身份和从多元化的角度理解国家认同的做法具有合理之处(21)。按照“切割论”的观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国家认同对于公民来说尽管重要,但它并不是惟一的认同形式,除此之外,宗教认同、民族认同、性别认同、环境认同等也很重要。“切割论”所说的其他认同有许多不能纳入国家认同的范畴,但这并不排除国家认同同样具有多重表现。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超越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单一民族国家的视界,从阶级关系、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的视角做出分析。
阶级因素不仅可以使赞同性国家认同与归属性国家认同的关系变得复杂,而且还可以催生新的国家认同形式,如阶级认同、规划性认同等。前面所说的三种观点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不论处于何种社会地位的公民,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都是同质的,具体体现在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具有相同的认同程度上。事实是否如此?如果我们把阶级的因素引入分析的视野,可以发现,这种同质性假设事实上并非如此,国家认同后面隐含着更多复杂和多元的因素。不言而喻,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公民群体都分属于不同的阶级或者阶层,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只存在一个阶级的情形。公民的阶级划分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认同的裂变,另一方面则为国家认同增添了新的因素。从前一方面来看,可能形成的结果是:公民尽管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所处的祖国,但却无法从政治上对自己的国家产生认同感——因为正是这些政治制度造成了部分公民屈居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事实——从而造成前文所说的赞同性国家认同与归属性国家认同背道而驰的情形。从后一个方面来看,阶级分化催生阶级认同。阶级认同尽管属于群体认同的形式,但在性质上却无疑属于政治认同,并且与国家认同紧密相关。统治阶级由于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可能形成阶级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与之相反,被统治阶级则可能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而形成政治认同与阶级认同的背离。阶级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当阶级斗争趋于和缓平静之时,整个公民群体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更趋于一致。当阶级斗争变得激烈之时,两种认同的分离程度也相应越大,下层阶级对于本阶级的阶级认同很可能超过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另外,曼纽尔·卡斯特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认同形式: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是一种不同的生活规划,有可能是以被压迫者的认同为基础”(22)。对下层阶级而言,他们对于理想国家的“规划性认同”很可能超过对当前国家的认同。这一点在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未来国家的设想中可以得到印证(23)。
超出一国的视野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和敌对关系可以建立起公民对于本国的“差异性认同”。“维系论”和“匹配论”在分析国家认同的时候,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民族国家内部,没有认识到国际关系、国际安全所建构的差异性认同。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在《认同的空间》中提出“差异构成了认同”,认同涉及排斥和包含的关系(24)。前文刚刚谈到,曼纽尔·卡斯特区分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认同,抗拒性认同是其中之一。抗拒性认同建立在反抗既有社会体制或者其他国家的基础上(25)。将这两种认同理论结合在一起,可以表明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在形构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国家认同可能被某些外敌(他者)的存在所强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在英国,曾经存在着一个著名的有关国家认同的研究,认为英国的国家认同是从与法国的长期敌对状态中塑造出来的(26)。百年战争的结果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不太一样,但对两国动员民众反对外部威胁、创造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在地理上分开纠结在一起的法国和英国,形成民族国家来说,意义却是一样的。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民族主义,但荷兰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原来为对抗外敌而凝聚起来的民族主义对国民的感召力随着“他者”的消失而弱化,由“他者”所界定的国家认同也开始出现危机(27)。类似的观点或许还能说明前苏联出现的情况。在进行卫国战争的过程中,联邦各共和国的人民逐步建立起对苏联的国家认同(28),但随着外部敌人的消失,苏联的国家认同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并被迫重建。
“阶级”、“外敌”的视角尽管是催生新型国家认同的因素,但它们仍然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然而,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对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又将产生何种影响?“维系论”、“匹配论”和“切割论”在提出其观点时隐含着一种假设:公民的国家认同是排他性的。正是假定公民在政治和文化上只会认同于自己的祖国,“维系论”和“匹配论”都主张将公民身份重置于民族国家的樊篱之下,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同体文化来充实公民身份的基础。“切割论”则主张切割民族国家与公民身份的关系,使公民身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里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国家认同是否具有排他的性质?公民除了在政治和文化上认同于自己的国家以外,能否再认同于其他的政治共同体?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将“全球化”引入分析的视野。它将表明,国家认同并不是排他性的,公民在认同自己国家的同时,还可以持有“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
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发展潮流催生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旋律,夹杂着政治、文化等复合变量的全球一体化趋势;二是以地方自治、地方独立为主旋律的地方化趋势。与这些发展趋势相一致,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化。从公民身份的一端来看,除原有的国家公民身份以外,超国家公民身份和亚国家公民身份也得到发展。从国家认同的一端来看,则体现在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同时得到发展上。鉴于前文已经对单一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多有论述,这里将主要集中在超国家公民身份、亚国家公民身份所导致的各种认同上。超国家公民身份集中体现在欧洲公民身份(European Citizenship)的发展上。1993年,随着欧盟条约(通常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欧洲公民身份也正式得到确立。这意味着,公民除了拥有成员国的公民身份以外,还正式拥有了“欧洲公民身份”。欧洲公民身份不仅赋予成员国公民相应的公民身份权利,而且还力图形成公民的欧洲认同感。为此,欧盟发行了自己的护照、设计了自己的盟旗、采纳了自己的盟歌。尽管时下成员国公民对于欧盟的认同程度还体现得参差不齐,但它无疑已成为公民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29)。与亚国家公民身份携手同行的是亚国家认同的发展。亚国家公民身份不仅体现在联邦制国家成员单位的公民身份上(如美国各州的公民身份),而且还体现在城市公民身份(municipal citizenship)的复兴上(城市公民身份在中世纪意大利等国的城市共和国中早已存在)。与亚国家公民身份的发展相一致,公民的亚国家认同(如对于城市和地方共同体等的认同)也得到发展,甚至出现“在地方主义得到发展的地方,地方认同和权力通常比国家当局所拥有的认同和权力要大得多”的情形(30)。
以上分析表明,国家认同并不像“维系论”和“匹配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政治或者文化因素的结果,它还存在其他的形成性因素和表现形式。公民的阶级地位不仅可以引发赞同性国家认同与归属性国家认同之间的错位,而且还可以催生阶级认同、规划性认同等国家认同形式;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和敌对关系可以催生公民的差异性认同;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促进了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的发展,使公民的国家认同更趋复杂化。
国家认同是否完全是公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切割论”在这一问题上语焉不详,“维系论”和“匹配论”则持彼此相反的立场。在“维系论”看来,共同体文化是公民身份的底色,文化使公民身份变得充满意义。言下之意,文化决定了公民的认同结构。“匹配论”在评价自身意义时则提出:“一方面,它可以为公民理性地确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提供策略性选择……另一方面,它可以为国家(政权系统)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战略性指南。”(31)从“能动”(agency)与“结构”(structure)的角度衡量,“维系论”代表的是“结构决定论”的立场,其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个体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32)。“匹配论”代表的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强调公民在形构国家认同时所具有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在形成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作用。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国家认同到底是公民理性选择的结果还是国家有意识地培养的结果?“匹配论”尽管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综观其分析,它实际上站在前一立场上而忽略后者的作用。本文无意忽视公民在建构自身国家认同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但同时认为,国家认同也是社会结构性力量的产物,尤其是国家政权有意识地“培养”或者“灌输”的结果。从总体来看,国家认同是个体“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重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来看,“维系论”、“匹配论”分别代表了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种对立的立场。客体主义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作为典型,两者尽管存在某些明显的差异,但都倾向于把自然和客体置于分析的核心,强调社会整体相对于个体所具有的至高无上性。主体主义则以解释社会学作为典型,集中体现了客体主义所一贯反对的“人本主义”立场。在它看来,相对于人类行动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行动和意义,而不是客体主义者所一贯强调的结构与功能,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解释人类行动的意义来理解人类社会的整体构成。把这些立场与“维系论”、“匹配论”的立场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前者把共同体文化看作是公民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代表了客体主义的核心主张;“匹配论”则把国家认同看作是个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反映了主体主义的特征。问题在于,在人类认识形成的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离开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认识活动将无由开展;反过来,离开了客体因素,人类的认知活动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对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立场进行了有力的综合,并且提出了前文提到的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存在,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结合在一起的各种社会实践”(33)。
将这种观点用于分析国家认同,可以看出,公民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是一种彼此互动而不是彼此分离的关系:一方面,国家认同的形成以公民所具有的能动性作为基础,离开了公民的理性和主体性,国家认同的形成也就无由谈起;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则是公民个体形成其国家认同的条件和环境。后者尤其体现在通过国家政权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上,国家政权通常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有意识地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公民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通过历史经验得到印证。以移民为例,移民的国家认同建构最能反映旧国家认同与新国家观之间的互动作用。当某个公民移居到另一个国度,其内心通常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考验。例如,由于“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而带来的是否该认同移入国文化的考验,由于政治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带来的是否该认同移入国政治制度的考验,由于社会生活差异而带来的是否该认同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考验等。对于这些考验的反应方式和适应过程也就是移民理性地重建自身国家认同的过程。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在谈到美国早期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时,霍华德·芒福德·琼斯指出:“旧世界把关于习惯、力量、实践、价值和假定的一套丰富、复杂而矛盾的体系投射在新世界;而新世界接受、改变或拒绝这套体系,或用自身的发明来融合它。”(34)正是通过旧国家认同与移民新观念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同样的情形也反映在两极格局瓦解之时。1989-1991年,伴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瓦解,两极格局也宣告结束,前苏联裂变为15个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人们的国家认同也开始迅速调整,“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35)。
提出国家认同是公民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双向互动的产物,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持一种僵化的立场,认为不论在何种条件下和任何一种认同中,主体与客体总是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毋宁说,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总体性立场。随着时间和条件的转移,主体与客体所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尽相同,这尤其体现在国家所发挥的作用上。为了促进公民的国家认同、提高国家的合法化水平,国家通常会有意识地对公民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要印证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经验加以分析。19世纪德国俾斯麦统治时期,国家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扮演着一种微妙角色。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而实现统一的德国以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作为基础。不论是君主、贵族还是教会,都不愿把普遍的公民权利给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权力的排他性、私有性和专断性(36)。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水平,俾斯麦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将公民身份权利分离开来,有意识地发展公民的社会权利(建立福利制度),但却抑制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另一方面,进行大规模义务教育,向学生灌输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要求他们在观念上认同和忠诚于自己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德国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而且还使人民的忠诚、义务和认同程度得到明显提升(37)。通过政权的力量来塑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或许还体现在此后出现的纳粹统治上。在这一时期,宣传和恐怖构成了极权统治的双轮。正如科恩所指出的那样:“若无宣传,恐怖就会失去其大部分心理效果;若无恐怖,宣传就无法包含力量。”(38)如果上述情况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些特殊的情形的话,那么,通过历史教育、爱国教育、文化教育等手段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却是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惯常手段。
由此可见,国家认同的形成既不像“维系论”所说的那样,是共同体文化决定下的产物,也不像“匹配论”所说的那样,是公民理性地进行选择的结果。人类认识起源于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互动。把这一认识论立场用于分析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可以看出,国家认同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尤其是国家)“结构性制约”的结果。但是,在国家认同形成的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通常体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中某一方可能更居于主导地位。
注释:
①Anthony Giddens.Sociology: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82,p.17.
②Thomas Janoski.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9.
③[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④肖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⑤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90页。
⑥转引自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第93页。
⑦⑨Will Kymlicka.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83,pp.8-9.
⑧Ronald Dworkin.A Matter of Principl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28.
⑩T.K.Oommen.Citizenship,Nationality and Ethnic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pp.21-22.
(11)Keith Faulks.Citizenship.London:Routledge,2000,p.37.
(12)肖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3)例如,日本政治学家大前研一就曾作类似的断言,参阅Kenichi Ohmae.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cs.New York:Free Press,1996.
(14)[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5)[德]柯武刚、史漫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6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第408-409页。
(1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英]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9)Anthony M.Messina.The Logics and Politics of Post-WWⅡ Migration to West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
(20)Ibid.,pp.3-4.
(21)[英]基思·福克斯著、郭忠华译:《公民身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136页。
(22)[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5-307页。
(24)[英]戴维·莫利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25)[美]曼纽尔·卡斯特著、曹荣湘译:《认同的力量》,第6-7页。
(26)转引自[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7)郭艳:《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展国家:国家认同遭遇“去中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28)[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29)Maurice Roche.Exploring the Sociology of Europe.London:Sage,2009,pp.219-221.
(30)Derek Heather.What is Citizenship?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132.
(31)肖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2)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London:Palgrave,1979,p.2.
(33)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p.2.
(34)[美]迈克尔·卡门:《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3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6)Michael Mann.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Sociology,Vol.21,1987,pp.339-354.
(37)Charles 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78.
(38)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440页。
标签: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移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