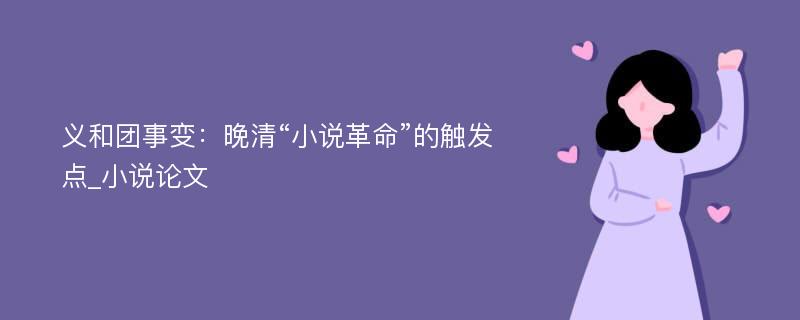
义和团事件: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和团论文,晚清论文,事件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倡“新小说”,鼓吹“小说界革命”。此举得到社会普遍响应,次年(1903)即出现了晚清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第一次高峰,据统计该年产生的小说总计高达一百四十七部,比此前数十年产生小说的总和还要多①。是什么因素促使小说产生如此巨大而迅猛的转变?对此学界已作了种种探讨,在已知的各种因素当中,研究者大多强调现实政治的重要作用。如有学者便认为:“事实提示我们,在1901—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的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② 不过,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研究者忽略了,即现实政治如何与小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或者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触发点是什么,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予以专题讨论。此点不明,二者关系不唯难以坐实,而且也无法将研究推向深入。本文即针对此一问题,通过对晚清“小说界革命”触发点的探查,及其如何触发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问题予以辨析,以期对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作更为具体的考察。
一
在研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时,笔者对其批判传统小说的文字作了仔细分析,与以往仅泛言“诲淫诲盗”相比,他增加了“言鬼神”一项重要内容,如该文中说:“吾中国人妖巫狐兔(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③关于梁氏的另一条材料更能确切地说明这一点,他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谓人类之公性情,一曰英雄,二曰男女,故一切小说,不能脱离此二性。可谓批郤导窾者矣。然吾以为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庸性焉,曰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该尽中国之小说矣”④。神怪小说是传统小说的一大门类,与所谓“诲淫诲盗”的小说相比,它所遭受的指责要少得多。王韬曾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不过为下愚人说法:明则有王法,幽则有鬼神,盖惕之以善恶赏罚之权,以寄其惩劝而已。”⑤ 正是出于神道设教的考虑,统治者对神怪小说的态度往往较为宽容,梁启超曾云:“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无愆尤。”⑥ 士大夫不仅不避讳谈鬼论神,甚至创作神怪类的小说也是常有之事。因此,朝廷禁毁小说不唯甚少涉及神怪小说,而且士大夫批判小说,也往往泛言“诲淫诲盗”,而不及“言鬼神”——就其总体而言。“言鬼神”被重点提出显然别有缘故,这起因于义和团与小说的直接关联,而且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亦与此有直接关系。这些问题暂且留待后文讨论,这里先讲义和团与小说有何直接关联。义和团与小说的直接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义和团的咒语多出自于小说。义和团又名义和拳,“入其教者,虽名为习拳练技,实为演诵符咒”⑦,“练习时,由大师兄拈香诵咒,其人即昏然仆地,俄顷倔起,谓之神来附体,则面目改异,辄自称‘沙僧、八戒、悟空’之类,狂跳踊跃,或持刀矛乱舞,呼啸如狂醉”。经过如此演练,拳民以为术成之后,即可“矢石枪炮,均不能入”⑧,以致“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⑨。关于拳民所诵咒语的内容,罗惇曧这样记述道:“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⑩ 这一咒语在各地与义和团有关的史料记载中,多有反映,其中所请神灵全为小说中人物。义和团的咒语当然非止此一种,但多数源于小说,劳乃宣说:“彼符咒法术之说,仍稗官戏剧,游戏装点之词。”(11) 龙顾山人亦云:“拳中神咒多出稗野,如《封神传》之姜太公,《西游记》之孙行者,皆所崇奉。”(12)
第二,义和团神拳仪式的主要特点是降神附体,其所奉神祗大多来源于小说中的人物。据《清鉴》载,义和团法术“以降神为主,佩符诵咒,谓有神降附其身,所降之神,多半小说所云樊梨花、刘金定之类,男子则孙行者、猪八戒、李太白、刘伯温之类”(13)。义和团所奉神祗中的小说人物,据时人记述,常见者主要有:梨山老母、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灌口二郎神(杨戬)、龙王三太子、柳树精、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梅山七弟兄、南极仙翁、太上老君(《西游记》);刘玄德、关公(关羽)、赵子龙、马孟起(马超)、黄汉升(黄忠)、华佗、诸葛武侯(诸葛亮)、关平、张飞、周仓、王平、马谡、姜维(《三国演义》);武松、九天玄女、宋江、李逵、燕青、张天师(《水浒传》);黄飞虎、姜太公、黄天化(《封神演义》);冷于冰(《绿野仙踪》);黄三太(《彭公案》);济颠(《济公传》);尉迟敬德、秦叔宝、李元霸(《隋唐演义》);杨继业、穆桂英、杨宗保(《杨家府演义》);常遇春、胡大海(《英烈传》);黄天霸、张桂兰(《施公案》);樊梨花(“说唐”系列小说);刘金定、高君保(《宋太祖三下南唐》);汉钟离、铁拐李、何仙姑、张果老、吕洞宾(《八仙出处东游记》);展昭、白玉堂(《三侠五义》);岳飞、岳云(《说岳全传》)。虽然义和团所奉神祗还有其他来源,比如历史人物、佛教、道教等,但亲历者都一致认为主要来源于小说,如吴永说“率以出于《西游》、《封神》、《三国》、《水浒》诸小说者为多数”(14),罗惇曧则强调“《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15)。除奉小说中人物为神外,有些拳民甚至直接冠以小说人物的名号,如“菩萨”、“赵云”、“关老爷”、“周仓”、“唐僧”、“关平”、“黄天化”、“黄天霸”、“黄忠”(16) 等,充当运动的带头人。
第三,拳众对小说及戏剧舞台上情境的模仿也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观层面的道具的模仿上,如拳民的服饰与所持之“武器”,柴萼《庚辛纪事》中有云:“其坛主之富厚者,更为其党制备衣履刀矛,装束一如剧中之武生,恒执木棍招摇过市,美其名曰‘二郎神棍’。”(17) 另如龙顾山人说:“拳众侈述所用兵器有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引魂幡、捆仙绳、翻天印、火扇子种种。”(18) 此外,还有所谓的“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亦为拳民崇奉的常见“宝物”。这些“武器”大多出自《封神演义》与《西游记》诸小说。拳民以为这些“武器”具有神力,以至“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置之棚中,认为至宝。凡盗窃神物名曰‘盗宝’,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之利不足惧也”(19)。除道具外,拳民对小说戏曲中对白、行为方式及场景的模仿也十分引人注目,如下文:
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以至阖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神气极可笑。(20)
红灯照皆处女为之,亦安炉奉香。每出行,数十为群,左手执帕右执扇,皆红色,拦街舞蹈,若跑秧歌状。前后以黄衣力士护卫。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候其过尽乃行。其附体之神,则有樊梨花、穆桂英、张桂兰、刘金定等类,亦摭自说部。(21)
通过这些描述,义和团与小说,尤其是神怪小说的密切关系已十分明显。就史料反映的丰富程度而言,此点为时人所习知亦是无可置疑。那么,就此一点是否就能使“言鬼神”的神怪小说凸显出来,从而成为人们批判的焦点呢?问题当然不会如此简单,这还需要从它的实际影响说起。加入义和团崇信神怪小说的,非止所谓的下层“愚民”,“当其初起事时,亲藩倚之,政府信之,士大夫称许之,愚民附和之”(22),可谓是上自朝廷,下至士夫,“一唱百和,举国若狂”(23)。当然,朝廷与士大夫借重义和团可能有种种原因,如排外等,但也与其信仰基础有密切关系。在义和团起事之初,有不少士人认为义和团的“神术”可信,并建议当政者重用义和团,左绍佐在《上徐桐书》中就说:“神道设教,尚有明文,狄青以卜钱鼓众,而勇气百倍;张良圯上之书,诸葛鱼腹之阵;神兵之术,信而有征。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辟易万人……又况其禁炮之术,皆万众所目验而无疑者哉……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其所奉者,关帝、至圣先师孔子及我圣祖仁皇帝也。”(24) 御史刘家模在上书朝廷的奏折中,也称义和团的“神术”可用,他说:“闻义和拳由僧授法,本神道设教之意,取八卦方位,分立各门教人,立坛供奉,练习拳勇,诵其咒语,若有神附,至一百零八日而成。其法如掩枪炮,避刀矛,炼光为火,几疑于怪诞不经。然以武侯借风、蚩尤作雾之类推之,亦未必毫无凭信。况夫心者人之神明,神依人而行,随心为用,至诚故能相感。”(25) 所以时人云“当其邪焰突起,虽号称荐绅先生者流,咸皆俯首听命于神,妄冀‘扶清灭洋’之实现,蚩蚩者更无论矣”(26),诚非虚语。这最终影响到了朝廷的决策层,事败后朝廷下发的一份上谕这样说:“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27) 上谕说“深信邪术”的“诸王大臣”挟制朝廷酿成大祸,并非完全属实,实际是这些“诸王大臣”说服了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曾在西狩途中接待慈禧并受到特别嘉奖的吴永说:“太后一日且为予缕述出宫情事,谓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28)
综上所述,在时人眼中,义和团与小说,尤其是神怪小说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灾难,是以往任何类似事件都无法比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朝廷与“素称读书之士大夫”也参与进来,与所谓的“愚民”一般无二。所以梁启超在事变后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说:“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而我二十余省之山河,四百兆人之性命,遂将从此而长已也。是不可不深长思者也。”(29) 国人如此“深长思”,“神怪小说”被重点提出不亦宜乎?
二
义和团之变被时人称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30),可见创痛之深,所以从官方到士人均展开了对事变发生原因的全面检讨。经过反思,人们普遍认为导致事变发生的主要根源是民众的愚陋迷信,而民众的愚陋迷信则完全是由小说教育而成的,所以归根到底小说是罪魁祸首。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该文认为义和团的出现“不始于今日”,“综其本末,乃是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其所列“四种新物质”中的第二种即“小说派”,并说:“此派之人,其脑中本洞然无物,仅有一种小说流入其脑而据之。支那小说,总不外四个缘故,一曰佳人才子,二曰仙人传授,三曰兴兵平番,四曰富贵团圆。案第一条、第四条常人之所乐有也,而非第三条不足以致之。欲致第三条,非得第二条不能。以故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登时确信以为实。然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31) 这里将小说,尤其是神怪小说视为义和团事变的主要根源的观点,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舆论。
事变发生的当年,邱炜萲也针对义和团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夫小说有绝大隐力焉。即以吾华旧俗论,余向谓自《西厢记》出,而世慕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浒传》出,而世慕为杀人寻仇之英雄好汉多;自《三国演义》出,而世慕为拜盟歃血之兄弟,斩木揭竿之军机多。是以对下等人说法,法语巽语,毋宁广为传奇小说语。巍巍武庙,奕奕文昌,稽其出典,多沿小说,而黎民信之,士夫忽之,祀典从之,朝廷信之,肇端甚微,终成铁案。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党之事,牵动国政,及于外交,其始举国骚然,神怪之说,支离莫究,尤《西游记》、《封神传》绝大隐力之发见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国家,可不慎哉!”(32) 既是“绝大隐力之发见”,则显见在时人的印象中,小说的“负面影响”至义和团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无疑给了他们以强有力的震撼。
义和团明显的鬼神信仰,很容易导引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神怪小说是事变的主要动力来源。《新小说》第六号(1903年)登载的《拳匪发难》一诗云:“运极时危出怪民,荒唐说部演封神。挥刀白战仇毛子,妖焰红镫煽妇人。蛮野方忧沦黑种,烽烟况又起黄巾。燎原未甚犹堪灭,忍令贻殃到紫宸。”这里指责拳民为“怪民”,欲以《封神》的荒唐神迹对抗洋人,结果不唯“贻殃紫宸”,而且差点使“黄人”成为“黑人”悲惨结局的重演。康有为在为《论语》作注时,也不免借题发挥道:“小说家多发怪力乱神之事。小说大行于时,则近者有拳匪之乱。故怪力乱神之事,非理之正,固深害乎人性。即鬼神之迹,虽非不正,然令举国若狂,以供木石,或方士以光影符术惑人,亦非所宜也。”(33) 鬼神之说能令人“举国若狂”,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认识,即民众脑海里装的全是神怪之类的小说,如时人云:“书符诵咒,以召鬼物,《封神演义》之学问,浸灌于髓海,其现象遂演出义和团之滔天大惨剧,斯又迷信神权之歧派也。”(34)
罗惇曧从义和团迷信神权产生的根源出发,深刻地指出这与有清一代的文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他说:“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此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35)
《庚子西狩丛谈》的笔录者刘治襄除强调神怪小说的“负面影响”外,还同时指出所谓的“诲盗”小说也是构成义和团精神原质的主要成分之一,他说:
义和拳之乱,所以酿成此大戾者,原因固甚复杂,而根本症结,实不外于二端:一则民智之过陋也。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小说,括而言之,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一为《水浒》、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36)
刘治襄称他是在“搁笔以后”,对事变进行“反复循绎”才得出的这一结论,可见并非一般的泛泛而论。由于义和团之变对社会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致使清季十年,甚至到五四运动前夕,人们都未间断对义和团事变的反思,小说作为事变主要根源的观点也几乎从未改变。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人在谈论小说对社会影响的文字中,还说:“小说之流行,亦有莫知其然而然,隐兆祸乱之先几者。南人本好言情小说,前十年间,忽自北省传入《三侠五义》一书,社会嗜好,为之一变。由是而有《彭公案》、《施公案》、《永庆升平》诸书,皆从燕、齐输入,而遂有庚子团匪之祸。”(37) 光绪三十年(1904)陈独秀曾撰文说:“鬼神本是个渺茫的东西,煽惑愚民,为害不浅。你看庚子年的义和拳,不都是想学戏上的天兵天将吗?”(38) 1918年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市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万众的欢愉声中,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被拆毁,陈独秀闻听此事,感慨万千。他认为“这块碑实拆得多事”,“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不准将来义和拳会再度发生,为警戒国民的“健忘”,他又对“过去造成义和拳的原因”作了一番总结,在五种主因中,他认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义和拳所请的神,多半是戏中‘打把子’‘打脸’的好汉,若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黄三太、黄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戏剧特盛,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模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模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非是鄙人信口开河罢!”(39)
要之,对义和团事件的反思,神怪小说的问题得以凸显,人们对传统小说“负面影响”的固有认识也更加深化与全面化了。同时,义和团的“崇鬼神”实际已使它成为中国民众迷信与非理性的一种象征,这恰与甲午战争以来有识之士提倡“开民智”的理性与科学精神成一尖锐之对立,小说与民智的关系问题迅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小说界革命”的观念亦因而得以创生。
三
义和团事变后,改革成为社会的普遍呼声。由于事变所暴露出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民众的愚陋迷信,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时下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改良民众社会。由于认定民众的迷信愚陋完全由小说所造成,因此欲改良社会,自然应以改良小说为先。
光绪二十六年,衡南劫火仙撰文说:“夫以《封神》、《西游》之离奇逼人,《三国传》之荒谬无据,尚足使百世之下,作历史观之,推崇其人,脍炙其事;且不独孚信于人民,即朝廷亦著为典则,以崇祀之……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欧美之小说……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是,其立意则在消闲……小说界之腐败,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40) 衡南劫火仙从义和团事件的总结中得出“小说界之腐败,至今日而极”的结论,并认为这是由小说“立意”为“消闲”所造成的。他将“吾邦”小说“负面影响”极端化的观点为后来者所反复强调发挥,从而使它成为晚清改良小说观念创生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
梁启超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首倡者,庚子事变以前,他并非没有提倡过小说,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就曾倡导“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振厉末俗”(41);戊戌政变后甚至还积极提倡译印政治小说,以使“爱国之士,或庶览焉”(42)。但二者均未明确提出“改良小说”的观点,而且前者仅为其政治活动之“补益”,可见并非当时急务;后者因“未能大集同志,广译多类”(43),显然影响亦十分有限。与这两次提倡小说相比,梁氏的“小说界革命”,无论是革新小说的观念还是由其所造成的影响,均可谓是一次质的飞跃。若深究其因,仍不能不归结到义和团事件上。对义和团与小说的关系,之前梁氏早已注意到“尤有咄咄怪事者,如前者日本之役,今兹团匪之难,竟有通都大邑之报馆,摭拾《残唐》、《水浒》之谰语,以构为刘永福空城之计、李秉衡黄河之阵者,而举国之人,靡然而信之。”(44) 堪称“小说界革命”理论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受到了这一认识的直接影响,如该文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前文已言及梁氏对“言鬼神”小说的重点批判源于义和团事件,而且如果将这四个设问简化归类,与前引《中外日报》将“支那小说”归类为“四个缘故”几无二致。另外,该文还直言:“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由此可见梁氏不仅认为小说是义和团事变发生的主要根源,而且还因此激起了他对传统小说的全面批判。义和团事变前,梁氏批判小说多泛言“诲淫诲盗”,而不及“言鬼神”一点,此文则重点强调了“言鬼神”,加之后来他说“以此三者,可以该尽中国之小说矣”,可见正是由于义和团事件的刺激,梁氏才展开了对传统小说的全面检讨,并因而提出了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的极端化观点。正是有此一观点作为前提,梁氏才坚定地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与以往不同的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观点甫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领了晚清小说的转型与繁荣。梁氏的观点为何会得到社会的普遍响应?海天独啸子在《〈空中飞艇〉弁言》(1903年)中说:“我国说部多名家,绮丽缠绵,盛矣!观止矣!然作者好道风流,说鬼神,势力所及,几为社会之主动力……至其崇信鬼神之风潮,几于脑光印烙,牢不可破。民间爆发者辈,亦皆假此为利器,振臂一呼,四处皆应,如先时之红莲、白莲,近时之义和团,皆职是也……今者世界文明,光焰万丈,此等网罗,允宜打破,则小说改革尚焉。顾虽言改革矣,毋如我国民,自欧势阑入,政府窘迫,一蹶再蹶而后,相顾失措,四望彷徨之时,脑筋之影泡顿渴。此时正宜慎选其材料,改换其方略,以注射之,使其新知新识,焕然充发,则小说之急于改革尤尚焉。”(45) 这里明确指出了义和团事件与“小说改革尚焉”这一社会思潮形成的内在关系,由此说明梁启超的观点不过是这一社会思潮中一个较为特殊的表述而已。当然,也许可以说这一社会思潮乃梁氏观点影响所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人们接受其观点的认知基础正是对义和团事件的深刻反思。
继《新小说》之后创刊的《绣像小说》,其创刊缘起中这样说:“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借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46) 据王学钧先生考证,此文当出自李伯元之手,且直接从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一文剥来(47)。文中提到了“庚子一役”,这无疑直接指明了李伯元提倡改良小说的缘起。《新小说》与《绣像小说》是庚子事变后出现的两个最早的小说专刊,其改良小说的启念均与对义和团事件的反思有密切关系,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另外,《庚子西狩丛谈》也为笔者的上述判断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刘治襄在对义和团事变作出深刻总结(前文已引)后,说:“拳乱初定,当局皆怵于已事,因而深筹密虑,乃以调和民教为惟一治本之至计……衡以全局,犹本中之标也。此愚民游民之两种社会,若不彻底改革,廓清涤荡,去其所以为乱之原质,任遇何事,奸人皆可以随时利用而构煽之……今欲为拔本之计,必先深求其本中之本,从改革民众社会着手。一则注重于普通教育。改良小说,改良戏剧,组织乡约里社,实行宣讲,以种种方法,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以相当之知识,递相输灌,俾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勿侈言学校普及,炫难得之远功,而忽可能之近效,则事半而功自倍。”(48) 这里明确指出防止义和团类似事件发生的根本之计是改良社会,而改良社会应以“改良小说”为先,因为学堂教育缓不济急。改良小说不唯可收“可能之近效”,亦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思想理路生动地道出了晚清改良小说提倡者的普遍心理。
类似上面的例证仍可举出一些,直接的证据尚且丰富如此,那么受到义和团与小说关系的直接影响而未明言者,就更可想见了。为进一步证实笔者的判断,下面拟就创作及一些改良小说的实际活动展开具体论述。
义和团之变后,民众的迷信神权被归因为小说的教育,因此破除迷信遂成为此后改良小说的重点之一。如吴趼人在利用《国朝先正事略·循良传》创作《剖心记》时,其中“载有李明府死为栖霞城隍神之说”,虽认为“此为旧日小说家之绝好材料”,但“以语近神怪,不合于近时社会,故略去之”(49)。甚至在创作必须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时,作者有时竟现身予以解释说明,如吴趼人《九命奇冤》第六回有言:“看官!须知这算命、风水、白虎、貔貅等事,都是荒诞无稽的,何必要叙上来?只因当时的民智,不过如此,都以为这个是神乎其神的,要这样做出来,我也只可照样叙过去。不是我自命改良小说的,也跟着古人去迷信这无稽之言,不要误会了我的意呀!”第七回又言:“哪里有什么大王菩萨,来管你这闲帐呢?不是这等说,在当日那迷信鬼神的人,大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神情。他肯叫出这句话来,正表得他是正直无私,不是赖帐的呢。不比得近来风气渐渐开了,迷信的人渐渐少了,在热心世事的人,他还在那里暗暗欢喜呢!他说好了,好了,把这神权打破了,我们中国的民智要开起来了,听天由命的话头抹煞了。”(50) 颐琐的《黄绣球》第十三回也说:“我们中国人,也不但和尚尼姑,都是迷信鬼神,如今正要破去世界上的这种迷信,岂可还用那神道设教的法子,再把《封神传》、《西游记》的影响,造起因,证起果来?”(51)
《绣像小说》甚至出现了专门破除迷信的小说《扫迷帚》,该小说第一回说:“自西汉诸儒,创五行之论,以为祸福自召,而灾祥之说大炽,于是辗转附会,捏造妄言。后世变本加厉,谓天地鬼神,实操予夺生死之权,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由是弃明求幽,舍人媚鬼,淫祀风靡,妖祠麻起。自宫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唱百和,举国若狂……日醉心于祈禳祷祝,其遗传之恶根性,牢不可破……虽学士大夫,往往与愚夫愚妇同一见识……故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欲改革习俗,而不先举层层关键,一拳打破……从实理阐起,实事作起,则胶粘丝缚,障碍多端,窃恐再更三百年,中国犹如今日。”第二回又言:“古今来乱民奸贼,又大率借此惑众,号召一切。陈胜之鸣狐,张角之妖书,大都肆荒诞之言,行煽惑之计,一般无识之民,皆受其欺而不觉,其弊之极,乃至流为庚子之拳匪。”(52)毫无疑问,该小说创作的启念显因义和团事件而起,其思路与前述诸人如出一辙。
除了著者自觉避免语怪以外,编刊小说的人也有意加以引导。关于《老残游记》刊发的一则轶事颇能说明这种情况,据言该小说第八回“桃花山月下遇虎,柏树峪雪中访贤”:
原回目为“桃花山月下遇狐”,商务改“狐”为“虎”,且删改文字。《绣像小说》刊出后始知,连先生据约责言。商务谓现方破除迷信,我辈社会中,不能再语怪。连怒,谓既有成约,约中又无语怪之禁,何得擅改,汝辈社会不语怪,我辈社会专语怪;汝尽可不登,我亦尽可不卖。(53)
此故事中的连先生为连梦青,刘鹗的《老残游记》最初是为资助好友连梦青而作的。连梦青说“汝辈社会不语怪,我辈社会专语怪”显然是一时气话,此轶事说明义和团之变后,整个社会对“语怪”的禁忌,并对小说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神怪小说自然是很难有市场的(54),而传统小说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也在无形中渐趋消解了。此为义和团事变促成晚清小说改良的显例。
此外,庚子以后各地政府与一些民间组织纷纷发起了改良小说与戏曲的实际行动,这些行动的启念往往与义和团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宣统元年(1909)四川省咨议局议员提出了《发起通俗教育社》的议案,该议案提请改良小说,并禁止发卖与宣讲《肉蒲团》、《绿野仙踪》、《金瓶梅》、《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类旧小说,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等类小说,发卖与宣讲亦需辨明其宗旨与误点。议员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议案,是因为他们认为中下层民众既不能全进学堂,又无家庭教育,往往拘墟旧习,阻挠新政,迷信邪说,妨扰治安。推厥原因总不外受小说、戏曲、宣讲等之影响。“中国小说善本绝少,非淫乱则荒唐,其最烈者如《西游》、《封神》等书,启人迷信,积之又久,以致有义合拳、红灯教之结果……农夫俗子容易蛊惑,以故壬寅(川西南红灯教)戊申(开县红灯教)之乱,多出于乡民……宣讲生(指旧日者言)每于晚间作传谕、降鸾、下阴曹、打神拳等狡狯伎俩,说神说鬼,愚人骗钱,不特为拳教之影响,而且有拳教之事实。一遇民教交涉或凶年饥岁,遂至激为大变……种种恶俗,大致不出怪力乱神四字,是非仍从通俗教育着手,改良小说、戏曲、宣讲等类不足以遏乱源”。经过一番辩论,议会同意立案,《修正后决议案》这样说:“国民教育之普及与否,为国家文野强弱之所由分。而陶铸国民,其训练在学堂,其熏染则全在社会。国不能人人入学堂,不能终日终身不出学堂……故普及教育不可不改良风俗,而其事必自通俗教育始……此项通俗教育社应请饬提学司、巡警道会同教育总会专任提倡创办之责。其办理之事项,一则发行白话报刊,二则改良宣讲书本,三则改良戏曲唱本,四则编译新小说,五则批评改正旧小说。”(55) 这清晰地显示出小说作为义和团事变主要根源的观点对晚清改良小说的启念、新小说的编译以及旧小说的改编等诸种新现象的触发作用。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义和团事变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得以全面爆发的直接触发性因素。当然,这里所说的“触发”绝非是指“小说界革命”是由其所“引起”或“造成”,而是前有渊源,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此点而得以凸显或明朗化而已;而且义和团事变之所以能够充当“小说界革命”的导火索作用,也说明此时“小说界革命”得以产生的其他各种条件已趋成熟。本文试图明确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方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晚清小说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义和团事件的作用问题(56),无疑将有助于我们面对晚清如此丰富而复杂的史料,更加客观地构建现实政治与小说之间的因果关系。
注释:
① 见陈清茹博士学位论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研究》(未刊稿),第2页。
②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 《新小说》第一卷第一号。
④ 《小说丛话》,《新小说》第一卷第七号。
⑤ 《淞隐漫录·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⑥ 《新民说·私德堕落之原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页。
⑦ 《山东巡抚袁世凯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⑧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页。
⑨ 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49页。
⑩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6页。
(11) 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第四册,第471页。
(12) 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13) 印鸾章编《清鉴》下册,上海书店1980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851页。
(14)(20) 《庚子西狩丛谈》,第15页;第30页。
(15) 《庚子国变记》,第14页。
(16) 详见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38、43、151、152页。
(17) 《义和团》第一册,第307页。在晚清,小说的概念中常常包括戏曲,因此本文在论述时对此不予严格区分,以避免枝蔓。但引述材料时仍尽量避免涉及戏曲,以求论证符合学术规范。
(18)(21) 《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3页;第34页。
(19) 《犍为县志》,转引自《义和团史料》下册,第1065页。
(22) 《论中国欲自立宜先求开民智之策》(《中外日报》),转引自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19页。
(23) 《海城县志》,转引自《义和团史料》下册,第1005页。
(24) 《悟澈源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32页。
(25)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7页。
(26) 《滦县志》,转引自《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89页。
(27)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39页。
(28) 《庚子西狩丛谈》第86页。
(29)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
(30) 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61页。
(31) 转引自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9页。
(32) 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33) 《论语注》,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页。
(34) 《论疆臣之迷信神权》,《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1904年12月31日。该文原注“录九月初四日《岭东日报》”。
(35) 《庚子国变记》,第26页。
(36) 《庚子西狩丛谈》,第146—147页。
(37) 蛮(黄人)《小说小话》,《小说林》第九期。
(38) 《论戏曲》,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原载1904年9月10日《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署名三爱。
(39) 《克林德碑》,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09—417页。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15日。
(40) 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清议报》第六十八册,1901年1月1日。
(41)(42)(43) 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8页;第38页;第47页。
(44)《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五》,第24页。
(45)(46) 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07页;第68—69页。
(47) 见王学钧《李伯元,〈绣像小说〉编者的确认》,《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第154页。
(48) 《庚子西狩丛谈》,第147—148页。
(49) 《〈剖心记〉凡例》,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81页。
(50) 《新小说》第二卷第二号。
(51) 《新小说》第二卷第七号。
(52) 壮者《扫迷帚》,《绣像小说》第四十三期。
(53) 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54) 晚清虽然也有一些前代神怪小说的翻新之作,如《新西游记》、《新封神传》等,但其旨趣已与此前的作品相去甚远,徒具形似而已。此点可参看胡胜《近代神魔小说试论》(《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
(55) 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3页。
(56) 义和团事件与晚清小说的关系问题甚为复杂,本文仅涉及其中一点,嗣后将陆续撰文讨论,此不具论。
标签:小说论文; 义和团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封神演义论文; 西游记论文; 清朝论文; 文学论文; 封神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