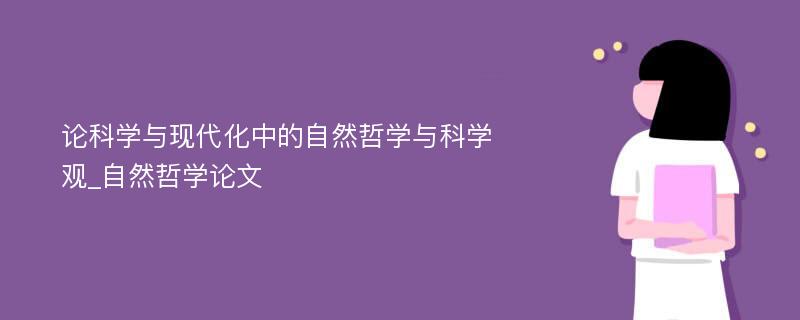
科学与现代性再论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现代性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千年来一向无害的一个准则,一个道德的老生常谈,突然之间竟转变成为粉碎了一个古老君主政体且震撼了欧洲大陆的一堆炸药。
——布莱斯勋爵(Lord Bryce)
《科学文化评论》第六卷第四期刊出拙文《“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对方正兄忽略科学兴起和现代性在西方起源的联系提出批评。陈方正在同期发表《对金观涛就〈继承与叛逆〉所作评论的回应》(下称《回应》),他认为:“‘现代性’那么宽泛、不确定的概念恐怕就很难具体地用到科学发展过程上去。”恐怕这正是我与方正兄分歧的要点,我觉得有必要对方正的《回应》再作回答,把已经开始了的有关为何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的讨论进行下去。
一 专业和工具理性的幻象:科学(自然哲学)在前近代的位置
方正和我的分歧在于科学和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李约瑟问题。它是从如何界定科学史研究的内核(严格地讲是李约瑟问题的本质)开始的。
我所讲的现代性是从普遍观念(价值系统)来界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本质不同,现代性可以归为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立足于个人的民族认同三大观念[金观涛2007]。我认为,作为观念的现代科学(当时称为自然哲学)的出现是和现代性的三大基本观念形成同步,甚至是和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起源直接相联系的,揭示这种联系是解决李约瑟问题的关键。方正关于现代科学为何起源于西方的大作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方正认为,他的著作是讨论科学史而非思想史,我的问题属于思想史,而他主要从科学史内在理路剖析李约瑟问题。在《回应》一文中他这样论证:“这(指《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以下简称《继承与叛逆》)涉及大量社会、宗教、哲学背景,因而蒙余英时兄和观涛兄推许为科学思想史之作。但即使如此,此书的“内核”仍然是科学史,而非哲学史或者思想史——虽然科学与哲学、思想强烈地交互影响,其间界线不可能完全清楚划分。无论如何,这‘内核’决定了全书方向和精神面貌,影响所及,处理不同题材详略自须有别。”
表面上看,方正言之成理,任何一个专业都有其内在逻辑,它和外史以及和外部诸因素不可混为一谈,不能要求一本讨论科学内史的著作来回答科学和社会思想关系的问题。但是我要问的是:在17世纪以前,真的有作为科学(或自然哲学)的“专业”存在吗?科学从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独立出来,获得自主性,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 (事实上,这一点本身就暗示科学观念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包括西欧)均没有做到这一点。在17世纪前,作为现代科学前身的自然哲学真的是一个具有不同于宗教、社会政治思想等有其内在发展逻辑的领域(让我们暂时称其为“专业”)吗?这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只要分析界定“自然哲学”这一术语的语义历史演变就可看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philosophy起源于希腊文、拉丁文的“爱智”(philosophia),原义是对事物及其起因的了解。但在中世纪,即后古典时期,其意义发生了改变,它是指实用智慧,甚至为虔敬地生活。在中世纪的大学里,Philosophy被区分为三个范畴:形而上的(metaphysical)、道德的(moral)和博学的(natural)[威廉士2003,页285]。前两个范畴都属于神学,而第三个范畴即自然哲学,它相当于博物学,其内涵远不是今日具有内在逻辑的某一专门领域所能涵盖的。熟悉中国传统社会的博物概念的学者知道,中国古代科学也是被包含在格致和博物中的(19世纪中叶甚至用“博物”译“科学”)。康熙年间陈元龙撰《格致镜原》一书,详细考订了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等三十类事物,完全是博物百科类书。”显而易见,它涵盖了极多的领域,与其说它有独立的内史,远不如将其归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更为妥当。西方17世纪前的“博物学”虽和中国不同,但不能作为独立领域却是一样的。
方正或许会反驳说,照这样说,古代科学史就没有内史可言了吗?当然不是!科学史根据今日对科学的定义在古代人类本属于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思想和行动中找出类似的东西,构成了科学史专业的内史;但请不要忘记,讲内史的时候主要是考察这些思想和行动本身,而不是去问为何当时有这些思想和行动。在此意义上,李约瑟问题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属于科学史内史的问题。以往我们在讨论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时,之所以将其分为内史和外史,是一种不准确的近似,即将研究经济条件、政治社会制度和古代科技关系称为外史,把思想因素放到内史中。这也是我认为《继承与叛逆》是从内史进行全新探讨的原因。方正却把古代科学思想本身当作内史,且不说这在逻辑上不通,即使可以这样讨论,立即会发现,西方的自然哲学本来就不是中国的博物和格致,李约瑟问题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了。
破除了专业的幻象后,我们还必须走出另一种当代幻象,才能准确地抓住李约瑟问题。这就是由对工具理性误解而产生,故我称之为工具理性的幻象。方正在《回应》中把排斥终极关怀之科学研究称为现代性,指出它不能用来把握科学家的思想:“开普勒经历艰苦思想奋斗而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其相关著作恐怕不能够说没有‘现代性’,但他的《宇宙之和谐》则仍然贯穿着毕达哥拉斯神秘教派的宇宙乐音和谐思想。牛顿的经典力学没有哪位科学史家能够否认是现代科学精神的起点,我们倘若因为他对炼金术(其实,他的炼金术研究还被多位学者认为,是和他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相关)和神学的着迷亦即具有强烈终极关怀而否定他的‘现代性’,那不是很吊诡吗?这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相当狂热地信奉、推尊天主教的19世纪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史家)迪昂(Pierre Duhem),和自认具有深厚宗教情怀的爱因斯坦又将被置于何地呢?”
把工具理性在西方的产生设想成排斥终极关怀的理性之出现,这种看法就是一种极大误解。所谓工具理性是指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即意识到这两个领域使用的方法和价值标准是互不相干的。这并不是说科学家是无神论者或没有宗教感,更不是说在科学家研究科学和他心底里的信仰无关。方正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了。我曾明确指出,西方中世纪特别是经院哲学中,理性包含启示真理和ratio两种成份,而工具理性是指两者二元分裂。它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亦可以表现在社会行动和社会人群的分离上。韦伯把现代性形成称之为解除魔咒,准确地讲就是在理性(ratio)研究对象中排除启示真理,这并不是说不再相信启示真理。原则上,我们不能用今日之无神论和常识的科学观来理解工具理性刚形成时的心灵状态。当然,正因为现代性中理性和终极关怀是二元分裂的,其进一步发展才可以导致终极关怀消失或退隐,愈来愈多的科学家成为无神论者,以至于用今日的观念去想象17世纪会出现工具理性幻象。
二 古代自然哲学为什么衰落?
如果我们准确地抓住了问题,那么研究自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完成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为何在西欧发生,就成为理解现代科学起源的关键。显然,不仅现代科学的观念形成与此有关,而且个人权利和基于个人的民族认同出现亦是和它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现代科学的出现只是现代性起源的一部分。事实上,新教伦理、宗教改革以及自然和社会(它们是理性认识的对象)的去巫术化(解除魔咒),都是这一过程在宗教内部和社会上的表现。它们与现代性以及和现代科学的关系早已表达为韦伯命题和默顿命题。如果不是李约瑟问题中出现一些超出韦伯命题和默顿命题的新取向,我是没有必要把终极关怀和理性的关系从16、17世纪的语境中抽取出来加以专门讨论的。
那么,李约瑟问题(其本质是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关系)所包含的超出韦伯命题的新取向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科学的独特性,它不仅仅是一种去巫术化的理性精神而已(这在其它文明并不一定没有),而是以欧几里得几何为推理体系的数理天文学。记得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常常和方正兄讨论古希腊科学起源的神秘性。它绝不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人神同型的理性宗教所能孕育出来的。事实上,苏格拉底之死已经表现出古希腊宗教对成熟的爱智精神之排斥,站在苏格拉底肩上的柏拉图思想绝不是古代逻格斯所能包涵的。但是,我们又清楚地知晓,古代科学都是不能和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相分离的。那么整个基于柏拉图理型论的成熟希腊哲学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呢?
一些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将其归为从苏格拉底开始的道德和社会转向,即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爱智精神是在道德哲学和政治法律的关切中成熟的。其实,培根早就指出过这一点,在《新工具》一书中他明确讲过,自泰勒斯以后,希腊人致力于道德与政治的研究,因而使人心转离自然哲学。②我在《“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一文中,所指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分期亦是立足于此。③我总觉得将其归为道德和社会转向这种说法有问题的,因为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这是轴心文明中中国文化的超越视野;如果古希腊哲学自苏格拉底起也发生这种转向,就不能解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巨大差异。方正在他的大作《继承与叛逆》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方正著作对思想史的重要贡献。简而言之,所谓古希腊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其本质可以归结为把苏格拉底思维过程定义注重的理性精神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结合,产生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而形成的典范。柏拉图的理型论一方面把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作为自己的推理模式,使得几何精神、数之比例ratio从此成为理性的代名词,另一方面这一强调几何式清晰思维之哲学是指向灵魂不死的,有着和古希腊罗马人神同形的理性宗教明确不同的终极关怀。
当然,理型论的认知典范一旦创造出来,并不等于用此推理模式的所有人在终极关怀方面都和柏拉图相同。确如方正兄所说:“亚历山大学宫时期是希腊科学的黄金时代和顶峰,但就学术体制而言,它是承接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堂(Lyceum)而非柏拉图学园(Academy)传统,就精神而言,它亦已独立于毕氏神秘教派的笼罩和色彩,而是凭借已经建立起来的唯理精神发展[陈方正2008,页183-184,233-234]换而言之,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科学发展与毕派或者柏拉图神秘主义即已逐渐分家——我们并没有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隆尼亚斯或者阿里斯它喀斯的著作涉及‘终极关怀’的任何证据。”我认为,一方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能判断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另一方面希腊人用新典范从事数理天文学研究不必都涉及终极关怀。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几何学和数理天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必须纳入一种可以传承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才会发扬光大。这种社会文化不是古希腊罗马人神同形的理性宗教,而是基督教,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科学才会衰落。即虽然古希腊亦有自己的哥白尼和牛顿,但现代科学不可能直接从古希腊科学中产生。也基于同样理由,我才强调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希腊罗马思想向基督教转化中介之重要性。
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所谓两种观念系统之中介,是指从一种观念系统转化为(或接受)另一种观念系统的桥梁或经过的中间阶段,而非指另一种新观念系统源于它。这方面,方正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他在《回应》中说:“至于兴起于3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则是和基督教强烈对立的,其中坚人物波菲利(Porphyry)以撰写《反基督徒》一书知名,奥古斯丁(Augustine)在《上帝之城》中要花大力气反驳他。更何况,新柏拉图学派在始创者柏罗丁(Plotinus)之后就陷入高度非理性的‘法力’(Theurgy)泥沼[陈方正2008,页253-255]。因此,‘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希腊爱智主义……和基督教之间的桥梁’之说恐怕还需要斟酌。不过,话说回来,基督教和毕氏神秘教派倒的确很可能有密切关系,即是在于后者将‘末日审判’、‘永生’和‘天国’等观念嫁接于希伯来宗教(它的祭司、文士本认为人死不可复生,到耶稣时仍然如此),从而促成基督教出现,但这当是远在新柏拉图学派兴起之前,与之有关的是新毕达哥拉斯教派的尤多鲁斯(Eudorus)和菲洛(Philo of Alexandria)甚或更早期人物。”[陈方正2008,页240-241,246-247]事实上,新柏拉图主义作为古希腊罗马思想向基督教转化中介是公认的。奥古斯丁成为基督徒之前,就信奉新柏拉图主义。观念史研究者甚至把奥古斯丁作为中古时代基督教中新柏拉图主义的源头。④
作为中介的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了它之后,一些本作为异教的观念可以顺利地成为基督教精神的一部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自然法(iusnaturale)。斯多噶学派最早提出自然法,认为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理性,与人所共有的理性相对应的法律就是自然法。后来,该观念完全被基督教接纳[赛班1991,页171,181],虽然基督教自然法背后的理念不一定是斯多噶学派的理性。照理说,斯多噶学派属于异教,它的观念应被基督教拒绝。但正是由于中介的存在,基督教和西塞罗才可以具备政治思想上的某种交集。
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来宗教在思维模式上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凭人的求知意志即可认识上帝,而后者则强调上帝的恩典,即理性必须从属于启示真理。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向基督教之转化,实为爱智的理性精神从属于启示真理之过程。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对奥古斯丁来说,罗马制度的瓦解不仅是异教神学的失败,更是在希腊罗马哲学中体现的理性意识形态的失败。……罗马制度的衰亡动摇了人用理性来理解这个世界能力的信心。”[Keyes 1966,p.14]该转化之初,一定是对古罗马的经验理性主义的否定,它导致理性在观念系统中地位之丧失,自然哲学也随之失去了存在之社会条件。因此,罗马帝国灭亡后,自然哲学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直到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被植入基督教神学之中,科学(自然哲学)之树才终于可以生长更肥沃的土壤之上,不断壮大以至结出现代科学的果实。
三 教皇革命:文明融合对现代科学的意义
我和方正的另一个重要分岐,是如何评价教皇革命对现代科学产生的意义。我们都同意古罗马文明衰亡后,自然哲学花果飘零,科学的种子——几何学和数理天文学一度寄生在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廷文明中。但是,在那里都没有孕育出现代科学。直到12世纪之后,西欧才再度领先,成为孕育近代自然哲学的温床。我认为这一切均源于教皇革命导致古希腊罗马之爱智(理性)精神和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也就是两种文明的融合。唯有这两种文明的融合,才能形成现代性(包括现代科学)起源的条件。
方正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除了个别主教外,找不到教皇革命和自然哲学复兴之间的证据。他在《回应》中这样论述:“中古(11-14世纪)教会思想是通过翻译阿拉伯典籍来认识古希腊的,那基本上限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经院哲学(scholastism)就是建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神学,而中古科学也以亚里士多德的‘地上’科学即光学和力学为主。在此阶段柏拉图的思想和数理天文学都没有影响力,都得不到发展,柏拉图《对话录》在此时期甚至还未曾翻译成拉丁文。因此《评论》第3节最后一段很成问题。当然,如《继承与叛逆》在§10.2所讨论,经过1200-1300年间多次的冲突和妥协教会终于容纳了亚里士多德,而且,由于大阿尔伯图(AlbertusMagnus)的关键性作用,教会对自然规律的态度也有了决定性转变[陈方正2008,页437-439]。可是这和发生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以及相关的法学运动并无直接关系——是在那场革命之后,欧洲才迎来12世纪拉丁翻译运动,然后,到再下一世纪即13世纪,才开始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
要理解该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何为教皇革命?它源于西方教会为了摆脱世俗王权的控制,于是到罗马法律中寻找统治和组织系统的正当性根据。这就导致教会法的产生以及大一统教会组织成为最早的法制(rule of law)政府,并使得西欧进入法制封建社会。⑤方正看来,法学运动和对自然规律的态度转变没有直接关系,而我认为这种再直接不过的联系却因专业幻象被掩盖,居然为科学史家视而不见。请问法学背后的观念是什么?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法的统治就是理性的统治。当法制成为教会组织(请注意,教会代表了上帝的统治)正当性根据时,理性必须和启示真理平起平坐了!众所周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神学大全》为亚里士多德学说(以及新柏拉图主义)成为基督教教义一部分之象征。为什么教会接受大阿尔伯图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关键在于:理性是以法律的形式存在的。当法律精神成为基督教神学一部分时,其表达方式一定要基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请注意,我这里讲法律精神成为基督教一部分是指两种文明(准确地讲是两种超越视野)的融合,这和两种文明共存或一种文明的要素被另一种文明体制吸收或包容(如拜占廷整理罗马法或伊斯兰文明吸收古希腊科学)根本不同,后者作为自然哲学的观念和终极关怀无关,而对于前者,科学理性的种子是终极关怀的一部分,它将随着终极关怀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并在终极关怀自我分裂时脱颖而出。这一切对于没有经过融合的文明(如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是不可能的。唯有经过教皇革命,理性才能通过法律成为上帝观念的一部分。例如阿奎那认为,宇宙间存在四种法律,它们是:永恒之法(Eternal Law)、自然之法(Natural Law)、神授之法(Divine Law)和人类之法(Human Law)[赛班1991,页270-271]。永恒之法是上帝理性本身,作为数学真理的上帝观念开始出现,而自然之法则是上帝为自然立法,而神授之法是十诫中给人类定下的道德律,人类之法才是我们今天意义下的法律(它不能和其它三种法矛盾)。
在这四种包罗万有的法律中,和科学(自然哲学)直接有关的是自然法。那么,自然法又是什么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文明融合,它和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已有微妙的区别。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是人凭理性制定的法律,而经院哲学的自然法是上帝为整个宇宙制订的法则。正如拉夫乔伊(A.O.Lovejoy)所指出的,“自然”与“自然的”共具有66种不同含义,它和超自然、人为的、习惯性的相对立;在希腊,“自然”是指未被人改动的世界,而对基督徒而言,是上帝刚创造的世界,人类未食禁果前的状态。⑥也就是说,经院哲学的自然法包括自然律、万物在宇宙间的关系、每个物种的本性以及一切自然生成之物之法则(例如自然形成的习惯法)。正因为自然法包罗万象,远远越出今日人们对法律的想象,有关中世纪自然法的研究碰到了一个内在的困难:一方面,人人知晓自然法之重要,但另一方面,法学家不能具体地指出自然法是什么。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自然法只能去发现而不是去制订。这里,“发现”不是如斯多噶学派那样在理性中体悟到人类的法律,而是用理性在宇宙间寻找万物遵循的法则,这不仅是西方法制(rule of law)的基本精神,而且已蕴含着近代科学才有的自然律观念了。
方正反对教皇革命和现代科学直接有关的重要理据是:近代科学(哥白尼、牛顿)从数理天文学开始,而中世纪神学重视的是亚里士多德学说,故科学革命和教皇革命不存在直接联系。确如方正所说,最先受到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而非柏拉图以及数理天文学。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翻译的先后固然是一个外部条件,但观念史更重视人类关注事物的内在逻辑。正因为教皇革命实现了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法律精神的结合,它对古代爱智精神和思维模式之接受必定是先肯定亚里士多德学说,然后才是关注柏拉图和数理天文学。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远比柏拉图重视法律,虽然柏拉图在临死前完成《法律篇》,但柏拉图精神的代表是《理想国》,理想国不是法治国。亚里士多德却不同,法律始终作为理性认知的代表并贯穿其全部学说。教皇革命作为法学革命,一开始重视亚里士多德理所当然。但是,从思想变迁内在逻辑讲,基于亚里士多德认知方法的神学一定会走到柏拉图。这样,从关心月下界的自然界必然会发展到与数理天文学相关的宇宙。
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先理解亚里士多德思维模式和柏拉图的关系。就爱智精神本身而言,存在着认知(指向未知世界)的意志和知识本身两个方面。柏拉图更关心认知的意志,对现实世界知识本身的注重始终是第二位的。正因为如此,柏拉图虽然知道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但依他的理念,哲人治国的理想城邦中哲学家人治是高于法治的,只有当理想达不到时才注重法律。亚里士多德则更关心爱智在现实世界的表现。正如政治思想史专家赛班(George H.Sabine)所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理想国家,往往就是柏拉图所指的次好国家。”[赛班1991,页107]我认为,这一评论也适用于整个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柏拉图主义的关系。因此,只要爱智精神充分展开,必定会从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走向认知的意志,柏拉图主义会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显现出来。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是来自于柏拉图的学生优多克索(Eudoxus),即它也是建立在数理天文学之上,只是不那么“先进”而已。正如奥康诺(D.J.O' Conner)所说:“优多克索把宇宙描绘成一套以地球为其共同中心的同心层球体。每一层分别以不变的速度和不变的方向的环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球体是宇宙真实物质的部分……故真空不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然(physis)是具有内在运动源泉的那些事物的总和。”[奥康诺1998,页119-123]这样,一旦透彻地掌握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定会回到柏拉图和数理天文学。况且,我们不要忘记,新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模式一直潜含在基督教中。新柏拉图学派在始创者柏罗丁(Plotinus)提出的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是中世纪神学的深层思维模式,正是这位大阿尔伯图在他的《论动物》中指出:“自然如果不产生各类之间的中间物就不会使‘动物的’类分离开来,因为自然不会从一个极端跳到一个极端,除非通过中介。”[诺夫乔伊2002,页93]这种认识逻辑,不仅表现出对存在之链深信不疑,而且柏拉图那种把宇宙视为一个处于不同等级的巨大有机体的观念亦时隐时现了。换言之,柏拉图主义在经过教皇革命后的西欧是一个逐渐凸显的过程。
四 自然法分裂的逻辑
《继承与叛逆》一书用了两章讨论文艺复兴前西方科学的进展。我想,方正不会否认,自然哲学的繁荣发生在教皇革命之后,而数理天文学的凸显更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被神学吸收、特别是托马斯主义盛行以后的事情。为什么自然哲学繁荣和数理天文学大发展要在这两种转化之后?关键在于,古代科学的种子到这时候才获得合适的土壤。从观念史角度看,古希腊认知精神纳入基督教不仅导致两个世纪中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然哲学终于在此过程中转化为现代科学。深究其思想演变的内在原因,它恰恰基于阿奎那神学体系的解构。换言之,结合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天主教神学的解构产生了现代价值系统的所有基本要素,而现代科学只是解构中与现代价值同步形成的观念而已!
特拉诺伊(Knut Tranoy)为了形容阿奎那的神学体系将上帝、宇宙、自然界和人的封建等级整合起来的严密性和完备性,将其比作只有一个船舱的大船:“船上每一个人,都是同一集体中的成员,虽然各个的地位不同。从船的一端到另一端,距离可能很远,但从头到尾原则上却可以沟通交流。……假如它开始漏水,不论漏在何处,整条船以及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将面临危难。”[奥康诺1998,页327]事实上,最早在这一负载着古希腊罗马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整合之大船上打开缺口的,是14世纪的唯名论[威柏1987,页84-85]。接着,宗教改革将本属于经院哲学内部的争论普及为人人皆知的思想,几乎所有新教徒都是唯名论者。
我在《“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一文中这样论述唯名论带来的思想冲击:“唯名论在主张共性为名(不真实的)背后,蕴含着否定新柏拉图主义的两项最基本的主张。首先,上帝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意志,认识上帝必须依靠启示,和理性无涉。该主张虽然和早期基督教一致,但出现在天主教神学中则意义完全不同。因为其后果不是如早期基督教那样排斥认知意志,而只是把认知意志放到和信仰无关的层面而已;结果导致理性和终极关怀的二元分裂。更有甚者,唯名论认为唯有个体才是真实的,而经院哲学中来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式的‘种’和‘属’,它们作为共相,只是一个名称,不是实在。这样一来,人和存在之链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将封建社会视为一个上帝设计的理性有机体观念不再成立。国家亦是由一个个不可进一步分割之个人根据法律组成的。”
在结合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天主教神学中,只要同意唯名论,个人的信仰和理性就不再相干,工具理性因此而出现了。同样,只要同意唯名论,必须接受唯有个人才是真实的。这样,只有个人才能是自然法的载体,原作为万物各得其所(正当性的道德基础)将自然律和习惯法融为一体的自然法的解构也就不可避免了。我认为,自然法在解体中变成三种不同的观念:自然律、个人的自然权利和国际法。自然律对应着现代科学观念,而个人的自然权利是现代性的核心,国际法则为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重要部分。在此,我们看到,现代科学和现代价值系统是同时产生的,故我认为,从思想变迁的逻辑讲,没有现代性亦不会有现代科学。这是以前研究现代科学为何起源于西方时被忽略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如果现代科学是普世的,那么和它同源的现代价值之核心——人权亦是普世的。
准确地讲,从14世纪的唯名论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只是经院哲学的解体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同一体系中不同要素本来是互相整合的,一旦体系解构,这些要素在从体系中分离下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变构,成为了新价值。在此意义上,用唯名论和新教伦理导致神学大船从漏水到倾覆的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不能把握从体系中解构下来的碎片变成新东西的过程,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曾经用埃舍尔的名画“解放”来比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方法制封建社会中的形成[金观涛、唐若昕1987,页133]。其实,用该画代表现代价值(包括现代科学的观念)如何从融合了古希腊罗马理性精神的天主教神学体系解构中产生更为妥切。在该画中,最后飞出的那些白天鹅和黑天鹅分别代表现代价值系统和现代科学的观念。表面上它们是互相独立的,但从本质上讲,它们分别由画面上的那些白色三角和相嵌的黑色三角形演变而来的。这些三角形分别代表中世纪神学中互相整合的信仰、理性和自然法等不同环节。如果不是古希腊罗马理性精神和基督教互相整合,形成高度完备的体系,所有这些互相联系的现代性产生所必需的内在要素不可能都存在着。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形成的认知精神纳入基督教,使得天主教成为具有两种超越视野的观念系统(即发生轴心文明的融合),工具理性、个人权利、自然律等现代科学观念居然在17世纪同时出现在经过宗教改革的西欧是不可思议的。
必须注意,以上分析完全从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来讨论现代性和现代科学观念产生的内在关系。这并不是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不重要。显而易见,没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前提,就不会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但是如果缺乏观念系统变化内在逻辑这一环,我们便不能解释为什么第一个现代社会是新教国家,以及认识科学革命和新教徒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没有观念史的显微镜和放大镜,我们会误以为现代科学观念和现代性(社会组织蓝图)是互相独立完全无关的,看不到它们在展开过程中的同构性,即来自终极关怀的历史联系一直在制约着它们各自的演化。
五 两种机器: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和机械自然观
为了说明现代科学观念和现代性(社会组织蓝图)在展开过程中的同构性,让我们来详细分析“必须用理性发现自然律”这一新观念(它是现代科学观念的一部分)形成的过程。它源于唯名论式的个人(体)观念出现对托马斯体系中自然法的解构。如前所说,自然法作为上帝为自然立法或一切自然形成东西必须遵循之法则,它包括自然律、万物在宇宙间的关系、每个物种的本性以及自然形成的社会有机体之法则(如习惯法)。它们共同组成了存在之巨链,托马斯神学将其视为一连续整体,其中每一个“真实”的环节必须是共相而非个体。而在唯名论中,共相只是名称而非真实存在,自然律和作为封建社会有机体的各种规定(习惯法)就不再有内在联系,于是,它们分解为两个不同领域。现代科学的观念和现代价值的核心——人权观念正是在这一分裂过程中同时形成的。
我曾经详细分析过,唯有个人才是真实的这一观念如何导致自然法转化为个人权利观念。在西欧封建社会,习惯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对不同的封建等级而非个人而言,一旦作为有机体的封建等级不是真实存在,自然法立即变成上帝制定法律下的个人自由即天赋人权。这里,自然法从一种古老的道德老生常谈转化为打破传统社会有机体的炸药。而且,既然社会有机体是虚幻的,社会只能被视为由独立个人通过契约组成的机器,17世纪社会契约论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终于得以形成。⑦关于该过程,因它是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哲学家作过详细的探讨。特别是社会被当成由个人组成的可以根据功能分解为不同部分机器的观点,被韦伯高度强调,它是工具理性贯彻到社会组织的象征。但与其平行的过程即自然律之观念怎样起源和形成以及进一步演化,一直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众所周知,17世纪自然律之观念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机械自然观的出现。令人深思的是,把自然界当作机器是和把社会当作机器的观念居然是同步发生的。两者存在着隐秘的内在联系。人们常把机械自然观形象化地概括为自然界为一架巨大的时钟。其实,17世纪这个比喻出现时,讲的是自然界和上帝的关系,因为有钟表必有其制造者——钟表匠。当启示真理被逐出自然界时,自然界的一切根据自然律在运行,只有时时不忘其制造者,钟表的比喻才是恰当的。确实,正因为上帝制造了自然界这个大钟表,规定其运行法则,故自然律的存在必须先认定上帝的不变性。笛卡尔这样论述:“从上帝绝不改变,以及它总以不变的方式而行动,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某些法则的知识,这些法则,我们称之为自然律。”⑧从上帝不变和上帝为自然立法转化为机械自然观的自然律,只是17世纪现代科学观念形成的第一步。第二步即为宇宙图像的形成。
当机械自然观不那么强调上帝与自然的关系时,并不需要钟表比喻。这时更恰当的宇宙图像是微粒运动论(corpuscular-kinetic theory)。事实上,当时在自然哲学家心中(统治近两个世纪之久的)宇宙图像不是钟表,而恰恰是微粒运动论。何为微粒?它是古希腊原子的现代版,但和古希腊明显不同的是,古希腊从未用于指涉原子的词“不可分割的”(individuus为atomos的拉丁文翻译)指涉个人,即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从未和组成城邦的基本单位等量齐观过。到了17世纪,individual则成为个人的代名词。更有甚者,莱布尼茨干脆把个人的灵魂赋予微粒运动论中的粒子,这就是单子(monads)说。从这里可以看到,把社会视为由独立个人组成的基本观念是与微粒运动论同步出现的,由此看来,自然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类似性似乎表明背后存在着某种相似的逻辑结构。
这种隐秘的同构性,还表现在对物质性质作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上。刘青峰曾指出,牛顿力学的前提是认为月球和苹果的运动遵循相同的自然法则[刘青峰2006,页61],而这一信条来自于16世纪以来被广泛认可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不同。所谓第一性质是指物体的空间广延性、质量,速度,而第二性质是颜色、味道等。从16世纪开始,自然哲学家普遍认为唯有第一性质是客观的,即物体本身具有的,而第二性质是主观的,即人的意识附加给客体的。正因为如此,月球和苹果的运动才是可以比较,它们位置、速度变化可以用相同的自然法则来把握。为什么当时自然哲学家会有如此古怪的信念?事实上,在它们的背后,存在着和唯名论对自然有机体(它们由共相规定)之解构类似的观念变化历程。伽利略的说法几乎和唯名论一模一样:“酸甜、香臭、红绿等等,如果关联到我们安顿它们的那些物体身上去讲,则可以说它们不过是一些空名而已;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⑨
17世纪以来自然机器和社会机器的同构性表明,“必须用理性发现自然律”这一观念,虽然和“独立拥有权利的个人组成社会”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并且各自独立发展,但两者却遵循着相同的逻辑。用今日眼光看,前者为现代科学观念之组成部分,后者是现代性核心价值——人权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两者不应该有任何关系。但事实却不是如此,两者隐秘的同构性不仅说明其起源相同,而且这种来自同一结构的历史联系一直成为制约它们各自发展的深层背景,使它们同作为轴心文明价值的不可分割之部分。我认为,人们把社会视为机器和把自然视为机器存在同步性,是现代社会在轴心文明中成长的表现。当自然被当作新的有机体时,社会往往也成为某种新有机体,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作为文化有机体的民族国家观念也是同时出现的。20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观背后亦是一种公然批判机械论的科学观和自然观。后面我将指出,这种深层来自终极关怀的背景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
六 科学与人权:现代性起源的系统观
“必须用理性发现自然律”这一新观念的形成,只是现代科学观念之一半而已,另一半是受控实验观念的兴起。关于科学实验的出现,方正更认为它和现代性无关,并且断言这不是观念史所能揭示的。他在《回应》一文中这样写道:“《评论》4节8段强调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实验方法的兴起有关,这为许多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家所津津乐道,而且的确不错。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史实:在古代同样有科学实验方法,包括静力学、弹道学和气体力学的实验[陈方正2008,页188-9,231-2],而在光学方面,以可控实验来作研究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从欧几里得、托勒密以至伊斯兰时期的海桑(Alhazen)和中古欧洲的大阿尔伯图、维提罗(Witelo)和西奥多里克(Theodoric)都是如此[陈方正2008,页289-290,341-2,444-7],他们都可以说是牛顿光学实验的前驱。因此,说伽利略的动力学实验(那其实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获得突破是对的,说‘没有宗教大传统本身的变化,实验精神兴起是不可能的’则恐与事实不符。至于炼金术屡屡为中古教会所禁止,主要原因是这成为了铸造假币的途径,而与思想、学术并无关系)——例如,教会主要思想家,也曾经出任主教的大阿尔伯图就有众多炼金术著作[陈方正2008,页454-8]。因此,现代科学出现的关键就不再是可控实验为何出现,而是这传统为何产生突破,那牵涉的因素很多,难以单纯归于思想转变了。”
真的是如此吗?在方正书中专门讨论了科学(受控实验起源)和魔法巫术的关系。他介绍了半个世纪前耶茨(Yates)的工作,耶茨根据“魔法热潮从费齐诺开始以至卡索邦结束这前后150年(1460-1610)刚好与科学革命的酝酿期重合”,证明魔法和现代科学出现有某种重要内在关联。为什么魔法热潮从勃兴到衰亡的历程正好与受控实验的兴起重合呢?方正似乎同意魔法巫术有可能“激发出走向真科学及其运作的意志”,并指出梅森—伽桑狄—弗卢尔德论战对魔法衰落的重要性[陈方正2008,页515-516,561]。其实,背后起作用的恰恰是普遍观念的变化(如果对观念变化视而不见,当然觉得两者直接相关不可思议了)。众所周知,和魔法直接对应的西方大传统是新柏拉图主义。在15世纪魔法热出现的背后,正是宗教文化的变化:柏拉图主义受到关注和基督教入世转向。熟悉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入世转向最后结果是宗教改革,而新教是高度强调去巫术化的观念系统。请想想,在和魔法混同的各种控制自然的行动中去巫术化会发生什么?这难道不正是实验和魔法的分离和科学实验的兴起吗?
方正再三强调,大阿尔伯图是“炼金师、星占师、相信施魅魔法(enchantment),像他那个时代多数学者一样,爱用超自然原因来解释所有令人惊讶的事物”[陈方正2008,页515]。这里,我想借用方正的“施魅魔法”一词来说明受控实验与魔法和炼金术的关系,因为它正好和另一个形容现代性出现的词相对应,这就是“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韦伯把现代化称之为解除魔咒,今天该说法已太多地被理解为这只是一个社会目标丧失魅力的过程,而事实上在16、17世纪,它是一个遍及整个生活界的对社会和对自然看法的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柏拉图主义在天主教神学中兴起促成了用魔法对付自然的热潮,而随之发生的宗教改革则强调去巫术化,其后果正使得实验从魔法中解放出来,和数理天文学与机械自然观并存。而这一切不正是思想大传统的变化促使现代受控实验观念的形成吗?如果说机械自然观的出现与把社会视为机器之间的联系是时隐时现的,那么,受控实验和16、17世纪西方思想的巨变(现代性在天主教神学解构中产生)之关系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如前所述,科学观念和现代性虽然是各自发展,但由于有同一历史来源作为其深层结构,这就使其在演化中存在类似性。那么,和受控实验精神相对应的人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这就是17世纪席卷西方的社会契约论。在此,我不可能详尽论述。做实验的个人是认知的和控制自然(环境)的主体,如果用这样的精神面对社会机器,正是主体通过契约把他想达到的目标中那些必须由他人提供的条件固定下来,社会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根据契约变更的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机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科学观念和人权展开时现代社会组织原则隐秘的同构性。
理解了科学观念和现代性在历史上的关系,就可以说明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了。我和方正都同意,21世纪的科学已和17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科学出现了重大差别。正如方正所说:“《评论》还在第5节提到,技术和受控实验对于21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可能已经超过数学与理性分析。这的确如此:事实上,今日科学的性质和发展模式已经迥异于20世纪之初,更不用说牛顿的时代。然而,它之所以能够有此发展,却是建立在过去三百年的理论与分析基础上,它当今的技术与实验,是与它此前所发展的所有理论密不可分的。因此,理论与实验、技术实为推动科学前进的两条腿,孰前孰后,视乎发展阶段而定,两者不但无本质上的高下轻重之分,实际上也已经浑然融合为一体,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同。”而我则认为,当今的科学之所以脱离数理天文学的轨道,实验愈来愈重要,乃在于科学观念和现代价值所存在的终极关怀背景不断弱化以至完全消失。
固然,现代科学的观念和现代价值的核心——人权是在同一的自然法中孕育,它们所处的终极关怀背景三百年来一直制约其演化,而使两者表现某种同构性,但两者在领域上和逻辑上毕竟是不相干的。因此,一旦终极关怀在公共生活中退隐或消失,科学以实验为中心,并不再给予那在早期阶段因终极关怀而决定的数理天文学特殊地位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现代性和现代科学的起源都缘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融合之后的解构,它们在本质上仍是属于轴心文明的。我把今日终极关怀完全退出公共领域称为人类走出轴心文明之象征,在此意义上,今日科学之种种特点都是人类21世纪走出轴心文明的表现而已。
七 新的反思:观念史视野下的科学史研究
我的整个分析一直在强调观念,认为忽略了观念的大转变会使人看不到真正的内史。其实,这正是我和方正根本分歧所在。方正这样批评我的“观念决定论”:“《评论》认为,应该‘把作为思想的科学史转化为科学的观念史。观念史注重普遍观念本身的变化,这样个别思想家个别论述带来的干扰就不会掩盖科学观念主线’。这种将思想视为独立于具体个人以外的事物而直接加以研究的做法,可能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人(包括科学家)的思想不能够以常理测度,同一脑子往往会装载截然相反的思想。强以思想发展必然有明晰、合理轨迹可循,往往不免陷入忽视事实的泥沼。诚然,每个时代都有些相当重要的‘普遍观念’,它深刻地影响到许多人的思想,它兴起、嬗变的轨迹肯定值得关注、研究。然而,普遍观念并非独立实体,它最终建立在大多数人的思想和其影响力之上(我们好像又回到唯名唯实之争了),但人的思想既无整体性,它的转变也无规律可循,那么这种研究恐怕是不宜向具体和细致方向发展的吧?”
表面上看,方正很有道理,普遍观念并非独立实体,特别是对于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他头脑里的观念可以互相矛盾,某人凭何种理念以做出某一科学创造,是很难判断的问题。但是,方正这里把科学家在自己脑子里构想理论和该理论被社会或科学共同体接受混为一谈了。或许,一万年以后,科学史家都不可能知道牛顿是怎样做出划时代的发现的。但科学史内在逻辑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发现为何及如何被科学共同体接受,并成为另一位科学家工作的前提。这里,重要的是一种作为社会活动的科学。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接受某种共同规范共同体的一种社会行动,普遍观念恰恰是社会行动分析的基本单位之一。特别是当我们考察的时间长度超越个别科学家生命时,普遍观念和科学家个人哪一个更基本?普遍观念是社会行动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个别科学家变幻莫测的个性和想象力却不是(除非他恰好能被纳入社会行动)。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只是作为普遍观念的载体而已!方正认为他强调科学家个人类似于唯名论,而我注重普遍观念是唯实论,他的立足点比我更正确。岂不知唯名论唯实论实际上都是错的,今日思想史看重唯名唯实之争,不是在于谁对谁错,而是作为普遍观念的唯名论和唯实论在历史上的意义。
当然,如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观念的展开是可笑的;但是,把社会行动看作没有观念支配的活动同样是有害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史研究中经常出现这种倾向)。经济学和政治学之所以不考虑观念,专门考察行动和制度本身,那是因为支配行动的观念通常不会被行动后果改变,可以把观念悬置起来。而历史是一条观念支配行动、行动反作用于观念的互动链。理解该互动链,涉及三种关系,它们分别是:观念之间的关系、观念和行动的关系以及行动和行动之间的关系[Jin and Liu 2008,pp.57-107]。方正所谓“强以思想发展必然有明晰、合理轨迹可循,往往不免陷入忽视事实的泥沼”说的是只用一种关系来代表整个转化链,同样以为(不考虑观念的)行动发展必然有明晰、合理轨迹可循,难道不是一样会陷入忽视观念变化导致社会行动巨变的泥沼么?我不是一个观念决定论者,但我在分析中强调观念展开的内在逻辑,这是因为它在观念支配行动、行动反作用于观念的互动链中最容易被忽略。我将其作为内史的核心,主张只有把它整合到观念和行动的关系以及行动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之中去,才能理解社会行动是如何展开的。
我和方正根本分歧的另一个要点是,我主张以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本身作为分析对象,而不一定以今日的专业分科来确定何为内史,去限定观念的范围(在观念史研究中,这相当于把今日之观念安放到过去的社会行动上)。这样一来,考察17世纪前在科学研究中起作用的观念必在今日界定的科学史以外,我更重视在和终极关怀有关的领域考察它们(这是当时更长程起作用的观念)。以“观念史”广受推崇的哲学家拉夫乔伊曾讲过,观念研究今日已不自然地分裂为12个“学门”。文学、艺术、科学、神学,教育、社会思想的学者,每个人都强行带走西方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彼此皆孤立地在他们的密室里极其仔细地去分割它,而整个有机体便在这种过程中死亡了。⑩十分有趣的是,拉夫乔伊列出的12个学门中第一个是哲学史,而第二个正好是科学史。
我的论述表明,在以观念史为核心的探讨中,李约瑟问题只是现代性在西方起源的子问题。李约瑟问题刚提出时,常识和直觉告诉我们,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和为什么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应该是一回事。李约瑟问题的观念史视野不仅使我们验证了原初的直觉,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从经济决定论和科技决定论中解放出来,走向比较文明研究的系统演化论史观。正如为什么西方最早进入现代社会这一问题,必须由将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结合的系统论史观才能回答一样,(11)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亦必须用同样的整体方法来研究。
必须强调的是,我注重观念但不同意观念决定论,因为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和展开都必须通过观念和社会行动的互动,它涉及把观念史整合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化中去的整体观(我称之为系统演化史观)。我相信,李约瑟问题的真正意义是使我们越出专业的樊篱而走向整体宏大的史观。它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挑战西方,用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问中国为何没有走上类似道路,在不同文明的对比中,使反思意识超越某一种文明的局限性。李约瑟问题的提出在中国更是和启蒙意识的勃兴联在一起的。它的每一次讨论都使我们对普世价值和中国及西方文明的认识到达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意义是中国人对科学精神的认识和对科学主义的反思,那么,今日的再次思考则有助于克服新的盲区。这种思想的盲区,或许从李约瑟问题的社会影响本身就可以看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与此相匹配的问题“个人权利在中国的普及为何步履维艰?”一直没有取得李约瑟问题的历史地位,甚至今天仍被知识界忽略!因此,对今日思想界,李约瑟问题并没有过时,任何宣称李约瑟问题已被解决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注释:
①陈元龙:《格致镜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1-1032册。
②Sir Francis Bacon,Novum Organum,BK.I,Aphorisms 70-80; Valerius Terminus (1603),in The Work of Francis Bacon,James Spedding (eds.),Taggard and Thompson,Boston,1863,Vol.VI,p.32.
③方正似乎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这样响应:“《评论》(指《“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观念: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谈起》一文)指出,一般西方思想史学者以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奠基者,而并不看重前苏格拉底哲学,……剑桥大学的格思里半世纪前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把两卷半亦即大约40%篇幅给予前苏哲学和智者(Sophists),苏格拉底只占半卷,其余三卷则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外,诸如德国策勒尔(Eduard Zeller)和奥国贡佩尔茨(Theodor Gomperz)在20世纪初出版的多卷本巨著,以及许多八十年代以降的著作,也都大体依循此模式,最近汪子嵩等的希腊哲学史亦不例外。”要知道,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在上个世纪有关著作中所占比例和它在古希腊哲学典范中的位置是两回事。
④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部主编1988.《观念史大辞典》(哲学与宗教卷).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页554。
⑤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第六章(未刊)。
⑥《观念史大辞典》(自然与历史卷),页250-251。
⑦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第五章。
⑧Descartes,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转引自Franklin1988,页93。
⑨Galileo,The Assayer.转引自Franklin1988,页58。
⑩《观念的历史编纂学》,见拉夫乔伊2005。
(11)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
标签:自然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终极关怀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继承与叛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古希腊论文; 哲学家论文; 法律论文; 自然法论文; 数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