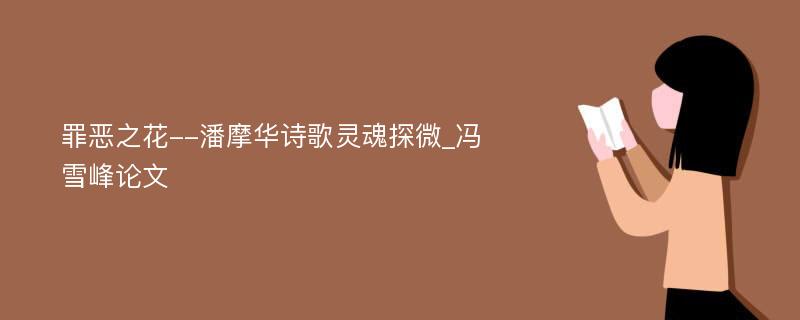
罪之花——潘漠华诗魂探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花论文,潘漠华诗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2)06-0064-05
没有潘漠华便没有晨光文学社,基于晨光社核心基础上的湖畔诗社也会有所或缺;而潘漠华却是湖畔晨光、青春辉映里的一个“异数”。与他人青春的明丽或偶有浮云的忧郁不同,对潘漠华而言,与青春共生的是他无法切割的罪感,在那爱情萌醒之时注定不被原谅;而诗便成了他深味人生痛苦,试以超越与救赎那注定无望的情感宿命的唯一途径。那偏于一隅背负沉重的个人吟诵,于湖畔的青春重奏中,遂鸣响出别一种音色。
潘漠华15岁时自浙江宣平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执教于本村小学。二哥潘详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心眼开阔,常常会寄一些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回乡。时值“五四”前夕,潘漠华受此影响颇深,未入学先受其教。
1920年夏,18岁的潘漠华考入他心向往之的“浙一师”,由此开始新诗的创作。潘漠华恰与汪静之同班。因为自己写新诗,他一看汪静之也在写,便生出亲近感,结成了好友。随后,柔石、魏金枝等也因共同的兴趣志向加入进来。
浙江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晨光社由此便渐渐有了雏形。参加者除了经常一道谈诗论文的潘漠华、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一师”同学外,还有惠兰中学、安定中学与女子师范学校的新文学爱好者,共20余人。至于指导者,潘漠华更是请了时任“一师”国文教师的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来做晨光社的顾问。1919年10月10日,晨光社正式宣告成立,约定每月聚会一次,选一佳处评判近期的诗作,或交流习诵诗文的心得体会,或以一经典名著为具体文本例证进行讨论。出版《晨光》周刊一份,登载社员的作品。社名“晨光”二字是潘漠华拟定的,除却字面容易生出如光明、希望、未来这些引申之意外,据说还缘于汪静之曾写有一首题为《晨光》的诗:“我浸在晨光里,/周围都充满着爱美了。/我吐尽所有的苦恼郁恨,/我尽量地饮着爱呵尽量地餐着美呵!”但事实上潘漠华自己也有同题的《晨光》诗一首:[1]
晨光从云托着的太阳里射出,
透过迷茫的大气,
照映在每一个底身上手上,
跳着在每一个胸膛里底热血:
紫薇也点头了,
乌桕也欠伸着摇伊底红衣了,
玉兰也揉着伊底眼睛了,
蔷薇也高兴得舞起来了,
呵一切,——一切都从梦里醒来了!
于是诗人微笑了!
从久愁着的枯湿的脸上,
涌出欣悦的有希望的笑的花了!
此诗一反他沉郁顿挫的调子,扎实地应和着诗题的昂扬。特别是最后的自抒,“笑”与“花”这样正面的表情在这位“久愁着的”诗人“脸上”真不多见。2002年潘漠华百年诞辰时,他的家乡浙江武义县委宣传部编的纪念集名为《永远的晨光》。这“晨光”不知是否含有对诗人英年早逝的唏嘘?如果有,那么以其诗题来命名,就带着些许反讽的宿命感了。
关于“湖畔”时期的诗作,朱自清说,“咏人间的悲哀的,大概是凄婉之音……这种诗漠华君最多”。[2]读《湖畔》诗集,应修人也说,“漠华的诗使我苦笑”;在《湖畔》印行之前,潘漠华写信给应修人,建议扉页上印:“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哭”者,颇似自况。小作统计一番,《湖畔》集中共收入潘漠华诗16首,诗中无不渲染着哀伤、孤寂、怅惘的情绪,出现决绝的“泪”字的就有9首。
境由心生。当汪静之在湖畔因爱情之欢畅淋漓而“放情地唱呵”①之时,潘漠华正因爱情受状如炼狱的自我折磨。兹以《若迦夜歌》组诗(收入《春的歌集》)为例:若迦,潘漠华的笔名;夜歌,不言而喻的长夜当哭的哀歌。从字面推究,就是晨晚间、朝暮间、无时无刻间潘漠华与情人的相聚离别,是哀婉的诉衷情与绝望的伤离别。
我心底深处,
开着一朵罪恶的花。
从来没有给人看见过,
我日日用忏悔的泪洒伊。
——《隐痛》
这“隐痛”的源头便是罪之所在,这样的隐秘不得轻易示人、只能向知己好友告解、以求慰藉。同样收录于《春的歌集》里冯雪峰《秋夜怀若迦》文中,为好友切切的思虑,表明冯氏显然是知情人。应修人日记云:“来漠信,说他恋人事……”(1923年6月16日);“得漠信,说他底妹要他把《夜歌》大部分改用秋田名”(1923年8月31日);“夜复雪信,说漠事,说我愿望他和他底妹妹逃亡……”(1923年9月10日)。[3]只是说“恋人事”未必尽然,但好端端的不同于寻常恋爱男女要宣告全天下的态度,却要改名,似有隐情。既然劝到要逃亡这般离经叛道,是想其所想,痛其所痛之举了。关于1922年4月15日应修人致潘漠华信中的一句“说你品格居第四,我就不信你一切话”,汪静之为其注释说:“漠华为什么说他自己在湖畔四诗友中品格居第四呢?因为他所爱的姑娘是封建礼教所不许可的,他心里一直觉得有愧,所以他自卑自责。1921年上半年他曾和我谈过他这个秘密……”[4]在后来的访谈中,汪静之掀开了最后的面纱:“漠华诗里的‘妹妹’,其实就是他的堂姐潘翠菊。他们俩从小感情很好,后来就相爱了。”[5]
潘翠菊本人在潘漠华纪念文集中,写有《参加革命,不盼长命》一文,②文中罗列了一些她保存的潘漠华的遗物,除亲笔书信外,还有手稿。其中有未完成的《深山雪》一篇,是潘漠华记叙1922年寒假回乡,参加水灾调查救济工作,深入山乡,无意中与家里以前的染布工人施火吒重逢这一段,即最终成型的《人间》。[6]
小说讲述“我”在查访灾民的时候,恰好来到施火吒的家中,目睹了他的妻女以及家中的窘迫,在离去的路途中碰到了暌违多年的施火吒。文章的旨归,自然还是要落到人祸天灾、底层大众的疾苦上去;但值得注意的是,咀嚼之下,小说中还有潘漠华关涉自我的更深一层,在“我”碰到施火吒跟他拉起家常时,先是“我”宽慰施火吒“境况虽不好,但请你得过也且过吧。妻子固累人,也总是妻子”,为他稍稍宽一下家庭带来的心理担责,接下来是施火吒的应和与释怀:“妻子虽累人,但无妻子,这样的深山中,更难久住了”,也就是说施火吒并不以妻女为负累,反是当作支撑扶助。这想法让“我”深深感怀。直至尾声,“我”把这层理性感性的逻辑关系又重理与强调了一回:“他底肩上,是挂着一串一串,由人间给他的苦恼;他底棕包里,当装满人间底忧虑了。他说,‘妻子虽累人,但无妻子,这样的深山中,更难久住了’。这种由苦恼丛中细细尝出的滋味,是几回使我低泣了。爱着人间,穿过痛苦去爱着人间!”
凭着“爱”活在苦痛“人间”,并且借着爱体味出这苦痛“人间”的滋味来,便是这逻辑关系所在。如果从小说本身来看,这逻辑关系只是在两人语言意念中出现,显得单薄与苍白;但对于当时的潘漠华,施火吒的这番言说,是他流着眼泪微笑着去信奉的终极!不难想象,这一层情理也是潘漠华留得这手稿在潘翠菊处的缘故了。
同手稿一起交给潘翠菊保管的,还有潘漠华自小佩挂的一块银制长命锁与一对包金的银手钏。在长命锁正面下端,有潘漠华亲手镌刻上去的八个字:“参加革命,不盼长命”;在银手钏上,则是“包办婚姻,信物不信”,不啻是象征着对生命与情感的全权相委!
洞悉了这一层,就不难理解潘漠华本人与他反映在诗文中的纠结:渴望相伴守但又碍于礼法与至亲家人的感受;有破除一切的新风尚、先进理论支持,但是无论从遗传进化的科学还是单纯直观的人伦来讲,自己都觉得无法直面突破。这样无从跳脱的自我困顿与抑制,致使他首先陷入哀伤的重坠,掉入水中,自我放弃浮力的下沉,感伤的波纹推衍开去,即使水面本无痕迹,但由他的视角中心观望,何处不沾涟漪?皆是小我的心情,全部是大我的描摹。“我”是不幸的,而从怀着悲悯的心看来,人间遍地哀苦。这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善意。比如《罪徒》:
河边柳树下的石道上,我逢着他们。
热闹的大街上,我又逢着他们。
城脚寂静的冷巷里,搭在水面的浮桥上,我又逢着他们了。
他们推着独轮车,腰间系了铁链。凶严背着枪的警士们,三三五五地跟着。他们只能面面相觑,望得大家苦笑了,各个得了一些无聊的慰藉。他们不知青碧的天宇下,有红灼灼的杜鹃花从山脚开到山顶。他们不知静妙的夜里,有朗月和明星浴在清澈的湖心。在他们荒凉的心田上,只长满了愁闷的乱草。
我每次逢着,我咬牙蹑足走过去。
我归来后,每次想起他们来,即合十字在胸前,每次都低头歔欷着了。
这样的屡屡“相逢”,自然不是一般的相逢。他的悲哀外化与自我定论,已然成为一种由己及人的常态,成为一种自我判罪、自定角色的哀者见哀、自哀自怜的惯式。
他的爱是幸福与苦难的原罪,这是他已经接受的命运现实。他只能将自己置于劳燕分飞与道德评判的双重煎熬中,无法再多迈出一步去成全一方而抛却另一方。从此又可推衍出斯时潘漠华推崇白居易的新乐府诗的某种基准情绪、某种脉承渊流:《新丰折臂翁》是不舍亲情,为与家人相守而自残身体、以避从军戍边却至暮年仍保持欣喜的老翁;《缚戎人》则是无论胡、汉都驱逐排斥的、没有归属莫衷一是的可怜人。潘漠华又特别注明感人最深的两篇:《李夫人》是无视白居易主观带有的“尤物惑人”想法,却只悼这死生相隔、永不聚首的情人;以劝诫“止淫奔”为主旨的《井底引银瓶》更是潘漠华引来戚戚,与奔出去找到幸福的人悍然为敌的标的物。[7]
我们除却望见诗人当时及之后在作品中的遥相致敬外,也完全可以发见诗人早为自己情感决定的终程,与为自己的心划定的牢矩。身陷情感漩涡的现在时,却已对他感情的唯一善局(为情抛却一切出走的结局)做出判断——失败。既然一定是失败,自然没必要选择;应修人后来建议的逃亡之说在潘漠华的心中最初就已经被否决了。
对于潘漠华来说,完美的图景莫过于:
明天呵,我愿光明的天宇下,
故乡的乡南,乔仰着一株
苍老的高松,——那是我的母亲;
在那高松底荫阴下,开放着
我那羞怯的花蕾,——那是我底妹妹。
——《若迦夜歌·三月八日晚途中》
如何能两全其美?“撕碎”、“分裂”的意象充满了潘漠华的诗。他与“妹妹”的爱,是“有缺陷的完全”,与融合着“母亲的爱,家的爱,乡的爱”的“全般的爱”终是不可兼得的。
终生都左手牵着母亲,
右手又舍不下妹妹底手:
我将分裂我底生命。
虽说“舍不下”,但终生的“左手在先”排序已经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分裂。但是又怎么能放得下,怎样终结彻骨相思,到底要有怎样一个图景才能在现世达成彼岸的希望?他没有真正放弃过反复追问,一直在踯躅蹀躞,才会在闻听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死讯时,受到极大的震动。[8]有岛武郎,日本白桦派作家,受唯物主义学说与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颇深,将自己北海道农场所有的土地分给佃户,把庄园住宅分给农民居住;并变卖私产,作为工人运动的经费。1923年与有夫之妇、记者波多野秋子一同自缢于日本轻井泽别墅。事件的永不可恢复性决定了真相的喑哑,而只可能是各人自见自在。
日本当代的通俗小说作家讲述不伦之恋的畅销书《失乐园》里自耽于这样糜靡的形容:“两人是上吊而死,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的一个月梅雨期间,没被人发现,等到发现时两人遗体已经腐烂。发现他们的人说:‘他们全身都生了蛆,就像从天花板流下来的两条蛆的瀑布一样。’”或是日本“国民导演”深作欣二的影片《华之乱》,借有岛武郎故事努力再现大正时期风貌,特别是1901年到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日本社会的发展变迁。大正年间,正是变化最为激越的年代,政治风云变幻,文艺风潮跌宕。那么,革命与爱情以及革命与爱情的终局无法脱卸,都应该是跟世俗告别的理由。周作人说:“有岛君为什么情死的呢?没有人能知道。总之未必全是为了恋爱罢。秋田雨雀说是由于他近来的‘虚无的心境’,某氏说是‘围绕着他的四周的生活上的疲劳与倦怠’,大约都有点关系。……我们想知道他们的死的缘由,但并不想去加以判断:无论为了什么缘由,既然以自己的生命酬了自己的感情或思想,一种严肃掩住了我们的口了。我们固然不应玩弄生,也正不应侮蔑死。”[9]
探寻爱、光明、理想的有岛同时深陷与虚无的颉颃,对于潘漠华,这样多重的对应映现令其几乎崩溃。以冯雪峰《秋夜怀若迦》里的话来说,“凭吊有岛武郎,并凭吊你自己”,让不能牺牲母亲与故乡的爱、做不到逃亡,“结合不得”,但又“撒开不能”的潘漠华想到这样毁灭性的出路——“趁我俩能结合时,毁灭了我俩!”
我们杳杳地逃亡呀,
你我都舍不得家乡去;
故乡底夜的南野,
当天长地久有我们底夜泣:
你我都愿接受全般的爱呀!
这是《若迦夜歌》组诗的最后一首《爱者底哭泣》的终结,“夜泣”的“全般的爱”实在隐现着不祥的气息。这想法是让湖畔诗友们两颊“立刻紧张”、喉咙“立刻哽咽”的“天大的恐怖”,但要如何开解安慰可得?这便是为什么湖畔诗社的诗辑《春的歌集》要特收这么一篇冯雪峰致潘漠华的《秋夜怀若迦》文,跟在《若迦夜歌》组诗之后,压在卷末。
潘漠华翻译出版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长篇小说《沙宁》。冯雪峰还就此事与他争执。[10]冯雪峰因为沙宁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所以质疑译介的意义;潘漠华说自己并非是沙宁的崇拜者,翻译这部小说的动机是因为小说里的个性解放可以冲击中国封建伦理的禁锢。说到后来,都有点愤然了。冯雪峰是一以贯之的简单为小说定性;而事实上,关于虚无颓废绝望,是否曾打动过潘漠华、引起过他的共鸣、引发了他最初的阅读与翻译的兴趣,确是微妙的表征。潘漠华在《沙宁》译序中指出,沙宁以虚无与享乐主义构建了个人主义,这样的反动性状况没有出路。他在最后一节说:“我希望读者,能用了以上的观点来读本书。不然,我们怕没有权利可把它当作文学遗产而接受吧。”这不坚定的口气让人不禁又返回文中,潘漠华选择了一些人物的言行,来为他这一小段不容忽视的话作明证:“郁里时代与沙宁时代,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但这有点不同,一是想革命,却因为阶级根性和没有明白的政治理想之故,而不能革命,而烦闷;一是爽爽快快否认一切政治,否认一切社会改造运动,明目张胆地宣扬个人主义的反动的生活。”这应该是潘漠华忠实自己内心理解与感悟的表现。
冯雪峰与潘漠华,“浙一师”的同窗,湖畔诗社的好友,分别是南北“左联”的领导人物,但又在这共性上充满了差异性。两人曾在同游时作过相同题材、主旨的诗作。与冯雪峰的《灵隐道上》同是“同情”轿夫之作,潘漠华的《轿夫》则是在轿夫身上交融着“我”的移情:
倦乏了的轿夫,
呆呆地坐在我底身边,
俯首凝视着石磴上纷披的乱草与零落的黄叶。
倩笑的姑娘,
烂漫活泼的童子,
赤裸裸卧在海边号哭的妇人:
这些可使我笑可使我流泪的,
尽在我膝头展开的画册上鲜明地跳跃。
但这于他有什么呢?
他只从纷披的乱草里,
看出他妻底憔悴的面庞;
他只在零落的黄叶里,
看出他女儿底乌黑的眼睛。
冯雪峰天真投入,只瞥得一眼便倾怀同情轿夫与轿中年轻妇人,一径地在为“人间的苦痛”定性。这显然与潘漠华无论是自我本身的纠结,还是自我与外界之间抵牾的痛楚不同。两位诗人(同时也是两位革命者)的些许不同是耐人寻味的。潘漠华的投入显然带着某种现代性:
脚下的小草呵,
你请饶恕我吧!
你被我蹂躏只一时,
我被人蹂躏是永远呵!
——《小诗六首》之一
救赎大众,在某种程度上亦意味着获得自我救赎。
潘漠华学名潘训,漠华为其笔名。虽因“罪”被贬出伊甸,即便在不被赋予的沙漠中,仍要努力绽放出自己的花来——那“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的诗魂。[11]
注释:
①参见《蕙的风》初版本扉页上汪静之的恋人符竹因的题词。
②参见吴国平《永远的晨光:纪念潘漠华诞辰一百周年》,中共浙江武义县委宣传部编印,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