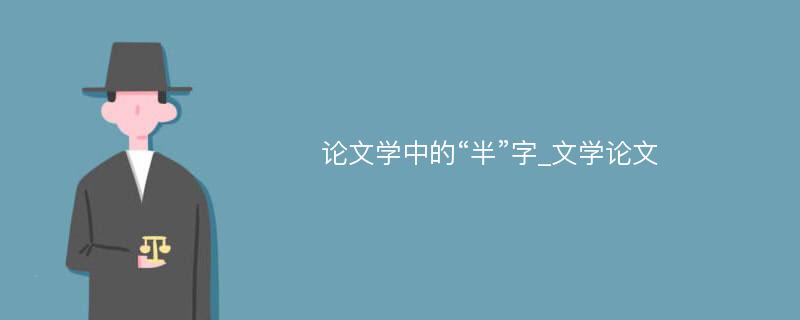
论文学里的“半”字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字体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学里的“半”字体,是指两种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的毗邻或对立文体,在它们交接和融合的中段,出现的一种具有双方面因素且大致平衡的“中间”状态,一种“亦此亦彼”的文学体裁。向来的文体分类,只讲区分,不讲联系,以避免体裁的混淆和维护体裁的纯洁,事实上,在横向的“原种”文体之间并没有壁垒,在纵向的“新旧”文体嬗变之间也没有鸿沟,它们总是相互沟通和渗透,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半”字体,这是客观的存在,常见的文学现象。
“半”字现象是一种历史的广泛存在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半”字现象,是早就被人指出的,诸如:白天和黑夜的中介是黎明或黄昏,介于人兽之间的是类人猿,有导电性材料和绝缘性材料,还有半导体材料把八度音划分为十二个音,两个相邻之间的音程叫做半音,城乡结合部的郊区是半城半乡,学业上的人际称谓有半师半友,甚至早已用于社会经济状态和历史发展的考察,例如半自耕农、半无产阶级,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
事物的中间状态也存在于文学艺术领域。早在三十年代,叶圣陶就谈到过这一情况:
再说文学跟非文学并没有划然的界限。好比每一种颜色有深有淡,等级很多,在无数等级的中段,是深是淡,只有在对比之下才辨得清。然而最深跟最淡的两个等级,那就不必对比,谁都能一望而知。精粹的小品文是一个极端,好比最深色;讲义体中间尤其坏的是另一个极端,好比最淡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就只有程度的差异,越接近小品文的越是文学,越远于小品文的越不是文学,如此而已。①
叶氏以颜色的深淡为比喻,说明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划然的界限,在最深色和最淡色之间存在着一个有着无数等级的广阔的中间地带,越深的越是文学,越淡的越是非文学。那么,深淡参半的“中段”是什么呢?实际上可视为半文学。为了使得这个意思表达得更为显豁一点,不妨如此比喻:假如把文学喻为一种原色,把非文学喻为又一种原色,那么,在两种原色相接相融的“中段”,便是第三种颜色,即间色,象红色与黄色的中段是橙色,黄色与蓝色的中段是绿色;这“间色”虽是两种“原色”的产儿,与“原色”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兼有“父本”和“母本”的双重特性,但毕竟是一种独立的、新颖的、自有其性质和价值的、区别于“原色”的第三种颜色;“半”字体就是这第三种颜色──间色,它是不可混淆的,客观存在的。
苏联的美学家莫·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一书里提出了一个在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光谱系列的概念,认为:两种艺术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恰恰相反,是一片过渡地带,这种过渡不是急剧的、跳跃式的,而是平稳的、逐渐的,成了宽窄不等的中间地带,例如时间艺术的形态学光谱系列是:“散文──过渡形式的系列──诗歌──语言音乐综合体(宣叙调)──音乐语言综合体(旋律歌咏)──再现音乐──纯音乐”②。这个光谱系列是由散文──诗歌──音乐之间的相互沟通和渗透而形成的,这种相互关系可以各有侧重,但是在接近于某种平衡的“中段”,即出现了“半”字体,半诗歌半散文──例如自由诗、散文诗或诗散文,半文学半音乐──例如宣叙调和旋律歌咏。
如此种种的“半”字现象,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作出了理论的概括和说明,他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又指出:
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③恩格斯是举了许多自然界的例子,诸如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鱼和两栖类之间,鸟和爬虫类之间等,来说明它们之间都有“中介”或“过渡”,并告诉人们要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辩证法的这一原则不仅适合于自然观也适合于艺术观,作为采用同一媒介、反映同一对象的精神产品,作为最活跃、最有融合力、最富创造性的艺术,作为最能兼收并蓄、溶化世界一切文化之长的文学,怎么能在各体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怎么会黄牛角、水牛角、角(各)管角(各)?它是更加广泛地存在“中间阶段”、“中间环节”的,更应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的“半”字体。
好久以来,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流传着一种“文体纯粹”或“文体分立”说,中外都如此,认为“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为之,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④认为“大自然提示了二十种相对的类型,在不同的希腊作家之间划了一条清楚的线;没有一个类型即使越出了自己的范围,能够进入另一个类型的领域”⑤。是的,各种文体──例如诗歌及格律诗与自由诗、戏剧及悲剧与喜剧──的质的规定性或独立性,都是现实地、不可改变、不能排除地客观存在的,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却并非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它们犬牙交错,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出现了“中间”或“过渡”,例如诗歌和戏剧之间的诗剧,例如在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格律诗(或半自由诗),例如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第三个主要剧种──正剧,它们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不能抹煞、不能视而不见的。应该破除只讲区分、不讲联系,只讲遗传性、不讲变异性的封闭僵化的观念,在适当的地方承认“半”字体,如此才符合实际情况,并显示出文学园地的多姿多彩。
“半”字体拆除了文体之间的壁垒
文体相互之间的壁垒是某些文体分类学家人为制造的,要人们信奉和遵守,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不伦不类,不予承认,由此而造成了种种束缚。可是另一些文体分类学家面对实际一看,并不是这么回事,于是就动手拆除它,时至今日,一段一段的拆除已经不少。
在欧洲,悲剧和喜剧有着严格的界限,互不掺和,大相径庭:悲剧取材于神话或历史故事,以王侯贵族、上层人物为主人公,歌颂这些英雄主角,喜剧取材于下层社会,以平民百姓为主人公,对他们采取讽刺和揶揄;悲剧主人公遭到不幸,引起人的怜悯和恐惧,使情感得到陶冶,喜剧逗人笑乐,通过嘲笑起教育作用;在古希腊,甚至在演出上也各不相同,悲剧面具眉毛向上扬,嘴角向下垂,脸上皱纹作垂直线条,喜剧面具作开口笑,脸上皱纹作曲线线条;悲剧演员穿高底靴,喜剧演员穿矮底靴;连剧作家也是,写悲剧的不写喜剧,写喜剧的不写悲剧……壁垒十分森严。许多人想拆除这中间的壁垒:古罗马的普罗图斯写出了《昂弗屯永》,表示“我将从中制成一出混合的悲喜剧”;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瓜里尼又编剧又写文章来倡导悲喜剧,认为“马和驴并不同种,可以交配产生出第三种动物──骡”;接着,西班牙的维迦表示响应,并戏称“这又是一个人身牛首的怪物”……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和自称是他学生的博马舍,为了反对封建专制,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才算打破了墨守成规的、久攻不下的悲剧与喜剧不能掺合的戏剧法则,开出了一个新局面,创造了一种介于“英雄悲剧和叫人愉快的喜剧二者之间的一种形式──严肃戏剧”,但在当时,他们的这种新剧体的理论和实践受到了攻击,被称为是“暧昧的形式”,是“杂种”,是黑格尔在《美学》中勇敢地作出了肯定,他把这种既有悲剧性又有喜剧性、经过悲剧式的冲突转为喜剧式的结局的正剧,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剧种”,是“处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第三个主要剧种”⑥。十九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又继续宣扬:戏剧包括三个科──悲剧、正剧和喜剧,它们是各有特点、各有功用的。
从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到别林斯基,外国文学采用的是三分法──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诗,可以说源远流长、普遍接受,但是事实上的“混淆”又常常使人陷入深深地困惑。别林斯基一方面认为“诗只有三类,再多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了”,一方面又看到了“它们之间不是经常划着明显界限的,相反,它们常常混杂在一起而出现”⑦。杜勃罗留波夫也是主张诗只有三类的,但是又指出:“要避免这种混合是不可能的”⑧。到了现代,苏联的波斯彼洛夫在他的《文学理论》里则直接了当地指出:
“纯”叙事文学和“纯”抒情文学似乎是语言艺术的两个极端,而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多种中间结构,其中某些中间结构把叙事和抒情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使它们达到某种统一,并使两者处于同等的地位,这样的作品我们称之为“抒情──叙事”文学。它可以既在“质”的方面,又在“量”的方面包含“叙事”因素和“抒情”因素的结合⑨。波氏举了涅克索拉夫的《大门前的沉思》、茨维塔耶娃的《斯捷潘·拉辛》作为实例,剖析了它们就是“均衡”的抒情─叙事诗,此外,他还认为存在着“抒情──戏剧文学”等。经过艰辛的跋涉,波氏算打破了向来的框框,走出了困惑,可是他仍缺少“半”字意识,应该再跨出一步指出:这类作品就是“半”字体文学,即半抒情半叙事文学之类。中国的文学研究者也常常碰到类似的苦恼,例如屈原的《离骚》,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到底是什么文体,就有争议。假如跳脱旧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框子,以“半”字观一透视,难题便可迎刃而解:《离骚》是半抒情诗(或半叙事诗),《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半叙事散文(或半抒情散文)。
在中国,格律诗的“格律”和自由诗的“自由”是看作为互相对立的,中间隔着楚河汉界的。何谓格律?就是为了诗歌的铿锵悦耳非得遵守的音律要求,犹如用兵之纪律,用刑之法律,严不可犯。自由诗呢,废弃原来一切的规约与诗形,不限音节,不限押韵,“解放”的,“裸体”的,“随口”的。“五四”以来的新诗,从形式方面说就是在格律诗和自由诗两者之间曲曲折折地走了过来。象一股风,一会儿吹向那边,一会儿又吹向这边。可是在诗体形式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却涌现了大量“半自由体”(或“半格律体”),何其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中间状态,并且为它下一个定义:
“半自由体”就是指那种行数固定、也大致押韵、但行里面的节拍却没有规律的诗体。从行数固定、大致押韵方面说,它是倾向于格律化;但行里面的节拍没有规律,却又是自由诗的最大特点。⑩
常常有如些情况,由于受到习惯思维定向的限制,在彼领域是司空见惯的,在此领域却依然故我,不去拿来,不去移用。对诗体的认识就是这样,要么是格律诗,要么是自由体,不讲平仄,即非律诗,不讲押韵,即非诗歌,哪来什么中间体、过渡区、“半”字状态?何其芳不囿于常规,提出诗歌中存在着一种“半”字体,犹如冲决了一个文学禁区的缺口,是对传统的文体观念的一个非同寻常的突破。倘若由此“缺口”乘虚而入,以“半字”观审察文体分类,那么人们便会惊奇地发现,“半”字体不在少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总要碰到一种特殊的文体──赋,赋是什么呢?它既有诗歌的因素,又有散文的因素,它是诗歌的衍变,又独立成类,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算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半诗半文体裁。除此之外,例如骈文、颂赞、箴铭、哀祭之类,就其形式而言,一般均有诗歌音乐性的特点,,就其内容而言,一般均有散文功能性的特点,徘徊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属于半诗半文的中间体裁。现代文学里有一种叫做“散文诗”的,它不限音节不限押韵,倾向于散文,它有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又倾向于诗歌,“散文诗”的名称就标志了它是一种半诗半文的体裁。其它如诗剧、诗体小说、对话体小说乃至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科学诗等等,无不兼有“父本”和“母本”的双重特性,是文学中的苹果梨、杂交稻、艺术体操。
许多科学家认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空隙当中堆积着大量课题,今后重大的发现或发明都产生于这一交汇或交叉之中。反观文学,把文体相互之间的人为壁垒,在一段一段逐步拆除之后,一鼓作气,再给以全部、一概、彻底地拆除,那么,人们又会看到在它们之间竟然还有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自觉地去开发这一片一片土地,必然会获得比以往时代更丰硕的收获!
“半”字体填平了新旧文体之间的断裂
现在再跨进一步,把“半”字观从横向的文体分辨带到纵向的文体嬗变中去审察文学历史现象。这也是许多文学史家一方面受到“非此即彼”观念的束缚,一方面又面对“亦此亦彼”的状况,从而感到无所适从的。
初唐产生了“近体诗”,其特征是格律严谨,诸如篇有定句、句有定字、讲求对偶、运用平仄、诗必用韵。应该说,这标志着中国诗艺的成熟,对诗歌的形式美由必然走向了自由,杜甫说他“老去渐于声律细”、“新诗改罢自长吟”,把格律当作了一种心爱的工艺,琢呀、磨呀、刻呀,以致玲珑、细致、精巧、完美,叮当作响,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一般认为,这种律诗产生于初唐,例如唐元稹说:“沈(期)、宋(之问)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例如清钱木庵说:“律诗始于唐初,至沈、宋而其格始备”。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明徐师曾认为:“按律诗者,梁、陈以下声律对偶之诗也”,“梁、陈诸家,渐多俪句,虽名古诗,实堕律体”。古体诗与近体诗(律诗)的界限到底断在六朝梁、陈时期,还是初唐沈、宋阶段,就成了一个有争议、有讨论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各执一端的两种意见都有相当根据的。初唐沈、宋手里形成的律诗体式,决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他们顿悟出来的,相反,经过了一个孕育、衍变的过程,这孕育、衍变则始自梁、陈。中国的诗歌由二言、而四言、而六言、而以五字和七字为主的乐府体,经过缓慢的发展,到了梁、陈,顺着它自然的流向,吸取了魏晋以来的汉语、特别是声韵研究的成果,接受了汉魏、特别六朝以来崇尚骈偶的影响,就已经开始渐讲声律、追求对偶,至于定扁、定句、定字、押韵更是屡见不鲜,如此,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到了初唐才定于一尊。那么,自梁、陈至初唐这一阶段的诗歌,包括沈约、谢眺、庾信、薛道衡等的诗作,算古体还是近体呢?当代学者褚斌杰有一个说法:
齐梁诗歌确有它的特殊性,它一方面渐讲声律,与它以前的所谓“古体诗”已有不同;但另一方面,它虽已逐渐具备了后来所谓“律诗”的某些要求和某些因素,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定式,与唐初以后的所谓“律体”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那么,到底算什么呢?褚斌杰判定:“只应把它们看做是‘古诗’或‘古体诗’的某种‘变体’”(11)。或许,对这一判定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只应把它们看做‘今诗’或‘近体诗’的某种‘潜体’”。无论是“变体”或“潜体”,在实质上可视为半古体诗或半近体诗,半天籁体或半格律体,即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诗体。
“五四”产生了新诗。新诗的产生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来文化的影响,一是晚清阶段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他们倡导的诗界革命的影响,甚至连现今通用的“新诗”这个概念也出现于那个时候。站在历史渊源和文体嬗变角度看,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到胡适的“作诗如作文”,从晚清诗界革命中的诗歌“满纸堆积新名词”,到胡适初期的诗歌“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从黄遵宪的以“流俗语”入诗,到胡适的“不避俗字俗语”主张……甚至是诗作也有某种形式上的雷同,试读黄遵宪《己亥杂诗》:
我是东西南北人
平生自是风波民;
百年过半洲游四,
留得家园五十春。
再如胡适的《蝴蝶》,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脱出了旧诗窠臼(例如平仄等),又都脱不尽(例如五七言一路的句式等),用胡适的话说:是“放大了的小脚”,“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因此,新诗如果从胡适的《尝试集》算起,那么从黄遵宪开始的诗作就已经潜在着新诗的因子,其实,从黄遵宪到胡适的诗作统统可以看作为不新不旧、又新又旧的半新半旧诗体,真正的新诗是从被闻一多称作“现代第一诗人”郭沫若开始的,他凭借诗歌变动的必然趋势,凭借了从黄遵宪到胡适的半开拓之力,从外国诗歌中接受了影响,写出了“新诗进化期中已臻成熟”的《女神》。
现代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种类虽然首先出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决不是从地里突然冒出来的,除了应将它水平地置于产生它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外,还应该将它垂直地与历史传统联系起来的。这样便发现现代小说的祖先原来是史诗:由史诗到中世纪的传统文学、而流浪汉小说,是它发展过程中互相连接的环扣;由史诗的历史生活描写的“逼真性”与浓重神话色彩的“奇特性”,到现代小说现实生活描写的逼真性与悬念、巧合、吃惊的“奇特性”,是它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演进;《奥德修记》中奥德修斯离开伊里昂城──海上漂泊──回到故乡伊塔克,《鲁滨逊飘流记》中鲁滨逊出海经商──身陷孤岛──最后回到英国,这简直是情节结构上的类似……当然,史诗采用的是诗体,小说采用的是散文体,但是英国早期小说家菲尔丁在他的小说《约瑟·安德鲁传》和《汤姆·琼斯》的序言中就提出了“散文滑稽史诗”,后来《弥尔顿传》的作者载维·马森在《英国小说及其文体》中又说“最好的小说是一部散文史诗”,表明了面目虽异而血缘相通──英国十八世纪的现代小说乃是史诗的散文化产物,用黑格尔的话说,小说是“资本主义的史诗”。大家知道,美丽的蝴蝶是由毛毛虫变态发育而成,仪态万方的服饰起始于树叶的遮身,灿烂的太阳最早却是一团暗冷的星云,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发展演化过程,而在两个极端之间总有一个连续而无间断的阶梯,追踪起来,在史诗──小说之间也是可以寻访到半史诗半小说这个阶段的。
承认文学体裁嬗变中的过渡性的“半”字现象,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表现,“半”字体的运用,可以拆除上下之间的森严壁垒,填平新旧之间的楚河汉界,弥补古近之间的缝隙裂口。进一步说,过去的文学史更多地注意了上下、古近、新旧文体的研究,而对过渡阶段的中间环节往往忽视,假使改变了这一状况,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那么,就可以使人们的思想少一点保守性,多一点自觉性,从而促进文体的“更新换代”。
注释:
①《小品文与漫画》34-35页,生活书店1935年版。
②莫·卡冈《艺术形态学》,第30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5页。
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
⑤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51页,为谢尼尔《创新》中的诗句,他认为类型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自然现象。
⑥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第294页。
⑦见《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91页、177页。
⑧《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一卷)第427页。
⑨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第142页。
(10)何其芳《新诗歌发展问题》第257页。
(11)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