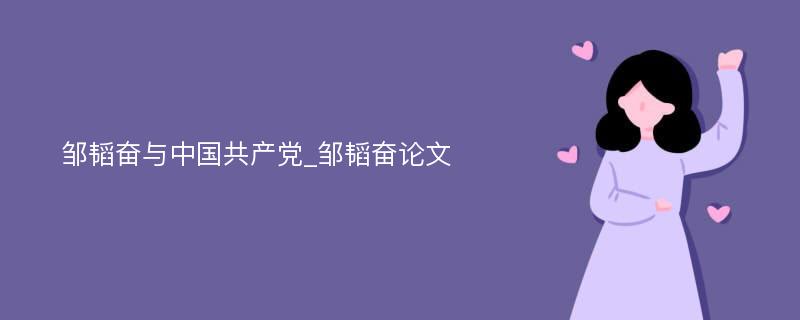
邹韬奋与中国共产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韬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最终放弃陈见,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密友,有些人甚至成长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邹韬奋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一
“九·一八”事变之前,邹韬奋基本上保持超然党外的态度。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他没有任何党派背景,自称“以公正独立的精神,独往独来的态度,不受任何个人团体的牵掣,尽心竭力”地去办《生活周刊》;《生活周刊》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站在“正义”和“大众”的立场上,不为任何党派“培植势力”〔1〕。
但是,邹韬奋并不回避党派问题。在他看来,“政党并不是绝对的坏东西,倘若一党的党纲及事业,的确是为国为民,便是一个好政党”〔2〕。他宣称“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 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就无异于我已加入了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3〕。
邹韬奋从改良社会的角度出发,对取得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寄予较高的期望,并与之保持比较积极的合作态度。他支持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北伐”,拥护国家的“统一”,赞同“裁兵”和“财政统一”,欢迎“训政约法”,并“尽我所有”地提出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抵御外侮的建议。然而,内战、政争、贪污、腐化、怯外等现象严重败坏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形象。邹韬奋在现实中看不到乐观的景象,只好“姑作未来的乐观”〔4〕, 对于国民党根本上就没有产生过要加入其中的冲动。
邹韬奋对共产党的了解起初多来源于国民党报刊或道听途说,因此不免片面、错误。1930年5月,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 对被红军打死的国民党的江西省南丰县县长吴兆丰称颂备至,认为吴氏为“保境安民而能奋不顾身,死而后已”,这种“只知有群众幸福而不知有一己私利之精神”,实“值得国人之讴歌悼惜”。显然,在邹韬奋的眼里,共产党还是一个被误解的政党。
二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对党派的观察、思考和取舍全以在事实上能否救此垂亡的中国为转移。他认定“凡能在事实上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都是我们国民所要拥护的人物或集团”,否则“虽是架子十足,宣言堂皇,在我们国民看来,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5〕
国民党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对外尽量地不抵抗,对内尽量地打内战。东北的迅速沦陷,上海抗战因“后援不继”而失败,热河在有声有色的大逃跑中被敌轻取,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实深深刺痛着邹韬奋的心。他深刻地认识到“把国事交给军阀和他们的附属品干,无论你存何希望,终是给你一个幻灭的结果。”〔6 〕国民党在事实上救不了中国,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予以无情的谴责和大胆的警告,蒋介石、何应钦、汤玉麟等所谓“领袖”人物均被邹韬奋指斥为民族罪人。
邹韬奋对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态度已趋缓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周刊》虽还有少量的“剿匪”报道,但更多地是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1932年1月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信箱栏答复读者时指出:共产党问题“其根本解决在从政治上迅速积极解决大多数劳苦农工民众,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枪炮所能解决,只有从速解决一般平民的民生问题,则不解决而解决”。同日同期《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政治上的出路》(作者系邹韬奋的好友及同事毕云程),认为“中国兵匪之所以多,完全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良好农民虽终岁勤劳,仍不容易得到生活上的需要,以致为饥寒所迫而投身于非兵即匪之一途”,“兵匪”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予以解决才能根本解决。
从敌寇不怕官军只怕民军(东北义勇军)的事实中,从踊跃捐输支援马占山抗敌和十九路军作战的热烈场景中,邹韬奋深感民众力量的伟大。但他又知道这种力量只能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深信中国要得救,要走上轨道,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起这个使命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的集团,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负得起这个重大的使命。”〔7〕他虽觉得国民党靠不住了,但对共产党又了解不多。 他不知道所向往的“集团”在哪里,“现在我们所焦急的,也可以说犹成问题的,是要团结民众力量以从事整个民族的抵抗,什么集团在事实上能把这个重大的领导使命肩负起来?”〔8 〕他不止一次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询问。直到1933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之前, 邹韬奋都没有找到所向往的“集团”,因此不能说“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立即就跟共产党走了。
邹韬奋曾得到鲁迅和胡愈之这两位思想进步并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人士的大力帮助。
邹韬奋早就景仰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与鲁迅一同被推为中央执委,彼此间有了更多的接触。鲁迅关心邹韬奋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从1933年开始,生活书店陆续出版发行的《文学》、《太白》、《世界文库》和《译文》等文学杂志,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上述杂志合计发表鲁迅的著译达78篇之多。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小约翰》、《錶》等书都是交由生活书店出版的。1933年5月, 鲁迅得知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已经完稿,主动提供20多幅高尔基的画像和漫画。鲁迅的“战而不屈”的凛然正气给邹韬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6年10月,鲁迅逝世,邹韬奋在公祭大会上发表最简短也是最有力的演说:“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鲁迅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9〕随后,连续发表文章称颂鲁迅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10〕鲁迅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启蒙大师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道路,无疑给邹韬奋以很深的启发和影响。
胡愈之在促使邹韬奋接近共产党的过程中起着更为主要更为直接的作用。1931年9月,邹韬奋撰文介绍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后,读书思人,很快拜访胡愈之,并向他约稿。胡愈之当时思想很进步,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1933年9月正式加入共产党), 答应为《生活周刊》写稿,但建议应以宣传抗日为重。邹韬奋赞同胡愈之的建议,此后每期组稿时,都邀请胡愈之参加,并把宣传抗日救国定为刊物的主要宗旨。“一·二八”事变后,胡愈之帮助邹韬奋编辑《生活周刊》,并担任撰述,还参与筹办《生活日报》。《生活周刊》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生活书店的创办都是在胡愈之的建议下实行的。1933年,胡愈之又协助邹韬奋进一步把生活书店改组成为出版合作社,规定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的原则,使生活书店成为进步的文化堡垒。晚年,胡愈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是这样我对邹韬奋起了影响作用,使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靠近了党。”〔11〕胡愈之使邹韬奋“靠近了党”这是确凿的事实,因为胡愈之是当时邹韬奋所能接触到的离共产党最近的人,并受到胡愈之多方面的帮助和影响。
三
邹韬奋在流亡海外期间(1933年7月—1935年8月)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邹韬奋游历、考察了英、法、德、意、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元气大伤,一时还没有恢复,唯苏联一枝独秀,欣欣向荣。出国前,邹韬奋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源,都可归结于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取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走,而绝非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和西洋的虚伪民主政治的老把戏所能挽救。……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12〕“百闻不知一见”,通过对几个“比较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国家(含苏联)的考察,邹韬奋更加真切地感觉到世界资本主义即将“油干灯草尽”和世界社会主义如日东升,前程似锦。
邹韬奋在国外考察过程中,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出国前,《生活周刊》虽然发表过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但就邹韬奋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则不全面、不系统。到伦敦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攻读马列主义书籍,并做了大量而详尽的笔记。归国后,他把这些笔记加以整理翻译,得《读书偶译》一本,于1937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书的“目次”主要有:“马克斯研究发凡”、“马克斯的理论体系”、“马克斯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的解释”、“唯物辩证法”、“马克斯的经济学”、“恩格斯的生平和工作”、“恩格斯的自白”、“列宁的时代”、“列宁的生平”、“列宁的理论”。邹韬奋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并对革命导师们产生了强烈的爱戴之情,以为“革命的思想家的奋斗生活,常常能给我们以很深的‘灵感’。我每想到马克斯和列宁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无时不‘心向往之’。”〔13〕
邹韬奋特别推崇苏联共产党,认为“苏联的党和勤劳大众是联络成一片的。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代表勤劳大众的利益,是因为能领导人民为着勤劳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党是领导大众的中心力量”,他们的人数虽仅占全体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但“这少数分子是具有阶级使命的意识和自我牺牲决心的人们”。〔14〕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苏联共产党的认识加深了邹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了解。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邹韬奋指出:“我们的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我们的出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决不能依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去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15〕这里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邹韬奋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大众赢得“民族解放的斗争”。
邹韬奋出国时,“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考察欧洲诸国(含苏联)后,则目标已定,方向已明,不再彷徨和苦闷。赴美途中,他欣然写道:“时代的巨轮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着,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路线,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16〕邹韬奋已经彻底挣脱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巢臼,踏上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征途。
访美期间,邹韬奋曾与中共留美人士(徐永煐)谈及自己的思想发展情况,坚定地表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可任意选择的两条路。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获致,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之后,他们还讨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7〕这说明邹韬奋不仅找到了能够救国救民的“集团”,而且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
四
1935年8月,邹韬奋从美国回到上海。 此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路上,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处于高度隐蔽状态,邹韬奋没能及时与党组织联系上。同时,华北危机严重,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邹韬奋既是服膺共产党的号召,又是出自对于国事的研究和认识,没有主张立即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仍然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战斗在上海和香港。他先后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生活日报周刊》),回上海续办《生活星期刊》(由《生活日报周刊》易名而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而大造舆论,其思想境界之高、言论之精当远远超过《生活周刊》时期。
1936年2月,《大众生活》遭禁,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 在香港筹备及主办《生活日报》及其附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的过程中,邹韬奋与共产党人有了较多的、主动的接触。“西南事变”发生时,香港报界有的主张讨伐西南,有的主张反抗“中央”。邹韬奋通过柳湜等共产党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决定把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体现在报纸的宣传中。〔18〕胡愈之应邹韬奋电邀也从法国回到香港,在许多方面予邹韬奋以实际支持和影响。
在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得知《生活日报》及其附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即将创办,曾化名“莫文华”给邹韬奋写了两封长信,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思想,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期望邹韬奋所办报刊“应担负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组织”的宣传。邹韬奋把这两封信均刊登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并加编者按说:“莫先生的这封信对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有着剀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不过我们还有一点愿提出研究,那就是“人民阵线’这个名称用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容易令人误解,不如用‘民族联合阵线’来得清楚”。“人民阵线”一词来自西班牙内战。西班牙人民为推翻德、意法西斯全力支持的佛朗哥独裁统治而结成最广泛的“人民阵线”。该阵线是个人民的组织,不包括政府及政府军。而中国的情况不同,国民党当局虽然怯外,但还没有充当傀儡,可以逼它抗日。因此,诚如邹韬奋所说,在中国引用“人民阵线”一词确实会引起误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一开始并没有把蒋介石及其嫡系军队列入统一战线之中。刘少奇的第一封信写于1936年5月24日,第二封信写于6月19日,正处在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过渡时期。信中不只用了“人民阵线”,同时也用了“统一战线”、“联合阵线”等名称。名称的混用反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过渡时期的某些不成熟性。邹韬奋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加进了自己的智慧,为该政策走向成熟作出了贡献。
1936年夏,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5月31日, 各地救亡团体聚会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坚决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邹韬奋虽不在上海,仍被推为执委。参加该会的代表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因此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为了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找到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明,并由胡愈之起草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该文件和《八一宣言》调子相近,站在中间派立场上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邹韬奋和陶行知认可签名后,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请沈钧儒、章乃器签名。该文件经修改,以《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为名,于7月31 日发表在《生活日报》上。由此可见,邹韬奋已在暗中自觉地听从共产党的指令了。
《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发表后,毛泽东曾来信支持,并有意突出该文件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差别。信中说:“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还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为此,毛泽东委派潘汉年与他们保持经常的接触。〔19〕于是,邹韬奋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取得了直接的联系。
五
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组成,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活动。邹韬奋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交往甚密,并多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经香港、广西前往武汉。12月中旬,在张仲实的陪同下,邹韬奋到八路军汉口办事处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有时也到生活书店,用谈天的方式讲解共产党的政策。邹韬奋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为着革命事业的需要,周恩来回答说:“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比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20〕自此以后,邹韬奋实际上已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他后来回忆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21〕
到重庆后,邹韬奋常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向他请教政治问题,并接受中共中央对国统区文化工作的指示。邹韬奋再次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仍要求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工作,并说:“目前党还是需要你这样做”。当时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邹韬奋常请周恩来到会讲话,介绍当前政治军事形势,并亲自伴送周恩来离开会场。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把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逐步转移到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邹韬奋一面公开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一面有计划地疏散书店人员,把出版发行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把生活书店的领导中心移至香港。邹韬奋本人也被迫出走香港。
邹韬奋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临死前,邹韬奋呻吟病榻,念念不忘胡愈之和周恩来这两位一前一后引导他不断走向进步的忠实的共产党朋友。他曾对生活书店骨干人员张锡荣说:“我的著作许多地方不成熟,如果能整理出版,请周恩来副主席或胡愈之先生帮我删削修改,因为我毕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他们两位是我最敬佩的。 ”〔22〕
邹韬奋是文化界名人、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和国民参政员,社会威望很高。国民党当局虽对他和由他主办的文化事业迫害、摧残有加,但也曾千方百计地拉笼过他。1938年初,蒋介石亲自找邹韬奋谈话,要求他们加入国民党。邹韬奋予以拒绝,并说:“中国是否能够只有一个政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3〕1939年7月, 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找邹韬奋谈话,强迫生活书店与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组织总管理处或董事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领导,并要求邹韬奋加入国民党。邹韬奋拒不同意。8月,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是南洋公学同学的身份,几次约见邹韬奋,重提将生活书店与官办书店合并,要邹韬奋加入国民党,均遭到邹韬奋的严辞拒绝。1940年7月, 国民党主管文化出版工作的总头目刘百闵向邹韬奋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与官方合作,保存书店;要么不与官方合作,听候“全部消灭”。邹韬奋义无反顾地回答:“我认为失去店格就是灭亡,与其失去店格而灭亡,还不如保全店格而灭亡。我的主意已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24〕
国民党威胁利诱、软硬兼施,邹韬奋誓死不入其彀中,共产党既无丝毫强迫,更不刻意笼络,邹韬奋却心向往之,多次主动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从这个事实中,不仅可以看出对国共两党人心之向背,更可以看出邹韬奋在选择了共产党后立场是多么坚定。从表面看,他属于中间派,但实际上他早已确认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了。从上海到武汉,到重庆,再到香港,虽然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安排,他始终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一直是以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来参加战斗的。
然而,邹韬奋不逞一时之勇,也不泄私人之愤。只要国民党还在抗日,只要蒋介石还没有做“汪精卫第二”,他都支持、督促国民党抗日,并在《全民抗战》上大力宣传蒋介石的抗日言论。邹韬奋切齿痛恨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反对民主、反共摩擦等倒行逆施行为,但不同意“推翻现政府而另换一个政府”的主张,并曾多次撰文劝导持这种观点的人。把革命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邹韬奋是一位有韧性的战斗者和杰出的统一战线工作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陷入敌手。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邹韬奋先转移到东江游击根据地,再转移至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光荣的归宿。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于上海。 他在遗嘱中最后一次恳请中共中央审查他的一生,“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家属,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唁电还称颂:“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25〕这一高度评价,邹韬奋是当之无愧的。
** *
周恩来曾把邹韬奋所走过的道路称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26〕就大的方向而言,每个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无不经由自我走向社会,在风雨如晦的社会里,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几经探索、思考、选择和磨砺,最后才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们都关心国事民瘼,具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并都自觉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因此,研究邹韬奋从误解、认识、接受到追求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对于加深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必然性,以及加深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正确性都有重要意义。
注释:
〔1〕《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1930年12月13日)。
〔2〕《生活周刊》第2卷第10期(1926年12月26日)。
〔3〕邹韬奋:《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页。
〔4〕《生活周刊》第5卷第20期(1930年4月27日)。
〔5〕《生活周刊》第6卷第44期(1931年10月24日)。
〔6〕《生活周刊》第8卷第10期(1933年3月1日)。
〔7〕《生活周刊》第8卷第4期(1933年1月28日)。
〔8〕《生活周刊》第8卷第6期(1933年2月11日)。
〔9〕《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1号(1936年10月25日)。
〔10〕《韬奋文集》卷1,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1页。
〔11〕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12〕《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1932年7月2日)。
〔13〕邹韬奋:《读书偶译·弁言》,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14〕《萍踪寄语三集》,《韬奋文集》卷2,第483页。
〔15〕《萍踪寄语三集·弁言》。
〔16〕《萍踪忆语》,《韬奋文集》卷2,第499页。
〔17〕徐永煐:《韬奋的共产主义思想》,《世界知识》第20卷第4期(1949年7月8日)。
〔18〕柳湜:《韬奋逝世十周年》,《光明日报》 1955年7月24日。
〔19〕《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64页。
〔20〕刘景华:《周恩来与邹韬奋的友谊》,《光明日报》1979年7月24日。
〔21〕沈一展:《难忘的一夜》,《书林》1979年第2期。
〔22〕〔24〕 邹嘉骊编《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269页。
〔23〕穆欣编《邹韬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页。
〔25〕〔26〕《韬奋文集》卷1,卷首插页、卷首周恩来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