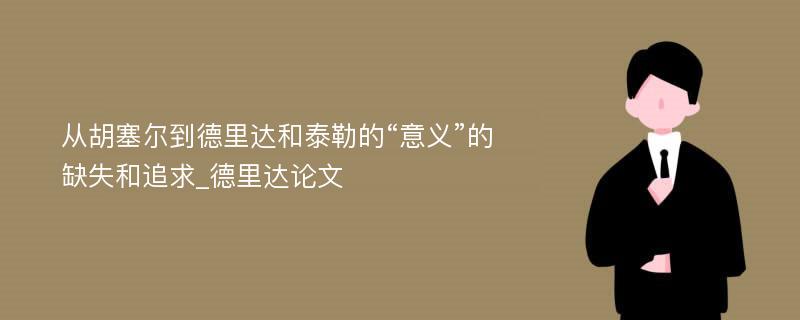
“意义”的缺在与追寻——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与泰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泰勒论文,在与论文,意义论文,德里达论文,胡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3)03-0122-09
罗丹(Auguste Rodin)那尊名为《思想者》(Thinker/Poet)的雕像是公认的西方艺术经典,它不仅成功地将诗人但丁(Dante)在地狱门前构思诗句的场景凝固为永恒瞬间,而且表达了但丁、罗丹,乃至每个人对自己人生、所处时代及整个世界的深沉思考。的确,自古希腊开始,如这尊雕像所呈现,有关意义的一切都被埋藏在思想深处,但尽管如此,它却被视为唯一照亮人之存在的生命之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甚至称之为“在场的遮蔽”①,因而希腊哲人及其后继者的任务就是竭力去把握、揭示它,使其澄明。而在德里达看来,诸如思想、真理、理性、逻辑这些名称无疑属于意义秩序,又不可避免地与基础、原则、中心相关联,它们共同为使意义成为一个永恒的在场而努力,也正是这种对于在场的热爱构成了以往西方哲学思考与研究的动力。[1]
的确,物质世界中“在”成为“不在”带来的变化使人们无法完全把握事物。因而,人们总对永恒不变的知识模式充满渴求。在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这正是对西方文化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本体论”传统,它给予“同一性”(same)以特权,任何差异、变化的他性事物如果想被认识主体了解,必须放弃自身的“不同性”(alterity)才能显现在同一性的层面,否则只能是缺在。[2]因而,无论是“在场的形而上学”还是“本体论”,它们对在场的渴求无非是想消除变化、差异及缺在带给人的不确定感与恐慌感。但是,如果那看似可以成为基础的在场原本就是建立在一片不断流动的“延异”(différance)的沙丘之上,“在”不过是“不在”产生的差异性效果,那人们渴望获得的稳定的生命意义无疑成了一个永远的缺在;不仅如此,当人的生命为之产生并展开的那个意义被揭示为不过是种历史中暂时的故事性叙述,那么,对于意义的寻找与依托如何才可能达成?
一、对意义的渴望
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及亚里士多德《解释篇》(16a3-8)开篇部分的论述曾在西方语言学研究史中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其真正的研究兴趣。“《克拉底鲁篇》驱使我们进行研究的并不是语言学而是本体论”,[3]因为在柏拉图看来,“那跟随名称寻找事物,分析事物意义的人正陷入被欺骗的危险中”,语言不是真理,仅仅是“声音的模仿”。[4]亚里士多德也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语言哲学或符号学。据麦克基恩(Richard McKeon)分析,亚氏所说的“心灵”、“言语”、“文字”可分别对应“内在沉默的话语”、“外部言说的话语”、“外部书写的话语”,内在话语本身具有意义,而外部话语依靠习俗获得意义。[5]因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想与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理想的语言应该像“数”一样,可直接清晰地反映思想,而他的最终愿望更是抛弃外部符号直接进入心灵中“事物的像”(the likenesses)。不仅如此,亚氏依靠数学模式构筑了讲究逻辑的思想体系,关注“一般命题”并强调“普适命题”的绝对真实与不可怀疑性。②因而,在他看来,“真正的哲学”需要依据这种由语言到心灵的“科学的”原则来建设。
而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对于语言的哲学论述及其背后真正的意义旨归,在歌德笔下通过浮士德对神圣文本《圣经》进行翻译得到了一种文学化的思考:“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古本,怀着至诚的心情试将神圣的原文翻译成我心爱的德语。上面写道,‘太初有言’!这里就卡住了!谁来帮我译下去?我不能把‘言’抬得那么高,如蒙神灵开导,就得把它译成另外一个字。那么,上面可是‘太初有意’了……”[6]
的确,对西方人而言,语言(言)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创世神话中宇宙的主宰者以言创世,他还将语言作为礼物赐予人,伊甸园中人对万物的命名就是它们的“专有名称”(proper name),而即便这种“命名的语言”(name language)[7]在巴别塔变乱后永远地失落了,语言仍被视为“通向真理之途”与“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是闪现着救赎之光的碎片(本雅明)。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发现,西方人对语言的偏爱总是易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般,抛弃“声音的模仿”与“外部的符号”指向具有“一般命题”乃至“普世命题”性质的“意义(意)”。而“太初有……”(In the beginning was……)的叙述更表达出一种原初性意义的预设及对其进行回溯性探问的渴望。
1938年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问世,对意义的探讨再次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生成现象学”的方法)进入西方哲学家的关注中。而按照他本人的强调,对于几何学起源问题的探讨具有一种示范性意义,这“必然导向最深刻的意义问题,那也是一般科学和科学史的问题,并且最终甚至是一种一般普遍史的问题”。[8]值得注意的是,在胡塞尔的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几何学在某一时刻因着它“最本源的意义”第一次进入了历史,“并且从此作为千年传统被保留在场,对我们仍然有效,并持存于一个不断建构的活生生的状态之中”。[9]于是,以往看似“现成的”几何学被胡塞尔揭示为“一种不断生成的传统”,而对于几何学的学习乃是对这种传统“发生的再激活”。
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努力无疑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并继续了前辈的遗产,热衷对“意义”的追求。但胡塞尔有两点独特的贡献:第一,胡塞尔通过分析欧式几何如何从欧几里德(Euclid)的主体内产生而成为一个普适性的几何公理,使“从先验主体性出发产生意义的行为”获得了“中立化”③,有力克服了柏拉图式的二元划分可能导致的自然论与客观论的危机;第二,胡塞尔揭示出几何学传统是一种“主题性”的历史构成,几何学在历史中不断地将自身带回到它最本源的意义,而正是这意义使几何学成为其所是。但也正是在对这两点贡献的思考中,德里达与泰勒发现,胡塞尔式的对于意义永恒在场的追求是一个无法完成但却值得不断渴望的梦想。
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中,德里达尖锐地指出,胡塞尔已经认识到几何学的全部意义起初并不能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规划(即胡塞尔所说的意义的“蓝图”)而存在,它必须不断产生于历史中,因而胡塞尔才要寻找一个意义产生的开端。但悖论的是,这样一来就已经假设了几何学的全部意义是已知的和完成的,也只有这样,它的原初意义才能在历史中被不断认出。由此,德里达评价称,《几何学的起源》仍停留在构成性分析之内,因为,胡塞尔为几何学预设了一个原初意义,这又代表了几何学的全部意义。而更进一步的考察可见,胡塞尔几何学(以及所有科学)的理想性,不仅在于它是最初发明者精神空间中形成的一种本质直观的结果,还在于这种“内在于个人的本源的涌现”在历史中达到了它“理想的客观性”。④德里达紧接着评价,“胡塞尔的整个历史哲学也停留在构成性分析之内”,这即表明,尽管几何学声称自己的产生具有原初意义,但几何学必须在历史中不断对此进行证明,才能确立这原初意义的先验性,而这历史证明的过程显然是后发生的,并且继续在发生着。[10]泰勒在《差错:一种后现代非/神学》中,从对《圣经》类型学分析入手,揭示出曾对西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基督宗教思想及其历史的产生与确立有着与几何学相似的构成性特征。在泰勒看来,像基督宗教这样以逻各斯为中心而形成的历史,虽然看似具有一种神圣的先验性,但它不过是众多故事性叙述(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而通过泰勒的分析,可以发现,胡塞尔对几何学进行的主题性的历史学考察,未必能帮助他寻找到具有“理想的客观性”的意义。
二、几何学梦想的瓦解
“如果年轻时掌握了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Pythagoren theorem),对于今天的我而言,它仍旧保持不变。”[11]这不仅是人获得知识的理想状态,更表达了哲学家们努力摆脱变化无常的物质世界进入永恒理念王国的愿望,而在胡塞尔看来,这正是一种几何学式的梦想。
尽管称不上是一位绝对的柏拉图主义者,但胡塞尔对理念却有着浓厚兴趣,在《几何学的起源》中,他以几何学为代表探讨了理想事物(ideality)的历史。在胡塞尔看来,欧几里德的几何最初产生于欧几里德这个发明主体内,而它的意义及其所包含的内容都同时在场于欧几里德的头脑中。但尽管几何产生于主体世界,而与其他同样存在于主体世界中的“精神的存在”不同,“几何学的存在”具有典型客观性。⑤因为,几何学的真理适用于任何人,无论在发明者最初的原始语言中还是翻译中,都始终保持相同;不仅如此,与那些我们只能在特定时空中看到某些特定面相的普通物质客体不同,几何学的存在可以毫无保留地被完整给出,它可以独立于任何个体而存在。胡塞尔认为,所有理想事物都具有这种客观性,它适合于整个文化世界的精神产物。
的确,借由几何学,胡塞尔继续搭建着前人留下的完美理念王国。但与之不同的是,这“理想的客体”必须在历史中不断证明自身完美的客观性,因为即使是今天人们看来具有完美客观性的几何学,它仍有一个历史:这是欧式几何如何从欧几里德这个主体内产生出来并成为一个几何公理的历史。⑥那这历史如何形成的呢?胡塞尔称“通过语言”,即几何学真理“获得了它语言上的鲜活身体”。[12]但是,具体化的语言如何能完成将几何学真理客观化的任务呢?为此,胡塞尔首先处理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创造了一个共同体,在这里成员们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主体间的交流,达成理解。这无疑为分享几何学的知识提供了条件,它可以从第一个发明者的脑海中走向外在的客观。然而,在发明者与他的伙伴都已不在的时代,几何学的知识如何才能长久地存在?胡塞尔指出,“书写”将几何学的真理记录下来以免随着发明者的死亡而消失,但同时也使那真理成为文字中的“沉淀物”,而这也是他提醒人们注意的语言中一种永久的危险性。因而,几何学当初的自明性需要后来的读者“再激活”,为此需要区分“消极的理解”与“唤醒经验”的阅读,因为“语言的诱惑容易产生一种读者群体,他们只是被动地了解……而没有回到事物本身”,但无论如何,对胡塞尔来说,书写都是必需的条件,正是它使几何学成为永恒的真理。[13]
德里达敏锐地察觉到,胡塞尔一直渴望脱离任何具体的物质性联系而获得理想客观性,但即便是最符合这种要求的几何学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尽管胡塞尔一再表明理想事物的客观性具有超越任何具体语言的能力,但他最后却不得不求助语言来实现这种客观性,否则理想的事物只能被封锁在第一个几何学家的脑海中,“正是历史地道成肉身释放了超越性,而非禁锢它”。⑦德里达指出,在几何学成为真理的历史中,仅仅依靠发明者将它说出是不够的,在发明者不在或永远不在的情况下,几何学如果想继续流传下去并获得持久的客观性,必须依靠文字记载的帮忙,这是一种言说者不在场的交流,因而,德里达论述称“书写创造了一种独立超越的领地”,[14]在那里语言成为一项公共财产,它可以在第一个几何学家与他的第一位对话者都不在场的情况下依旧发生作用。由此看来,是书写保证了几何学“理想的客观性”(也即指真理、意义等)永恒存在,而它同时也提醒人们,这已被视为基础的“在场”(几何学)不过是那“不在场”(几何学的发明者)的产物。此外,德里达还吸收现象学方法继续讨论“在场”这个复杂的建构:例如一支飞矢,我们通常认为它在运动的每个瞬间都在场,但如果每个瞬间的在场都是一个特殊的点,那它只能是一个个断点而不是运动的箭,因而,如果箭从它飞行开始到结束的每一瞬间都在运动,那这运动在每一个当下都从不在场,它总是处于过去与未来的痕迹中。由此可见,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每个瞬间都真实在场,是因为当下的瞬间看起来似乎是个无法分解的绝对时刻,过去是前一个当下,未来是即将来临的当下,但却没注意到当事物在瞬间发生时,这个瞬间已经分割了自己并被不在场所占据。[15]因此,德里达要求我们在差异(difference)与延迟(deferral)的关系中思考在场,“假设在场……不再是存在的绝对基本形式,而是……‘效果’,在一个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在场而是延异”。[16]
进而言之,在场与不在场的悖论关系不仅存在于几何学真理为了延续它的客观性不得不求助于书写的阶段,在几何学从它的发明者那里走向外在公共交流空间获得自身独立性的那一刻就已开始,胡塞尔称其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德里达称之为“结构与事件”的吊诡运动,“意义”正从这运动中产生。[17]人们通常认为言说者说出的意思就是语词的意义,但只有获得接受者认可,该意义方能成立,这即表明语词的意义实际上存在于一个语言系统中,只有同处该系统中并熟悉其规则的人们才能理解语词的意义,而此一系统的形成却是凭借以往人们的交流行为与经验为基础,因而“一种语言的结构(语言标准与规则的系统)是事件的产物,是先前言说行动的结果”。⑧但当我们把事件看做语言结构的来源时,却发现每一个事件本身都已经为之前的结构所决定。因而,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寻找语言最初的源头,得到的只能是结构与事件间的区分。不仅如此,即便是远古时代的洞穴中人,在他刚开始习得语言的时候以某种特殊的声音来指示“食物”,这种声音也已经与其他声音区别开了,而意义的行为正是建立于这种差异的基础上。[18]
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详细分析了“语言产生于差异”。对索绪尔来说,只有服务于表达与交流的声音才能成为语言,因而他将“语言”定义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19]而讨论语言就是讨论符号的本质,语言符号性质的“第一个原则”就“符号的任意性”,符号的构成及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仅仅“以约定俗成为基础”,当然这并不是“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而是指符号“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20]因而,一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只依于符号间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声音符号中,如“bat”与“pat,mat,bad,bet”的差别;也表现在文字符号中,如字母“t”与“l,f,i,d”的差别,而无论是“bat”还是“t”,只有在与其他不在场符号的关系中才能被“说出”与“写出”。[21]而这也导致了结构主义及符号学中的其他区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符号系统中的差异、能指与所指的差异。[22]索绪尔总结,符号并非确定的实体,而是差异的结果,“在语言系统中只有差异”。[23]对此,德里达评论,“无论在书写还是言说的话语中……每一个要素——无论是音素(phoneme)还是字素(grapheme)——的构成都与序列或系统中其他要素留下的痕迹相关。这种结合与交织就是文本(text),它只有通过另一个文本的转换才能产生。无论是在要素还是系统中,没有事物是简单地在场与不在场。只有差异与踪迹的踪迹。”[24]
因而,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想努力确证一种意义的永恒在场,而在其论证中,这梦想的实现主要依靠语言这个中介,但经过对语言的分析,德里达发现任何“在场”其实都已被“延异”所占据,它不过是已经“不在场”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延异就那个产生意义的最终基础,相反,延异总是另一个延异的结果,这将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局。于是,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探询意义的几何学式梦想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历史的终结
《几何学的起源》中,论述几何学如何在历史中表现出它的“理想的客观性”时,胡塞尔指出:“从一开始,历史就只是意义的形成和本源意义的积淀的相互关联、相互蕴含的活生生的运动。”[25]在这里,胡塞尔不仅预设了任何一种具体历史都有其先验目的性(即本源意义),而且他还继续解释称,对此先验目的性的把握就是“去认识”(即:意义的形成),而这必然会导向一个最高的问题“即关于理性的普遍目的论的问题”。[26]胡塞尔对于历史的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历史的经典阐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总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这实际上已经被认识到了,并在不断地被认识……那就是历史中的理性,这被哲学地表现出来而且必需如此……没有这种目的的历史将仅仅是一种无意志的想象消遣,甚至连童话故事都称不上,因为即便是孩子们也要求故事有趣,至少能感觉到某些意图及事件与行为之间的关联。”[27]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两位后现代思想的代表——尼采与德里达看来,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这一论断恰恰是对历史的终结。
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指出,黑格尔所说的历史不过是“绝对知识中作为自我在场的存在的历史,是自我意识无限在场的历史,这是一个封闭的历史,因为,除了作为知识与权力的在(Being)之显现与所有在场的存在者的重新聚合,历史什么都不是。而由于意识中的绝对自我在场是完满在场的无限召唤,绝对知识的实现就是对无限的终结,这只能是没有延异的声音中概念、逻各斯与意识的结合”。[28]因而,这种历史不过是纯粹的智性沉思,没有真正处理存在于现象界中的、与历史相关的重要议题:时间、自我及构成历史的众多事件。与黑格尔相比,胡塞尔关于历史的看法显然有所进步,他注意到了特定时空内事物的多样变化与发展,并揭示了历史性的主体“人”已被预设了的视阈,但胡塞尔同时却也强调,所有作为历史事实而构成的东西,都必然具有其内在意义的结构,它们共同证明着历史中的普遍先验性,因而,这仍是对黑格尔式的封闭历史的继承。而尼采则颠倒了黑格尔的逻辑,表达了对历史的“另一种阅读”。他指出:“每一个故事都必须有一个目的,因而人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也是这样,这意味着:因为有‘世界史’,所以在世界的进程中一定有某种目的……我的生命没有目的,这明显是因为它发生的意外性,但我能为自己假定一个目的则是另一回事。”[29]而如果众多的意外发生可以被称做“历史”,那它们一定需要一个目的,因而,在尼采看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历史都更像是一个“故事”。
泰勒深受解构思想影响,他将尼采的观点明确表述为“历史总是故事”。而且在他看来,至今仍对西方保持影响的基督宗教历史是对此最有力的佐证:经过创造、堕落、道成肉身、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救赎这五个重要行为,众多在时间上看似散在的事件,被构思为一个整体,而这完整历史过程最关键的中点(mid-point)即是“基督事件”(Christ/Logos/Word-event),这个事件具有特殊地位,被赋予解释的力量,因而,对于信仰者,耶稣的这种启示特征使所有其他事件成为可以被理解的。[30]但事实上,从一个民族宗教发展为普世宗教,基督宗教的历史并非始终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在《圣经》文本没有获得正式统一的权威以前,对于犹太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基督宗教是对犹太教的接续还是完全背离。对此,承认《新约》合法性的人们将耶稣看做犹太教预言传统最新的表现,而反对方认为两者无关联,典型代表为公元2世纪的诺斯替教徒马西昂(Gnostic,Marcion),他坚称耶稣的上帝并不是耶和华,认为犹太人的圣经与基督宗教的《新约》也并无连续关系。[31]马西昂的立场在以往研究圣经的学者看来无疑是对一神论信条的破坏,但如何使写于不同时代的文本统一为整体,如何将被“沉默时期”隔断的犹太人的历史与耶稣的诞生、受难与复活融合为连续的历史呢?对此,泰勒指出“类型学的解释”功不可没。
“类型学”(typ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tupos”与“logos”,其中“tupos”与“tuptō”相关,与之对应的英文为“strike”,意为“击打、冲压及其留下的痕迹”,是神学研究中最常用也是最典型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最早可见于奥古斯丁说的“旧约中隐含着新约,新约显明了旧约”,[32]而这种见解源于他从安布罗斯(Ambrose)那里习得的解释旧约的“一种比喻的方法”。根据泰勒的分析,奥古斯丁不仅在《论基督徒的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与《论灵魂与书信》(On the Spirit and the Letter)中发展了这种比喻的解释并为之辩护,而且这种“灵性的”解释学也帮助他将柏拉图/新柏拉图与犹太—基督宗教的思想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综合体系并一直保持某种影响。[33]因而,依据类型学的分析,犹太圣经中记录的事物与事件是基督生活与基督徒经验中各种事物与事件的预兆与模本,《新约》则是对《旧约》的补充与丰富而非替代。因为在类型学的解释者看来,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义的,世界总是“充满着背景与神秘性”。[34]但需要注意的是,类型学解释虽然仍是逻各斯中心的,却与本体论神学的解释传统有所不同。在后者看来,所有事物与事件都并非表面呈现的样子,而是超越自身指向一个被遮蔽的意义,即它们的真相(truth),因而在旧约与新约之间形成了“潜在与显现”的二元划分:“肉身与精神、阴影与光照、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深层、前景与背景、字面的与比喻的、神话与逻各斯等等”,但类型学解释却是要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第一个不仅表明自身也指示着第二个,第二个包含并实现了第一个”。[35]另外,类型学还暗示了类型(type)与比喻(trope)的密切关系。在比喻中,某个语词或短语被应用于适合它的另外的意义中,并不与原来意义形成冲突,据此,基督宗教中形成了道德解经(tropology)这种引申义的解释方法,它与类型学一道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督宗教的历史观念。不仅如此,泰勒称“隐喻”(metaphor)最有效地诠释出类型学解释与道德解经间的内在关联。与符号间偶然组合构成的换喻(metonymy)不同,隐喻中的能指与所指具有某种相似性,并且这种相似性保持了利科(Paul Ricoeur)所说的相同与差异之间的张力,因而,隐喻中的符号更准确地说应是象征(symbol),它使潜在居于显现中,使象征参与到被象征的事物中。以此视之,基督宗教中充满着众多的隐喻,它们将新旧约联合为统一的历史,而这当中最重要的隐喻就是神圣的逻各斯,因此我们称类型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的解释。
泰勒简要梳理了逻各斯观念的发展史及其重要影响,无论在赫拉克利特、斯多葛学派及柏拉图思想中,还是在犹太哲学家斐洛创造的逻各斯教义中,逻各斯一直指称那存在于表面现象与混乱经验之下的秩序与原则。而在《约翰福音》里,逻各斯还被赋予了另一个新意涵——与上帝同在的逻各斯而非他的从属者,这神圣的逻各斯是一个包含着阿尔发(Alpha)与欧米伽(Omega)的整体,而逻各斯的活动构成了整个被造的秩序,并表现在那些看起来似乎并无关联的人与事中。因而,在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类型学的帮助下,古希伯来的以撒献祭、公元1世纪耶稣的受难及此后多次基督徒被迫害这众多事件被联结在一起。不仅如此,逻各斯内部还蕴涵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张力结构,因而,一个事件既是自身起源的回声,也是未来实现的基础,它总在“考古学”与“目的论”之间摆荡,但这并非意味着简单地重复循环,过去与未来并不相同,后来的发生不仅仅是对先前的完成与实现,更是对它的超越。而这种类型学的解释,最突出的例证即是保罗在《罗马书》(5:12-17)中将基督视为“第二个亚当”,而在从亚当到基督的过程中,人“从婴儿成长为成年……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冲突与痛苦。是拯救展开了一个历史……第二个亚当比第一个更伟大,而第一个亚当是为了第二个”。[36]因而,神圣的逻各斯是“线”,将开始、中间、结尾联合为统一的整体,使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成了有意义的模式。[37]
在泰勒看来,正因为神圣逻各斯的巨大影响,在西方这个已经基督宗教化了的世界中,历史既是神学中心的也是逻各斯中心的,可如果目前的世界像尼采宣布的那样“上帝死了”,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可我们仍能清楚地感到时间在继续,那在这种情况下“说历史结束了可能意味着什么”?历史并不是唯一的,那条逻各斯之线固然神圣,却只是众多叙述之线中的一条,它被人们想象并创造出来以对抗时间带给我们的恐惧感。那叙述又是如何塑造了一个历史呢?[38]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利用一个线团帮助她的情人成功走出了围困怪兽的迷宫。泰勒借此指出,由于表示“时间”的希腊文为“Xpóνos(khronos)”,它的首字母“X”是死亡的标志,而且“Chronos”这个词还是一个专门吞吃自己孩子的神的名称,因而,时间正是这样一个产生死亡的迷宫;而叙述则如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它是救生索,可以杀死(X-ing out)时间与死亡之神。不仅如此,“X”不仅是唤起人们恐惧之感的交叉股骨图形(crossbones),更代表了各各他(Golgotha)的十字架,它是一个亲吻、鱼,是基督,是构筑了基督宗教历史的逻各斯。因而,通过叙述,时间成为历史以对抗时间。泰勒指出,日常经验中,时间总是表现为不断地连续,而我们永远无法看清其中的内在联系,“编年史”就是对这种时间的再现,它只是按照事件的发生顺序将其排列出来,其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联,有时甚至还存在着断点,而且编年史也没有任何对事件的评价,没有所谓的中心事件与主题,而即便它以某个事件为开始进行记录,但也并非意味着这就是一个绝对的开端,更不用说有一个最终的结尾。但叙述却不同,依靠情节(plot)⑨每一个散在的事件都有特定意义,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因而,叙述是一个具有开端、中间、结尾的封闭整体,在这当中人自我及世界的意义被塑造了。于是,在泰勒看来,历史总是一个故事,那些所谓的事实总是已经被叙述之网过滤过的,而真实也只能在言语的建构中才能成立。
胡塞尔几何学式的意义梦想,需要在历史中完成对自身理想客观性的证明,但时间却是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的迷宫。对此,泰勒认为,“叙述”可以将编年史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使人们享受到时间的完满,而这也正是对一个不受差异与缺在打扰的完全在场的渴求。的确,历史制造了一个“起源的神话”,以此来回避原初的缺乏,但这种驯化时间的企图总是被无法避免的死亡所破坏。因而,在时间的残局中,那些有着怀乡病的流浪者只能依靠不断地讲述故事来“扼杀”时间,以便在这过程中获得暂时的意义依托。而胡塞尔的努力无疑表明他正是这当中的一员。
在《立场》(Positions)一书中,德里达毫不留情地指出,一种要求完全在场的幻想已经控制了整个西方思想传统,这误导人们认为,思考一种自我指涉的概念是可能的,它在场于思想面前,独立于任何语言与符号指示系统之外。而这种德里达称之为“超越的所指”的概念,一直以来被人们冠以“真理”、“意义”、“上帝”等名称。正是有了这种“可能”的鼓舞,胡塞尔努力实践他的几何学梦想,渴望获得一个永恒不变的意义公式。但事实证明,没有语言的帮助这梦想将无法实现,而这梦想也正因为语言而被延异。不仅如此,胡塞尔为了获得意义梦想而运用的历史考察方法,在德里达看来仍是执著于对“在场”的偏爱。而正如泰勒所言“历史总是故事”,虽然它以逻各斯为中心而构成,但历史却不是唯一的。因为只要时间还存在,胡塞尔那种需要在历史中证明自身具有理想客观性的意义就不可能真正完成,毕竟这证明完成之时即是历史终结之处。
在德里达、泰勒那里,胡塞尔关于意义的梦想永远失落了,成为一个不断延异的弥赛亚,但他们并未否认胡塞尔寻找意义的努力,这努力仍“在路上”,而只有最大可能地包容任何一种关于意义的叙述,意义本身才能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获得胡塞尔所渴望的那种超越历史的理想客观性。因而,经过德里达、泰勒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尽管永恒的意义只能以缺在的方式表明自身的在场,但这“缺在的意义”与“为获得意义而建构历史”之间的内在张力恰恰保证了人们对意义不断寻找的激情,而对于这种张力结构的揭示,将为人们对那个缺在的意义进行更加丰富而多元的阐释敞开空间。这也正是一个在世俗世界如何捍卫多元、平等与绝对正义的启示。
收稿日期:2013-01-08
注释:
①弗莱堡早期,海德格尔曾说,“人不可能像丢掉他的小刀那样丢掉上帝。”对此伽达默尔指出,事实上人也不能仅在小刀不在场的意义上就轻易丢掉它。当一个人丢掉小刀这个长期熟悉的用具时,他不断发觉“它不在”这一事实正表明了它的存在。由此,“本质”被具体化了,我们也才能证明当下的东西如何同时是“在场的遮蔽”。而事实上,所谓意义与本质总是存在于具体与过程中,但希腊哲学把本质作为客体目标进行研究,造成了对意义本身的遗忘。参见[德]伽达默尔著:《伽达默尔集》,严平选编,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②此处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可参见Susan A.Handelman,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p.6-8.
③德里达称,“对于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揭露从未像在《几何学的起源》中那样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过。”参见德里达:《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第267页。
④如胡塞尔所言,几何学并非是产生于某个人意识领域中的存在,而是对“所有人”来说,某个客观地在那里的存在,甚至从其原初奠基就是一种超越时间性的存在。参见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引》,钱捷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出版公司,2005年,第185-187页。
⑤该问题可转换为:是欧几里德发明了几何,还是他发现了几何?参见James K.A.Smith,Jacques Derrida:Live Theory,New York & London:Continuum,2005,p.136.
⑥胡塞尔认为,几何学在发明主体内的产生是“内在于个人的本源的涌现”,这即是最本源意义的涌现,它具有“自明的理想客观性”,而几何学在历史中不断回溯性的发展则最终达致并证明自身的理想客观性。可见胡塞尔给出的是一种循环论证,也证明了德里达对其“构成性分析”的评价。参见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第203页。
⑦德里达借用基督宗教的“道成肉身”类比以具体语言的方式对抽象客观理念进行的表达,表明了理想的客观性是在具体的历史中被不断证明与完成的。参见Jacques Derrida,Husserl's Origin of Geometry:An Introduction,trans.John P.Leavey,Stony Brook:N.Y.:N.Hays,1978,p.77.
⑧此处分析参见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95.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分析,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对此德里达指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符号系统中:‘语言系统对于一个言说事件是必须的,但后者也是语言系统的建立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循环……因而,他必须认识到,先于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之前是一个差异的系统。”参见Jacques Derrida,Positions,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28.
⑨“Plot”(情节)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做动词用时表示“在图上标出……的位置”,因而它可以把事件安排在其应处之位形成一个连续的发展线索,并由此提供一个指引;而作为名词用时,它表示“计划”或“特定用途的一小块土地”,这样一来,情节不只是构成故事的基础,更为它规定了一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