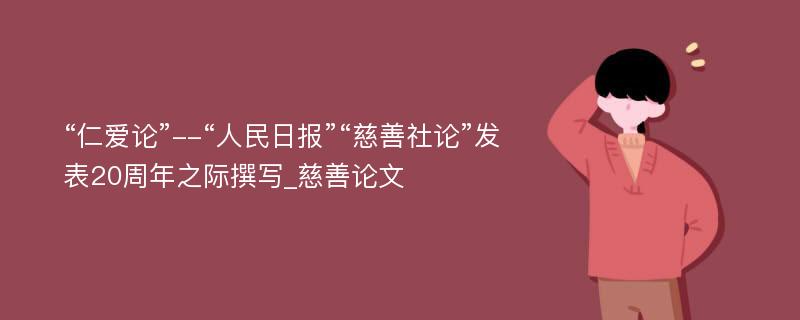
重新为慈善正名——写在《人民日报》社论“为慈善正名”发表二十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慈善论文,人民日报论文,二十论文,社论论文,写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2月24日,值“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十分特别的社论——《为慈善正名》。①这篇文章借主流媒体的声音和力量,以一种中国式的舆论宣教方式,一扫以往对“慈善”的妖魔化描述,褪去裹挟“慈善”的污名化外衣,让“慈善”公开重返政治舞台和公众视野。以这篇文章为发端,中国慈善事业回归正途,开启了一场漫长持久的自我“正名”之旅。慈善身份的“拨正”和慈善观念的“扭转”,不仅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久违的慈善记忆,释放了社会的爱心能量和公众的慈善热情,而且赋予了慈善合法身份和合理角色,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黄金二十年。 在这二十年里,中国慈善事业在政府主导下,重返正常发展轨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类慈善组织纷纷成立,蓬勃发展;募集资金物资成倍增长,力度空前;捐款捐物、志愿服务极其踊跃,爱心涌动;慈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慈善、参与慈善、监督慈善,慈善事业在“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种种问题。诸如“官办慈善”、“政府公益”、“暴力慈善”、“被慈善”、“慈善腐败”等“中国式慈善”问题,无一不触动着人们敏感的善心,体制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捐赠信息不透明、监督管理不规范,让中国人“闻善色变”,批评、嘲讽、质疑和观望接踵而来,让中国慈善事业陷入信任危机,饱受公众质疑,跌落舆论冰点。 二十年前,中国慈善迫切需要“正名”,挣脱政治枷锁,获得政治承认,重回发展正途;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慈善事业亟需重新为自己“正名”,洗脱社会污名,重拾公众信任,找回身份认同。时代在变,慈善在变,人们对慈善的理解也在变,从“善行中华”的黄金年代,到“谈善色变”的冰点时代,中国慈善事业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的冲击下,遭遇前所未有的身份尴尬和认同危机,其发展已经到了亟待转型的节点。喧嚣过后,官办慈善能否实现转身?慈善事业能否破冰前行迎来春天?慈善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实现复兴?这需要我们在转型的视域中,恰当地理解慈善、准确地定位慈善、积极地发展慈善,从历史经验、思想认知到文化认同、制度设计,重新为中国慈善正名。 一、慈善的“污名”:从“接纳”到“拒斥” 慈善事业是一个历史范畴。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②,作为道德事业的慈善公益,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着绝然不同的表征和功能,其道德基础、表现形式、历史定位、大众认知均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在历史脉络中审视中华慈善,我们不难发现,慈善事业在中华民族“大传统”的熏染下,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基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小传统”。仁者爱人、民胞物与是中华慈善持久不衰的精神动力,孝慈为怀、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崇尚仁政、宽厚待民是统治阶级约定俗成的政治方略。在这种共通和鲜明的历史基调中,慈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表现仍然存在天渊之别。 春秋以后,孔子以“爱人”释“仁”,描绘了“仁爱”为基础的大同社会理想;孟子视“恻隐之心”为“仁政”之始,倡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至此,“尚仁爱、重人本”的慈善思想踪迹已清晰可见。入汉唐,佛教兴盛,寺院慈善迅速发展、僧侣布施异常活跃。至宋元时期,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相伴发展、交相辉映,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慈幼局、婴儿局等官办慈善规模逐渐壮大,日趋兴盛发达;范仲淹开“义田”,朱熹事“社仓”,刘宰办“粥局”,民间慈善异军突起,蔚然成风。清末民初,善书、善堂、善会十分兴盛,同善会、广仁会等民间慈善团体相继发展,现代慈善萌芽。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在欧风美雨的席卷和西学东渐的洗礼下,国内善举仿行西方,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等近代慈善机构纷纷成立。民国时期,民间慈善组织发展渐入佳境,教养并重、官绅商教多元参与的慈善模式初具规模。 从总体上看,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慈善救济对收揽民心、安定社会的重要作用,纷纷把社会救助思想上升为国家惠民政策,将慈善救济活动纳入官僚行政体制,故,怜贫济弱、力行慈善成为开明君主的“恩赐”和有为政府的“仁慈”。③因而,在“德治”理念的驱使和“王道”政治的引领下,慈善在不同朝代的境遇虽有所不同,但一直被政府接纳,占据一席之地。统治者的接纳,使慈善活动犹如涓涓细流,持久而绵长地流淌在历史长河中,养成了乐善好施的大众风尚和扶危济困的中华传统。 1949年后,慈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境遇发生了巨大扭转。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总体性权力和再分配经济相结合的总体性社会,具体表现为: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和包办全部社会职能;在社会整合方式上,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党-国家的治理架构,使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色彩。在这种国家超越社会、政治压倒一切的逻辑中,中国共产党对旧有的慈善机构进行接收、改造和调整,从而巩固新生政权建设、维持政治社会秩序。1950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立,将原来各类民间慈善团体统一并入其中。由此,民间慈善机构既被接收和改造,便不再独立,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活力。慈善事业的衰熄和停滞也就势所必然了。 随着极“左”思潮的蔓延和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社会生活被贴上了各种政治标签,在这种情势下,慈善事业也难逃政治化、阶级化的历史命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慈善被视为洪水猛兽,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腐蚀和瓦解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毒药和砒霜,‘狠批猛斗’,以致使人们避之尤恐不及,谈‘慈善’而色变,直到我们几乎忘却了这个词。”④激荡汹涌的政治运动给“慈善”戴上了几顶沉重的帽子:帝国主义殖民的“麻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封建统治者蒙骗人心的“工具”、地主阶级愚弄民众的伪善之举。于是,政治化的“慈善”遭到政治的否定,在主流话语系统失去了存在的合法基础。社会上既无人倡导慈善,也无媒介宣传慈善。“‘慈善’二字,……被长久地故意地回避。仿佛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甚或,仿佛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有害的话题。似乎一公开倡导慈善,反而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了。”⑤自然而然的,慈善成了禁区,备受冷落,长期无人问津。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慈善事业的发展受到阻断,一度停止。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慈善事业彻底走向中断。“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方式,剥夺了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党-国家的强势干预和一系列的改组、接管、取缔措施,使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慈善被冠以“封资修”的帽子而饱受批判。在这一历史背景中,慈善成了贬义词,被主流政治扫地出门,彻底排除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在此期间,中国社会不存在任何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也没有出现任何组织化、规模化、经常性的慈善活动。与此相适应,党和政府成为社会救济的唯一主体。在慈善事业不复存在的岁月里,政府救助成为慈善救助的代名词,社会福利资源几乎被政府垄断,社会救助功能完全由政府包办。政府和集体主办的社会福利事业规模庞大,并一枝独秀。 虽然影响慈善发展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命运则更为典型地说明了政治环境对慈善事业的深沉影响。由新中国慈善事业的漫长“中断”历史可以窥见,“在影响慈善事业的诸因素中,政治因素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由于政治的影响,导致慈善事业的畸形发展,乃至消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⑥ 二、慈善的正名:国家赋予合法性与重启发展 政治意识形态对慈善事业的无情打击和彻底否定,延缓了慈善事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从整个历史脉络来看,“本来中国慈善经过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发展了70余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就应当进行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慈善向当代慈善转型”。⑦然而,由于历史局限和政治禁锢,近代慈善向当代慈善的“第二次转型”,被人为阻断了30余年。这一长时段的中断和空白,使中国慈善事业错过了传承和接续民国时期发展精髓的最佳机遇,也导致中国慈善的现代化进程存在难以逾越的历史鸿沟,亦引发中国慈善“先天不足、后天积弱、发展畸形”的现实难题。 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加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意识的解冻为慈善事业的复兴提供了契机。1981年,中国首家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辅助国家发展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它实施了两项颇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1987年,新中国第一张公益彩票突破层层阻力,谨慎登场,开启有奖募捐的历史先河。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书写了中国慈善事业史中不能绕开的动人乐章——希望工程,成为中国最动人、最知名的公益项目。1994年,中国迄今最大的综合性公益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开展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八大方面的慈善项目,形成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这些由特定事件串联起来的历史线索,闪耀着人性光辉、经历着风雨彩虹,构筑起中国慈善事业重回正轨的重要里程碑。 在社会转型发端之际,“为慈善正名”作为一个重大事件问世,正式翻开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崭新篇章。1994年2月24日,以辽宁省慈善总会成立为契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慈善正名》,吹响重启慈善事业的响亮号角:“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⑧在这篇旗帜鲜明、立场明确的社论中,《人民日报》用灵动深沉的语调,为慈善“正本清源”:“我们与‘慈善’二字是久违了的。……积德行善、救困扶危,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我们世代传诵的行为规范之一。事实上,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行侠仗义、疏财济贫、助孤扶残、尊老爱幼的传统,有做这类善事的‘好人’和‘善人’,所谓‘史不绝书,代有传人’。在人类历史上,亦复如是。而在现代,它又与人道主义、尊重人、关心人、爱他人等美德联系在一起,成为维系人心向善从美的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动力”。⑨ 虽然这篇社论带有惯常的政治味道,但它却使慈善卸去政治枷锁、洗脱政治污名、重获政治承认,富有转型与巨变的标志性意义。随着党和国家“为慈善正名”,慈善事业不再被当作“旧社会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装饰品”、“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而扫地出门,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民族美德和优良传统;不再被视为“封建毒素”、“愚民工具”、“伪善之举”而大批特批,而是华丽转身,成为维系人心向善、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不再是政治禁忌和社会禁区,而是可以公开谈论、自愿参与的公共议题。从此,慈善获得承认和新生,重启公益理念启蒙、公益行动探索的历史进程,它不仅再次以正面形象呈现于国家主流话语系统,承担起辅助社会建设的应有角色,而且重新回归日常生活空间和社会公共领域,在媒介平台和社会空间渐趋活跃,并占据一席之地。 从上述意义上说,《为慈善正名》一文的公开发表,具有十分显著的启蒙价值和历史意义,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回望中国现代公益二十年的发展征途,不难发现,慈善事业与改革开放相伴相携、一路同行。如果说改革开放对于慈善的意义在于“释放社会自由、激发社会活力”,为慈善开辟空间和土壤,那么,“为慈善正名”就是在国家倡导下,赋予慈善合法性,让慈善“起死回生”、获得生命,再度启程。换言之,“为慈善正名”不仅是普及慈善精神、探索公益道路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辅助国家政权建设、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战略之举。正所谓,“改革推动公益,慈善改变中国”。 从古至今,无论是从“接纳”到“排斥”,抑或从“否定”到“承认”,还是从“污名”到“正名”,“国家”都是影响慈善发展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历史语境下,国家不仅能够赋予或剥夺慈善的合法性,使慈善获得或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可以采取行政吸纳、官民合办、官督民办等方式,让民间慈善参与和辅助国家建设。从本质上说,保障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是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核心目标。发展慈善事业、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需求,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国家对待慈善的态度,不论“打”、“压”还是“推”、“拉”,都事关国家政权建设议题。正如波齐所言,“国家总是代表自己作为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的核心,超越地方主义,凝聚所有的个人、从社会中建构权力。”⑩因而,国家政权建设不仅在于集权,消除障碍性组织和分散化权力,增强组织、动员和控制能力,更在于增权,理顺各种权力关系,整合国家整体利益与公民个体权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调整、改造直至取缔慈善组织,在于集权的需要,增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我们更不难理解的是,民国时期,欧风美雨、外侮内乱导致国家动荡、政府衰败,来自政权力量的干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慈善发展的社会空间,成就了慈善事业的“蓬勃生机”。总之,“成功取代其他统治替代者,最终成为辖区内所有公民利益和权利的归属中心”(11),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目标,更是国家抑制或发展慈善的主要动因。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为慈善正名”,赋予慈善正常地位,客观上是为了缓解体制转轨和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张力,但其深层原因则涉及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增量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社会转型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而且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亟需国家职能和政府角色的转变。在新形势下,“国家不仅是……象征主权的组织,国家还必须完成一种面向公共组织的性质转变,使自己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管理公共财物,为公共社会服务的组织。”(12)所以,恢复慈善名誉、发展慈善事业,是党和国家在市场条件下做出的角色调整,是势之所导、时之所需。它有利于增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 恰如福柯指出,作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政府必须履行“牧养”(Pastoral)功能,进而言之,负责任的政府都会强调人口福利和保护性“治理术”。(13)而慈善救助是社会福利与安全机制的重要内容。从上述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国家有限的财力无力承担起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重任,因而发展慈善事业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慈善事业呼之欲出。在此条件下,党和国家因势利导,“为慈善正名”,推动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便是为了履行“牧养”功能,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市场转型的长期性和社会建设的艰巨性,不仅意味着慈善事业将会长期存在,也决定了国家主导和助推慈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慈善的危机:行政吸纳与官办慈善的兴衰 自1994年慈善获得“正名”以来,慈善事业从受到政府批判到被政府肯定并大力推动,从被定义为“具有伪善性和欺骗性”的反面事物到“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崇高事业,经历了巨大的身份扭转。(14)这种鲜明反差更加凸显了国家“为慈善正名”的重要历史价值。具体言之,国家赋予的合法性不仅为慈善事业的重启和拓展提供了社会空间,让中国慈善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使中国慈善打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中国慈善成长为“中国式慈善”的未来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党和国家主导的“为慈善正名”,不仅让慈善在中国社会“复活重生”,而且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二十年的黄金发展期,走过了一条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再国家化”之路。二十年来,国家主导的慈善复兴之路融合了本土特色和国际范式,使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破土而出、击水前行,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慈善”模式在激荡中成型。这二十年,是国家主导、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二十年,是官办慈善组织集中发展、不断壮大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官办慈善组织从萌芽吐绿到开花结果,走过了光彩照人的重要历程。 在重启发展之初,由于中国慈善事业已经中断多年、一片空白,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并不存在,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开启全面复兴之路的慈善事业并非原有慈善组织的延续,而是另辟新路、另起炉灶。(15)为了另辟新路、填补空白,政府凭借自身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吸纳能力,从其内部分化出非营利组织,以便用合法的手段汲取民间分散的慈善资源。(16)大量慈善组织依托于民政部门建立,和各级政府有着极其紧密的血肉联系。它们名为“民间公益组织”,实为“政府派出机构”,不仅组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接来自政府,享受政府财政拨款和税费减免,而且组织运作基于政府逻辑展开,与政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组织外部形式与实际运作逻辑的明显背离。 在慈善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国家采取‘社会的方式’进入社会,但是进入社会的国家已经不同于‘纯粹的国家’,而‘社会的方式’又打上了‘国家的’烙印,国家对第三部门组织的干预和影响无处不在。”(17)显然,这种慈善事业的“再国家化”历程集中体现了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配作用。与制度文本的规定有别,在实际的制度实践中,政府是慈善事业的真正组织者、实际运营者、主要资助者。(18)它代替了民间力量,直接控制慈善组织的准入、干预慈善组织的业务、介入慈善组织的运作,严重限制了慈善组织开展活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甚至可以说,在国家主导的基本框架下,党和政府决定了慈善事业发展的动力、方向和道路。在中国,发展慈善事业仍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行为,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尚未完全发育。 笔者以为,国家主导的慈善复兴之路,是“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模式的最好映证。在此,所谓“行政”,既包括政府或国家的“象征意义”,又包括政府或国家的“具体行为”,而“吸纳”则意味着政府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市民社会无法养成,市民社会反抗国家之类的社会结构更是无法滋生。按照康晓光等人的分析逻辑,“行政吸纳社会”模式建立在“分类控制”体系的基础之上,其核心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控制和功能替代。“‘控制’是为了防止第三部门组织挑战政府权威,是为了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而‘功能替代’是通过培育‘可控的’第三部门组织体系,并利用它们满足社会的需求,消除‘自治的’第三部门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从功能上替代那些‘自治’的第三部门组织,进而避免社会领域中出现独立于政府的第三部门组织,最终达到消除挑战势力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目的。”(19)因而,在“行政吸纳社会”模式下,“控制”优先于“支持”,“支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控制”,而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起来提供诸如慈善救助的公共服务,只不过是“控制”的副产品。从本质上言之,“‘功能替代’是一种更为精巧的控制手段,通过主动回应来自社会的需求,从功能上‘替代’被统治者的‘自治’诉求,从而达到‘通过替代实现控制’的目的。通过运用这些策略,政府不但赢得了权威政体的稳定,也赢得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 这种对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式解读,恰当地诠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深层逻辑。基于“控制”与“功能替代”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机制,虽然具有明显的权威色彩和工具特质,但却决定了中国慈善事业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路线,是“中国式慈善”得以发展成型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国家主导的慈善事业不断获得了现实政策的大力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不仅成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被纳入到党和政府的宏观发展规划之中,慈善事业的地位被提升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慈善事业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并将它提到“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定位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更加突出地强调“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使发展慈善事业成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总之,国家的政策话语和制度文本不断地“拔高”慈善事业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凸显了慈善的社会能见度和公众影响力,而且强化了“中国式慈善”的官办色彩。 在“行政吸纳社会”的发展逻辑下,官办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遍布全国的慈善会、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是它们的典型代表。以慈善会为例,截至2012年6月,我国县级以上慈善会总数达到1923家,基本构建起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的慈善网络。全国慈善会已成为我国接收社会捐赠的重要渠道,所接收社会捐赠总量多年来稳步增长。其中,2011年,全国各级慈善会共接受社会捐赠203.89亿元,占全国捐赠总量的24.13%。这些官办慈善组织依托以政府权力为运作核心的公益动员体系,具有巨大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能维持“低社会参与下的高慈善投入”式的高效发展(21),在灾难救济、扶贫助困、教育培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历史功勋。在1998年“抗洪救灾”、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2年“雅安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中,官办慈善组织活跃的身影和积极的行动,书写了许多公益实践的精彩篇章,记录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丰碑。 随着慈善事业的深入发展和公众关注度的提升,慈善逐渐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慈善事业也成长为一种颇具公共性的社会事业。2008年,全国爱心齐聚汶川、刮起全民慈善风暴,中国慈善迈进媒体宣称的“公益元年”,“中国式慈善”也获得井喷式发展。高潮过后,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低潮。随着郭美美事件、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曝光,国人掀起了“问责风暴”。特别是“郭美美事件”之后,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陷入舆论漩涡,饱受公众质疑,公信力危机重重。2011年以后,在“全民问责风暴”的持续冲击下,全国接收捐赠总额和红十字会系统的募捐额连年下降,个人捐赠降幅明显。 四、重新为慈善正名:从“承认”到“认同” 肆虐和持续的“全民问责风暴”,不仅是对官办慈善弊病的质疑和抨击,使官办慈善陷入信任危机,而且是对慈善事业名誉的侵蚀和损毁,使中国慈善发展跌落谷底。在此背景下,如何洗刷慈善的“污名”,重拾公众信任,创造性的回应广大公众关注的问题,重新为慈善正名,成为中国慈善事业正在面临和亟需解决的关键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问责风暴”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它既将官办慈善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饱受民众的口诛笔伐,也暴露了中国慈善事业的短板和缺陷,为“中国式慈善”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如何“转危为机”,重塑慈善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既考量政府管理部门的胆略和智慧,亦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协作和参与。 辩证地看,“全民问责”意味着“全面关注”,其本身就意味着慈善的反省和进步。慈善不再限于少数精英群体,不再囿于狭隘社会领域,不再属于富人的专利和明星的秀场,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自由进出的领地,是他们关注、参与、行动的公共领域。因而,“全民慈善热情”及接踵而来的“全民问责风暴”,掀起了人人关注慈善的热潮,标志着中国慈善进入社会化、大众化、草根化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慈善,每个人都是慈善行动的参与者、宣传者和监督者。所以,在这个时代,慈善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然改变,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成为推动慈善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 在现代慈善公益活动中,社会认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命题。围绕“我是谁”这一终极命题,泰菲尔(Tajfel)从个体和群体的互动关系中理解社会认同,即“个体认识到其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群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2)有别于这种心理层次的界定,社会学将社会认同纳入到“社会的”范畴,认为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社会情绪和共同行动,是社会成员对身份角色、阶层地位、制度安排、变迁过程的认知和评价。面对网络社会的来临,卡斯特指出,认同是人们主动建构意义和经验的过程。(23)因而,在一个具体慈善活动中,社会认同是公众意愿和态度的体现,体现为公众对于慈善活动价值理念、组织发动和运作流程的肯定和信任;社会认同也是公众行动和力量的展现,展现为公众积极参与、热情奉献公益活动的程度和过程。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价值观念的分化,中国社会的实践系统和观念系统在转型之中日趋自由、独立、开放、多元。诸多传统社会共识被打破,新的社会共识又尚未形成,社会认同呈现多元分化态势,价值观念的碰撞和话语冲突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背景中,官方慈善组织由于淤疾沉珂的暴露和负面事件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来自公众的认同,耗尽了公众的信任。所以,就社会认同而言,“全民问责风暴”是官办慈善组织的社会认同危机的集中爆发。 正如前文所述,在过去二十年,慈善事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赋予的。国家“给予”的合法性,不但为慈善事业的复兴之路提供了动力和空间,也使慈善的合理存在获得了社会“承认”。因而,在国家整合社会的基本框架下,国家的“承认”和允许构成了公民“承认”慈善的基本前提。在国家权威的主导和推动下,行政化的慈善事业快速发展,迎来了官办慈善的春天。这一历史渊源既使慈善事业高度依附于政府,打上了强烈的国家主义烙印,亦使政治话语解读慈善成为一种惯例,发展慈善事业成为一种典型的国家行为。 但是,国家权威的“承认”建立在治理社会、维护稳定的刚性需求之上,进而言之,二十年前,国家“为慈善正名”,恢复慈善的正常角色,在于利用慈善事业的治理功能,满足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在党和国家的视域中,慈善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而存在。恰如卡斯特所言,“认同所组织起来的是意义,而角色组织起来的是功能”(24),国家恢复和承认慈善的“角色”,接受的仅仅是慈善的实用价值和外部性功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接纳慈善,更没有从根本上接受慈善事业蕴含的“意义”和基本价值。换句话说,国家“正名”慈善,只是赋予了慈善的行政合法性,没有赋予慈善认同合法性,而它的行政合法性建立在服务社会治理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诸如自由、平等、开放、独立、自主、个性等元素,是慈善公益的本意和特质,是慈善事业能够获得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这些价值的缺席,为国家主导的慈善复兴之路埋下了隐患,为官办慈善事业陷入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 建基于国家“承认”的官办慈善系统,是一个由政府运作、从上到下的庞大系统。它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在动员、募集、配送慈善资源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正是长期以来政社不分的状态,使慈善组织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滋生了论资排辈、官僚作风、形式主义、资源垄断、效率低下、暗箱操作、贪污腐败等诸多问题,导致了“全民问责风暴”的来袭和慈善信任危机的爆发。表面上,官办慈善存在的诸多弊病,是引起舆论诟病的始作俑者,但实际上,慈善意义和基础价值的缺失、公众认同的转变和分化才是诱发信任危机的真正原因。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公众对慈善的社会认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官办慈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多事之秋的空前冲击,在阴霾未散的信任危机中,已悄然迈出转型发展的步伐。笔者以为,慈善事业的深度转型,不仅仅是组织架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转变,更是慈善事业的社会文化认同的变化和重构。过去,人们习以为常地将慈善视为政府行为,把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民政福利等同。现在,人们开始以民间的立场和社会的眼光看待慈善,在质疑和拒斥官办慈善组织的同时,呼吁慈善“褪去行政色彩、回归民间本色”。特别是“郭美美事件”后,慈善捐赠资金的流向出现了明显变化,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备受冷落,壹基金等民间慈善机构成为个人捐赠的主要对象。这些均表明,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同、理解和接受,已经呈现出分化之势,发生了从政府行为流转为社会行为的巨变。 当居于垄断地位的官办慈善机构饱受责难之时,处在社会边缘位置的草根公益、民间公益、网络微公益喷涌而出,异常活跃,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量,与官办慈善机构的持续低迷形成了鲜明对照。(25)这些扎根民间的草根组织,常常由无名精英振臂一呼,响应者众。它们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工具,发起了诸多轻松快乐的平民公益项目,诸如“大爱清尘”、“免费午餐”、“爱心衣橱”、“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等,深受大众喜爱。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行动、人人都能够创造公益价值,透明、开放、自由、平等、便利、高效是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典型特征,也是他们被大众认同的基本元素。这些民间公益项目的“认同建构是一个主观追寻意义的过程,而不再像传统社会认同那样是一个被动寻求角色归属的过程”。(26)正是在这种更广泛的、主动的认同力量的驱动下,大众性、草根性、社会性的慈善事业已是大势所趋,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暗箱化亦成为不可逆转的改革潮流。 从上述意义上说,官办慈善的公信力危机,是国家赋予慈善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是一种深度的社会认同危机。危机事件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标志着慈善事业的社会文化认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7)国家赋予的合法性,以权威主义方式“承认”了慈善存在的合理空间,但它缺少基本价值“内核”的驱动,不能维系慈善生命的持续,也不能给予慈善组织持久的养分。换言之,国家的“承认”给予了慈善的生命,却无法维系这一生命的持续健康成长。而进入大众化时代,慈善事业的生命力量最终需要公众认同的呵护。特别是当公众对慈善的认识和理解发生巨变时,慈善的认同合法性应来源于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他们的参与、信任和认同是慈善事业源源不竭的动力,也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源泉。 因而,“中国式慈善”需要回归公共空间、还原民间本色,通过广大公众的选择、参与和评判、建构来重塑自身的合法性,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接纳,这是“重新为慈善正名”的基本路径,舍此别无他途。可以说,“中国式慈善”的命运在于能否重获社会认同。慈善终究是社会行为,终究要回归民间,在官方慈善机构深陷泥潭之际,这一诉求显得尤为迫切。庆幸的是,在“问题倒逼”之下,政府已开始尝试一系列改革创新试验,从民办非企业草根组织直接登记、非公募基金审批权下放,到官办慈善机构自我改良,尽管一切尚“在路上”,但已触及慈善事业组织、运行和治理的深层肌理。 五、结语 为了去除沉疴,官办慈善“去行政化”的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似成医治“中国式慈善”病灶的一剂良方。在公共舆论的视野中,“去行政化”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焕发生机的必经之途。毋庸置疑的是,权力垄断和干预成为官办慈善陷入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因而“去行政化”确是对症下药之举。但“如何用药”需把握好火候。倘若用药过猛,则会欲速则不达,良方也会适得其反。所以,“去行政化”之路须因时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切不可操之过急。笔者以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尽管国家的控制力有所弱化,但国家仍然是社会生活系统的主导者,控制着社会话语的表达、社会规则的制订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尤其是国家拥有赋予或剥夺行政合法性的能力,而行政合法性依然是普通大众辨别慈善组织良莠真伪的重要标准之一。因而,慈善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不能脱离国家的支持和鼓励,若离开国家的支持,慈善事业便如水中浮萍,任凭风吹雨打,孤苦无依,前途未卜。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支持并非盲目的干预,而是依法适度行使公共服务的职能,为慈善事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这一要求下,党和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应适时转变,由“官办”转变为“官助”是势之所驱。它需要政府调整职能,从“限制”、“监控”转变为“服务”、“监管”,放权、让利、服务是基本原则,解除维稳“紧箍咒”、松绑社会组织是基本取向。目前,由于大势所趋,中国慈善事业已开始谋求转型发展契机,是否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决定官办慈善能否实现转身的基本条件。只有松绑社会组织,建设性力量方能生成;只有回归民间本色,重构慈善事业的社会认同才是可能预期的结果。 二十年前,党和国家力主“为慈善正名”,在党和国家的力推下,慈善事业获得了二十年的发展黄金期;二十年后,“重新为慈善正名”,国家仍然是主要责任者。与二十年前不同的是,国家不仅要承认慈善的角色和功能,更要接纳慈善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④⑧⑨孙月沐:《为慈善正名》,《人民日报》1994年2月24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103页。 ③王俊秋:《中国慈善与救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⑤梁晓声:《论慈善事业之当下意义》,《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 ⑥张奇林:《论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四大因素》,《经济评论》1997年第6期。 ⑦(15)周秋光、林延光:《传承与再造:中国慈善发展转型的历史与现实》,《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⑩〔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11)王巍:《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2)〔法〕莱昂·狄冀:《法律与国家》,冷静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3)Foucault.‘The Subject and Power’.In Dreyfus,H.& P.Rabinow,eds.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p.221.Foucault.Sécularité,territoire,population.,Paris,Gallimard,2004,p.91-113. (14)(16)田凯:《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7)(19)(20)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0年版,第288页。 (18)刘亚娜:《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分析——基于中美比较的借鉴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8期。 (21)刘威:《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东南学术》2010年第4期。 (22)参见〔澳〕迈克尔·A.豪格等:《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23)(24)〔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5)(26)宋辰婷、刘秀秀:《网络公益中认同的力量——以“免费午餐”为例》,《人文杂志》2014年第2期。 (27)刘威:《冲突与和解——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历史文化逻辑》,《学术论坛》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