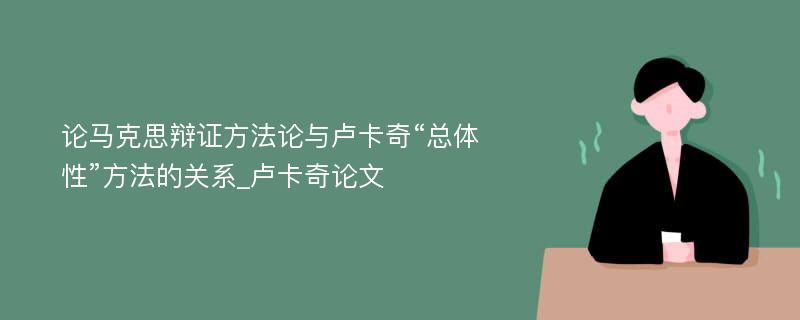
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论与卢卡奇“总体性”方法的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总体性论文,马克思论文,方法论文,卢卡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卡奇是本世纪最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与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相关性的讨论、分析,厘清在卢卡奇哲学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总体性”思想的得失。
一、辩证法与“总体性”的一般含义
与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和把列宁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根本的理论基础的论断相一致,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亦即“革命的辩证法。”(见《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8页,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而这革命的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便是“总体性”。“总体范畴”“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第76页)。
撇开卢卡奇在关于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上对恩格斯的错误指责不谈,卢卡奇对辩证法的理解,进而对总体性范畴的规定性的主要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首先,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篇文章《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标题下这个十分醒目的地方作为座右铭,这是意味深长的。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他自己的总体性方法其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就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卢卡奇将实践的范畴引入辩证法,认为“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第50页),这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次,在肯定辩证法“改变现实”的实践功能的前提下,卢卡奇认为辩证法就是“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达到对“现实的认识”(第56页),指出马克思关于“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观点,“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第57页)。据此,他强烈地谴责伯恩斯坦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步庸俗经济学家的后尘,对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作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解释,指出他们只是把这些因素“简单地拿过来,既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也不把它们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因此,在他们那里“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去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第57页)从卢卡奇对伯恩斯坦等人的批判中可以看到,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合力论”的理论一样,要求在考虑个别事实和局部领域的相互关系时,突破单线的因果关系的束缚,强调在研究每一时代、每一局部领域时都必须将它们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加以分析和研究。从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到卢卡奇对伯恩斯坦的尖锐批判,到总体性范畴的创建,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因时代的变化、工人运动的具体进展而曲折地延续、发展的历程。无可否认的是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较之一切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更加“正统”的地位。
另一个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卢卡奇与恩格斯一样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联系观和历史发展观的双重界定,亦即在将个别的社会事实、局部的“经济因素”或“经济规律”放置在“整体的社会的关系”中加以考察的同时,放置在“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把反映经济关系的“经济范畴”(如商品、货币、资本等等)理解为具体的现实、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突出了辩证法的历史分析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历史的观点内在地包融在普遍联系的观点之中,而联系的观点必然地发展为运动的、历史的观点。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沿着这一方向,辩证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联系观和历史观。强调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中,“科学想了解的一定的经济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必定变成一定的社会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第64页)阐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及物与物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的经济范畴,揭示着人与人之间非常确定的关系,它们处于相互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并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展示出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因而,在卢卡奇看来,经济现实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所控制只不过是“个别资本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偏见和无知。
概而言之,在卢卡奇对总体性范畴的一般含义的规定中,洋溢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辩证法透彻理解的闪光思想:以人的活动、实践为基础,讨论和分析社会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横断面;拨开笼罩在各门社会科学学科之上的脱离总体性而独立的神秘外衣,指明“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第62页)进而,科学的认识将在辩证法方法论的指导下结成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达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它的主观反映形式——庸俗经济学、法学等等敌视人和分裂人性(人的整体社会性)的物化(异化)性质;无产阶级意识及其实践将作为主体(同时又是客体),作为历史的中介重建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性。
二、马克思的主体本体价值论与卢卡奇对“总体性的渴望”
卢卡奇和马克思一样,将理论的批判功能和实践功能视作辩证法或总体性的生命之所在。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践功能是实现主体本体这一价值论主张的中介环节和必然途径。那么,在卢卡奇这里,总体性的理论和实践功能又是为了实现怎样的一种价值论主张呢?他的价值论主张与马克思的主体本体思想又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马克思认为,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作为主体,他不仅是物质交换过程中的设计者、能动者,而且赋予物以能动形态,使物上升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工具系统),上升为社会存在物,进而使整个自然界成为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客体对象和为人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成为价值客体,人成为价值本体。在马克思的这一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论考察中,隐含着一个理论的和实际的前提,这就是人是在社会中,进而连同整个社会才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本体的价值定位。“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也就是说,人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整体起作用的。以下的分析将表明,卢卡奇的“对总体性的渴望”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主体在价值论上的本体地位,是马克思对人所设定逻辑上的本然状态,是批判和改造现实世界的价值基点、价值尺度,因而也是人们现实生活中所企求的应然状态。同样,总体性范畴在卢卡奇那里也是逻辑上先行的批判和改变现实世界的价值标准而存在。卢卡奇依据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和分析,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一直处于主体与客体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中,也即人生活在物化的状态中;商品这一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主要结构的存在物,掩盖了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使人际关系披上了物及物与物的关系,人的关系成了物的关系;商品交换关系联同它的客观基础——分工生产和机器体系,既造成生产客体的分裂,又造成主体的分裂,“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并且“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建立了全社会的“统一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结构以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工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一部分,而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建立在私有经济计算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合理化”,使得上述对立变得更加尖锐,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统一的经济结构”变成一种”支离破碎的体系”,变成“僵死的、对抗的结构”。
卢卡奇认为这种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相分裂的状况,导致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运动采取一种纯客体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纯客体运动的形式统治着主体而不是被他们统治。他渴望克服这种物化的社会结构,渴望总体性——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意志与现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这里,卢卡奇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异化现象都根源于社会结构的思想,强调扬弃物化的社会结构,重建“总体的现实”的重要意义。依据费尔巴哈、爱尔维修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人也创造环境的启示,依据德国古典哲学寻找“行为”主体——这个行为主体作为“现实的具体总体”的创造者而存在——的传统任务,通过考察社会历史辩证的“自我运动”和无产阶级在物化的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地位及其上升为阶级的历史过程,卢卡奇最后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乃是“具体总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化身,有着“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本质”,是“创世的我们”,“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同时也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同时也就是意味着自觉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目标”(同上书,第228页),亦即实现总体性,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扬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支离破碎”和“僵死的、对抗的”性质,恢复人性的及其社会的统一性。诚如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的最后所写道的:“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
上述概略的讨论表明,卢卡奇在对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本质、物化关系对主体的压迫,及其克服物化关系的实践主体的认定等等方面,表现出与马克思价值学说的高度一致,尤其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未曾发表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然而,卢卡奇通过渴望总体性、重建总体性而表露出来的价值论思想,诚如许多批评家和卢卡奇后来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错误。这里仅限于指出卢卡奇在哪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价值论思想的轨道。首先,由于卢卡奇只看到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而忽略了社会正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关系的基础上的根本规定性,所以他没能在马克思价值学——主体本体范畴的高度上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物化的社会结构,而仅仅在认识论地范围内兜圈子:把资本主义的物及物与物的关系,仅仅解释为主体与客体、认识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等等的分裂亦即总体性的分裂来看待;其次,由于卢卡奇没有引起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价值学意义的足够重视,他的总体性范畴的价值含义就具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性质;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第三,他无法对客体的物化性质与异化性质作出区分,而这种区分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一区分中,马克思的主体范畴才能真正确立起来,才能厘清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客观根源和革命的对象、目标及边界,才能避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极左派”的虚无主义。
三、马克思的“四位一体”思想与卢卡奇的“总体”把握
马克思认为个人、活动、社会、历史四者处于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为中介的一体化联系中,是“四位一体”的关系(参见:胡承槐《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前提与辩证性》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3期)。进而,从这种一体性关系出发,整体中的任何一个子项都被看作是一体性关系中的一个具体环节,在与其他子项的关系中,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和特殊内容。显而易见,“四位一体”说是辩证法关于社会历史的具体的理论体系的展开。
卢卡奇对马克思“四位一体”理论的继承,着重表现在他关于必须在历史的联系中和社会关系中考察现实、考察“经济事实”的思想中。
卢卡奇对伯恩斯坦等机会主义者的“不偏不倚”的经验论的方法论态度深为不满。在卢卡奇看来,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而且,这一过程由于自然现象被归结为纯粹数量、数和数的关系来表现的本质而更加加强,于是就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当这种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被运用于社会科学时,卢卡奇指出这种方法的“搬运”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它仅仅只是表述了现实的“假象”,而未能揭露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因为,那些似乎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和机会主义者以“纯粹”科学态度掌握的“事实”,它们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且按其“客观结构”来说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
卢卡奇直接秉承马克思的历史分析观,认为为了能够从那些表面的假象的“事实”(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就必须了解它们本性的历史制约性,并且抛弃那种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即将假象当作本质来对待的观点,并郑重宣告:“事实”本身必定要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第55页)。历史的考察方法,其长处在于把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而归结为“总体”的有机联系,并进而达到“具体的综合”。这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唯一途径之环节之一。离开历史的考察方法来解释事实,事实仍将是抽象的、孤立的。就无法“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第61页)。卢卡奇的上述论述与马克思的思想可说完全吻合。卢卡奇“总体”把握方法论的第二个重要性是强调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考察社会现象和经济事实。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理论思想,卢卡奇在考察资本主义拜物教假象时指出,物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只有透过这层关系才能看到社会发展的真实过程。他援引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在这里,卢卡奇所特别加以强调的是以下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对经济事实、经济范畴的正确理解只有在历史的联系中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才能达到;尽管经济事实、经济关系(范畴)在全部社会生活中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它本身的存在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个部分的存在形式、具体的现实性质和意义是在社会关系整体中被得以确认的。虽然,卢卡奇的某些表述如将总体方法与经济优先性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但其总的思路是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尤其是与“四位一体”理论相一致的。特别是联系当时机会主义者“经济决定论”漫天喧嚣之时,卢卡奇敢于顶风而上,恢复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总体观”,确是十分可贵的。
马克思的“四位一体”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性批判性通向现实地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实际活动的理论桥梁。现实世界为什么是可批判的?“四位一体”理论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从它的历史暂时性以及系统结构性;从人的主体性与客体的对象性、客观性等诸方面证明社会历史依着其内在的必然规律向前发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必然地要被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所扬弃。同样,卢卡奇也赋予他的“总体”方法论以这一理论意义。卢卡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本质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分不开的、两者都是社会的同一发展过程的环节。”“对无产阶级说来……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而只有认识它自身的阶级地位才具备“行动的必要前提”,“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第71页,第70页)
卢卡奇“总体”理论的批判性,首先根植于历史的考察方法。在卢卡奇看来,当把社会事实、经济事实看作为“社会整体总过程”的一个有机的历史部分时,亦就在理论上直接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暴露了经济事实理解为“永恒”范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及机会主义应声虫的理论虚伪性。无疑这是非常正确的。
其次,在卢卡奇看来,停留在“纯粹的”经济事实、“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假象上,是不可能达到辩证认识的,是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只有透过拜物教的假象,并把它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人的实践(劳动),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经济事实的社会本质和历史性质,并进而把握历史的现实走向和认定历史主体。卢卡奇在他自己的“总体性”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无产阶级地位和历史地位的分析,认定无产阶级既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认定改造和埋葬资本主义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膀上(第70-73页)。
卢卡奇的“总体性”并不仅仅限于为社会主义运动寻找现实的物质力量,寻找历史主体,而且矛头直指伯恩斯坦等人“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这样,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也就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活动结合起来,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为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运动作了理论上的辩护和肯定。
总而言之,不管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应当肯定的是,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形式。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之无愧;卢卡奇“总体”的辩证法,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有着诸多方面的指导意义。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胡承槐的帮助,并采纳了他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表示恳切的感谢。
标签:卢卡奇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