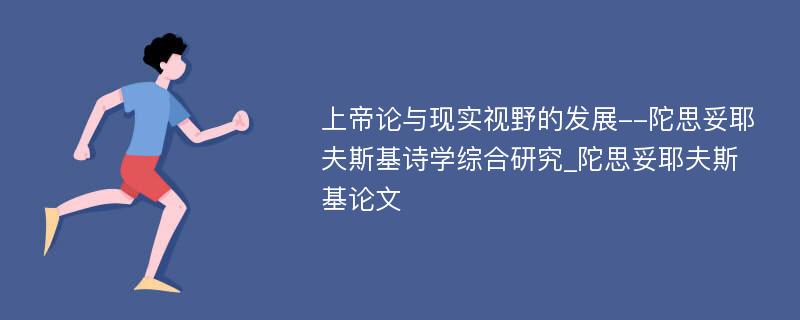
神正论与现实视野的开拓——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论论文,诗学论文,斯基论文,耶夫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恶具有的不是社会含义,而是广泛地弥散于人的心灵之中。希望的哲学对此无能为力。
——维克多·叶罗菲耶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全部作品中前所未有地广泛触及了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把他与果戈理相比,因为果戈理开了俄国自然派的先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种“自然派”的中坚力量。他因果戈理强大的批判力量而将其称为“魔鬼”:“我们曾有过魔鬼,真正的魔鬼;……他嘲笑整个生活,嘲笑自己和我们,而我们大家都跟着他笑;以至于最终我们在笑声中哭泣起来。……这是何等强大的魔鬼啊,这在欧洲是从不曾有过的,你们也未必会允许有这样的魔鬼存在。”(注:Достевский,Х.М.,Рял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суре,Введеине//Полн.собр.соч.,л.,1978,Т.18,С.59.)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师承有自,然而他在秉承自然派创作法则的同时,又声称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显然,在他与果戈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巨大的差别就在于,果戈理所展示的主要是社会之恶的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对恶的追问拓进到人的灵魂。其实别林斯基早在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篇小说《穷人》的手稿时就已断言:“这是一个开始崭露头角的天才所写的长篇小说。这位先生长得什么样,他的思想有多么广博——我还不知道,但这部小说已经揭示了俄罗斯的种种生活和性格的奥秘,而这些是在他之前任何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您想想看,在我们这里,这可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注:См.:Аненков П.В.,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ПБ., 1909,С.290.)也就是说,别林斯基并没有把《穷人》以前包括果戈理在内的作品视为“社会小说”,而所谓“社会小说”实际上也就是指真正广泛而多维地触及现实——包括心灵现实尤其是发生在心灵中的恶的现实——的作品。批评家瓦·迈科夫针对人们往往把《穷人》的作者看作果戈理的学生的说法作出更为明确的论断:“果戈理主要是一位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位心理诗人。”(注:参见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王健夫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的超越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文学理念从根本上植入了人的灵魂之中,他在人的灵魂中开辟了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天地。在这一问题上,德国人赖因哈德·劳特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声称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给予肯定,指出:“深刻的现实主义有别于‘自然派的’现实主义,它尝试能看到完整的精神现实,而不只是显露在外面的部分,即在这种现实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上的灵魂生活。同时,他在此前存在过的‘盲目’现实主义与虚构的现实描写之间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盲目’现实主义较之最不可思议的虚构更危险,因为它对现实只做局部的、简单化的描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他的基本意图则是研究灵魂的本质,揭示出它的各种能力,抓住它内在的运动并深入到它与生命、自由、上帝等事物最隐秘的关系中去”。(注:Райнхард Лаут:ΦилосоΦия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м Изложении,Перед. И.С.Андреевой,М.,1996,С.25,22—23.)正是在人的心灵的种种隐秘关系中,他遇到了一生都令他备受煎熬的恶的问题。也许,他是从果戈理那里接受了有关恶的教诲,但作为虔诚教徒的果戈理却未能或未敢在藏有神性的人的内心世界中触及这一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竭尽毕生精力,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大胆而痛苦的质询、追问和尝试性回答。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的追问久已被现代主义者所关注,他因此而与克尔凯郭尔一起被视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现代主义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发现了对存在之荒谬的最深刻描述,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加缪,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作出了极端的论断:“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人的存在是彻头彻尾的荒谬,这荒谬并不崇信永生,绝望的人因此会得出以下结论:‘……我以不容置疑的原告与被告、法官与被告的双重身份,判决这种轻率的、毫无顾忌的本性,它使我为着受难而生——我判处它和我一起灭亡。’”(注: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第124—125页。)可以说,存在主义者完全是从一个自足解读者的角度去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们的阐释与作家本人以宗教乃至东正教思想对人与世界、与上帝关系的论证分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中。韦勒克极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存在主义者只看到陀思妥耶夫斯身上那个‘地下室人’而忽视了那个有神论者、乐观主义者,那个甚至还盼望着一个黄金时代——人间天堂——到来的乌托邦空想家。”(注: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邵殿生译,见《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美国人考夫曼在《存在主义》一书中也认为:“作为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和他所创造出来的任何角色一样令人感到困惑;但我们决不可把他的地下室人物的眼界和观念都归属于他,因为他毕竟还是信仰上帝的。”(注: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5年,第4页。)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帝、 自由、罪孽、恶等问题上的观念究竟如何,更重要的是,他的诗学原则是怎样在这些观念之上建立起来的,西方人甚至俄国的宗教哲学家们也没有作出系统的解答。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置于宗教文化的语境之中来进行还原解读,已成为当今文化批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因此,本文尝试从神正论观点和东正教学说出发,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确立其“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时代正是俄国农奴制走向衰落、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的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混乱与矛盾的景象,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意识到恶的存在,都会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质询。当时的一位保守派人士在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悲惨的景象就代表了我们当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恢宏的志向,没有公正司法,没有朴实,没有相互敬重的风尚,一句话——没有任何道德力量健康、自然和蓬勃发展的证明”;“一个对俄罗斯而言是可怕的时代,我们生活于其中而看不到任何出路。”(注:См.: Бердяев Н.А.Русская Идея//О Россиии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М.,1990,С.106.)说这些话的尼基琴科曾经担任彼得堡的书刊检查官,应该说他是代表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而连他也有如此强烈的感受,足以见得时代的激忿之情。而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死刑与苦役之后,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更可想而知。但是,与事情的进展或许恰恰相反,他并没有成为想象中的革命家,多年的积愤以及在现实中的无法宣泄,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转而将思想的矛头对准了人的内在世界。或许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面对现实的无能,但不能不承认,他从表象现实的逃离为我们展示了深厚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恶。
对恶的追问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过程,从《穷人》一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穷人》被普遍认为是果戈理《外套》的承袭之作,如生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接近的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便认为:“在被大肆吹捧的《穷人》中,每一页都能让人感觉出果戈理的影响。”(注:格里戈罗维奇《文学回忆录》,鲁民译,见《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0页。)不错,《穷人》几乎在形式与内容上都留有果戈理的影子,但它无论怎样试图追摹《外套》的遗风,却无法模仿果戈理以谐谑来消解巴什马奇金悲剧命运的笔法,因为《穷人》描写了真正的善的毁灭,描写了在恶的挤迫下秉有“上帝类似”(注:“上帝类似”为东正教神学的重要概念,即人由上帝而造,具有上帝之形及与上帝类似之特性。有关论述可参见Булт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озерцания иУмозреиня,М.,1994,Отд.3,гл.1:4。)的人的痛苦。连作者本人也借题辞以自问:“唉,这些个讲故事的人啊!他们不去写点有益的、愉快的、使人高兴的东西,他们却把过去全部隐藏着的事情都挖出来了!我要禁止他们写作!”(注:《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中短篇小说选》,文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者不仅以对一个“偶合家庭”中心灵与心灵的对抗掀开了掩盖着仇恨与罪孽的虚伪外壳,而且借助于他的主人公们道出了一系列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久已回荡而未被道出的众多悖论。比如当伊万·卡拉马佐夫谈到对婴儿的屠杀时,这个崇尚人的无限自由的准哲学家却表达了对人类之恶的无奈:“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因此,他面对耐心的对话者阿辽沙,在给上帝留一点面子的前提下断然否定了上帝的造物:“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52—356页。)显然,伊万的结论是有道理的。无论我们怎样冷静地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调意义,无论我们怎样正确地理解其作品中每一个“思想者”的独立价值,我们仍然能够从伊万的声音中听到作者本人同样的激忿。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诘问呢?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神正论”(теодиея,或称“上帝正义论”)的提出与辩驳。因为迄今为止,神正论是从理性上解决恶的存在问题的最典型学说。
对恶的问题的关注首先是基于对万能之神的信仰的失落,因此,怀疑主义出现于希腊化时期便不足为奇,随着雅典统治的衰落,奥林匹克神祗逐渐不为人所信奉,围绕着神的存在与善恶问题争论渐起。怀疑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内亚德可以说最早提出了成为神正论焦点的神之善恶问题,他说:“那些积极肯定神存在的人,就不能避免陷于一种不虔敬。因为如果他们说神统御着万物,那么他们就把他当成是罪恶事物的创作者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说神只统御着某些事物或者不统御任何事物,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把神弄成是心胸狭隘的或者是软弱无能的了,而这样做便显然是一种十足的不虔敬。”(注: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第304页。 )在中世纪,当基督教学说作为一种新的话语形态确立上帝地位的时候,对神的质疑之声略有减弱,但文艺复兴之后,尤其到了17世纪,理性主义开始风靡欧洲大陆,上帝的正义问题再次为许多哲学家所关注。法国人皮埃尔·倍尔“宣称并力图证明信仰和理性不相容,理性能够揭示宗教信条中存在着的那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尤其是,在理性看来,世界上的邪恶、罪孽和祸害是与智慧的、善良的和正直的上帝形象不相容的。”(注: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104页。 )费尔巴哈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对于上帝为什么不制止罪恶这一问题,从伊壁鸠鲁直到近代唯理论者皮埃尔·倍尔,怀疑论者们的回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要么是上帝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他果真是全能的吗?要么他不愿这样做;既然如此,他还是神圣的、公正的、善的吗?或者,他既不能又不愿意这样做;那么他难道不是既无能又心怀妒忌吗?最后,他能够并且愿意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一切糟糕的事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呢?”(注:参见汉斯·昆《论基督徒》(下),杨德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5年,第618页。 )费尔巴哈在这里提到了伊壁鸠鲁,许多论者都把后者视为无神论观念的原创者之一,因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原子的组合、分解和运动的结果,与神无关,神既不参与世界的设计,也不参与世界的操控。这样一来,他便将神与世界、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分离了开来。但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最早对神的否定,不如说是最早的为神与世上之恶无关所作的辩解,或者说这为后来神正论的出现提供了榜样。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于1710年出版了他的重要哲学著作《神正论》,目的在于反驳倍尔的论断。他的基本论证是:怀疑论者与辩护论者都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上帝是万能的,或者说是完善的,因此,被造的世界一定是上帝尽其所能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已生活在逻辑上可以想象的最好的世界之中。上帝本可以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世界,但是没有了恶也就没有了相对的善。因此,他必须找到一定的品质组合才会达到创世的最佳目的。就上帝与造物的关系而言,上帝是造物主,但一般说来,他只是存在的创造者,而不是本质的创造者,不是理性真理的创造者,因此,上帝也只是物质的存在的创造者,而不是物质的本质的创造者。而就上帝与理性的关系来说,理性是最初的本质、最初的原因,因为理性表象着本质,上帝被理性所规定,而不是理性被上帝所规定。但上帝是第二个原因,因为上帝只有借助于自己意志的威力才能使理性得到实现。上帝只是执行官,理性却是立法者。造物是有局限性的存在物,这就是造物的定义,是它的特征。可是,这种局限性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它自身,因此,上帝不仅对造物的恶而言是无辜的,而且对创造的本质而言也是无辜的。造物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只能归因于它自己,即“它是它自身的原因”。(注:参见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节;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 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5—207页。)于是,莱布尼茨在此将信仰与理性达于统一,成功地解脱了人们对上帝本质的诘难。
像任何为上帝辩护的学说都会被理性哲学寻隙抨击一样,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同样不是无懈可击的。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借助持“一切向善”论的邦葛罗斯博士的形象,所嘲讽的正是莱布尼茨的“盲目乐观主义”,并且专门撰文就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一事质询上帝同无辜者受难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莱布尼茨的思想应该是熟悉的,(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的手稿中曾有阿尔卡其和丽萨及母亲谈论有关莱布尼茨的“单子”问题的对话,但定稿时被删去。编者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可以读到弗·伊·格里耶的《莱布尼茨和他的时代》(两卷本,彼得堡,1868—1871年)”,从而了解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7卷,列宁格勒,1976年,第76页注和第418页注。另可参见弗兰克《俄罗斯世界观》, 见《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1999年,第20页:“在西欧大思想家中,除纯粹的神秘主义者巴德尔和波墨外,最接近于俄罗斯思维的是谢林和莱布尼茨。虽然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风行一时,但从19世纪初到50年代在俄国思想界居主要地位的仍是谢林。而在科学—哲学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莱布尼茨,俄国哲学家曾利用他的思想一致为心理学本体论主义而斗争,反对实证主义及其无心灵的心理学。”)并且对伏尔泰在反对盲目乐观主义中表现出来的消极意识持保留态度。他虽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论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之二《××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等著述中也与伏尔泰一样嘲笑过邦葛罗斯(莱布尼茨的原型),但他同样反对对人类灾难持消极态度。他在1877年的笔记中写他晚年要做几件事,其中第一件便是“写一个俄国的老实人”,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法庭”,(注:См.:Достоевский,Х.М.,Полн.собр.Соч.,Л.,1976,Т.15,С.409—410.)对莱布尼茨与伏尔泰的立场重新作出评价。但我们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早熟”一节里少年柯利亚与阿辽沙的争论中,可以约略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柯利亚说:“不相信上帝同样可以爱人,您以为怎样?伏尔泰不信仰上帝,却爱人类,不是么?”因为他读过伏尔泰的《老实人》。然而阿辽沙很轻易地否定了少年的话:“伏尔泰是信仰上帝的,但似乎信仰得不多,不过他对人类好像也爱得不多。”(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834 页。)可见,在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的,或者可以说,莱布尼茨的思想无论如何,都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解决上帝与恶的悖论时提供了一种根据。
此外,或许谢林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俄国哲学家具有更为切近的意义,他的宗教哲学思想也对俄国知识分子在对恶的思考方面富有启发意义。较之莱布尼茨,谢林是在肯定上帝与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基础上,对恶的存在加以合理性解说。他提出,恶的根基就存在于上帝,恶产生于上帝,是上帝理念的一部分;恶是善的一种扭曲,善永远存在于恶,如健康之本永远在病痛中发生作用一样。所以,要想让恶不存在,必要条件就是上帝本身不存在。谢林较之前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恶的问题推进到了“自由”的范畴。他发现了人的双重性,并认为这种双重性取决于人是两种意志——部分的、个人的意志和整体的、类属的意志——的载体,因此人在这两种意志之间获得自由,恶就产生于当人将自我与整体割裂开来并使二者对立的时候。
从对伊壁鸠鲁学说的理解来看,对恶的问题的关注最终将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无神论,另一种是不同方式的神正论。也就是说,当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现实和人性之恶的时候,他必须做出选择,或者是否定上帝,或者是为上帝辩护。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做出明确的抉择。在情感上,他不能否定上帝;在理智上,他找不出比伊万的否定论更为有力的证据,找不到莱布尼茨式的公式。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必须为自己建立一种肯定论的神正论,以缓解自身的精神与信仰危机(他必须有信仰!);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像莱布尼茨或谢林那样超然于尖锐的现实之恶,而对自己为上帝的辩解提出种种质疑。因此,他留给我们的便是意味深长的对话:恶与自由,苦难与幸福,无辜者受难与怀疑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对上帝正义的思考来自《旧约·约伯记》,其中以利户的辩辞与约伯的皈依均是启示性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在灵魂中坚定信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想象的触动。他在1876年6 月22日致安·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写道:“我正在读《约伯记》,它将我带入病态的兴奋之中;我往往放下书,在房间里成小时地踱步,几乎要流下泪来……这是我一生中最早让我感到震撼的书之一,而那时我几乎还是个孩子!”(注:Достоевский,Х.М,Полн.Собр.Соч.,Л.,1986,Т.29,кн.ii,С.43.)然而,启示只能让他产生某种顿悟,却无法让他面对现实的诘问。因此,信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面对思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莱布尼茨的神正论中,恶是来自上帝的一种世界始基,上帝造恶是为了以恶来彰显善,使善有可对抗的对象,从而使人享受到善战胜恶的幸福与快乐。而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而言,他是否回避了这一论点,这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宗教哲学家洛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否定了那些认为恶是善的必要条件的伪学说。例如存在这样的论点,仿佛恶是整体和谐的必要瞬间,如同对一部音乐作品之美来说不协和音也许是必要的一样。他不同意恶作为认识善的条件必不可少的说法。”(注:Лосский Н.О.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Его Χристианско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Вог и Мировое Зло,М.,1994,С.110.)洛斯基举了伊万与阿辽沙那段著名的对话来说明他的观点,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似乎极少在争辩双方达成统一的对话中,这段对话应该是最能代表作者本人的声音了:
“请你回答:假设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请你坦白说,不要说谎!”
“不,我不能答应。”阿辽沙轻声说。
“同时你能不能那样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筑的那些人会同意在一个受残害的小孩的无辜的血上享受自己的幸福么,而且即使同意了,又能感到永远幸福么?”
“不,我不能那样想,哥哥。”(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洛斯基的看法是,既然双方都认为善不能建立在恶之上,则恶并不是上帝的选择。而在笔者看来,这段对话里显然存在着对上帝的质疑,因为正是他建造了人类命运的大厦,这应该是无可辩驳的前提,那么也就是说,正是上帝答应了伊万的征询,阿辽沙所不能答应的,上帝答应了。如这样推论的话,则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面临着走向反神正论的立场。他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是一个将信仰植根于灵魂之中的虔诚信徒所无法面对的。当然,《约伯记》中的上帝正义论是启示性的,无法压倒怀疑论的力量。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试图从两个方面来修正自设的悖论,并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神正论。这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特色的神正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基督“虚己”(кенозис)的意义,二是将恶归罪于人对自由的滥用。
较之天主教,“虚己”这一概念在正教神学中尤为重要,它指上帝通过道成肉身虚其神性,并以受难的方式警醒和拯救世人。(注:一般认为对“虚己”这一概念最早的神学解释者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据《正教神学百科大辞典》(莫斯科,1992年。Полный Православский Ботословский з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в,М.,1992 )“虚己”条:“希腊语词。意为上帝俯就于人。虚己说是对上帝的实际二性的研究;据此,作为上帝的基督承受苦难和死亡以示对人类之爱。在这一行为中道出了神子自我贬抑的思想。道成肉身的完成意在表明,人作为守信者将经过地上的痛苦而在上帝的彼岸世界获得永恒的荣耀。”)正教神学家谢·布尔加科夫在谈到这一概念时说:“世界的创造根本说来是上帝之爱的自我牺牲行为,是上帝有意的自我损耗或自我降低,是他的‘虚己’,这种行为只能在他自身、在做出牺牲的爱的欣悦中找到证明。但这种创世中始终存在的上帝普遍‘虚己’永远包括一种具体的虚己——神子的肉身化与他的受难。”(注:Бултаков,С., СветНевечерний,Созерцания и Умозрения,М.,1994,С.289.)在布尔加科夫看来,上帝在创造人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类似体,这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虚己,即在上帝赋予人神性的同时,也体现了上帝对人的体认;而基督受难则意味着对人罪孽的承担和对人如何运用自由的启示,其意义等同于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神正论中接受了这一思想,通过对基督虚己的认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上帝作了辩护,因为在人的上帝形象渐趋暗淡的时候,是化为肉身的上帝分担了被罪孽败坏的世界和人的命运,以十字架上的受难标示本质受损的世界的新生和上帝的终结性创造行为。
但是,“虚己”论并没有解决恶的来源问题,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自由”。在“自由”问题上,俄罗斯正教神学发展了谢林的观点,这种“自由”论的基本构架是:上帝在创世时安置了所有生命的力量和种子,同时也赋予人以继续创造的自由,此时,世界只是在人身上被预先创造,人还必须以上帝所给的自由最终完成创造的总体计划。或者可以说,世界在理论上存在着两种形态:必然形态和偶然形态。上帝以其理性设置了世界的必然形态,然而世界的实际存在却是偶然的,因为上帝把自由交给了人类,人是否能够实现上帝的必然性却是一个未知数。只不过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道德或法则的必然性,人如果能够遵循这种道德的必然性,则整个世界的完成将是善的,否则便是恶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回到了人自身:人作为受造物而秉有自由,也就同时成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动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也曾写过:“基督教使人负责,以此承认人的自由。”但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重视人的自由,甚至别尔加耶夫认为他是人类自由的辩护士,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人在使用其自由时却往往是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自由使人带有神性,但并不是使人成为“超人”或神化,人必须遵循世界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法则,或者说,人获得自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世界的创造,因此,这种自由从根本上说是附带条件的,不是绝对的,在此限度之内的自由是善的,而跨越了这一限度,自由便产生恶。正如别尔加耶夫所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关于自由的论题是和关于恶与罪的论题紧密相关的。没有自由,恶便无法说清。恶出现于自由之路。……自由之路转向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导向恶,恶导致罪。罪的问题占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中心位置。”(注:Бердяев,Н.А., Миросозерцани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рага,1923,С.88—89.)
然而,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核心是“罪”,不如说是“罚”。罚并不等同于佛学观念中的因果报应,它在正教观念中所指的更多是觉悟后的痛苦。这种罚体现着善的绝对,因而它便成为对自由的制约,使人的自由意志服务于世界的必然意志。用莱布尼茨的话说:“罪孽以一种先定和谐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引起惩罚,而这种惩罚又始终是以善为目的。”(注: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第266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恶也就是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循环:至善→自由→恶→罪→罚(痛苦)→善。最典型的例证便是佐西马长老所讲的故事中那个神秘的造访客,他杀死了拒绝他求婚的女子,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但是精神的惩罚却使他无法安宁,他的一生都在痛苦的梦魇中度过,直到最终当众宣布了自己的罪行,临死时说:“我知道我就要死了,但是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感到了快乐和平静。我刚刚履行了应做的事,心灵里就立刻出现了天堂。”(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66页。 )洛斯基在体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时说:“说到恶,它任何时候也不是绝对的:它一直要么自身包含着善的一面,要么至少会导致有助于善的因素出现。甚至死亡也只是相对的恶,如果考虑到死消灭的仅是作为存在物不完善的一面,并且打开了通向新的、更加高尚的生活的道路。……痛苦是人所应得的惩罚,这种罚将人的灵魂引向炼狱。”(注:ЛосскийН.О.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го Χристианско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Вог и Мировое Зло,М.,1994,С.113.)炼狱则是通向天堂的必由之路,所以,苦难就是使人走向幸福的必经之路。像伊万的梦魇对他说的:“痛苦也就是生活。没有痛苦,生活里还有什么愉快;那就会完全变成没完没了的祈祷仪式,这固然神圣,但未免有点无聊。”(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972 页。)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罪恶的现世也就不必进行没完没了的质询了。佐西马长老的哥哥在临死前说道:“妈妈,你不要哭,生活就是天堂,我们大家都活在天堂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知道这个,如果愿意知道,那么明天全世界就都会成为天堂了。”(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432页。 )这也许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要说的话,因为他的神正论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
然而,他的神正论仍不是万能的,换句话说,他的思考比起哲学家来更为深刻而残酷。正如洛斯基所说的:“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从哲学角度论证神正论。在他那里许多问题终其一生也未解决。特别令他痛苦的是儿童受难的问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柳比莫夫的信(1879年5月10日)中可以看出, 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凡人的智慧可以解决:‘我的这位主人公选择的问题依我看是无可辩驳的:孩子们受罪是荒谬的,从而得出整个历史现实是荒诞的结论。’”(注:Лосский Н. О.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го Χристианско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Вог и МировоеЗло,М.,1994,С.119.)他的神正论在这一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打击,因为其神正论的方法论基础是从自由概念推导而来的,而自由必然涉及到选择,婴儿固然已被赋予自由,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选择,也就无所谓对善恶的认同。他们无辜地成为恶所施暴的对象,是否只是为了给恶的出现提供一个条件呢?但这仍然不符合神正论的辩证法,因为根据这种辩证法,与恶相关的种种因素都是可以向善转化的,然而儿童受难却只意味着牺牲。赖因哈德·劳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重视孩子们的苦难,这种痛苦始终如身受般令他战栗,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受折磨,被弄死,他们毫无理由地受罪,根本谈不上他们因有什么罪孽而受苦。有人试图指明,他们是为父母的罪孽而受苦,这样为这种苦难作解释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任何一个讲求道德和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无辜者应为罪人受苦。”(注:赖因哈德·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沈真等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96 —197页。)也就是说,正如伊万提出而被阿辽沙认同的那样, 谁也不能答应可以在孩子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人类命运的大厦”。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将他的神正论推进到底,留下了无法解决的悖论,但也正是这种无法解答的问题的提出,将人们对世界与人的思考推进到了更深的领域。
如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不是因为他对上帝的追问与辩护,而是因为他的艺术表现的力量。有人提出,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寄托在如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这样的人身上,但伊万·卡拉马佐夫对上帝的指责比佐西马和阿辽沙为上帝的辩护更为有力。针对这种观点,洛斯基指出:“他们不明白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给出的答案不是在理性的论题中,而是在‘艺术的画面’中。”(注: Лосский Н.О.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Его Χристианское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е//Вог и МировоеЗло,М.,1994,С.120.)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表现的力量又与其隐秘的宗教情愫和哲理思考密切相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力量的表现之一,即所谓“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拓与探索,对人物的悖谬性生存的描绘,早已被许多批评家所发现并肯定,但他们在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功绩的原因时,往往把目光集中于社会与历史的因素。苏联时期的批评家们固然避讳谈论有关宗教的话题,而那些西方的学者甚至俄国的宗教哲学家也很少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与其宗教思想的关系。巴赫金曾经高度评价维·伊万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观察世界方式的论证,但同时也指出:“伊万诺夫没能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待世界的这一原则,如何变成了对世界进行艺术观察的原则,构筑小说的语言整体的原则。应该说上述的原则只有作为具体地构筑文学作品的原则,而不是作为抽象的世界观中的宗教伦理原则,对文学艺术家才有重要意义。而且只有如此,上述的原则才有可能通过具体文学作品的经验材料,得到客观的揭示。”(注: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第34—35页。)巴赫金的话启发我们提出如下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像普希金那样将现实之恶加以过滤,而是在果戈理展现社会之恶的基础上揭示人的灵魂之恶,从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维艺术世界,其原因不仅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已进入了俄国历史上新的时期,更重要的是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基于信仰立场所进行的种种悖谬性思考及其最终的个性化神正论选择。这种个性化的神正论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是对存在的一切给予“合理化”认定,从而使艺术中的现实视野摆脱了古典时代的诸多束缚,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主体所观照的意象,给他的艺术世界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展示空间和更为复杂的表现内容,由此形成他自称的“更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并且具体体现在对人的终极性自由追求、选择与滥用、人在罪孽之途上灵魂中的痛苦与苦难的揭示与辩证体认,以及展现现实悖谬、世界对应因素的互动等方面。
为了充分显示恶的力量即人类在自由之路上的迷途之远,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对苦难的极大的耐心与兴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称为“残酷的天才”、“恶毒的天才”。高尔基的观点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但他是我们的恶毒的天才。他非常深刻地感觉了、理解了、并且津津有味地描写了被丑恶的历史、艰苦而屈辱的生活所培养起来的俄国人身上的两种病症:彻底绝望的虚无主义者的残酷的淫虐狂,以及——和这相反——被压溃的、被吓坏的、能够欣赏自己的苦难、幸灾乐祸地在大家面前和自己面前津津乐道这种苦难的一种人的被虐待狂。即使被无情地打倒了,却仍以此为荣。”(注:高尔基《论“卡拉马佐夫气质”》,满涛译,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然而,我们看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是从其独特的神正论观念出发来描写苦难的,苦难是通向幸福的必经之路。像佐西马长老的哥哥临死前所说的,“我们大家在所有人和所有事件中都是有罪的”,因此,所有人都应当受难,满怀希望地接受苦难,以体验耶稣受难为我们带来的新生的欣悦和快乐,以使恶最终转化为善。这一思想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的艺术态度以及对苦难描写的热衷。在这一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的认识可以说是颇为深刻的,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化现实为快乐。他往往把他的笔浸在污泥潭里,甚至从这污泥中得到快乐。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以为污泥是好的。不,人生的污泥使他痛苦。他常常反复地想:受苦具有赎罪的意义。他认为人人都应该受苦,因为人人都要对每一个孽障、每一项罪行负责。犯罪是普遍的现象,刑罚应该加于所有的人。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而它是同他的艺术风格密不可分的。”(注:卢那察尔斯基《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蒋路译,见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15、21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是多维的、多声部对话的,造成这一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作家的神正论思考。既然在神正论的世界中恶与善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那么这个世界便成为互动的、对话的、狂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恶与善、上与下、死亡与复活、高尚与卑劣、高贵与低贱等,虽然都具有自身的品格,保持着独立的姿态,保留着自己的声音,但是,它们并不分处于不同的层面,并不是孤立、绝对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在普希金时代所习惯看到的那种带有古典主义影响的“和谐化”状态,而是一种新的呈不和谐状态的“和谐”。上帝给了这个世界里所有人以自由,使他们自由地创造世界,自由地造善与造恶,并因此而享受善的欣悦,承受着恶带来的罚的痛苦。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伊万与阿辽沙、宗教大法官与耶稣、梅什金与罗果任等,代表着不同品格的人处在同一种语境中,进行着善与恶、必然与偶然、地狱与天堂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将所有观念的主体平等地呈出现来,而不对他们作出评判,从而以复调的形式展现出多元的世界。从伦理上来说,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契合于“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ъ)的。(注:соборностъ指有共同聚合于上帝身边的特性,亦可译为“凝聚性”、“集合性”,其理解近于“宗教性”。有关聚合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笔者将在另文中阐述。)
巴赫金也曾试图把狂欢化理论中的“上升”与“下移”运动、低贱者的加冕和高贵者的脱冕等概念更深入地应用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分析,可惜他似乎在复调与对话分析之外没有来得及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在他留下的笔记中已可以有所领悟,如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类型(体裁类型)的历史》中写道:“大罪人的神圣性(上层与下层的结合,脸和臀的结合,翻筋头,小鬼作为伊万的反面,同貌者)。斯梅尔佳科夫形象的狂欢节基础:在醉酒的(狂欢节的)夜里,破戒者同装疯者(教徒)的交媾,老爷同最下贱女人(最低的下层,连个子都是小的)的交媾;澡房(湿淋淋的)里的降生,私生子,厨子(重要的传统),肉汤和肉馅,弑父,癫痫病,掉进地窖,伊万的相似者,最卑下的虚无主义(否定任何理想性),狂欢节(农神节)上的‘一切都可允许’,奴隶(仆人)想同老爷对换位置(同合法子女,同兄弟);把奴隶扮的皇帝吊起(钉上十字架);狂欢节上的秘密(谁杀死的?),替代牺牲(无罪者抵偿杀人罪);降生与死亡(母亲与阿辽沙,莉扎维塔·斯梅尔佳莎娅临产死亡);斯梅尔佳莎娅形象的两重性,发臭的圣洁性,发臭的死亡与复活。”(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类型(体裁类型)的历史》,白春仁译,见《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0页。)这里所勾勒出的是一个恶的世界,但在这种恶里孵育着新生,因为在对话与狂欢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动态的、变化的。巴赫金所列举的正是种种对立与互动的关系。从最下贱的交媾中诞生出无罪的婴儿,从婴儿变为成年人,成年人又滥用他所获得的自由,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恶产生了,而当他走向死亡的时候,他获得了最终的灵魂的复活。叶萨乌洛夫在分析斯麦尔佳科夫这一形象时说:“在最令人厌憎的和最受人推崇的人——斯麦尔佳科夫和佐西马长老——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蔽的类似,尽管是通过‘腐臭’的中介。佐西马的肉体在其死后意外地发出腐臭,正如斯麦尔佳科夫的灵魂在生活中发出腐臭一样。”(注:Есаулов,И А.,Категория Собор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1995,С.126.)但在笔者看来, 这二人的隐蔽类似应该是体现在佐西马长老生前的高尚与斯麦尔佳科夫死时的灵魂升华,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神正论与人正论宽容性的本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