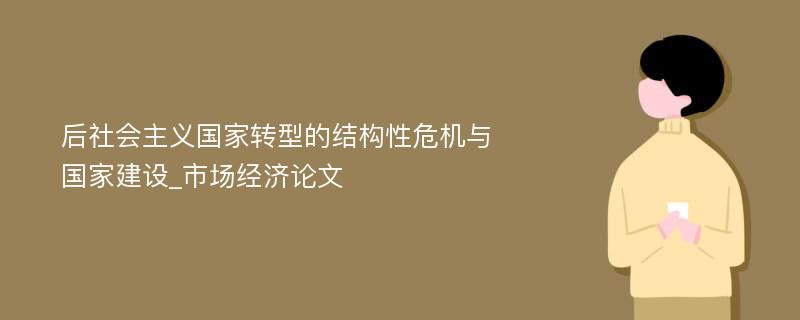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与国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危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3-0035-07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东欧剧变后,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市场化经济转型与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双重大变革。在经济转型方面,这些国家实行自由定价机制,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鼓励民间私有部门的发展,重新设计适应私营经济的税收制度,创造新的金融部门,改革外汇制度、实施浮动汇率,推行财政预算和货币的双重紧缩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建立产权制度等。在政治转型方面,这些国家创制宪政,改革议会,建立法治,寻求三权分立,推行多党制,实行普选,扩大和保护公民权,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以及信仰自由,鼓励公民社会发展,消除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严密控制等。从理论预设而言,市场化经济转型和民主化政治转型将实现增长与民主的双重目标。然而,许多国家的实际结果显示,转型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与民主,反而使这些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结构性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历程及其后果,吸引了诸多学科学者的广泛检讨与反思,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经济学家引发的激进主义者与渐进主义者围绕经济转型路径的持续争论。也有一些论者致力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比较案例研究,试图通过描述经济转型历程,检讨如私有化、财政政策改革等方面的得失,从而全面了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实践。与经济学家关注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路径、历程与绩效不同,政治学家起初较为关注苏东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以及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历史根源,尔后则较多关注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历程与后果。随着对民主化研究的深入,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成为新的理论热点。而伴随着后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性危机的加剧,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深入剖析转型进程及其危机以探讨解救之道。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日益被视为危机的真正根源,由此,不少学者强调转型进程中国家能力与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后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发生,既有经济转型战略和改革措施选择失当的原因.也有民主化与市场化相互干扰、制约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能在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因其较多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对国家角色、国家能力、国家制度建设或国家建构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来重新思考国家的作用。文章从考察经济转型中的国家作用出发,通过考察转型国家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作用,试图回答市场化、民主化与国家建构之间可能的顺序问题。我们相信,这样的工作对于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我国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经济转型中的国家作用
围绕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对两种转型路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作出一个恰当评价并非易事,因为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转型战略,与各国的历史条件和机遇有关。基于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不同,转型国家往往缺乏作出不同选择的余地。因此,抽象讨论激进式与渐进式转型路径孰优孰劣,并不能为我们反思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更多的东西。相比之下,有的学者基于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激活了关于经济转型与国家作用的新思考,反而值得重视。
博戈莫洛夫和格林基娜从俄罗斯与匈牙利的比较中发现,后者的成功正因为“不惧怕保存必要的国家监督……国家在拯救经济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做法保证了经济过程的可控性,避免了经济和权力大规模刑事犯罪化(像俄罗斯这样),明显地缓解了改革的社会后果”[1]。波兹南斯基指出,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造成的经济衰退、生产下降始终得不到制止,根源就在于国家的过度退出、缺乏有效的国家机构[2](P3)。王绍光则引用科尔奈1990年的警告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3]
确实,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激进式与渐进式转型路径都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律化的市场制度,以法治作为支柱。事实上,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这是争论双方(无论休克疗法还是渐进主义)一致的认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建立起能规范市场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比如在产权和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有效立法。但许多转型国家往往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规范市场的法律制度。在俄罗斯,由于缺乏能够维护市场公平原则、保障公民财产权、规范市场经济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及俄罗斯司法机关自身的腐败,导致俄罗斯形成了畸形的市场经济。而且,市场经济所需的“特定制度不能由个体的经济活动者来创造或增强”,它们需要国家主动和积极地承担责任。以此观之,“俄罗斯国家很少把资源放在发展一种能够维护投资者或产权拥有者利益的法律制度……(而且)一些市场支持制度,如银行、商品交换甚至股票市场,却是自发出现的。但没有一个能够规制这些制度的国家,制度之芽就很难培育成长”[4](P237)。这可以看做是经济转型失败的根本教训。
同时,经济转型的成功,不但需要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也需要国家对市场经济发挥积极的干预角色,“市场只有在公共机构强有力的干预作用下运作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说在原苏联和东欧往往存在一个越位的国家,那么在转型时期,这些国家中得到支持的经济政策往往“建立在大大弱化国家作用的基础上”[5](P322-323)。
由此,许多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应该首先强调在急剧的市场变迁中坚持行政精英的权力,强调国家是重建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强调控制市场改革的进程、控制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控制社会转型的步伐,尤其是在市场改革初期阶段[6](P401-435)。与俄罗斯缺乏国家规制市场的教训相印证,同样实行激进改革的捷克却取得了成功,其成功经验正表明了国家不应当从经济转型中退出。比如,由国家银行主导的私有化对市场经济转型起了很大作用。捷克政府采取“两手抓”来实施其私有化计划,一手是政府通过发行600万债券而直接为60%的企业私有化提供资金,另一手是在国家指导下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在私人缺乏充足资本的情况下,允许向银行借贷来购买。在这两手中,国家银行部门都起到了主导和监督作用[7](P161-177)。同样地,在波兰“从没有疗法的休克到没有休克的疗法”的战略转变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波兰逐渐发展出强大而有效的政府决策能力和国家规制能力。1989-1991年间波兰实行“休克疗法”,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引发人民的普遍不满,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新生的市场经济乃至新政权岌岌可危。为挽救局面,波兰政府于1992年果断结束“休克疗法”,推行新的“波兰战略”,加强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法制监督,改革国家的税收和金融制度,增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增加政府财政支出、重新实施政府预算赤字等。而正是实行了坚决的稳定性措施,制定了合理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有效而彻底地改进了政府对私营和国营企业的管理,波兰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
可以看到,政府对市场的放任自流、缺乏有效的国家机构以及国家决策能力、战略能力和制度能力的低下,是导致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对此,福山指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家建构”,“国家构建这个议事日程……几乎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思考或者重视,结果造成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在许多国家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确实,某些国家由于缺乏合适的制度框架,实行经济自由化后的状况比如果不实行更为糟糕”[9](P5)。一个自主而有效的国家是推行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三、民主化与市场化:相互促进抑或相互颉颃?
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陷入结构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其不适时的民主化。在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同时,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动了民主化政治转型。这既出于新掌权的民主派巩固权力、“避免回到旧政体”的现实政治需要,也出于他们对民主的乐观信念: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互为条件,市场化转型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给民主制度赢得合法性,而民主制度则会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民主派的信念,而且,“转型国家的民众常常带有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坚持和支持民主原则与民主制度,就能自动地享受发达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各种好处”[10](P214)。
但是,在不少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结果却正相反,既没有获得经济增长又没有实现民主的巩固和发展。许多学者认为,民主化与市场化同时推行是导致经济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经济的恶化又反过来威胁新生的民主制度。
民主需要相当的经济富足为物质条件。亨廷顿指出:“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11](P70)从转型国家的现实国情来讲,它们大多数都不具备马上实现向民主过渡的经济条件。而且,实行民主还必须满足法律的、智力的、心理的、防卫的条件[12](P105)。转型国家通常也不具备相应的法制和心理条件。就前者而言,民主派一方面几乎完全废除了旧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新的法制又不能一时间铸就。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对法律制度的作用重视不够”[13],没有积极地承担起创制法律的责任。就后者而言,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遗产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公民的民主文化匮乏,而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却分野清晰。这种遗产导致公民身份与政治阶级身份截然区分与对立,“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常常非常激烈,造成“民主的僵局”[14](P156-170)。不仅如此,转型国家还明显缺乏支撑民主的基本社会结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基础,“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新的,而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十分虚弱”[15](P75)。
草率匆忙的民主化引发了“不良民主之痛”。在转型国家,政党林立,甚至在一夜之间就冒出成百上千、形形色色的政党。由于民主化是政治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而激进转型产生了大量利益冲突的集团,各种政治派别常常利用国家机构和公共资源来寻求政党的特殊利益,由此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造成国家政权的频繁更替以及政策的不连贯性,严重的甚至引发内战、叛乱、割据、种族屠杀等——这些对经济增长和民主发展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实际上,亨廷顿在1968年关于民主化与政治秩序的一部著作中就曾指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是不能相容的。”[16](P392)
民主化政治转型的状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进程。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冲突,常常使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服从于政治目的或巩固当权派权力的需要,经济问题往往演变为政治问题。比如,在俄罗斯激进改革之初,由于新生的民主宪政未能理顺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职能,两大权力机关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转型理念的不同更激化了对抗,议会主张渐进改革、反对休克疗法,不支持总统及其政府的经济改革,并且试图通过议会来限制总统权力从而推行自身的转型理念和战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支持盖达尔,维持‘休克疗法’是出于巩固政权,防止改革进程逆转,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宪法秩序的需要,至于执行这一政策的经济效果在其考虑中则已处于次要地位了”[17](P88)。而不计效果的经济决策导致了政府经济改革的失败,民众越来越不信任民主派。而民众强烈的政治反应也使左翼政党重返政治舞台,但“左”派也“往往局限于利益集团层次的政治追求而缺乏对全局形势的宏观宗旨”[18],他们急于掌握国家政权而不是与右派达成妥协以便能够稳定政局、寻求经济发展。政治冲突与权力斗争日渐激烈,政府更替频繁。进一步的经济转型或改革也因之更加举步维艰,或因政府频繁更替而导致经济改革政策的不连贯,或当政府出台重要的经济政策,就成为反对派借以出击的箭靶,政府与议会争论不休,要么新政策得不到议会的认同和支持,要么使政府错失实施新政的良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勒德克警告说:“民主不会自动地保证一定会产生明智的政策。”[19](P282)
作为结果,民主政治本身也遭遇了合法性危机。一方面,经济的持续衰退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由此引发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普遍不满。因为,“要唤起民众服从与参与,民主必须产生实质性结果”[20](P19)。民众越来越不关心、不参与民主选举。比如,1991年波兰议会选举时,投票率下降到了43.2%,1993年也才得到了52%的选民的选票。另一方面,由于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和党派冲突侵蚀了大部分民众对冲突与不稳定的承受力,他们难以承受“民主的僵局”甚至民主本身。据调查,在1994年有78%的俄罗斯人表示不支持任何党派。
严重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在俄罗斯,社会开始失序,“普遍的犯罪化”成为“俄罗斯现象”的重要特征。在其他一些转型国家,危机严重到爆发“颜色革命”,如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从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来看,往往是政治变化、政治因素较之经济本身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许多论者认为,问题不在于民主化与市场化的目标不可欲求,而在于市场化与民主化的推行有先后顺序,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与民主化改革同时进行,不但不能收到相互促进之效,反而会相互颉颃、相互羁绊。对此,卡瑟琳·丹克斯不无讽刺地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需要民主,它需要的是市场和稳定。民主未必有益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一个提高了期望值而生活水平又正在下降的时期,更是如此。”[21](P1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必定对市场化产生负面作用,市场化也可能因民主化的深入推进而得到解决。在转型初期,因政体重组、权力洗牌,党派竞夺资源不可避免。然而,民主化不等于党派政治,民主的实质在于公众广泛参政议政。广泛的公众参与,可以制衡党派过度竞争,决定转型进度及其战略。在转型国家,民主的动力因党派竞争过度激烈且公众参与相对匮乏而最终耗竭并畸形化,从而抑制着市场化转型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民主化与市场化相颉颃的怪圈,并不是废止民主化,而是深入推进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目标的民主化。瓦莱丽·邦斯通过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深入推进民主化的国家往往能够很快从转型初期的经济挫败中复苏,市场化经济转型最彻底也最成功,而民主化程度偏低的国家则刚好相反。
四、“民主顺序”与国家建构
随着后社会主义国家结构性危机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强调国家建构的重要性。他们并不否认市场化与民主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但认为要实现这两大目标就必须率先进行国家建构——“政府首先要寻求秩序,继而是经济发展,最后才是民主”[22](P11)。这种主张常常被称之为“民主顺序说”。实际上,亨廷顿、李普塞特等主张在实现中等富裕水平之后才开始推动民主化,这一观点本身就包含了“民主顺序说”的基本内容,只不过他们假设事先存在着一个基本完成了国家建构的国家。
“民主顺序说”是一些论者基于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提出的。在这些论者看来,非洲的失败经验表明,国家建构是一个首要问题。不首先巩固政权,就难以巩固民主和实现经济增长,甚至最初步的现代工业化①。与此同时,他们肯定了东亚“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成功经验。马克·拉维纳指出,国家建构首先指建立一个政治秩序。二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并没被完全废除权威政体,宪政建构也没有依据美国模式,存在着长期的一党执政(自民党),这些都有利于政治秩序的巩固,这样的权威政体很快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复苏,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民主转型②。基于上述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民主顺序说得以提出。马尔库斯·考克斯指出,宪政鼓励所有政党政治参与,而这可能为创建一个有能力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行使职能的国家制造障碍。在社会冲突严重的波黑,民主宪政转型不但激化了社会冲突,导致政局动荡并严重削弱了国家,而且刺激了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这导致国家既不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又不能巩固公共权威,反过来更不利于最终的民主宪政目标。因此,国家建构要优先于经济增长和民主宪政建构③。
国家建构是指在既定领土疆域内创造出一个处于中央政府统治权威下的主权民族国家,建立起国家对暴力和强制权的合法垄断,以及国家在诸如维护领土主权、公共行政管理、税收管理、社会控制、宏观经济管理、保护公民权、创建法制、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的制度、组织和机构建设,以强化民族国家的政权强度和提高相关职能范围的国家能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它们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通过国家建构提高和增强国家的强制能力,恢复政治秩序,重建国家权威,从而为寻求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权基础。
就经济增长而言,通过国家建构建立起一个强国家是前提。因为“即使是缩小公共所有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目标(私有化、市场化),强大的国家(依据能力)也比弱小的国家执行得更有效”[23](P13)。国家的自主性是强国家的首要特征,也是保证国家能力的关键前提。只有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性,尤其是政策自主性,国家才能够在与社会活动者的博弈中保持国家功能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由于国家缺乏自主性,很多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演变成“俘获型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常常服从于经济寡头的利益。如赫尔曼和考夫曼所指出的:“转轨国家有一个最突出特点,那就是所谓经济寡头在制定政策,甚至是为自己制定游戏新规则时所发挥的作用,它们在这方面享有巨大优势。我们称这种行为为‘政府俘获’。”[24](P49)
就民主建设而言,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确立起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就草率推动民主化政治转型,这是不合时宜的,它反过来又影响到民主政治的稳固和完善。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许多国家,最后都重新遭遇了国家建构问题。有的学者在考察了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结构性危机后甚至指出,脆弱的民主化国家比巩固的独裁政府更容易引发冲突。
可见,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推进市场化、民主化转型的前提不是削弱国家,而是开展国家建构,建立一个强国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建构一俟完成,就必定能够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这固然是因为强国家需要有效地推动现代化建设,培育市场经济,从而达到民主所需的经济水平,也因为民主与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一般来说,就民主对国家建构而言,民主可能会使国家分裂,虚弱的国家可能会加剧这种分裂。而且,国家首先要能够代表和执行公共意志,但民主往往难以形成一致的共识。就国家建构对民主而言,只有国家才能推动民主建构。但这首先要求国家完成了强制权的垄断,但对强制权的垄断过程常常会形成国家官僚的特殊利益,这反过来会遏制民主。民主与国家建构之间的这种紧张使得很多国家陷入困境,强调民主往往导致丧失和平,强调国家建构往往导致丧失民主。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权威主义政体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例子。这些国家在战后成功完成了基本的国家建构,建立起一个权威主义政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除个别国家(如日本)外,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却历尽坎坷。卡罗瑟斯指出,如果国家建构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建设一个民主国家。显然,权威政体在第一阶段能够鼎定乾坤,却很不适合于第二阶段的任务④。而且,强大的权威政体也逐渐会成为进一步获得经济增长和推动民主建设的主要障碍,民主制度的缺位“为官僚的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滋生空间……一个行政权力不受民主监控的体制蕴含着各种危险”[10](P222)。
由于,我们既不能线性地理解国家建构、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将国家建构与民主对立起来。从历史上看,在欧美一些先发国家,国家建构与民主宪政建构经历了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战后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正在于“消除贫困的斗争一直与国家机构的建设并行不悖,同时致力于经济的增长和民主政治建设”[25](P12)。相比较而言,在一些后发国家,国家建构与民主宪政建构之间常常表现出较为严重的不均衡性。但这并不是说,后发国家不可能实现两者的均衡。按“民主顺序说”倡导者卡罗瑟斯的说法,民主正是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目标。如前所述,国家缺乏政策自主性、被经济寡头所俘获,常常使政府的改革政策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导致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常限于寡头所希望维持的局部改革,并且大部分改革成果为寡头所掠夺。而通过国家建构,国家因重获自主性而摆脱了“政府俘获”,但它又存在演变为“勾结型政府”的风险。要成功控制特殊利益集团,抑制“政商勾结”,避免国家自身也演变为垄断利益集团,从而保障改革成果为大部分公众所享有,就必须扩大参政和议政的公开度,扩大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提高公共决策的透明度,让公众监督政府与国家公共资源的分配(赖洪毅:《如何制约特殊利益集团——中国可借鉴东欧模式》,载《联合早报》2008年3月26日)。在这里,继续深入推进民主化依然是保证经济社会转型最终成功所必需的政治支撑。就民主建设而言,我们还应“淡化经济决定论的迷思”,印度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启动民主并获得稳步发展,其成功经验有力地表明在经济水平与民主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机械的联系。而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业已成为转型国家所有严重问题的根源,则突出了国家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同样以俄罗斯为例。自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俄罗斯开始致力于“国家主义”的国家建构,提出并实践“可控民主”,改革政党制度,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打击经济寡头,镇压车臣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同时,大力加强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规制,提出“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税制,整顿银行部门,重新推动由国家主导的私有化等。这些措施,使俄罗斯在经历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颓败的十年之后,重新走上了强国复兴之路。当然,不少民主派人士对于普京的国家建构之于民主宪政的影响忧心忡忡。这也表明,民主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俄罗斯需要认真面对的现实挑战。
五、结论与启示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程,为我们在新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国家角色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对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我们要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抽象对立。市场经济长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矛盾,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风险,“全能市场”与“全能政府”之间的选择既不可能也不可行。现实地认识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角色,要求我们不是简单移植“更多市场,更少国家”之类口号,而是需要在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匡正市场失灵的功能。对于转型国家而言,由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具有不稳固性、幼稚性,因此,不但需要国家充当市场经济的培育者、助产者、规制者,也需要国家发挥比发达国家更多的积极角色。
一个国家的转型,既是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也是政治结构与国家制度的重构。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市场化经济转型与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同时,不能忽视国家制度的建构或重构。在一个缺位、弱化或无能的国家中,既不能获致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不能实现民主的巩固与发展。现代社会正变得日益复杂,国家要积极承担起管理系统之间、组织之间、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重任,只有在国家有效的策略协调与干预下,才能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一致与共同演化。一个自主的、有效的国家是必需的。国家建构既是制度转型的必要前提,也是制度转型的目标之一。转型国家的国家建构,其目的既不能是构建一个大而全的国家,也不能是形成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而是要结合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在适当的国家职能范围内提高国家能力,同时为民主宪政建设开放空间。
在转型国家,特殊利益集团掌控经济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垄断利益集团既是实现成功转型的桎梏,又是阻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樊篱。若国家成为最大的垄断利益集团,即便能够获得经济增长,也会造成国富民穷的局面。这里的出路在于保持民主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合理张力,寻找两者之间新的平衡点。这既意味着不能停留于国家的过度退出或严格管制,也意味着对于垄断利益集团,不管是政府、大资本还是垄断行业,都要通过扩大公众的民主参政议政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监督,以控制其无限膨胀,防止发展成果被垄断者独占。
收稿日期:2008-01-15
注释:
①参看Constance G.Anthony,"Africa's Refugee Crisis:State Buil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25,No.3,1991,pp.574-591。
②参看Mark Ravina,"State-Build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modern Japa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4,No.4,1995,pp.997-1022。
③参看Marcus Cox,State Building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Lessons from Bosnia,http://www.reliefweb.int/library/documents/2001/bih_casin_31jan.pdf。
④参见托马斯·卡罗瑟斯:《民主如何出现——“顺序之悖论”》,载《民主》2007年第1期。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