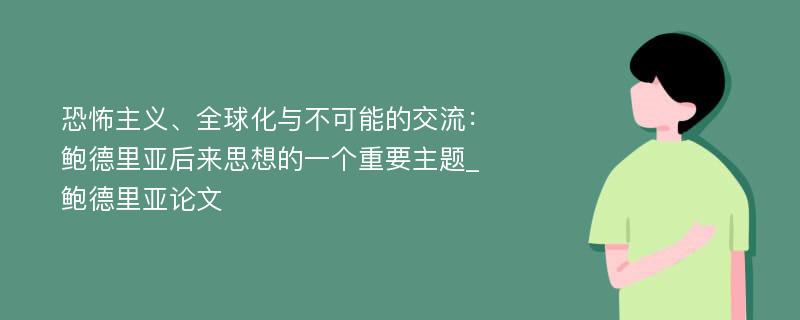
恐怖主义、全球化与不可能的交换——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不可能论文,恐怖主义论文,一个重要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4-0035-07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不断,尤其是美国的“9·11”事件重燃了老年鲍德里亚的理论热情和批判智慧。“9·11”造成了4000多人罹难,它唤起了人们对死伤的广泛同情、对恐怖行为的谴责。然而,鲍德里亚却对此发出“怪论”,认为这是一个“高水准的事件”、“绝对事件”、“所有事件之母”,“一件在其内部把所有从未发生之诸种事件集聚起来的纯事件”。① 当超级强权“在熠熠火焰的荣光中完结”之时,他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恐怖分子之所为,正乃吾望”。② 每一个人,包括被剥削者和既得利益者都对强权存有恶意与憎恨,在无意识深层都曾经梦想过强权的毁灭,都“有着一种看着它们消失的隐秘之欲”③。
鲍德里亚的这一反应遭到了西方社会普遍的不满。批评者指责他的理论行为不道德,说他是在为恐怖主义辩护。鲍德里亚辩解说自己是“分析的道德”④。那么,鲍德里亚何以为“分析的道德”?为了弄清这一问题,还需从全球化问题入手。
一 全球化的暴力
当今全球化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于:这是一个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鲍德里亚发现,全球化在其胜利和顺应历史发展大潮的表层荣光之下,掩藏着更深层的权力暴力和权力支配因子。其具体表现为:首先,就价值体系而言,以美国为领导的全球化,自然以美国价值为主导,且美国将这一价值巧妙地转译为“普世价值”,以此垄断全球范围内自由、人权、文化等的定义权。这里,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对启蒙时代“普世价值”的一种延续和挪用,它承继了“普世价值”的“普世性”,也即标准化、同质化精神,并设法将此“普世价值”通过罗兰·巴特所谓的“去历史化”操作,自然化为人类文化的终极理想、标准与神话。
其次,就该价值体系的影响而言,凭借全球化的绝对利器,西方不但将“普世价值”去历史化,而且还将它向外强行推广,从而造成对独特性他者文化的扼杀。启蒙时代的“普世价值”具有超越性、理想性和定位自身的否定性精神,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普世价值”却抛弃了这些精神,于是,一种肯定性精神开始盛行⑤。这是一种对交换价值体系的肯定。从此,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可以像商品一样流通,而非货币的、不可量化的象征交换价值则无存身之地。美国价值体系就是这种典型的“以可讨价还价、可被量化的交换价值”为重心的价值体系。其将“普世价值”异变为“交换价值”的目的,并把自己的价值打造成一种“全球化的命令”,以便随心所欲地殖民他者。
普世价值推广的方式通常有二:其一为软形式,它使巧计,给自身披上一层外衣,以拯救者、普度众生的面貌出现,如要给予阿富汗等国人民以“自由”(鲍德里亚说,这是一种“别扭的自由”),从而使受害者看上去像受益者;其二为硬形式,它靠威胁、敲诈等手段建立,把自身打造为一种全球性的命令,让他者文化绝对按照自己的规则进行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从而构成了对康德绝对律令的败坏。交换价值的盛行以及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普世价值的强行推广,开启了一种暴力、一种“世界独裁”的暴力、一种殖民主义的暴力、一种猛兽般的暴力、一种猎杀独特性他者文化的暴力。交换价值的绝对统治,使得“所有非货币的价值”,也即无法在全球领域内流通的他者文化价值在无奈中被过滤出局。而全球价值以普世名义,向他者文化强行输送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在客观上消灭与扼杀了所有独特性、唯一性的他者文化,进一步巩固其对价值的垄断权和定义权。与启蒙时代尚存对他者文化的包容精神相比,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西方文化对他者文化无丝毫包容之心,他者文化亦无丝毫存身之地,用鲍氏的话来说,“我们无不遭遇到这种根本性之拒绝”⑥。
再者,西方价值的这种全球性强行推广,不仅是对他者文化的扼杀,更是一种羞辱。但理解这一点还需联系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这一被鲍德里亚寄托了文化甚至人类学理想的象征交换理论,乃以莫斯礼物交换理论为参照,它强调交换的可逆性与互惠性。鲍德里亚分析说,单向的礼物是一种权力行为。西方人向全世界推广自身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其实是向他者文化施礼,而他者文化无足够力量做出平等的对话与回报。其结果,一方以主人自居,一方则处于被给予的奴隶般被俘生活的状态。鲍德里亚描述道:“其结果,我们就处于接受,接受,总是接受的冷酷境况之中。况且,现在亦不是从上帝或自然那里接受,而是通过一种普遍化交换与普遍的满足之技术体系来接受。所有的东西都在无形之中强加于我们……我们处于一种奴隶的境况之中,虽被允许生存,但却被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所束缚”。⑦ 这一奴隶的状态正是他者文化遭到西方价值羞辱后的处境。
二 恐怖主义的抵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全球化对他者文化羞辱与扼杀的结果,必然是报复与暴力的反应。鲍德里亚说: “一种失去了自身价值的文化,只能对其他文化的价值进行报复”⑧,“对于这一全球化体系之整体主义(integrist)的进攻,只能通过一件异常事件的爆发来回应”⑨,而“对其不施之于反抗性的暴力,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⑩
从启蒙时代普世价值向全球化转移的结果,既是一种同质化,也是一种无限的碎片化。何以“碎片化”?面对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消解的权力,(启蒙时代经典的)普世性破碎了,这使得独特性和异质性的力量开始在地方崛起——“不只是差异而已,同时也是对抗”(11)。这一地方化、碎片化正是独特性对全球化抵抗的表现形式。在此之中,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难以约简的独特性力量”(12),它“在其他反抗形式还不可能出现时,横空出世”(13)。也就是说,此时恐怖主义是作为对全球化抗争过程中独特性、异质性力量之一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视恐怖主义为“一种具有活力的反抗力量”,“一种对全部融入流通与交换之全球性进行反抗的力量”,“一种在全球化过程之核心中所出现的激进敌对的力量”,“一种不能约简为世界整体性(integral)技术及精神现实化的力量,一种不能约简为走向终极全球秩序这一难以撼动之运动的力量”(14)。
作为一种抵抗性力量,恐怖主义针对的是全球化的暴力,其目标是要复活“一些不能够在差异与普遍化交换体系中进行交易的东西”(15),并将这些在单极权力下招致死亡的“不可约简之独特性”恢复到普遍交换体系的核心,以展开对单极支配性权力网络的报复行动,从而向以双子塔大楼为象征的西方力量、解放、流动和算计性的狂欢展开攻击,对整个西方“功效与霸权主义的极端形式”发出解构性质疑。所以,恐怖分子报复行为的性质,已经超出了政治、宗教、民族、意识形态乃至文明的层面。鲍德里亚说,“这不是‘文明冲突’的问题”,“而是一种——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学上的——对抗问题,即在无差异的普遍文化与无论在何种领域均保持一种不能约简之他者性(alterity)的事物之间的对抗。”(16) 这一对抗问题“远远超过伊斯兰和美国”(17)。“在其针对白宫的粗疏拙劣的袭击行动中(而在针对双子塔的袭击中,其成功则远远地超出了其目标),他们无意间表明,这座建筑并非致命的目标”,(18) 这意味着政治并不是攻击的首要目的。当然,攻击的性质也不简单是意识形态,不是理念的,甚至不是伊斯兰理念。恐怖主义的这种超政治的攻击性质直接印证了恐怖主义的巨大能量,其煽动力之强足以让新的冲突演变为一种新的世界大战——第四次世界大战。鲍德里亚指出,这场大战“再也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体制和意识形态之间,而是整个人类在与其自己作战”(19),是“大获全胜的全球化正在与它自己作战”(20)。这场战争没有前线和边界,“敌人就位于正在与其作战的文化的核心所在”(21)。
这里,鲍德里亚虚晃一枪,进而深入到恐怖主义问题的深层:它是全球化与自己的战斗。之所以如此,乃是全球化体系自己不检点、不道德的结果。“当今,这一实际上已达到顶峰的单级世界秩序,在所有的动荡中,都发现自己正在与分布于全球核心区域的对抗力量展开肉搏——一场涉及到所有细胞、所有独特性,以抗争的形式进行反叛的不规则碎片形战争(fractal war)……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却在别处。它长期不断幽灵般地缠扰着每一种世界秩序和所有的霸权统治。”(22) 全球霸权与谁都处理不好关系,其实也就是自己打自己,自己和自己决战,自食恶果。
三 恐怖主义的幽灵与双子塔挽歌
全球权力体系与自己战斗,自食恶果,这反过来意味着恐怖主义的抵抗行动是成功的。恐怖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自然离不开其所使用和拥有的两大武器:霸权体系的武器和高度象征性的武器。前者是西方霸权体系所支配的现代资源和科技产品,如金钱、股市炒作、电脑科技、飞机技术、奇观和媒体网络等,这其中包括鲍德里亚重点提及的媒体的影像与传播(“媒体即是事件的一部分,即是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若没有媒体,恐怖主义将什么也不是”(23));后者则是恐怖分子自己的死亡,鲍德里亚也称之为“死亡的象征性礼物”,它成为挑战体系的“绝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中,前一武器主要用于身体层面的消灭,后者则用于象征层面的羞辱。两者单靠其中之一都不能获得成功,可一旦它们结合起来,也即“操作性结构”和“象征性誓约”结合起来,“一切都改变了”,“零死亡战略(zero-death strategy),即所谓‘干净’(clean)的技术战争战略,它与借助象征力量来改变真实力量(‘real’power)相比较,确实是难以同日而语。”(24) 恐怖主义的这种抵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逐层解读:
其一,恐怖主义幽灵的出现。鲍德里亚喜欢用“病毒”(viruses)一词来形容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宛若病毒一般,无所不在。它伴随霸权体系而遍布全球,与霸权体系如影随形;同时它也时刻准备着在各处活动,就像是一个双重间谍。”(25) “恐怖主义,宛若病毒,它无处不在,没必要以阿富汗作为基地。”(26) 鲍德里亚这一修辞的目的,一则描述这一无形“病毒”比狼群还难对付;更为重要的在于,如病毒一般的恐怖主义无孔不入,让人产生草木皆兵之感。这也正是恐怖主义的幽灵效果。恐怖主义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它透过让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从而制造出潜在恐怖攻击无时无处不在的紧张局面。鲍德里亚曾将其描述为“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它“像病毒一般,渗透于整个世界,悄悄地潜行于地球的各个角落,从权力的所有空隙中溢出”,“对抗处处都有,同时也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27) ,它把整个西方投入于安全的着魔中,投入一个“恒久恐怖的隐蔽形式中”,迫使西方让自己感到恐怖。这样,西方的治安神经就始终处于一种类似冷战的紧张状态,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镌刻于肉体与社会习俗之上的第四次世界大战”。(28)
其二,面对恐怖主义的幽灵,体系“借助于病原体(contagion),通过连锁反应的操作”,做出过敏反应,从而“渐渐使我们失去所有的免疫力以及与其对抗的力量”(29),导致体系内部免疫机制的崩溃。当然,恐怖主义的这种效果借着恐怖攻击这一外因触发体系内在的脆弱性和自我毁灭冲动,从而以共谋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行动假设。说到底,恐怖攻击行为本身仅为外因,西方全球化及其强权的脆弱乃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在的攻击是自我毁灭的契机。鲍德里亚不无幽默地说:“即便是上帝,也不能向自己宣战。然而,上帝却能。西方,正以上帝的身份(神圣的无限权力,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呈现出自取灭亡的倾向,从而向自己宣战”。(30)
其三,站在象征交换的角度理解,面对恐怖主义的双重武器,体系只有以自身的死亡作为回应,正如双子塔的倒塌一样。这其中有一个假设——恐怖主义者的假设:“要对死亡和自杀造成的多种挑战做出反应,体系本身必将会自我毁灭。因为,体系和权力两者都具有象征性的职责……在这多变的、死亡不可能交换的循环中,恐怖分子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个无限小的点而已,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或空无,即一种巨大的环流。环绕着这一极小之点,真实的和权力的整个体系积聚而起,复生惊恐,又有简短之振作,最终则由于自身的超负荷功效而消亡。”(31) 恐怖主义通过自身的自杀行为现实化了这一假设,“在这一自杀过程中,独特性同时也使他者自我毁灭”(32),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个体自杀换取霸权体系自杀的象征性对决关系”(33)。
这种“以死亡换取死亡”的关系,在双子塔倒塌的象征性场景中得到充分体现。双子塔本身是全球权力的象征,它是“大脑”,是“神经中枢”,是“国家心脏”。双子塔被攻击意味着心脏受到攻击。同时,双子塔的倒塌反向暗示了其内部结构的脆弱。其中原因与塔内生活的恐怖相关,“4000名死于两座塔楼里的受害者的恐怖,与生活在楼中的恐怖(即生活和工作在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石棺中的恐怖)是分不开的”(34)。当然,更主要的在于,双子塔的消失可能成为“全能可能消失的象征”。鲍德里亚解释说:“我们只能设想双楼的倒塌——这本身就是现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件独一无二的事件——预示着一种戏剧性的终结,也就是说,是这种建筑形式以及它所象征的世界体系的终结。”(35)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不无幽默地调侃道,双子塔拜恐怖主义之恩赐而成为全世界最美的建筑——“世界第八大奇观”。(36)
四 西方的假设
对于恐怖主义及其胜利,西方价值体系始终不能做出有效解释。其通常的看法或假设,要么认为恐怖分子“怯懦”——“因为他们选择了自杀”,“因为他们牺牲了无辜”(37);要么认为恐怖分子是在敲诈——“他们已经富裕了起来(拥有所需的资源),却没有放弃要毁掉我们的欲望。我们认为,就我们的价值体系而言,他们是正在欺骗”(38);再就是认为此事件纯属意外,——“‘9·11’所构成的,仅仅是走向不可逆之全球化路途中的一次意外事故或偶发事件”(39);对于其自杀行为,西方人更是觉得不可理喻。总之,在西方人眼中,“伊斯兰不应该如此这般”!(40)
西方人的这种解释与认同,鲍德里亚称之为“零度假设”,也即最小化假设。它是“最终让人觉得绝望的假设”(41),它设法淡化恐怖主义的影响,掩盖其内在的丰富意蕴,所以“根据零度假设,该恐怖事件毫无意义”,它“仅仅是更增加了单极权力与单极思维方式的全球权势”。(42) “零度假设”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西方人对问题的理解受其自身文化视角的局限,所以对某些事件无法做出客观分析。比如,在西方将生存当做“普遍人道主义层面的拜物教价值观”(43) (生命至上)的影响下,很难理解恐怖主义的自杀行为;个人英雄主义观念也很难做出有效解释。再如,由于西方垄断了善恶判断权,所以它将任何抗拒和违反我们价值的行为,如恐怖行动,都归咎于“意识的一种盲目性”(44)。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占据了客观判断的空间。其次,“零度假设”源于西方的自大,自大到只知道(认可)自己的一种评价体系,而对他者体系视而不见;自大到将所有反对者均视为恐怖,视为异质,并加以消灭。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微妙的原因:共谋的秘密。导致恐怖主义的深层原因,它是西方拒绝理解和阐释的。何以“共谋”,谁与谁共谋?在《恐怖主义的精灵》(The Spirit of Terrorism)、《恐怖主义的假设》(Hypotheses on Terrorism)等几篇重要论文中,鲍德里亚多次提及此问题。我们提到“其之所为,正乃吾望”即是一种共谋,这是恐怖行动与人们希望霸权毁灭的欲望形成的共谋。鲍德里亚提醒道:“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该事件就失去了任何象征性的维度,从而成为一起单纯的偶然事故,一种十足的率性之为,一些狂热分子凶残的幻影,接下来要做的一切就是除掉他们……假如没有这种由来已久的共谋,事件则不会有现在的这种反响。”(45) 当然,这只是共谋的一个层次。更深的层次则在于外在的摧毁与内在的脆弱(乃至自我毁灭、自己向自己宣战)形成的里应外合式的共谋。鲍德里亚指出:“一个完整体系的象征性坍塌,是由于无法预测的共谋所导致的,似乎这双子楼,通过自身的坍塌,通过自杀,参与了事件,使其圆满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说,整个体系由于其内在的脆弱,向先期的行动伸出了援手。”(46) “这场象征性的坍塌是由于无法预测的共谋所导致的——似乎这整个体系,由于其内在的脆弱,参与了自取灭亡的游戏,由此也卷入了恐怖主义的圈套之中。”(47)
对于这种共谋的秘密,西方人始终不肯承认和面对。其原因不言自明,承认共谋就等于否定自己。所以,西方采取了一种策略:它设法将注意力引向那些可见的东西之上,而不管其象征部分隐含的意义和价值潜能。其目的一则转移人们对其内在的脆弱和霸权的发现与关注;另则为自己更大的阴谋行为找寻借口,“竭尽全力地聚焦于冲突,实则是为了制造一种看得见的对抗以及基于武力解决方式的哄骗而已”(48)。所以,“美国人的战争只是聚焦于他们想要摧毁的可视客体,但‘9·11’事件所象征的一切却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被彻底摧毁,在阿富汗的那些狂轰滥炸,也完全是一种不适当的替代性行为而已。”(49)
五 鲍德里亚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恐怖主义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西方却不能做出有效阐释,这源于西方的自大。这一自大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鲍德里亚通过种种分析,从“零度假设”分析到“最高假设”,目的在于表明:要想真正理解恐怖主义,须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如当代理论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一样。鲍德里亚的深刻与精彩也体现于此。
在西方的价值视角下,所有反对它的东西,所有差异性、独特性,甚至“所有不听话的形式,实质上都是恐怖主义”。鲍德里亚举例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自然灾害即为一种恐怖主义的形式。大规模的科技偶发事故,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与恐怖主义行为和自然灾害也有几分相似。……所有偶发的空难事故都可以被称为恐怖组织所为。不合常理之事的特性就在于它们可以被归咎于任何人或任何的事儿。……在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中,数千名韩国人惨遭杀戮,原因是他们对这次灾难难辞其咎。”(50) 显然,恐怖主义是欲加之罪的一种命名。恐怖主义在西方体系中不合其价值规范,它也因此被视为不道德的,更加上其大规模的死亡画面给这种道德谴责辅以图像“实证”。但问题在于,如果关于恐怖主义的分析仅在这种一般道德层面上漂浮,就很难在理论上有所深入。
当我们尝试跟随鲍德里亚,用超越的眼光,也即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就会对差异、异端、独特性和恐怖主义有另种阐释。当然,鲍德里亚承认恐怖主义无疑是不道德的,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恐怖主义的不道德?通过层层分析,鲍德里亚告诉我们,恐怖主义的不道德是本来就不道德的全球化直接刺激产生的。这一看法构成了鲍德里亚恐怖主义理论的核心。全球化本身是不道德的,但在西方体系中却堂而皇之成为道德的。这一颠倒导致了整个评价体系和所有评价事件的颠倒与混乱。所以,鲍德里亚从根本上反对的是西方价值体系及由此而来的全球霸权行为,反对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这一反对、这一深度分析正是其智慧的表达,同时亦是一种智慧的责任。其中,“真理的道德”、“分析的道德”自然萌生其间,所有对于鲍德里亚的道德主义诽谤亦将不攻自破。鲍德里亚不无幽默地调侃:“就让我们是不道德的吧”,“让我们带着邪恶的理解探讨此事。”(51) 他对分析过程的关注表明了一种更高的道德存在,他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了一个具有“分析的道德”和“真诚的责任”的道德者。
结语
鲍德里亚关于全球化的分析,之前在学界并不受注意,如果将其置入宏观的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视野,不只是出于对鲍德里亚理论的简单辩护,亦可总结出一些特色。其一,鲍德里亚是从“恐怖主义”问题中“无意走入”全球化论题,视角独特,它是以问题为背景,这与实验层面的理论演绎不同。其二,全球化问题其实并非鲍德里亚理论驻足的最后驿站与支点,它更多地是从全球化深入到对文化深层精神的分析。其三,与当下时髦的“球域化”和“帝国”理论(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的理论)相比,鲍德里亚更关注霸权与抵抗的互动问题。这其中有历史轴线的史学支撑。鲍德里亚不仅发掘了全球化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关联,同时亦注意到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将全球化与霸权联系的思路并非新解,但结合恐怖主义、从霸权与抵抗之互动角度诠释全球化及其未来,应该说,它比球域化和帝国理论更能展示出矛盾的多样性和丰富性。(52)
需要提及的是,晚年鲍德里亚的理论风格渐趋晦涩。我们在细致品味其恐怖主义理论的同时,也需对其保持一份警惕和清醒的批判意识。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11)(12)(14)(15)(16)(17)(18)(20)(22)(23)(25)(27)(28)(29)(30)(31)(32)(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0)(51) Jean Baudrillard,The Spirit of Terrorism:and Other Essays,Trans.Chris Turner,London & New York:Verso,2003,p.4,pp.4-5,p.42,p.92,p.74,pp.102-103,pp.97-98,p.76,p.94,p.58,pp.57-58,p.74,p.97,p.11,p.46,p.11,p.12,p.31,p.10,p.15,pp.81-82,p.94,p.7,pp.17-18,p.65,p.41,pp.40-41,p.48,p.68,p.23,p.51,p.66,p.51,pp.51-52,p.68,p.67,pp.5-6,p.8,p.45,p.11,pp.98-99,pp.12-13.
④⑩(13)(19)(21)(26)(49) Jean Baudrillard and Samir Gandesha.“This is the Fourth World War:The Der Spiegel Interview With Jean Baudrillard.” in:IJBS.Vol.1,No.1,2004.(English),http://www.ubishops.ca/baudrillardstudies/spiegel.htm.
(24) 所谓“零死亡”,即西方的一种战争观念及其所追求的战争效率和战争理念,以最大可能避免自身人员伤亡为代价来取得战争的胜利。见Jean Baudrillard,The Spirit of Terrorism:and Other Essays,Trans.Chris Turner,London & New York:Verso,2003,p.21.
(33) 朱元鸿:《第四次世界大战及其共谋,见过吗?》,http://www.chinese-thought.org/whyj/003200.htm.
(52) “帝国”、“球域化”理论都强调地域的消失对全球权力的影响。美国的霸权在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发展进程中衰落了。鲍德里亚也谈到美国的衰落,但角度不在地域/空间,而是从权力本身、从权力的互动角度来谈。当然,这与其象征交换理论有关,在权力双方礼物交换的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化霸权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