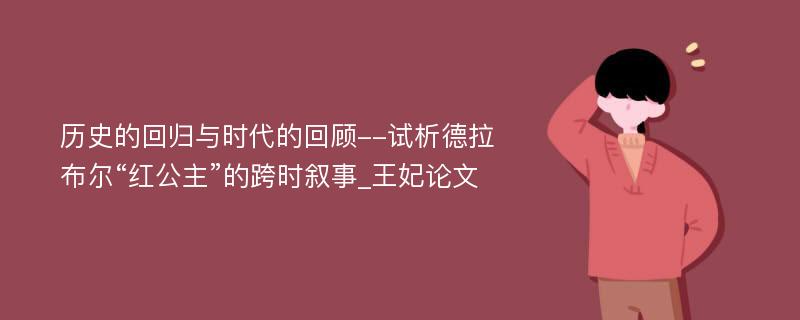
历史还魂,时代回眸——析德拉布尔《红王妃》的跨时空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尔论文,王妃论文,德拉论文,时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6-0054-09
在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的当下,当代文学呈现出厚重的历史之思,小说家们意欲通过审视历史来拷问当下,历史题材拟写成为现时的主流话语。以创作现实题材、反映当代生活著称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也加入到这一历史潮流之中,《红王妃》(The Red Queen,2004)即是例证。女作家将对人类普遍命题的探讨置放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神秘的东方,投向遥远的历史深处,在历史叙事中展现永久的人类生存困境,以历史警示现世,表现出高度的全球观念和强烈的历史意识。与众不同的是,德拉布尔在《红王妃》中启用一个亡灵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展开历史叙事。辞世二百年的朝鲜王妃阴魂不散,真实的历史人物以神灵的形式出现,同时充当历史当事人和讲述者的双重角色,给人真切的历史感。亡灵忆往叙事从零聚焦视角切入历史,在叙述话语上超越了常规叙事的固定模式,打破了叙事主体的时空局限,使作家在行文时拥有了宏阔的观察视野和充分的叙述自由,在人鬼之间建构起沟通的桥梁,实现亡灵与生者的对话,无疑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观照方式。
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德拉布尔采用了复数叙述者,以旁观者的视角追随当代人的寻访历史之旅,同时审视当下的现实,使相隔两个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两大时空并置同构,互为对照,在对异质文化的观照中实施对当代现实的认识和反思。“作者巧妙地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用一根血泪和欢笑的红丝带把两个完全迥异的女人串联在一起。陌生又熟悉的生者和逝者互相交流,古代和现代互相交织。”①
由此,女作家充分行使小说家的虚构特权,采用亡灵忆往的叙事策略,在今生与往世、现代与古代、西方与东方之间实施了多重时空跨越,完成了超越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历史对话和精神交流。时空的随意性穿越以及表述的畅达自如给故事增加了戏剧化的审美特质,为作家探寻跨文化、跨时空的人类共性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大多数评论注意到了小说的双重时空设置,却并未深究作者为实施这种复式叙事所选取的话语形式,亦忽略了作品所传达的普世意义和人文精神,而这正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亡灵忆往,幽明对话
表面上,《红王妃》是一个阴魂不散的鬼魂故事。实际上,《红王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鬼魂故事。传统的鬼魂故事多为生者偶入冥界,讲述游地狱的故事,以阳间的视点来观察神出鬼没的阴间世界。像苏美尔女神伊南娜下冥府,希腊史诗英雄奥德修斯入冥遭遇鬼灵等;或是亡故之人灵魂显现,探访生者,发生一段人鬼未了情。元代杂剧如《盆儿鬼》等戏中都出现了鬼魂显灵,与生者通话的场景,而西方文学则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
《红王妃》亦有别于一般的鬼魂叙事。这种叙事往往启用一个亡灵叙述者,以阴冥的亡魂为聚焦人物来观察现实世界的人与事,形成一种死者观照生者的死亡视角。如方方《风景》中早夭的婴儿以隔世的旁观视角对家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叙述。在唐镇的《同一条河》中,被杀身亡的“我”讲述家族三代人的故事,正所谓“一个幽灵的自白”。亡灵叙述者在西方文学中也不鲜见,爱伦·坡的多篇小说由鬼魂充当叙述者。在阿丽·史密斯的《旅馆世界》(Hotel World)里,主人公萨拉的鬼魂身份使她获得了全知全觉的叙事特权。谭恩美的《拯救溺水之鱼》也由已死亡的小说人物充任叙事主体。这种非常规的叙事视角,以死亡为依托,巧妙地解决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悖论,合情合理地跳出了限知视角的局限,实现了常规视角和视角越界的自然跨越。
然而,德拉布尔的《红王妃》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鬼魂故事,也不局限于死者观照生者的死亡视角。叙述者是亡故的主人公,但是讲述的不是鬼魂在冥界的经历,而是死者离世前的生存体验;叙事采用的是死亡视角,但是所观照的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主人公长达八十年的人生经历。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已辞世二百年的朝鲜王妃仿佛一个阴魂不散的叙事精灵,向当代人亲口讲述两个世纪前的宫廷故事和人生感悟,亡故的主人公所实施的回顾性叙事形成了独特的亡灵忆往模式。这种设置巧妙的跨时空叙事打通了阴阳两界的分界,历史当事人化身为一个无影无形的叙事幽灵从历史的深处向当代人讲述历史的场景,当代人得以穿越岁月的尘埃,聆听历史之声,双重时空相连交错,历史与当下融合交流。小说并未因鬼魂叙述者的出场而失去其真实性和生动性,却成功地除却了惯常的虚幻性和荒诞性。
亡灵忆往的叙事模式在文学史上较为罕见,只有唐宋传奇如钱易《越娘记》、秦醇《温泉记》等出现过类似的叙事。在当代作家笔下也不多见,在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亡灵的回顾性叙事突破了生与死、人与鬼、现实与梦境、意识与潜意识、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等界限,展现出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荒诞世界。但是德拉布尔《红王妃》中的亡灵忆往较之东西方文学史上的同类叙事表现得更为集中与明显,其时空跨度长达二百余年,地域跨度由英伦及至韩朝,文化跨度穿越东西方。
《红王妃》缘起德拉布尔读到的《王妃回忆录》。作者是朝鲜王妃洪玉英,历史上确有其人,即朝鲜李氏王朝第二十一代君主英祖国王的儿媳、思悼王储的妃子、第二十二代君主正祖国王的母亲。王妃在世时幽居深宫后院;身心压抑屈辱,历经命运磨难,并因其女性身份而为历史所忽略。“我没有名字,却又有很多名字。我是个无名的女人,我的真名并未载入史册。我是名人,却又无名无姓。”“如今的银质宝座空空如也,没有供奉我的画像,没有我的身影。我的名字已被湮没,我的身影也不复存在。”她贵为王妃却没有话语权,只能在回忆录里悄悄地倾述自己对时政世事、人生命运的评判,吐露个人的心声感受:
在生之时,我在十年间写过四本不同的回忆录,每本的目的略有不同,每本所披露的话刻意掩盖的事件也各不相同。现在,以鬼魂的身份叙述,我会力求真实,但我不敢打保票,也许鬼魂也会自欺欺人呢,谁说得准呢?(德拉布尔,2007:56)
时至21世纪,在德拉布尔的巧妙安排下,昔日王妃的鬼魂从历史的深处浮出,打破缄默,变成了“一位先知先觉者”、“一种奇特生命的代言人”,超越了时代的束缚、地域的界限和文化的羁绊,畅所欲言地向后世倾诉心声、传达史实,在现代文明和历史之间建立起交流。
小说伊始,王妃的亡灵直接显现充任叙事主体,用第一人称向21世纪的当代人展开回顾性叙事:
我辞世已两百年,但一直未敢懈怠,我一直在重新思考我的故事,反思我的历史。……如今,两百年过去了,以我生时的经历加上两百年来的见识,我将再次讲述我的故事。我期望再度得到关注,期望会有一个全新的读者群。我已选好一位年轻富有活力的替身,她将延续我的生命,同我合作,继续我从来不曾止息过的探索:对苦难和生存意义的探索。(德拉布尔,2007:4)
亡灵叙述者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带领当代读者进入历史叙事,开始人类生存意义的永恒探索。
以亲历者王妃的特殊视角切入历史,并借助其鬼魂身份与当代人展开对话,达成跨时空叙事,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艺术构思。亡灵叙述者随意纵横时空,凭吊历史,感叹现实,甚至直接现身与读者展开交流:
我发现,回忆混乱不堪,令人痛苦的年代已使我厌倦,更何况还得劳神费力地加以解释说明。读者诸君,你们之中有谁还有耐心听这个故事,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充斥着阴谋诡计、排除异己、杀戮放逐的故事?(德拉布尔,2007:111)
这样,历史当事人和叙述者合二为一,外视角转变为内视角,远距离转换为近距离,民族的集体记忆呈现在主观色彩浓重的个人记忆中。历史近在眼前,往事真切可信,大大缩短了历史对象和当代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叙述者的鬼魂身份又使之神奇地超越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局限,获得了与时俱进的认知能力:“我现在已是隔世之人,成熟自不待言,加之读了19、20世纪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专著。”历史叙事因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我发觉我现在已不知不觉开始使用一些不属于我的词汇,一些我那替身悄悄告诉我的词汇:后现代文本主义、普救教化论、解构主义、自我概念……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一个词非‘全球化’莫属。”亡灵叙述者甚至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双重距离,以西方哲学思维和现代科学眼光来看待现世,反观历史,作出当下性评判:
现在想来,我儿子懿昭的病根在于免疫系统太弱,但在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人体有这么个系统存在。(德拉布尔,2007:34)
在虚构的文本世界,无形的鬼魂自由地超越生界和死界,依附于当代女学者,发生了合乎情理的视角越界:
我已派我的替身去查阅我和思悼王子六十年金婚庆典的有关记录。……我的这位后世代表戴着白棉纱手套,在文物管理员的严密监视下,一页一页翻阅着这本珍贵的记录册。……借助我替身的双眼,那图文并茂的记录册勾起了我对宫廷生活的记忆。(德拉布尔,2007:21)
王妃的鬼魂甚至将当代人的历史追溯置于她的全知视角之下,督促着当代人物的访古进程,“两百年后,我派我的替身去首尔寻找她的陵墓。它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旁边不远处是网球场。”有时鬼魂叙述者又如同作者式叙述者,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直接向读者交代叙事意图:
请耐心一点,我这就加快速度,告诉你故事的结局。我那位对这个故事着了迷的替身已急不可耐地催我了。……这位替身跟我本人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关系。我俩都是理性主义者,都振振有词地称自己不相信有超自然的生命存在,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又在这里携手合作,讲述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似鬼非鬼的故事。我和我的替身交替出面,互为讲述者与被讲述者。我将把我漫长的人生余下的部分做一个概括,用不多的段落做简单交代。因为我的替身已开始对我不耐烦了。她急着跨越时空,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德拉布尔,2007:111)
鬼魂叙述者既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又无所不能的超自然能力,又有全能的叙述语言及全面的叙述经验。第一人称叙述自我突破限知视角的界限,合情合理地跨入了全知视角,从容地上溯几百年,亲历般讲述王朝的命运,连其身后事也明察秋毫,并坦然地在叙述中进行个性化评论,而毫无唐突意外之感。享有充分话语权的叙事幽灵在小说的虚拟时空里自由飘荡,制造了一个亡灵诉说的叙事幻象。
我的著作留存下来,但刚开始时知道它们的人寥寥可数。……而作为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作为这个真实故事见证人和主人公,我几乎不为人知。现在不同了,我的作品开始流传,并被译成若干种文字。我惊愕而饶有趣味地关注着它们的传播。我的故事激发后世人的无限遐想,一些我们那时闻所未闻的传媒手段大显身手,将我的生平故事做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加工。翻译和录入员在电脑上忙活着,时不时地还会出点舛误。我得鼓励鼓励他们,给他们加加油。我乐意让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故事。(德拉布尔,2007:118)
德拉布尔把王妃这一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当作“脱离躯体的灵魂”,让她以鬼魂的形式穿越时空,充任历史和现实的媒介,因为“她既是一个真实存在,又是一种讽刺性注释,是对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质疑,她是这两个部分的结合”。(李良玉:157)亡灵忆往的特异视角跳出第一人称叙事的限知悖论,拓展出跨越时空的多层次视域,既保留了第一人称叙事的主观性、真实性和亲切感,又实现了全知叙事的客观性、权威性和戏剧性,使叙述意图得到最佳实现。于是,人鬼殊途、幽明异路、阴阳阻隔的界限被打破,虚与实、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混同合一。亡灵忆往,幽明对话,古今相通的跨时空模式成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话语。
第一部分“古代篇”临近结束,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者决定隐退,将自己的叙事特权移交给王妃的鬼魂所派遣的密使们,由他们去展开当代叙事:
好了,现在请跟我来,我要引领你们跨越时空,把一切不和谐的喧嚣抛诸脑后,让我们穿越金属与塑料构建的地狱,进入华丽舒适、全球一体的新千年。屏住呼吸抵御污染,塞紧耳朵摆脱噪音,跟我来,我们去一个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你们会喜欢它的。它,就是未来,是你们的未来,好好把握吧,未来属于你们。(德拉布尔,2007:119)
通灵附体,访古探幽
小说进入第二部分“现代篇”,叙事的焦点发生了大幅度跨越,时空从二百年前的东方闪回到当代西方,英国女学者芭芭拉·霍利威尔替代朝鲜王妃成为故事的主人公,红王妃的亡灵附身于现代替身来继续她凄迷的人生。至此,王妃的鬼魂退居幕后,而她所派遣的密使们则取而代之,仿佛如影随形的精灵,以第三人称称呼主人公芭芭拉,以故事外复数叙述者的口吻向读者报告他们的观察所得:
我们注视着她,而她对我们的闯入却全然不觉,为什么我们会被召唤到她的床头?是藏在她手提袋里的那本书把我们给招来的。……那本书蕴含着两百年前的久远信息,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让我们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进入这个房间。我们就像长着双翅的小密探,挤挤撞撞地聚成一团,浮游在天花板上,俯视着床上这个睡不安生的女人。(德拉布尔,2007:123)
王妃的密使们跨世纪而来,用超越时空的眼光观察着当代主人公芭芭拉以及她置身其中的环境:“我们学东西够快吧,马上就记住了她的名字。”“会有人来整理床铺、打扫浴室、清洗杯子吗?现在的英国人还用不用仆人?”不期而至的《王妃回忆录》将遥远历史和异域文化带进芭芭拉的生活,促成了她的远东之旅,她从此被王妃的魂灵附体了。
于是,王妃的鬼魂神不知鬼不觉地设计了芭芭拉的首尔之行,急不可耐地催促当代人回访她那个时代的历史。“王妃跟霍利威尔博士一样性急,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抓住这个女人的注意力。”在飞往首尔的飞机上,芭芭拉
取出《王妃回忆录》随意浏览着。……时间、空间的概念全都不存在了。她被王妃的魂灵紧紧攫住了,她成了这个没有名字的洪氏贵妇的奴隶。……从肉体到精神,她已彻底被王妃给控制了。芭芭拉·霍利威尔博士已经不是她自己了。……王妃就像科幻影片里的外星生物,已经进入到她的体内,在里面扎根生长。(德拉布尔,2007:133)
芭芭拉鬼迷心窍,身不由己,开始聆听历史之声:
在她那小小的深绿色的旅行箱里,一本《王妃回忆录》正等待着她。回忆录的作者正等着同她对话。死亡已让这位作者缄默了许多年,现在,她又找到了一位新的倾听者,眼前这个时睡时醒的女人就是她的一个新的上当受骗者。这本书是一个陷阱,一种传染病,一颗定时炸弹。(德拉布尔,2007:124)
阅读着王妃的回忆录,人与鬼之间发生了神秘的交流,芭芭拉
感觉王妃没有完全道出事实的真相,有些细节让她捉摸不透。她告诉王妃说她必须休息休息了。……在这高空中,王妃也感觉有点儿不舒服,无影无形的她答应暂且松松手:她确信霍利威尔博士现在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以放心地让其舒缓一下神经。(德拉布尔,2007:133)
王妃的鬼魂无影无形,无人察觉,却为无处不在、全知全觉的叙事精灵所捕捉,由旁观者的视角反映出来:
王妃紧挨芭芭拉坐着,因为无形,没人看得见她,她从两个世纪的沉睡中走出,十万火急地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霍利威尔博士被选中作为这些信息传递的载体。她有点儿不太情愿,她肩负不了如此重任。不错,她很聪明,但还没有聪明到那个地步。她感到了压力,感觉无助。她干嘛要远离家乡,跑到首尔来?她什么都不明白,她试图说服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但在此刻,她仿佛身处旋风的中央无力自拔。她迷失了,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德拉布尔,2007:151)
在古老神秘的历史面前,当代人深感迷茫无助,只有被动地俯首听命。于是当代女学者来到了王妃度过一生的宫殿园林。她的脚印覆盖着悲悼王储的脚印,王妃的鬼魂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她。
终于,她看到了那些古老的宫殿,那些亭台楼阁。噢,这不是王妃的孙子纯祖国王的手迹吗?他书写的匾额悬挂在富丽堂皇的宫门上。……再下一处是颂蒙殿,是纯祖国王的曾祖父,那个喜怒无常的英祖国王亲自接见并殿试太学生的地方。(德拉布尔,2007:157)
芭芭拉被王妃的灵魂附体,置身于陌生国度却产生了似曾相识之感,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关联。
对她来说这是完完全全的异域文化,她一点儿也看不懂,却又觉得那么熟悉。难道是在法航班机上就一直跟她纠缠不休的王妃的鬼魂又一路跟了来,催促她不断前行,走向真实人生的另一种结局?是不是王妃已经侵入她的记忆,强行赋予她某些新的使命?(德拉布尔,2007:160)
远处传来诵经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久远时代的逝者在向活着的人倾诉交流。芭芭拉“没来由地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解读《王妃回忆录》文字背后的东西。芭芭拉有一种感觉,感觉王妃同她之间有着直接的交流”。
至小说的第三部分“后现代篇”,叙事精灵们惊喜地观察到,霍利威尔结束了她的远东之旅返回伦敦,却仍然着魔于王妃的故事,“在这书山之中,我们发现了那本曾随她远赴东方的《王妃回忆录》,书已被翻得皱巴巴地卷了角,书上被她写了许多批注。另外两种译本也在书堆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女人对王妃的故事简直走火入魔了,因为她收集了无数与之相关的书籍和杂志来潜心研读。我们看到,这里有她从图书馆借来的新版的伊莎贝拉、伯德的经典名著,此书记叙了她的朝鲜之行。”
王妃的鬼魂亦如影随形紧跟着芭芭拉,期待自己的故事永远传承下去:
关于生命永恒的故事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讲述。不过不用等太久,芭芭拉·霍利威尔将会遇到一个人,一个可以把讲述故事的任务托付给她的人。这些故事不会就这么在历史的长河里湮没。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芭芭拉将很快遇上一位史学家或心理分析家,一位犯罪学家或小说家,他们会接过讲述故事的任务,让这些故事代代相传,直至永远。(德拉布尔,2007:231)
于是小说中出现了令人称奇的一幕,本书作者德拉布尔以芭芭拉的新朋友的身份现身,并对王妃的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芭芭拉有一种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现在已把王妃转交给了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她可以把王妃忘掉了。……至于王妃,就让她折磨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去吧,芭芭拉要回到自己的新生活中去了。”德拉布尔以福尔斯式的后现代策略安排了自己的出场,自觉地承担起小说家传诵历史的必然使命。
历史循环,镜相共生
德拉布尔将小说题为《红王妃——一部跨文化悲喜剧》,分成古代、现代、后现代三个篇章,明确标示着作品跨时空的历史探索主题,其中的人物事件也都有史可据。(李良玉:154)但是德拉布尔创作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也不局限于历史叙事的细节真实性。正如德拉布尔在序中所言:“我无意描写朝鲜文化或者重现18世纪晚期朝鲜宫廷的‘真实生活’,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生命的本质,关于跨文化的人性存在的可能。王妃是我探索的起始而不是终结。”德拉布尔刻意建构的跨文化叙事不是探索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异质成分,而是展现全球化范式下超越时空和地域的人类文明共性。这种探索源于女作家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文主义思想。德拉布尔在论及今日英国小说家时曾提出“人类状况小说”一说,并指出文学作品中人性的整体性观照应该以个体生命体验的描写为出发点,从富于地域文化特征的叙事中演绎出人类共同的本质性特征。(德拉布尔,1994:8)
小说的“古代篇”着眼于18世纪的朝鲜王室。王妃自幼被选入宫,婚配王储思悼,却如同身陷囹圄的囚犯,身心倍受压抑,并历经杀戮、疾病和死亡等重重灾难,时刻处于阴谋与权术的漩涡中。她的公公英祖国王专制跋扈,实施强权统治,对儿子思悼也没有表现出常人的父爱,却将其视为王位觊觎者而加以排斥迫害,父子屡屡发生激烈冲突。思悼贵为王储却受尽蔑视和折磨,富贵奢华和荒淫纵情都不能使他解脱身心的痛苦,以致精神癫狂,几欲自杀,最后被父王赐死,在米柜中活活饿死,难逃悲剧性的宿命。王妃说,“即使在今天……我想他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也许换一种我无法想象的方式”。王妃的长子懿昭孱弱多病,她作为母亲却无能为力,最后眼睁睁看着儿子夭折,经历了难以言说的丧子之痛。王妃为封建制度所禁锢,为儒家礼教所约束,在历史的边缘艰难求生,封建制度下的历史人物只能被动地依从命运的摆布。
在“现代篇”中,时代已进入21世纪,主人公芭芭拉是一位活跃在当代学术圈里的成功女学者,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享有风光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物质生活。在当今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现代女性拥有追求事业、享受生活的充分自由,这是王妃时代的女性无法想象的。但是与18世纪封建王朝的王妃相比,21世纪的现代女性并未显示出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性。芭芭拉表面风光,内心苦闷,与王妃一样经历坎坷,命运多舛,她们的人生惊人地相似。
芭芭拉的丈夫彼得·霍利威尔系出名门,其父是称霸学术界的权威人物,也如思悼的父王一样严厉霸道,“他父亲的本事是一般人学不来的,正因如此,他对儿子的要求太高,而他的儿子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疯掉了”。彼得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苦闷抑郁,与思悼王子一样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多次出现自杀倾向,住在精神病院生不如死。古今两代父子都经历了俄狄浦斯式的父子冲突。芭芭拉的儿子本内迪克和王妃的儿子一样患有罕见的综合性免疫缺陷症,在医术发达的当代也属不治之症。芭芭拉身为医学博士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和王妃一样经历了丧子之痛。现代女性陷入了人生同样的怪圈,世界历史的循环性决定了人类悲剧的普遍性。
在首尔的会议上,芭芭拉邂逅了学界的帝王占·范乔斯特教授,并与之发生了疯狂的情爱。短暂的欢愉过后,这位“像皇帝老子一样的名人”却意外地猝死在芭芭拉的怀抱里。“躺在被单下的占·范乔斯特就像一位刚刚驾崩的皇帝,他看上去是那么高贵,胜过古罗马的任何一位君王。”范乔斯特最后的演讲题为“铅匣:关于《启示录》的思考”:
整篇演讲朦胧晦涩,最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简单却又费解的图景,一幅躺在坟墓里的活死人的图景。占·范乔斯特便是人类的代表,躯体活着,却被困在匣子里,在这个越来越黯淡的星球上,在这个空虚死寂的宇宙中,慢慢的却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德拉布尔,2007:178)
范乔斯特从没有听说过思悼王子,他描绘的死亡情形却与思悼王子惊人地相似,“铅匣”与“米柜”成为人类共有的死亡意象。穿越两个世纪的时空,异化的人类仍然在经历精神癫狂,生命夭亡的共同悲剧,苦痛与悲情照样充斥着当今社会生活,古代与现代两个不同时空呈现出极其对称的镜像结构,王妃和芭芭拉的命运交织重合。夫妻隔膜,父子冲突,生命夭亡,精神疯癫,什么都没有改变,历史循环往复,社会病态、人类异化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清晰地展现出来。“这情景显得既真实又不真实,它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它是超时代的。”《红王妃》从个人经历入手,却在全人类的层面展开生命过程的整体性描述,超越了地域、时代和文化,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德拉布尔实现了自己一贯的文学主张:“作家需要对于自我和场景的具体而特殊的感受,把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忠实地加以描绘,通过某种神秘莫测的作用,个别的变成了一般的,在个性之中反映共性。”(德拉布尔,1994:8)
同样,相距遥远的地域背景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两个不同的国度发生神秘的关联,“跟18世纪的朝鲜一样,牛津这座到处是修道院和回廊的城市同样被陈规陋习所浸淫,从古到今两地一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在小说的另一处,芭芭拉路经伦敦的加拉克斯桥,
这桥让她想起了首尔的那座人行天桥,它将思悼的秘密花园、王妃的宫殿与皇陵连在一起。这不正是几个星期、几个月来一直在她的意识深处若隐若现、却苦寻未果的那种关联么?现在她终于找到了,这桥便是关联,便是纽带。这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而这桥是她无法回避、必须跨越的。(德拉布尔,2007:233)
人物的跨文化之旅发现的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景观,而非异质的地域属性,不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彼此认同。
而故事中一再出现的红色,作为人物的个性爱好,跨越两百年的时间和空间演变成具有延续性的人类共性,如同一根延绵的红线联系起不同时代的主人公。王妃一生迷恋红裙子,故被称为“红王妃”。芭芭拉和王妃一样地热爱红装,每每为红衬衫、红袜子所吸引。连偶然出场的小说家德拉布尔也身着红色套装,并在后记中诉说关于红裙子的记忆。红色如同生命的血缘使东西方发生关联,让人类得以传承。“她的故事的确有一根贯穿的线索,那是一根红线,但她不知道这根红线会引向何处。……过去和现在,伦敦与首尔,它们有时泾渭分明有时又互相重合,但并没有融为一体。”于是,《红王妃》中的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地域相距遥远,却在历史的循环中由永恒的人性联系起来了。
芭芭拉和范乔斯特的遗孀维维卡一起领养了中国女孩陈建依,这无疑是当代人意欲展开东西方文化交流,达成历史传承的积极之举,虽然这种努力不无困难,“小小的陈建依让两个女人惶然不知所措。她们不知道该怎样和她沟通。她想要什么?想让她们怎么做?”“她们之间仿佛横亘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而小女孩的目光正越过这鸿沟,吸引着她们的注意。”芭芭拉和维维卡不由自主地为历史所驱,试图跨越地域和文化的鸿沟,“她命令她们来到她的身边,而她们响应了她的召唤。这是一个奇迹,一个谜。”时光流转,生命轮回,东渐西移,人类历史后继有人,王妃的亡灵得到告慰,因为陈建依“有着王妃的气度,肩负着王妃对未来的期盼。朝鲜王妃满意地注视着她的这位新的继承人,知道她一定不会让自己扫兴”。
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贝尔:31)德拉布尔在《红王妃》中所探讨的正是文学艺术关于生命存在之普遍意义的永恒命题。女作家将《红王妃》放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充分发挥小说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利用亡灵叙述者的超自然叙述视角,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双重叙事,在时代的更迭和文化的冲撞中抽绎出人类千古不变的共性,揭示人类共有的悲剧命运,反映人类同处的生存困境。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发生关联融合,不同时空的历史与现实形成镜相对照,分属不同时代的人物命运形成交织轮回。德拉布尔说,《红王妃》“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每个人以启示,它不只是发生在某个具体时间、地点”。(李良玉:160)在广阔的时空联系中,个体生命的私密体验揭示出人性的共通性,人物的个人命运展现出人类生存困境的普遍性。女作家深信,我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生活的世界需要我们彼此理解,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彼此理解。这就需要我们跨越文化并且明白彼此理解的可能。”(李良玉:162)当今世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类困境日趋严重,《红王妃》表现出厚重的历史之思,以及人类沟通、文化交流之愿,顺应了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给世人以警醒和启示,作品的深刻性和超越性正在于此,女作家的历史意识、现实情怀和人文精神亦尽显其中。
注释:
①见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中文版封底。文内引文皆出自杨荣鑫译本,见参考文献。为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