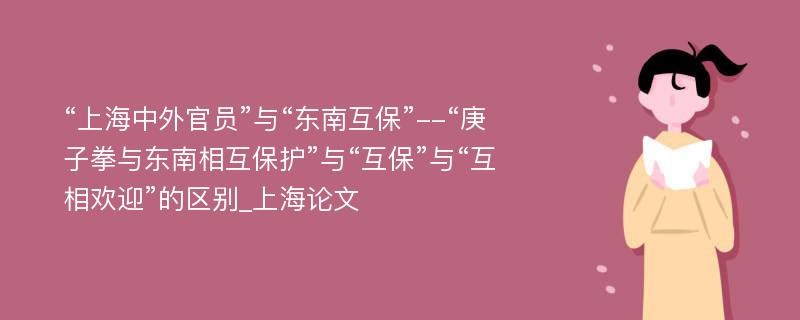
“上海中外官紳”與“東南互保”——《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箋釋及“互保”、“迎鑾”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中外论文,東南互保论文,拳禍東南互保论文,迎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紀初年,春夏之交,義和團運動迅猛崛起於中國北部,自戊戌以來日趨緊張的中外關係與地方社會愈演愈烈的民教衝突相互激蕩,釀成一場以一敵八的國際戰爭;與之同時,東南各省卻自外於戰事,與列强國家議約互保,基本維持了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和平局面。這一歷史的陰差陽錯,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國內政治與遠東國際關係的走向。幾乎所有的近代史著作,在描述“東南互保”事件時,都注意到上海是在南京、武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駐節地點——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醞釀地點,也往往强調“上海中外官紳”這樣一個羣體發揮的作用,列舉其名者有盛宣懷、余聯沅、沈瑜慶、陶森甲、湯壽潛、沈曾植、張謇、何嗣焜、福開森(John.C.Ferguson)、汪康年、趙鳳昌諸人。①這一羣體人物衆多,關係鬆散,背景也較複雜,在性質上很難給出準確定義。其中不乏在近代舞臺上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也有身後寂寂無聞(卻未必不曾煊赫一時)的歷史過客。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些在近代學術、文化、經濟領域爲人所熟知的名字,他們在歷史中本有着各自的特殊位置和人生軌迹,但卻在時空縱橫的這一具體交匯點形成罕見的交集。這就難免使人好奇:這羣人如何走到了一起,在“東南互保”事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又在何種層面上發揮了作用?多數研究已注意及此,卻少有深入探究,往往一筆帶過,這就容易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印象:好像是一羣人聚在一起召開圓桌會議,一致決定了某個重大事件,並推舉出民意代表,向更高層的官方請願。結果除了被推在前臺的盛宣懷摇曳生姿,令人印象深刻,其他人的形象都顯得模糊不清。也有一些著述,爲表彰個別人物的業績不遺餘力,樂於選擇對單方面有利的材料,一言論定功罪,不止一人被認爲對同一事件起到了決定性的關鍵作用,不論事實有否誇大,至少在邏輯上也有不通之處。如趙鳳昌所撰《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下簡稱《紀實》)一文是被廣泛引徵的文獻之一。②作爲當事人的回憶録,《紀實》勾勒了互保發起的主要線索,也提供了一些在其他類型史料中不易見的有趣細節,因此被很多研究者視爲是解釋“東南互保”起因的權威資料。不過,其中的不少説法存有訛誤,並且缺少驗證,如果孤立引用的話,仍不免有相當的風險。本文擬以《紀實》一文爲基本線索,對所涉內容略作箋釋,事關重大而語焉不詳處,將予以重點考證,《紀實》不及或其他文獻失載、誤載的若干事實,也進行扼要説明,希望在東南地方歷史變遷的背景下,探討“東南互保”事件中各色人物的行事軌迹和心路歷程,爲理解晚清歷史作一有益的注腳。
一 發自上海之倡議
(一)上海成爲風暴眼:炮臺、製造局之爭
《紀實》一文開首謂:
自五月初良鄉車站拳匪發難,京津響應,各省人心浮動,或信以爲義民,或迷其有神術。上海遠隔海洋,忽傳城內已有拳匪千人,飛渡而至,旅滬巨室紛紛遷避內地,有剛首途而被劫者。其時南北消息頓阻,各省之紛亂已日甚,各國兵艦連檣浦江,即分駛沿江海各口岸,保護僑商。英水師提督西摩擬入長江,倘外艦到後,與各地方一有衝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禍。(頁289—290)
趙鳳昌(1856—1938)久處張之洞幕府,時人謂以“張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倚之如左右手”,③可見兩人關係非同尋常,後因彈劾案牽連,遭革職處分,但仍被安排差使,在湖北電報局挂名支薪,常駐上海,充湖廣督署耳目。民國時黃炎培説過,晚清至民國“此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這位老人有關”,唐振常先生嘗引用此話,並加有按語:“其言或有誇誕,此人參與了東南半壁不少大事則是事實。”④趙鳳昌以其特殊身份及人際關係,不僅親歷近代許多重大事件,而且常扮演關鍵先生的角色。光緒二十六年(1900)策動“東南互保”,就是他在政治舞臺上一次重要的表演。前引《紀實》語扼要交代了“東南互保”發生的背景,除華北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外,外國軍艦雲集上海、有意駛赴長江口岸的動向,最爲當事人所注意。所謂“英水師提督西摩爾擬入長江”,其事不確。查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爾(E.H.Seymour)在五月中旬率聯軍由津赴京保護使館,遇清軍與義和團聯合阻擊,被迫折返,至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敗退天津租界。其後原地休整,南下赴滬時已在六月末,⑤《紀實》文中與英艦入江事相混淆。
華北局勢惡化之初,作爲在長江流域擁有最大利益,並最具政治權勢的英國表現出積極干預的姿態。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西摩爾聯軍尚在途中,英國駐上海代理總領事霍必瀾(P.L.Warren)已開始策劃避免同樣的騷亂蔓延至南方,他建議“立即與漢口及南京的總督達成一項諒解”,使當地得到英國軍艦的“有效支持”,從而在轄區內維持秩序。英國動向曾被一些研究者理解爲首倡“互保”的證據,⑥而其真實含義在於提供單方面的軍事保護,在東南督撫看來,則是暴露了外人“窺伺”的野心。這一認識成爲張之洞“自認保護”的前提,所以向劉坤一一再示意“英水師欲據長江,若我不任保護,東南大局去矣”。在事件過程中,兩人迅速達成了共識——“爲今計,惟有力任保護,穩住各國,一面添兵自守,鎮懾地方”。⑦在試探觸壁後,英國暫未在長江流域擴大干預,但最先申請軍事保護的領事當局不甘心就此收手,要求增兵的持續呼聲仍然是左右倫敦決策的重要因素,這爲後來英國繼續嘗試軍事冒險埋下伏筆。⑧
戰雲密佈、驟雨欲來之際,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口岸城市,商業繁華、華洋雜處之地,也不復昔日平靜。進入五月中,每天從天津開來的輪船都是滿員,大量避難人羣湧入上海,他們也帶來北方拳民或者神奇、或者野蠻的種種傳説,排外揭帖開始出現,各類謡言在市面上流行。很多人相信這是大亂的前兆,本地居民通過輪船、民船、車馬等方式紛紛往寧波、杭州、蘇州等地遷移,而多有半途遇劫者。⑨這即是所謂“旅滬巨室紛紛遷避內地”的實情。地方最高長官上海道余聯沅(1840—1901)⑩一面將教會人員及教民遷入城中,以防不測,一面傳諭各屬及紳董切實辦理巡防,加强地方秩序的控制。五月初三日(6月18日)起,上海知縣汪懋琨傳令每晚八時封鎖各城門,嚴禁私自啓閉。(11)這些舉措仍主要着眼於“防內”,通過“自清匪患”,安撫內外人心。
外國軍艦仍源源不斷駛入吴淞港,不久傳來大沽炮臺被奪的消息,中外之間彌漫着宣戰前夜的緊張氣氛。謡傳列强將占據吴淞炮臺和上海製造局,重蹈大沽覆轍的慘劇似乎近在眼前。上海周邊相應加强了清軍部署,駐紮吴淞炮臺的盛字五旗,一律改旗爲營,每營添足五百人,總數達到二千五百人;製造局附近駐軍也添加到七百人,另外撥隊駐江灣等處,護衛淞滬鐵路。(12)上海道余聯沅奉兩江總督札委,兼理海防營務處,獲得便宜行事調度防營的權力。(13)
租界內的外國人,也處在極度恐慌中。關於拳民的種種怪誕傳説,隨時可能演變爲羣衆的排外風潮,而清軍的調動部署,已經構成現實威脅,大沽開戰後北洋艦隊轉舵南下,似乎預示戰爭隨時可能發生。(14)在滬各國領事緊急會議,決議組織人數約四百二十名的義勇兵隊,以此加强租界自衛體制。(15)英國領事霍必瀾期待更多作爲,前述向長江派艦遭拒後,又數度出擊,先是藉口“滬上流氓欲劫製造局”,示意“願代保護”,復利用大沽交戰後緊張氣氛,渲染列强可能攻占吴淞炮臺的危險,向中方試探由英國艦隊臨時接管的可能。劉坤一對此表示,“如德、倭奪臺,盡力抵禦,若危急,再求英助”。(16)換言之,不情願將炮臺直接移交,但希望必要時與英合作,共同阻止其他列强行動。英國的單邊行爲也爲他國所反對,消息靈通的盛宣懷報告稱:
福開森面稟,各領事並無占吴淞之意。英領事要我請其保護,是其僞術。若爲所愚,各國必不服。白藻泰已將此情電法,等語。自吴淞以迄長江內地,公應飭滬道告知各國領事,自認保護,勿任干涉。(17)
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美國人,時爲南洋公學監院。(18)白藻泰(Georges G.S.Bezaure),法國駐上海總領事。英國單獨保護的做法爲各國所“不服”,盛宣懷認爲可以因勢利導,同時向各國領事承諾“自任保護”,利用列强競爭的均勢避免軍事干涉。因外部的異議聲音,劉坤一轉而表示:“英允保淞,確係詭計,已電滬道密阻。就目前惟有穩住各國,方可保全長江。”(19)這裏需區別的是,派艦入江得到了英國政府授權,而要求代管炮臺,則是霍必瀾的一次個人行爲。不過兩者都遇到了相當阻力。盛宣懷和日本駐滬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幾乎在同一時間提出了新的建議——以中外會議的方式達成和平諒解,長江流域的局勢迅速朝着“東南互保”的軌道滑行。(20)
(二)“中外官紳”之活躍
扼要介紹事件背景後,《紀實》繼謂:
憂思至再,即訪何梅生老友商之云:事已如此,若爲身家計,亦無地可避,吾輩不能不爲較明白之人,豈可一籌莫展,亦坐聽糜爛?其時各省無一建言者,予意欲與西摩商,各國兵艦勿入長江內地,在各省各埠之僑商教士,由各省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護,上海租界保護,外人任之,華界保護,華官任之;總以租界內無一華兵,租界外無一外兵,力杜衝突。雖各擔責任,而仍互相保護,東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梅生極許可,惟須有任樞紐之人,盛杏生(蓀)地位最宜,謂即往言之,並云此公必須有外人先與言,更易取信。當約一美國人同去。旋杏生(蓀)約予往晤,尚慮端、剛用事,已無中樞,今特與外人定此約,何以爲繼?予謂此層亦有辦法,可由各省督撫派候補道員來滬,隨滬道徑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公不過暫爲樞紐,非負責之人,身已淩空,後來自免關係。(頁290)
文中“何梅生”,即何嗣焜(1843—1901),(21)係趙鳳昌、盛宣懷武進同鄉,時爲南洋公學總辦。劉垣(厚生)撰《外舅何公眉孫家傳》謂“庚子事變朝命不行於京津以南,時公在上海,佐盛宣懷與各國領事交涉,立東南互保之約”。(22)趙鳳昌首先提出華、洋兩界由中外分任保護的設想,“由督撫聯合立約”,基本上已接近“東南互保”的實質內容。何與盛宣懷交密,遂推舉盛爲“任樞紐之人”,並建議約一美國人同往遊説。所謂“美國人”,即指福開森,(23)曾爲劉坤一顧問,時受聘任職南洋公學。(24)盛宣懷在事後獎敍“在滬出力華洋官紳”時稱,“庚子之變中外咸互相猜忌,雖彼此推心置腹,究未能融洽”,該洋員“疏通其間,彼此猜忌盡釋”,周旋之力居多。(25)趙鳳昌面見時提出“互保”具體辦法,由上海道出面與各國領事交涉,各省則派出代表隨同議約,盛宣懷因此“身已淩空”,地位相對超脫,故發言較易。可謂“三個老鄉一齣戲”,盛、何、趙的聚首,已發“東南互保”之先聲。
義和團運動期間,盛宣懷以督辦鐵路公司名義居留上海,他自稱“局外閑人”,事實上忙得不可開交,在剿拳、救使、阻西幸、調李鴻章督直等關節均有重要表現,當東南情勢告急,作此出位之謀並非偶然。夏東元對此頗多論述,認爲盛宣懷在庚子時的表現是其“辦大事、做高官”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一面承認其爲“東南互保”的導演者,一面强調此舉使得一貫的“反動的立場”更其鮮明。(26)更早前,臺灣學者戴玄之已提出盛宣懷首倡“東南互保”之説。(27)如果注意到當時朝局變化、國際競爭及盛宣懷與周邊人物的互動,可以發現所謂“首倡”之功很難明確歸繫於某人,這其實是由多元角力呈現的後果。即使落實到盛本人想法,在短時間內也經歷了發展過程。已如前述,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盛宣懷已向劉坤一提出“自認保護”的建議,其背景是英國要求單獨托管吴淞炮臺,引起各國反彈,因福開森的情報,盛意識到大沽開戰後列强在東南地區並無統一意志可言,托一國保護不僅於利權有損,還包含觸犯他國的風險,不如自任保護,利用各國牽制,避免軍事干涉。稍後趙、何等人的建議則使得“保護東南”的操作方式進一步明晰化,盛的思路也由“自保”向“互保”轉變。這一策略的目的,在於穩定上海秩序,預防義和團運動蔓延南方,也爲抵制外國(主要是英國)借機出兵上海及長江內地。
這不僅是趙鳳昌等少數人的想法,在當地有着巨大利益的紳商階層從自我保護的立場出發,也希望采取措施維護安定。汪康年主編的《中外日報》連篇累牘刊登社論,幾乎一日一文,要求戡亂保和,流露出濃烈的地方意識。(28)當聞知英國意欲派艦入長江護僑,汪康年本人以“此時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與各國切實訂約,使中外相安不可”,亦有“贊助上海各官紳商”倡議“互保東南”之舉。(29)供職南洋公學的張元濟,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讀報後即致書盛宣懷,以“現在事變更急,斷非尋常舉動所能挽回”,建議“似宜速與各省有識督撫聯絡,亟定大計,以維持東南大局”。(30)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輪船招商局會辦鄭觀應在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致函盛宣懷説:
頃詳報載,天津租界已爲華兵掃平,殊深焦灼……如有確音,務祈示慰。勢似瓜分,恐各國分兵踞地(如京津與西兵大戰,恐英踞吴淞炮臺,復派兵入長江內地驚擾,不堪設想)。各公司宜早籌備,刻徐雨之來談,亦擬換旗,已諄囑各董妥商後(有云不必換,有云宜緩換),稟請裁示祗遵。(31)
全電語氣流露出對中外失和可能損害利益的擔憂,所擬“換旗”之舉,即外兵一旦入據長江,將中國公司轉移至外國名下,以圖自存。可見其觀念中,保護實業利益最關緊要,對外萬不可戰,戰亦無倖免之理,在上海及長江內地中外共有利益基礎,合作大於對抗。秩序,是紳商和工廠業主第一位的要求。北方戰事雖未直接波及東南,但仍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導致市面蕭條,對和、戰前景不確定的預期,更深刻影響到上述羣體的信心。以輪船招商局爲例,自津沽失陷,與上海往來貿易停滯,所收水腳不及平時十之四五。上海錢莊平日主要依靠外國銀行短期拆放,與中小工商企業發生聯繫,此時人心浮動,紛紛收受規銀,以至市面銀根吃緊。時人記載:“滬上震驚,人心慌亂,各銀行但進勿出,各莊家周轉更爲不通,銀拆一兩五錢,現銀缺乏,洋釐頓提八錢八分,無洋可購。旅居申江者,紛紛遷移。”(32)上海商人祝大椿、沈敦和、李平書、施敬則、葉澄衷等多次找盛宣懷、余聯沅,要求地方告示安民,力保穩定,而盛宣懷本人無論在傳統典當、錢業方面,還是在近代性的工商企業領域,都擁有重大利益,他所控制的輪船招商局、上海電報局、華盛紡織總廠、中國通商銀行、漢冶萍公司,全部集中在長江流域,東南一旦變爲戰場,勢必動摇他多年經營的基業。(33)
無可否認,“東南互保”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確乎體現了“民情”,而出身於江南、並與紳商社會有着極深淵源的盛宣懷在其中發揮了“擔綱領銜”的作用。作爲電報事業總負責人,他在資訊傳輸中處於樞紐地位,並與李、劉、張這幾位在當時最爲重要的地方大吏均有交情,可謂最適合、並最具條件説得上話的人。與聞內情者如沈瑜慶(1858—1918)對盛氏推崇備至:“天下絕大事業,只在一二人之交驩。庚子之患,微公居此中聯絡,則粵、江、鄂鼎峙之勢不立。彼三公者平時各不相謀,而因公之故,遂相固結,以紓世難。”(34)盛宣懷本人也是當仁不讓,自謂:“保護東南,非我策畫,難免生靈塗炭。”(35)及盛氏逝世後,陳夔龍所作神道碑文稱:“拳亂作,疆吏定東南互保約,隱微匡救,多本公謀。”孫寶琦爲《愚齋存稿》作序,亦加推許謂:“公在上海,實總其樞紐,國不遽覆,公之力也。”(36)
在“東南互保”的形成過程中間,盛宣懷周邊的部屬、幕僚、紳商的作用當然不容忽視。(37)其事先與日本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的密商同樣值得注意,而最後促使他作出決斷,則緣於朝局的突然變化。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盛宣懷分別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明確提出中外互保的辦法:
濟沁電萬勿聲張。滬各領事接津電:津租界炮毁,洋人死甚衆。英提帶兵千餘殁於路,已各處催兵,看來俄日陸軍必先集,指顧必糜爛,如欲圖補救,須趁未奉旨之先,峴帥、香帥會同電飭地方官上海道與各領事訂約,上海租界准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均歸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商民人命產業爲主。一面責成文武彈壓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懲,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壞,留東南三大帥以救社稷蒼生,似非從權不可,若一拘泥,不僅東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難。(38)
他意識到總理衙門照會公使離京,預示中外即將決裂,一旦外兵集結,可能造成全局崩壞。事急之下,東南三大帥對朝旨“從權”取捨,“留東南以救社稷蒼生”因之具有充分的政治正確性。就在同一天,小田切領事也分別向劉、張去電,基調與盛一致,內容略有區別,不僅授權上海道與各國領事直接交涉,而且提議由江、鄂分派代表赴滬與議。(39)
“東南互保”的倡議最終得到積極迴響,但考諸事實,劉坤一、張之洞皆未在第一時間覆電答應,其最終決策經過了極爲慎重的考量。(40)當時往返於滬寧之間的沈瑜慶、張謇諸人,以及圍繞劉、張周邊的湯壽潛、施炳燮、陳三立、沈曾植等幕僚,聯袂出場,皆有表現,他們對於江、鄂總督均做過遊説,事迹零星見於史册,而遊説活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幕主的決策,至今尚難精確定論。
二 遊説劉、張諸情節
(一)滬寧之間——沈瑜慶事迹鈎沉
交代趙、何、盛等人在滬會商“互保”事後,《紀實》謂:
即定議由其分電沿江海各督撫,最要在劉、張兩督。劉電去未復(覆),予爲約沈愛滄赴寧,再爲陳説。旋得各省復(覆)電派員來滬。盛即擬約八條,予爲酌改,並爲加漢口租界及各口岸兩條,共成十條,並迅定中外會議簽約之日。(頁290)
江、鄂兩處接盛電後,各自反應稍異,比對覆電時間,張之洞次日即覆允,而劉坤一則幾乎拖了兩天時間,(41)與文中“劉電去未復”情形正合。所謂“予爲約沈愛滄赴寧”一節,是指趙鳳昌出面,特別聯絡沈瑜慶,約其代爲勸劉的故事。(42)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保留了一段掌故,記趙鳳昌口述此事,描述頗爲生動:
老人爲予言,是日爲六月某日,爲星期六,時由滬赴寧必以輪船,星期例停開,濤園方以道員在峴莊幕府,詗其回滬宴集,亟走訪之,尚記座客有陳敬餘(季同),(43)以人多不敢言,捉衣令著,納車次,熱甚,汗如洗,默無一語,到盛處,始詳言之,即請下船詣南京勸劉。至濤園如何促峴莊,雖不能知,要其在幕府有大功則不妄也。(頁293)
沈瑜慶爲沈葆楨子,以江南候補道先後委辦江南水師學堂、宜昌鹽釐局,甲午戰時佐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籌辦防局營務處,劉坤一回任兩江後,繼續在江蘇留用,爲劉幕重要成員之一。翁同龢曾予評價:“識略極好,且有斷制,不愧爲沈文肅之子。”(44)時以道員督辦吴淞清丈工程局。其人工詩,當時與滬上官紳文士多所酬唱,並常常往返於滬寧之間。
趙、盛約沈勸劉,文中作“六月某日”,查照《愚齋存稿》,實際發生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約去電建議“東南互保”稍後,盛宣懷復致電劉坤一如下:
靄蒼今晚赴寧,請速定東南大計。(45)
沈瑜慶乘坐當晚輪船赴寧,據張謇日記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條:“藹蒼來,議保護東南事,屬理卿致此意。”(46)可證其到達南京後,偕同劉幕中人就“東南互保”事展開遊説。稍後,又被派爲兩江代表回滬參加會議,與領事商訂保約。(47)沈子成式作《沈敬裕公年譜》,對譜主在庚子年的事迹也有記述:
五月,拳匪亂作,北方糜爛。公與武進盛愚齋宮保宣懷以東南半壁,華洋雜處,萬一有變,鹽梟土匪,藉以爲機,全局不堪設想,宜與外人訂約,租界內地,各擔責任,俾宵小不得滋事,東南乂安,足以補救西北。遂電武昌,並入寧面陳,於是東南互保之約成。又代表忠誠蒞滬與各國領事定盟。(48)
《濤園集》有壽新寧宮保兩絕句,其一云:“平戎仲父憂王室,薦士梁公感舊京。痛定若思茂陵策,故應險絕念平生。”即詠“東南互保”事,後兩句可見當時劉坤一尚有猶疑,而沈力勸,故謂“險絕”。陳三立所撰《沈敬裕公墓誌銘》稱:“拳匪亂,東南互保之約成,公首奔走預其議,補淮揚海兵備道,護漕督。”(49)沈得授淮揚海道,如詩中所謂“薦士梁公感舊京”,可證其言之甚力,故劉“感激而力保之”。③當年嚴復由天津避禍南下,與沈瑜慶會於滬上,後作贈詩,其自注云“庚子東南互保之約,君實發其議”,(50)亦多推許之情。
此外,沈瑜慶對“東南互保”的貢獻另有一端,多不爲人知,即勸囑劉坤一收容避戰南下的北洋艦隊,避免加深當時中外間業已嚴重的相互不信任。北洋海軍没有參加大沽之戰。戰爭發生時,主力艦隊正在山東登州、廟島一帶操巡。大沽炮臺失陷後,北洋艦隊失掉了統帥,而朝廷意向不明,下一步如何行動成爲了懸念。爲躲避聯軍鋒芒,山東巡撫袁世凱竭力促其由黃海海面南下,於是海軍主力由“海天”艦管帶劉冠雄、“海琛”艦管帶林穎啓帶隊,轉舵駛往上海。北洋海軍此行本意在於避戰,但抵泊吴淞港後,卻造成一個意外的後果——上海租界僑民視此爲戰爭信號,引發集體恐慌。(51)日本總領事小田切就抓住了這一動向,以此作爲動員本國派兵的理由。(52)正在上海籌議“東南互保”的盛宣懷等人也明顯感受到壓力,他向劉坤一去電稱:
北洋各兵輪來言,接余道照會,各領事商囑移泊吴淞口外,以免洋商誤會。沈道則請駐江陰,又恐鑑帥在江陰飭炮臺放炮,則兵輪必危。擬請電余道明告領事,斷無他意,如必欲移泊淞外,亦無不可。(53)
各國領事認爲停泊本港的北洋艦隊,距離租界咫尺之遥,因此深感威脅,他們通過上海道余聯沅要求各艦駛離上海,或移泊較遠洋面。“沈道”,即沈瑜慶,其意見更爲直接,請將北洋各艦轉移至江陰駐泊。“鑑帥”,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1830—1900),字鑑堂,時駐蘇州,因外國軍艦入江,計畫赴江陰以武力拒阻。查沈瑜慶生平,與海軍頗有淵源,其父沈葆楨即爲南洋水師的創辦人。其本人在甲午戰時任職兩江營務處,曾爲張之洞獻策,收留戰敗南逃的水師將官。陳三立因此對其“兩收海軍餘燼,稍保聚於南紀”的功績大加褒揚。(54)《沈敬裕公年譜》録有庚子年沈瑜慶致劉坤一的一封電報,透露了北洋艦隊南下一行的許多細節,文録下:
據海琛管帶林參將穎啓面稱,在煙臺途次奉東撫袁三次電云,大沽炮臺已與各國開釁,屬兵船速南行等語。該管帶遵即到廟島,與薩幫統鎮冰商酌,薩因廟島之美教士懇留保護,一時不能遽來,飭海琛、海籌、飛鷹、復濟、通濟先行南下。海琛、通濟本日已進口,泊下海浦。海天到吴淞,海籌、飛鷹、復濟明日可到。統領葉鎮駐海容,船在大沽,英國水師隊中各國兵輪,問此船係團匪抑係官兵,葉告以係中國國家水師。答云既係國家水師,當不助團匪,請照常停泊。惟三雷艇在大沽口內因昇火裝雷,爲英水師所拘,尚有一雷艇並飛霆獵船,在船塢爲俄人所據。此次我兵輪在海上遇各國兵輪,不認失和,彼亦未以失和相待。該管帶等以北洋電已不通,東撫又促南來,伊等無所秉承。此數船所值不貲,本日此間又有據炮臺及製造局之謡,愚見不如飭令駐紮江陰,以壯南洋門户,可收將來之用。京畿亂未定,各省司關應解京餉,應飭一律截留,勿爲盗賫。開平煤礦被據,煤源將竭,船無煤不行,應飭支應所及早儲備。事機間不容變,請公與香帥合力主持飭遵。職道本擬趨轅面陳,因滬上多謡,候示進止。職道瑜慶禀。宥。(55)
該電韻目作“宥”,知發電日期應爲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南下軍艦包括“海籌”、“海琛”、“海天”、“復濟”、“通濟”、“飛鷹”等六艘,其中三艘在當天已經抵滬,沈瑜慶建議由江、鄂飭令北洋艦隊轉駐江陰,這出於保存海軍實力的考量,同時也注意到當時流行的“據炮臺及製造局之謡”。至二十七日,北洋艦隻已全數抵滬,沈瑜慶再次呼籲:“現存各船不足禦各國,靖匪則願竭其力。團匪召外釁、殺無辜,得罪天下。可否佈告各國:請暫作壁上觀,中國水師情甘剿匪。如果不效,再請協助剿匪。即所以自解於各國也。”(56)
劉坤一依議而行,調北洋艦隊駛離上海,加入“東南互保”行列,這也得到租界當局的歡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日本領事小田切万壽之助向外務省報告説:
劉坤一已下令目前碇泊本港之北洋艦隊向江陰轉移。此一措施大獲本地民衆贊賞。(57)
除上述六艦外,不久北洋水師幫統薩鎮冰也率“海圻”艦南下,一并開往江陰駐泊,加入“東南互保”的行列。有研究者認爲,“就海軍而言,這是它第一次不執行朝廷命令,在某些實力人物支持下,擅自行動”。(58)劉坤一入奏“覆陳籌辦防務情形摺”,提及“一面調集各項兵輪、雷艇、蚊船,暨北洋駛來之海圻、海籌、海琛、海天、復濟、通濟、飛鷹七兵艦,分泊江陰等處,俾收水路夾擊之效”。(59)在這裏,他是把北洋水師的臨時安頓當作佈置江海要隘防務的業績來敍説的,當然隱去了迫於壓力而爲之的內情。這一性質模糊的行爲當時部分化解了外人的質疑聲音,爲“東南互保”的成功增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籌碼,事後也得到了朝廷默認。盛宣懷出奏獎敍“在滬出力華洋官紳”,沈瑜慶亦赫然在其列,保奏語云:“吴淞爲上海門戶,彼時各國兵輪於吴淞口外鱗次櫛比,兵輪水手不時登陸,該員聯絡邦交,措置得宜”。(60)
(二)劉、張周邊:幕僚表現
劉坤一、張之洞最終定議“互保”,多經曲折,而周邊環繞陳説者不乏其人。史書記録各自偏重,莫衷一是,或張冠李戴,難作對證,因此有必要一一列舉,稍作釐清。最爲人所熟知的勸劉主力是張謇(1853—1926)。《嗇翁自訂年譜》對此有過極具現場感的描述,引證者頗夥:
與眉孫、愛蒼、蟄先、伯嚴、施理卿炳燮議合劉、張二督保衛東南。余詣劉陳説後,其幕客有沮者。劉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雖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爲其名不足以存也;雖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爲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某客曰:“頭是姓劉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應。(61)
文中“眉孫”,即何嗣焜,沈瑜慶、施炳燮(字理卿)、湯壽潛(字蟄先)、陳三立(字伯嚴),皆劉幕賓客。此段情節繪聲繪影,交代前因後果則稍顯簡略。劉垣所撰《張謇傳記》據此濃墨重筆大加發揮,稱盛宣懷爲難之際,何嗣焜舉出兩人,“請張謇説服劉坤一,趙鳳昌説服張之洞”,並以急電將張謇由南通召至上海。又據上引《年譜》條文,進而解釋“此條係張謇與何、沈、湯、陳、施五人在上海共同決議之意見,而由張謇一人至寧説服劉坤一也”。(62)其後張謇於滬寧之間兩次往返、兩次面説劉坤一,至於遊説情景,傳記亦有大段對話式的詳細描述。
劉垣係張謇忘年交,一生過從甚密,但庚子時尚未侍事張謇近旁,所記並非親見,只是糅合了張謇自述年譜和其他一些耳食的傳聞,或有心爲傳主飾美,筆下不免虛構成分。也有學者不以爲然,相信劉、張自主決斷,所謂“説服”云云本係烏有,是“劉厚生的誇張”。(63)不管有無承認張謇遊説之功,兩方面的説法其實都忽略了一個前提,細考史實可以發現,當時張謇本人正在南京。
據張謇日記,五月十九日(6月15日)由南通啓程,次日抵南京,其後一直在當地活動,直至六月初四日(6月30日)離寧赴滬。(64)“東南互保”議論出臺前,張謇已在考慮如何應對時變,充任劉坤一的謀士。前一時期的主要活動,是勸説幕主招撫長江鹽梟徐寶山。(65)章開沅指出“張謇把招撫徐寶山看作是與帝國主義達成‘互保’協定的前提條件”,所謂“外應”就是策劃“東南互保”。(66)查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張謇日記有“北信益警”語,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記録空缺,二十九日(6月25日)記“藹蒼來,議保護東南事,屬理卿致此意”。日記空缺的數天,正是盛宣懷等在滬醞釀“互保”、向江、鄂去電建議的時間。如前引《張謇傳記》所述,短短數日內張謇奔走南通、上海、南京多處,兩度遊説劉坤一(行程記載並無明確繫日),不僅就當時交通條件而言,是個絕大難題,證之於日記,張謇之行也不可能由南通始,其間有無離開過南京仍然懸疑。(67)由於史料缺失,張謇是否到過上海難以確論,他與盛宣懷有無直接聯絡也無據可尋。考慮到張、何係至交,通款殷勤,最有可能通過此管道得到盛的授意。(68)由滬返寧的沈瑜慶也奉有使命,帶來最新消息。可以肯定在五月二十九日,即劉坤一覆電同意“東南互保”當天,張謇正在南京,並做過遊説。此外,同在劉身邊的施炳燮、湯壽潛、陳三立等人也發揮了一定作用。所謂上述諸人在上海“共同決議”一説,顯係錯誤。歷史上並不存在這樣的“碰頭會”,各人只在當時所處位置上,爲贊助“東南互保”各出了一份力。
陳三立(1859—1937),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原任吏部主事,是維新變法的活躍人物。因政變株連,與其父同遭罷職,歸鄉息居。庚子年初,移家南京。(69)其與劉坤一往來頻繁,雖未正式入劉幕,但對時事多有建言。劉坤一逝後,曾作《祭劉忠誠公文》,彰揚劉在戊戌、庚子兩大事變中所立功業。文中將庚子肇亂者喻作“蛇龍之孽”,下筆辛辣,可見對那拉氏主持之北方政府的反感,而劉坤一對內“馭控”、對外“旋斡”的手段,則爲其所激賞。(70)下文還將敍及。陳三立矚望劉坤一者遠不止於此,在當時並未能完全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湯壽潛(1856—1917)與劉坤一並非舊識,只是在庚子年臨時參與了劉幕活動。(71)鄉人馬一浮爲其作傳謂:“及庚子拳亂,召八國之師,國之不亡者,僅君往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定東南互保之約,所全者甚大,其謀實發於君。”(72)文章指明傳主謀畫“互保”的形迹,確是鮮爲人知的事實,但徑推爲首倡者,表彰太過。考湯壽潛入劉幕事實,乃出於盛宣懷直接推薦。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盛致電劉坤一謂:
時局至此,公砥柱東南,統籌軍國,須得忠亮宏達之士參謀左右,前青陽知縣湯壽潛其人也。此君現在滬,公以爲然,當代敦勸來寧。其人之詳可問季直殿撰,乞裁示。(73)
“季直殿撰”,即張謇,與湯素相善。(74)劉坤一很快表示接納,覆電推許“湯君著作頗富,久聞其名”,請儘快赴寧。(75)除擔負遊説之命,湯壽潛在南京還有其他表現。本年初李秉衡奉命巡閱長江水師,時赴江陰炮臺,欲以武力拒阻英艦。趙鳳昌《紀實》文稱:“李秉衡素偏執,不達外情,其時奉調北上,欲巡閱沿江炮臺,江督劉慮其貿然與長江外艦開釁,密飭臺官預將各炮炮閂取去,杜其逞憤。”(頁291)其記聞近謔。按,劉坤一聞警後電商張之洞會奏,“請飭李毋得干預防務,以一事權而免貽誤”,意在削奪李干預防務之權,可見其聯手應變之志。(76)湯、張、陳等人聚商,有意勸李以“安危至計”,免蹈北方政府之覆轍,也可視作落實“東南互保”的一環。北行追説李秉衡,時間應在六月初三日(6月29日),其時李已由江陰北上,湯追説未及,隨後即返上海。(77)湯在南京停留時間很短,前後不超過十天。(78)但他加入劉幕應該説是有備而往,表現也是不辱使命。張一麐《古紅梅閣筆記》言:“時東南數省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盛宣懷與外人定保護南數省商教章程、保護上海章程,得以無事。奔走其間者爲湯壽潛,文稿多出其手。”(79)更有論者將他在庚子年的事迹,與其生平最爲輝煌的領導浙江保路風潮相提並論,以爲“當時湯壽潛見識,雖不高於南中他人,而其任奔走,爲説客,較他人爲烈”。(80)
施炳燮以監生隨辦洋務,久居劉幕,以主持水師學堂得力,屢受嘉獎,可謂最受劉倚重的洋務幹將之一。區別於其他幾位幕僚,或有科名家世的背景,或有文學撰述的特長,施可謂典型的“紹興師爺”,純以實幹起家,勤於任事而嚴守職分,因此深得幕主信任。(81)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回憶,魯迅考入南京水師學堂時,有一位“專辦洋務的施師爺”,即指施炳燮,説他“一直在兩江總督衙門裏,東家換了,這位西席總是不動的”。(82)諳熟文案事務、後以整理張之洞檔案聞命的許同莘,曾從施氏習幕府事,對其有很高評價:“會稽施理卿先生在幕府數十年,南洋交涉之事,一手擘畫,不習洋文,而條約章程,研究獨爲透徹。……劉忠誠以庚子保護東南,辛丑參與和議,壬寅、癸卯會議商約,其文筆議論,推勘入微,六通四辟,大率先生稿也。我經江海,僅見此人。”(83)事過經年,施炳燮去世後,張謇作挽詞悼念,仍不忘表彰其功:
光緒庚子拳匪之亂,東南互保議,倡於江南,兩湖應焉。歐人稱劉總督臨大事有斷,如鐵塔然,雖不可登眺,而巍巍屹立,不容褻視,亦人物也。施君佐劉幕久,是役助余爲劉決策,尤有功,亦爲兩湖總督張公所重。(84)
論史者多謂劉坤一其人氣質平庸,而晚年在政治上卻屢有非凡表現,有人懷疑其才非過人,謀略當不及至此,故作評論“劉峴莊後半世,手眼名聲,俱稍勝者,聞皆幕僚之力”。(85)合上觀之,就劉坤一定計“互保”而論,“幕府有大功”之説應爲事實之一面。
至於張之洞方面,同樣不乏異説。前揭《張謇傳記》述何焜嗣之言,“可請張謇説服劉坤一,趙鳳昌説服張之洞”,又稱趙“一諾無辭”,嗣後得張覆電“即派辜鴻銘到上海辦理此事”。(86)趙鳳昌與武昌督署函電暢通,應屬事實。《紀實》又稱:“予即每日到盛寶源祥宅中,渠定一室爲辦事處,此室只五人准入,盛及何梅生、顧緝庭、楊彝卿與予五人,負責接收京津各電報消息,有關係者,勿稍洩露,共籌應付,此即創議東南互保成立之事實也。”(頁291)“寶源祥”,盛宣懷辦公之處,其地在上海租界外灘,即民國時期之客利飯店。顧緝庭,即顧肇熙(1841—1910),江蘇吴縣人,曾署臺灣布政使,時爲招商局總辦。楊彝卿,浙江人,時被派爲浙江省代表,仿江、鄂辦法在滬參加中外會議。(87)關於其人“説服”張之洞一節,則無由證明,至於親身赴漢面説,絕無此事。徵諸《紀實》,對相關情節毫無所述,該文意在自我表彰,事涉重要而故意遺漏,似不可能。而辜鴻銘奉派至上海辦理外交之説,應屬無稽,一則張正式派滬與議的代表爲陶森甲,且此舉係謀定而後動,時已在定計“互保”之後;(88)二則辜鴻銘當時只是督署一洋文案,專務隨同翻譯,按其身份、地位不足以擔當外交代表。(89)
沈曾植(1850—1922)是另一個屢被提及的人物。據劉垣《張謇傳記》:“之洞當初頗遲疑不決,遂由張謇、沈瑜慶等公請沈曾植到武昌向之洞面陳。”(90)王爾敏前揭文説,上海各官紳議定辦法後,“武昌方面由沈曾植前往陳説”。(91)其説未注出處,大約來源自劉書。沈曾植行迹究竟如何?據王蘧常所撰《沈寐叟年譜》稱:
五月,自里北征,而輦轂拳亂卒作,公停於上海主沈濤園,痛北事不可救,以長江爲慮,與督辦商務大臣盛杏蓀、沈濤園、汪穰卿密商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決大計於兩江總督劉峴莊,來往於武昌,就議於兩湖總督張香濤,而兩廣總督李少荃實主其成,訂東南互保約款凡九條,其後大局轉危爲安,乘輿重返,公之力爲多。(92)
按此年譜,“互保”發軔之際沈瑜慶正在上海,後奔走於南京、武昌兩地,多有建言。據鄭孝胥日記,本年五月十二日(6月8日)沈由揚州抵武昌,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離鄂赴滬,六月復返揚州。(93)其在張幕任事爲時短暫,在滬與沈、盛、汪等人交密,與議“互保”,或於五月末往返寧、鄂處,爲促成兩總督定議助力。《年譜》引述盛宣懷語,謂“峴帥意識堅定,香帥則志尚遊移,非子培爲香濤所素服,猶未能速決也”。(94)
此外,鄭孝胥(1860—1938)、岑春蓂(1860—1944)、(95)梁敦彥(1857—1924)、(96)汪鳳瀛(1854—1925)(97)等人,皆爲張之洞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或參謀。張氏接盛宣懷來電後,於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晚連發數電,均與定計“互保”相關。鄭孝胥時爲蘆漢鐵路南段總辦,客張之洞幕府,復按當天日記:“夜,復入督署,商擬數電,至三點半乃出。”(98)可旁證張之洞就“互保”事與親信幕僚商議,並連夜覆電的情形。次日,又派鄭、岑、梁等人分赴日、英、美三國領事館,宣佈中外保護之決意,欲先取得各國諒解。(99)
綜上,江、鄂決策“東南互保”之曲折過程,大略如此。
三 出位之思:“互保”、“迎鑾”辨
《嗇翁自訂年譜》記庚子五月事言:
藹蒼至寧,與議保衛東南。陳伯嚴三立與議迎鑾南下。(100)
前者即指地方保護之倡議,已詳前文,後者則拈出另一重要題目,“迎鑾南下”已入勤王運動範圍。劉厚生謂:“當初張謇與何嗣焜、陳三立、沈瑜慶、湯壽潛、施炳燮六人,決定拉攏劉坤一、張之洞兩個總督,聯合起來以東南互保爲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權爲最大目標。”(101)按此解説,“東南互保”似僅爲手段之一端,而最終指向則在解決帝后政爭之大問題。從戊戌到庚子,一系列政治風波前後相繼,論者多已注意到朝野勢力分化組合,對北方拳變、東南互保和勤王運動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予以特別强調。如果不把“勤王”作偏狹的理解,這一運動與“東南互保”實有錯綜複雜的連帶關係。在庚子語境中“勤王”應該是一個複詞。現下引用最多、論證最詳者,係指以與當時朝廷對立的康、梁爲領袖,以民間力量爲重心的“勤王舉義”。(102)其實,在戰時應朝廷之召,地方各省督撫派兵入衛京師,立意與前者相反,而名稱同樣號爲“勤王”。更有甚者,意欲借用地方勤王之師,專爲成全“助(光緒)帝復辟”之謀,在這裏兩種意義上的“勤王”實已合二爲一。上述張謇、陳三立所謂“迎鑾南下”之議,也應在這一層面上進行解釋。查張謇日記,五月三十日(6月26日),即中外會議“互保”當天,有如下記載:
與伯嚴議易西而南事。江以杜雲秋爲營務處,鄂以鄭蘇龕爲營務處,北上。(103)
“杜雲秋”,杜俞(1854—1916),時以候補道統帶江南防營。“鄭蘇龕”,鄭孝胥,時爲蘆漢鐵路南段總辦,湖北鐵路護軍營歸其總制調遣。(104)當時北京形勢告急,已出現宮廷西遷的各路傳聞。資訊靈通的盛宣懷從蛛絲馬迹最早嗅出形勢不妙。(105)劉坤一對“西遷説”則全然不抱樂觀,以爲此事果確,則全局瓦解。(106)張謇、陳三立等人惟恐那拉氏挾持光緒帝遷逃內地,與政治保守勢力合流,故有密議“易西而南事”,迎帝南下的力量則欲借重江、鄂北上勤王之師,而設想與彼輩政治意識接近的鄭孝胥等人督辦營務,也是爲操縱軍事、便宜行事做有利於己的安排。
接奉勤王之旨後,劉坤一欲將李秉衡調離北上,(107)後者隨即渡江,由揚州動身。(108)復按張謇日記六月初二日(6月28日)條:“與伯嚴定蟄先追謁李帥,陳安危至計。”即前述湯壽潛追説李秉衡事,出於張、陳合謀,所謂“安危至計”,極可能與“迎鑾南下”相關,儘管李本人“勤王”志殷,其北上一行客觀上卻被寄予多重希望,因追趕失時,終於遊説不及。至於兩湖方面,張之洞固不乏“入衛之忱”,但慮及地方,訴諸行動時已多虛應故事的成分。時人鄒代鈞觀察到:“鄂寧雖允保東南,以我觀之,都係空言搪塞,幸無蠢動,聊貪天之功耳。設有竊發,不知何以應之,又遑問其舉兵討賊耶?即入衛之兵,亦屬烏合,慮其半途散盡,不助匪爲虐,則幸甚。可笑已極。”(109)至於外人方面,亦有類似觀察,日本駐漢口領事有報告稱:
因北京政府向各省屢發詔旨,要求派兵保護京師,而各督撫也陸續遣送勤王部隊北上,若惟獨湖南、湖北不派兵隊,恐招致嫌疑。張之洞將訓練有素的護軍營及愷字營專門留用,擔當地方保護之責。派遣北上者,爲湖南新募兵五營,湖北半數爲新募兵,半數爲固有之兵,兩省合計大約五千人。湖南統帶之員爲素以頑固排外著稱的布政使錫良。張之洞有意將與義和團臭味相投的錫良調離出省。此任命頗有深意。(110)查當時劉、張的工作重心,仍在經營地方保護,對欲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甚而干預中央政局的激進建言,意態則多有保留。張謇日記透露“易西而南事”,商之於劉坤一的細節已不可考,然計畫夭折,終無下文。
又海外學者周康燮曾披露同時期陳三立致張之洞幕僚梁鼎芬的一通密札,該札作於六月十三日(7月9日),文曰:
讀報見電詞,乃知忠憤識力,猶曩日也。今危迫極矣,以一弱敵八强,縱而千古,橫而萬國,無此理勢。若不投間抵隙,題外作文,度外舉事,洞其癥結,轉其樞紐,但爲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計,形見勢絀,必歸淪胥,悔無及矣。竊意方今國脈民命,實懸於劉、張二督之舉措(劉已矣,猶冀張唱而劉可和也)。顧慮徘徊,稍覽即逝,獨居深念,詎不謂然?頃者陶觀察之説詞,龍大令之書牘,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擴充,竭令贊助。且由張以劫劉,以冀起死於萬一。精衛之填,杜鵑之血,盡於此紙,不復有云。節庵老弟密鑑。立頓首。(111)
其內容指向庚子事變時期一部分趨新士紳遊説南方大吏“題外作文、度外舉事”的情節,周康燮附跋語謂:“文中隱寓別闢蹊徑,乘勢局事,廓除障礙,以爲扭轉樞機之圖,欲謀擁帝復辟之情,盎然活躍於紙上。如此艱巨任務,惟有寄望於炙手可熱之劉坤一與張之洞。”陳三立意欲“題外作文”,原與“東南互保”係同一時期之產物,也是與張謇等人共鳴的結果,此輩中人身份相似,皆爲與東南督撫關係親近的地方士紳,而政治意識上亦有濃厚的“帝黨”色彩。(112)密札提及“陶觀察之説詞”,“龍大令之書牘”,論者多謂皆不可考,而從文脈推測,立意應與陳三立相合。“龍大令”,龍澤厚,康有爲弟子,時列名中國國會,被舉爲幹事,事敗後遭通緝。“陶觀察”,陶森甲(1854—1914),其人遊説劉坤一的情節,可據日文史料獲得線索,事詳東亞同文會上海支部會員報告書。(113)又據旁注“劉已矣,猶冀張唱而劉可和也”,陳三立、陶森甲等人應對劉坤一有過勸説,但未奏功,於是轉而向張之洞運動,試圖通過張幕要人梁鼎芬鋪路,然後“由張以劫劉”,成就勤王事業。(114)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地方督撫抱有期待者頗不乏其人。六月下旬,中國國會成立於上海,其宗旨所在:一,不認通匪矯詔之僞政府;二,聯絡外交;三,平內亂;四,保全中國自主;五,推廣中國未來之文明進化。(115)而它內部山頭林立,亦不免派系之爭,如張之洞舊屬汪康年即以“借資鄂帥”爲其政治方針的鮮明特色。(116)汪氏“贊助”中外保護之舉,已如前述,幾乎同時其人“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説上諸張孝達制軍,又至江寧托人將前説上諸劉峴莊制軍”。(117)這一動向,反映他欲在政治上有所作爲的心態,也包涵了與日本在華人士如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等密謀的潛因。(118)上述活動與“互保”的醞釀策動同時發生,彼此內容多有重合、互補之處。因此,也就不必奇怪,在當時相當數量的江南士紳眼裏,對“東南互保”本有一體兩面的觀感,順此思路再往前走遠一步或數步,確有邏輯可循。
前述張謇等人謀“迎鑾”未果,後來仍未放棄努力。據張謇日記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條:“與新寧書,請參政府速平亂匪,爲退敵迎鑾計。”(119)當時北京城破,情勢已然翻轉,“退敵迎鑾”作爲應對新局勢的方案,實則還處在原來“迎鑾北上”議論的延長線上。此外,中國國會成立時,汪康年曾潛赴南京,試圖再次説服劉坤一“舉兵入都護衛兩宮”。(120)及李鴻章奉召北上,在滬留滯觀望,汪康年、鄭觀應等滬上維新名士十四人連署陳情書,“擬請會商各督撫,速行遴派勁兵,協籌餉項,並公舉統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以布兵西道,防“賊臣謀擁兩宮西走山陝”。(121)然其説皆未見采用。後汪康年牽連於自立會起事,上書辯解稱“勾結革命黨人”、“勾通江湖中人”諸情事均係被人“污蔑”,此或爲自解之辭,但强調此前所爲“大率歸重於朝廷,致望於督撫”,則確有實迹可證。(122)
四 餘論
戊戌政變發生後,新舊異途,雙水分流之勢顯然。清廷對新黨實行雷厲風行的清算、重用滿洲貴族,張揚排外姿態,乃至掀起以廢立爲陰謀的建儲風波,這一連串動作無疑阻礙了曾寄望於中央改革的趨新人士再建信心,而北京政府近於倒行逆施的形象也嚴重戕損自身合法性基礎,將越來越多人士推向自己的對立面。利用通商口岸便利的輿論條件,南方推出新的民意代表,新/舊、滿/漢、南/北、保守/改良這些畛域的分野日益被重視和宣講。及庚子事起,又有大批新學士人避亂南下,以上海爲中心的東南區域隱然爲維新運動的一大策源地。在前文排比諸多人物與事實後,我們可以發現,爲數不少的江浙滬士紳直接參與了“東南互保”的醞釀、策劃過程。這批人物或爲直接爲東南督撫服務的幕僚,或爲地位相對超脫的賦閑紳士,幾乎無一例外具有趨新取向,多數人在後來列名中國國會,如果將他們大致歸類爲新黨,似不算大誤。魯迅注意到,“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123)羅志田揭出這裏的“羣”是指士大夫,而一些封疆大吏與士人的看法相類,“互保”局面的出現,就是那些曾在清廷與太平天國之間選擇了前者的疆臣,這次卻在清廷與列强之間選擇了中立所致。(124)重要當事人張謇詩贊曰“聯盟豈第全商務,抗命方能保聖朝”,立意與地方督撫“留東南以救社稷”的初衷相當一致。(125)列名中國國會副會長的嚴復,對與聞其役的沈瑜慶亦有“一約公傳支半壁”之激賞語。(126)黃遵憲作《述聞》系列紀時詩,其第五韻詠嘆“聯盟守約連名奏,賴有維持半壁才”,(127)也是標榜“互保”之舉的明智與穩健。由地方督撫主導的“中外保護”,在江南士民紳商中得到了擁護,當面對華北的千萬義和團拳民,兩者的界限似已非常模糊,他們中的多數確可被劃入“自强變法或維新變法中的局中人或同路人”。(128)惟須稍作申論的是,東南督撫和維新士人在“互保”一點上達成暫時的共識,但在後者應對時局的設想中,“互保”僅是一折衷手段,或曰階段性方案,甚而在趨新的士紳羣體內部,對政局的總體判斷及應變的目標設定也自有分野。
檢索當時海內輿論,不以“東南互保”爲然者,一則稱爲不遵朝命,斥爲海外叛臣;一則稱爲坐視叛逆挾制朝廷,而不聲罪致討,斥爲雌伏東南作壁上觀。(129)前者與站在正統立場的清流辭氣遥相呼應,均以“君父戰於西北,臣子和於東南”之類“市恩夷狄”的行爲而不齒,大致同屬保清一線,這類批評尚不構成輿論主流。更值得注意的是後一種嚴厲的批評。事實上,這一批評恰是以承認“東南互保”爲前提,鮮明反對排外,視義和團爲“匪”,其鋒芒所向,直指清朝政府,不滿東南督撫“徒恃成約”而圖苟安,無論擁光緒復辟,或割據南方自立,這兩方面實在都比東南督撫要走得遠得多。
除言論表現,上述觀念也落實於行動。前述張謇、陳三立等人企圖策動督撫,謀“迎鑾南下”而未果,這可算是戊戌政變以後帝后黨爭之餘緒;汪康年、陶森甲遊説地方權力人物,爲“勤王”試探道路,其背後或隱或顯,已有外國勢力的推手。鄭觀應希望東南大帥在“聯絡自守疆土”之上更進一步,不僅自外於戰事,且“設一公共政府,以期聯爲一氣,爲將來與外人講和地步”。(130)即穩健平正如張元濟,亦視“剿團匪”爲當務之急,甚至有“饗勞”、“撫恤”外人以便平情辦理外交的言論。(131)如此種種,以後起標準衡之,或多可議之處,但在當時語境中卻不能劃定爲“非常”。前有研究認爲,那些活動“都起了嚴重的消極作用,無形中爲當時帝國主義列强和地方督撫間緊鑼密鼓加緊策劃的東南互保打了掩護,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東南互保順乎民心的假像”。(132)其實,這恰恰不説明“順乎民心”的一面,而體現出精英士紳與普羅大衆的觀念差異。總體而言,當時主流輿論基本不以東南督撫與北方朝廷立異爲錯,因中央政府被頑固重臣把持已不復有合法性,其不滿者恰在於主持“互保”的地方督撫獨立得不夠徹底,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133)
相當數量的趨新士紳(一度包括後趨向激烈革命的一派)的主要關懷之一,是推動以地方大吏爲主導的地方自立運動(在是否“尊王”上則又有觀念差異)。無獨有偶,1900年夏,孫中山也正謀求有力疆臣的合作,他發現因反對義和團而可能使李鴻章割斷與北京之間的聯繫,而英國人有意充當其間“誠實的掮客”。(134)孫中山的舉動多被理解爲因其一貫靈活的鬥爭策略使然,但無論如何,這對他自我塑造(並被後人繼續塑造)的始終如一的“共和革命者”形象是一個巨大的衝擊。(135)當年爲張之洞派赴日本遊學的兩湖書院學生黃興,在致其師黃紹箕的信中,雖信義和團“固猶是忠君愛國之忱”,但言下更多露出不滿,喟嘆“以一團匪之變,竟致掣動全局,此誠所不能解所不及料也”;相反,他將支撑時局的希望寄托在劉、張等東南大吏身上,謂“回首西瞻,欲東南半壁之持,其惟張香帥與劉峴帥乎”,並建議其能“聯絡各省督撫,肅清內匪,力保外商,便各國之師不入長江一步,則時事庶可爲”。(136)可見後來被定義的各種政治派別,在當時所持的觀念和行爲並未如意識形態教條那般鮮明分野,反而呈現出某種趨同性。(137)
“中國國會”基本上可視作當時背景各異而總體趨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結,地方督撫起初也基本持不置可否的默認態度,但兩者之間實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在國會內部,因近似目的而合作的各類羣體,思想往往呈現發展不同步的狀況,雖以“勤王”爲旗號示外,實則充斥觀念的歧異和競爭。汪康年等傾向於“借權”有實力的地方督撫“剿匪迎鑾”,若復辟不成則自建聯邦;而唐才常派在行動方略上主聯絡會黨武裝勤王,已爲參與議會的士紳名流所難夢見。章太炎在反滿道路上走得更遠。在義和團事起之初,曾經上書李鴻章,鼓勵“明絕僞詔、更建政府”,“示列强以藩鎮之可恃”。國會成立時,“割辮與絕”,正式選擇排滿;及自立會事敗,又寫出《分鎮匡謬》,對“借權之謀”痛下針砭,反省當初寄望於督撫的錯誤,把他們一概劃入清政府的反動陣營。(138)短短不到半年,心態如此急遽轉折,可見東南督撫在維新士人心目中地位的前後落差。
在“反對排外”一點上,一般認爲中國國會、自立會與“東南互保”宗旨相合。其實,在情勢變動下,各自的理解多有分歧,或者説也是“爲我所用”的。自立會起事之初訂立的方針是,一旦成功,“可與外人訂約,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在對外宣言中也對義和團進行了指責,聲明要“藉以驅逐排外篡奪之妄舉”。(139)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張之洞後來痛下殺手,卻將自立會引爲臂助的長江會黨與義和團籠統歸屬一類,特別强調具虛擬性質的“滋事排外”一條,借以籲求外國的諒解,而全然無視此前自立會自覺與義和團撇清關係的努力。在這裏,從既往較爲單一的分析思路出發,確實很難釐清已經打結的歷史關係,重新認識的前提,恐怕必須先將原本實體化的歷史对象分解爲若干層次,再仔細區分各層次因疊加產生的吻合與歧異。面對庚子世變中樞將倒的前景,東南督撫和維新士人羣體因應時局的宗旨和手段不乏重合處,又各有其嚴守的界限,雖持有“相類的看法”,一旦落實爲具體舉措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加以外國因素以隱蔽曲折的形式大肆滲入其中,两者之間迎拒離合、牽纏往復的情態殊堪再三體味。
注释:
①“上海中外官紳”語取自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頁151),廣義上也可包括江浙地區,如王樹槐就特別强調,作爲事件醞釀促成者的“江浙人士”所具的“機敏卓見”,見《江蘇民性與近代政治革新運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頁71。其他研究諸説對此羣體包含的人物或人數表述略有差別,歷史評價的取徑不盡相同,但大體指向仍然近似,參看王爾敏《拳變時期的南省自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13)《庚子拳亂》,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林世明《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互保運動之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大陸方面,成文較早並對史實建設貢獻最大的是王明中《義和團運動中的英國與“東南互保”》(《南京大學學報》1964年第3—4期,收入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編《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一文,儘管囿於時代不免有較重的政治批判色彩,但指出“那些買辦出身的官僚和官僚出身的買辦”奔走於武昌、南京和上海之間,“有着特殊的地位”。相對近期的論説觀感已發生變化,認爲“東南士紳包括資本家”羣體出於保護地方利益的願望而要求避戰,“近代上海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爲中外紳商的利益共同體”,參看謝俊美《“東南互保”再探討》,載中國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編《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晚清政治》(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39—240。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戊戌後士紳羣體政治意識的分野,對於與洋務派督撫密切合作的張謇、陳三立、沈曾植等人,突出强調其“帝黨骨幹”的身份特徵,參看章開沅《開拓者的足迹——張謇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15。
②趙鳳昌,字竹君,號惜陰,江蘇武進縣人。1884年入張之洞幕府,充任文案,參與機要。1893年張氏遭彈劾,以牽涉其中,被革職永不敍用,遂移居上海。1908年在上海南陽路建邸宅,命名爲“惜陰堂”,由張謇題寫匾額,辛亥革命時爲南北議和牽線人物。晚歲息影滬濱,以迄病故,撰有惜陰堂系列筆記傳世。《紀實》作爲惜陰堂筆記之一,初刊於《人文月刊》第2卷第5期(1931年),當時似未曾引起注意,後近代掌故大家黃濬訪問趙鳳昌,並將該文收入《花隨人聖盦摭憶》(1947年初版),遂漸爲世人所知。參看唐振常《半拙齋古今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56。案,本文所引《花隨人聖盦摭憶》,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以下凡引《紀實》文,皆於文後標明該書頁碼,不再另出注。
③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64,62。關於趙鳳昌生平概要,可參看陳時偉《趙鳳昌傳》,李新、孫思白等主編《民國人物傳》(7),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孔祥吉《評一代奇人趙鳳昌及其藏札》,《學術研究》2007年第7期。
④唐振常《讀史札記三則》,《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6期。
⑤《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英国「シーモール」中将搭乗ノ英艦来着ノ件》,明治三三年7月27日,外務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一·北清事変上》,東京,日本國際聯合協會,1956年,頁824。
⑥林世明《義和團事變期間東南互保運動之研究》,頁52—57。
⑦《致江寧劉撫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10),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7994;《寄張制軍、于中丞、鹿中丞、王中丞、松中丞》,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劉坤一遺集》(6),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563。
⑧其後“東南互保”交涉中,英國對於長江流域的軍事滲入仍舊是一條伏線,至同年8月英軍實現登陸上海,激起連鎖反應,德、法、日等國相繼派兵抵滬。需注意者,外交進程存在深刻的緊張關係,不僅英國方面與東南督撫進行了持續而反覆的博弈,即使在倫敦內閣和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之間,也有着針對是否出兵的觀念分歧。7月下旬西摩爾南下之行,就是英國政府尚爲登陸與否舉棋不定之際,所做的軍事實地勘察。説詳拙文《“東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軍登陸上海事件考釋》,《史林》2010年第4期。
⑨《上海地方の現狀·上海通信》,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3),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年,頁227—233。
⑩余聯沅,字晉珊,湖北孝感人。光緒三年(1877)進士,授編修,歷任河南道、四川道監察御史,禮科、吏科給事,福建鹽法道,署福建按察使,二十五年調蘇淞太道,後遷浙江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署浙江巡撫。二十七年回任湖南布政使,旋病卒。見汪光鏞輯《碑傳集三編》,《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頁1711上—下。《上海縣續志》述其事迹:“二十五年任蘇淞太道,越明年,北方拳匪亂,中外失和,通商各國調戰艦來滬濱,內地匪徒蠢動。沅稟承南洋大臣,與各國領事議定東南互保約款,飭縣嚴懲土匪,地方賴以安謐。”轉引自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彙編》(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1998年,頁657。
(11)湯志鈞主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頁548。汪懋琨,字瑶庭,山東歷城縣人,進士,以知縣簽分江蘇。1900年5月21日接印,任上海知縣。
(12)《余聯沅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王爾敏、吴倫霓霞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頁349;《劉制臺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張之洞全集》(10),頁7999。
(13)佐原篤介、浙西漚隱輯《拳匪紀事·各省防衛志》,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83),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2年,頁523。
(14)《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胡濱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61。
(15)《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各国義勇隊組織並居留地警備ニ関スル領事会議ノ決議ノ件》,明治三三年6月2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一·北清事変上》,頁790—791。
(16)《江督致鄂督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
(17)《盛宣懷寄劉峴帥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有關“東南互保”資料》,翦伯贊等編、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328。
(18)福開森,字茂生,生於加拿大,後入美籍,波士頓大學畢業,1887年以美會傳教士身份來華,先後在鎮江、南京工作,創辦南京匯文書院,任校長。1896年應盛宣懷之聘,參與創建南洋公學,翌年出任監院。福開森在華生涯與盛宣懷密不可分,後爲《愚齋存稿》作序,述及受聘南洋公學及前後交往始末。見《愚齋存稿》卷首,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13),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5年,頁44—45。
(19)《江督劉峴帥致盛宣懷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有關“東南互保”資料》,《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3),頁329。
(20)盛宣懷與小田切意見不謀而合並非偶然,事實上確曾有過密商,後者致外務省報告對此有所説明。參見《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ノ解訳ニ関スル領事会議決議ノ報告ノ件》,明治三三年6月2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一·北清事変上》,頁480。關於“東南互保”的發起原委,涉及論域較廣,擬另文專論。
(21)何嗣焜,字梅生、眉孫,江蘇武進縣人。早年以生員投身淮軍,先後爲李鴻章、張樹聲幕僚。1896年受同鄉盛宣懷所聘,赴滬籌建南洋公學,任總辦。1901年初病逝,著有《存悔齋文稿》。盛宣懷爲表彰其業績,特奏請在國史館立傳紀念。關於何氏簡要生平,可參考淩淑平《懷念先祖父何嗣焜》,《上海交大報》2006年2月27日。
(22)劉垣《外舅何公眉孫家傳》,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線普553404。
(23)王蘧常編著《沈寐叟年譜》記:“金甸丞丈云:保護長江旨議,發於英人福開森。”蘧按:“先大夫戊午三月十八日日記云:與沈乙丈小飲,席間談及拳匪事,並云劉忠誠、張文襄聯省保東南之策,實發於盛尚書宣懷,而丈亦預其謀者,不及福開森。金丈不知何據。”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37。所記將福開森誤作“英人”,但可作與聞“互保”之一旁證。“金丈”,金蓉鏡,號甸丞,浙江嘉興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善詩文。
(24)福開森在南京時期佐劉坤一辦理交涉出力頗多,深獲信任,劉因奏薦稱:“查有美國匯文書院掌教福開森,學問優裕,心氣平和,訓課諸生,成就甚衆,經歷派辦交涉事件,莫不實心相助爲理。現充南洋公學監院、江南高等學堂提調等差,亦復勤勤懇懇,勞瘁不辭。”《洋員辦事得力分別請獎片》,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劉坤一遺集》(3),頁1117。
(25)《義和團時期在滬出力華洋官紳職名摺》,光緒二十六年,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檔號:057611。
(26)夏東元《盛宣懷傳》,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9。
(27)戴玄之《盛宣懷與東南互保》,《大陸雜誌》第21卷第7期,收入《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13)《庚子拳亂》,頁177—180。
(28)劉學照《上海庚子時論中的東南意識述論》,《史林》2001年第1期。
(29)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3。前揭《沈寐叟年譜》亦有“公痛北事不可捄,以長江爲慮,與督辦商務大臣盛杏蓀(宣懷)、沈濤園(瑜慶)、汪穰卿(康年)密商中外互保之策”之語,可資參證。
(30)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34。
(31)《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80。徐雨之,徐潤(1838—1911),前招商局會辦。
(32)周憬自編《惜分陰軒主人述略》,民國九年(1920)無錫周氏排印本,轉引自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60。
(33)參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晚清政治》(3),頁239—240。
(34)《沈瑜慶致盛宣懷函十二》,王爾敏、吴倫霓霞合編《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中),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頁1403。
(35)《致呂蟄盦函》,1912年7月11日,轉引自夏東元《盛宣懷傳》,頁286。
(36)《愚齋存稿》卷首,頁4,46。
(37)據盛宣懷保奏庚子事變期間在滬出力華洋官紳名單,包括:蘇淞太兵道余聯沅、總辦江南製造總局江蘇存記道潘學祖、上海商務公所總董候選道嚴信厚、前辦吴淞清丈會丈局現任淮揚海兵備道沈瑜慶、督辦淞滬釐捐總局江蘇候補道錢志澄、辦理江南商務局江蘇候補道劉世珩、辦理吴淞開埠工程局江蘇候補道何福海、前辦上海文報局江蘇候補道黃承乙、廣東雷瓊道楊文駿、總辦上海招商總局前福建臺灣道顧肇熙、總辦上海招商總局候選道鄭觀應、總辦上海電報總局河南候補道楊廷杲、仁濟善堂總董直隸候補道施則敬、三品頂戴南洋隨員福開森、三品頂戴南洋正律法官擔文、南洋副律法官候選道羅貞意、上海道署英文翻譯官候選知府鳳儀、上海道署法文翻譯官萬鍾元、統領吴淞盛字全軍浙江處州鎮總鎮班廣盛、提標右營參將廖得勝、管帶督標奇兵右營候補遊擊羅楚材、管帶撫標滬軍營候補副將龍鎮國、管帶提標副中營水師候補遊擊劉吉祥、前辦製造局文案兼辦炮隊兩營文案指分江蘇試用府經歷吴彭年,總計二十四人。《義和團時期在滬出力華洋官紳職名摺》,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檔號:057611。
(38)《寄李中堂、劉峴帥、張香帥電》(《愚齋存稿》卷三六,頁844)原注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研究著作多據此展開論述。此日期實係誤植,查該電韻目爲“沁”,《張之洞全集》(10),頁8028;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70,發電時間應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日本學者藤岡喜久男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参見氏著《張謇と辛亥革命》,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1985年,頁97。另需说明的一點是,上諭以“六百里加緊”經驛路傳遞,五月二十七日送抵濟南,袁世凱以電訊通報大意,而長江以南省份尚未正式接旨,故盛電中有“須趁未奉旨之先”之語。
(39)《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ノ解訳ニ関スル領事会議決議ノ報告ノ件》,明治三三年6月2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一·北清事変上》,頁480。
(40)在南京的劉坤一和在武昌的張之洞分別於五月二十八日辰刻(午前8時)和巳刻(10時)後接盛宣懷來電。《張之洞全集》(10),頁8028,8029。小田切電報於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下午7時由上海發,到達南京和武昌的時間約在當晚至次日淩晨間。張於二十八日亥刻(晚10時至12時)覆電同意“互保”事。《張之洞全集》(10),頁8029。劉坤一覆電較前者爲晚,遲至次日(6月25日)纔覆電贊同,其間曾去電張之洞徵詢意見。《張之洞全集》(10),頁8029;《愚齋存稿》卷三六,頁845。
(41)《致江寧劉制臺、上海盛京堂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10),頁8029;《劉峴帥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愚齋存稿》卷三六,頁845。
(42)沈瑜慶,字藹蒼、愛滄,號濤園,謚敬裕,福建侯官縣人,前兩江總督沈葆楨第四子。由附生恩賞主事,簽分刑部,光緒乙酉科(1885)舉人。光緒十七年(1891)捐升道員,指分江蘇試用,二十六年經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奏補淮揚道,次年奉旨護理漕督。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8),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75。
(43)陳季同(1851—1907),福建侯官人,曾任駐德、法等國參贊,旅居歐洲多年。歸國後留北洋辦理洋務。義和團事起,與汪康年等人呼應,上書劉坤一:“爲今計,南方數省,建議中立,先免兵禍,隱以餘力助北方,庶幾有濟。”參看桑兵《陳季同述論》,《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4)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5),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911。
(45)《愚齋存稿》卷九四,補遺七四,頁17。
(46)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編《張謇全集》(6),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435。
(47)《復張制軍》,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劉坤一遺集》(3),頁2567。沈瑜慶參與議約的具體活動,主要在於秉承江、鄂意旨,在約款中强調限制外艦入江的意思。事見《陶榘林森甲、沈靄蒼瑜慶兩觀察致南京、武昌兩督署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愚齋存稿》卷三六,頁854。
(48)沈成式《沈敬裕公年譜》,載福建省文史研究院整理《濤園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62—163。
(49)陳三立《詔授光祿大夫貴州巡撫沈敬裕公墓誌銘》,《散原精舍詩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978。
(50)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頁293。
(51)王栻主編《嚴復集》(2),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63。
(52)《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領事会ノ遣艦請求決議並我遣艦禀請事情報告ノ件》,明治三三年6月22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一·北清事変上》,頁791—792。
(53)《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北洋水師ノ来港ニ当リ軍艦急派方禀請ノ件》,6月2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一·北清事変上》,頁793。
(54)《盛宣懷上劉坤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頁398。
(55)陳三立《沈敬裕公墓誌銘》,《散原精舍詩文集》(下),頁978。
(56)沈成式《沈敬裕公年譜》,載《濤園集》,頁163。
(57)《沈瑜慶、陶森甲致劉坤一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檔號:045984。
(58)《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北洋艦隊ヲ江陰ニ出向方發令ノ件》,明治三三年6月25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二·北清事変中》,頁202。
(59)姜濤《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頁481。
(60)《覆陳籌辦防務情形摺》,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劉坤一遺集》(6),頁1220。
(61)《義和團時期在滬出力華洋官紳職名摺》,光緒二十六年,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檔號:057611。
(62)《張謇全集》(6),頁861。
(63)劉垣《張謇傳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頁93—94,187—188。劉垣(1873—?),字厚生,江蘇武進縣人。何焜嗣之婿,長期佐張謇從事實業、政治活動。
(64)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頁153。
(65)《張謇全集》(6),頁436。
(66)《爲招撫徐寶山致劉督部函》,《張謇全集》(1),頁46。原函未署日期,查照張謇日記五月二十四日條記:“上新寧書,論招撫宜開誠佈公,昭示威信,不可使疑,不可使玩。”《張謇全集》(1),頁437。此函呈遞時間即在當日(6月20日)。
(67)章開沅《開拓者的足迹——張謇傳稿》,頁117—118。
(68)藤岡喜久男以《張謇傳記》爲信史,據此與張謇日記對照,排列出活動日程表:6月21日或22日,何、盛“商量”,招張謇由南通赴滬;6月22日,即張至滬,與何商量赴南京説劉;6月23日,第一次遊説劉,劉仍猶疑,張“當晚即回上海”;6月24日,“到上海的第二天”,劉召張再赴南京,“當晚啓行至南京”,作第二次遊説;6月25日,劉覆電盛。《张謇と辛亥革命》,頁246。藤岡以事涉敏感,張謇事後故意将6月22—24日日記删去。此表最大問題在於誤認張謇在南通應召赴滬,而安排6月24日當天往返滬寧,也過於勉强,似有强史料就我之嫌。
(69)張、何論交始於光緒二年(1876),長期共事,相知甚深。光緒二十七年初,何在上海突然病故,張痛心疾首,自謂:“嗟與梅生交,始自丙子,至今二十六年矣。學識練達,器局深穩,非予所及。比年以來,每有一事,必就梅生決之。與論世事,十常同八九。”《張謇全集》(6),頁449。據本年鄭孝胥日記正月十四日條:“得子培(沈曾植)、季直自滬來電云:‘梅生猝故,即來滬,盼切。植、謇。元。’吾黨爲之短氣,失一鉅子矣,傷哉!”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2),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786。鄭將何歸入“吾黨”行列,可旁證此輩人意氣相投,當時思想見解多近似。
(70)吴宗慈《陳三立傳略》,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131。
(71)陳三立《祭劉忠誠公文》,《散原精舍詩文集》(下),頁866。
(72)湯壽潛,原名震,字蟄先、蟄仙,浙江山陰縣(今紹興)人。早年以《危言》一書知名於世,有疏通知遠之目。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任安徽青陽知縣,旋以親老乞歸。甲午後入强學會,鼓吹變法維新。三十二年與張謇、鄭孝胥等創立預備立憲公會,爲立憲派領袖之一。辛亥革命後任浙江軍政府第一任都督。
(73)馬一浮《湯蟄先先生家傳》,鍾碧容、孫彩霞編《民國人物碑傳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97。並見張謇《湯蟄先先生家傳》,《湯壽潛史料專輯》,浙江省蕭山市委員會文史工作委員會,1993年編印,頁126。按此文係馬一浮代張謇作。又,宋慈抱《湯壽潛傳》云:“二十六年義和團之變,壽潛往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定東南互保之約,所全者甚大。”見錢仲聯主編《廣清碑傳集》,頁1177。該傳原載20世紀四十年代《浙江通志館館刊》,成文較馬一浮文爲晚,而文字雷同,似有因襲。
(74)《寄劉峴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愚齋存稿》卷三六,頁843。
(75)《嗇翁自訂年譜》光緒十五年(1889)記:“九月……始識山陰湯蟄潛與爲友。”此爲張、湯結交之始,關於二人交誼,張晚年已有總結:“予獲交湯君,垂三十年,粗能詳其志事。方是時,朝野洶洶,爭欲致力革新之業,予與君亦各樹議立事,國人並稱之曰‘張湯’。”參看章開沅《張湯交誼與辛亥革命》,《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6)《劉峴帥來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愚齋存稿》卷三六,頁843。
(77)《寄張制軍》,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劉坤一遺集》(6),頁2565。
(78)張謇日記六月初一日(6月27日)條:“蟄先來深談。”初二日:“蟄先謁新寧,新寧以甫聞德使被戕,京師焦爛,終夜不寢。與伯嚴(陳三立)、蟄先追謁李帥,陳安危至計。”初三日(6月29日):“與蟄先、莘丈(楊崇伊)同行,候蟄先故失船,莘丈先行。與蟄先同寓下關江岸。”又,《藝風老人日記》六月初二日條:“制軍以招撫徐老虎事略見示,與季直上制軍書,借小輪送蟄先追李鑑帥。”見祁龍威《張謇日記箋注選存》,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頁112。
(79)六月初四日(6月30日),張、湯由南京附輪啓程,次日抵達上海,當天張謇日記有“晚與蟄先別,誦‘無幾相見之’詩”之語。《張謇全集》(6),頁438。
(8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義和團史料》(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843。
(81)支那鈺一郎《浙江風潮湯壽潛》,《湯壽潛史料專輯》,頁175。
(82)施炳燮,字理卿,浙江會稽縣(今紹興)人。由監生隨辦南洋洋務,光緒二十年(1894)加捐縣丞,指分江蘇省試用。後於江南水師學堂獎敍案內,經奏保以知縣補用。後升道員,署理湖北交涉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8),頁595—596。
(83)止庵編《關於魯迅》,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67。
(84)許同莘《公牘學史》,王毓、孔德興校點,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年,頁238—239。
(85)《施監督挽詞(有序)》,民國七年二月,《張謇全集》(5),頁218。
(86)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頁194。
(87)劉垣《張謇傳記》,頁97—98。
(88)《浙撫劉中丞來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愚齋存稿》卷三七,頁866。
(89)《致江寧劉制臺、上海盛京堂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發,《張之洞全集》(10),頁8029。
(90)辜鴻銘在庚子年間的活動,限於文獻,尚難完整重建,因若干種後出的基於虛構而非記憶的“自述(回憶)”,使事實面目更加撲朔。影響較大者,如沈來秋《略談辜鴻銘》(《文史集萃》(4),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述及辜鴻銘赴滬與英國總領事霍必瀾三次會談的大致情形;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文史資料選輯》(108),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則直接認定辜鴻銘爲“東南互保”的創議人。朱維錚曾專文加以訂正,參其《辜鴻銘生平及其它非考證》,《讀書》1994年第4期。黃興濤所著辜傳,闢專章對其人與“東南互保”關係有所説明,可資參考。《文化怪傑辜鴻銘》,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08—112。辜鴻銘作爲洋文案,除草擬、翻譯對外函電及傳譯張之洞與外國領事會談外,在事變期間一項重要活動是促成張之洞向英國借款,這也構成維持“互保”一大助力。詳拙文《湖廣總督與匯豐銀行借款合同——“東南互保”的一個注腳》,《明清論叢》(8),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頁315—325。
(91)劉垣《張謇傳記》,頁99。
(92)王爾敏《拳變時期的南省自保》,《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13)《庚子拳亂》,頁132。
(93)王蘧常《沈寐叟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37。又,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以北征事《王譜》繫爲五月不確,應在四月。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26。許説仍誤。沈於四月初一日(4月29日)由嘉興啓行,十三日(5月11日)至上海,四月下旬居揚州,五月初七日(6月3日)赴武昌,留上海商中外互保事在五月末,其已由鄂返滬,與“北征”並非一事。
(94)《鄭孝胥日記》(2),頁759,760。另據《沈敬裕公年譜》:“六月,沈寐叟由京南下,主公上海虹口沈家灣湯恩路六號寓所。”《濤園集》,頁163。與王譜“公停於上海主沈濤園”説合,惟繫日作六月,亦誤。
(95)謝鳳孫《學部尚書沈公墓誌銘》較年譜更早成文,亦謂:“至庚子拳匪亂作,兩宮西狩,先生恐東南有變,乃奔走寧鄂,密與劉忠誠、張文襄謀中外互保之策,長江賴以無事,事定而人不知其謀多出於先生。”《碑傳集三編》,《清代碑傳合集》,頁1668下。按,沈曾植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始入張幕,掌教兩湖書院史學,深獲器重。張之洞譽其爲“鳳麟”,赠有“平原賓從儒流少,今日天驕識鳳麟”句。見《送沈乙盦上節赴歐美兩洲二首》,《張之洞全集》(12),頁10583。
(96)岑春蓂,字堯階,廣西西林人,岑春煊弟。監生出身,時任湖北漢黃德道兼管江漢關。
(97)梁敦彥,字崧生,廣東順德人。1872年入選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肄業於美國耶魯大學。1881年回國,分發北洋電報學堂英文教習,1884年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隨辦軍務文報。1889年張調督湖廣,隨同赴鄂,充任洋務文案,總管電報翻譯差。1899年奉派專辦交涉所文案,兼充工藝局提調。
(98)汪鳳瀛,字荃台,蘇州元和縣人。1885年拔貢,隨其兄汪鳳藻出使日本,歸國以知府分發湖北,入張幕。1897—1907年長期負責湖廣督署總文案,庚子時期奉管洋務局事務,外交事件由其總其成。章太炎撰墓誌銘云:“光緒末,八國聯軍入宛平,東南戒嚴,總督張之洞聞君達治體,召置幕府。之洞卧起無幾式,午夜或有所召命,雖監司必攬衣奔赴之,而君於參佐尤親,治奏牘,論文史,幾無寐時。”《前總統府高等顧問汪君墓誌銘》,《民國人物碑傳集》,頁347。
(99)《鄭孝胥日記》(2),頁761。
(100)《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及匪徒剿定ニ關スル各督撫ノ连署上奏並张总督ノ態度ニ付報告ノ件》,明治三三年6月25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二·北清事変中》,頁206;《鄭孝胥日記》(2),頁761。
(101)《張謇全集》(6),頁861。
(102)劉垣《張謇傳記》,頁100。
(103)這方面的最新力作,可參看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但桑著在使用“勤王”這一概念時,未作明確界定,在描述不同性質的“勤王”事件時混用此一辭彙。某種意義上,這也是造成一些讀者就“勤王事件的緣起”,始終無法在桑書中找到“清晰的説明”的原因。朱宗震《評桑兵先生對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挑戰——讀〈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第6期。
(104)《張謇全集》(6),頁437。
(105)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132。
(106)五月下旬,盛宣懷致各省電謂:“鑾駕仍回澱園,傳工部造布篷八百架,此意須深思。”雖未點破,所指宮廷預備西巡事,心照不宣,語多深意。見《盛京堂來電並致江寧廣東成都濟南安慶督署》,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張之洞全集》(10),頁8011。
(107)《江督致鄂督電》,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
(108)《寄李鑑帥》,光緒朝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劉坤一遺集》(6),頁564。
(109)《巡閱長江水師李秉衡摺》,光緒朝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04。
(110)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804。
(111)《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北京派兵內情報告ノ件》,明治三三年7月9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册二·北清事変中》,頁237。
(112)周康燮《陳三立的勤王運動及其與唐才常自立會的關係——跋陳三立與梁鼎芬密札》,《明報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收入吴天任編《梁節庵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頁139。按該札原文影印件可見於黃氏憶江南館藏《近代名人翰墨》,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63),頁94—96。
(113)章開沅《開拓者的足迹——張謇傳稿》,頁115—116。
(114)《近衛篤麿日記》(3),頁232—233,246。陶森甲,字渠林,湖南寧鄉人。時以道員代表湖北赴上海與議“東南互保”。戊戌至庚子期間,在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中多見陶森甲的身影,但呈現出來的面目卻模糊不清:在代表官方辦理交涉的同時,又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會,因與日本的淵源而備受江、鄂兩總督倚重,爲對日聯絡牽線搭橋,又有證據表明曾受日人驅使,不斷反向供給情報。關於陶森甲這類遊走中日之間、同時爲雙方所用的兩面性人物所涉關係較繁,史實層面的情節尚待釐清,不易輕易定性。詳拙文《陶森甲: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雙面人”》,《史林》2012年第3期。
(115)關於此札文背景及內涵的解説,詳拙文《“題外作文、度外舉事”與“借資鄂帥”背後——陳三立與梁鼎芬庚子密札補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16)孫寶暄《日益齋日記》,杜邁之等輯《自立會史料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頁113。
(117)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55—269。
(118)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頁53。
(119)《義和団事件私信》,1900年6月12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東京,原書房,1975年,頁85。
(120)《張謇全集》(6),頁440。
(121)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頁54。
(122)《上海通信·上海维新党中重なる人士の李鸿章伯に呈したる意见书(7月23日)》,《東亞同文會第十回報告》,1900年9月1日,全件譯文録於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頁275—276。
(123)《上江督劉峴莊制軍書》,汪林茂編校《汪康年文集》(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580—581。
(124)《魯迅全集·中國小説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434。
(125)羅志田《異端的正統化:庚子義和團事件表現出來的歷史轉折》,载氏著《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7。
(126)“東南互保”事出非常,隨之也引發“讒慝”之言,張謇特上書劉坤一,爲之作政治合理化的解釋:“行臺承制,晉代有之。蓋申朝命以繫人心,保疆土而盡臣節,非獨反經合道之權宜,實亦扶危定傾之至計也。公之忠勗著於王室,信義孚於列强。伏願堅持初計,慨然自認,以待不測之變,堅明約束,以固東南之疆圉。”《爲拳亂致劉督部函》,《張謇全集》(1),頁45。
(127)《送沈濤園備兵淮揚》,王栻主編《嚴復集》(2),頁363。
(128)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892。
(129)楊國强《1900年:新舊消長和人心丕變》,《史林》2001年第1期。
(130)王爾敏《拳變時期的南省自保》,《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集13·庚子拳亂》,頁166—167。
(131)《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圖書館藏“盛宣懷檔案”,檔號063942。
(132)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頁35。
(133)駱寶善、桑兵《民族資產階級與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編《義和團運動史論文選》,頁490。
(134)同時應注意到,本文論及的官紳羣體,因出身、履歷、學養、職業及交遊圈子等諸多差異,各自與督撫親疏關係、對清朝政治的直接觀感,乃至其後政治道路的選擇也不盡相同。與劉、張關係相對較近的張謇、湯壽潛、鄭孝胥、沈曾植等人,庚子事變時曾一度合作,新政發軔之初又聯手爲江、鄂二督草擬變法覆奏,可謂聲氣相求,而清末十年已漸見羣體內的分化,及至民國肇興,或投身共和革命,或甘爲亡清遺民,莫逆終成陌路。辛亥革命後,鄭孝胥日記寫道:“武漢亂後,國人多以排滿爲心理,士君子從而和之,不識廉恥爲何物,於黎元洪何責焉;宜作書一正張謇、湯壽潛之罪,他不足道也。”《鄭孝胥日記》(3),頁1361。批評措辭之嚴厲,觀念割裂之決絕,前後對照,令人感慨繫之!此條史料承沈潔提示,謹致謝忱。
(135)〔美〕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57—187。
(136)已有研究者注意到這一國父“革命”神話與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間的糾纏關係,提示孫中山早期反清運動,因後來革命意識的流行,也有被長期“革命化”的趨向。參見陳建華《孫中山與現代中國“革命”話語關係考釋》,收入氏著《“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7)《黃興留日與上師書》,田伏隆主編《憶黃興》,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頁178—179。有謂當年自立軍發難,黃興曾回國參與其役,“協助他們運動清軍中的湘籍軍人不加阻礙”。周震麟《關於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後的孫黃關係》,《辛亥革命回憶録》(1),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331。實則黃興在是否依靠東南督撫問題上,與態度轉向激烈的唐才常有所分歧,據其自陳:“及聞拳匪滋事,各國有瓜分中國之言,心甚憂危,思圖補救。以爲義和團在北方如此野蠻,南方當可以獨立。因在日本會議數次。然同志太少,孤掌難鳴,乃遄返祖國,借察形勢。既至湖北,適唐君才常密謀起義,友人因以相告,兄弟以北方雖亂,而南方之勢力尚堅,且軍隊未及聯絡,實不可冒昧起事,談論之間,意旨不合,兄弟遂回湖南舉辦團練,乃未幾得武漢之惡(噩)耗,唐君竟至敗死。”《在湖南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説》(1912年11月8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外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213。
(138)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07—111。
(139)馮自由《中國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載《自立會史料集》,頁22。
标签:上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