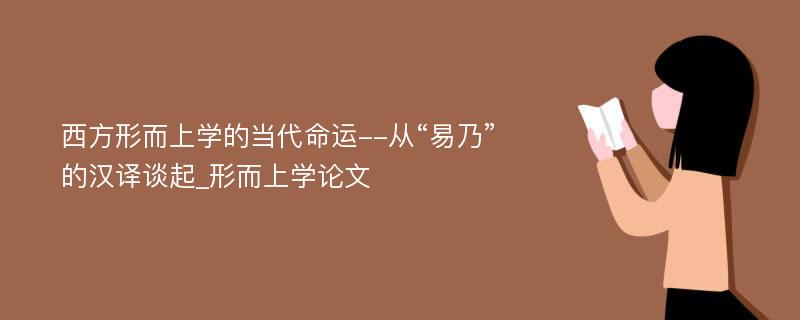
西方形而上学的当代命运——从einai(to be,sein)的中文翻译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中文翻译论文,当代论文,命运论文,eina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苗力田先生主编的中文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苗先生已经把以往翻译成“本质 ”的希腊文词组toti en einai翻译成“是其所是”,以与词组to on hei on即“作为 存在的存在”相并而立。这种翻译的改变以及近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界的相关讨论,都表 明中士学者对于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形而上学在认识和研究上的深入。本文拟从翻 译问题入手,考察对于einai不同理解的哲学意义以及形而上学在反形而上学思潮中的 命运。
一
对于异质文化之“文本”作翻译,包括如何理解翻译的本质和意义的问题,在近年的 西方哲学史讨论中多有涉及,但似乎还有待深入理解和研究。对于那些找不到对应词的 专名例如einai(to be,sein)的翻译难题(即不可直译性的问题),大家似乎都看得清楚 ,比较重视,但是对于能找到对应词的专名(即具有可直译性的专名),是否都能译得恰 如其分、没有问题了呢?这就涉及到对异质文化之间的异质性认识程度如何的问题了。 事实上,除了科学专名多为单义性外,在人文科学特别是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里, 即使是能找到对应词的专名,由于其意义并非单义,所以对应也是相对的,能否找到真 正的对应词,也不是完全靠词典所能解决的。可见,翻译虽然首先碰到的是语言文字问 题,但是真正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还要从文字出发,进而深入到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底 蕴。对于翻译之难,只有驶入翻译的大海,才能真正知道其风浪的险恶,才能知道翻译 决非易事。近代中土大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对此体会最深。他说:“译事三难:信 、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注:《严复 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1页。)。不难看出,严复这里所说的“求其信已 大难矣”,就是指体味作为异质语言文化“文本”的文化底蕴“大难矣”。此外,问题 还在于即使你的外语非常好,并能深入体味其异质文化的底蕴,但能否把“文本”的内 涵用本土语言文字传达出来仍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正如有人指出的,翻译就是给不能阅 读异质原文“文本”的读者看的。如果你的翻译让读者不知所云,那么就如严复所说的 “顾信矣不达,则虽译犹不译也”。可见,信与达是两种功夫,若要使翻译信而达,则 还需要对本土语言文字具有良好的修养。太庆先生在他的遗稿中指出,做好翻译单纯靠 外语好还不行。这正是他终其一生从事翻译工作的重要体悟,很值得后人深思和记取。
严复只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但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做到“信、达、雅”? 他并没有明确回答。不过,他那部轰动一时的著名译作《天演论》却并没有按“信、达 、雅”的严格标准翻译,而是一种意译且夹有他的发挥在译文中间。对此,他作了这样 的解释:“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 则不倍(与“背”字意义相通——引者)于本文”;对此他自己的评说是:“题曰达旨, 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天演论·译例言》)。严复其所以离开“正法”, 是与他当时急于要把新思想用最通达的本土语言介绍过来,为他唤起民众觉悟的启蒙目 的服务,而不是将之作为学术研究的学术翻译。但是现在要问:其翻译“正法”即其追 求的“信、达、雅”能否完全实现?如果承认异质文化之间的思想观念表达于文字确有 不可直译性,亦如关于einai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词等情形,那么“信、达、雅”的追 求虽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目标,但实际上只能相对达到,不可能绝对实现。正因为如此 ,可以认为翻译的实质确实是对原文“文本”的一种再创造。就此而言,我比较赞同德 里达的看法。他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 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实于原 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 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 书店2001年版,第168页。)从以上所说可知,如何深入理解翻译的本质和意义的问题, 还有待深思和研究。
二
如果说西方文化区别于中土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西方的语言(或语音)中心主义,那 么,这个特征也体现在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从诸多论说可以看到, 自古希腊开始,经历中世纪到近现代,西方哲学各学派的分野和竞相发展,其根基差不 多都系于对einai(to be,sein)的理解和诠释之不同。不同的语言文字是不同文化的根 ,文化的异质性必然要溯源到不同的文字上。例如einai以动态的系词意义为主,又兼 有表真、表存在、表方位等多层意义。这乃是古希腊等西文所独有的词语,在中文或其 他东方语言文字中都找不到对应词,无论中文将之译为“有”、“存在”、“是”,都 不可能作到真正对应。即使现在不少文章主张把eina(to be,sein)翻译成“是”,但其 实中文的“是”也不能说是一种与之真正对应的词语。虽然中文的“是”具有系词性, 但却不具有einai等此类西文词语的动态性。严复所说的“求其信已大难矣”,在这里 表现得最为清楚。所谓“大难”,就难在异质文化之间,确实存在语言文字上难以沟通 的硬结。为了克服这个“大难”,有的文章提出应当根据“文本”的语境,分别将eina i相应译为“有”、“存在”和“是”,而不是固定一种。但即使如此,也难尽“文本 ”中einai(to be,sein)之原义,因为对于不懂西文的读者来说,他们只能在中文传统 的语境中理解“有”、“存在”、“是”,所以作出有悖于“文本”原义的理解几乎是 必然的。由此联想到,前面所引述的德里达的说法“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 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洞见。就是说,再好的翻译都不可能“复 制”原文的“文本”,而只能是一种实际上具有“演义”成分在内的“文本的崭新历史 ”。而且,就两种异质的语言文字而言,由于表义的词法和语法不同,翻译“文本”在 这方面与原文“文本”的区别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这一方面,诚如德里达所说, 再好的翻译“文本”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和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现在要问的是,这种“ 远离”和“区别”难道对于原文“文本”思想内涵的传达不发生影响吗?不难看出,近 年来西方哲学界对如何理解、翻译einai(to be,sein)所展开的讨论,在中西语言文字 、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深刻揭示了这两种语言文字与思想文化的异质性。这不能不 说是中土外国哲学界从哲学角度对于中西思想文化认识和研究的一种重大深入。可以预 料,这种深刻异质性的揭示,不仅对于西方哲学、思想文化,而且对于中土哲学、思想 文化的认识和研究,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例如,由于这种深刻异质性的揭示,种种庸 俗浅薄的“西学中源”说就不攻自破了。再如,中西哲学、思想文化如何相互借鉴、融 合、互补以求创新这样的研究课题,也能从这种深刻异质性的揭示中受到重要启迪。对 此,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知其大异”,方能“进而求其大之同”。就是说, 只有深刻认识中西哲学、思想文化的“大异”,方能找到求其“大之同”的正确出发点 ;相反,漠视这种“大异”,只从一些外在的相似点作类比或附会,是毫无意义的。
前文把einai(to be,sein)称为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奠基性范畴,这样说似乎还不够 ,其实还需要补充。应当说,einai还是西方形而上学内部各时代不同学派演化的基础 性范畴,同时,它还是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西方哲学各学派演化的基础性范畴。近年 来西方哲学界有不少文章在这方面的论述都相当深入,具有深入西方哲学真正底蕴的深 刻性。例如有文章指出,从康德否定einai的谓语意义开始,即否定einai的存在意义, 沿着这条路线,把einai完全系词化的过程,就是罗素、维特根斯坦一直到现代分析哲 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此外,在黑格尔把einai作为存在概念成为《逻辑学》的开端 、并由此演化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以后,黑格尔的存在论就成为反形而上学的众矢 之的。基尔凯郭尔的“单个人”论的存在主义,就与批判黑格尔的整体存在论密切相关 。海德格尔在追溯存在论历史中,也批判了黑格尔对einai本真意义的背离。有趣的是 ,海德格尔与老师胡塞尔分道扬镳,也与对于einai的不同理解和诠释相关。
三
与对einai的不同理解相关,现今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19世纪末叶以来出现的反形 而上学哲学思潮至今方兴未艾。这样就很自然地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 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
中国哲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重视研究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 而只重视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问题。一般读者所知的形而上学,就只限于后边 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作为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之后一直到现在,都 受到西方反形而上学思潮的批判。而黑格尔作为西方最后一个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大家 ,曾经对形而上学给予崇高的评价。他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 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注:黑格尔:《 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页。)黑格尔之所以这样评价形而上学,是因 为他把形而上学看成民族魂或民族精神的本质,对于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不是尚未摆脱 原始状态的野蛮民族)来说,失去形而上学就会丧魂落魄。尽管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他 身后已经被合理地批判解构,但我们对此仍要发问的是,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评价,是 否也已经过时或者也需要加以批判解构呢?不错,作为民族魂的民族精神不是一层不变 的,对过时的、陈腐的内容,应当加以批判解构,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可以不要作为 民族魂的民族精神吧。现今,现代化这架“发动机”把世界引向“知识爆炸”、“科技 崇拜”,人们由此只重视追求不断升级的物质享受和获得这种享受的实际练习和实用教 养,由此漠视精神问题,对于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兴趣更是日益淡漠,甚至对有志于此的 少数人持嘲讽态度。这样,人们就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异化中使自身精神变得日益空虚。 人们在物欲横流中获得“富有”和“享受”的同时,由于精神匮乏而人性弱化,甚至丧 失基本人伦而向动物性倒退。在“科技崇拜”所推动的“科技失控”中,不仅核武器毁 灭人类的威胁远未消除,而且随着“克隆技术”的发明,千万年积淀的崇高的人性价值 ,也面临被毁灭的威胁。因此不能不发问:人怎么会变得这样残酷?为什么会走到既要 毁灭精神家园、又要毁灭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村以致最后还要毁灭自身?这里最深层次 的原因,是不是与形而上学精神的失落有关?
人们面对着从西方反形而上学思潮中传来的“上帝死了”、“理性消解了”等等精神 地震,从中到底感受到了什么?“上帝死了”意味基督教最高价值观的失落,也是中古 以来西方最高价值观的失落,同时还隐含着论证这种价值观的形而上学的失落,由此导 致理性消解也是一种必然。但是“上帝”与理性的双重失落,或者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 的失落,是否意味人们从此不再需要形而上学?或者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以交往理性 超越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应当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超越观是极其软弱无力的, 不管借助语用学在“生活世界”中建立起怎样的互动的沟通和理解,却沟通和理解不出 一种有如“上帝”一样崇高的价值观念,以至哈贝马斯也不得不与宗教妥协。他认为交 往理性“既没有宣称离开了上帝的世界毫无希望,也没有充当救星。交往理性抛弃了排 他性。只要它在有说服力的言语媒介中找不到更好的语词表达宗教所言说的内容,它就 会保持克制,与宗教共存,既不支持宗教,也不反对宗教”(注:哈贝马斯:《后形而 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哈贝马斯这种对于宗教若即若离的心 态,很能代表西方一些思想家在填补形而上学精神失落所留下的价值真空时所陷入的束 手无策的心态。
无论西方反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在批判、解构形而上学时揭示出其多少理论的虚构性 、非真理性,但是其有一个基本的合理性和价值是否定不了的,那就是西方理性的、逻 辑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乃是从形而上学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而由理性的、逻辑的、 科学的思维方式所创造的种种具体科学的早期形态,就是形而上学这个包罗万象的哲学 的一个个科目。近代以来,具体科学逐渐从这个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对此恩格斯在《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已不复存在,哲学只剩下逻 辑和辩证法。这是恩格斯对形而上学或哲学所持的终结观。海德格尔与此不同,他在《 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则认为,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乃是哲学的一种 完成。虽然恩格斯和海德格尔对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已终结的看法 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论述却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各门具体科学与形而上学是血 脉相通的。恩格斯的看法至少表明,各门具体科学曾经是襁褓在形而上学之中,而海德 格尔则认为还不止于此。海氏所谓哲学的终结意味哲学的完成,乃是指虽然各门具体科 学独立了,但它们仍保持在哲学的视阈之内。
由此可知,如何正确评价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反形而上学思潮对传 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或解构而得到合理的解决。面对当今社会存在的道德沦丧、失去精神 家园的严重危机,以及因“科技失控”而危害地球和人本身的生存危机,世间有识之士 都在呼唤一种合理有效的价值观的重建。这种对价值观重建的呼唤,是不是也在间接地 呼唤一种合理有效的形而上学的重建?因为,任何价值观如果没有形而上学作为理论基 础都是难以确立起来的。如果说,旧的形而上学应当批判、解构,那么这种批判、解构 不应当是扬弃式的吗?不应当扬弃地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使之成为新的民族魂或民 族精神的理论基础吗?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