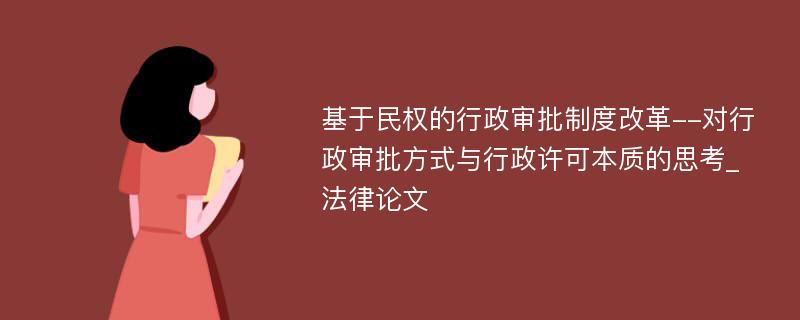
基于公民权利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进路与行政许可本质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行政审批论文,公民权利论文,制度改革论文,行政许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为何要重思行政许可之本质 行政许可究竟为何物,曾是我国行政法学界聚讼纷纭之话题。虽然有少数学者持复权说,[1]认为行政许可制度乃国家将权利还给人民,由公民恢复其自由与权利之行为与制度,但学界通说则持赋权说,认为行政许可乃行政机关为公民解除禁止、赋予公民权利或自由的具体行政行为。①《行政许可法》采纳并贯彻了后者,如其第12条第2款、第54条第1款明确将行政许可视为赋予公民特定权利、资格的行为。就此而言,在实证法制业已采纳赋权说的背景下,许可本质之争当属尘埃落定之话题,不应重提。 然而,值此以“简政放权”为旗号的行政审批②改革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之际,仍有必要提这一话题,重新界定行政许可的本质。这不是单纯的理念之争,而是为了给行政审批改革开辟新的进路、新的着力点,以便巩固当前改革的成果,并深化整个许可法制的变革。细言之,当以国务院为首的行政机关视当前改革为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放权”改革,是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公民、市场与社会的过程,[2]从而将改革重心放在审批事项的削减和审批权的下放方面时,就表明这一改革不经反思的以赋权说为主导思维,从而将改革所要服务的对象——公民——置于被动接受改革而不是以权利主体参与改革进程的尴尬地位。而在公民无法以权利主体身份参与改革的情况下,改革就会因为缺乏公民权利的参与与制约,停留在指望改革者自身意识与水平的层次。而不受权利制约的权力是无法依靠行政自制就能自行保持在善治轨道上的,因此行政审批改革很可能重走以往简政放权的老路,再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此,要实现改革的深化,巩固改革的成果,就必须重提赋权与复权之争,证成复权说的正当性,进而树立复权说对审批改革的主导地位,树立公民权利对行政审批权力的制约机制。 诚然,行政许可关涉公益、经济、社会与公民个体利益等方方面面,故许可的立、改、废属于立法事务,国务院及有权行政机关得基于行政许可法的授权,以立法者的逻辑来主持、主导。因此,纵使公民可以基于公众参与的逻辑参与这一过程,也不能动摇行政机关在这一层面的主导地位。但是,公民个体依然可以也应该在行政许可的实施环节起主导作用。基于复权说,对许可实施环节进行相应改革,以便公民能够基于权利主体地位制约行政机关的许可审批权,从而顺利依法获得许可,不仅可以充分落实既有改革的成果,使其从抽象的“放权”切实成为公民通过合法申请就能获得的红利,还可以正本清源行政机关在许可实施环节的地位,由此去除其官本位观念的根源,从而扭转、去除其“施恩于民众”的放权思维,促其树立许可乃人们恢复权利的思维。 进行以公民复权为中心的行政审批改革,在反腐行动如火如荼且日益制度化的当下,更有制约懒政、怠政、行政不作为,保障反腐运动有效进行下去的意义。在今年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一些嘉宾指出,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形成了不接电话、不批文件的“新常态”。[3]对此,固然要以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厘清政府与市场之边界的逻辑加以应对,[4]也应当以公民获取许可的权利来制约。毕竟,在管制制度本身正当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公民获得许可、审批的权利来加以制约,而不能通过简政放权方式来解决问题,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为此,就必须贯彻复权理念的行政审批改革,确立公民在审批制度中的权利,以公民权利去制约行政机关的审批权力,让审批权力服从于公民权利。 而要实现这一进路的改革,首先就必须正本清源行政许可的自由本质,承认公民形成、实施行政许可的权力,承认公民在行政许可实施环节的主体地位,从而在这一逻辑下展开行政许可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为此,本文首先从法律逻辑出发,推翻当前将行政许可视为行政机关为公民创设自由或权利的赋权论;进而基于许可制度的自由精神,重新厘定许可制度的制度构造与规范性内在,正本清源行政许可的复权本质,证成行政许可乃公民行使权力,通过许可制度恢复为管制所限制的自由的行为。由此,本文得以重新厘定许可申请与许可审批行为的法律属性,指出许可审批机关只能审批、监督行政许可而不能实施行政许可,公民才是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在此基础上,本文展现行政许可制度的完整逻辑构造,并基于复权视角提出改革行政许可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行政许可赋权论之批判 的确,在私权领域,许可是有权力的私法主体基于自我意志为他人创设自由或权利的过程。基于私法自治原则,除非公益的限制,任何个人无权要求私权主体为自己创设许可,许可只能是基于私权主体自由意志的恩赐,许可在逻辑上只能是个别人、部分人能享有的特权,而非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普遍自由。也正因为在普通法观念中,长期以来个人与国家被同等对待,且英国法传统上,来自国家的许可从来不是源自人民主权观念下的国家,而是韦伯所言的那种基于传统而获得合法性的王权国家,③所以,在美国,尽管存在悠久的宪政传统,但公法领域的许可长期被视为政府的恩赐的特权,不受法律保护。[5]因此,如果将行政权等同于私权并以之作为许可制度的基点,赋权说似乎不无道理。 然而,仔细推敲,可以发现这种观点至少存在如下两方面的不足。 其一,它不符合行政许可的自由本质。行政许可究竟是公民的权利,还是政府恩赐的特权,曾是美国行政法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基于行政许可对公民实现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普遍抛弃了恩赐说,承认行政许可乃公民的自由或权利。[5]尽管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确认了公民通过司法诉讼保障其获得许可的权利,但我国主流的赋权说所蕴含的逻辑恰恰有与此相悖之嫌。细言之,不管我们如何界定自由,我们至少都会认可,自由包含着意志自由这一要素。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个人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因此,尽管表面上是行政机关在赋予许可,但实际上,如果公民不想获得某种自由,不提出与此相关的许可申请,就无所谓机关的批准与授予。而且,一旦当事人提出许可申请,行政机关就必须进行审查,并依据相应的程序与时限来决定是否解除管制。当事人的申请由此构成许可行为的必要要件。就此而言,没有相对人的申请,就无所谓许可机关对禁止的解除。这足以表明行政许可与公民自由意志须臾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当赋权说将许可视为机关创设自由的行为,却不能厘清解释公民意志在这一过程中的法律作用,不能解释公民申请有什么效力、为什么能约束行政机关、效力源自何处等一系列问题时,就必然给让人以为它没有肯定个人的意志自由,只肯定行政机关的意志自由,必然给人们带来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基于自我意志随意创设、恩赐的产物的感觉。 其二,最关键也最有问题的是,它在法律逻辑上无法自洽地解释行政机关不予许可行为的法律性质,无法一以贯之地界定许可审批权。 一般认为,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依法做出准予或不准予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是……基于行政职权而作出的能够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6]据此定义,不管是准予还是不予许可,都应是行政权力的运用,都应当能直接引起法律效果。显然,将准予许可解释为行政机关据此权力给公民创设自由的行为,显然与赋权说没有冲突,也与行政行为定义没有冲突。然而,不予许可的行为又引起何种法律效果呢?这种法律效果该如何被界定,才能满足不予许可行为作为行政行为,所具有的“能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特征呢?诸多教材没有回答。显然,仅仅将之理解为“公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是不够的,因为公民申请许可前就没有该“应有权利”,故“公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还是过去的法律状态,不能算是不予许可行为的法律效果。为此,德国学者毛雷尔将不予许可行为界定为将临时性禁止变为最终禁止的行为,[7]以求符合不予许可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性质:能够处分公民权利,引起新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而运用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④将行政许可视为行政机关运用霍菲尔德式权力为公民创设自由或权利的行为的朱新力、余军教授,则不得不将公民在行政许可制度中所承担的义务分解成所谓的普遍性禁止义务与对特定个人的禁止义务,前者是立法者通过管制性法律剥夺公民自由的结果,后者则是不予许可行为的产物,即行政机关为特定公民创设个别性禁止义务的行为,[8]以符合他们将审批权归类为霍菲尔德式权力——依行为人意志创设、变更法律关系的能力——的设定,以便解释这种权力在不予许可时到底发挥了什么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功能。 然而,将禁止界分为临时性禁止与最终禁止的区分是值得商榷的。依据毛雷尔关于附许可保留之禁止的界定,即使行政机关不予许可,只要这种禁止是附有许可保留之禁止,那行政机关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拒绝许可,将这样一种许可变为不附许可保留之禁止,因此许可申请人在其申请被拒绝之后,依然保留有今后成就条件获得许可的机会,而不是被禁止了该种自由。也就是说,不予许可并不产生最终禁止。毋宁说,不予许可仅仅意味着行政机关确认了公民当时处于一种没有资格或能力获得许可的法律状态。 同样,将不予许可界定为设定个别性禁止义务的行为,将公民未经许可不得作为的义务界分为所谓的普遍性义务与个别性义务,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无法支撑审批权乃霍菲尔德式权力的界定。一方面,它与法律状态并不相符。因为这意味着在获得许可前公民处于自由状态,否则行政机关根本就没必要运用行政权来消灭其自由,给其施加义务。但是,若此前公民已经处于自由状态,为何还要申请许可?事实上,当立法机关创立许可制度时,公民已经被许可制度确定为不自由了,因此公民才需要通过许可来获得自由。因此,行政机关根本无须在此通过拒绝予以许可,再行创设一个此前未有的所谓个别义务,当事人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此前没有一个明确不得作为的义务。另一方面,它不符合法理。其实,许可制度所创设的禁止公民未经许可不得作为的义务对任何公民来说都是个别义务,而非所谓的普遍义务。在此,我们有必要引入霍菲尔德关于对物法律关系与对人法律关系的研究加以阐释。霍氏在研究对物关系和对人关系时指出,没有什么所谓的对物法律关系,所有的法律关系都是对人关系。因为,所谓的对物法律关系,实际上是针对无数个体的个别性对人关系而已。[9]以所有权为例,任何人得基于对物的所有权而与所有人形成的所谓对世性对物法律关系,其实质就是每个个体不得侵犯这种物的个别义务。如果我们将许可制度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抽象为民法上的物那样的权利客体,那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行政机关作为公益或公共秩序的维护者与代言人,同样能与全体公民形成这样一种对世性质的对物法律关系,而任何公民未经许可不得侵犯公益或公共秩序的法律义务,就相当于任何个体不得侵犯物权的法律义务。而所有公民不能违反许可法律制度、未经许可不得为某种行为的义务,就单个公民而言,同样是个别义务。所以,将所谓的义务的分成所谓的普遍性义务与特定个人的义务,进而将许可制度之创设理解为普遍义务之创设、不予许可理解为个别义务之创设,于理不通。 二、行政许可法是授予公民复权之权力的法 赋权说出现上述重重问题的根源在于,它比照财产权的处分权能,将行政许可权视为类似行政处罚权、行政征收权的行政处分权,进而将这种处分权作为理解行政许可的出发点。然而,行政许可不能按照私法许可的逻辑来理解。这是因为,现代民主国家不同于私权主体,他在政治层面必须服从一个更高法则:自由。因此,正如我国宪法第23条所规定的,他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公民作为自由主体,自然在政治层面、进而在法律层面有权要求国家建立制度来为公民获得自由、行使自由建立制度和条件。因此,行政许可必须从公民自由角度加以理解,以公民自由而不是国家权力作为逻辑出发点。[10]行政许可法第12条即充分表明这一点:公民自由预先于国家,国家只能基于公益去设立许可,限制公民自由。也正因为许可法中流贯着的自由精神,行政许可制度必然有着迥异于私法许可的制度构造,行政许可法必然是赋予公民复权之权力的法,行政许可必然是公民恢复自由的行为。 (一)行政许可法是赋予公民复权之权力的法 基于行政许可制度的自由本质,行政许可制度从设立到实施,必然具有如下三阶段的制度构造。 第一阶段,国家收权于民,行使立法权力限缩公民的自然自由。在主流政治哲学中,自由总是和诸如免于、远离这样的否定性用词关联在一起,处于“freedom/liberty from……”的结构中,意味着从某种人们当作不好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意味着免于他人的强制。由此,自由被等同于消极自由。[11]然而,在更为本源的意义上,自由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12]这才是自由的本质,也正因为如此自由才具有了成为最高法则的正当性,才需要与选择自由紧密关联在一起以实现自由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但是,相较于以因果关系串联着的历史,作为可能性的自由,也仅仅表明了向着未来的开放性而已,它一旦付诸实践,就进入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历史因果链的一环。因此,自由不能不受因果律的约束,不得不处于卢梭所言的“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的纠葛之中。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康德所言的启蒙,发现自我作为自由主体的本质,以自己的理性为支撑,自我而不是经由别人引导而展开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自我,并因此拒绝那种由一个外在主体包办一切、主宰个体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自由也必须受到规范与训诫,以摆脱自然界因果律的影响,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诚如福柯所言,启蒙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训诫,[13]训诫是自由的内在部分,不通过训诫,个人自由无从真正得以实现。因此,人类必然要通过国家来规训自我,⑤避免自我无节制地滥用其自然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设立许可制度,首先意味着国家行使立法权,收走公民原本拥有的一些自然自由,以便公民能有节制地行使其自由。⑥相应地,公民被施加于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义务。于是,在这一阶段,首先由国家行使立法权力,在自由法则的指引下剥夺了所有公民的自然自由,设定了权利(国家)—义务关系(公民)。 第二阶段,国家还权于民,建立许可制度确立公民有通过许可获得法律自由的权利。从自由出发,管制之后就必须实行许可,无许可即无自由,因为自由是面向未来的无限自我发展的可能,管制却限制了自由所蕴含的可能性。所以,国家必须在管制之后建立许可制度来给予公民恢复自由、发展自由的机会与空间。许可制度就是国家在限制自由后给公民开的一扇门,规定公民行使自由的条件,待公民满足这些条件后行使有节制的自由。由此而来的是,如果一种限制自由的制度没有许可制度及相应司法审查制度伴随,那么或者是因为这种自由并非是主权者所承认的、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比如使用暴力的自由⑦,或者是因为国家没有尽到为公民行使自由提供必要服务的义务,或者是国家过度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为此,在制度建构层面,看是否需要在管制之后建立许可制度,就要考察公民在宪法上是否具有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权。相应的,从逻辑来说,应当建立立法审查制度以约束立法者的管制创设权,救济被违背自由精神之立法所限制自由的人民。 第三阶段,公民有权力自行决定是否恢复自由。既然自由是更高法则,那么公民何时实施自由、恢复自由,就只能由公民自我意志自行判断,而不能由国家来认定,国家只能在公民提出申请后判断公民是否具备了行使自由的资格。一方面,自由是高度个人化的事业,只能由个体自主并由个体自我负责。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公益维护者与训诫机关,既无法主动去判断个体公民是否具备了恢复自由的能力,也不能代替公民决定是否行使这种自由。如果国家未经申请而自主恢复某人做某种行为的自由——就像所有权人基于恩赐而赐予他人进入其花园的特权,则该人很可能因为不具备行使这种自由的条件而滥用这种自由,损害公共利益——比如不会开车的人被允许开车上路后重则伤人轻则扰乱交通秩序。这种做法必定违背许可制度所欲实现的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如果国家为赋予某人许可而要求该人为此进行训练以具备某种能力,其实是给此人施加了义务,从而将自由变成了义务,取消了许可所内含的选择自由,无法体现个人对自我发展可能性的自主安排。因此,许可只能是由公民根据自己发展的意愿和可能性,秉承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的精神而提出,而不能由国家包办、分配。因此,国家在通过立法权剥夺人民自由后,不仅要实行许可制度给公民恢复自由留下一扇门,而且要把这种开门的自由选择权留给人民,由公民自我决定是否去改变既存法律状态,恢复自由。换言之,许可的自由精神不仅在于只有为了公益才能限制自由,不仅在于创设许可制度以便公民恢复自由,更在于要将恢复自由的决定权交给公民自己行使,由公民根据自我发展需要或偏好,行使行政许可法赋予的权力,解除第一阶段立法权所设定的法律关系,恢复为自由(公民)—无权利(国家)关系。只有如此,才是彻底地还权于民。 综上可见,正是因为公民在政治层面拥有只能限制但不能剥夺,且得由公民自行恢复的自由,许可必然不是政府的恩赐与创设。我们不能只看到政府有权力建立管制,但看不到基于自由法则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建立许可制度,有权力通过许可来恢复自由。进言之,行政许可法不仅是限制公民自由的管制法,同时也是授予公民形成许可、恢复自由的权力的法。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学者胡芬才能说“如果存在某个基本权利上的行为的法定限制,那么请求权就直接产生于该法律规范本身。”[14] (二)行政许可中公民权力的规范性分析 如上所述,行政许可法制在限缩公民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了公民恢复自由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是什么样的法律权利呢? 这种自我决定是否恢复自由的法律权利,在霍菲尔德那里被界定为区别于狭义权利、自由与豁免权的权力,在哈特那里是区别于狭义权利、制裁权与确认权的变更权,[15]在大陆法上则被界定为区别于请求权的形成权。[16]我们姑且沿袭从大陆法系习惯的用法,将之称为形成性权力。这种形成性权力广泛存在于甚至包括民法在内的各种部门法中,其法律效果是当事人能够依照自我意志改变他人的既存法律关系,其实质则是:权力主体相对于法律关系另一方,具有实质性决策权或立法权,而对方居于被动和屈从地位,只能接受决策权行使的结果,接受权力拥有者所建立的法律关系。[17] 根据行政许可法所赋予的这种形成性权力,每个符合条件但还没有获得许可的公民,除了和行政机关处于管制状态下的义务—权利关系——未经许可不得从事某种行为的义务,还处于(公民)权力—(行政)服从关系,即行政机关必须被动接受公民行使权力形成行政许可的行为。尽管可能有的公民出于个人意愿与需要永远不会行使这种权力,但不行使这种权力并不意味该公民和行政机关没有这种法律关系,不意味着这种关系不是具体关系而只是抽象关系。就像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授予的处分权而与公民处于权力—服从关系,因而可以向公民发号施令从而单方面建立新的法律关系以取代国家原本所应承担的不侵犯公民私权的义务一样,公民基于许可法所拥有的改变自己与国家之间现有法律关系的权力—服从关系,同样是具体的、实在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说,当许可法规定了公民恢复自由的各项条件时,公民即由此获得了一种“现时”(present)的权力,得随时根据现时有效的许可法律规范来行使权力,建立新的法律关系。就此而言,从许可法律生效之日起,只要该法没有改变,公民在此期间就有了这一法律地位。因此,尽管公民可能因为不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拒绝授予许可,但只要他日后成就条件,就能依法而申请并获得许可,而不会因为一次被拒绝许可就永远失去获得许可、恢复自由的机会。这种权力是无时效限制的,只能被立法者基于立法权而创设的新法所终结。当然,基于许可制度背后的自由法则,除非管制完全消除因而不需要用许可制度来给公民留出一扇恢复自由的大门,否则新法又会赋予公民新的恢复自由的权力。⑧也就是说,公民随时都能依法恢复自己自由的权力,从而确保了公民随时根据自己意愿与偏好选择自我发展方式的自由。比如公民可能在当下不想实施驾驶自由,但他日后可能因为兴趣的转移、职业的需要而需要开车,那么,他今后仍然可以通过苦练技术而获得驾驶许可。 因为许可法规范或制度的一般化而认为这种权力—服从关系是抽象的、潜在的,认为只有在行政机关颁布许可时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才有法律关系的观点,⑨是不正确的。这种只见行为却不见安排法律关系之制度的静态法律关系观,这种行政处分中心主义式法律关系观是过时的,它会误导我们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认识与相应制度之建构。制度经济学派学者即指出:“将法律关系仅仅界定为行为,会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误解,即,一旦关联行为被干扰,那么这些法律关系就不再存在了”。[18]也就是说,如果不认可这样一种权力—服从关系,我们就可能会认为公民不申请许可时,他与许可实施机关之间就只有义务—权利关系。实际上,作为一种制度,法律及法律所安排的法律关系,固然依赖于个体的思维与行动,但不能简化为思维与行动。因为,即使没有具体的行为,公民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法律所创设或确认的权力—服从关系,它不会因为公民不行为而不存在。正像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学者在批评那种将制度仅仅理解为行为模式的观点时指出的,“在皇室成员都睡着、皇家仪式不在的时候,不列颠王权就没有了吗?当然不是。即使是在不行使的时候,特权与权力依然在。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在昭示着制度的存在”。[19]实际上,就权力—服从关系而言,获得权力本身就形成了法律关系,因为权力地位的获得,有效地排除了行政机关就同一客体的权力地位,并使得它背负着服从地位,从而形成了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持久而稳定的权力—服从关系,进而使得公民此后据此所建构的新法律关系具有规范性与正当性。对此,行政许可法第53条可为有力佐证。该条规定,对有关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许可,行政机关必须采取招标、投标程序,并且必须确保招、标投标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并将许可颁发给招投标程序所确定的中标人、买受人,否则当事人有权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这就意味着,一旦上述许可制度设立,上述资源分配的权力就归属于公民,而不再属于行政机关。一旦公民行使了权力,依法做出了获得上述资源的意思表示,那么就这些资源使用权的归属,他们就形成一个其内容与效力有待于竞争性程序来最终形成、确定的法律关系,而行政机关只能服从他们的参与性意思表示,不得拒绝,并且要接受竞争性程序的结果,将许可颁发给其中的优胜者。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公民不申请许可,或是放弃申请,就否认公民权力的存在,否则我们只能认为不行使权力时公民就没有改变此前法律状态、获得行为自由的资格与地位。只有承认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区分行政机关作为管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和公民作为自由主体时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服从法律关系,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一方面公民在没有获得许可时要服从行政机关的管制,但另一方面又可以随时要求行政机关赋予许可从而解除禁止,这两种看似矛盾但又同时并存的法律状态。 三、许可申请是公民形成许可、恢复自由的法律行为 规范的功能在于提供解释框架。[20]既然许可制度是国家对公民自由进行管制但又将恢复自由的权力交给公民,由公民自行决定是否恢复自由的制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依照许可的这一内在规范,对行政许可的实施环节进行更为细致的全景框架式分析。这一分析将弥补此前学者对许可申请之规范性分析不足的缺憾,同时也回应本文前面所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既然许可是当事人自行创设自由的行为,那么行政机关的审批扮演着什么角色?许可审批权在法律上的定位又是什么? (一)许可申请行为是公民行使权力、表达意志、为自己创设自由的法律行为 几乎每本教科书都会指出行政许可行为是应申请行为,但是它们都没有细致界定许可申请的法律意义。它们仅仅停留在没有申请就没有许可审查、没有申请就不能赋予许可的层面,却没有说明为什么没有申请就没有许可,也没有阐释除了启动审查外许可申请还有哪些法律效果。徐以祥等少数学者则将其界定为公民向行政机关主张给付请求权的行为,这种给付请求权是基于自由与财产权而生的干扰防御请求权的特殊类型。[21] 然而,将许可申请权视为给付请求权的行使,值得商榷。一般说来,请求权意味着存在确定的权利与义务主体,权利方能够向相依的义务方提出作为或不作为某种行为的主张,义务方则须依此主张进行给付。这种给付义务可以主动履行,也可以在请求后履行;如果义务方不予履行,那么国家机关将启动强力、采取各种合理措施落实权利—义务关系。从请求权的这一特征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许可申请绝非在主张所谓的给付许可请求权。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在公民提出许可申请之前就有一种许可请求权,那这只能意味着,公民在还没有提出许可申请前已经被法律确定了朝向何种方向以何种方式来发展自我。这实际上否定了公民基于许可制度的自由发展权,和许可的自由精神有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公民没有提出某种许可申请,就意味着此时公民还没有确定是否要恢复何种自由来发展自我。相应的,行政机关也无从知晓哪一公民要恢复何种自由。也就是说,在当事人提起许可申请之前,既无所谓确定的请求权,也无所谓确定的请求权主体,更无所谓确定的给付义务与义务主体,遑论其对该义务的主动履行了。一言以蔽之,在公民提出许可申请之前,他与行政机关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确定的给付性权利—义务关系;相反,纵使批准许可是行政机关的义务,这种义务也是在公民提出许可申请后产生的,而不是在许可之前就有的。 因此,将许可申请理解为公民行使形成性权力形成许可的行为,更为合理。或者说,与其说公民根据给付请求权来申请许可,不如说公民根据许可法赋予的形成性权力来创设行政机关的给付义务,许可给付请求权由许可申请所确定。进言之,许可申请行为其实是申请人向许可实施机关作出意思表示创设新的(公民)自由—(国家)无权利关系、消灭过去(公民)义务—(国家)权利关系的法律行为,设权行为。公民通过行政许可,不仅要恢复自由,还要消除此前管制制度所规定的他与国家之间的义务—权利关系。由此,许可申请背负双重功能与目的,故兼具旧法律关系之消灭功能与新法律关系之生成功能的设权行为属性,才满足许可申请行为之功能期待。此外,将许可申请行为理解为公民行使权力的行为,不仅更加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行为的规范性本源,更足以体现公民在这一环节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体现并强调了公民得随时依照自我需要去生成新法律关系的法律地位。以上这些,都是静态属性的请求权概念所不具备的。 就此而言,许可申请行为也是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告知行为:公民要改变此前行政机关有权利而公民有义务的法律状态,恢复为公民有自由而行政机关无权利的状态。如果没有这一意义上的申请,就没有意思表示,就无所谓许可形成权力的行使,就不能产生约束行政机关的新法律关系,就不能阻断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管制,公民也就无从恢复自由。 也正因为许可申请权本质上是基于权力—服从关系的许可形成权,所以许可申请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因为它所表达的意志,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尽管因为公益的需要,公民自己无法赋予这一行为有效性——对此下文将展开阐述,但许可申请依然有一定的法律效果。具体表现在:(1)行政机关尽管可以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但不能否定这一行为的成立与存在。相反,他有义务就该行为是否有效进行法律裁断;(2)许可申请所形成的法律关系虽然是效力待定的,但也具有一定效力,能约束行政机关的相关后续行为。比如公民参与申请有关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许可时,行政机关有采取招标、投标程序并且必须确保招、标投标程序之公平、公正、公开的义务,并要将许可颁发给招投标程序所确定的中标人、买受人,而不得将资源给予其他未参与招、投标程序或是在此程序中未胜出之人;(3)许可申请决定许可审批的法律适用。许可实施机关必须根据当事人据以提出申请的许可法规范来审查许可申请,而不是后来的法律。这是因为,公民依据现时有效的法律申请许可,其实就是认为自己现时符合了恢复自由的条件,能够依法享有自由了。行政机关根据后来的法律来审查该法生效之前的许可申请并否定许可,实际上就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后来的法去调整此前人们的行为,以后来的法律去否定此前公民本该享有的权力,从而构成对自由的不当剥夺,也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二)行政机关颁发许可的行为是第二性确权行为 在将许可申请界定为公民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意思表示行为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行政机关对要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批准?这种审查、批准行为究竟属何种行为? 众所周知,除了具体行政行为等基于国家公权力单方创设新法律关系的设权行为外,其他任何基于权力—服从关系给他人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比如民事法律行为,都不具有公定力,不具有从成立之日起就被法律推定为有效的法律效力。因此,尽管公民的许可申请行为在法律逻辑上消灭了此前的(国家)权利—(公民)义务关系,生成了(公民)自由—(国家)无权利关系,但因为缺乏公定力,所以该行为所建立的新法律关系尚未生效,而其所欲消灭的旧法律关系尚未失效。公民因此依然要遵循此前的法律义务,否则要承受相应法律责任。 公民的许可申请不能具有公定力,是因为,许可申请要消灭公民对公共秩序的义务,属于重新调整和界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的行为,不能由公民自行赋予其有效性,否则就违背了一切公共权力只能由国家来垄断这一现代政治基本原则。因此,既然公共利益的边界何在只能由公共机关行使公共权力来界定,那么在公民意欲通过许可行为改变公私之间边界时,就必须由国家来确认这种改变是否可行,而不能完全交由私人自行确认,否则公共利益就会被吞噬殆尽。相应的,公定力这种“为了公共目的,而赋予行政决定的效力”,[22]自然不能赋予许可申请行为。 基于上述政治与法律逻辑,许可申请行为所建立的,只能是效力待定的法律关系。而为了克服这种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就必须引入哈特所言的第二性确认权,⑩或是像制度经济学大家康芒斯那样,将确定这种关系之有效性的公共权威机关,引入法律关系之中,承认这种法律关系不是单纯由私人所决定的、自身有权威的法律关系,而是需要由权威来认可的法律关系。(11)哈特指出,为了解决第一性规则或第一性法律关系之不确定性问题,最简单的补救方式就是引进“确认规则”(a rule of recognition),[15]来确认某一规则是否该社会共同体所要遵循的规则。毫无疑问,对于许可申请这种重新确定公民与国家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行为,自然要由行政机关来确定其有效性与权威性。而颁发许可证书,正如哈特所言的,“在有确认规则的时候,通常某份官方的证明文书或官方立法文件就足以充分证明立法行为已完成。”[15]当然,并非所有的许可申请行为都需要官方以要式文件来确认其有效性。在很多情形下,许可机关在逾越法定期限后仍不明确拒绝许可申请的行为,即可视为许可机关默示认可了许可的有效性。 因此,许可实施机关审查、批准许可申请或是拒绝申请的行为,不是所谓的为公民设定自由或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类似于司法裁判行为的行政确认行为。(12)因此,依法予以许可不是行政机关为公民履行所谓的实体性给予许可义务,而是在履行类似法官的程序性依法审判义务。因此,相对于公民而言,行政机关依法批准许可的义务是程序法上的义务,而不是实体法上的义务;它对应着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而不是公民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在这个国家认证(确认)职能、国家权利认证体系与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的时代,[23]这种程序性权利就像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一样,[24]同样意味着国家的绝对义务。 (三)小结:行政许可的真正实施主体 综上可见,在行政许可制度业已确定的情况下,基于公民形成许可的权力,是否申请许可,申请何种许可,何时申请许可,完全由公民自主选择、决定,行政机关只能被动等待而无法强制,更不能去采取什么作为以实施许可。而且,公民提出许可申请时,该申请不仅决定着许可法律关系的内容,也决定着行政机关的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审查范围与法律适用,行政机关的审查受许可申请的全面约束。许可申请不仅是行政许可行为的起点,更全程决定着除了终点之外的行政许可程序的其他环节与方方面面。就此而言,行政机关所谓的许可实施权,除了具有被动的确认、把关权能外,不具有任何内容,它并不能参与许可的形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无论是许可申请之前还是许可申请之中,对于许可的实施,行政机关没有任何主动性可言。相反,是公民在掌握着主动权。因此,与其说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许可,不如说是公民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实施环节的中心是公民而不是行政机关。 四、复权视角下深化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若干措施 行文至此,行政许可的复权本质与公民在行政许可实施环节中的主导地位业以证成,行者许可制度的全部逻辑构造或者流程也得以完整呈现:(公民)自由—立法禁止(公权力作用)—解除与申请(公民权力作用)—行政审批与确认(公权力作用)—(公民)自由。立法者、行政机关与公民在行政许可制度中的角色也同样清晰可见:立法者是许可设立者,公民是许可实施者,行政机关是许可申请的审批者与许可实施的监管者。在这一制度中,不是行政机关在解除对公民的禁止,而是公民自我解除禁止;不是行政机关在为公民赋予权益,而是行政机关在确认公民拥有了自由。国家和公民不再处于对抗关系,而是处于服务关系,国家通过确认来服务于公民实现有节制的自由,维护公益甚至他人自由。通过公民的权力和许可机关的确认权,公益和私益、自由和秩序实现了动态权衡。 基于行政许可的复权逻辑,我们可以从如下角度改革、完善行政许可制度。 (一)转变赋权思维,确立服务观念 解放思想是改革与开放得以成功的前提。对此,无论是作为行政许可的设立者,还是行政许可的审批者,行政机关都应当转变赋权思维,确立复权思维,在复权思维的指导下履行行政许可制度的相关职能并展开行政许可的改革。 其一,国务院及其他有权设立许可的行政机关应该认识到,基于许可的自由本质,许可首先是剥夺公民自由的制度;他们固然在法律上有权力设立许可,且这种权力至今还不能被司法审查,但这种权力并不是毫无制约的。以国务院为首的行政机关必须基于自由法则,在公共利益需要且通过管制自由才能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设定许可;反之,则不应该设立许可。因此,行政机关放松管制、废除许可,并不是放权于民,而是还权于民,将人民原本拥有的自由与权利还给人民。为此,行政机关不能以放权思维来改革,而必须抱着尽可能维护公益与私益之间平衡的宗旨,根据社会发展之需要,灵活机动而非运动式的进行许可的立、改、废。 其二,作为行政许可的审批者,行政机关应当认识到,他们固然有权审批许可,但并不能赋予许可。他们只能作为服务者、把关者,确定许可申请是否满足法律要件。立法者设立许可,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公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公民有节制行使自由,从而促进个人更好发展与公共福祉的提升。限制公民的自由绝非许可的本意,鼓励、支持并服务于公民合法获得许可,以便在不侵害公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发展个人自由,才是行政许可法应有的追求。公民既是实施许可的主体,也是许可法制之目的能否充分实现的关键。为此,行政机关一方面要严格把关,避免不合法的许可影响公共福祉或是侵害其他公民本可以获得的自由,另一方面则要为公民申请许可创造条件,帮助公民迅速合法地恢复自由,而不是将许可审批权作为寻租的工具。 (二)修改《行政许可法》,确立公民许可实施主体地位 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许可法采纳的是赋权说而不是复权说。这种定位既不符合许可的本质,又容易滋长行政机关的放权思维。进言之,作为行政许可制度的根本准则,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行政许可法的赋权定位,那么以行政许可法为权力依据的行政机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转变赋权思维,确立复权思维。因此,有必要以复权说为圭臬,对行政许可法进行如下修改。 其一,确立公民作为行政许可实施主体的法律地位。正如复权视角下行政许可逻辑结构所展示的,在立法者设立行政许可制度之后,是公民行使权力去形成许可,而后才是行政机关对许可申请是否有效进行确权。因此,在立法章节的安排上,应当先确立公民对许可的行成权,并规定公民申请许可(做出意思表示)的程序、方式及条件,然后再确立行政机关的确认权及其审查程序。但赋权说主导下的现行行政许可法恰恰与此相反:在规定许可设立的第二章之后,先以第三章明确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权力及其许可实施机关地位,然后才在第四章规定公民申请许可的程序。因此,立法者在修改《行政许可法》时,应当先在第三章明确公民实施行政许可的主体地位与权利,对其权力行使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将现在的第三章变为第四章,复位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审批机关的地位,明确其许可审批行为的确权性质。同时,对行政许可法中有关“行政机关实施许可”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其二,修改相关条款,确认公民恢复自由与权利的权力。基于赋权思维,现行行政许可法的诸多条款都将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照的行为视为赋予特定权利、资格的行为。为了复位行政许可的复权本质,就必须对这些条款进行修改,将“赋予权利、资质”改为“审核”或“确定”资质、资格或条件等,或是规定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性程序决定权属。 (三)改革许可审批制度,保障公民形成许可之权力 当前行政许可审批环节问题重重。基于赋权思维,行政机关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放权于民,因而总是怀有高高在上的恩赐心态,并基于这种心态人为的增设条件、提高标准、再设环节、拆分事项并且拖延办理,以求寻租权力谋求私利。为此,我们应当基于复权说,对许可申请与审批环节进行再造,以公民的权力来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 1.分立申请程序与审批程序,免除公民在审批环节的额外负担。行政许可是公民行使权力恢复自由的行为,意味着公民才是许可法律规范的适用者,而行政机关只是这种法律适用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核者,因此,行政许可行为由两个环节组成,前者为公民的申请即意思表示环节,后者即行政机关的审批环节;前者为外部环节,后者为内部环节。只要公民根据对外公布的许可条件与标准等,按照相应期限提供材料给行政机关,他就完成了一个意思表示,其“角色”就扮演完毕,剩下的就是行政机关依职权的内部审查环节,当由行政机关就该环节以内部程序模式进行审查,而不需要公民再行参与。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在法定许可要件、程序之外,再设条件、再立程序、再增审批环节,也不能再要求公民在审批环节往返于同一职能部门的不同办公室。要求公民满足法定许可条件之外的其他条件,或是要求公民再走其他审批程序的,公民可以拒绝,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行政机关承担。为此,应当着力推行电子政务系统,将法定许可流程与要件软件化、模式化,使得公民申请许可只要在网上填报相应材料即可,而行政机关不能再自行添加新的环节与新的要件;行政许可设定机关也应当尽力实现许可实体要件的明确化,尽量限缩许可审批机关法律解释上的裁量权。 2.强化行政许可审批时限制度。应当明确行政机关的审批期限,到期不批准的,推定行政机关批准了许可,公民可以此为依据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发放证照。如果因为行政机关增设非法定条件、增设非法定程序引起的期限延误,其法律后果由行政机关承担,并且不能算在法定的审批期限之内。行政机关如果在应诉时的法定期内不能提交为何逾期不决或是拒绝许可的理由的,认定行政机关败诉,公民许可申请行为有效,应当获得许可。如果事后发现该行政许可在实体要件上存在瑕疵或缺陷的,由行政机关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当前反腐运动如火如荼,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处于怕招惹是非或处于消极对抗之目的,而不行使审批权力致使公民无法获得许可进而无法开展相关业务时,这—做法将是制约懒政、怠政的良药。 (四)建立形成诉讼类型,体现并保障公民形成许可的权力 为保障公民行使权力形成、实施许可的权力,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机制,以监督行政机关不予许可的行为。然而,基于赋权说,当前主流学说将不予许可之诉界定为撤销之诉和履责之诉,[25]有误导该诉讼类型建构的可能。 从复权说来看,该诉讼是形成诉讼,而不是履责诉讼。一方面,基于行政审批行为的确权性质,行政机关不予许可之行为,属于认定公民形成许可、恢复自由之意思表示行为之无效性的行为,其法律效果是使公民权力无法落实,而不是剥夺了这种权力。为此,要保障公民权力,就必须通过诉讼来落实公民行使权力所欲形成的法律关系。为此,法院当作为确权机关,确认公民所形成的新法律关系的有效性,而不是责令行政机关重新展开许可审批程序。后者对救济公民权益毫无意义,也不符合公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因此,从形成诉讼原理来看,[26]不予许可之诉本质上只能是形成之诉,是落实形成权的诉讼,当以公民适用法律、运用权力形成新法律关系的行为为核心加以构建相关诉讼制度。另一方面,因为公民行使权力、提出许可申请的目的在于创设公民的自由与行政机关的无权利地位,所以诉讼的核心不是行政机关有没有实体法上义务,而是公民所创设的自由—无权利关系是否有效。所以在不予行政许可之诉中,公民所要形成的,不是行政机关的义务,而是自己的自由与行政机关的无权利,其要旨是消解行政机关此前的权利地位,而不是给行政机关设定新的可执行义务,所以在这样的诉讼中无所谓行政机关的给付义务或是责任履行,更无所谓法院去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所谓的给付职责了。也正是因为公民申请许可,本质上是在设定新的法律关系,所以在德国法上,针对不予许可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乃义务之诉而非给付之诉,其要义正在于,义务之诉的本质是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一个类似具体行政行为的意思表示行为以改变此前法律关系,而给付之诉的本质则是要求行政机关去落实已经确立但还没有被落实的权利—义务关系。[14]当然,德国人的观点也有问题,即其受制于行政行为范式,没有认识到行政机关此处的权力不是处分权(变更权),而是确认权,故其依旧将行政机关准予许可的行为视为处分行为,依旧将行政机关而不是公民视为新法律关系的创设者。 如上所述,法院在该诉讼类型中的职责是确认公民所欲形成的新法律关系是否有效,所以在公民满足许可要件的情况下,法院应当行使审判职权,准予公民获得许可。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行政机关要依照法院关于实体法律关系的认定而准予许可,是符合法理的。因为不予许可之诉要以法院确认公民在行政法上的自由为终点,所以在具体判决方面,可以考虑这样的制度设计,以免行政机关在收到判决拒不颁发许可证照——法院在判决主文第一项判决公民满足了获得许可的法定条件,在第二项判决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照。当然,因为确认自由—无权利关系意味着法院在界定公共利益与公民自由的关系,所以,法院原则上必须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即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裁判权。具体而言,在裁量为零的情况下,可以如上所述径行作出确认判决,确认公民享有自由。在许可存在裁量的情况下,且裁量合理的情况下,法院则应当尊重行政机关不予许可的决定。但为了保障自由,可以要求行政机关进行相应解释。为此,法院可以作出答复判决。[14] 需要说明的是,如本文前面在论述许可申请对许可审查在法律适用方面的约束时指出的,法院在审判时应当以公民据以提出许可申请的许可法律规范为依据。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前半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许可案件,应当以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后实施的新的法律规范为依据”,值得商榷。为了符合行政许可之自由精神,应当修改此一司法解释。 五、代结语:正视公民在行政法上的法律权力 行政审批改革制度的宗旨就是限缩和规范行政机关设立、审批行政许可的权力,扩张与保障公民的自由。然而,因为我国尚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公民没有基于自己的自由权去否定行政机关设定行政许可制度的法定权利,所以尽管我们可以为行政机关设定行政许可制度献言献策促使其科学化、合理化,但终究无法以法律手段去控制行政机关的许可设定权。就此而言,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许可设定权而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为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公民获得行政许可的权利,规范行政机关审批行政许可的权力,由此来确保公民的自由。进言之,尽管行政机关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制度来管制公民的原初自由,提高公民行使自由的门槛,但许可制度同样赋予了公民获得许可、恢复自由的权利(广义),所以只要确保这种权利能够规范行政机关的许可审批权,那么公民就能够获得原本就拥有的自由。 但现行行政许可法的观念与制度却并不足以保障这一方式能够得以有效实施,因为它奉行的是赋权观念,并没有完全并有效的确立公民在许可审批与实施环节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强化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恩赐意识。因此,我们必须以行者许可的自由精神为灵魂,回归行政许可的复权本质,确立公民恢复自由、获得许可的权力,让行政机关回归到行政许可的审批机关而非赋予机关的地位,从而确立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权能。为此,不仅行政机关应当转变观念,也应当修改《行政许可法》,通过调整其相关章节结构、修改相应条款来确立公民恢复自由、形成许可的权力,还要分立许可申请与审批程序,强化行政许可申请对行政机关的法律约束力,并建立相应行政诉讼类型来保障公民在行政许可制度中的权力。 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习惯性的定性为权力—权利关系,认为只存在着行政机关对公民的处分权,却认识不到公民和国家之间也有权力—服从关系的存在,认识不到公民在行政法上也有法定权力,也有改变既有法律关系、为自己和行政机关立法的权能,是赋权论的根源所在。换言之,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此前没有注意到现代行政权是由抽象立法权、具体处分权、制裁权、确认权与强制执行权等权力所构成的集合体,更在于那种只有行政机关才能掌握公法权力的潜意识。这实际上是把法律、法学领域的权力等同于社会学领域或政治学领域的统治权力了。不错,行政权是统治权的一个分支与形式,也具有韦伯所言的那种政治学、社会学上权力概念的属性:“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27]但在具体的法律关系领域,行政权也是实证法秩序中为法律所授予的法律权力,而不再只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统治权。同时,在法律领域,行政机关并不是始终、全面拥有行政处分权。它既存在不行使处分权而是行使确认权的情形,也存在不具有权力而具有服从地位的情形,还存在完全不存在权力或权利,只有自由,甚至无自由而只有义务的情形。如,行政许可表明行政机关在法律上的服从地位,而国家赔偿责任则意味着行政机关在法律上的义务地位。[28]与此同时,公民在行政法上不仅作为义务主体、服从主体存在,也作为权利主体、自由主体乃至权力主体而存在。 此前也有学者论证了公民在行政法中的权力地位。[29]但她所证成的权力,虽具有规范性,但并非完全的法律权力,而更具有社会学领域中权力的属性,其落实有待于公共决策参与各方之实力的角逐,因而具有极强不确定性。本文所证成的许可形成之权力,乃法律权力,即公民一旦行使即产生法律所能保障落实之法律效果的权力,具有较强确定性。不仅在行政许可中公民具有如此权力,在公共行政合同、政府采购、行政补贴以及其他诸如公立学校招生、国企招标等公共资源分配领域都有存在这类权力的空间。论证这种权力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我们更为正确的认识与之相关的行政法现象,重构因具体行政行为理论无法回应这些现象而出现的但又问题重重的一些理论——比如行政合同、补贴等带来的所谓双阶理论,还能建构相应的行政法制度,从而能够更好的规范行政、实现法治、实现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确立公民在行政法中的权力地位,由此确立公民在一些行政领域的支配地位与立法权能,将有力地改变当前行政法学以行政权、行政机关为中心的现状,建立以公民为中心的行政法制度及相应学说,从而有力回应如今公共参与、多元治理日趋蓬勃的现实。 注释: ①如姜明安(2011:225-226);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德国学者也持如此观点。如毛雷尔(2000:209-210);[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3页。 ②“行政审批”是一个内涵外延宽于但又涵盖“行政许可”的术语,有些行政审批并不为《行政许可法》规范和调整。基于法治与公民权利保障的立场,本文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反思以行政许可为论域,因此除非特别说明之处,本文所用“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概念同义。 ③如早期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英国法释义》中指出,“特许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所指的是由臣民所掌握的,但属于王室特权或国王特权之分支的东西”(see Blachkstone,Commentaries[*]37,Cf.Glanville Williams,The Concept of Legal Liberty,Columbia Law Review,1956.56(December):1133)。 ④美国学者霍菲尔德认为存在四种广义的权利及与之相依(correlative)的四种广义的义务,从而组成自成一体的两层次、四类型的实体法律关系:第一层次的是狭义权利(请求权)—义务关系及与其相反(opposite)的(特权)自由—无权利关系。自由代表着特定法律关系中法律主体无法律义务、他人无权利要求自由主体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法律地位,权利则代表着权利主体可强制性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法律地位;第二层次为权力—责任(服从)关系及与之相反的无权能—豁免(不服从)关系。权力指法律主体可以依照自我意志改变与他人法律关系、从而对他人形成支配的能力,而豁免指向免受他人权力支配的自由。See W.N.Hohfeld(1919:36-60)。因此,笔者此处所运用的“权力”,有其特指,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所泛泛理解的社会学、政治学上的“权力”概念。对此,还请各位读者明察。 ⑤李猛指出,近现代国家治理术的发育,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简单扩张,而是与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塑造,一种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是将一种权力技术与一种自我技术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近现代国家具有规训个人的功能。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⑥自由包括“自由的人民为有序的追求幸福而对不可或缺的、但长期被认为是特权的(许可)的普遍享有”(Meyer v.Nebraska,262 U.S.390,399(1923),Cf.Ernest Gellhorn & Ronald M.Levin,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Law Press,1999,p201)。 ⑦当然,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公民具有行使暴力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无法通过许可制度来恢复和创设,无法经由国家许可制度之逻辑而生成。因此,公民使用暴力的自由不属于许可制度规范的范畴,以特权而不是自由称之更为合适。 ⑧也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是符合许可制度之自由精神的。该条规定:被诉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违反当时的法律规范但符合新的法律规范的,判决确认该决定违法;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细言之,尽管许可人在获得许可时是不符合当时法定条件的,但在新的法律放宽了条件、许可人根据现行法律能够获得自由的情况下,取消此前的许可并无意义,因此只能判决被告违法。如果此前获得许可须经过竞争,那么一方不合法的取得许可,就意味着第三方的权利被侵犯。为保护第三方权利,就有撤销原许可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⑨一些学者否认这种法律关系的实在性,认为这种关系,除非经由基于具体的行为,否则就只是潜在的关系,抽象的关系。参见李建良:《行政法律关系序说》,《月旦法学教室》2005年第30期。 ⑩一般认为,哈特所言的第二性确认规则类似于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用于解决法律体系的究极渊源问题,因此争议很大。但是,正如哈特本人指出的,确认规则是用来解决规范是否符合法律规则的,因此,尽管终极的确认规则究竟为何确实是聚讼纷纭的问题,但是在既定的法律体系下存在确认规则以及相应的确认权,当毫无疑问,否则社会将如哈特所言,无法解决某一有争议的规则是否存在、有效的问题。而诉讼类型中的确认之诉,无疑正是这种确认权的体现。 (11)霍菲尔德以纯粹的逻辑方法,从私法领域中的司法判决中提炼法律关系时,并不考虑法律关系的落实问题与确定性问题,所以在他那里,行使权力所生成的法律关系就是自身有权威(authoritative)的法律关系。而在康芒斯看来,现实世界中一个法律行为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更涉及各自的竞争者,因此必然出现法律关系不确定的情形,由此必然需要公共裁决者。所以在他那里,权力所生成的法律关系需要上升为权威所认可(authorized)的关系,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关系。因此,康芒斯将法律关系分为自身有权威的法律关系和权威所认可的法律关系(See Massimiliano Vatiero,2010:853)。 (12)其实,确认行为与审判行为在很多时候是合一的。哈特即指出,确认规则很多时候就是赋予司法机关审判权的审判规则(See H.L.A.Hart,19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