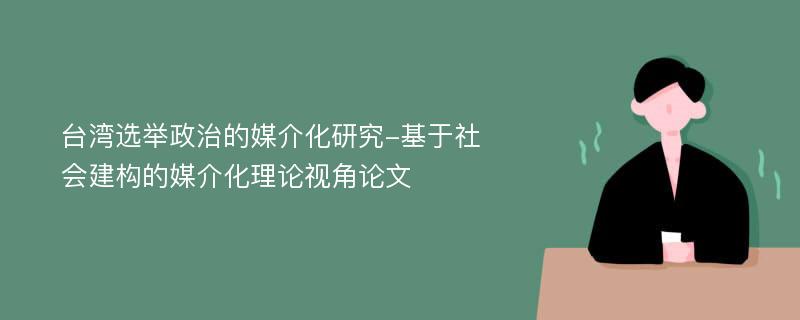
台湾选举政治的媒介化研究
——基于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视角
吴 静,连子强
(华侨大学 海峡两岸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361021)
摘 要: 在一个以信息和媒体逻辑为主导的“媒介化时代”,社会各领域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媒介化的动态发展中。 从戒严时期的“政治侍从”到“解严”后的政媒共生与政媒角力,再到当下围绕媒体逻辑运作的媒介化政治景观,与日俱增的媒介影响力一步步影响和塑造着当今的台湾地区选举政治。 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复杂的媒介化过程。 基于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视角,通过剖析不同时间节点和社会文化条件下台湾选举政治的媒介化过程,将获得审视台湾媒介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选举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全新视野,以更好地解释当下台湾选举政治的诸多现象。
关键词: 台湾选举;媒介化理论;社会建构;元过程;特征
随着互联网Web2.0 和移动终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强势介入与融合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媒介化生存阶段。 传统媒介理论和效果研究已无法解释当今媒介对社会各领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大量有关媒介化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个案考察(诸如政治媒介化研究、宗教媒介化研究、游戏媒介化研究等等),使得媒介化研究已经成为近十年来欧洲传播学界中的一门“显学”。[1]与国内传播学界尚处于译介欧洲媒介化理论或仅将媒介化作为背景使用不同,欧洲媒介化研究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从广义上讲,“媒介化”指代一种社会变革过程,它是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联系中发生的。 而媒介化研究,便是在重新审视和定义媒介及其自身技术价值的前提下,致力于媒介化概念的清晰化,并聚焦关注媒体及其传播过程与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媒介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前,媒介化已经成为一个思考媒介、文化和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框架。[2]
在对媒介及其技术对社会影响的学术辩论中,不同的理论基础使媒介化研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研究传统。 以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克洛茨(Friedrich Krotz)、赫普(Andreas Hepp)、舒尔茨(Winfried Schulz)等英、德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传统”(social-constructive tradition),以“社会建构论”为理论基础,主张从社会、文化整体的、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媒介化过程,是对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的“制度化传统”(insititutionalist tradition)用单一的媒介逻辑来解释媒介社会效应的纠偏。[3]他们主张将媒介化视为一个同全球化一样复杂的、持续不断发展的元过程(meta process)。它是一个媒介与社会、文化现实长期互动建构的动态性过程,在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中具有不同的强度和方向;其核心议题是关注媒体变化与日常生活、身份认同、文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4]克洛茨和赫普二人将媒介的定义一般化为“传播过程的调节器或修饰器(as something that modifies and transforms communication)”,即传播塑造者,因为媒介具有社会制度与规范网络、技术设备、舞台装置、经验空间四重特征,其中前两者属于结构性特征,后两者属于情境性特征。 “只有当一项媒介技术作为一个经验空间,并通过社会制度和规范、个人和集体的期望融入社会,这项技术才发展成为一个结构和情境的独立存在体,从而实现媒介化运作。”[5]这意味着,当人们基于传播目的使用一项媒介技术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期望将作用于这项技术并创造出特定的媒介环境。 这个媒介环境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社会行为活动进一步结合,不断产生新的媒介现实。 从最初的对人类传播能力的延伸(extension)到媒体部分替代(substitution)社会交流活动,对事件性质产生塑造和改变;再到媒体的使用被编织进日常生活结构,与非媒体领域深度融合(amalgamation);最后达致媒体日益重要,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行动者不得不适应(accommodation)媒体运作方式和逻辑规则。 舒尔茨用“延伸”“替代”“融合”“适应”归纳了社会变革过程中媒体发挥作用的四个过程。[6]其中,“适应”过程采纳了制度化传统中对媒介逻辑的论述,这一过程在斯托贝克(Jesper Strömbäck)对政治媒介化的具体研究中被进一步表述为:当媒体基本独立于政治机构之外,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且媒体内容和政治行为者都受到媒体逻辑制约和支配时,我们可以说政治媒介化进入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7]归纳而言,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要点有三:一是媒介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元过程,需要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具体观察媒介的影响;二是将媒介的四重特征及其运作的四个变化过程作为分析工具,从而考察媒介在社会变革中如何发挥关键作用;三是媒介化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关注媒体变化与日常生活、身份认同、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总之,“‘媒介化研究’所呈现的是一场重构媒介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理论转向”,已然成为媒介化生存时代的“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8]当这一理论框架与中国这个多元内涵的社会文化土壤及瞬息万变的媒介实践之间相互碰撞,必将激起崭新的思维火花。 当前国内已有运用制度化传统的理论视角研究单一媒介对某一特定领域的作用,[9]但这些研究大多忽略了制度化传统的局限性,无法以更加具体的、历史的维度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与当时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欧洲媒介化研究的社会建构视角及其理论方法,依托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中社会利益多元复杂、舆论场角力激烈、政媒互动发展的社会文化情境,展开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媒介化研究,展示长期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媒介的发展变迁和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当今台湾地区的选举政治。 期望通过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更加翔实而充分地了解不同媒介和社会文化环境作用下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发展脉络和行为逻辑,为当下高度媒介化时代的台湾选举政治传播研究打开新的研究思路。
一、1950—1987 年: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萌芽期
(一)政论杂志开启选举的媒介化运作
国民党自1945 年退台之后,因政治资源分配不均引发台湾社会严重的省籍冲突问题,并于1949 年5 月进入战后戒严时期。 为装饰民主门面,寻求国际社会支持和缓和岛内社会矛盾,国民党于1950 年开始推行地方自治选举制度。 但此时的地方自治选举制度镶嵌于戒严体制中,国民党不仅实施报禁,全面垄断报业和广电媒体,而且严厉禁止组建新政党参选。 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报纸和广电系统正发挥着一种社会制度与规范网络的结构特征,媒介控制者通过政治控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去实施一套符合国民党“全面戒严、反攻大陆”目标的单向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由此看来,受到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和广电媒体只是一种依赖政治制度的技术设备,仅仅是政治行为者的“传声筒”,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尚未形成一种情景特征和结构特征相结合的媒介化运作机制。
合作学习应该是全体小组成员的合作学习,每一个小组成员都是学习的主体。教师要重点观察个别学生消极学习的现象,这些学生往往依赖于其他小组成员,缺乏参与的主动性,教师要通过观察,及时加以引导,激发消极学生兴趣,使全体小组成员主动参与合作学习。
作为国民党装饰民主门面和社会“安全阀”的政论杂志,既是国民党统治考量下承担公众舆论表达的社会制度与规范媒介,也是被政治异见者及广大民众赋予民主自由、打破威权专政等社会期许的重要技术设备。 面对国民党森严的思想钳制、言论管制、政治参与自由限制,从1950 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各界反对势力与之进行了不懈抗争。 从1950 年代初《自由中国》到1970 年代的《大学》《台湾政论》,再到1980 年代的《美丽岛》《八十年代》,台湾社会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充分发挥政论杂志的技术优势,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宣传民主理想,抨击国民党威权,呼吁政治革新,利用杂志来集结反对力量,助力反对派人士选举,为反对派组织化、党派化提供重要场所。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政论杂志最终成为反对派人士进行选举动员、集结力量的舞台装置,同时也借由“美丽岛事件”为台湾民众营造了重要的经验空间,具体地、情景化地建构和解释了台湾民众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威权的政治认同。 在此,政论杂志成为一个情景特征与结构特征并行的媒介化运作机制,在台湾政局风起云涌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政论杂志与多元复杂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共同作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与台湾岛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为党外运动的活跃和选举政治的媒介化运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首先,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 1971 年蒋介石集团代表被逐出联合国、美国承认“一个中国”、1970 年代末美蒋“断交”接连冲击岛内社会各界所持“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信念,重创国民党执政合法性,使得国民党威权体制逐渐陷入危如累卵的境地。
独立学院大多依托母体高校建立起来的,而母体高校是一本、二本学校,他们的教学观念和教学体系与独立学院有很大的区别。母体本科院校注重理论教学,注重培养工程型人才,而独立学院培养目标是“技术型”人才,具体说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独立院校在建设初期,往往是依托母体的优势专业或者是特色专业建立起来的,因此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基本都是照搬母体学院,造成了独立学院教学体系与母体基本相同,培养目标不明确,失去了独立学院的办学特色。
综上,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媒介化进入融合期,媒介的四重特征进一步发挥作用。 社会各领域与媒介深度互动,共同建构起“选举至上”的政治经验空间。 在这里,人们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民主观念和日常生活都被媒介所建构和影响。 当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带来一个更为开放、鼓励参与、双向互动的媒介环境时,政治逻辑逐渐失去对媒体内容和政治行为者的绝对支配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网络媒体在选举政治中仍旧只是传统媒体的补充和延伸,尚未完全显现颠覆性的政治影响力。 以电视、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仍然是2014 年之前影响选举政治的关键媒介。
再次,“美丽岛事件”作为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对立冲突达到高潮的标志性事件,使政论杂志的情境特征进一步凸显。 在这一事件中,党外势力、普通群众与国民党高调对抗的角色扮演,高雄人权纪念日游行活动警民冲突的激烈情境,以及事件公开审讯论辩过程中辩护律师和家属的受迫害者角色演绎及情境感染,在岛内外媒体的传播下,撕开了威权体制的民主假象,显示出国民党专制独裁本质,在台湾社会和国际社会中引发强烈反响。 事后,台湾民众对党外人士的隐性支持上升为显性支持,深刻影响了1980 年代初的选举结果。
最后,1980 年代国际社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1]席卷全球,国际局势和岛内社会压力共同推动台湾地区进入政治和社会转型关键期。 发达的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迁,中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使得台湾社会各界力量的民主诉求和社会诉求进一步升级。 大势所趋下,1987 年7 月国民党正式“解严”,“党禁”“报禁”随之解除,1986 年民进党的成立结束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台湾地区从此迈上多党竞争的政治民主化之路。
总而言之,在台湾地区选举政治制度实施之初,政论杂志就逐步参与到竞选传播过程中,在推动台湾地区民主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出于执政当局“安全阀”的政治考量、政治反对势力的能力所及和社会期许,政论杂志当仁不让地发挥结构性特征(社会制度和网络规范、技术设备),肩负起党外人士的传播目的,并在实践中,逐渐凸显其情境性特征(舞台装置、经验空间),使政论杂志成为政治生活、选举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初步形成了选举政治的媒介化运作机制。 同时,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具体、情境化地呈现和解释了国民党和党外势力、省籍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及其权力争夺,孕育出了“选票即一切”“选举至上”的选举文化。 “美丽岛事件”则是政论杂志这一媒介与1970 年代台湾社会复杂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共同发生作用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为受“美丽岛事件”触动的新生代党外势力建构起共同的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社会体验等经验空间,为日后民进党以政党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当然,在肯定政论杂志的积极意义的同时需要指出,这一阶段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媒介化程度仍处于萌芽阶段,因为人们获取重要信息的途径来源是多元的,并非以媒体为主。 媒介并未独立于政治制度之外,媒体内容和政治行为者也主要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
二、1988—2000 年: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延展期
(一)媒体资源解放带来媒介化新发展
1988 年元旦,台湾地区正式解除“报禁”,台湾报业进入自由市场竞争时期,选举政治也随之进入新阶段。 1989 年台湾地区修改“公职人员选罢法”,删除此前“候选人或其他助选员不得利用大众传播工具刊登广告从事竞选活动”的规定,标志着竞选广告在台湾政坛解禁。 作为普及性最广、信息量大、时效性和权威性最高的新闻媒体之一,报纸逐渐成为人们了解时事的主要信息来源。 报纸媒介在这一阶段得以充分发挥其结构性特征,在社会监督、公众舆论乃至丰富公众娱乐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报纸也通过议程设置和拟态环境来建构人们的政治认同、身份认同、日常生活乃至民主观念等。 然而,竞选广告的可观收入和与政经利益结盟带来的政策利好使台湾报业的言论及政治立场难免受制于政治逻辑。 不同的政治立场导致各大报纸在公共治理问题和选举议题上偏向不同的政党团体,在影响选民对选情认知和判断上发挥显著的议程设置功效。
和报纸一样,广播电视等媒体资源也被社会各界普遍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和规范网络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同时电子媒体强大的传播功能必然被新兴政党视为扩大政治影响力、获得更多选票跻身政坛的必要工具。 因此,向垄断电子媒体资源的国民党手中争夺媒介话语权,争取媒体资源的全面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务。 除报纸之外,体制外的非法媒介“地下电台”亦成为建构人们政治认同、社会行动的重要经验空间。
首先,地下电台技术门槛低,成本低廉,且架设简便,易于躲避查禁,具有很强的空间地域传播效果;使用闽南话广播、关注民生议题等接地气的传播方式,帮助其迅速填补了主流媒体传播的“盲区”,在台湾广大偏乡地区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逐渐为民进党累积和号召了大批中下阶层的支持者。 其次,地下电台在帮助民进党赢得选举方面功不可没,而行政权力的获得也为地下电台的合法化和要求开放广播媒体资源提供了政治保障。 1993 年国民党当局开放广播频道资源,标志着台湾地区广播媒体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新阶段。 民进党整合手中掌握的合法电台和地下电台资源,迅速构建起一张遍布全台、可与国民党抗衡的全岛性广播媒体网络。 最后,民进党一面利用平面媒体和电台资源论证开放电视频道资源的必要性,使电视频道开放成为广泛的社会议题;一面联合“知识界反政府迫害联盟”“台湾学生制宪联盟”等民间团体发动抗议游行、座谈等社会运动,呼吁社会关注国民党长期垄断电子媒体的问题,[12]向国民党施压,并最终获得了电视资源开放。1995 年6 月,以民进党为背景的“民视”获得经营许可,它的设立昭示着民进党最终突破国民党的电子媒体垄断,扭转了自身媒介话语的弱势地位。
1.2.2.3 独立生活能力训练:每周1次,每次40 min。向患者讲解良好的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进行基础评估,与患者共同制定个体化日常行为规范,督促其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整理病床、洗漱、自动排队进食服药及定时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组织患者看电视、报刊和杂志。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患者有规律的生活和自理能力。
(二)全面直选为媒介进一步影响选举提供支持
如果说2014 年之前,在对台湾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的社会运动(如反媒体垄断、洪仲丘案等)中,社交媒体已经开始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补充的话,那么,“太阳花运动”则是社交媒体对台湾政治的塑形力和影响力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 一方面,在“太阳花运动”中,社交媒体使更多台湾民众成为大众传播者,使之能以更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影响力进入到公共领域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进而有力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 2014 年底“九合一”选举中作为“政治素人”的柯文哲凭借“网络选战”策略获得广大台湾青年的支持成功当选台北市长,便是对社交媒体政治影响力的再次确认。 另一方面,自2014 年底“九合一”选举之后,社交媒体正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影响议题、引导舆论、动员投票、筹集捐款的关键战场,并催生新的“网红”竞选模式,使非典型政治人物粉墨登场。 此后接连三场选举皆印证了政治行为者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不得不积极适应新媒介环境变化与媒体逻辑规则。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目前尚缺乏公认的下肢淋巴水肿评估及诊断标准,造成相关妇科恶性肿瘤术后下肢淋巴水肿发病率报道不一;(2)尚不清楚疾病分期、术后随访时间、具体合并症等对水肿发生的影响,有望在后期研究中进一步明确。
首先,社交媒体最大特征是赋予每个用户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21]这让众多网络用户成为意见表达者,民众影响力被释放,从而汇聚形成社交媒体影响力。 而拥有一定数量拥趸者的任意网络个体都可能成为某一话题的意见领袖,或在政治事件和议题中展现出强大的号召力。 台湾学者陶振超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的相连的自我中心网络、汇总资讯媒体,以及分享三项特征,建立起“虚拟接近性”,使人们重复暴露于相似主旨的资讯,观察学习引发仿效行为,从而提高了社会运动参与的机率。[22]因此,社交媒体既是民众监督政府、意见表达、交流互动的社会机制和沟通网络,同时也是一个情绪扩散、寻找盟友、动员抗争的大型剧场,任何个体都能在其中兼具演员和观众的双重角色,被他人或真或假的经历所感动,从而成为建构集体记忆和促发集体行动的经验空间。 进而,网络议题设置和舆论导向的隐蔽性、突发性、多元性等不可控因素使媒体行业精英和政治组织难以及时有效地监测和抑制,致使传统媒体行业和政治组织的政治传播策略发生了从“带风向”到“看风向”的转变。
[ 2] Andreass Hepp,Stig Hjarvard,Knut Lundby. “Mediatization: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Media, Culture & Society,2015,37(2):315.
三、2000—2014 年: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融合期
(一)社会各领域与媒介深度融合,边界消失
2000 年台湾地区首次政党轮替,岛内政治生态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泛蓝”“泛绿”两大对立阵营,围绕选举产生的蓝绿政治恶斗成为21 世纪以来台湾地区政治生活的主线。 另一方面,进入21 世纪的台湾地区媒体业蓬勃发展,频繁的选举活动为媒体行业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广告来源。 日益精进的新闻采编与影视制作技术,以及民众对娱乐消遣的需求,使电视政论、政治模仿秀等电视节目类型大受欢迎。 由此,台湾大众传媒业与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深度融合,媒体与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政治领域的边界逐渐消失,高度媒介化环境下人们的政治参与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均受到媒介建构的媒介现实之影响,台湾地区选举政治媒介化进入融合期。
由于媒体经营的生存压力,广告费和政治文宣费等成为重要的获利来源,它们一旦被政治势力控制,媒体便很难有独立的坚持。[15]除了使用经济手段控制媒体之外,民进党上台后还利用行政手段“喂养”亲绿媒体,给异己媒体设置障碍,甚至发动“联合报退报”“包围中天”“围剿郭冠英”等社运公然干涉言论自由。 其目的是通过媒体建立起话语霸权,独占“新台湾人”和“民主”的解释权,使言论市场向民进党意识形态靠拢。 另一方面,在商业化竞争加剧和大众文化消费导向下,媒体也往往选择具有争议性和娱乐性的政治花边新闻、政论节目和政治模仿秀等来吸引受众。 选举政治蕴含极大商业价值,故媒体趋之若鹜。
v点最坏情况下关联个3-面,个6-面,v的邻点均为3度点且v的非三角邻点关联着一个3-面。由R1,R2.1,R3.1或R3.2或R3.4及最坏3-面9+-点情形得:
法院微信文章同时还提到:“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生态修复性司法,根据谁破坏谁修复原则,承办法官庭前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林某娘家属,敦促林某娘复植补种或缴纳复植补种保证金,并深入被毁坏山场现场勘验其复植补种情况。但家中经济条件尚可的林某娘至判决前始终未落实复植补种措施,也未缴纳复植补种保证金,使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场至今仍处于荒废状态。”为此,法院认定林运娘在毁林后没有悔罪情节,酌情从重处罚。
(二)高度媒介化环境下的台湾选举景观
据统计,自2000 年政党轮替后到2014 年3 月前,在此13 年间,台湾地区共举办11 场选举活动,其中包括3 场地区领导人选举。 由此,台湾政治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选举奇观:大大小小的选举接连不断,竞选广告和文宣攻势铺天盖地,各路媒体紧锣密鼓地跟进选情、挖掘边角话题。 无论是传统大众传播媒介还是新兴的互联网,它们对于选举活动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都在日渐增强。 政客们既可以利用媒体制造舆论、炒作事件和议题来吸引选民注意和支持,也可以将自己置于镁光灯下,进行符合选民心理预期的政治角色扮演,还可以利用历史事件激发社会矛盾,迫使选民在“外省人或本省人”“迫害者与被迫害”“统一或独立”“民主与专制”等二元对立的单选题中做选择。
在此,非黑即白的叙事策略,夺人眼球的政治表演,喧嚣吵闹的政见表达都可以成为“媒介事件”引发争议。 这使得竞选团队的媒介化操作不断专业化、政党斗争在媒介现实中恶性发展、社会认同不断被撕裂,使民粹式的政治操作有机可乘。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04 年“大选”期间发生的“两颗子弹”事件。 选前最后一天,民意支持落后的陈水扁在台南遭遇枪击,一时间“子弹在扁身上”“生死未卜”“国民党与大陆迫害暗杀台湾之子”“台湾人悲情”等谣言四起,绿营媒体疾呼“台湾人选台湾人”,最终使陈水扁一夕翻盘当选。 “两颗子弹”事件疑云密布,不少人质疑这是一场民进党自导自演的“选举奥步”。
物联网接入网关内置多种协议设备模板,可以将不同协议的设备数据转换为标准的软件组件,通过标准TCP/IP协议、支持XML的数据处理和开放的API为智能楼宇应用服务提供无缝的、统一的设备数据视图,从而实现数据融合处理和跨系统的互联互通。
随着Web2.0 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交流、获取资讯方式、公众讨论空间乃至普通民众的媒介话语权等均被改变。 网络媒介在聚合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优势和四重特征上,进一步对选举政治产生影响。 从2010 年开始,台湾地区选举开始延伸进网络领域。 互联网媒介成为又一个竞选渠道和舞台装置。 在选举中专门抹黑竞争对手形象、制造竞争对手负面谣言的“网络绿林军”也应运而生。
其次,国民党应变求存,逐步推行“政治革新”,为党外人士壮大力量提供重要条件。 1969 年国民党政权便因限制党外人士参选、缺乏新鲜政治力量而导致政权老化问题,出于获取岛内社会支持的目的,国民党主动开放增补选举,使康宁祥、黄信介等台湾本土政治人物和党外运动核心人士有机会进入政坛。 一定程度的言论空间和政治参与开放极大鼓舞了党外运动人士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也使反对派人士参与竞选并成功当选的概率大大升高。 党外人士积极“藉由选举推动政治改革,利用胜选后的公职保护杂志”[10]来壮大党外势力。
四、2014 年至今: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适应期
(一)社交媒体翻转台湾地区选举政治
媒体资源的全面解放为媒介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带来了选举政治媒介化的新发展;与此同时,李登辉主政下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又为媒介进一步影响选举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持和议题储备。
社交媒体之所以借由“太阳花运动”翻转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不仅在于其本身具备颠覆性的政治潜能,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交媒体被年轻网络世代赋予了重要的社会期许,在严重分化的台湾社会中承担起了促进选举政治转型的催化剂角色。 清华大学郑振清教授指出,台湾社会存在的四大社会分化问题,既包括几十年来既有的认同分化、阶级分化问题,也包括近几年凸显的贫富差距分化和世代分化问题。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网络化社运动员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显著,“各类新、老分化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行动能力十足的社会力量、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社会舆论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冲击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精英主导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选举动员模式,改变了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16]2008 年国民党重返执政后奉行“不统不独不武”政策,助长了“台独”分子持续搅乱台湾社会的势头。 长期的恶性政党斗争,扭曲撕裂的国族认同,加上不断涌现的新社会矛盾持续刺激着不同社会群体的自利意识。 在绿营媒体、网络“绿林军”对两岸经贸合作关系的抹黑和污名下,“恐中”“反马”的对抗思维蔓延开来。 2008 年以来不断分化的社会致使激进的网络世代不满生存现状,“台独化”、年青化、网络化的政治化社会运动不断涌现,并与选举政治相互交织,[17]冲击执政当局的执政效能,影响政治决策过程。 有分析指出,2014 年“太阳花运动”的爆发正是台湾社会世代矛盾、蓝绿矛盾、阶级矛盾和国民党内斗四大矛盾有机结合的产物。[18]
(二)政治行为者适应社交媒体逻辑的必然性
根据台湾地区媒体白皮书显示,到2014 年互联网已连续8 年成为台湾地区12-65 岁民众第二大消息来源,2014 年网络涵盖率近七成(68.5%)。[19]2014 年《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数据亦指出,2014 年台湾民众使用网络社群应用的比例超过浏览网页高居首位(64.32%)。[20]可见,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习惯乃至行为方式。
英当然知道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死亡,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的归宿。这一辈子,英目睹过太多的死亡,亲戚乡邻,年老者自然而去,年轻者猝然离世。死亡对英而言并不陌生,并不可怕,也并不遥远。但是,突然倒下的英却不停地颤抖起来,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害怕,是害怕死亡?还是害怕疼痛?归根结底,是害怕在疼痛中死亡,垂死挣扎的凄凉,漫长而痛楚。她是希望自己安然而去。
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利用“解严”后岛内社会对民主化的期待,将台湾的“民主政治扭曲成为一种超脱法制与宪政体制的民粹主义”。[13]所谓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反对精英主义,强调极端平民化倾向的社会思潮或政治运动,在政治实践中常表现为政客利用“人民的名义”牟取政治资源和利益。 如在选举制度方面,李登辉积极推动1990 年代初“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直选和199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的实行,宣告台湾地区从地方到“中央”进入“全面直选时代”。 同时通过对宪制性文件的数次修改使得地区领导人的权力不断扩大,严重破坏了民主制衡原则。 因此,岛内各方政治势力为抢占选民,纷纷利用手中的资源在媒体经营领域“圈地”,媒体成为各党派政治表演、权力斗争、抹黑对手的舞台装置。 在选举议题上,李登辉还善以诉诸民意的方式煽动民粹排挤、打压、制裁异见媒体(如1992 年的“退联合报事件”),左右民众认知;同时大力鼓吹“台湾主体意识”,炒作“统独”争议,设置议题主导舆论成为重要的竞选策略之一。 在大众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中,政党权力斗争甚嚣尘上,“对抗”成为台湾地区政治转型以来政党互动的主要方式和突出特征,[14]确立了当下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基调。
其次,社交媒体带来台湾地区民众的民主自觉。 它冲破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拓展民众的政治认知,尤其刺激网络年轻世代的政治参与意识。 民众开始挣脱被操纵的木偶和投票机器的角色设定,对政党和政治人物行为更多的是警惕、质疑和纠偏,并开始运用新媒体积极主动地介入选举政治以图改变自身处境。 台湾学者何明修直言,“太阳花运动”之后,一股青年参与的风潮崛起,台湾社会已被彻底翻转。[23]萧新煌亦指出,“太阳花运动”后,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力量开始散逸出来,2014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结果就是明显例证。[24]范畴观察2014 年至2018 年的三次选举结果后指出:“2014 年的地方选举是台湾政治的某种转折的开始……多数选民已经形成一种概念,即任何没有自省能力、纠错能力的政党都是不可信的;台湾最急需的是真人说真话、实人做实事。”[25]总之,2014 年台湾政治出现了“新政治人物、新阶层(特别是年轻族群)、新技术与新媒体、新意见领袖、新舆论操盘手”[26]五种新兴力量。 他们以新技术与新媒体为中心,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从“太阳花运动”、2014 年底“九合一”选举,到2015 年以“太阳花运动”参与者为背景的“时代力量”成为“立法院”第三大党,从2016 年选前的“周子瑜事件”引发两岸网友“脸书大战”间接影响当年选情,[27]到2018 年底“韩流”席卷全台,反复证明台湾地区选举政治媒介化进入一个以媒介为中心的阶段。
自2014 年台湾选举政治正式进入社交媒体选战后,手执社交媒体“武器”的选民在政媒角力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党及候选人—选战媒介—选民三者间的力量对比从此发生改变。 网络世代依靠社交媒体实现政治变局,催生了新的政治参与路径和选举动员模式。 媒介技术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运行机制,也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2019 年年初,台湾政坛刮起“网红政治风”,蔡英文勤更社群媒体搏人气,被质疑为博下一届不务正业。[28]这进一步表明,当下台湾政党、政治人物等都不得不积极适应社交媒体的运作逻辑来谋求政治目的的实现,选举政治的媒介化已然步入一个以媒介逻辑为主导的稳定状态。
五、结 语
在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框架中,台湾地区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与以大众媒介为基础的政治行动互动建构起了特定的媒介环境。 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媒介环境也处在动态变化中,不断与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共同建构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情境。 戒严时期借由政论杂志助力选举,扩大政治活动空间,最终推动民主化转型;“解严”后反映在媒体资源竞争上的政党斗争和全面开放的选举制度开始撕裂台湾社会认同;民主巩固时期呈现在电视图像上的蓝绿恶斗和“选举至上”的媒介景观持续降低民主品质和撕裂社会;以至于当下社交媒体与网络直播等新媒介日益成为塑造选民、政党、政客乃至媒体行业行为的框架。 当前,台湾地区选举已进入“以媒体为中心的动态之中,政府、政党和其他既有政治机构的精英正在失去对公共领域的政治传播和解释方式的控制,一种复杂的,通常是矛盾的、动态的离心力过程,将政治传播引向媒介逻辑、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29]可以说,台湾地区的选举政治是台湾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历史文化心理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与变化发展着的媒介长期互动建构的结果。 因此,通过对选举政治的媒介化进程的梳理,可以把握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发展脉络,也可以从媒介化现状的把握,进一步理解台湾地区选举政治的实质,探寻选举政治的未来发展动向。 大众传媒是当前两岸传播的重要渠道,当前两岸社会处于媒介化生存的不同历史阶段,面对变动不居的两岸关系,媒介化研究范式也不失为研究两岸传播的种种问题的新思路。
注释:
此外,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领域也在媒介技术连接下与政治领域深度交融。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不仅是主要的政治信息来源,亦是日常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电视名嘴、意见领袖对公共议题和政治话题的唇枪舌战、报纸“腥色膻”的政治娱乐新闻、电视政治模仿秀等与层出不穷的政党人物丑闻、议题争斗、政治作秀等交汇在一起进入民众日常生活,不仅成为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话题,也深刻影响选民的政治认知、态度和情感。 加之频繁曝光的政治和选举活动、重大社会活动、各类社会运动通过多媒体报道成为重要程度加深、仪式感增强的“媒介事件”,让选民的政治参与感有所提升。 由此个体在媒介构建的意识形态撕裂的社会文化空间中逐渐建构起民粹化、泛政治化、包容度低的思维方式和狭隘、撕裂的政治认同与民主观念。
[ 1]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 ——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5 期,第47-48 页。
12 年间,尚在起步的台湾地区民主政治与公民社会在图谋“夺权”的在野党与图谋“台独”的当政者的联合夹击下,被窄化为“数人头”的选举政治,民主政治的品质极大降低。 这一时期,报纸、广播、电视媒体逐步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来源,部分摆脱了对政治资本的依赖。 媒体内容和政治行为者行动虽仍受政治逻辑支配,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党竞争、选举议题撕裂国家认同、竞选传播走向民粹化等一切特征都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解放和深度参与。 媒介不断延伸进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形成新的媒介现实,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方式、生活场景和行为习惯。 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台湾地区选举政治媒介化的延展期。
[ 3] 尼克·库尔德利:《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42-143 页。
[ 4] Friedrich Krotz. “Mediatization as a Mover in Modernity: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hange”,Knut Lundby. Mediatization of Communication,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4,pp.136-139.
[ 5] Friedrich Krotz,Andreass Hepp. “A Concretization of Mediatization:How Mediatization Works and Why ‘Mediatized Worlds’ Are a Helpful Concept for Empirical Mediatization Research”,European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2013,3(2):119-134.
[ 6] Winfried Schulz.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4,19(1):88-98.
[ 7] Jesper Strömbäck.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8,13(3):228-246.
[ 8]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第147-156 页。
火热的背后,是截至去年底申报上来的统计数字,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发布的统计结果,我国当前有269个平台类产品,装备、消费品、原材料、电子信息是主要应用方向。工信部有关负责人称:“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快速增长。目前,有一定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区域平台超过50家。”
[ 9] 如唐士哲:《从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电视政论节目作为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中华传播学刊》2014 年第25 期;黄旦:《报纸革命:1903 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6 期;潘祥辉:《“秦晋之好”:女性作为媒介及其政治传播功能考》,《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1 期等。
[10] 美丽岛事件口述历史编辑小组:《走向美丽岛》,台北:时报出版社,1999 年,第86 页。 转引自佟文娟:《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1949—2007)》,厦门大学学位论文,2008 年,第25 页。
[11] 根据亨廷顿的定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的是1974—1990 年间大约30 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转型。 本文仅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时间性解释影响台湾政治转型的国际大环境,对该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意义不做深入探讨。
2.3 分娩方式 高龄组(高龄初产、高龄经产)剖宫产率54.6%(20 875/38 255)明显高于非高龄组的35.5%(69 694/196 5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12] 佟文娟:《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98 页。
[13] 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 年,第319 页。 转引自倪延年编、张晓锋著:《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第4 卷·港澳台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511 页。
选取2015年3月—2016年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动脉瘤患者24例,其中男性患者11例,女性患者13例,患者年龄40至65岁,平均(56.2±7.1)岁,所有患者均经过外科手术证实为动脉瘤。
[14] 林劲、郭红斌:《当代台湾政党互动分析》,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 第186 页。
[15] 王茹:《民进党对媒体及民调的政治运作》,《台湾研究集刊》2002 年第4 期,第34 页。
[16] 认同分化问题指基于省籍—族群—“统独”问题的认同分化;地域分化问题主要指南北部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贫富分化问题指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包括阶层分化、财富分配不均、反商仇富心态等;新兴的世代分化问题主要指以“首投族”为代表的新世代与中老年世代在社会心理、国家认同、政治参与、生活态度等方面的矛盾。 参见郑振清:《分化社会挑战民主政治——台湾政治周期及其经济社会根源》,《文化纵横》2016 年第2 期,第58-65 页。
[17] 张文生:《2008 年以来台湾社会运动的政治化倾向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5 年第6 期,第3、5 页。
[18] 马军:《港刊分析反服贸背后的台湾社会四大矛盾》,海外网,2014 年3 月25 日,http:/ /opinion.haiwainet.cn/n/2014/0325/c345416-20448577-3.html。
[19] 台北市媒体服务代理协会:《2015 年台湾媒体白皮书》,第7、72 页。
[20] 吴沛真:《2014 年〈台湾宽频网路使用〉调查结果公布》,财团法人台湾网路资讯中心,2014 年8 月19 日,https:/ /www.twnic.net.tw/NEWS4/135.pdf。
[21] Antony Mayrield.“What is Social Media”,Icrossing.Co.uk/ebooks,August 1,2008, https:/ /www.icrossing.com/uk/sites/default/files_uk/insight_pdf_files/What%20is%20Social%20Media_iCrossing_ebook.pdf.
2.1.3 CGF促进骨组织修复再生临床应用 CGF在口腔外科方向临床运用上,国内外学者做了多方向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结果。有学者[15]通过在临床上拔除下颌智齿60颗,将CGF压制成膜放入拔牙窝中,在术后3个月和6个月用影像学观察拔牙创,得出结论CGF可减少拔牙创吸收、减少炎症反应以及促进创口软组织的愈合。龚仁国等[16]在下颌第三磨牙拔出后的牙槽窝内放入CGF,通过观察创口出血情况和术后并发症发现CGF可以减少拔牙创面的出血情况和干槽症的发生率,并且在饮食、疼痛等方面的 PoSSe值均低于对照组。这些临床研究提示:拔牙术术后运用CGF可比较明显减轻疼痛和并发症,加速骨组织和软组织的愈合。
[22] 陶振超:《社交媒体的动员力量:网络机会模式之观点》,《新闻学研究》2017 年第131 期,第49-86 页。
在对程序进行静态分析时为了构造和逼近程序的不动点理论,Patrick Cousot和Radhia Cousot在1977年提出了基于格的抽象解释理论[8]用于对程序的语义进行可靠近似。程序具体的对象域上的计算称为程序的操作语义或者指称语义,描述了对象域上的计算过程[9]。对程序的抽象解释过程可以描述为通过对待分析程序在抽象域上的计算,使得抽象域上的计算结果尽可能地逼近程序在具体域上的计算结果过程。通过程序在抽象域上的计算结果来获取真实程序计算结果的某些信息。抽象解释实际上是通过损失一部分的计算结果的精确程度来取得较高的计算速度。是在计算结果的精度损失和计算时间效率之间的一种平衡。
[23] 何明修:《历经318 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社会已被彻底翻转》,关键评论网,2015 年8 月19 日,http:/ /www.thenewslens.com/post/132636。
[24] 转引自《第三势力崛起,政治现实大考验》,《中国时报》(台北)2016 年1 月17 日,参见:https:/ /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60117000600-260107。
[25] 范畴:《做自己还是听政党? 选民要真人政治》,《中国时报》2018 年11 月6 日,参见:https:/ /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81106000723-260109。
[26] 邹振东等:《大数据视域下的2015 年台湾网络舆论场》,《台湾研究集刊》2016 年第6 期,第46 页。
[27] 根据台湾智库民调显示,2016 年选前因“周子瑜事件”引发两岸“脸书大战”间接影响三成二(32.8%)的年轻人返乡投票支持民进党。 参见台湾智库研究部:《2016“总统”大选后:台湾民众对新政局的期待民调记者会》,2016 年1 月21 日,https:/ /www.taiwanthinktank.org/single-post/2016/01/21/2016。
[28] 《蔡英文启动网红模式勤更社群媒体搏人气 网友:为了下一届?》,中国台湾网,2019 年1 月15 日,http:/ /www.taiwan.cn/taiwan/jsxw/201901/t20190115_12131865.htm。
[29] Kees Brants,Katrin Voltmer.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Postmodern Democrac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1,p.2.
Mediatization Research on Election Politics in Taiwan:Based on Social-Constructive Tradition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Wu Jing, Lian Ziqiang
Abstract: At present,we're entering the age of mediatization dominated by information and media logic with all fields of society experiencing a historic symptom of mediatization. From the “political servant” in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to the coexistence of political and media force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then to the current political activities around the logical operation of the media, the growing media influence has gradually influenced and shaped Taiwan electoral politics. This election politics is undoubtedly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development. The social-constructive tradition of mediatization theory will provide us with a new filed of visio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media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ion politics.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ow different time node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ffect the mediatization process of Taiwan election politics,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hange,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elector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so as to help us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lection politics under way in Taiwan.
Key Words: Taiwan election,mediatization theory, social-constrctive, meta-process,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590(2019)05-058-09
基金项目: 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语境下海峡两岸民间传播与社会认同建构研究”(14CXW017)
作者简介: 吴 静,女,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连子强,男,博士,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唐 桦)
标签:台湾选举论文; 媒介化理论论文; 社会建构论文; 元过程论文; 特征论文; 华侨大学海峡两岸传播创新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