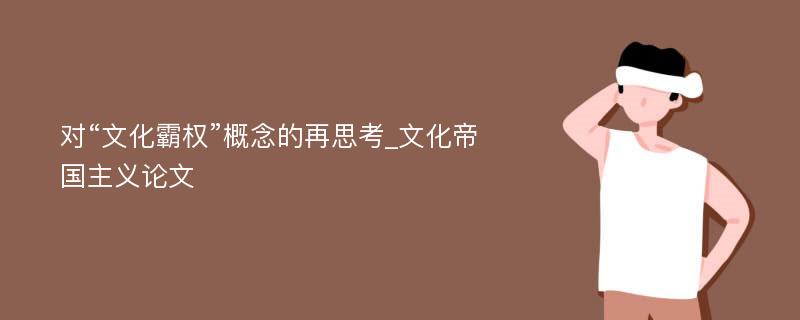
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概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化霸权这一概念里有一个重要的子概念——霸权。霸权一词源出于古希腊,其对应的英文是“hegemony”。据考证,hegemony一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形式是egemon和egemonia,本义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统治者,一般用作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注:陈燕谷:《Hegemony(霸权—领导权)》,《读书》,1995年第2期。)。hegemony一词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88年版,1993年重印,简化汉字本)中是这样解释的:英文解释是:“leadership,authority,influence,esp of one state in a groupof states”;中文解释是:“领导权,霸权(尤指数国中之盟主权),权威,势力”。同样这个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年版,第四版,简化汉字本)中又解释为:“leadership,esp by one state in a group of states”;中文解释是:“领导权,支配权,(尤指国家集团中的)霸权”(注:参见《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36页;《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3页。)。这两本词典是同一词典的不同版本,后者是前者的修订本。这两本词典对hegemony一词的中文解释没有多大的变化,而英文的解释却有重大的差别。后一版本与前一版本相比,认为hegemony一词只具有leadership的含义,去掉了authority和influence的含义,尤其是authority的含义。这一“去掉”是否反映了随时代的变化而对hegemony一词所作的修正,抑或其中也隐含了为西方的殖民、侵略等作辩护的意思?但不管怎样,这两个版本的英文解释都强调了hegemony一词的leadership(领导权)的含义,中文解释都有领导权和霸权(支配权)的含义。
汉语中的“霸权”有做事专横、蛮不讲理、欺压和统治的意思。汉语中的“霸”字可以指依仗权势或武力欺压他人的人或集团,如霸王、霸主、春秋五霸等,也可以指奉行强力政策,或实行强力占有,如霸权,指一国处于操纵或控制其他国家的地位,又如霸道,指以武力、刑法、权势等统治、镇压他者的政策和气势。显然,汉语中的“霸权”与英文中的“霸权(hegemony)”具有不同的含义,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文化霸权”概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根据现有的资料,“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无疑来自于葛兰西。在葛兰西那里,霸权(hegemony)包括强制和同意两个方面,统治阶级主要用两种方式进行霸权统治:第一,以实力直接仗势强制控制,即“强制”统治的方式;第二,“同意”的方式,领导权的方式(注:国内有的中文翻译者把葛兰西著作中的hegemony直接译成“领导权”,以便把它和hegemony中的“霸权”区分开来。),也就是通过社会主要团体积极同意而取得的道德和哲学的领导。这后一种方式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统治阶级说服从属阶级接受,适应和“内在化”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二是指说服从属阶级相信,不论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有何种看法,不论他们与这种秩序格格不入到何种程度,任何替代选择可能都是更坏的灾难性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实际上就是指上述的第二种统治方式,所以,有的学者干脆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成是“文化领导权”,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说法。因为,“领导权”排除了“霸”的含义,它是一种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是通过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自觉自愿的认同来实现的。这实际上也是现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使用的“文化霸权”的概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看来,领导权是与霸权相对的概念,领导权没有暴力和强制性的意思。领导权的思想和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王道”、“王”的意义相近。“王道”指以仁义统治天下的政策;“王”,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荀子也说过,“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注:转引自孙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1期。)。因此,严格说来,“文化霸权”中的“霸权”不是汉语意义上的“霸权”——直接的强制统治,而应是“领导权”——以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统治。“文化霸权”中的“霸权”也和我们经常所说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经济霸权”中的“霸权”有所区别,后面的这一“霸权”就是上面所说的汉语意义上的“霸权”,它具有直接的强制性,虽然“经济霸权”中的“霸权”的强制性较之于“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中的“霸权”相对弱些。
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简·穆罕默德把殖民主义划分为“统治”(dominant)和“霸权”(hegemonic)两个不同的阶段。他认为,在“统治”阶段起作用的主要是物质和制度的力量,殖民者直接依赖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迫使殖民地人民就范,在这一阶段殖民话语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而在“霸权”阶段,殖民地人民已经部分或是全部地接受了殖民者的价值体系,包括他们的世界观、道德准则、文化趣味,在这一阶段起作用的便主要是殖民话语的力量,殖民者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退隐到幕后或仅仅作为背景因素存在。简·穆罕默德还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看作是结束殖民“统治”进入“霸权”阶段的标志。他提醒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殖民地民族,独立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能结束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独立常常不是摆脱而是更深地陷入殖民话语的控制(注:简穆罕默德:《善恶对立寓言的体系:殖民主义文学中种族差异的功能》,《批评探索》,1985年春季号,第59~87页。转引自罗钢:《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简·穆罕默德所说的“统治”和“霸权”两阶段实际上就是葛兰西所说的以强制方式和同意方式实行控制的两种形式,但葛兰西并没有说“两个阶段”,而说“两种形式”,而且这“两种形式”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并不是象简穆罕默德所说的“两个阶段”是线性区分的,“统治”阶段结束以后便是所谓的“霸权”阶段,在“霸权”阶段,经济、政治、军事等力量都不再起作用了,这“两个阶段”是绝然“对立”的。
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我们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文化霸权”这一概念,需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文化霸权具有非强制性,它不同于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是继这几种霸权形式之后的一种新的西方对与东方的殖民形式;第二、文化霸权也可以叫做文化殖民,是指文化强势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的控制,从而取得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第三、文化霸权不以强夺领土边疆或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获取”弱势方的头脑和灵魂,使弱势方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认同和接受强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自觉站在强势方的一边,自愿接受强势方的统治和控制,达到自己称霸世界的目的;第四、采用文化霸权的方式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已经不起作用,它们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独立后的原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意识的增强,那种赤裸裸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方式已愈来愈不得人心,遭到上述国家和民族的强烈抵制和反抗,作为强势方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弦易辙”,以这种看似“和平”的方式来达到传统方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第五、文化霸权不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那种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经历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再到现在的文化霸权的线性历史观是错误的。
“文化霸权”概念与“文化霸权主义”概念也是有区别的。而所谓“霸权主义”,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国际上凭借军事和经济手段称霸世界的政策。这种解释虽然有偏颇,比如,霸权主义所凭借的,并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还有文化手段,但它毕竟说明了“霸权”是不同于“霸权主义”的概念。实际上,“霸权”是一种统治的手段、方式或形式,而“霸权主义”则是关于“霸权”的政策、思想或理论,是关于“霸权”的思维方式,借用福柯的话说,也是权力话语方式。“文化霸权”是“霸权”方式之一种,同样,“文化霸权主义”也是“霸权主义”之一种,是使用文化手段进行文化殖民、文化控制的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
在赛义德那里,“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是相通的,两者往往是放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到一块别人的土地上去定居并对那里进行控制,这种斗争是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士兵与大炮,还涉及到思想、形式、印象与想象。他说,“我使用的‘帝国主义’这个术语,指的是对一个统治着边远疆土的都市中心的实践、理论与态度”。在《帝国、地理与文化》一文中,他肯定了米哈尔·多伊尔关于帝国主义的看法。米哈尔·多伊尔说,“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其中,一个国家控制着另一个政治社会有效的政治主权,其控制的方式可以是武力的、政治勾结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是一种文化依赖”。赛义德援引了米哈尔·多伊尔的话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简言之,帝国主义就是建立与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或策略。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殖民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完结,然而我们将看到,帝国主义仍以其在政治、思想、经济与社会实践中的特有形式,在普通文化领域中徘徊”。“无论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都不是一种积累与获得的简单行为,支持、甚至推动它们的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结构,包括一些国家与人民要求、恳求被统治的思想以及附属于统治的各种知识形式”(注:爱德华·W·赛义德,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通过赛义德的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把帝国主义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强调帝国主义的文化属性和文化的帝国主义属性,他所说的帝国主义更多的是指文化帝国主义。他注重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详细分析了文化为何及如何参与帝国主义事业。我国学界绝大多数学者也把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放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本文同意这种用法。
三
关于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国际上有很多学者对此给予关注。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一书中,从政治学角度根据帝国主义所用的典型手段,将帝国主义区分为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并且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而能获得成功的话,则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注: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90页。)。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提出当今世界存在着“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思想殖民化”问题。佩查斯在《20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中提出了一个“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已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的目的”(注:汤林森,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第51页。)。哈里森在《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中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是阴险的控制形式,征服人们的心灵,使之惟命是从。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培植当地的买办,通过“比照集团行为”,将某一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而使人刻意效仿。通过教育、广告、传媒,在第三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比照集团”引诱意志薄弱者仿效,从而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注:保罗·哈里森,钟菲译:《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4~49页。)。马克思虽然更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也同样揭露了西方对东方的文化霸权(主义)。马克思指出,殖民主义的掠夺和统治往往通过意识形态在文化心理上对被奴役人民进行控制。他说:“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注:马克思:《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1870年4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1页。)。约翰·汤姆林森(又译为约翰·汤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是指全球文化多多少少倾向于成为一种霸权式的文化。他说,“文化帝国主义”汇集了一系列主导性话语:“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或多或少主导了其他所有的制度及其所有的人”(注:约翰·汤姆林森,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第117页。)。但约翰·汤林森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文化帝国主义”是采取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来分析的。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虚妄的,应该给予严厉的批判。
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汤林森以文化过程的动态本质为立论的依据,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提出质疑。首先,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依据是一种共时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保持两种空间上分割的时间上固定的文化。在他看来,所谓“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威胁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如果只是完全以“共时性——空间”的模式构思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但却忽略这些文化过程的本质,那么将在概念上出现许多问题。其次,这一概念的另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汤林森认为,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起源来看,民族国家及其文化是“想象出来的社群”,当今社会,在日常行为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形成具有意义的文化认同了。因此,对外来的生活方式的采纳,不会构成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威胁。最后,汤林森也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大国的文化霸权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构成威胁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所谓“我们的文化”从来就不是纯粹由“本地生产的”,都包含着先前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以及影响。所谓的“文化传统”是“发明出来的”,之所以发明传统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永恒不变的文化本质、一种文化幻觉,并赋予这种发明出来的传统以“正统和权威”。这样,那些人们发明出来的所谓的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功能似乎只是用文化的建构来告诉我们历史的恒定和稳固。所以,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并无威胁,它所威胁的只是“我们的具体想象的内涵,以及我们心目中的确定不移的过去的文化”。
在谈到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时,他对诸如“侵略”、“霸权”之类的术语用来描述文化的说法提出质疑,他用了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影响”。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还极力批评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分析,认为他们都坚持了政治经济分析的优先性。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化帝国主义’所代表的话语让人浑身不自在,原因有二。一方面,他们企图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以及不同‘民族——国家’的支配关系之间建立对应图,而这样的企图注定会造成紧张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马克思理论原本难于处理‘文化’这个概念。表面上,这个大问题经常显现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简化论’”(注:汤林森,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第51页。)。《文化帝国主义》一书谈论的重点是认为,当今世界,文化帝国主义已被文化全球化所取代,文化全球化将造成全球文化的同一化和均质化。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全球化与文化》中得到详尽地阐述。汤林森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文化)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以全球的、历史的眼光去看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然而他的这一立场,使他否认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而单方面地强调其同一性、全球性,从而在忽略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制约、霸权等问题时,将资本主义全球化作了普适性的理解。这种观点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他的观点中所隐含的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