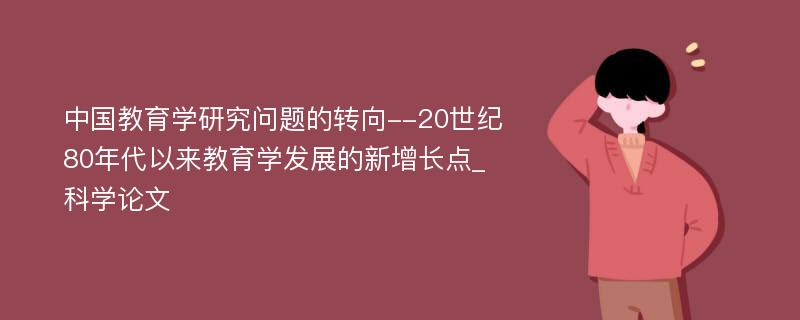
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生长点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学研究开始出现某种新的变化,多学科话语向教育领域的渗透正在缓慢地改变着教育学的学科形象,使教育学出现一种边缘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旨在揭示这种转向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转向的特征及其未来走向,并试图对其做出评价。
一、源于不确定性的苦恼
在中国,独立的、具有现代内涵的教育学大约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经过了中国学者的改造,并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进行了试验和推广,教育学这门学科最终在中国植下了根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群中成型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早登上高等学校讲坛的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在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中,教育学者一直在为教育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而苦恼,为教育学这门学科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而求索,至今没有完结。这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是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催生下产生的,这样一个背景,导致教育学这门学科在其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自然科学的某些印记。其实这也不是教育学的独特现象,那个时代产生的社会科学,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只是教育学至今未能脱胎换骨而已。
大概说来,近代自然科学对早期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双向的。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理性把握,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三个先验的形而上学预设,这就是:自然一致性、实体永恒性和因果性。这三个预设都暗含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确定性。因此,可以说确定性构成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核心,通过确定性的预设,近代自然科学为自己划定了科学研究的阈限,提供了一个合乎理性的结构,规定了严格的方法论原则,界定了最基本的范畴和概念。在人类对自然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这样一种科学理性是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以至于许多人曾经把确定性这一理性的形而上学预设当做理所当然的事实。当这种观点被推到极端时,就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唯科学主义夸大了人类理性的力量,是一种面对宇宙的过分自信乃至自负的态度。唯科学主义不仅给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而且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教育学的学科史上,来自自然科学的理性扩张所造成的影响大概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德国人赫尔巴特可以说是关注教育学的学科化问题并力图推动教育学科学化的第一人。他认为教育学必须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科学化。为此,他用数十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心理学。他在写于1806年的《普通教育学》中,已开始提出教育者必须把心理学作为自己手中掌握的第一门重要科学。30年之后,在《教育学讲授纲要》一书中,他又明确地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教育学的心理学基础。(注:夏之莲.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21-736.)在赫尔巴特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了实验教育学,主张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儿童发展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实验教育学反对传统教育学思辨式的和经验式的研究方法,转而强调定量研究的方法。该学派受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倡导的实验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影响也不可与赫尔巴特同日而语。然而这些不同时代的思潮都强调教育学发展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重视以经验归纳为主的科学理性,因此具有某种相似性。
教育学传入中国的一百年间,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发展历程与西方国家教育学的发展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这一期间曾出现过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是一个哲学独显其尊的时代,哲学取代了其他社会科学,哲学话语取代了其他社会科学的话语,社会科学出现了集体失语症。因此到了80年代初,当国内学者的眼光又重新转向定量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教育学的实证改造来提升它的品质时,其心态是极其复杂的。许多人认为,教育学能否科学化,取决于能否揭示教育现象背后的所谓规律,他们希望依靠新的研究技术和采用过去大多只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的和计量的方法来揭示这些规律,从而赋予教育学以一种“科学”的性质。于是,确定性又成为一种时尚。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中国教育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场有关元教育学的理论讨论,可以将其看成是为教育学的确定性所作的最新一次努力。这场讨论至今尚未取得共识,这表明中国的教育学者们仍然被有关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所困扰。有关元教育学的理论讨论在学科信念、研究范式、知识构成、话语规则以及教育学研究者共同体的学术生存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推动了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但是这一讨论就其初衷而言,并不是为了增加实际的教育知识,而是源于许多人对教育学的一个基本看法,即教育学是一门尚不成熟、尚不确定的学科。作为一种反身抽象,元教育学研究试图把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对象化,作整体性的反省。这种反省或是试图进行自我确证,为教育学学科进行价值定位,或是试图寻找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新路。总之,人们希望有关元教育学的讨论最终能形成有关教育学的确定性知识,并进而影响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注: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唐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这场以教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研究中,证明教育学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是研究者孜孜以求的一个基本目标。相当多的学者持这样的观点,教育学的科学化取决于能否按照科学的逻辑提出一套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范式,这些范式应该能为整理教育的知识提供确定的理论框架。然而教育学在追求这种所谓的确定性的过程中,始终不能避免一个两难的问题,即一方面它要如同自然科学一样进行事实的研究,必须保持一种价值的中立;另一方面又始终不能不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的问题,因此又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也就是说必须把价值作为自己关注的一个出发点。为了追求这种确定性,教育学正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不断地做出痛苦的两难抉择。
二、超越事实与价值
教育学一百年来的发展表明,在这样一种源于确定性的螺旋式历史发展中,中国的教育学者始终受到一种“科学”眼光和标准的困扰,而缺少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本应有的人文意识。在学科的研究任务方面,人们过分注重教育知识的确定性,追求那种现实中一般并不存在的假设的东西;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则盲目相信定量方法,试图建立学术研究的中立形象,因此未能揭示貌似自然的事实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价值选择、价值冲突和价值整合。
近代发展观念中的胚胎发育隐喻(metaphor)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发展与生物体的自然成长之间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所以社会历史发展的机械决定论就被看做是自然的、无需考究的事实,使得人们看不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人类自己的价值选择密切相关,意识不到社会和人的发展的价值基础或文化基础。中国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起始于两个基本问题,即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和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又可以分解为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个人的社会化、教育与身心发展阶段、教育与个性特征的关系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用一种决定论的观点,用一种既定的胚胎发育式的发展论来解释这些教育的关系问题,试图把教育现象解释成一种既定的、受某种“规律”左右的过程。中国的教育学在很长时间里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寻找和揭示“教育规律”,并用以指导教育实践。
关于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假说只是科学思维的一种逻辑形式,尽管它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工具和手段,但工具和手段并不能代替目的本身。因此,科学理性不是、也不可能作为解决人类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在力图突破原先的科学范式,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也在反思传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范式的片面性。因为在一个变化万千的自然界中,在一个被科学和技术支配的世界中,传统的科学理性和科学范式难以解释和包容当今社会中的许多问题,所以科学的价值问题和不确定性问题也在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科学家已经从传统自然科学的理性形而上学中走出来,注重自然现象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性问题,从而使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综合性的和相互交叉的体系。(注: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浑沌与新自然法则[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一些科学家和教育家因此还提出了STS教育的思想,即重视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的社会观。STS教育思想表明科学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传统眼光中的那些问题。科学与人有关,它不仅包括着事实问题,也包括着价值问题和伦理问题,它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科学应当有助于激发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兴趣,提高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积极的和消极的)的认识;深化人们对工业在社会的财富创造和积累中的作用的认识;使人们了解科技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将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环境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深化人们对使用自然资源的认识,精心地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等等。以上事实表明,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也不能不面对科学事实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原先的学科范式已不再是铁板一块。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学应当如何重新定位,应当如何确定自己的学科性质呢?
三、教育学:一个专门化的学术研究领域
其实,源远流长的教育学的学术传统并不简单是一种用确定性方式表达的精确定理,而是一种原则、一种信仰。与自然科学产生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不同,教育学产生于对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问题的关注。孔子和苏格拉底开创的教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珍重和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承认。孔子的“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之说,无非是在强调对人性价值的追思和对均衡状态的遵从,强调有效的教育过程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必须遵从人类本性所表达的自然秩序。但这种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和对人的本性保持敬意的直觉表达在现代教育学中并没有完全得到理性的继承和解说,所以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恰恰在于纠正由科学理性所引致的人类对自己理性的过度夸张和狂妄自大。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教育学并不是一门建立在确定性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的意义远不是一些公式和数据所能表达的。因为教育学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职业的知识或技艺,不仅仅是一堆结论或者一组定量的数据,甚至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或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人的道德、意志和信念。对社会和人的问题的思考就其最高境界而言,它应当关注的是人的现实,人的命运与发展,人的心灵世界,为理解我们自身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贡献智慧。因此,对于教育学而言,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的确定性问题,而是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教育学才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开始体会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意味着人类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和改变,而超越则意味着一种不同于预想的因素参与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价值因素。价值因素穿插在现实以及对现实的超越之间,是教育学必须面对的客观存在。在教育领域中,一个事件如何发展,何者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优先权,哪种因素或关系获得重视,哪些问题得到优先解决,都要直接受到参与这一事件的各方主体的价值选择的影响。这种价值选择既有政治的价值取向,也有经济的价值取向;既有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有个人的价值取向;既有科学的价值取向,也有人文的价值取向。因此,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用不同的话语来分析教育现象背后的价值问题,来讲述对教育问题的不同理解,教育学的发展由此正在呈现出某种多元化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教育学与其他一些学科的边缘交接之处,正在发展出一系列新的交叉领域和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法学、教育人类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生态学等等。
教育已经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学的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教育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再追求确定的学科范式,不再主张把学科的方法、知识绝对化,不再把理论看成是人类一切价值生活的决定者,不再以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假说来解释教育的问题,就此而言,教育学可以说是“法无定法”。同时这种研究又总是处处透露着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价值追思,因此教育学又可以说是“道有常道”。尽管教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会有共同使用的语汇、语境、逻辑和方法,还会有共同认可的原理、原则、理论和学说,因而还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及其共同关注的问题领域,但是教育学正逐步成为一个边界不断扩大的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多学科的渗透使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越来越模糊,因而缓慢地趋向于多元化。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尽管不同的国家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路径不尽相同,但是变化的结果却是非常相似的。(注:可以举出大量的学术文献来证明教育研究的这种边缘化发展趋势,如:Michael Apple,Ideology and Curriculum,Second Edition,Chapman and Hall,Inc,1990;Michael W.LaMorte,School Law:Case and Concepts.7th ed.Allyn & Bacon A Pearson Education Company,2002;Harry Brighouse,School Choice and Social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Revised Edition Basil Bernstein,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Theory,Research,Critique,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ers,Inc.,2000;Geoff Whitty,Making Sense of education Policy,Paul Chapman Publishing,2002.)
因此,教育学的问题既不单纯是逻辑实证的问题,也不单纯是语义分析的问题,而首先是历史观、价值观的问题,是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所依据、所坚守的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就此而言,教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强调教育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相反地,这样一种定位提升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育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因为科学即使可能为我们提供教育目的和手段所依据的许多事实细节,但它还是不能代替我们作出决定。
四、中国教育学发展的重要走向:教育政策研究
近十年来,教育学的研究文献中开始越来越多地用新的话语、新的理论来讨论一系列新的问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公共教育政策已经成为教育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人们所讨论的问题领域相当广泛,例如,国家与教育,政府、市场与学校,政府的教育功能,市场介入教育的可能性,教育与社会分层,教育发展中的地域不平等和人群不平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其办学自主权,教师的法律地位及教师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构建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教育政策问题的高度关注使许多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集合到一起,用不同的话语来讨论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教育学的面貌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这种研究的变化已经导致教育学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研究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本文拟以2003年《教育研究》杂志所发论文为例,来说明教育学研究的这种转向。该杂志2003年共刊登各类教育学术论文181篇(不包括书评与学术动态两个栏目的15篇文章)。论文涉及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德育、农村教育、教育心理等20个方面。在所刊发的论文中,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与教育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共计65篇,占全年论文总数的35.91%。这表明,课程教学改革、高等教育与教育基本理论一起正成为当前教育研究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说明教育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并努力使教育理论研究服务于教育实践。(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课题组.2003年:教育研究的新进展[N].中国教育报,2004-3-20.)
从研究的主题(论文可重复统计)看,涉及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包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教育改革、农村教育的创新、现代学校制度的构建、教育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教育政策的范式转移和话语特征、师范教育的转型与教师素质的提升,等等。内容更丰富,研究更深入。
从研究的类型看,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三方面。其中应用研究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50.28%。这说明,研究者不再仅仅侧重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而是更加注重研究课题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与应用价值,相当多的论文是以政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
以上数据说明,教育学的研究视野、话语、方法都有了极大的转变,上述变化可以说明政策研究已经成为教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教育学的新的研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