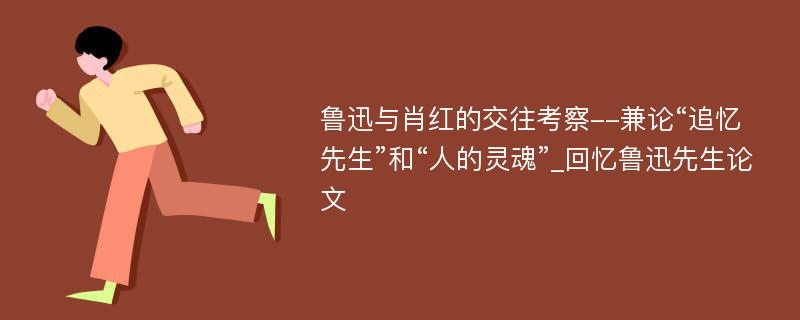
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兼论《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鲁迅先生论文,民族魂论文,兼论论文,萧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鲁迅说过,“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注:《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曾表示,“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为了培育萧红这朵中国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园圃的奇葩,鲁迅甘作春泥,甘为人梯,在她的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去世之后,萧红从悲痛中振奋起来,陆续出版和发表了《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又像春泥一样,继续滋养着中国文坛的茂林佳卉。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动人情谊已经成为文坛佳话,被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诵……
萧红与鲁迅初次见面虽然是在1934年11月30日,然而早在中学求学时期(192年至1930年),萧红就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当前,在鲁迅研究领域和萧红研究领域,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影响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通过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的比较研究,认为萧红的作品跟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诸如大胆打破传统规范的创新意识,对文学启蒙使命的自觉承担,对底层人民悲苦命运的深切关怀,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痛苦的深入揭示,就是鲁迅对萧红的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必然结果。因此,深入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就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为此,笔者在前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收集和鉴别了这两位作家交往的全部史料。将其中最生动感人的精彩部分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再现,并对《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的创作过程重点进行了考察和比较深入细密的理论分析,试图弥补此前对这两部作品研究的不足,显示这一课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 相见相识
1934年6月至11月,萧红跟萧军从哈尔滨旅居青凫。“在此期间,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0月初,二萧给他们精神上和文学上的导师鲁迅寄出了第一封信,立即得到了鲁迅的回复。鲁迅在10月9日的复信中不仅就创作题材问题回答了他们的询问,而且表示同意在百忙中挤时间审读萧红的《生死场》。收到这封复信,萧红和萧军俨然返童为两个孩子:他们或者一个人先读,另一人后读;或者一个人朗读,另一人倾听;或者一边漫步,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着谈着。每读一次,他们似乎都能从信中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四十四年后,萧军在重新注释这封信时仍然动情地写道:“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注: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同年11月3日,鲁迅收到了《生死场》的抄稿和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以及一帧二萧的合影。照片上的萧红穿的是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短袖旗袍,两条短辫上扎着淡紫色的蝴蝶结,呈现出她的特色:无邪的天真。
萧红、萧军是于1934年11月1日跟咸鱼、粉丝挤在一个杂货舱里,从青岛飘泊到了上海的。最初的住处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带——先住在拉都路283号,后搬到同一条路的411弄22号,第三次又搬到同一条路的351号。这里距鲁迅寓所有二十多里地。当时他们行囊羞涩,举目无亲。在这种流浪岁月中,他们第一次跟鲁迅晤面和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情景自然会长存在心灵深处。初次会见的日期是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地点在霞飞路一家白俄开设的咖啡馆。这是上海冬季常有的阴暗的日子,但是萧红和萧军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当鲁迅介绍萧红跟他的夫人许广平相识时,萧红紧握着许广平的手,泪水不知不觉涌出了眼眶。临别时,鲁迅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萧急需的二十元钱。由于他们山穷水尽,身无分文,鲁迅还留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银角和铜板,供他们回家乘车之用。萧红接过鲁迅的血汗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于12月6日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日期是193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下午六时,地址在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名义是庆祝胡风夫妻的儿子满月。同席共九人,即鲁迅一家三口,二萧,聂绀弩夫妇,叶紫。另有一人,萧军在《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一文中有意不说出他的真名实姓,而称他为C先生,说他是:“开店的老板”(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这位“神秘人物”究竟姓甚名谁?查鲁迅当天日记,这位“老板”名叫“仲方”。经考证,仲方就是茅盾,因为茅盾的曾用名之一,叫“沈仲方”,曾以“仲方”为笔名发表过《文学家成功秘诀》一文,载1933年1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同日日记载:“仲方赠《话匣子》一本。”《话匣子》即为茅盾的散文集,1934年1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关于这次宴请还有两个生动的细节:一是萧红为萧军赶制礼服,二是萧红向海婴赠送“棒槌”。萧军原只有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为了赴宴,萧红买到一块降价的黑白方格的绒布头,使出晴雯补裘的气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为萧军缝制了一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赴宴前,萧军又扎上了一条小皮带,围上了一条绸围巾,就显得英姿飒爽、风度翩翩了。那对棒槌是萧红送给小海婴的礼物。据萧军回忆,这对用枣木旋成的小棒槌是1934年他们从哈尔滨路经大连时一位名叫王福临的朋友赠送的;而据许广平回忆,除了这对小棒槌之外,萧红还送给海婴两枚醉红色的核桃——这是她祖父的遗物。萧红把她的传家宝和患难中随身相伴的玩具作为礼物相赠,鲁迅一家都深为感动。海婴特别喜欢这对棒槌。鲁迅同年12月20日致二萧信中写道:“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作为“主宾”的胡风夫妇可能因为请柬没有及时送到反没有出席。由此可见,鲁迅特意介绍上海著名左翼作家跟二萧见面,是为了给这两位初出茅庐的东北流亡作家从政治上、创作上、生活上以全面关怀。为了纪念这次宴会,萧红和萧军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拍了一帧合影,照片上的萧红顽皮地叼着一只烟斗,稚气的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二 “母性”的爱
萧红曾经当面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沉吟片刻,慢慢地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注: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当然,鲁迅深知对青年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对自己先利用后打杀的青年,对于那些投官告密、当友人脖子套上了绞索还要拽其双脚的青年,对于那些少年老成、城府颇深或哇喇哇喇谈口号、发空论的青年,鲁迅是存有戒备之心的。但他对青年的群体却寄与了无限的希望和厚爱。对于萧红的关怀和提携,就是鲁迅挚爱青年、培养青年的一个生动事例。不过,在鲁迅接触的青年中,鲁迅给予萧红的“母性”的爱又似乎更多一些。有一位研究者是这样描述的:“随着青年流亡者萧红的到来,他的孤寂已久的心地,仿佛有了一次融雪。她像他一样,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创伤。而且病肺,身心严重受损。对于无法返回的故园,两人都怀着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他们的小说,诗一般地散发着大地的苦难气息。此外,同样的喜爱美术,对美特别敏感。这样,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注:林贤治《一个人的爱与死》,《守夜者札记》第150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萧红与鲁迅之间的确存在着上述共同点。但笔者感到,鲁迅之所以对萧红和萧军既敞开门扉又敞开心扉,不仅因为他们是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而且跟他们的“稚气”和“野气’有关。鲁迅偏爱带“稚气”的青年。萧红的“稚气”,同时也使鲁迅恢复了青年乃至于儿童心态。这有他的书信为证。例一:二萧跟鲁迅第三次通信时,落款署“刘军、悄吟”。萧军原名刘蔚天,又名刘军;萧红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所以鲁迅复信时称萧军为“刘先生”,称萧红为令“夫人”和“吟女士”。萧红可能出于女性的独立意识不愿以“夫人”的身份出现于文坛,也可能认为作为前辈的鲁迅对后辈过于客气,便在信中天真地提出了“抗议”。鲁迅在1934年11月12日的复信中用调侃的语气答复说:“悄女士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妹,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大,或女士先生吧。”
例二:听说鲁迅先生很喜欢“壁虎”,所以也去信询问。鲁迅在同年11月17日的复信中说:“我的母亲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后来见面时萧红又提到这大蝎虎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其实我也并不特别喜欢蝎虎的,只是不赶走它就是,因为它于人是无害的,而且还有益……不能长相有点凶恶和丑陋……”
例三:鉴于上海文坛的复杂情况,鲁迅在1934年12月26日致二萧的信中嘱咐他们“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鲁迅虽喜欢萧红的“稚气”,但也认为“稚气”容易上人家的当,受害,所以在他们社交渐广的情况下特别加以提醒。萧红却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消极的“老鼠躲猫”的办法。鲁迅在1935年1月4日的复信中进行答辩:“吟太太究竟是吟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例四:萧红一度疏懒,睡觉多,人发胖,没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便请鲁迅像严师那样地催促她,甚至鞭打她的手心。鲁迅1935年1月29日复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二萧的作品中常描写东北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所以鲁迅用“蝈蝈”来形容发胖的萧红。
在鲁迅与萧红的上述往返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晚辈的萧红在鲁迅面前的任性率真和娇憨淘气,也可以看到作为父辈的鲁迅对萧红的体贴关怀和爱怜娇纵。萧红九岁丧母,父亲性格暴虐。只有从祖父那里,她才知道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毫无疑问,她一生中对人间“温暖”和“爱”的憧憬以及追求,只有在跟鲁迅交往的过程中才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然,鲁迅对萧红的关怀不仅是表现在生活细事上,更主要是帮助萧红出版了她的代表作《生死场》,从而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生死场》的抄稿是用复写纸在日本产的薄棉纸上誉抄的,字迹又小又密。鲁迅戴上老花镜,又在原稿纸下垫上一张白纸,有些字还是看不大清。然而,鲁迅并没有抱怨萧红的粗疏,而只是自责道:“唉!眼睛不成了……”(注:《鲁迅与萧红》,《团结报》2000年7月6日。)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使鲁迅深为感动,萧红作为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笔致又使鲁迅确信她在创作上的远大前途,因此,他热情将这部作品推荐到生活书店出版,并得到了同意。但送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查时,压置了半年,答复是不许可。于是,鲁迅支持萧军、萧红、叶紫结成了奴隶社,以“奴隶社丛书之三”的名义自费印行了这部书。“生死场”这个书名,表明中国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觉悟起来,由“为死而生”变成“为生而死”。鲁迅热情肯定了这个书名,并同意为之作序。写序之前,鲁迅重读了萧红精心校对过的最后的校样,从中又挑出了若干错字,并改正了若干版式。1935年11月1日,鲁迅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听着远远的犬吠声,为《生死场》写完了序言,希望广大读者从这部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吸取坚强和挣扎的力量。当然,鲁迅也并非认为这部小说完美无缺,比如,人物描写就稍嫌单薄——这也是萧红小说的通病。但为了顾及销路,鲁迅采用了一种委婉的表达方法:“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萧红读完校稿和序文,既为鲁迅的严谨而惊讶,又为鲁迅的热情所感动,但是她还有一个得陇望蜀的请求:要鲁迅亲笔签名,制成锌版。鲁迅对萧红的“孩子气”的请求予以牵就。他在同年11月16日复信说:“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除了这些,据许广平的《追忆萧红》介绍,鲁迅还更多的设法帮萧红介绍出版。有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等等。还把萧红介绍给美国的史沫特莱及日本的鹿地亘。
萧红跟鲁迅直接接触最多的是1936年春夏间。1935年6月,二萧的家从拉都路搬到了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0号,1936年3月,又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跟鲁迅家距离很近。这次搬迁的目的,据萧军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但是,萧军此后并没有常到鲁迅家来帮什么忙,倒是萧红成了鲁迅家的常客,甚至每天来一两次,每次来的时间又都特别长。当时二萧之间感情出现了裂痕,萧红内心的幸福感像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只留下了感伤和郁闷。她在短诗中写道:“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注:《苦杯·十一》《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在这种心境中,她当然特别需要寻求“温暖”和“爱”。不巧的是,鲁迅三月初肺病转剧,五月中再次复发,六月几乎卧床不起。鲁迅在1936年3月17日致唐信中说:“我的住址还不想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便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断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尽管如此,鲁迅家仍然欢迎萧红随意走动。为了减轻病中的鲁迅陪客的辛劳,许广平只好经常单独陪萧红说话,乃至疏忽了对鲁近先生的照料。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回忆道,夏天的一个下午,鲁迅先生睡午觉时忘了关窗,而风相当的大,因而着了凉,而害成了一场大病(注:原载1946年7月1日《文艺复兴》卷6期。)。不过,萧红当时并不知晓。如果萧红知道因她的来访而加剧了鲁迅的病情,一定会比接受鲁迅二十元资助更感到内心的刺痛。
1936年夏,萧红因健康欠佳及爱情生活波折,只身东渡日本。出国之前,她跟萧军约好,为了不给病中的鲁迅增添负担,都不要给鲁迅写信(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但鲁迅却一直惦记着这位后脑扁平、天真无邪的东北姑娘。直到逝世前十四天,即1936年10月5日,鲁迅还在致茅盾信中说:“萧红一去以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不料同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报纸上读到鲁迅19日逝世的文章和消息。因不懂日文,故将信将疑,觉得鲁迅先生的名字不应该跟死亡的字样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三个月前跟鲁迅告别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那是当年7月15日。许广平亲自下厨为她炒了几道可口的菜肴。病中的鲁迅坐在藤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叮嘱她:“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思想犀利、谈风颇健的鲁迅,怎么会猝然撒手人寰呢?22日,她又在日本报纸上看到“逝世”“损失”“殒星”一类字眼,而且跟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于是含着眼泪赶忙乘电车去拜访一位中国朋友。那位女朋友也不大懂日文,边查日文字典边劝慰道:“‘逝世’是从鲁迅的口中谈到别人的‘逝世’。你这个人阿!不要神经质啦!最近在《作家》、《中流》这些杂志上他都写了文章,他的身体可见是在复原期中……”于是,萧红似乎得到了宽慰,很安心地回了家。23日夜,萧红不能不哭了,因为她在一张中国报纸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鲁迅仰卧在病榻上的遗照。24日,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请萧军代她向鲁迅献一个花圈,并多多劝慰巨大悲恸中的许广平:“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信中还写道:“现在他(指鲁迅)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那里去了。”萧军对这封信注释道:“这句天真的、孩子气式的问话,不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伤痛呵!这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死了妈妈,她还以为妈妈会再回来呢!”萧红在信中表示她“想一步踏了回来”,让她的哭声跟国内追悼鲁迅者的哭声混在一道。后来,萧军、胡风、周文、聂绀弩在共同献给鲁迅的轭形花圈上加上了萧红的名字。《中流》杂志也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将这封来信刊登在11月5日出版的1卷5期上。
1937年1月4日,萧红从日本归国。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鲁迅墓。那是一个阴天,萧红在萧军和许广平母子的陪同下,在鲁迅墓边栽了一颗小小的花草。这时,坟场传来石匠敲凿石碑的声音。那石匠手中的铁锤似乎同时猛击着萧红的心扉。她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她在《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中写道:“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接着,萧红又投入了编辑《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工作。这部纪念集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义于鲁迅逝世周年之际出版。该书《后记》谈到编辑分工时说:“新闻纸的一部分的裁剪及改正,由萧红负责。”
三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是一位能够驾驭多种文学体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擅长回忆、酷爱回忆、经常从记忆深处挖掘写作素材的作家。一方面,她把生命灌注到她所回忆的人物身上;另一方面,回忆又使萧红的生话充满了春日阳光般的温馨。在萧红带有回忆性或自传性的散文佳作中,首屈一指的则是她的长篇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刚去世时,萧红写不出回忆鲁迅的文字。她在1936年11月9日致萧军信中说:“关于回忆L(指鲁迅)一类的文章,一时写不出,不是文章难作,倒是情绪方面难以处理。本来是活人,强要说他死了!一这么想就非常难过。”1938年,萧红情绪的波澜稍有平息,便为我们撰写了两篇回忆鲁迅的文字,即《鲁迅先生记(一)》和《鲁迅先生记(二)》,同时收入《萧红散文》一书,1940年6月由香港大时代书局出版。“记(一)”着重描写鲁迅寓所灰蓝花瓶里的“万年青”。鲁迅曾经一边抽烟一边告诉她:“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这几株万年青鲁迅生前摆在客厅的黑长桌上,鲁迅死后放在鲁迅的遗照前,后来又移到了鲁迅先生的墓前。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中,萧红想起了这几株万年青,想起了鲁迅坟头的瓷半身像,想起了墓上越长越高的荒草。这一切,都牢牢记在她的心头——因为鲁迅就是她心中的“万年青”。“记(二)”记叙鲁迅逝世在日本东京引起的反响:有真诚的悼念,也有对鲁迅的误解。这两篇文章篇幅很短,当然无法囊括丰富的内容,无法充分抒发对鲁迅的忆念之情。1939年3月14日,萧红约许广平写一篇回忆鲁迅的长文,供她筹办的刊物《鲁迅》刊登。她在信中向许广平恳切陈词:“导师的长处,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难的。其实导师的文章就够了,绞了那么多的心血给我们还不够吗?但是我们这一群年青人非常笨,笨得就像一块石头,假若看了导师怎样对朋友,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那或者帮助我们做成一个人更快一点,因为我们连吃饭走路都得根本学习的,我代表青年向你呼求,向你要索。”(注:《乱离中的作家书简》《鲁迅风》,1939年第12期。)后来,许广平根据萧红和广大读者的需求,陆续完成了《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等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鲁迅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1939年10月,萧红也在重庆完成了两万四千字的长篇回忆录——《回忆鲁迅先生》,作为她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一瓣心香。1940年7月,这篇文章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发行。这本书的附录部分还选收了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鲁迅的生活》和景宋(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两文。原因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字数不多,印成专书感到单薄,便征得两位许先生的同意,收入了他们的有关文章。许寿裳先生当时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10月初曾赴重庆。他当面鼓励萧红说:“还可以再写,积累起来,作为续篇。”该书的后记是端木蕻良于1939年10月26日以萧红的名义写的。文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萧红不同意这几句话,想要删去。她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还是许寿裳鼓励说:“不要删,将来写续篇时,知道多少说多少,知道什么写什么,怎样理解就怎样写,读者还可以从你的理解中多得到一些看法呢。”(注: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1940年10月13日,在鲁迅逝世四周年前夕,许寿裳先生买到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册,并将这件事郑重地写进了当天的日记(注:《许寿裳日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平成5年3月刊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萧红英年早逝,《回忆鲁迅先生》的续篇终于无法完成。弥留之际,她会感到“身先死,不甘,不甘”的吧!
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关于他的回忆录特别的多,据说仅日本友人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就多达60万字。1999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鲁迅回忆录》,选收的回忆文章也多达240多万字。然而,在林林总总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一枝独秀。它不仅是鲁迅回忆录中的珍品,而且可谓是中国现代怀人散文的楷范,是敬献于鲁迅灵前的一个永不凋谢的花圈。
萧红的这篇怀人散文兼备“史”与“诗”的双重因素,既具有散文的审美特质,又具备传记的基本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叙对象,剪裁提炼。由于作者萧红跟回忆对象鲁迅之间有着直接交往,对回忆对象充满着缅怀崇敬之情,素材又来自于亲历、亲闻、亲见,因此作品不仅富于史传性,而且也富于文学性。
萧红的这篇怀人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十五个片断,短的一两行,长的八十多行,内容涉及鲁迅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读书写作,休闲娱乐,特别是外人知之甚少的病中生活。文章除提供了鲁迅的史料外,还旁及许广平、海婴——有关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为研究鲁迅、特别是编撰鲁迅传记所必备。通过鲁迅著作的文本,读者可以感知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通过萧红的回忆录及其它成功的鲁迅回忆录,读者眼前可以浮现出一个血肉丰满、形神兼备的“活的鲁迅”——作为“人之子”的鲁迅。
《回忆鲁迅先生》的四十五个片断在内容上没有严格的逻辑顺序,材料与材料之间互不关联,形成某种断裂,有些片断即使倒置似乎也无碍于文章的连贯。这就表明,这是一篇非常情绪化的文章。作者动笔之前对于全篇的布局似乎漫不经心,全无预设。动笔之后,作者心底的感情如喷涌的泉水,飞湍的激流,尽情倾泻挥洒,形诸笔墨而成为艺术结晶。凡属作者感到有诗意潜质和倾诉冲动的内容她就断断续续写出,用感情的红线将素材的珍珠逐渐织成一幅清晰的画面。这是一种罕见的火一样的体验文字,是一种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是一种理性中夹杂着情绪性的文字,是一种打破了男性叙事结构的独具女性表达风格的文字。文章开头就是神来之笔:“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寥寥几句,一个乐观爽朗、平易近人的鲁迅形象便跃然纸上,跟一些人心目中“多疑善怒”、“冷酷无情”的鲁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萧红用自己心灵感受的非常个人化的鲁迅,是一个使常人敢于走近并能够伸手去触摸的可亲的鲁迅。
正如同历史学家往往要通过一枚枚石斧、石箭、燧石刀来研究史前学一样,人们都期待着鲁迅的同时代人能多提供为局外人所无从了解的生活细节,通过鲁迅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来感受这位文化巨人的脉搏,来接近一个真实而又富有人情味的伟人。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除开情真意切、直抒胸臆这一特点之外,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恰恰是通过女性作者的细心体察,敏锐捕捉到了鲁迅先生中许多有灵性的生活细节,表现出鲁迅的个性,情趣,魅力,气质,从细微处显示了鲁迅的伟大思想和人格。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采用的写作手法,其实就是中国历代怀人散文的传统手法。清代作家袁枚的《祭妹文》就是撷取凡人琐事刻划悼念的对象,收到了刻骨铭心、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袁枚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凡此琐琐,皆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正是通过生活细事抒发真情实感,让自己“一日不能忘”的事情通过她的笔长存在广大读者心中。比如,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价钱贵的招待客人,便宜的留着自己抽;夜里看完电影,让其他亲友乘出租汽车回家,而自己却带着小海婴坐在苏州河的桥边等车,神态像乡下老人一样安详。这些小事,都在无言中表现出鲁迅克己待人的精神。萧红笔下的鲁迅是崇高的,但又决不是令人感到高不可攀或难以置信。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提供的鲁迅生活细节很多是高度性格化的,在描绘鲁迅完整的生命世界时突出了他性格的个别性。比如鲁迅“欢喜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欢喜吃硬饭”;“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从“吃”和“坐”两个侧面,表现出鲁迅刚毅倔强的个性。萧红还形神兼备地描绘了鲁迅的一些习惯动作,比如走路很轻捷,“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这些动作表现出鲁迅一往无前、义无返顾的大无畏精神。淡淡几笔,就画龙点睛般地勾画出一个独一无二、鲜灵生动的“活的鲁迅”。前文已经提到,萧红跟鲁迅有较多的直接交往是在1936年3月至7月中旬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在鲁迅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他的生活、思想和后期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翻译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名著《死魂灵》,为怀念瞿秋白烈士而编校《海上述林》并为之作序;接待从延安来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以及被美国肺痨病专家托马斯·邓恩诊断为病危,并认为此病生在欧洲人身上则早在五年前就已死掉了……这些情况,在萧红的这篇回忆录中几乎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反映。描写特别生动具体的是鲁迅在寓所接待并宴请冯雪峰的场面。萧红笔下的冯雪峰开朗健谈,学问渊博,广闻多见,“走过二万五千里”,被鲁迅戏称为贩卖精神武器的“商人”。萧红的上述回忆和冯雪峰本人的有关回忆,是研究鲁迅晚年生活的极为重要的史料。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之所以感人肺腑,还跟她语言的情韵美和音韵美有关。情韵美取决于内情外物的融合谐合,音韵美取决于语言内在的旋律节奏。萧红对彻夜写作的鲁迅是这样描绘的:“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这一段文字,堪称人景融合的精美的散文诗。文中的太阳、夹竹桃、“金不换”毛笔,跟忘我工作的鲁迅完全融为了一体,把读者带入一种奇特的充满情韵美的崇高境界。萧红还通过文字和句式的参差错落,长短交错,张弛互现,缓急更迭,使文章产生出一种音韵美。萧红对鲁迅临终前四日的情况是这样描写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这段文字,是萧红为鲁迅谱写的一阕哀而不伤的安魂曲。萧红不愿意接受鲁迅逝世这一残酷的现实,所以她没有着意渲染鲁迅临终前的痛苦挣扎,只用“气喘”“喘着”两个词一带而过,极力烘托出一种静谧安详的气氛。这段文字中有排比,有对偶,有长句,有短句,朗诵起来舒缓而流利,自成韵律,洋溢着抒情诗般的调子。
毋庸讳言,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需要校正。如果从文学史料学的角度要求,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也偶有疏忽之处或疵点。比如文中有一段长文,记忆1935年10月1日她跟鲁迅夫妇长谈关于伪满州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但鲁迅当天日记写的是:“夜同广平往光陆大戏院观《南美风光》。”又比如记叙鲁迅在绍兴师范学堂任教期间夜间踢“鬼”(即盗墓贼)的故事,文中写的是:“‘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鲁迅在绍兴任教的时间是1910年秋至1912年初,准确地说应为“二十五、六年前”。不过,这是白璧微瑕,无损于全文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四 《民族魂鲁迅》
1940年8月3日,香港大雨如注。下午两点多钟,三百多名热忱的香港民众或手撑雨伞,或身穿雨衣,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位于加路连山的孔圣堂。是由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等六团体联合发起的“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的一次盛举,通过纪念“民族魂”鲁迅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纪念大会的主持人是著名作家许地山。当年1月从重庆飞往香港的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生平。会场的气氛非常热烈。剧《星岛日报》记者郡婴报道,发言者的“每字每句都抓着了听众的注意力,并没有像在其他会场中听众打瞌睡及谈话的现象”(注:《纪念巨人的诞生,加山孔圣堂昨天一个盛会》,1940年8月4日《星岛日报》第3版。)。
当晚七时三十分开始的演出更为精彩。节目包括有:一,话剧《阿Q正传》,田汉编剧,李景波导演,并自演阿Q一角。二,哑剧《民族魂鲁迅》,冯亦代与“文协香港分会”“香港文协漫画协会”的同人参照萧红所作同名剧本改编。鲁迅由一位原上海银行职员张宗占扮演。张宗占外形接近鲁迅,又经过画家张正宇化妆,故取得了形神兼备的效果。三,话剧《过客》,鲁迅原作,冯亦代导演。晚会观众约八百八。萧红跟乔冠华同坐在第二排观看演出。她频频向台上演员致意,演出结束后激动地跑上台跟演员握手。
哑剧《民族魂鲁迅》是萧红“费了几昼夜的功夫完成”的,在1940年10月20日至31日的香港《大公报》连载了十天。全剧共分四幕,每幕又分出场人物、剧情介绍、表演提示三部分。第一幕介绍鲁迅的少年时代,通过鲁迅作品中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蓝皮阿五等人物群像,说明旧中国人情的奸诈浮薄和改良民族性的刻不容缓。第二幕介绍鲁迅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及辛亥革命前夕的教学生活,着重介绍了鲁迅由选择科学救国道路到选择文学救国道路的转折过程。第三幕概述鲁迅北京、厦门、广州时期的生活,着重表现鲁迅跟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现代评论派的斗争。第四幕表现鲁迅上海时期的生活,以及去世后广大民众对他的悼念,其中突出了鲁迅反对法西斯蒂暴行的战斗精神及晚年所受商人、市侩的伤害。剧中人物三十多人,舞台美术设计也相当精巧壮观。
哑剧是十八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戏剧表演形式,其特点是不用台词而以动作和表情来表达剧情。哑剧又根据出场人物而分为独角戏与集体哑剧两种类型。萧红的《民族魂鲁迅》显然应划归集体哑剧。
欧洲的哑剧演出通常由轻松和严肃的场面交替转换,其中严肃的部分常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史实和神话,以使观众对演员形体动作的寓意有所了解;轻松部分的情节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时、地、人、事可根据增强戏剧效果的需要而随意变更。萧红的《民族魂鲁迅》借鉴了欧洲哑剧的基本样式,其严肃的部分取材于鲁迅生平史料及其作品(如幻灯事件、坟地踢“鬼”,以及鲁迅名篇《阿Q正传》、《孔乙己》、《明天》等),轻松的部分运用了夸张、象征等表现手段,将抽象的哲理变为具体可视的形象。比如,第三幕通过绅士对强盗的“宽容”“大度”(即所谓Fairplay)反遭强盗殴打劫掠的剧情,揭示了必须“痛打落水狗”这一人生真谛。又比如同一幕通过实验主义者试着用手走路和试着吃香蕉皮的情节,对这种理论强调直接经验而轻视理性的片面性进行了揶揄嘲讽。这种处理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不过,萧红创作的哑剧又是从中国国情和中国观众的欣赏趣味出发,对欧洲哑剧的表演模式有所突破。欧洲哑剧受古罗马面具遗风影响,演员多勾画带有滑稽戏谑色彩的白色脸谱。萧红哑剧中的人物则不勾脸谱,仅第四幕“少爷”“老爷”的表演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簧形式。又,欧洲哑剧演出时追求视觉效果,布景复杂精致,而限于战时香港的物质条件,萧红的哑剧则往往采用因陋就简的舞台设计:没有幻灯就用“拉洋片”的方式转换画面,没有电梯就用黑纸或木片扎成电梯模型,周边系上小灯泡,靠人力拉上拉下。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萧红对哑剧表演样式的突破和革新。尽管萧红创作《民族魂鲁迅》时已经考虑到演出的条件,但限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经济情况,以及人力不够和时间仓促(排演时间只有一星期),萧红的这部哑剧竟不能按原作与观众见面。当晚上演的《民族魂鲁迅》,是香港文协负责人冯亦代参照萧红原作改编的。全剧仍分四场,第一场由画家丁聪演独角戏,表现那个时代青年的彷徨。二、三、四幕的表演情况不详。据参与改编者之一的郁风回忆,演出增加了原作没有的悼念左联五烈士的场面。舞台上出现了鲁迅在月光下倘徉沉思的场面,随着音乐有男声伴唱,歌词即为鲁迅的七言律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尽管这部哑剧的演出规模进行了压缩,但演出效果是成功的。演出结束时八百名观众掌声不绝,久久不愿离去(注:郁风:《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9期。)。冯亦代先生也回忆道:“那天的会是不寻常的,不但团结了在港的各个救亡组织,而且在醉生梦死的高等华人之中,打了一针,使他们知道祖国在危急之秋,每个人对救亡都须作出贡献。自从这次会后,高等华人转变态度的的确不在少数,这对于我们以后的支援敌后根据地进行筹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注:《戴望舒在香港》,《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结语“与蓝天碧水永处”
1942年1月20日,萧红在太平洋战争的炮火声中因多灾多难逝于香港,终年32岁。临终前,这位“半生尽遭白眼冷遇”的女作家还跟友人谈论着鲁迅的作品,谈到与鲁迅先生的相识,有许多要在鲁迅面前倾诉而又一字说不出来的心情。她眼前不仅浮现出她故乡的黑土地,乌亮的煤块,闪光的黄金,潮水般翻涌的黄豆,门楼上的鸽子,柳树下的鸡群,原野上的奔马……而且还浮现出严师慈父鲁迅的亲切面影,似乎他正在对许广平说:“萧红做的葱油饼,我再吃几个好吗?”又似乎看到鲁迅从卧室的圆转椅上转过身来,跟几乎每天都要见面的她开着玩笑:“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注:《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
在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描写了信仰民主主义的“子”辈与代表贵族保守派的“父”辈的激烈冲突;而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父”辈和以萧红、萧军、胡风等为代表的“子”辈却是血脉相连、精神相通。鲁迅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曾给予过无限的鼓舞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毋庸置疑,若没有鲁迅的辛勤培育,就没有现代文学史上如此地位的萧红。由于萧红没有鲁迅那样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完善的知识结构,因而无法像鲁迅那样作出多方面的贡献,成为代表中国现代进步文化前进方向的大师,但萧红宣布“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注:1938年4月29日在《七月》座谈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把握了鲁迅精神的真谛和吸取了鲁迅创作的精髓。此外,萧红作品中的故乡情结,对人生现象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动人情感的深入发掘,以及为广大劳苦女性的苦难和悲哀而发出的呐喊,也都深得了鲁迅的承传。鲁迅去世之后,萧红曾表示:“L.(指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注:1936年11月2日致萧军信。)。萧红的全部文学活动表明,她实践了自己的上述诺言。
标签:回忆鲁迅先生论文; 萧红论文; 鲁迅论文; 萧军论文; 许广平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生死场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