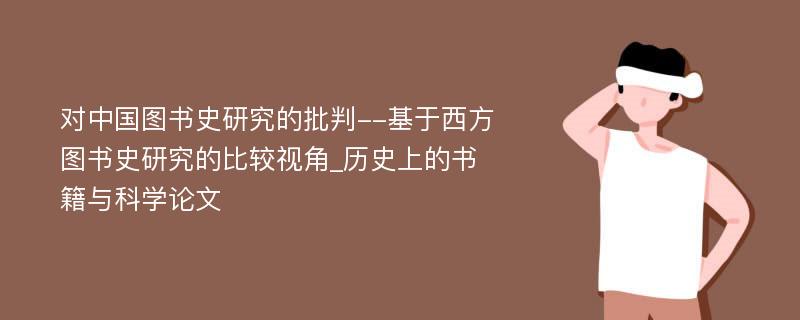
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书籍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1)05-0041-04
近10年来,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笔者研读了一部分国内翻译出版的欧美书籍史著作,例如:《书籍的历史》(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印刷书的诞生》(法:费夫贺、马尔坦著)、《阅读史》(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满满的书页:书的历史》(法:Bruno Blasselle著)、《文字与书写》(法:Georges Jean著)、《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英: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书架的故事》(美:亨利·彼得洛斯基著)、《帝国与传播》(加拿大:哈罗德·伊尼斯著)等。通过对这些书籍史著作的研读,不仅使笔者眼界大开,而且对我国近代以来的书籍史研究也颇多反思。笔者认为,我国作为一个书籍出版历史悠久,书籍历史资源与文化资源丰厚,古典文献研究十分发达,而近代以来又取得了治学意义上图书史、图书馆史、印刷史等领域显著成就的国家,研究自有特色,但是较之西方国家近现代以来的书籍史研究,在研究选题、内容、方法、材料、视角、文本分析、叙述策略以及写作诸方面,尚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与诸种不足。换言之,近现代以来,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在上述诸方面足资我国书史研究界进行文化、方法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与借鉴。
一、学术视野相对狭窄,视角单一
我国书籍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史、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史、书籍编纂史、印刷史、编辑史、造纸史、藏书史、发行史上。古典学术意义上的古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辨伪学、辑逸学等与书籍史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均作为专门之学而居之于传统学术的殿堂之中。一般而言,我国书史的研究只是作为一般历史的专门史而存在,例如编辑史,主要研究与讲述古籍的编撰,其视角为书史的一个子目。取材范围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史料缺少涉猎与采用,例如宋元明清时期大量的笔记小说,大量的美术资料,等等。西方书史则“不仅研究书籍的出版、流传、印刷,而且研究书籍的阅读、书写,以经济学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书籍史的研究,去揭示历史深层的一面”。“它围绕书籍的作者、书籍的出版者以及书籍本身三方面进行研究,把书籍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紧密结合起来,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透过书籍史的研究,揭示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与精神现象”。[1]例如,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其撰写的《帝国与传播》一书中,从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宏观视角,对“书史”作了既宏大又精微的研究与论述,以“书史”而折射出了一部世界文明史。
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不足,不尽合理
我国书史的研究一般还停留在专门史研究的理论层面上,微观研究的出现比较机械,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的状态而呈现。西方书史的叙述既注重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自然史研究,又注重对各层面的独立研究与表达。前者如法国Bruno Blasselle著《书的历史》,书中既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者联系密切。印刷商和出版商既是思想家,又是行动者,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2](P73)这样的理性表达,又有“做一本书要用上好几张皮,一本中等篇幅的书需要15张皮,价格不菲”[2](P18)(笔者注:羊皮书)这样平实仔细的文字。《文字与书写》一书中甚至用文字与图画相结合的方式描写了芦苇笔、鹅毛笔的制作步骤和细节。
三、历时性研究多,共时性研究少
我国书史的研究一般均从书史源头开始表述,一笔贯彻下来,研究文本(著作)呈现为“人的一生”,即呈现为线性研究,而对复杂性、多样性乃至丰富性的笔墨并不居主流地位。相对而言,历时性中关于共时性的研究与表达缺乏,研究思维主要依赖或习惯于“盘古开天地直到如今”之表述。西方书籍史注重对历时性中包含的共时性的充分挖掘、认知、展示、呈现与表达。它从社会史乃至私人空间、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并展开研究,为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内涵丰富而又生动的书史世界。例如,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一书中,专门写了“偷书”一章,读之既令人喷饭,又让人掩卷深思。该章(原书第十七章)中写到一个叫利百里的“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偷书贼”,此公于1803年生于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20岁即应聘为比萨大学数学教授,曾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法国学术圈深受欢迎。他的偷书丑闻被揭发,带着妻子逃往英国时,“随身还带着18箱价值25 000法郎的赃书。当时,一个劳工一天才赚四法郎”[3](P298-299)。该章关于“偷书”的文化学分析给读者提供了有益的认知。
四、研究方法单一,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
研究上,主要受制于古典文献学、史料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训诂学等传统学科的训练与惯性制约,缺乏创新。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处于同西方学术界“断裂”的状态,相互缺乏必要的交流机制,因此对西方学界的研究缺乏新的了解和认识,显得自闭而保守。对于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古代史)而言,这种情况表现更甚。书史研究自然也难以摆脱此一窠臼,基本上陷于古籍之“故纸堆”中。特别是对于西方近现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发展与研究,对其新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理论、新方法所知寥寥。这就造成了我国书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落后于时代,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世界学术界的“自闭”状况。
西方书史的研究,注重采用诸如政治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文艺学、阅读学、科学史、传播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体系、方法与文本语言。具体方法上,诸如实证研究、个案研究、计量分析、实验、观察、文本分析、图像分析(图解)等方法,皆得以应用。因而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书籍与社会的关系,展示书籍史的丰富的文化性、人文性以及科技性。例如,《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的两位主编分别是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讲师、教授。该书主要从科学史的角度以自然科学的严谨语言为读者展示了近代科学史、科学理论、科学文本、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的成就。全书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科学的崇高感,整个文章既像是一次近代科学的“实验”,又像是一本近代科学史的“百科全书”。尤其是书中关于近代生物学的演进,更是令人有归宿之亲近感与神圣感。该书精确的叙述乃是基于书籍史对科学书籍的进化性描述与文本分析。书中甚至不乏诗学、神学、科学与哲学合而为一的书籍史“高论”,如:“书籍的力量,似乎已经超越了信仰、民族和哲学信念。”“这是因为阅读凭借的是人性中永恒的特性,特别是激情。”[4](P333)
五、文本单一,语言与写作策略单一
我国书籍史著作(图书史、编辑史、出版史、印刷史、藏书史,发行史等)在写作体例、语言方面基本上是同一个“模式”,呈现为均值化的平面写作风格,体例与语言比较板正,讲究典雅而缺乏近现代风范,讲究严谨而有失生动,千篇一律,千书一面,在文本、语言与写作策略上缺乏创新与突破。研究的“语言”系统滞后,缺乏“现代性”的建构。当然,这种情况同研究理论、传统与方法的非现代性直接相关。西方书籍史研究著作在文本、语言与写作策略上表现出了多元性、丰富性与生动性,多有值得借鉴之处。例如,《文字与书写》、《书的历史》二书,在体例、语言与写作策略上即有明显的特点:1.图文穿插,图版配以详尽细致的文字,与正文叙述既为一体,又自成一格。2.体例上直接分章,章题具体可感,提炼中心词借以点题。3.附有“见证与文献”、“图片目录与出处”和“索引”,不仅丰富了全书的信息量,互为珠璧,而且具有极高的文献征引、检索利用价值。4.写作风格讲究叙事性、理性和人文性、科学性,议论寓于其中。一句话,注重对文献的综合利用,更注重对文献的分析(分解)利用,使文献的多种价值得以并重。
六、基本上是单纯的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
在我国,即使是定性研究,也缺乏它所必需的含义(如实地体验、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及其历史逻辑。西方书籍史研究则非常重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综合运用。历史形态、社会形态、观念形态、文化形态与逻辑形态有机结合,宏观中证以微观,微观中示以宏观,多方面折射出书籍史之历史、社会与科学文化的内涵。例如,《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既有宏观的历时与共时的定性考论,又有十分精确细致的自然观察、统计数据、实物图象分析以及经典个案叙述等。该书第十四章《自然之书的洛可可式读物》既是一篇专门研究与讲述18世纪贝类学书籍的文章,每一句定性的语言都基于科学观察,14幅贝类图尤其体现出了科学理性乃至博物学、动物志、美学的严谨。这使它对书籍的认识也非同一般。如:“书籍史家认为正是这种解读过程使书籍获得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图书是事物、文本和人之间组成的关系网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对图书的解读过程受到了诸如能力、社会和学术地位、财富与个人风格等事先使拥有者和读者持有偏见的因素的制约。”[4](P285)
七、对书籍史的科学与文化生态缺乏研究
从近代以来科学与文化的逻辑上去研究与诠释书籍史,并据以建构书籍史的科学(科技)与人文定义镜象与文本世界,从总体认知与完整著作方面看,我们的书史研究几近于无。西方书籍史研究则多数采取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的审视视角,叙事上注重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巧妙融合,既体现了宏观性,又具有主体的风格。这几乎成了西方书籍史主要著作的共同特性。
八、基本上局限于静态研究,受制于静止的文献与史料,呈现为传统的史料爬梳、罗列与静态分析、总结,因袭考据
我们一般将书籍史的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孤立静止的客体,研究与写作也是相对静态的,缺乏研究的生气与写作策略的灵气。西方书籍史则注重对书籍史作多维解读,并将书籍史视为历史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一个特殊因子,注重书籍史内在社会层面与学科层面的丰富性、多样性、互动性。
九、书籍生产与经营研究十分“薄弱”
西方一些书史著作非常注重经济分析,从经济史的角度作专门研究与阐释。这使读者可以了解到历史上书籍产品(商品)的生产流程及经济情形。从原料、成本、工价、劳力、设备、工具、性能、产量、技术等实际生产环节与要素上还原书籍史。例如,法国学者费夫贺、马尔坦著《印刷书的诞生》,其第四章“书籍商品”中,专门研究、分析了书籍生产的上述方面,罗列了详尽的数字——关于当时书籍印刷业的具体价格、设备多少、工人多少、磨损程度,等等,简直就像是一本印刷厂主人的生产“记录”与“清单”。相比之下,我国书籍史之经济史学著作几乎没有,即使是这种研究,也非常少见。
十、对书籍科技史的研究,或对科技书籍史的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
在这方面,《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不失为一部值得学习的“典范”之作。正像该书的“译后记”中所总结的:“书籍的历史又和科学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的成长对于书籍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科学史上里程碑性的成就大都是以书籍的名字为标志的,比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科学对于书籍的生产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比如科学书籍,尤其是几何学、天文学、博物学书籍,在图解、对事物的描绘等视觉形象方面都有了新的需求,这反过来也成为书籍发展的推动力量。”[4](P481)
十一、对书籍史研究的“客体”缺乏明确的界定
在我国,基本上把书籍史置于王朝史的框架中进行相对“孤立”的研究,主要研究政府出版,兼之以私人出版、坊间出版、书院出版、寺院(道观)出版,“五马分尸”,条块处置,机械组合,套用传统史学的理论、方法、概念和范畴。西方书籍史注重对书籍生产(生产要素、指标、生产力、生产关系)、书籍技术、书籍与社会变革、书籍与学科进步、书籍与人类文明、书籍与读者、书籍理性等多方面的研究,大概举凡书籍本身及其所关系到的一切社会意义方面,均为其研究对象。书籍“主位”与“客位”——书籍“近经验”与“远经验”尽在其研究与释读的学术视野之中。似乎可以认为,书籍丰富的文本内容就是书籍史研究的深刻对象与内在的“指向”。例如一本中世纪的神学书籍,它必然规定了对该书与其“神学”关系的研究视角。《帝国与传播》一般被认为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一,其实就是一部既“包罗万象”又“无微不至”的书籍出版史。即使在它意义引人入胜的众多注释中,也处处显示出书籍史的精彩“细节”。如“公元716年之后,科比地区的修道院收租时可以接受莎草纸”,“使用莎草纸时,教皇本尼迪克特签名常常用全名”。[5](P145)多么真实的历史细节!
总之,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就,以求能够进一步拓宽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书籍史研究的内容,使各科书籍所蕴涵的形式意义与内在意义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科学、文化与美学诸方面得到历史性的揭示、再现与还原,并且能够尝试运用诸如史性和诗性相结合的叙事性文本语言予以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