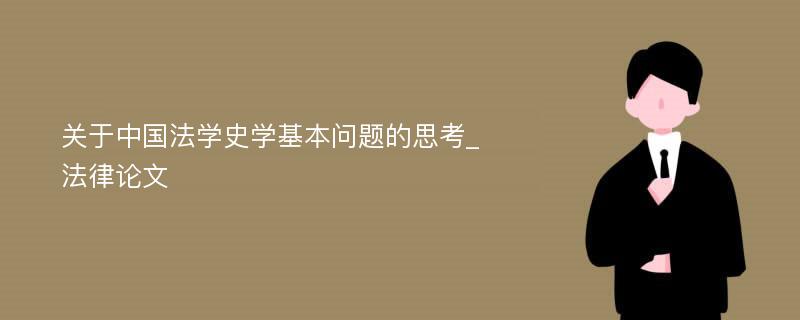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国法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08(2006)01—027—05
近年来,反思中国法史学发展的文章发表了很多。本文参考有关成果,拟对中国法史学的学科名称问题、性质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再进行一些反思,希望能为深化中国法史学的认识有所助益。
一、学科名称的变化和统一问题
中国法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于清朝末年。建立的标志是在清末的法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等高等学校里开设了中国法史学方面的专门课程。这门课程早期的名称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现行及历代法制沿革”、“中国历代刑律考”、“中国法制史”等称法。早期的中国法史学与中国历史上的典制体史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的内容主要是取自清人所编的《三通考辑要》。《中国历代刑律考》的内容取自汉律辑本、唐律疏议、明律和各史刑法志[1](P.43)。从早期中国法史学的课程名称和内容取向,可以看到,中国法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其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制体史学。另一来源则是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法制史》著作。清末民初的中国法史学教材多仿照日本学者有关著作的体例进行编纂。所以,中国法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其学术史渊源不是单一的,其奠基之作和奠基之人,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只是某一部书、某一个人或单受外国影响而形成的。我们应当认为:“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P.166)
早期中国法史学的课程名称和内容,都限于中国法律制度史方面。20世纪40年代,中国法律思想史列入高等学校法学课程后,中国法史学就包含两门课程了,但这两门课程是各自独立的,没有统一的名称。新中国建立之初,受当时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中国法制史的课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史的课程。该学科的名称和内容都突出了国家和政治的主导地位,法律制度的内容处于了从属的地位。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课程改为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也突出了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法律思想处于了从属的地位。两门课程仍是独立存在,没有统一的名称。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随后出版的《法律史论丛》把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的文章编在统一名称之下,学界遂用“中国法律史”的名称统称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两门学科,但有学者对“中国法律史”的学科名称和内容提出了改进意见。张国华先生认为:“在法律史上我们有个习以为常的传统,就是将思想史和制度史截然分开,形成两张皮,即使是联系很密切的问题也各说各的,不越雷池一步;二者共同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同样被人为地割裂,互不相通。近年来,不少学者已感到这种分工过细、过于机械的做法并非上策。加之各自又只是在一个平面上来谈问题,毫无立体感;只谈静态,不谈动态;只谈论点,不谈实践,殊不合理。其实,仅就中国法律史而论,也是个多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不应当把思想史和法制史看成两个孤立的世袭领地。因此,有人索性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改写成法律史或法律文化史,冶上下古今,立体平面、动静诸态以及各种纵横联系于一炉。但兹事体大,又涉及到学科分类的现行体制,一时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我们限于学力和水平只能逐步改善,小作变动。该书基本上仍以思想史为主,加进一些必要的制度史内容。至于大改大革只好俟诸来日和寄希望于后来居上的新秀。”[3](前言) 随后,又有学者认为,汉语“法律”一词比“法制”一词含义要窄,也不能涵盖“法律思想”的内容,所以用“法律史”一词来统称这两门学科不如用“法史学”一词来统称更为合适。实际上,日本法学界长期以来就是用“法史学”一词统称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和法律文献史等分支学科的。至于“法律文化史”的名称,其内容的广狭和方法的应用,尚处于探寻之中,还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得到学界共识的学科,故用“法律文化史”的名称代替“法律史”或“法史学”的名称是甚为不妥的。即使将来“法律文化史”发展成为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立研究方法的学科,也只是与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献史和法律社会史等学科并列的一门学科,统摄于“法史学”的总学科名称之下,而不能用来代替“法律史”或“法史学”的学科统称。
需要说明的是,学科名称和内容的分别,是由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所决定的,是学术自然演进的结果。学者可以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发表跨学科的见解,但不能凭个人主观的好恶或一时学术思潮的影响,而轻易否定传统学科存在的价值,否定学科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对新建立的尚未发展成熟的学科,更需要认真地研究,审慎地对待学科的合并或分立的问题。
二、学科性质认识的深化和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强调法史学科的史学属性和政治属性。史学属性的强调导致法史学者注重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历史沿革的考察,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政治属性的强调导致法史学者注重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阶级本质的分析,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说明。近年来,有学者强调要注重法史学科法学属性的认识和研究。笔者在总结前哲时贤论点的基础之上认为:“中国法律史学是一门具有法学的属性,又具有历史学的属性的二重性质的交叉学科。其主要内容、研究目的和基本方法是法学的,法学属性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国法律史学主要是属于法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它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法学基础学科一样,为各种应用法学的发展提供学理方面的资源,同时为丰富人们的知识,启发人们的才智提供人文关怀方面的资源。确切地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4]。梁治平先生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建立的法律史传统基本上出于法学,它在学科组织和建制上隶属于法学,而不是历史学……虽然史学和法学经历过同样的范式转换,但其渊源不同,传统有别,这使得历史学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不尽同于法学的法制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的法制史研究与史学的法制史传统同属于一种大的范式。如果说前者的法律概念来自于‘法的一般理论’,其历史观则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二者最后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此之外,则二者的关系便转为复杂。总的来说,中国法制史的主流在法学,不在史学,出于后者的法制史研究不但数量少,不成系统,而且由于学科建制的关系,其影响力完全无法与前者相比。问题是,这种情形与史学的法制史研究实际所具有的学术意义是很不相称的。”[5] 梁文对法学的法制史研究和史学的法制史研究的分别以及二者研究范式的分析,为我们深化认识法史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中国法制史学科组织和建制的法学属性,并没有真正使法学的法制史研究取得主流的地位。相反,“当下一些中国学者从史学的角度,以认识法制在历史上的源流演变、利弊得失或经验教训为目的的著作,只是史学分支学科性质的著作。这种性质的著作,还处于历史学的附庸的地位,没有进入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品格的法史学著作类型中。……这类著作不是‘法学的著作’,而是‘历史学的著作’。这类著作可能有助于深化和拓展某些历史问题的认识,但难于在深化和拓展法学的认识方面有更大的意义。”[6] 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杰出的法史学家的著作和研究方法。“从法学的视点做出分析和构设概念,并加以体系化的叙述”,使“中国法制史学这一特殊的法学学科真正能够有助于法学全体的深化和拓展”,使法制史著作成为“法学的著作而不是社会学的著作”[7]。这种属于“法学的”法制史著作,“将超出一般文献意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认识境界,而致力探寻法制背后的法的原理和法学意义”[6]。
运用现代法学知识,特别是运用部门法学的知识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部门法史研究视角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日本学者织田万写的《清国行政法泛论》、浅井虎夫写的《支那法制史》等著作,是运用西方近代部门法的体系和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法史问题的奠基性作品。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为梁启超等中国学者先后采用,成为中国近现代法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部门法史研究方法的发展,既有国外近代法学分类理论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法史材料存在特点的内部原因。中国传统社会诸法合体的法典和典制体史学方面的著作,为中国近现代部门法史的研究提供了刑事、民事、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法史材料,客观上形成了部门法史研究能够利用的历史基础。但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从部门法的理论出发,大量分析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传统法史问题带上了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有些观点如古代罪行法定主义说、古代行政法典说、判例法传统说等,掩盖了中国传统法史问题的真相,增加了准确认识传统法史问题的难度。特别是简单地从现代部门法体系出发,随意选择分割传统法典内容和法律体系,使传统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受到了破坏,导致了许多认识上的主观性和结论的片面性。在中国民法史、经济法史、行政法史的研究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我在1998年提交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法律现代化研讨会的论文提纲《部门法史研究的改进》中,即指出了部门法史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我当时认为:用现代法学知识去分析古代法律问题,首先要尊重古人的法律观念,不要随意将今人的法律观念强加于古人。其次要尊重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整体性,不要抓住片断史料随意发挥,以致提出违背古代法律基本精神的论点。如中国古代法律重视个人权利之说等类。还要深化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目的和层次的认识。研究中国法律史,不一定要与现实政治需要相结合,与现行部门法接轨才有价值,能够提供一种了解中国法律演变过程和法律传统特点的知识,提供一种法学理论基础方面的知识也是有价值的。勉强地去发掘古代法制的借鉴价值和在当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往往会使法律史研究沦为现实政治行为的廉价工具而丧失其学术价值。同时要改变以部门法史体系一统天下的教材编写模式,增加专题法史、法社会史和法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中国法律史教材的内容。并把部门法史研究的重心放在近现代,减少部门法史研究溯古的内容。并加强对部门法史研究的评论,减少重复研究,分清部门法史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界限,改变部门法史学附属于历史学的地位。
今天重新反思法史学研究方法的改进问题,我仍然坚持上述看法的基本立场。但应进一步说明的是:除要改进部门法史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改进用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批评中国传统法史学概念的问题,如用现代法治概念去比附批评中国古代的法治概念和礼治概念方面的问题。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用现代法学知识去分析说明中国传统法史问题表现出很多缺点,但这种视角的选择和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仍是形成和坚持中国法史学独立学科品格的主要路径。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会丰富中国法史学的研究方法,增加分析法史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但不能代替法学研究方法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形成中国法史学独立品格的学科发展要求。
三、法史学批评的良性开展问题
学术批评是推动或引导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法史学百年来的发展成果,与学术批评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近年法史学批评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及时总结。近年的中国法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官方组织的有关法史学选题项目的申请和相关评价;二是民间学术团体组织的有关法史学问题的研讨会;三是法史学者各自独立发表的法史学论著。官方的项目评价和学术团体的研讨会,对中国法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和引导作用。但由于这方面的评价渗进了过多的行政控制因素和人际关系因素,已难以适应法史学全面发展、多元发展的需要。于是,法史学者个人发表的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愈来愈受到法史学界人士的关注和敬重。如梁治平先生发表的《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的长篇评论,① 其影响已超出了法史学界,受到法学界、史学界、社会学界许多学者的关注和引证。在近年反思法史学的许多文章中,梁文不仅篇幅较长,而且分析非常系统、非常深入,更具有理论高度和创新见解。但梁文用的基础概念是“法律史”,而不是“法史学”。我以为用“法史学”一词作为学科基础概念,比“法律史”一词的包容性要更广一些,含义更灵活一些,也更贴切一些。梁文对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的评断,也有值得进一步商讨的地方。如梁文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集体,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大多具有教科书性质,因此可以被称为广义的教科书……”。梁文对教科书类著述的缺点进行了分析批评,总结说:“教科书最一般的特点,是它的缺乏个性。一望而知的套路,一成不变的方法,现成的结论,固定的表述,所有这些,借助于一套有效的复制技术和机制而造就一个庞大的家族”。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击中了近几十年来法史学教科书类著述的要害。但把“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统而言之归纳为“广义的教科书”,还是具有把问题过于简单化的缺陷。许多法史学专题研究的论著,是不能用教科书的编写方法和体例统论的。再说,“教科书”类著述,只要写得有学术水平,也会成为专业经典著作。远的不说,近年为中国法史学者广泛引用的张国华先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就既是一部教科书,又是一部经典性学术著作。梁文中特别称道的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早先也是作为教科书用的。梁文盛赞“瞿氏纳法律于社会与文化之中的尝试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并认为作者自己的某些著作“是对瞿著的发展”。梁文认为“瞿著虽然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比之当时一般中国法制史论著,却很少见教科书痕迹。这与作者基于社会学立场观察中国法律与社会,进而设计全书篇章结构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在我看来,瞿著的学术水准并不在于是否是教科书类著述,而在于如梁文所说的瞿先生研究方法的创新,更在于梁文所没有强调的瞿先生中学、西学两方面的深厚修养的展现。在这里,我想顺便说的是,瞿先生的这部著作尽管已是一部经典性学术著作,但此部著作注重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横断面问题的考察分析,不能兼顾纵向地考察中国历代法制沿革的问题。所以,如果要认识中国历代成文法体系沿革演变等问题,还得看沈家本、梁启超、杨鸿烈、陈顾远等学者的有关著作。
提到沈家本的著作,梁治平君的有关评论也有值得再斟酌之处。上引梁文中认为:“沈氏本人精于律学,对历代法制均有深入研究,所著《历代刑法考》足以令他侧身于中国历史上杰出法律史家之列。不过,由其著述我们也可以知道,沈氏尚未超越传统的历史观和法律观,其学术贡献仍在传统律学的框架之内”。梁文还引用《历代刑法考》点校者的观点,说明沈家本著作的两大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取材广博。二是文献考订精核。以证明沈家本的学术贡献仍在传统律学框架之内。我们认为,沈家本的著述已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的历史观和法律观,其学术贡献也超出了传统律学的框架。这方面的看法,可参看李贵连先生研究沈家本的专门论著,也可参看拙作《沈家本法学思想近代化简议》。② 此处不再多加引证。至于梁文所引的史学者点校沈氏著作的观点,只能代表文献史学者角度的看法,不能代表法律制度史学者和法律思想史学者的看法。
收稿日期:2005—11—20
注释:
① 原载《中国文化》第19—20期合刊(2003)。转载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90—241页。
② 原载法大沈家本法学思想研讨会编:《沈家本法学思想研究》,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转载刘广安:《中华法系的再认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159页。
标签:法律论文; 法制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法律论文; 沈家本论文; 梁文论文; 历史学论文; 部门法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