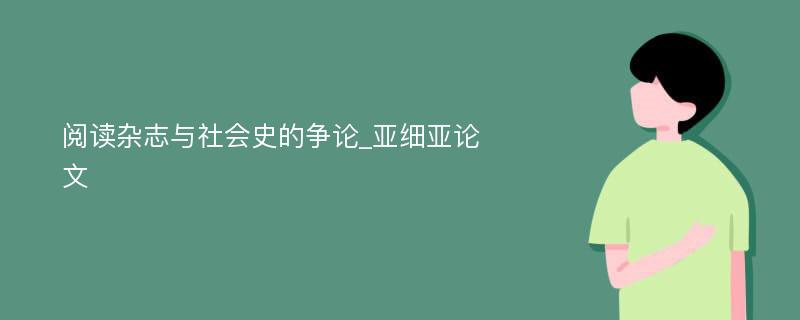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志论文,社会论文,大论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3)02-0051-07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所兴起的社会史大论战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瞩目,许多经济学 家、历史学家、思想家以及不少有志青年都投入到这场论战当中。人们围绕当时的社会 现实进行了激烈论辩,并且进而涉及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论战中,《读书杂 志》成为主要论坛,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虽然最终没有取得一致的、令人满意的成果 ,但在争辩中所论析的问题和所表现出的思路特点,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特别 是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颇有影响。
一
三十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的展开,同“中国道路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紧密相联。192 7年,北伐战争失败,人们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充满担忧与疑虑,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渴望,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希望能够对症下药, 以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正如郭沫若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 研究·自序》,人民出版社1954年。)。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社会史大论战广泛展开 。
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诸多的论辩刊物中,《读书杂志》是社会史大论战的主要阵地之 一,在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读书杂志》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在上海创办,它曾 以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为主题,相继出版发行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第一卷第 1辑于1931年8月出版,最后一辑出版于1933年。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读书杂志》连 续3年坚持出版印行,共出版3卷17期,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读书杂志》的主编为王礼锡(注:王礼锡(1899-1939),江西安福人。早年加入国民 党。1928年应陈枢铭之邀,参加创办神州国光社,主编《读书杂志》。又参加建立福建 人民政府的活动,失败后流亡英国。抗战爆发后,在英国从事国际援华运动。1938年回 国,任全国文协理事,被推选为作家访问团团长,率队北上。1939年8月,病逝于洛阳 。撰写有《市声草》诗集、《李长吉评传》《海外杂笔》等。)、陆晶清(注:陆晶清, 云南昆明人,原名陆秀珍,笔名晶清。1922年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后,加入国民 党,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何香凝属下任干事。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学任教, 同时协助王礼锡做神州国光社的编辑工作。1933年随王礼锡赴伦敦。抗战初期,与王礼 锡、向达、吕叔湘、钱歌川等人创办《抗战日报》。1938年回国后,至重庆,任文协理 事。1945年夏,以《和平日报》特派记者身份赴欧洲采访,1948年回到上海,任暨南大 学中文系教授,解放后合并为上海财经学院,转任该院教授直至1965年退休。出版有诗 集《低诉》《流浪集》,文学史稿《唐代女诗人》等。)夫妇。从总体情况看,《读书 杂忐》刊发的稿件虽然比较广泛,但是也有着比较固定的作者群,其中包括严灵峰、李 季、朱其华(新繁)、胡秋原、王宜昌、王亚南、熊得山、杜畏之、周谷城等。这些主要 作者的经历、背景、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踊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纵论天 下古今,他们从经济的、历史的角度观察剖析社会,抨击时弊,相互辩难,《读书杂志 》为我们保存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当时社会史论战的大致面貌。
二
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史大论战中的核心问题。通过《读书杂志》,我们可以基 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考历程及其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把握情况。
中国有无奴隶社会,这个问题最初由郭沫若提出,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 ,认为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西周即为奴隶社会。他的论点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 注并展开讨论。《读书杂志》刊发多篇论文探讨了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的问题,在社 会史论战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王宜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论文,支持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 所说的“古代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它是次于原始共有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立脚于奴 隶制度这一种生产关系上的经济阶段。奴隶制是引起最初的阶级发生与国家和政治发生 的根源,而且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他以古代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社会与 中国上古社会进行对比,认为中国古代自西周至汉代,是奴隶社会时期(注:《中国奴 隶社会史——附论》23《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在社会史论战初始阶段,赞成 中国经历奴隶社会的人并不多,王宜昌是其中之一,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他与郭沫若的 论点并不相同,但在论证中国上古经历奴隶社会方面却是相似的,其论点在学术界也有 相当的影响。
李季、胡秋原、杜畏之等则在《读书杂志》上撰文,否认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 李季从理论方面指出,氏族社会崩溃后,社会的发展道路,可以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案,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即是原始社会阶段)到达封建制度,也可以从奴隶制度到 达封建制度。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道路(注:《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 与批评》131《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胡秋原则从马克思《先资本主义的诸状 态》一书的有关论述中,指出“并不是原始共产社会以后一定继之以奴隶社会”(注: 《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否定奴隶社会的普 遍性。杜畏之则说,“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在氏族社会的内部孕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 ,因此在氏族组织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为道地的封建社会。……我们从此可以 得到一个结论: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不一定产生东方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古代社会,在他 的废墟上亦有建立封建社会的可能……还要看氏族社会之内部发展与氏族间的关系如何 而定”。(注: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 他认为,氏族社会之后的中国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没有经历奴隶社会。
王礼锡、王伯平则提出奴隶的存在与是否有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从而否定 中国上古存在奴隶社会。王礼锡指出“在中国的各时代中,奴隶是从来有的,但不曾在 生产上占过支配的地位。……奴隶社会这个阶段不但在中国找不出,就在欧洲也不是各 国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德国、英国就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注:《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 谜的时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王伯平认为,判断奴隶社会的主要标准 是奴隶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而不是社会中有无奴隶,他说“奴隶制度不能列作一 个社会进化的独立阶段,……至于个别奴隶,那自然是存在过的,且在殷墟甲骨文字中 就有奴隶存在的证据。但是奴隶制度,一定要根据有奴隶生产在那时期成为主要的生产 形式,奴隶所有者要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才能成立。这样的社会形式,以我们的知识说 ,在中国没有存在过”(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14《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 辑。)。在他们看来,奴隶制生产关系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奴隶社会不 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形式。
对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的问题,在《读书杂志》中,存在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从 《读书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著述中寻找根据,或将中国社会与古典的希腊、罗马社会进行对比研究,或探讨奴隶社 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标准,总之,试图从种种的途径来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虽然最 终没有获得解决,但它毕竟提出了中国史学领域中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开启了人们对问 题的思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亚细亚社会?这是社会史大论战中所探讨的另一 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郭沫若在1928年写成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 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阐 述。此后,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人们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有关亚细亚社会的讨论,可以说,是20世纪社会史论战中,出现问题最多,讨论最为 广泛的问题之一。当时有人曾说:“在历史理论的公式里,排在奴隶社会之前的亚细亚 生产方法是不是一个经济结构?这点在过去以至现在,不但在史料的发掘和论证上未曾 有人着手,在方法论上也各执一说,弄得非常混乱”(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 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就历史的开始已经把握不住端倪,有以为和欧 洲的情形一样。……马克思对于这奇异的国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对于社会的形式, 他特别举出一个‘东方式’的名词。东方式这个谜的提示,现在正迷乱着多少人们”( 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第9页,《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读书杂 志》第1卷第4、5期合刊,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一年五月版。)。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 ,一方面在于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处的历史阶段存在分歧,另一方面更在于人们思 维的混乱: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为东方社会所特有,中国的历史发展为东方式的还是与 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相同?
社会史大论战中,《读书杂志》刊登多篇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亚细 亚生产方式进行探索。论战中,胡秋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为东方社会所特有”这 一问题的回答颇具代表性。他在《读书杂志》中撰文,批判亚细亚“特殊论”的观点, 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东方社会所特有。他指出“特殊的亚洲生产方法论,从非马克思 主义者韦伯那里取得基本的‘水利’理论,又由最有权威的普列汉诺夫承继着一部分否 定的遗产,于是,在苏联就形成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一派,他们共同的见解不外: 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法者,是东方的,与奴隶的,封建的,农奴的生产方法根本不 同的特殊生产方法;这生产方法之本质,就是私有土地缺乏——土地国有,人工的灌溉 之决定意义——及政权由水利而生,以及东洋专制国家之政治,特殊官僚士大夫阶级之 存在等。这些思想,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找着了许多信徒”,在他看来,根本不 存在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针对着人们将农村公社与亚细亚社会联系起来的观念,他 指出“即在今日,农村公共体在苏联的某些地方,也还残留着。因此,它并不能决定亚 洲社会的特征。所以,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论者将亚洲社会看作一种与奴隶制,封建农 奴制,前资本制本质不同的社会,是毫无根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注:胡秋原: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2《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二卷第 7、8期合刊,民国21年8月版。)他认为,亚细亚并非东方社会所独有,中国的发展道路 与欧洲并无二致。
王礼锡也对亚细亚“特殊论”提出批评,他说“(有些人)觉得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 ,不是用历史的常态所可解释,于是在马克思文献中找出一顶特殊的帽子‘亚细亚的’ 或‘东方的’,来加冕于这一个时代。马扎尔就是这派的代表”(注:《中国社会史论 战·序言》,《中国社会史论战》第1辑。)季雷则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论文,对马克 思主义有关亚细亚学说的渊源进行考察,他分析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社会学说的形成过 程,指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以及东方社会的论述,事实上受到19世纪欧洲哲学家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而并没有对东方社会进行切实的考察(注:参考季雷:《 马克思的社会形式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 刊。)。
与亚细亚社会问题紧密相关,社会史论战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 道路是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同?多数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道路,同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所经历的路径相同,其特殊性只表现为很小的一部分。郭沫若指出,‘中国人有一句 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 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注:郭沫若:《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现代出版社1929年版。)。这一问题,在《读书杂志》上同样 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王伯平说“中国历史,并不有异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其不同之处 也不过是某种特殊条件,如山川河流等自然界环境发生之特别影响而已。其整个历史发 展规律,则完全是一样的”(注:王伯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发轫》2《中国社会史 的论战》第三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神州国光社民国21年8月版。)。 陈邦国说“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也同样可以解剖中国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 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注: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 道路》1《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读书杂志》第一卷第4、5期合刊。)。陶希圣 也指出“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 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7《中 国礼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王宜昌认为“假如我 们利用世界史底全盘,和中国历史比较,不只是用理论来观察中国,更不是用指导原理 底图式来观察中国,而免去一切理论上的抽象和含义混淆底困难。我们会发现中国底社 会史的阶段,同于西欧”(注:《中国奴隶社会史——附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第3辑。)。从总体情况看,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路径完全相同。这种求同 论的观点,在社会史论战中比比皆是,它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成果, 也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思想观念。
社会史大论战中,还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史学问题,如人们必须问答的问题有:中国奴 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在何时,或者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这一问题,也是《读 书杂志》中大多数论文所涉及的内容。从《读书杂志》大量的论文来看,人们对中国封 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已初步形成了夏代封建论(注: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 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殷商封建 论(注:胡秋原:《中国社会 = 文化发展草书》,《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3、4期 。)、西周封建论(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志》19 32年第2卷第2、3期。)、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注: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态发达 过程的新估定》,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 等学说。这些学说,初步论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间,在客观上影响了此后的古史 分期讨论。
在《读书杂志》的论文中,人们还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生产力问题、田制问题、社会中 人们的身份、封建社会衰落的途径等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是史学研究中的基础问 题,它们的提出,直接影响了此后的古史研究。
总合而言,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无论在理论问题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史学问题 方面,人们敏锐提出问题,积极进行探索,其开启之功,不可淹没。在社会史大论战中 ,《读书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重大理论问题纳入视野,积极探索,正是对理论 问题的敏锐性与积极探索,构成了《读书杂志》的鲜明特点所在,也使得《读书杂志》 在诸多杂志中脱颖而出,于社会史大论战起到推动作用,成为论辩的重要阵地。
三
20世纪三十年代所展开的社会史大辩论,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进行的,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初步尝试。
从《读书杂志》发表的论文看,无论学者们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至少从 表面上)接受了唯物史观。如在《读书杂志》上,常见有人称许自己“近年完全站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革命,常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注:孙倬章:《中国 经济的分析》,《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或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 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注:杜畏之:《古代中国 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或指明,“我们是马克思主 义者,我们不由马克思的话来作根据,又由什么来作根据呢?”(注:孙倬章:《秋原君 也懂马克思主义吗?》4《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 期。)或在论辨中,以自己宗奉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为克敌法宝,如谓:“新思潮派之主 张封建经济,而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则陷于资产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和马 克思主义的意识”,“主张封建经济者,排除帝国主义而后分析中国经济,以否认资本
主义的发展。此种理论,只算是不懂经济问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孙倬章: 《中国经济的分析》载《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读书杂志》1932年第1卷第4、5期。) 。“(陶希圣)自称为一位唯物论者——并且似乎是辨证唯物论者……他标榜着唯物论的 旗帜,反对唯心史观的统治——这正是他能够迷惑一般青年学者底一种主要根据……唯 物论在他的历史学中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注: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 》,《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在论辩中,常常可见人们在相互论辩、攻击中,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辩论之武 器,如《读书杂志》中刊载孙倬章对胡秋原的批评,“秋原君对于政治经济的修养,过 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过于缺乏,真正是‘就是警察禁止街上人的发笑,恐怕要 听见秋原君的马克思主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笑得牙齿落下来而警察禁止不住”( 注:孙倬章:《秋原君也懂马克思主义吗?》,《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胡秋原自然反唇相讥,但所攻击点是相同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真是象孙君懂的那个 东西,我就不懂并不以为惭愧,不,懂才怪丑哩!”(注:胡秋原:《略覆孙倬章君并略 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当时的情况,恰如《读 书杂志》中一封读者来信所说“论战中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 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注:见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 》1932年第2卷第2、3期。)。因此,有人断言“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没有唯心论者 插足的余地”(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言,《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 、5期。)。
总之,可以看到,不管人们是否真正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是人们依赖的重要理论工具,是当时的史学界最具号召力的学说,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 崭新的视角。正是初步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学者们才有可能对亚细亚生产方 式、中国历史是否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等 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人们的视野也才得以开阔。
在社会史论辩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讨中国历史,有大批的论著问世。《读 书杂志》所刊载的论文,至少从表面看,绝大多数论文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学者们就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 果是丰硕的,对历史研究而言,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之功。对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 运用,更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却由于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认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 具体研究,因此,社会史大论战中,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有些 论证与结论的得出往往出现教条化、绝对化的倾向,以公式化的挪用代替了细致分析, 以至于探讨未能深入进行。对此,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逐渐有所认识,并予以批评和 总结。这一点,在《读书杂志》中也有比较客观的反映。
如王宜昌说:“在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 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但同时是不了解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 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地所谓历史唯物论。……但他们一般只是应用这一根本原理 ,而没有正确地叙述这一根本原理底在中国社会史上的如何使用。直可以说他们是没有 仔细底考究方法论的问题”(注: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读书杂志》1931年 第1卷第4、5期。)。有人指出“既然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辨 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注: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1 932年第2卷第2、3期。)。李季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死的教条,而是实际生活的 指导者,——恰和列宁所说的一样,——马克思主义最精粹的地方就在于对于具体的情 形,加以具体的分析”(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读书杂 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
人们在批评中,也对今后的研究途径提出建议。有人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应当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也同样可以解 剖中国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定律相符合的 。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必须注意,我们不能,也不应抹杀一个国家由于某种特 殊条件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特点。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够呆板的把西洋史译成中 文,而只嵌上一些尧、舜、汤等等人物的名称,就可以塞责的。反之,他的发展是受着 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所限制,与其他各国不尽相同”(注:陈邦国:《中国历史 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有人反对公式主义,主张有“ 破”有“立”,“唯物史观固然与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 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 考察的时期。……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 希望短篇文章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 。……我希望大家于‘破’之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 无论者打翻”(注: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态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1932 年第2卷第7、8期。)。有些学者提出今后解决社会史分期所应具备的条件,“1、深切 了解马克思主义;2、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3、深切了解中国 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注: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 ,《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主张于中西对照中,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对运用唯物史观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省,力图予以改正 ,这为以后唯物史观的运用提供了教训与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者未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未必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但在社会史论战中,他们都初步地运用了唯物史观,并对初步运用中产生的一 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就今天看来,有些问题的提出还是颇中肯綮的。
四
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读书杂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整个社 会史论战的进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它又反映出那一时代论辩中的若干缺陷 。
就《读书杂志》所刊发的文章而言,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深度与细致 。既以社会史论战为主题,《读书杂志》中所发表的质疑、商榷性论文很多,但这些质 疑、商榷性的论文,往往只就对方逻辑表述方面提出问题,自己却并无太多创建;既以 讨论古代社会为目标,就有必要以材料为论说依据,但论者却在文献分析方面,并不着 力:既做了大的规划,就要有细微的论析做为基础,但论战时涌现的论著,常常喜从宏 观立论,乐于涉及大题目,却对旧有史实只做简单勾勒,如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题为 《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的论文(注: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读书杂志 》1931年第1卷第4、5期。),诺大的题目也只有几页篇幅寥寥数语便应付过去,关于古 代社会所做的说明并没有说服力。这种情况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并不是偶然的情形,因 此,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妨害了论战的深入进行。
其次,通过《读书杂志》可以看出,论证中,双方往往纠缠于相互的诘问,而疏于解 决问题,但学术之外,这场论争却十分激烈,论辨各方唇枪舌剑、不依不饶,以至于相 互讥讽、互相谩骂。如严灵峰曾说“‘骂人’不是我的‘本能’,实在含有‘以德报德 ’之盛意;‘骂人’非我目的,但有时遇着‘混蛋’的理论,欲为‘真理’而战;大有 非‘骂’不可,然而,从未敢‘谩’也”,又说“许多朋友常常警告我说:骂人不要太 尖刻了,但是,我所以骂的人,差不多都是他们,先前已经是太尖刻的骂过了别人。因 此,我只认为是他们求仁得仁之自然的结果。”(注:严灵峰:《关于任曙,朱新繁及 其他》,《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4、5期。)。在争论中,在《读书杂志》上,常常 见到“各位战士,你来一拳,我来一脚”(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前记 》。)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争论中的相互攻击之严重。
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即社会史论战未能与传统史学研究有机融合。 应当说,这是那一时期的整体特点,这在《读书杂志》中,也有明显体现。例如,王宜 昌曾经说,“在1927年以前,顾颉刚、傅斯年底对于古史的研究,便应用着古书的考据 方法,和新渗进了些神话解说等等。而在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 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很显然,他的意思是说明, 两种史学研究各自行进在没有交汇的轨道上。甚至,两种研究路径不仅没有融会,反而 相互抵牾,相互排斥,如杜畏之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当时传统史学的研究, “这些人除了校勘学以外又获得了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及社会史的肤浅常识,…… 然而汉学帮助了他们,汉学也限制了他们……因为他们的批判只是技术的批判(校勘学) ,所以他们只能得到技术上的成绩,因为他们只拿文字来整理古史,所以只能辨别古书 的真伪,却未能触到古史的边际。……这一派校勘学家本是古史研究之最卓绝的开道者 ,因为他们很高明地做了些技术的准备。但是当他们不安于室要跳出校勘学的门墙而到 历史的荒原中来旅行时,就做了不少错误。……他们越辩越疑,而真中藏伪,伪中藏真 ,真伪杂出遂使这些技术的批判家目迷五色,终于没有方法来突破这些疑云惑雾”(注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从他 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社会史论战与传统史学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史大论辩时期的 古史研究中,没有进行有效的交流、融会。这恐怕也是社会史论战中,对一些具体史实 的研究缺乏深度和力度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三十年代所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已有领导时 代潮流之势,并通过这个大论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就《读书杂志》来看,当时的研 究存在不少缺陷,但是它毕竟为学术思想大转变的时代提供了可贵借鉴。
收稿日期:2002-10-29
标签:亚细亚论文; 读书杂志论文; 1932年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王礼锡论文; 胡秋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