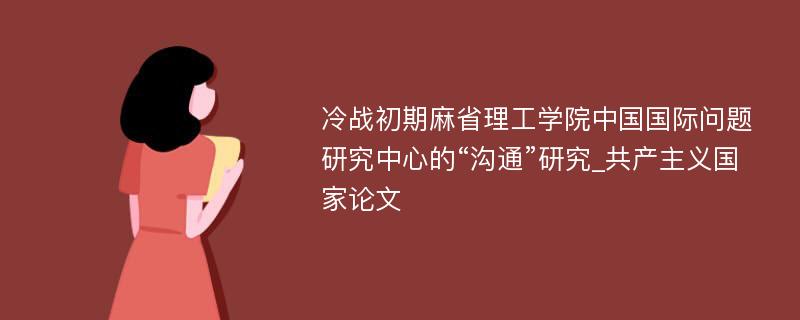
冷战前期MIT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传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中国论文,研究中心论文,国际论文,MI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6年1月,黄宗智先生登出长文,反思195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研究的变迁。他说这段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延续了长期以来贯穿西方中国研究始终的二元思维框架,“特别突出要么是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是其对立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中国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至更优越的。”(黄宗智,2016:156)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研究者最关心“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中国”,却摆出一个“非资本主义、非自由民主和非理性的共产主义”作为他者,并天然预设“西方现代化的优越性”。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相关研究中则出现了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之争。现代化范式将西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奉为近现代中国也须追寻的普世发展目标,而革命范式貌似反对现代化范式,但其本质也是西方优越论,不过是“设定一个更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的西方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西方”而已(黄宗智,2016:172)。这让人想起李金铨先生去年对同期美国中国传播研究的述评。1973年,由施拉姆和普尔领衔编纂的首版《传播手册》视野广阔,“冷战时期美国关心的国际宣传、第三世界现代化、原始社会传播、共产主义传播等问题”都被稠笔深描(Lee,2015:5)。普尔与其在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政治系的同事及学生所做的苏共和中共传播制度研究,更是当年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当然代表。我们的问题也由此而生,普尔等人当年的共产主义中国传播研究到底做了些什么?它们为何关注中国?他们的材料和逻辑又是如何被组织的?他们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他们的研究是否也如黄先生所言,乃二元思维框架的结果,并天然预设了西方优越性?我们期待回溯这段大陆传播学者不太熟悉的历史,为同侪摸清当前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中国传播研究的源流提供参考。 一、作为政治劝服的极权中国“传播”?:普尔在首版《传播手册》里的讲述 1973年首版《传播手册》的杀青是当年美国传播学界的一桩盛事,有后人胜赞此事为“传播领域争取合法性时代的终结”(McAnany,1988:115)。但也有学人毫不客气地点出,该书反映的是1960年代之初冷战高峰时期传播研究的美式沿海视角(the American Coastal View),如“将劝服凌驾于其它效果之上。在冷战两分立场上做文章,却忽视其它更基础的变量。”(McLoed,1976:331)手册两大主编之一普尔撰写了其中三个章节,而涉及中国传播议题的第十四章《极权社会中的传播》恰是上述批评的明证。 在普尔笔下,纳粹德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皆为与“自由社会”有别的“极权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如此预设与上文黄宗智讲到的第一代美国中国研究给定的“非资本主义、非自由民主和非理性的共产主义”的他者异曲同工。这些极权主义政权被认为具有下列共性,它们都“期待全体公民都成为党领导的组织的积极拥趸”(Pool & Schramm eds.,1973:464),并“试图通过大规模劝诫来改造人性”(Pool & Schramm eds.,1973:466)。可是,它们为影响舆论而展开的“受控的传播”活动却不被看好:“这些活动看重形式且过程僵化,更关心效果而非真相”(Pool & Schramm eds.,1973:463),将导致“公众最终厌烦这些宣传材料,变得心不在焉、无动于衷进而心生政治冷感”,公众甚至“为获知真相,学会在(材料的)字里行间读出言外之意。”(Pool & Schramm eds.,1973:463)上述“极权社会传播”讨论的起点,是将“传播”界定为从国家到民众、直指效果、目的明确的政治劝服。可问题是,普尔凭什么将“极权社会”和“自由社会”截然分开,断言这些“传播”活动只在前者中有而在后者中无呢?难怪惹来同行非议,说他讲述的这些极权社会传播的情况“听来像在诉说尼克松政府和水门事件的历史。”(McLeod,1976:334)正如黄宗智在批评美国中国研究的二元思维框架中指出,“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黄宗智,2016:155) 苏联和中国的故事,成了普尔佐证其针对极权社会“传播”所下上述论断的重要材料。一方面,中苏两国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走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走过的老路。两国都试图让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化,但均缺乏数量足够的现代大众传媒作为劝服工具,不得不发动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新闻纸、收音机等现代大众传媒资源更为匮乏的中国对人力资源的动员程度则远胜苏联,“中国人花费了大量气力和才智,建起了一套确能到达国土的每个偏远角落的大众传播体系,以惊人的效率扩散着宣传路线……并成功摒除了外界讯息流。”(Pool & Schramm eds.,1973:499)遍布中国城乡的黑板报、读报小组、收听小组等人际劝服方式令普尔折服,“在毛泽东主义者的实验中,数量如此之多的民众被卷入运动,他们被卷入的程度如此之高,这在人类历史上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Pool & Schramm eds.,1973:462) 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传播体系的社会动员程度被普尔捧得如此之高,可动员之后的劝服效果到底如何呢?普尔并未明确作答,只是总结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美国相关研究的三大进路。其一,随1950年代朝鲜战争而兴的中共“洗脑”研究。朝鲜战争中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相当数量的获释美军战俘,让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共产党中国思想改造的魔力心生疑惧,“美国民众普遍相信,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技术,能让理性者信服‘二加二等于五’或其它施术者选择的指令。”(Pool & Schramm eds.,1973:494)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洗脑”神话的光环渐褪。拜德曼(Albert Biderman)等人的研究发现,朝鲜战争中接受志愿军思想改造的不少获释美军战俘本来就士气低落;在香港调查中国人集体服从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的海内克(Paul Hiniker)更相信“中国人并无改变其真实信仰的压力”(Hiniker,1964),同样质疑毛泽东时代中国思想改造的实效(Pool & Schramm eds.,1973:495)。其二,白鲁恂(Lucian Pye)及其门生索乐文(Richard Solomon)等人所做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解释崇尚儒家隐忍之道的中国为何出现激进文革,点出和谐表象之下涌动的冲突潜流是毛泽东时代下中国集体狂热之源。表面上,“中国人的家庭结构忌讳公然对抗,害怕淆乱秩序的动荡”(Pool & Schramm eds.,1973:496);可骨子里,“中国人其实巴不得大乱,普遍心存积怨”(Pool & Schramm eds.,1973:496),而“文革”风暴则是“怨恨和反抗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Pool & Schramm eds.,1973:496)。其三,以刘平邻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的传播与中国国家发展或整合研究。刘平邻(Alan Liu)对有线广播、流动电影放映队的介绍,布洛曼(Barry Broman)对大字报功能的总结,都让普尔对中国人花小钱办大事的能力惊叹不已,“中国已建成这样的传播体系,能到达几乎所有公社和生产队,传达日常指令、口号及中央政府要求”(Pool & Schramm eds.,1973:497)。可是,刘平邻们当时不可能来大陆亲身调研,只能就上述传播体系的效果做出谨慎推断,“并无证据表明,社会主义新人们摒弃了所有中国文化旧识,成了毛泽东主义的彻底追随者。”(Pool & Schramm eds.,1973:499) 二、MIT中国传播研究的主线:国际研究中心、国际传播计划与《传播与政治发展》文集 虽然普尔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由国家推动的大众政治劝服的效果难下定论,可他仍推崇理解上述活动对西方的意义,“无论这些运动看似多么失败,事实证明,它们确能深入中国民众……毛泽东时代社会动员的价值在于,它们测试了大众动员的限度。”(Pool & Schramm eds.,1973:500)。从未涉足中国大陆、对中文一窍不通的犹太裔学人普尔又如何能就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劝服议题得出上述见识?我们认为,普尔在《传播手册》里涉及中国传播议题的讨论,既是其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在导师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等人指导下进行的纳粹德国及苏共宣传研究的延续,更是其自1950年代初赴MIT主持国际研究中心“国际传播计划”之后与社会学家勒纳(Daniel Lerner)、“中国通”白鲁恂(Lucian Pye)、华裔合作者喻德基与刘平邻等同事或门生切磋多年而水到渠成之结果。 1952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当年授权美国国务院组织的“争取头脑和心灵”的心理战息息相关(牛可,2009:64)。普尔主持的“国际传播计划”,米利坎(Max Millikan)与白鲁恂等操盘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计划”,罗斯顿(Walt Rostow)等领衔的“共产党研究计划”,被并称为该中心创建伊始的三大计划。虽然号称当时美国大学里最大的跨学科研究中心(Blackmer,1988:884),可国际研究中心的问世却颇具戏剧性。据该中心网站介绍,当年美国国防部本来只打算在麻省理工学院资助一项解决如何让美国之音突破苏联电波干扰这一纯技术问题的绝密级“特洛伊计划”,后来则在与院方沟通后醒悟技术问题并非关键,于是干脆在该校成立了一个为“美国之音应该播什么、对谁广播、要达到什么效果”等心理战策略献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国际研究中心。中心首任主任米利坎曾任职美国中情局,他的志向可远不止围着美国之音打转,而是要让中心成为一家“用学术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并回应国际事务”的“社会科学实体”①。在其领导下的中心拿到了来自中情局、福特基金会的大量资助(Morse,1966:124),也延聘了包括经济学者哈根(Everett Hagen)、政治学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等人在内的一批拔尖人才。1952年从芝加哥大学新获博士学位不久的普尔,则在次年听从拉斯维尔的建议来到中心,主持由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赞助的“国际传播计划”(Schramm,1984:525),并在1965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创系主任。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直至1984年离世。 “国际传播计划”打算做些什么呢?MIT国际研究中心筹备委员会(Planning Committee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下简称PCCIS)在1954年发表的一份规划中做过详尽展望。该规划直接亮出了该计划的冷战诉求,“我们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给学者们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PCCIS,1954:365)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的冲突、被割裂成东西两大阵营的欧洲、西方与克里姆林宫在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角力是报告中被挑明的几大挑战,报告背后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的二元思维框架显而易见。为应对上述挑战,“国际传播计划”意欲将新兴民族国家、欧洲国家、东西方冲突等领域涉及的传播问题作为突破口,并分别从精英研究、中介研究及长期研究等层面着手分析。以东西方冲突中的传播问题为例,该计划既希望考察精英层面的美苏外交谈判,又试图了解“身处非西方文化的民众对共产国家及民主国家新闻和宣传的解读状况”,而极权主义传播则成了规划中需长期跟踪的议题(PCCIS,1954:372)。 “国际传播计划”日后近二十年的研究重心走向,基本契合了当年这份规划中的构想。1950年代,普尔等人关心的是各国政治精英们如何形成他们的国际事务观,希望据此一窥各国的外交政策动态。1960年代,苏联与中国之间、共产主义国家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传播”问题成了新的研究重点②,一批以MIT国际研究中心名义发布、关注苏联和中国的相关报告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炉。霍兰德(Gayle Hollander)是苏联问题专家,他在1960年代中后期陆续撰写了《苏联的广播和电视》(1965)、《苏联广播和电视中的新闻》(1965)、《苏联业余广播运作》(1965)、《苏联报纸和杂志》(1967)、《苏联政治灌输:后斯大林时代的大众传媒与宣传》(1969)等报告。刘平邻在1963年底至1967年初加盟国际传播计划,整理计划里的中国部分。他相继执笔了《共产主义中国广播》(1964)、《共产主义中国电影产业》(1965)、《共产主义中国现代化中传统媒介的应用》(1965)、《共产主义中国的报刊与杂志》(1966)等报告。我们获得了《共产主义中国电影产业》、《共产主义中国现代化中传统媒介的应用》这两份报告,二者的材料均极度受限。前者介绍了新中国电影概况,如电影事业沿革、影片类型、观众集体观看行为推测、译制片主要来源国等。后者将剧场、故事会和民歌并称为共产主义中国被用于“宣传和国家建设”的三大传统媒介。作者坦言很难获得关于这三大媒介的详尽统计资料,只能尽量利用在美国及港台所能看到的中英文公开资料勾勒它们的模糊面貌(Liu,1965:i)。 1956年加入MIT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通”白鲁恂出生在中国山西,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早年在耶鲁大学政治系跟着导师饶大卫(David Rowe)与夏志清一起为美军编过《中国:区域手册》(China:An Area Manual),后来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他在1963年主编《传播与政治发展》文集,希望从传播视角丰富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政治发展议题的理解,普尔的相关报告也被纳入其中。在白鲁恂看来,若以“政治现代化”作为衡量标准,政治发展则可能与“动员民众能力、扩大参与方式、政权和平更迭”等现象有关(Pye,1963:17);“传播”则不仅与大众传媒有关,更是“人类社会的网络(web)、社会肌体的骨骼”(Pye,1963:4)。他将“改变态度”和“拉近统治精英与大众的距离”称作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两大关键,而它们都可被放在上述意义的“传播”视角下被审视。一方面,就民众态度改变而言,大众传媒独木难支,“只有得到与基本社会进程(basic social processes)紧密相连的非正式、社会性沟通渠道的全力配合,报纸和广播才能对人们的行事方式之改变产生深远影响。”(Pye,1963:10)。另一方面,就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而言,二者需求须被兼顾,“既要有高质量的(精英)报刊,也要有大众传播体系;若一味牺牲前者以迁就后者,则会招来煽动性政治之祸事。”(Pye,1963:9)白鲁恂基于西方“自由世界”经验的政治现代化标准勾勒出了一幅“政治发展”的普世蓝图,不出意外地对共产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传播经验”弹多赞少:“共产党的技术,至多只是控制和标准化那些非正式和随机的传播渠道而已。它们让面对面传播担当大众媒体传播之实责,却不考虑提升传播技术水准”(Pye,1963:10)。此举看似能弥合大众传媒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鸿沟,可实际却制造了另一条“公开的社会性传播与私下的主观即时感受之间的新鸿沟”(Pye,1963:257)。 同一论文集里普尔的报告的论调则与白鲁恂相左。普尔看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运用“作为发展手段的传播”之经验,希望借此反省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误区。这里的普尔不同于1973年《传播手册》中那位对极权社会“作为政治劝服的传播”评价不高的普尔。其一,他将“重视教育”还是“重视大众传媒”作为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和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发展计划的重要区别。埃及、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儿童基础教育和成人识字扫盲上投入甚巨,却在广播等传播设施上耗费不多。以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新兴国家则大力投资报纸、电影、有线广播等大众传媒,它们“高度重视那些通过传媒的劝诫式(hortatory)传播,这不仅是为了政治控制,也是推动发展计划的重要激励。”(Pool,1963:236)其二,上述区别的根本原因,被普尔归结为两大阵营的“传播”理念之别。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执政者们大都轻视或警惕传媒,认定“传媒看来难以催生重要行动变革……其引发的其它短期变革(如未付诸实践的观念更新)只会添乱(disruptive)。”(Pool,1963:238)相比之下,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掌舵人们更接地气,认定大众传媒要与直接人际沟通互相配合,笃信“传媒是有效的组织工具。一旦与人际组织接上轨,将对个人行为产生强大影响。”(Pool,1963:241)其三,共产主义“传播”理念更契合正奔向“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值得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里运营高高在上的现代传媒、脱离群众的西化精英们借鉴。共产党人们早已意识到,“传播其实被嵌入了一个被精心编织的特定人际关系进程之中,而非只是从传媒到芸芸众生的单向输出”(Pool,1963:245)。传统社会的情形往往就是如此。那里满是现代传媒灵活机动的替代形式,如走村串巷的戏班就善于因地制宜,随时可将本土元素与最新话题性事件揉进旧的剧本大纲之中。 三、MIT中国传播研究的支流:《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劝服》与《共产主义中国传播与政治整合》 在《传播与政治发展》文集里,还有一篇喻德基的报告。该报告在“政治劝服”意义上理解发生在共产主义中国里的“传播”现象,肯定建国后被中国政府逐步完善的那套传播体系“能让绝大多数民众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还可为党提供洞悉民意的长期信息流,是党毋庸置疑的一大法宝”(Yu,1963:295)。但喻德基也无法对这套“传播”体系能否切实赢得民心给出令人信服的评估,只能援引勒纳的一段旧说给出否定性暗示,“宣传无法改变现状,只能改变对现状的看法。宣传也无法强迫人们改变信仰,只可劝说他们这样做。”(Yu,1963:297)喻德基在1964年出版了专著《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劝服》,上述报告的核心部分皆被收入书中,而该书则可被视作喻德基自1947年离开大陆赴爱荷华大学求学之后,在美从事多年共产主义中国政治宣传研究的小结。他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曾在武汉和重庆两地任美国作战情报处翻译和新闻编辑(铁婴,1993:28)。1951年,喻德基拿到爱荷华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旋即加盟陈锡恩在南加州大学亚洲研究系主持的“中国文献计划”,后交出研究报告《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家庭服务广播简报》。凭着上述履历,他得以在1958年至1959年期间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MIT国际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喻德基是从大陆赴美的华裔学者,又有驻华美军情报人员经历,自是1950年代之后美国人心中介绍共产主义中国政治宣传概况的上佳人选。1953年,他在《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海外传播业”专栏发表《中国红色政权如何化大众悲痛为力量》一文,矛头直指“无处不在的中共宣传机器如何激起群众针对‘敌人’的行动”(Yu,1953:354),而此正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关心的热点话题。该文把中共宣传描述成“涵盖人类所有表达方式和影响态度之法”(Yu,1953:354)的治国方略,并总结出共产主义中国宣传的主题、渠道、重要技术等内容。喻德基提出,从艾思奇等中共理论家的表述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建国后宣传的核心目的,在于“唤醒、提升、明确群众的阶级意识,以凝聚政权的真正力量”(Yu,1953:355);为达到该目的,一整套包括党的宣传部门、政府有关部门、大众传媒、群众组织在内的宣传机器被迅速建立起来。喻德基特别提到了忆苦会等基层宣传形式,认为它们成效显著,可“将私怨变成公愤,把个体仇恨化为阶级仇恨”(Yu,1953:362);并不出意外地对共产主义中国宣传体系的整体持续性提出了一段证据欠奉的反讽式展望,“面对缺衣少食的现实,中国人民还能靠鲜亮的口号和甜蜜的承诺生活多久呢?”(Yu,1953:364)《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劝服》是美国当代中国传播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之一。该书志向远大,自我期许为“一份针对北京政权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及行为的全国系统的前沿调查”,可受制于材料的喻德基不得不看菜吃饭,除期望在与苏共的比较中凸显中共大众劝服的特性之外,只能依据搜集的大陆书报、外国人访华游记等文献材料归纳中共大众劝服体系的目的、理念渊源、渠道并推论其运作实况。其一,该书与美国苏共研究的勾连显而易见。喻德基在绪论中将英克里斯(Alex Inkeles)1950年出版的《苏联舆论:大众劝服研究》一书奉作样板,并断言“莫斯科和北京宣传系统的技术性差异远比想象中小;而中国的独创性在于其宣传-鼓动的强度、范围和手段,而非其哲学或实质。”(Yu,1964:155)为帮助美国读者想象大洋彼岸的情形,他也常借苏联范例解说中国事务,如以1920年代苏联的“Rabsel' kor”(工农业余记者)运动类比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的“通讯员网”(Yu,1964:106)。其二,基于有限材料的归纳性推理是喻德基成书的核心逻辑。他根据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论党》等党的文献及各级党报登出的相关决议英译的“阶级意识、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理论联系实际”等中共劝服理念大致不差,依据官方公开报告及外国人访华游记等材料归纳出的对中共大众劝服体系的主要渠道、发展水平等认识也有据可查。例如,通过1960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夏衍在中国影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所作报告披露的数字,他估算出新中国电影的历年发行量;再如,引用法国名记者吉兰(Robert Guillain)的畅销书《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1957)里的如下段落说明广播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今天一位好中国公民的头脑,就像一架收音机。在北京某处,强大的发射站播送着正确思想和被反复传颂的语句。千万个头脑接收了它们,千万张嘴巴重复着它们。”(Yu,1964:90)其三,该书对中共劝服体系运作实况的推论证据来源单一,难称信史。喻德基断言,从公开报刊的披露来看,这套劝服体系流于形式,“在常规政治学习和特定灌输运动中,宣传员们只是走走过场,人们也多在例行公事。当一切程序走完,既定目标貌似完成,所有人心照不宣,自动投入无休止的下一轮游戏之中。”(Yu,1964:158)可是,若要摸到当年中共劝服体系实情,仅靠解读公开报道中的话语岂能足够?用黄宗智的话说,“现实中话语和实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黄宗智,2016:178)从季羡林先生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日后的追忆来看,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等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次运动又岂是走走过场而已?喻德基生于1921年,在MIT国际研究中心只待了不到一年(1958年)。相较之下,生于1937年,在中心待了近四年(1963年底—1967年初)的后辈华裔学人刘平邻与中心的缘分更深。刘平邻离开中心之后在1971年推出的专著《共产主义中国传播与国家整合》被特意题献给了普尔和白鲁恂。在我们看来,喻德基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大众劝服》和刘平邻的《共产主义中国传播与国家整合》代表了早期美国共产主义中国传播研究同中有异的两条思路。前者是典型的美国区域研究。喻德基尽力为西方呈现共产主义中国“作为政治劝服的传播”经验,其追问的核心问题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劝服做了什么?为何这么做?有哪些西方经验难以涵盖的渠道?”,并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劝服是否有效?”做出推论。后者则不仅要为完善美国区域研究版块里的中国“传播”拼图做贡献,更尝试在西方理论观照下解释来自中国的“传播”经验,其理论建构企图显著。刘平邻除了归纳共产主义中国“作为国家整合手段的传播”经验并推论“传播运作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家整合是否有效?”之外,还结合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共产主义中国动员与宣传政策的摇摆”作出基于相关西方理论的演绎。在1971年推出专著前不久,刘平邻曾根据其在MIT国际研究中心整理的材料在《新闻学季刊》上登过两篇论文,归纳“农村电影放映队”和“有线与无线广播网络”这两大当时西方经验里的陌生事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特定时期的特殊角色。前者聚焦1960年代中国走村串户的农村电影放映队,详述它们的装备、人员、选片决策、放映流程等细节,并提出它们具有“促进农村科技进步、为农民开辟新的生活及社会视野”等现代化功能(Liu,1966:323)。例如,某放映队会在春耕时为生产队放映相关的科教片;另一支队伍则会放映《我们村的年轻人》,给正在修坝固堤的某公社青年们加油鼓劲。后者理解的“有线与无线广播”则是文革高潮期间毛泽东有效超越城市的局限、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主要工具。“文革”高潮期间的各级广播并未如许多报刊一般被关停或重组,反而获得高层垂青,“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决议会在见报前一天全国播送,各地红卫兵的游行也常遵广播号令行事”(Liu,1969:319)。这既与毛泽东重视发动农民、不信任知识分子扎堆的报刊有关,更与“发展广播对识字率、城镇化水平、政治参与等现代化基础要求不高”有关(Liu,1969:315)。上述两篇论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能有效促进共产主义中国国家发展的传媒形象,这是刘平邻在1960年代中期在MIT国际研究中心时的认识。他在1971年推出精装专著《共产主义中国传播与国家整合》,并获普尔亲自作序。该书在1975年再出简装本,还加上了长篇再版自序,此时的刘平邻与当年的导师普尔对共产主义中国“作为国家整合手段的传播”的效果的看法更为复杂。其一,共产主义中国对宣传的倚重,只是“在其它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面对现实采取的一条部分成功的权宜之计”(Pool,1975:xiii)。比如,在运动中用口头会议取代运输成本不菲、又离不开较高识字率的书刊传达,拿廉价的有线广播取代昂贵的电池收音机;工资普遍不高的群众看不起报纸也没关系,可以去邮局花几分钱租份报纸来读。其二,基础设施不足,让传媒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整合进程中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刘平邻强调,普及现代交通设施、统一语言、提高识字率等条件是国家整合的必要条件,“这些因素先于或伴随传媒发展,单靠传媒自身并不能带来国家整合”(Liu,1975:5-6)。曾被刘平邻看好的“农村电影放映队”和“有线与无线广播网络”现在都让他在《人民日报》当年的相关报道中发现了问题。有的放映队只去公路沿线的大镇,也有不少下乡的放映队反映观众大部分是来瞧热闹的孩子。此外,初装成本相对便宜的有线广播在农村的维护成本其实不低。广西的一个村子报告,村里的大喇叭断线是常有的事,坏了还得扛去外地修理,一来一去得奔波三天。虽然刘平邻本书中的流动电影放映队、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已非共产主义中国国家整合的关键,但与基于西方“自由世界”经验的政治现代化标准勾勒“政治发展”普世蓝图的白鲁恂类似,刘平邻对普及现代交通设施、统一语言、提高识字率等共产主义中国家整合前提的想象也是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标准的,契合上文黄宗智总结过的第二代美国中国研究里对现代化中国的想象。若刘平邻的讨论仅止于此,那么他这本专著的意义至多不过是从“作为国家整合手段的传播”视角将前人曾归纳过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相关经验材料再归纳一遍而已。但他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在归纳的基础上引入了演绎逻辑,试图在美国政治学名家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国家整合理论观照下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动员与宣传政策变迁之动因。多伊奇认为,“渗透”与“认同”是国家整合中的两大战略。前者以让中央权力渗入以往的政治和文化自治区为目标,常借助强力推动现代化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民众识字率,而传媒在渗透过程中的任务是“传递政治权威、催生大众的政治意识或认同感”;后者则更看重“在垂直层面的权威与民众之间、水平层面的公民及群体之间建立认同”,主张循序渐进地向民众散播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Deutsch,1963,转引自Liu,1975:3)。刘平邻提出,高层分歧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动员与宣传政策波动的根源,正可用多伊奇提出的“渗透vs.认同”两大国家整合战略之争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高层的激进派们倾心从上至下的“渗透”,信奉短期政治动员,“倚重草根们的口口相传,警惕无用而危险的‘正式文化机构’”(Liu,1975:7);保守的技术官僚们却青睐从下至上的“认同”,相信长期教育的力量,承认“大众劝服必须建立在大众主动参与传媒的基础之上;而且,传媒系统若想有效沟通领袖和群众,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复杂性与专业性。”(Liu,1975:7)如此看来,大跃进之后的短暂政治经济秩序整顿,定是“认同派”在做文章;而文革高潮时地方报刊等正式文化机构瘫痪、大串联席卷全中国,正乃“渗透派”全面占上风的标志。 四、结论与讨论:MIT中国传播研究的旨趣、逻辑、局限及意义 通过上述整理,我们应能对当年MIT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传播研究的面貌更为清晰。它们随因冷战问世、有美国政府反共心理战背景的“国际传播研究计划”而兴,关心既是“极权社会”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发生的“传播”现象。它们号称心系“媒介在培养宏观意识形态观念及激发长期社会转型”中的累积性角色(cumulative role)(Lee,2015:7),其实只是因为只能利用港台及流入美国的有限中文资料隔岸观火,无法深入描述和解释共产主义中国内部微观、短期的受众行为。在它们眼里,“传播”既是“极权社会”中国“从上至下的政治劝服”,又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手段”或“国家整合手段”。 普尔等人的逻辑也有迹可循。做过前驻华美军情报人员的喻德基谙熟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运作之道,他利用手头的新旧文献归纳出的共产主义中国政治劝服的观念源头、主题和渠道等情况是冷战初期美国亟需了解的情报。刘平邻不仅要做擅长归纳作为“发展手段”或“国家整合手段”的中国“传播”经验的中国研究者,更要做能演绎西方国家整合理论以解释中国动员与宣传政策沿革的政治学者。普尔对“极权社会”中国里“作为政治劝服的传播”或“发展中国家”中国里“作为发展手段的传播”的认识,则或源自其对他眼里同为“极权社会”的中国与苏联相似现象的比较,或源自其对喻德基、刘平邻等华裔学者相关论述的再总结。普尔等人的局限同样明显。结合黄宗智对同期美国中国研究的剖析,我们认为,虽然借助黄宗智的论断审视普尔等人的中国传播研究的整体面貌大致不差,但深究这些研究的局部细节却未必尽然。其一,黄宗智讲美国中国研究不是中国研究本身,“反映的其实更多是关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而不是关于中国主题的本身”(黄宗智,2016:175),普尔等人研究的问题意识,也源自当年美国政府出于冷战需求了解作为“共产主义对手”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冲动。其二,黄宗智讲同期美国中国研究的背后大都藏着崇尚西方优越论的中西二元对立框架,普尔等人的研究背后虽也同样暗含“自由社会vs.极权社会”“传统vs.现代”的二元框架,但细察之后可知,此框架下的美国学人们并非全盘否定中国经验。例如,普尔在《传播与政治发展》文集(1963)中曾呼吁非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要借鉴中国等共产主义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手段的传播”经验,只是到了《传播手册》(1973)那里,他才成了“极权社会”中国里“作为政治劝服的传播”现象的批评者。刘平邻也曾看好“农村电影放映队”、“有线大喇叭”等“作为发展手段的传播”之中国土法子;只是到了1971年,他才相信,这些诉诸传播的土法子只是难以持久的权宜之计,交通基础设施、语言统一、教育普及等西式现代化硬指标才是共产主义中国国家整合之关键。普尔等人当年的中国传播研究早已随着MIT国际研究中心在1960年代末之后的转向而走入历史,但它们背后深藏的“极权社会vs.自由社会”、“传统vs.现代”等二元框架仍值得当前以中国传播研究为业的华人传播学圈反思并警醒。普尔曾以国际研究中心拿到的由国防部和中情局资助的官方项目为荣,鼓吹“未来人道主义政府的唯一希望,就在于社会科学能尽量为政府所用”(Pool,1966:111),可这些官方资助项目在1969年的反越战风潮中成了饱受抨击的美国政府越界干预学术自由之铁证。1970年代,卫星广播、电子媒介等“新的传播和计算技术”成了MIT国际研究中心新宠,普尔最为国人所知的概念“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在其不久之后的名作《自由的技术》(1983)中的登场也就顺理成章了。反观当前大陆传播学圈的中国传播研究,我们早已不受普尔他们当年的意识形态局限左右,又可深入搜集身边的中国经验材料,可是,庐山之中的我们又是否敢说已经或能够反思甚至超越“市场vs.国家”、“政府规制vs.言论自由”、“全球vs.本土”、“城市vs.乡村”等舶来的二元框架而就中国传播现象提问呢?在我们看来,李金铨先生提出做从个案研究到比较研究、再到跨文化研究的“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李金铨,2014:142),黄宗智先生倡导“不仅要直面两者(中西)间的张力和矛盾,更要使其相互适应、结合与调和,乃至于超越”(黄宗智,2016:174),都是难得的洞见。 ①参见MIT国际研究中心网站介绍,Science & Technology。 ②参见MIT国际研究中心网站介绍,Science &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