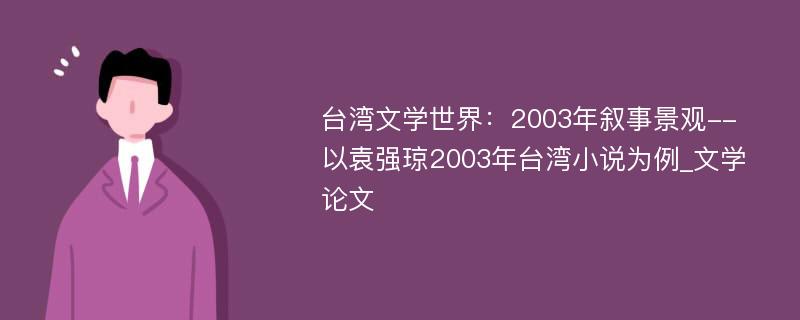
台湾文坛:2003叙事景观——以袁琼琼“2003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文坛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年度最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5-0055-04
对一个地区一个时段的文学景观做出某种价值判断,仅以某一编者的眼光为依据,便 以为也获得“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意义,即使是遭到怀疑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一 整年的台湾小说数以千万计,而袁琼琼主编的《2003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漓江出 版社2004年版)仅只选入9部?但笔者几度往返穿梭于袁琼琼的“最佳”,依然难以释怀 这份执拗,于是便也自以为是了。
袁琼琼也说:“事实上,我必须招供,在检视我所选出的这9篇小说时,我也有一些疑 惑,这些真的是2002年里最好的小说吗?……一个也许不是很有力的解释是,根柢上, 我选的是人,而不是文章。我所挑选的这些作者,我观察到他们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努 力与不甘停留。新的作家,我看到他们的未来,认定他们在写作这条路上还会走得很长 很长,而已有知名度的作家,我看到他们仍如新人一般面对他们的写作事业,他们还在 变化中,并没有因为成名而就此定型在自己的风格里。……”[1](P19)
显然,编者所谓“选的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出于励志的意义,但透过这一层面的 意义,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一个特别丰富的叙事图景:“最佳”中的文本世界、叙事策 略、审美特征及其创作主体,无不林林总总,由此而套说这一“最佳”即为台湾文坛一 个时期的“缩影”也不为过。而恰恰是“选的是人”,我们以为,这就大有意味了。在 这“入选”的九位作家中,除苏伟贞一人为50年代生人,如果还把虹影这60年代初生人 算上的话,其余均为60年代末、7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如此一来,我们的话题自然 就可以很丰富了,这既暗示了一个多元无序的文化背景,或许也在无意中确认了已然构 成的当下台湾文坛的创作主体及其价值理性和审美形态的事实存在。
一
论及台湾晚生代所“遭逢”的多元无序的文化背景,概而论之,应该始于台湾“解严 ”并90年代以降。因此,“世纪末”、“颓废”、“意义匮乏”、“虚无”、“焦虑” 一类的形态和说词烽烟四起,不绝于耳,甚至也在事实上诱发、暗示和强化了人们的“ 世纪末心态”,或曰“世纪末”的生存方式。“他们重视工作,但不会因此而牺牲一己 的休闲娱乐和生活品味;他们在工作中追求自我满足,但不会计较头衔、地位和薪资。 在讲究出人头地的上一代人眼中,可能觉得这一代是不求进取;但在他们自己,却以为 少背负一些竞争焦虑,而多享受一些自得其乐的生活。”[2]于是,在大多晚生代作家 作品中,对现实世相则表现出了“有憎恨也有歌颂,有排拒也有拥抱”的多元情感状态 ;充斥于文本世界的无不是一拨拨的“富庶族群”、“乐观族群”、“消费族群”、“ 感性族群”;至于叙事策略,也大多新奇怪异、大胆露骨、影影绰绰。但是,在这个“ 最佳”里的叙事表现,却似乎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些人们对于晚生代的几成定评的精神意 趣和叙事策略,尽管“最佳”里的创作主体与一般意义上的晚生代同处于一个价值多元 、世事无序的文化背景。
在李季纹的《睡意》中,美莲和宝华这两位“闺中女友”的友情深厚且尽人皆知,乃 至于可以为着友情的相聚而跨洋越海。然而,一场寓言般的大雪,竟使得这场日久年深 的友情莫明其妙地顿时化为乌有,甚至“使得美莲对于盐湖城这三个字有一种近乎难堪 的记忆”。(注:行文中凡引用的小说原话(打双引号而未标明注释序号处),均出自袁 琼琼主编《2003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漓江出版社2004年1月版。)直至十年之后, 美莲从别人口中得知宝华去世,在别人认为她应该难过而一再对她安抚劝说下,“美莲 的悲恸一发不可收拾,趴在办公桌上大哭了起来。”“那当然,周围的人期望她会难过 ,她只要负责难过就好了。”由此看来,美莲的“悲恸”或许因为还残存着对于友情的 些许记忆,然而,这场一发不可收的“悲恸”与十年来彼此形同路人的冰封状态所造成 的反差,显然在暗示,美莲的嚎啕大哭当然不完全是为着宝华的去世,她实在是陷入了 深深的悲哀和不解:她与宝华彼此间曾经情同姐妹的友情何以被消解得如此地不着痕迹 ?人与人的感情何以如此地脆弱隔膜?正如同此时办公室里这幅别有意味的场景:一边是 “皱着眉头想当年宝华的老公务员们”,一边却是“正以超大的音量非常强势地在电话 里跟厂商议价,嘴里还咕噜咕噜地喝着珍珠奶茶”或者“非常专注地在办公室里忙着” 的男孩女孩。于是,她倦怠了,麻木了,转而陷入了深深的“睡意”,以为如此便可以消解“那些无以名状的空洞,和那些无可奈何又无可宣泄的愤怒”。
成英姝的《女神》在一个寻求亲情的故事框架下,写的却是一个复仇女神附身,乃至 不时发生意外和死亡的故事,但读来并不给人以恐怖和畏惧,只是疑惑:琉花是因为被 附身才变得那般不同寻常,还是世相本就如此,亲情难觅而无处不是隔膜、防备、怀疑 乃至复仇和凶杀?
陈思宏的《挂满星星的房间》写一个在多年前“出轨”而造成自己妻离子散、事业全 毁的男子“叶老师”,在他55岁生日的那天,决定走向死亡。但在这之前,他要去见见 别离多年的妻子和女儿,以释心愿,然后到当年“出轨”的现场去自杀。尽管他最终并 未完全“如愿”,也尽管整篇小说的形式尤显突出,但是充斥于文本始终的追悔感和赎 罪感,无不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惊:在当下这样一个“声色犬马”的现实社会中,人们还 能顾及德行、灵魂的自我审判一类的精神本源?何以却由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未经世 事的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来充当社会的良知?
童伟格的《王考》倒是写得影影绰绰,神神秘秘。“海村、埔村及山村——村人,难 得一起聚财聚力,翻田越岭十数回,终于由城内尖顶山圣王本庙,求出圣王正身一尊。 ”但是,如何“安置”这尊集威严、福禄、好运、避邪消灾“功能”于一身的“圣王” ?“谁也不愿在轮流供奉的次序及供奉时间的长短上退让”,于是,一场几乎无可避免 的械斗即如弦上之箭。然而,是祖父“从午前径自说到了傍晚,祖舅公抹抹老挂到下巴 上的眼泪,只觉得,身旁众人为了祖父的话,时而笑,时而哭,时而怒号,时而安静, 到了黑暗逐渐沉落的时候,众人居然一派和谐,满面红光,宛如圣王亲临。”祖父何其 神秘?何其了得?叙事者透过“孙子”“我”的追问,难道不是在执着的追寻、或曰极力 重新建构现代人因着“拜金主义”的膨胀而民心不古,进而已然失落了的对于生命、对 于伟力、对于意义应有的敬畏感?
梁慕灵的《故事的碎片》其实是一个颇为“完整”的叙事。身为母亲的母亲,以为女 儿不喑世事而把带着女儿作为借口,外出与人幽会。于是女儿阿珠“我”便获得了“启 蒙”,于是姐妹间也都“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乃至于在最后“几个妹妹都先后离 婚一次、两次、或是三次……但是现在轮到自己也快要离婚了。”这一家女人支离破碎 的“世袭”婚姻状况实在颇有些宿命的意味。笔者以为其“完整”,就在于作者在一个 个“碎片”似的婚姻故事中,审视的对象直逼“母亲”,而困惑着的同是一个问题:“ 母亲”有如一个预设的生存模式并且决定着“女儿”们的知觉和行为,现代人的生存困 境竟是宿命般的无法逃遁和规避?
林奎佑的《阿尼》在这个“最佳”里,应该是“典型”的晚生代叙事了,写的是一个 “后现代浪子”的“游戏人生”或曰“网络人生”。阿尼在一个虚幻的网络世界里,执 着于强者的精英信念,执着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至于现实社会中的亲情、孝道 、行为规范……在他眼里无不是真正的虚幻。于是,他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去探望久病 于医院的父亲,可以毫无愧疚地面对母亲的埋怨和啼哭。其有悖于现实人伦的绝然态度 ,对于传统的道德规范无疑构成了彻底的解构,同样,对于现代人的价值重构无疑也在 提示着一种审慎。
苏伟贞和虹影在这里大概是“长者”了,因此她们写的大多是“过去的事情”,或许 是沾了些“晚生代”的气息,在表现上不免都透出些奇异来。“他们还在变化中,并没 有因为成名而就此定型在自己的风格里”。虹影的《鹤止步》在一个同性恋的故事背景 下,极力张扬的是男人间刎颈之交的忠诚与情义,尽管整部小说的价值理性极为含混。 苏伟贞的《日历日历挂在墙壁》则在极力“试验新形式和拓展新范围”[1](P2)。写一 个传统家庭中看似传统的故事。主角冯老太太,早年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之后,便开始写 日记,而且日记从此也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其它的一切都与她完全疏离。但是,她的 日记是写在尽人可看的“挂在墙壁”的日历上的。这就使得一个“弃妇”的故事变得有 意味起来。日记里,如同钟摆的准时一样,冯老太太的生活仍然一如既往:随老爷子赴 宴,给老爷子摆寿,与“孙女”同享天伦,直至宣布自己“寿终正寝”。老太太的日记 仿佛一个诡谲的迷宫,看似漠然却深蕴着对世事的洞明,以“无声”的话语权让全家人 看得心惊胆跳,真假难辩。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在老太太的日记和家里人的观感间,加 入了两种叙述,一是西蒙·波娃与纳尔逊·艾格林的情书内容,一是沈从文《边城》里 与翠翠相关的情节,而所加入的这两种叙述又与故事的展开水乳交融,这么一来,则从 “日记”表像的另一极突显了老太太对世事过于洞明而在自我深处所产生的难以抵御的 寂寥与无奈,也暗示老太太与这个世界的渐离渐远。偌大个世界,人事纷攘,一个女人 却这样可有可无地终此一生,整部小说因着表现手法的新异而充满了哀怨和苍凉。在这 个“最佳”里,甘耀明的《圣旨嘴》是最玲珑可爱的一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最“ 另类”的了。故事本身已然就很“另类”。“像根木头躺在床上腐烂”已经五年的“阿 公”,“百病、风寒、五毒及野害人蚀,早晚要入土为安”了,却在一个鸟语花香的初 春时节还过魂来,随后便与众人同迎恩主公,与恩主公游春访友。而它的真正“另类” 更在文字上。“除非亲自阅读,否则很难体会甘耀明这段关于死亡的叙述有多么地清甜 香美,一点不带秽气。甘耀明的文字既纯朴又优雅,而他所营造的那种几乎欢乐的氛围 ,让整个故事非常地明亮,完全是春天的感觉。”[1](P9)
然而,给我们带来“另类”感的,显然并不仅仅是这个喜剧化的恩主公民间传奇。
二
对于一个时期文学精神的审视和追问,人们张扬或者不屑于“宏大叙事”,欣赏或者 鄙薄“自我写作”。但是,如果我们也以这一预设的思维定势来诠释这个“2003年度最 佳”的话,将无法抵达追寻的彼岸。在这里,我们是没有看到感时忧国的命题,也没有 感动于叙事者在背负着家国的重任;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同样没有看到几成定评的“ 新新人类”的疏离崇高,消解意义,也没有感受到认同世俗,放逐欲望的刺激。诚然, 在这里,也有婚外情、凶杀、猜忌、背叛……可所有这些给我们带来的兴奋,显然更在 于应了这样一句“行话”: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
我们以为,这些林林总总的文本所以共同构成了一个“最佳”,就在于,尽管人文坚 守与“晚生AI写作作”往往被认为已然构成了事物的两极,而本文所指涉的“晚生代”却 以其现实而特别的姿态在根本上坚守着作为人文写作者起码的叙事立场和精神诉求。
我们不应否认,这些各个不同的文本事实上显现着一个深刻而隐秘的内在关联,即以 他们极具个性的生命体验和审视切口,直逼现代人的生存困挠,而其中最为突显依然是 对人的欲望、价值理性、精神归属……的追问和质疑。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在“美 莲”那沉沉的睡意中,在“琉花”的不同寻常中,在“阿珠”一家母女“世袭”的婚姻 状况中,也同样在“祖父”的神秘,在阿尼的“叛逆”,在“叶老师”的“追悔”中… …,深切地领受了到世相的诡谲,人性的苍凉,灵魂的挣扎。我们想强调的是,在一个 环境浑浊,价值迷乱的现实状态下,人文情怀的坚守是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情 结的,而对于未曾经历过“抛头颅,洒热血”的战争年代,对于未曾遭遇过极权掌控的 时代的“晚生代”则尤为不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理性地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 不能不承认:上一代的忧国忧民,还不是为下一代创造一个安逸的生活环境吗?在安逸 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不再涕泗横流地背负着家国的重任,岂不也是上一代的期望吗? ”“我们不禁要问:一定要把街头的示威游行、号子里的股价涨落写入小说之中,才算 反映了社会与经济的状貌吗?是不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表达情感的方法、人 与人的交接的态度,也会同样地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呢?如果后者也同样有它的意义的 话,文评家就不得不放宽尺度,敞开心胸,才能看出‘新人类’一代的作品的长处。” [2]
而如果我们还继续从“怎么写”的思路往下走,我们还发现这些“晚生代”的叙事策 略也同样给我们带来别样的“兴奋”。
对于“晚生代”而言,其“前行代”作家几乎把文学有史以来的叙事方式,特别是西 方现代小说的形式和技巧都做过“全方位”的演练,甚至还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这 无疑给这些后生者企图实现艺术的超越无意中造成了障碍。但是,在这里,本文所指涉 的“晚生代”也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可以言说的丰富性。
对于这些“晚生代”,“前行代”作家丰富的叙事经验和警示恐怕是在于:醉心于完 全自我的艺术传达而忽略丰富灵动的现实生活;叙事技巧的运作仅仅被当做一种技术来 操练而放弃叙事的质感和接受主体的审美感受,由此而使得文学与社会及其接受主体渐 离渐远。或许,这里的“最佳”们并未形成超越的自觉性,然而,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 出了不动声色的“尊重”:对自我人生体验的尊重,对接受主体的尊重。
苏伟贞的《日历日历挂在墙壁》在叙述主线中同时插入两种看似游离的声音,无疑是 经过了对所有经典文本的千筛万选,作者显然很是用了心机,但读来却不给人以突兀和 生硬感,恰恰相反,以为这两种声音本来就是为叙述者而准备的,三种叙述的并行不悖 而又浑然一体,使整部小说充满了哀怨和苍凉,也极大地拓展了接受主体艺术想象的空 间。成英姝的《女神》、童伟格的《王考》、梁慕灵的《故事的碎片》等显然也是在选 择叙事“载体”上很是“考究”的,但他们并不有意于文本的“陌生化”效果,因此, 其叙事怪异但并不使人惊恐,神秘但并不“莫测”,“破碎”却完整。或许他们已经看 到了不少“前行代”作家由于醉心于艺术实验而使创作不同程度地陷入某种困境,便有 意识地规避了自己,力图在自身的历史语境和人生体验中寻求艺术的突破,而这种寻求 又是建立在审美价值得以最大实现的基础上的。因此,这些“最佳”让人们透过他们对 世俗生活表像的叙述看到了生活底蕴的繁复,在他们的“不动声色”中触摸到到叙事者 内心真实而本质的感受。
以“前行代”作家创作的经验教训来规避自己,并不意味着不再重复或者运用富有质 感的形式和技巧。陈思宏的《挂满星星的房间》写追悔和赎罪,所以触动人们对灵魂的 拷问,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得益于其文本意象的生动和意涵的丰富。这里的“星星”其实 是内含了两个意象:一个是父亲为女儿卧房的天花板和墙壁上贴满荧光星星,关了灯, 便会出现满天星光,这一意象的恰如其分运用,更加强化了父亲的追悔而又无以追悔的 绝望感;另一个意象则来自男主人公看过的电视节目。“节目主持人拿着一个可以照出 精液遗留的灯具,在一家五星级饭店的房间里四处探照,结果各个角落都有精液的残留 闪闪发光,窗帘上、墙上、桌上、落地灯罩上、挑高的天花板上,精液简直是房间里的 繁星点点,无处不在。”而男主人公“出轨”的地点正是一家饭店,两相联想,让其感 到被“曝光”的无疑就是主人公自己,强烈的无地置容感,至使自己也永远地失去了“ 制造星星的能力”。生命力的丧失,有如真心赎罪却无人接纳,如此深重的无助感,结 束生命恐怕就是最好的解脱。显然,作者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其形式与技巧并没有散漫 于文本之外,而是渗透于生活本身,以通过最世俗的生活本身获得了最深刻的灵魂震动 ,这无疑在传统的写实与不少“前行代”作家的西方技巧实验中实现了一次很好的艺术 突围。甘耀明的《圣旨嘴》更是在语言的运用上既活络了传统写实小说中的“一板一眼 ”,又摒弃了西方现代派小说有意构织语言迷宫的作派,使其“文字好到极点,文辞雅 俗并济,往往随处画龙点晴一两字,把整个老俗句子都脱胎换骨了。他的描述五觉并置 ,让人看到,听到,闻到,嗅到,尝到。”[1](P11)
显然,作为叙事策略的“策略”,在这里,已然被深深地植入了各个文本的肌理,而 各个文本所暗含的“意义”、“价值”这些形而上的精神拷问也因着可触可感的世俗物 象而避免了悬置感。因此,不满足于对“前行代”作家成功经验亦步亦趋的追慕,亦清 醒地看到“前行代”作家在创作上,或者机械地偏执于“铁肩道义”、或者醉心于纯粹 的主观化而陷于某种困境,并以此作为实现创作突围的内驱力,从而确立属己的叙事策 略和形成自身的美学特征,这恐怕就是“2003中国年度最佳台湾小说”这道令人瞩目的 文学景观的意义所在。
收稿日期:2004-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