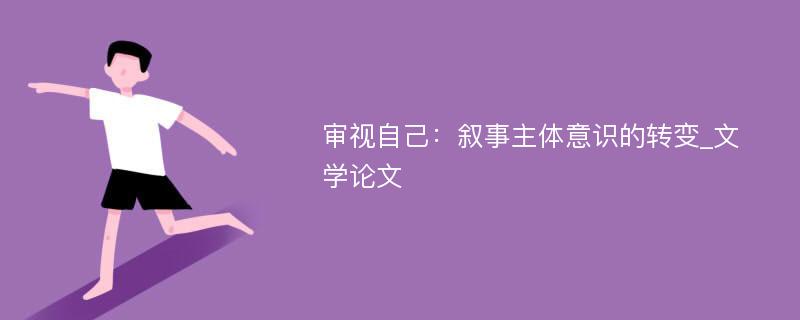
守望自我:叙事主体意识的变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意识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5-0065-09
叙事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叙事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表述行为,其自觉性和人为主显而易见。任何叙事都是由一个叙事主体来实施的,或隐在或显现的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以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事件进行选编加工,最后使之呈现为文本。没有叙事主体的自觉行为,便不可能有叙事文本的产生,自在状态下的客观事件不可能成为叙事文学的内容。毋庸置疑,叙事主体在文本创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
叙事的主体意识可追溯到叙事传统之初,柏拉图等人对叙事模式的划分就涉及叙事主体的隐现问题。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试图区别诗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讲话”,讲述“他人的故事”,还是摹仿人物的口吻,“要我们相信是另一个人在讲话”。(柏拉图:96)柏拉图不赞同诗人进行过多摹仿,主张诗人在叙事中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其时叙事的自觉意识已开始产生。古文中常见的“君子曰”中的“君子”会在叙事中表明叙事意图,张扬主体意识,即叙事学所称“介入式叙述者”。据傅修延考证:
叙事主体在《左传》中频繁地现身文本,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评价,显示出一种指导阅读的高昂姿态。……凡此种种,表明这些作者不但意识到自己在叙事,明白自己是为某种既定的目的而叙事,而且意识到自己是叙事的主宰。(傅修延:56)
马克·柯里这样描述“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
当代叙事理论普遍认定这样一种观点,即叙事只是建构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其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我一直在描述着的是一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叙事中的自我意识。(Currie:118)
柯里的后现代叙事观突出了作为叙事主体的人的主观意识,因为人是叙事的自觉施为者,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或隐或现的自我意识。
作为叙事话语的发出者,无论叙事主体以显著的方式陈述自己,还是以隐蔽的方式伪装自己,其自我意识总会在叙事中被感知到。西摩·查特曼根据叙事主体被感知的程度提出了“公开的叙述者”和“隐蔽的叙述者”的概念。“公开的叙述者”可以是小说人物,也可以是外在叙述者,往往对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定的情感倾向;“隐蔽的叙述者”则含蓄寡言,避免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不露痕迹地隐身于叙事中。(Chatman:34)此外,依据叙事主体对叙述的介入程度可分为两类叙述者。如果叙述者对故事保持不介入的态度,不在文本内公开自己的写作过程,即为“自然而然”的叙述者;如果叙述者对事件、人物发表评论,并在小说内说明自己在叙述,即为“自我意识”的叙述者。(胡亚敏:37)
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是与叙述行为相伴而生的,作者的修辞意图主导着叙述活动的全过程,其主观能动性不可忽视。无论采取哪种叙述方式,叙事的主体意识始终存在其中。经过叙事主体对客观之事的增删和重组,文本便脱离了对事物的机械复述以及对话语的简单转陈而成为自觉的艺术创造。在后来的叙事活动中,曾有人提出“作者之死”的概念,倡导“作者隐退”,尝试“零度写作”,试图消解叙事的主体意识,叙事的自我意识渐渐淡化甚至隐而不见。至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时期,在巴赫金的复调等理论影响下,叙事主体进一步发生分化,自我意识趋向多元,突破了传统的一元化叙事格局,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热烈景象。纵观由古而今的叙事传统,叙事的主体意识历经强化、淡化和分化几个阶段,叙事自我的多样化产生了多姿多彩的叙事文本。然而细察之下,叙事主体虽变化不居,却无处不在,叙事的自我意识只有程度上的强弱之差,或隐现之分,却从未完全消失。本文拟从叙事主体在叙事文本中的三种存在形态来考察叙事的自我意识之变化规律,以期领悟叙事主体在叙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避免的自我意识。
一,自我张扬:叙事主体意识的强化
1.“公开的叙述者”:叙事自我的强化
关于叙事的主体问题,罗兰·巴特总结出西方理论界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叙事作品是一个人(就该词的实足的心理意义而言)表达出来的,这个人有个名称,即作者。在作者身上有个定期写故事的、清晰可辨的人。他的“个性”和艺术不停地相互交流,因此叙事作品(主要是小说)仅仅是作品以外的“我”的表达。第二种看法把叙述者当作一种完整的意识,似乎是无个性的,该意识从超高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讲故事。因此叙述者既在人物之内(既然人物心中所想的一切他全知道),又在人物之外(既然他从不与任何一个人物认同)。第三种看法是最新的看法(如亨利·詹姆斯、萨特),规定叙述者必须将其叙述限制在人物所能观察到的或了解到的范围之内,因此叙事作品的表达似乎是轮流由每个人物担当。(巴特:29)
由此,叙事主体体现为三种形式:作者、叙述者及人物。叙事作品首先是作者的创作成果,由作者的话语行为所构成,是作者个人意识的体现,作者是文本的意义之源。然而,除个别极端的例子外,通常情况下作者本人不在作品中直接现身。因为从逻辑上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无法进入自己创造的虚构小说世界。于是叙述者作为作者的代言人进入文本,行使作者的话语权,传达作者的意图。这种作者式叙述者拥有上帝般全知全能的叙述权威,当仁不让地掌控着整个叙事格局。另外,叙事主体可依附于某一人物进行限知叙事,而作者作为真正的叙事主体隐身幕后。无论叙事文本采用何种叙事情境,叙事主体都可以通过叙述者或人物之口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我意识。
早期的叙事文学中大都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公开的叙述者”,作为承担叙事话语的行为主体,以全知视角来叙述事件、塑造人物,并对之进行评说,韦恩·布斯称之为“早期故事中专断的讲述”。(布斯:21)叙事主体往往借托某种身份现身于文本的叙述层,以第一人称“我”或“我们”自称,直呼读者为“你”或“你们”。叙事完全由叙述者的自我意识所支配,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都服从叙述者“全权主体”的绝对权威,叙事主体表现出一种十分张扬的话语霸权,单一的权威声音形成典型的一元化叙事。
中国古代的史著作者自视无所不知无事不晓,且有评判是非之能力,故史传类叙事通常启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史记》的叙述者以“太史公”的身份现身于文本中,对事件和人物加以褒贬。兴致所至之处甚至议论多于叙述,自我意识十分张扬。《左传》的叙述者高频率地使用“君子曰”,借君子之口行己评之实。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姿态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主体意识鲜明的叙事传统。早期叙事多沿袭这种传统,故事外第一人称叙述者直接现身,直呼读者为“列位”、“看官”等,在读者与故事之间充任中介,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十分明显。明清小说如《西游记》的叙述者自称“野史氏”现身叙事文本,而《聊斋志异》的叙述者以“异史氏”之名展开叙事。无论叙述者借托何种身份,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始终存在于文本中。《红楼梦》的开篇,叙述者就开始调遣“听众”,直截了当地以全知全能的权威口吻展开叙事:“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鲁迅的《阿Q正传》仍可见这种叙事传统,在展开叙事之前,作者式叙述者对将要进行的叙事行为进行说明,“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西方的叙事文学始于长篇史诗,再由浪漫传奇向小说演变而逐步成熟。人的自觉意识的产生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张扬形成了一种由叙事主体掌控的全知叙事,与中国的叙事传统殊路同归。全知叙述者俨然是文本世界的创造者,具有上帝般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力,穿梭于不同时空,操纵人物,展示事件,发表己见。如巴尔扎克、菲尔丁等人的作品多采用无名的第一人称作者式叙述者,以“我”或“我们”自称,直接介入叙事。在萨克雷的《名利场》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自称为“本书作者”,并将自己与“细心的读者”、“随和的读者”合称为“我们”。叙述者在开场白中把《名利场》比作一出木偶剧,自称为指挥表演的戏班班主,众人物如同听凭其操纵的木偶,任由他评头品足。这种公开议论观点鲜明,情感直露,反映了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叙事学家申丹在指出介入性叙述之缺陷的同时,也承认这种议论所起的画龙点睛的作用。(申丹:208)
这类叙述者往往难以分清自己与作者的区别,在叙述中自觉不自觉地与作者发生身份认同,对故事内容同时也对描述话语进行随心所欲的干预,是典型的“自我意识”叙述者。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最后一章题为“就此搁笔”,第一人称叙述者哈克以明显的自我意识总结叙事:“再也没什么可写的了,不过我心里倒挺高兴,如果我事先知道写书有多麻烦,我压根儿就不会动笔。”更令人称奇的是,爱略特的《亚当·比德》中的故事外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小说作者的名义亲自出面,与小说人物直接交流,两者之间的对话长达四页之多。
如果是第一人称人物自叙,叙事主体名正言顺地以主人公身份现身于文本的故事层,叙事主体的“我”和叙事客体的“我”(即叙事学所称“叙事自我”和“经验自我”)合二为一。一方面,作为行为主体的“经验自我”在虚构的故事世界里行动着,另一方面,作为叙事主体的“叙事自我”又在描述和评价作为叙事客体的“经验自我”,作品中处处充斥着叙述者的身影和声音,主体意识尤为张扬。如斯特恩《项狄传》中的叙述者醉心于自己离题万里的叙述过程,而将主人公的故事放逐到叙事边缘。叙述者特里斯川以活跃的叙述行为和对这一行为的有意炫耀侵占了叙事的中心,喧宾夺主取代主人公特里斯川成为小说的灵魂。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叙述者身份,天经地义地享有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特权,文本充满了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我想告诉你的只是我去年圣诞节前的那段荒唐生活。”第一人称人物叙事所特有的明显情感倾向、浓烈的主观色彩以及过度张扬的主体意识无疑形成了一种话语霸权。
2.主体显现:虚构的权威
这种由“自我意识”叙述者施行的“关于叙事的叙事”,即叙事学意义上的“元叙事”。叙述者全面参与叙事活动,对叙事格局进行总体安排,还对叙事本身加以评析,形成自涉性叙事。叙事主体高度膨胀,自我意识十分张扬,叙事话语肆意妄为。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尝试过这类叙事,早期有斯特恩和马克·吐温等,晚近则有福尔斯和加斯等人。其实,叙事主体的高度集权、叙事行为的过度暴露恰恰反映了叙事文本的虚构本质,损害了作品的逼真效果,文学反映真实的愿望只是一则虚构的神话。
斯特恩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他将《项狄传》的一章题为“有关章节的章节”,专门讨论写作过程,暴露叙事陈规,戳穿叙事花招,警告读者故事的虚构性。特罗洛普的《巴切斯特大教堂》中也常见自涉性叙事,叙述者中断故事叙述,对自己的写作意图进行说明。同样,巴斯的《迷失在开心馆中》的叙述者在叙述主人公漫游开心馆经历的同时插入自己对小说的构想,包括细节描写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对叙事本身的讨论无疑暴露出文本的虚构性质。更有甚者,《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在小说中谈到作者马克·吐温及马克·吐温的小说写作。叙述者故意暴露模仿真实的叙事手法,打破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幻觉。
叙事意识的过分张扬,叙述痕迹的过度暴露,无疑动摇了作者叙述的权威性并损害了人物叙述的真实性,“可靠的叙述者”不再可靠,叙事主体的话语霸权受到质疑。但这也标志着某种认识上的进步,叙述的自我意识意味着对自身缺憾的觉悟,戏谑式自涉正是对自身虚构性的警醒。作家们不再掩饰叙事的虚构性,不再利用种种手段制造真实的幻觉。于是,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第五十五章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小说作者以一位面目阴郁的男士形象现身于百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跟主人公查尔斯同坐一列火车,肆无忌惮地对人物进行观察,同时又以作者身份与当代读者进行交流:“亲爱的读者,总有那么一天,有人也可能这样注视您。……目光中奇怪地混杂着探寻、严厉、讥讽和恳求:我可以利用你吗?我怎样来处理你这样一个人物?”这个场景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叙述者在与读者的想象性对话中,将文本的创作过程贯穿于叙事之间,有意识地披露人物处理、结局安排等人为手段。这样,文本的叙事过程进入小说叙事之中,与小说指涉的事物一起成为叙述对象。而当代作者极其荒谬地现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则彻底打破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幻觉,文本的虚构性昭然若揭。实际上,这种有意为之的自涉性叙事突破了叙事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而揭示出其虚构本质。
中国叙事文学中也有类似现象,其中马原的创作最为典型。马原公开声明他的故事是虚构的,自己就是一位虚构大师,他的一部小说就题名为《虚构》。叙事开篇,“自我意识”叙述者就公然声称:“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个自称“马原”的人一会儿是作者,一会儿是叙述者或人物,在几个平行的故事中来回穿梭,时时插入怎么写小说的讨论,引导读者对叙事行为而不是故事本身加以关注。作家不再伪造真实感,而是将叙事过程展露出来。这种背离常规的叙事理念标志着对传统叙事的挑战和颠覆,使读者得以认识作者的想象力、故事的荒诞性及作品的人为性,叙事的虚构性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自我隐退:叙事主体意识的淡化
1.“隐蔽的叙述者”:叙事自我的弱化
西方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发展至现代,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福楼拜和詹姆斯等人看来,传统叙事体现了过多的主体意志,情节安排、人物形象都是叙事自我的主观表达。人物的思想和话语、叙事的方式和风格都由作者意志所统摄而成为一个意义固定的文本世界,严重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他们主张作者约束自己的权力,尽量保持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自觉地在创作中消除自己的痕迹,最大限度地进行客观叙事。福楼拜表示,“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一样。”(伍蠡甫:210)
在福楼拜、詹姆斯等人的倡导下,西方叙事艺术创立了新的审美准则,全知型主观“讲述”受到质疑,反之,客观“展示”成为小说叙事的主流。作家式叙述者放弃了无所不能的全知视角,不再对人物与事件发表干预性评论,从上帝般唯我独尊的权威地位上隐退了。“作家隐退”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艺术法则。
正是福楼拜等人的创作开始了叙事观念的变革。《包法利夫人》的开头便是这样一项标志性革新,“我们在自修室上课,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这个“我们”仅在包法利首次出场时短暂地介入,且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既不是传统的第一人称作者叙述者,也不是同时充任叙事主体和客体的主人公叙述者,并很快在后面的叙事中消隐不见了。福楼拜此举是一则有意味的暗示,传统叙事中那种大于人物通晓一切的叙述者从此隐退了。于是自然而然的“隐蔽的叙述者”取代了滥发议论的“公开的叙述者”,了无痕迹地隐身于文本之中,让人物和事件自行呈现,以消解叙事作品的虚构性和人为性,从而制造一种逼真的效果。卢伯克这样描绘莫泊桑的叙述者:“他好像根本就不在那儿,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分明需要评判的事儿,他一点也不会使我们想起他是在场的。他在我们背后,我们看不见他,也想不到他。”(Lubbock:113)
现代文学史上叙事观念的变革就是“讲述”和“展示”两种相对应的叙事方式的冲突。“讲述”以全知叙述者为中介,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概括和评论,叙事主体的过多介入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感;而“展示”是事件和对话的直接再现,避免了作者的个人意识,所以更为客观真实。现代小说家推崇“展示性”叙事,呼吁“作者隐退”。叙事主体取消了惯常的权威姿态,不再对人物和事件妄加评论,放弃了“全知全能”的无限权力而退居幕后,或依附于某一人物,随人物视角不动声色地展现小说场景,叙事严格地限制在人物所能感知的范围内。
最极端的情形是作者完全隐身幕后,采取外聚焦模式,不进入任何人物的意识,只将人物语言和行为记录下来,甚至略去了“他说”、“他想”这类基本叙述语,尽量消除人为的叙述痕迹。如海明威在《一个洁净明亮的地方》中以极其简略的对话展现咖啡馆的一幕,不多的几个人物无名无姓,只被称为“老绅士”、“年长侍者”或“年轻侍者”,叙述者佯装置身事外不知内情的旁观者,不交代人物的来龙去脉,不加评判地转述人物对话,录写人物行为。作者无意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读者,以含而不露的“冰山”风格而著称。
意识流小说往往不加解释地录写人物的思想化语言,同样可取得淡化主体的效果。“公开的叙述者”转化为“隐蔽的叙述者”,叙事依据人物的意识流动自然进行,客观地展现心理真实。小说中至多间或出现“他说”、“他想”之类的引导词,介入性叙述者的解释性话语几近灭迹,叙事主体明显弱化,自我意识异常淡薄。意识流技法的运用迎合了“作者隐退”的时代要求。
这种主体意识淡化近乎“无我”的叙事情境同样也是中国叙事艺术的审美追求。晚清学人黄摩西的小说评论就可见这种意识:
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媛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角色出场,横加一段开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著我一之见,如《水浒》之写侠,《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艳,《儒林外史》之写社会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题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孟昭连:64)
中国现当代叙事积极接纳西方叙事理念,掀起了“作者隐退”的文学潮流,开始由“讲述”向“展示”转向,施行“零度”叙事,反叛过往叙事文本中无限膨胀的自我主体。池莉的《烦恼人生》以从容含蓄的叙事风格反映主人公在生存重压下那种无助、无奈、无为的消极人生,全无传达某种政治意义或者进行道德说教的主体冲动,也没有作家主观情感的强烈参与,那种是非鲜明的叙事自我在文本中已销声匿迹。显然,中外叙事文学都是循着由“主观”到“客观”,从“有我”到“无我”的轨迹发展的。作者、叙述者和人物,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叙事主体,叙事逐步免除了作者主观狭隘的诠释,取消了叙述者的高谈阔论,甚至放弃了暗示性议论,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2.“作者隐退”:虚幻的真实
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学界“作者隐退”甚至“作者之死”的呼声不断,主体消隐的客观叙事大行其道。由于作者的隐退,叙事主体趋弱化之势,没有了活跃在前台喋喋不休的“公开的叙述者”,现代小说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叙事姿态来反映生活,作品似乎显得更真实可信。在一定意义上,叙述者的隐现策略成为衡量叙事真实性的标准,叙事主体的显现方式不一,作品的逼真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这种刻意为之的客观叙事是表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本相,还是仅仅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幻景呢?
其实,叙事的所谓“主观”与“客观”、“有我”与“无我”都是相对的,“讲述”与“展示”也各有千秋,并无优劣之分。任何叙事都是主体姿态的体现,是作者意图的表达,无论自觉与否,都渗透着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客观真实”只能是相对的,典型的“展示”也无法脱尽“讲述”的痕迹,只是主体意识更为隐蔽含蓄,叙事始终指涉着文本之外的作者的审美观。最含蓄的作家如海明威依然会在其叙事话语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取向,暴露自己的隐性立场,让人感到“冰山”下所潜藏的情感倾向。叙事主体作为叙述行为的承担者可以选择或公开或隐蔽的存在方式,但是不可能彻底消隐。正如布斯所说,“作者可以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但他总是存在于作品中。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布斯:23)叙述者更无法在叙事中保持中立和公正,因为“最中立的议论也会暴露出某种信奉”。(布斯:85)布斯断言,无论什么样的小说,作者的声音从未真正沉默。
福尔斯则表示完全不相信“声音是已经死亡了的技巧,没有任何技巧能够使我们摆脱‘全知作者’的罪名……如果一个作家仍然在从事写作,并且像罗伯特·格里耶那样写得不错,那么他就会出卖自己的声音。”(Fowles:143)申丹认为,即使在意识流这类现代小说中,人物的思想仍然是由作者所创造,作品中用“自由直接思想”或“自由间接思想”来实施的心理叙述仍然是叙述主体的行为结果,只是叙述干预较轻而已。(申丹:334)
中国新写实小说要求“作者隐退”的呼声最高,作品中叙事主体尤为隐蔽,文本中难觅作者的身影,叙事评价十分含蓄,叙述者仿佛中止了价值判断,放弃了作品的倾向性表达,追求一种客观真实的叙事风格。其实,这只是作家们一厢情愿的奢望。任何叙事话语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介入,叙事内容的选取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包含一定程度的叙述干预,其虚构性和人为性是无法避免的,“中立叙事”、“零度情感”完全不具绝对性意义。福楼拜等人所倡导的“作者隐退”、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都未能改变叙事话语的权力格局和主体意向。现代小说中介入性叙述者逐步隐退,自我意识趋向弱化,作者的话语权力受到限制,并不意味着叙事的主体意识已彻底丧失。叙事主体的隐在或显现只显示主体干预的程度差异而已。现代小说中隐身于叙事进程背后的叙述主体作为一种缺席的客观存在,永远有着不可忽略的功能和价值,它所占据的霸权地位仍然无法取代,作者并未逝去,非意向性的叙事只是一种真实的幻觉。
三,自我分裂:叙事主体意识的分化
1.众声喧哗:叙事主体的多元
如前所述,任何叙事行为都是由叙事主体来实施的,叙事文本中的行为主体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有时是隐含的作者,或出场的叙述者,也可以是作品中的人物。多重主体意识共存的叙事情境势必形成主体意识分化的现象,这种分化有时是叙述者意识和人物意识之间的分化,有时是作者意识与主人公意识之间的分化。赵毅衡认为,主体分化是任何虚构叙述行为都有的普遍现象,不同叙事作品的主体分化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赵毅衡,1998:28)因此,多元分化是叙事主体存在的特殊形态。
传统文学中的叙事主体较少出现意识分化,作者和叙述者往往不加区分;在大多数叙事情境中,作者即叙述者,作者意识作为叙事中唯一的中心意识凌驾于其他意识之上,充当全体人物的话语表述者;整部作品都是作者权威声音的独白,体现了一种官方的、教条化的语言规范。因而传统叙事通常为一元化叙事,即巴赫金所称“独白小说”。叙事主体的高度集权在不同叙述话语之间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主人公的个性和意识都受制于作者意志,只能由作者的一元化独白来展现。显然,这种独白性叙事与我们呼唤平等、倡导多元的时代精神是极不相容的。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呼声日益强烈,要求瓦解中心和权威等后现代思潮得到广泛认同。巴赫金以对话为核心的“复调”理论适时地流行起来,叙事主体也因之发生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分化,由单一趋向多元,众多相互作用的意识并存,形成复调型叙事格局。作者在叙事中放弃主权,改变全知的俯视姿态,平等对待主人公意识,赋之以思想的独立和话语的自由,与他们展开平等对话。作者式叙述者的退场使话语主权旁落,人物的自我意识得以凸现。主人公由被描绘的纯粹客体转化为另一叙事主体,以独立的自我之声参与对话。叙事主体的严重分化使文本意义趋向多元繁复,各种意识平等相处却互不相融,不同价值体系发生碰撞交流,形成了一个主体多元、众声喧哗的语言场所。
在现代人看来,真正优秀的叙事作品,主体都出现分化……主体各部分的冲突,叙事作品容纳这些冲突主体的声音于同一文本的努力使作品呈现一种多元复合的戏剧性张力。(赵毅衡,1990:7)
意识流小说对人物意识活动的展现就是叙述者在转述人物的思想化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主体分化现象。叙述者的声音与众多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文本中形成双重或者多重主体共存的叙事情境。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叙事分别由四个人物叙述者轮流进行,同一事件由多种不同的声音来描述,这些声音立场各异甚至相互矛盾,叙事主体出现分化。伍尔夫的《海浪》也可见多个主体意识的平等展现,主人公通过独立的话语进行自我展示,每个人物的立场和意识都处在与他人意识的对话中,同时共存又互不认同,文本因之呈现出多元意义。一时间,多元主体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趋势,仿佛主体分化越严重,作品就越出色。昔日的那个一元化叙事主体逐步消失,支配与被支配的既定关系悄然瓦解,单一的主导思维受到质疑,异质的话语获得了存在的机会。
人物话语的转述方式是主体分化的文本表征,例如在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以人物立场表现人物心理,同时传达叙述者和人物的两种声音,不仅保留了人物意识,也反映了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一种多重主体共存的现象。申丹所举《傲慢与偏见》中的一例即为明证。在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一幕中,柯林斯啰唆地陈述了一大堆荒唐可笑的理由,这时文本中出现了这么一句话:“现在非得打断他不可了。”据申丹分析,此句应为用自由间接引语表达的伊丽莎白的内心想法。但其语言形式类似于叙述语,因此也可理解为叙述者发出的评论,还道出了读者的心声。三种声音的和声同时传达出作为直接听众的伊丽莎白和作为间接听众的读者以及叙述者三方的意识。此时的人物意识被吸收为叙述者的话语,主体意识一分为三,形成了多语共存的态势。(申丹:349)
中国小说叙事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主体分化、自我多元的现象,如莫言的《檀香刑》中的眉娘等几位人物分别在文本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在表明各自的思想和立场,不再为作者意识所左右,改变了以往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类似上帝与造物之间的等级关系,代之以平等互动。叙事主体的多重分化使文本中的人物意识趋向多元,形成复调性叙事和开放性结构,多种独立话语和不同价值都以前所未有的多样性立体地展现出来。
2.主体分化:虚伪的民主
从表面上看,叙事主体的多元分化迫使作者最大限度地放弃自我意识和主导地位,对主人公采取一种平等的对话立场,并赋予他们以独立的意识和自由的个性。获得了自我意识的主人公和作者意识平等共存,以独立的声音参与对话,与他人意识展开交锋,表现生命个体的精神存在,享有自我言说的充分民主而不必受制于作者的意志。
然而,任何叙事文本都是由作者创作出来的,选题取材、对人物进行审美观照、赋予作品以形式等等,都是作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体现。主人公本身也是作者创造活动的产物,无疑要服从于作者的意图;其自我意识始终处于创作主体的控制之中,因而无法彻底改变被动的客体地位从而获得足以与作者意识抗衡的充分主体地位,也不可能与作者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更不可能排除作者的思想和声音而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话语权力。作为文本的创造者,作者支配一切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作者的声音无疑是复调中那个高昂的主调,主导着他人的声音和意识。那种有着众多平等意识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狂欢,也是作者依据自己的意志安排的。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分化使叙事自我丧失了中心地位,由一个理性和谐的统一体转化为分裂松散的多重矛盾体。思想的差异性和表述的杂语性致使文本意义悬置、价值瓦解、秩序混乱、旨归不明。主体分化并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叙事文学的价值性意义。因此,巴赫金构想的“作者意识、主人公意识及其他人意识平分秋色,按照小说的主题各自发展、争斗、对话”的理想格局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景,多数人享有同等话语权的“民主”仍然是一则神话。
叙事文学是一项以人为主、技巧性为基本特征的虚构艺术,而真实性则是作者与读者双方默认的游戏规则。叙事活动的根本性质是虚构,却以追求真实为目的,这种悖论性使其发展始终处于一种矛盾运动中。每一代作家出于自己对真实性的理解,采取种种不同的叙事策略,叙事的重心逐渐由作者、叙述者至人物发生位移,叙事主体也经历了从自我张扬到自我隐退终至自我分化的变更。高谈阔论的主观叙述者为冷静含蓄的客观叙述者所取代,最终分化为具有平等意识的多重叙事主体,叙事立场发生了由显性向隐性再至平等的转化,完成了从类型化的单一叙事到写实性的客观叙事再到多元化的复调叙事之转型。正是叙事主体的多元形态引发了叙事格局的繁复变化,显在与潜隐、自觉与被动的主体姿态左右着叙事文学的发展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叙事文本仍然是、也只能是主体意识对叙述内容合乎规律的主观把握,作家意识仍然主宰着叙事进程,实施对客体的渗透和控制,叙事主体依然以各种方式坚守自我,顽强地表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