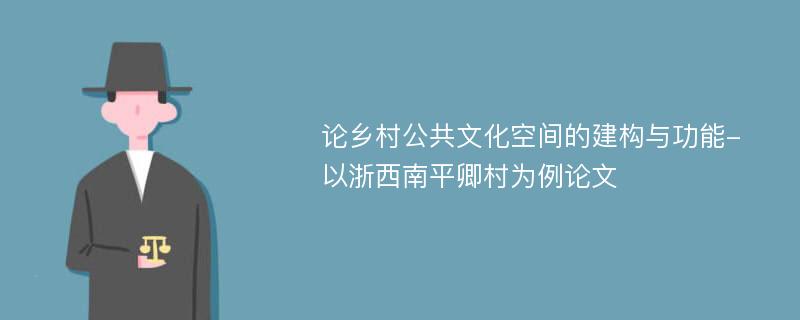
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与功能
——以浙西南平卿村为例
贺 少 雅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A摘 要: A本文以浙西南平卿村为个案,重点剖析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体系和特征,肯定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和意义,讨论公共文化空间的现代重构问题。文章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是基于村落内生动力的产物,是村民生产生活和精神需求的物质载体,具有强烈的神圣性、实用性、规范性以及一定的现代性,符合当前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又与公共文化建设具有矛盾之处。
关键词: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空间建构;文化功能;基层社会治理
一、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以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空间研究转向① 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其中,福柯侧重对空间与知识、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列斐伏尔则在《空间的生产》(1973年)一书中论证了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重性的辩证统一② 李山: 《文化空间治理:作为文化政治的行动策略》,《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2期。 ,提出了“文化空间”概念,但并未对其作具体阐述。1990年代,“文化空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以利用,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空间理论亦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日益受到国内学界重视,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融合③ 参见伍乐平、张晓萍: 《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3期;覃琮: 《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 。
近年来,随着国内乡村建设热潮的兴起和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大力推动,公共文化空间理论逐渐从城市走向农村,成为乡村研究热点话题。作为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公共空间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自由平等对话、讨论公共事务和参与政治的空间④ 王江涛: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0页。 。但在本土化实践中却催生出一个新概念“公共文化”“其内涵和外延都极具中国属性”“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创新的标志”① 高丙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及服务体系建设的双元主体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学者看来,“是一个既包括农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又涵盖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制在内的整体性概念”② 关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学界还有一些界定,但未有定论。参见傅才武、侯雪言: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艺术百家》2016年第6期。 ,融合了文化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理论框架,这是本文讨论的重要基础。就乡村公共空间的划分,有的学者根据型构动力不同,划分出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前者属于外部行政力量介入的“行政嵌入型”,后者指源于村庄内部传统、习惯和现实需求的“村庄内生型”③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第4期。 。有的分为“内源性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现代公共空间”④ 李志农、乔文红: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学术探索》2011年第8期。 。还有的按照时间维度,划分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和“新兴的公共文化空间”,前者包括传统节日仪式空间、庙会集市等,后者包括村委会、学校、医院、文化广场等⑤ 马永强: 《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和实现途径》,《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这些划分方法各有所长并存在交叉,本文借鉴“神圣—世俗”理论框架,按照公共文化空间的性质不同划分出“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前者包括庙宇、祠堂、香火堂等,后者则有村委会、学校、小卖部、村头巷尾等。限于篇幅,主要讨论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神圣空间。
学者们从公共文化建设入手,对空间的内容建设和空间重构,空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场域(或称“表征的空间”“第三空间”)的构成要素及其价值作用的论述很多。高丙中指出,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虽然在硬件建设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但也存在公众参与不足、内容建设不足等问题,就此他提出构建国家与社会双元主体,吸纳非遗资源,构建地方特色公共文化等建议⑥ 高丙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及服务体系建设的双元主体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高春凤认为可以引入叙事理论,解决乡村文化空间建构只重视物质建设,缺少内容连接的不足⑦ 高春凤: 《叙事性表达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路径》,《学习论坛》2019年第2期。 。陈波、侯雪言基于文化场景理论解释框架,探索提升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率的对策⑧ 陈波、侯雪言: 《公共文化空间与文化参与:基于文化场景理论的实证研究》,《湖南社会学科》2017年第2期。 。袁瑾从公共空间理论入手,对绍兴舜王庙会的构成要素即空间的地理承载、基本结构和公共精神进行了剖析,讨论传统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型⑨ 袁瑾: 《传统庙会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以绍兴舜王庙会为个案的讨论》,《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年第2期。 。桂胜等聚焦湖北恩施非遗传承的困境,提出通过文化空间再造的模式,力图整合非遗资源和既有非遗保护方式,实现非遗项目传承保护与助力精准脱贫的双赢目标⑩ 桂胜等: 《文化空间再造与少数民族“非遗扶贫”的路径探析——基于鄂西恩施市的田野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1期。 。还有的将文化空间作为非遗的一个类型展开研究,但更多的是将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聚焦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承载的民俗事象,诸如节庆、仪式和庙会等,进行历史、结构、功能、价值等深入研究⑪ 参见覃琮: 《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一文对文化空间类研究的梳理,《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 。基于此,本文仍以文化空间为切入点,将其置于乡村社会治理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以浙西南平卿村为个案,重点剖析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体系和特征,肯定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和意义,并针对当地社会转型中的新问题,探讨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问题。
二、三种边界与三层认同: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的结构要素和价值体系
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① (美)迈克·迪尔(Michael J. Dear): 《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收入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3、86页。 。日常生活所处的自然地理空间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理存在,也在人类改造和利用过程中被赋予某种人文意义,体现着人们看待世界、观照自身以及构建生存意义的精神理念。
本文所讨论的平卿村位于浙西南松阳与遂昌两县交界处近800米的高山台地之上,气候温和湿润,竹林绿树环绕,生态环境优越。据村内《周氏宗谱》记载,周氏先祖“伯仁公始自遂昌四墎周”“迁居于松阳十二都大岭脚而居焉,其幼子三道公由大岭脚而见其平卿山川秀丽田园广庑,遂卜宅而居焉”② 《汝南周氏宗谱源流序》,清道光四年(1824)《汝南周氏宗谱》,平卿村民存。 。村民也流传说周姓始祖三道公放羊至此,羊儿因水草丰美不喜走,遂在今周氏香火堂位置搭建棚屋而居。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至今仍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依托。2000年前后,村民陆续由传统水稻种植改种茶叶,适宜的海拔、气温、光照、雨水(水质)等使平卿出产的高山云雾茶质量优质,价格高出平原地区近一倍。高附加值的茶叶种植令村民收入大幅增长,生活条件逐步改善。
在支护图中可以看到指示喷混凝土厚度的斜线,喷混凝土的厚度随着Q值的减小和洞室尺度的增大而增加。线与线之间的位置,可以进行插值确定。如果有变形发生,比如有高应力引起,加筋混凝土应当应用于所有的支护类别。
平卿村民不仅依赖自然,也在与自然生态共存共生过程中,改造着自然,形成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风水。据当地人介绍,平卿村整体呈“燕窝形”,为锁住风水,护佑子孙,先祖们察地形观风貌,种下了百余棵风水树,环绕着整个村庄。同时他们还建构出实用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公共活动和交往对话的物理场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祖先信仰为核心的香火堂、祠堂和多神信仰的各色庙宇;二是村头巷尾、小卖部、学校等休闲玩耍之地。围绕着神圣性公共空间,人们通过“会社+头首”组织制度,有规律地开展节日仪式、人生礼仪等公共活动,形成了三种文化边界,分别强化房支、家族和村落的文化认同,编织出一张村落运行的意义之网,体现着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
(一)强调血缘认同的香火堂
香火堂(民间又称家庙、祖堂、祖庙等),是安放一个家族或房支香火之处③ 学者王媛在松阳大东坝镇石仓研究发现,香火堂就是家族支系的小支祠,一般来说,香火堂建造较早,规模更大的祠堂是家族达到一定实力才能建造,时间靠后。但平卿香火堂、祠堂的建筑年代无文献可考,村民也语焉不详,所以暂时难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且从平卿香火堂和祠堂在神灵祭祀、活动内容和功能分配上的差异(详见正文)也难以作出确定判断。所以,关于香火堂的性质判定留作以后讨论。参见王媛: 《浙南山区明代普通民居发现的意义——以松阳石仓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平卿村共有周、张、李三姓,周姓入住最早,后有张姓迁来,现在两姓人口数相当,另有几户李姓。村内共有四座香火堂,其中周氏大香火堂一座、张氏香火堂三座。
香火堂一般来说始于家庭初立或者房支初分香火之时,由一家或者几个家庭合力建造① 参见王媛: 《“香火堂”:血缘的依附与独立——石仓阙盛宗家族1710-1850年的住屋史》,《史林》2011年第5期。 ,现在所见有厅堂式和独栋式两种,前者直接将香火神主牌位安放于住宅厅堂的神龛内。在浙西南山区,通常几户或者一个大家庭共居于两层楼建筑内,楼下中间为厅屋,两边是东西厢房。人们建房必在厅堂上方设立神龛,祭祀本家直系先祖,乞求祖宗庇护。香火堂就摆设于厅堂中间,隔开前后进。张氏二房香火堂即位于一座大屋的厅堂内,大房香火堂则位于张家长房大屋的阁楼上。更常见的是三代以内去世直系亲属的遗像被悬挂于堂屋正对门的木板墙上方,以示怀念。独立的香火堂分两种情况:一是经济条件改善后,家户迁出,整个老屋则作为香火堂,并常以香火堂名之② 松阳石仓的香火堂还可能因子孙无嗣、老宅转卖他人而改奉他人。参见王媛: 《“香火堂”:血缘的依附与独立——石仓阙盛宗家族1710-1850年的住屋史》,《史林》2011年第5期。 。二是初建造即为单独的香火堂。周氏香火堂与紧邻的张氏小房(三房)香火堂皆为独立建造。前者较大,独门独院,建造面积相当于一幢大屋,后者则类似于单独出来的大屋厅堂,无门无院。
在平卿村,除香火堂、祠堂外还建有几座庙宇和神位:社殿(当地又称山庙、社庙)、四相公庙、三太子庙、主人神树以及仙岩寺望祭台等。这些庙宇皆位于村落周围,构成平卿村与相邻村落的神圣性文化边界。其中,社庙是最主要的信仰空间,形制最为完整。该庙坐北朝南,供奉主神平水禹王(又称社公、土地公),以及陈林李氏三夫人、温袁唐葛周元帅、法青、法通、田三郎、田三嫂等地方神。大禹为松阳、遂昌等地普遍存在的土地神,四相公庙和三太子庙仅为水泥制作的简易神龛,三太子被当地人视作调皮的神灵,若有不敬会带来麻烦,比如弄丢一头牛或者几头猪,村民因惧怕而生敬意。主人树信仰与山民从事林业生产有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上山砍树是人们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人们用以祈求平安。望祭台因仙岩寺而来,仙岩寺位于今遂昌境内,为松阳与遂昌交界处多个村庄信仰中心,因寺内供奉有平卿先祖敬献的神佛,所以村民设一块长方形条石(当地人称为石桌)而祭。
香火堂严格来说为供奉祖先神主之处,但民间信仰常体现出基于地域实用性需求的杂糅性和多样性。同属松阳县境,石仓阙氏家族香火堂主要供奉各房支祖先,小竹溪村香火堂供奉观音大士等,平卿香火堂则供奉主神徐侯大王,并千里眼、顺风耳、招财童子、进宝郎君、陈林李氏三位夫人以及三十九大夫等神灵。徐侯大王传说原籍龙泉,常为民谋利,被视为民间保护神。陈林李三位夫人中以陈十四夫人(又称临水夫人)最有名,为江浙一带民间广泛信仰的女性神。据了解,村内两姓家族祖先神主旧时皆安放于各自的祠堂内,后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香火堂内一直供奉地方神,未安放过神主牌。
事实上,同处一个生存空间的周、张两个家族之间合作和冲突并存,既保持着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又通过民间信仰体系创造出调和边界冲突的合作机制,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组织稳定和文化认同,共同划定与外部的边界。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是教育思维模式的颠覆性变革,“关键是将教与学的重心真正地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上来,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中心的转变”[1]。把这一理念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既涉及到教师的教学习惯,又与学生的学习习惯有关。就教学本身的目的而言,这一理念也应运用于指导成人教育。我们这里提出的“以学习者为中心”,不仅强调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中心,更要明确指出,教育教学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学生为中心,真正地把提高学生的核心能力作为成人教育的中心任务。
在平卿村,香火堂是红白喜事的举办地。村民去世后,便会被抬至香火堂处理善后。④ 平卿村周、张、李三姓各有差别,红白喜事、逢年过节摆祭等,周家入周家香火堂,张姓各房支入各自香火堂。李姓在自家办理。 参加红白喜事的一般限于本家族或房支族人、亲友和近邻。同时这里也是添丁分饼之所。添丁分饼是村内独特风俗,大年初一早饭毕,当年内所有添男丁的家户要按照家族内男丁(18-59岁的男子)人数分饼,每人四个,昭示着一个家族的人丁兴旺。这一习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各家族祠堂内举行,1980年代随着家族文化再度兴起,周氏家族恢复了香火堂分饼,张氏家族未恢复。另外,逢春节或者村里做福① 关于做福仪式的介绍,详见下文。 ,香火堂是必须祭拜之地。大年三十晚上,本家族或房支男人们准备好鸡、肉、豆腐、糕、饭等至香火堂摆祭,凌晨方可收回祭品,天蒙蒙亮时,人们燃放鞭炮接年神迎新年。按照村里人的说法,香火堂“人人有份”,家族内每家每户都可以分得一份祖先荣耀,也有责任进行管理和维护,平卿香火堂每年在家族或者房支中按户轮值确定头首二人,负责香火堂修缮、逢年过节看护打扫,尤其是春节期间,初一到初五香火堂每天均有祭祀和燃放鞭炮者,需每日查看。
(二)融合血缘与地缘的祠堂
祠堂作为家族成员祭祖、家族管理和公共议事的文化空间,在村落建筑中居于重要地位,一般多位于聚落中轴线或较为开阔的空间内,有的依山傍水,有的地势相对较高,彰显出庄重威严。族人通过祭祀先祖及其他神灵,维持着家族稳定,体现着敬宗报本之意。正如明代程昌编撰的《窦山公家议》中所说,“追远报本,莫重于祠。予宗有合族之祠,予家有合户之祠,有书院之祠,有墓下之祠。前人报本之意,至矣!尽矣!思报本之义而祀事谨焉”② 周绍泉、赵亚光校注: 《窦山公家议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19页。 。
平卿村共有周氏、张氏两座宗祠,皆靠近村口位置。周氏祠堂居前“坐丙向壬”③ 《平卿周氏善庆祠堂志》,清道光四年(1824)《汝南周氏宗谱》,平卿村民存。 ,紧邻风水口(如今入村公路旁),张氏宗祠靠后,但地势稍高。周氏祠堂建立时间较早,并曾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大修,《平卿周氏善庆祠堂志》记载道,“第历有年,风雨难除,渐次倾圯,见者凄然,是以嘉庆二十四年岁在己卯仲秋之初,裔孙士怡……等追孝前人,肯堂肯构,经营大厅三间,外复造客轩两廊并工绘戏台……又觉式廓频增至于腊月之望计所入以颁胙”④ 《平卿周氏善庆祠堂志》,清道光四年(1824)《汝南周氏宗谱》,平卿村民存。 。这次修缮参与者甚多,廊宇扩建,且做专志记录,可见家族当时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张氏家族后起,祠堂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⑤ 清咸丰乙卯年(1855)重修《张氏宗谱》,卷一议约,平卿村民存。 ,也曾多次重修。两座祠堂形制基本相同。
见面的地点定在律师事务所。6 3岁的谢修平比实际年龄更显老,这是乡下人共同的特征。身体还壮实,看不出有什么不便的地方。苏楠握了握他的手,说她代表委托人,谢谢他出来作证。
综上所述,平卿村以祖先、社神等神灵为载体构建出的信仰体系,形塑了房支、家族和不同姓氏之间的边界,体现着不同圈层的认同,有交叉有互斥,有冲突有调和,通过公共的仪式活动稀释个体的矛盾纠纷,最终实现村落整体运行。关于文化边界问题,早在20世纪初,西方学界就开始了讨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莫斯认为,“文明元素是超越疆界的,它们有的是通过某些特定中心自身的扩张力量而得到传播,有的是作为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结果而得到扩散”② (法)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载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纳丹·施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罗杨审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7页。 ,“文明的区域是指被视为此文明标志性特征的普遍现象得以完全传播的地理范围(几乎此领域的所有社会)……也指由共享构成这一文明遗产的象征、实践和产物的社会所占据的全部地”③ (法)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载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著《论技术、技艺与文明》,纳丹·施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罗杨审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64页。 。民俗学和人类学者也常用“祭祀圈”“信仰圈”等来讨论边界问题,考察地域社会中人群互动以及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的关系④ 参见周大鸣: 《祭祀圈理论与思考——关于中国乡村研究范式的讨论》(《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以及《民间信仰与村落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讨论》(《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 。平卿村的个案说明,村落社会中并非一个同质化的信仰圈层,而是根据人们的实际需求存在着多样化的圈、层,调和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祖先神灵之间的关系,维持着村落共同体的稳定运行。
首先,祖先信仰是村落认同的重要元素。在平卿村,祠堂的象征意义并未因公共活动减少而消失,每年村里有新出生的男丁,家人仍要到祠堂贴红对联、挂红灯笼。几乎每家每户仍要到祠堂燃香摆祭。同时,香火堂的作用凸显,并在某种程度上较祠堂的地位有所上升。我们知道,在家族组织比较完备的历史时期,祠堂承担着较多的社会功能,香火堂社会功能较少,地位较祠堂为弱,如清乾隆《绩溪县志》载:“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岁时伏腊,生忌荐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礼较严肃。春分、冬至,鸠宗合祭,盖报祖功、洽宗盟,有萃涣之义焉。宗祠立有宗法,旌别淑慝,凡乱宗、渎伦、奸恶事迹显著者,皆摈斥不许入祠。至小族,则有香火堂,无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③ (清)陈锡等修,赵继序等纂: 《绩溪县志》卷一《方舆志》,“风俗条”,收入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107册,《安徽府州县志》第7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2—363页。 ”由于家族组织1949年以后逐渐失去政治合法性,1980年代祠堂虽有重建,但各种公共活动大为减少,村民的大家族概念也逐渐淡化,相反以香火堂为中心的房支之间互动仍非常活跃。这与北方地区小亲族在乡村社会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不谋而合④ 董磊明: 《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50—55页。 。
祠堂活动除了促进家族内聚力以外,还构成族际边界。在平卿村,不论一年一度酬神祈福的立秋戏,还是上级部门送戏下乡,均设在周氏祠堂。这一传统因政府处理两姓家族纠纷而形成。据《汝南周氏宗谱》记载,清道光十七年“张周二姓为合乡邻省冗费事,原子午卯酉迎神赛,愿若各起灶炉,殊觉不睦费烦。今两姓酌定,历年赛戏还愿,周姓古祠演起,张姓接抬神明,赫赫威光以赛愿之先后而福报有厚薄哉。至于迎送仙圣戏箱、值奉香烟油烛一切社甲之事,以齿轮流,周而复始,不得推诿。如周姓轮不着甲头,张姓直办,若张姓轮不着甲头,周姓直办,不得争竞。如有分头接社,顽梗不驯,禀公律究,庶几乡党和睦,费用省约,岂不懿哉”④ 民国丁丑年(1937)《汝南周氏家谱》卷一山场,第32页左,平卿村民存。 。另外,1980年代恢复祠堂春节摆祭以后,张氏族人根据老人回忆重建了比较规整的祭祀规则。正月初五收祭品时,村内每个家户抓阄购买第二年需备置的祭品。到第二年摆祭时,购买的祭品清单誊写在红纸上公布。祭品摆放也很有规则。但周氏族人则无正式公布的祭品清单,祭品摆放也缺乏规则,为张氏族人所诟病。
(三)凝聚村落认同的村庙
有学者发现,相较于祠堂,香火堂一般供奉相对较近的直系祖先,体现着中国人强烈的延续香火观念,是将开基祖的血缘和地缘融合起来,“把一座大宅的空间范围变成了他(开基祖)世代专属的领地”,强调“祖先与后代之间更加紧密和直接的联系”③ 王媛: 《“香火堂”:血缘的依附与独立——石仓阙盛宗家族1710-1850年的住屋史》,《史林》2011年第5期。 。香火堂划定了家族或房支的活动边界,圈里是互动最多的小亲族,圈外是其他房支或者家族,这集中体现在人生礼仪和岁时节日上。
香火堂的建造与家族或者房支的综合实力直接相关,拿平卿村来说,张氏家族虽为后起,但是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经济实力相对丰厚,分出的房支也建有香火堂,且张姓族人搬迁至本县其他村庄建村后也建造了香火堂,比如位于平卿村下方的孟坑村为张氏小房迁出所建,村内张姓繁衍五六代300余人,共享一座香火堂。周姓虽也分为几个房支,但只有一座香火堂,在张氏族人看来,周姓重“耕”轻“读”,未出过仕宦,家族实力不够。
就目前所见,社神是村内地位最高的神,保佑全村人的健康平安和生产生活安定,构成一种超越宗族的宗教情感① 王逍: 《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围绕着社神信仰,村民依照农业生产节令开展带有时间秩序感的祭拜仪式② 祭拜活动若按照规模大小,可以分为家庭祭拜和社区祭拜,本文仅论公共性社区祭拜活动。 ,通过节日仪式等公共活动来突破家族和房支以及不同姓氏之间的界限,促进村庄和谐。
做福是祈求农业生产顺利的一种岁时节令活动,在浙西南一带普遍存在,只是形态上略有差异③ 参见王逍: 《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第二章第三节相关论述。 。平卿做福传统上由村内年满18岁的四位男丁(称头首)主持,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恢复后主持者皆已在33岁左右。做福一年共八次,分为四个“大福日”和四个“小福日”。“大福日”依次为“上山福”“下山福”“立秋福”和“八月福”,分别对应谷雨、小满、立秋和白露节气。“小福日”在四个大福日前后。大小福日活动稍有不同。大福日里杀黑猪一头,并按照全村18至59岁男丁人数筹米,把米全部煮熟,猪头、尾和骨头等煮熟,猪身不煮,然后按照参加做福男丁人数均分生肉、熟肉和米饭。小福日只是头首们准备肉饭祭拜社神。另外,农历六月初一,头首们还是按照男丁数筹米包粽子,并按照男丁人数均分到户。每一个大福日,头首们在分肉之前,都要祭拜社神、四相公、三太子等神灵,“下山福”要在社庙门口望祭位于平卿下方东北殿的胡公大帝④ 东北殿位于平卿村下方,大岭根村上方,为平卿村附近“七社八坦”(即七个社八个村,分别是大岭根、大岭里、孟坑、坳后、平卿等八个村)的总庙,里面供奉着胡公大帝、关公、陈十四夫人等。1960年代被毁,现存部分残迹。至今仍有附近村民去拜祭,且七个村庄每逢春节舞龙,一定要先到东北殿拜祭方可出龙。 ,“上山福”和“八月福”时村民分肉之后,还要先到香火堂祭祖。做福仪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均分食物,不论姓氏、家族、力量强弱,以男丁为标准,一视同仁,这就突破了村落内部既有的边界,体现出强烈的公平、公正、和谐、协作精神。仪式不仅对于个体成年和成长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也对人际互动调整、促进村落认同和维护村落秩序起到了推动作用① 关于做福仪式详细内容,参见拙文《乡土文化传统在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探讨》,《社会治理》2018年第5期。 。
除了做福,春节祭拜和舞龙也体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并凝聚着促进村落认同。平卿村春节祭拜一般从初一持续到初五,每天村民们早上要先从家里出发拿着香纸鞭炮等至香火堂祭拜,然后至祠堂,最后经主人树和社庙,晚饭前后又手持香纸从社庙经祠堂至香火堂一路拜祭回来,遵循着严格的神圣性秩序。春节之间的板凳龙隔几年举办一次,全村人齐动手,扎龙舞龙,不仅在村内舞,还要走到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既是村落实力的展现,也在强化村落认同。
请戏、修路等也是促进村民合作的公共活动。平卿村请戏有两种:一种是每年由社庙头首来负责的木偶祈福戏,每年秋收前后,酬神娱人。另一种是前述所提到的子午卯酉年做农戏。每年立秋时节,社庙头首、周氏和张氏祠堂头首共计12人头首联合起来,邀请村外的婺剧、越剧团们演出。公路没通之前,头首们要组织人力肩挑背扛地把戏班子请到村里,这就需要村民之间的合作协调。另外,每年白露时节,社庙头首们要组织全村男丁修缮村内以及与邻村之间的山道,大家出钱出力,齐心协力。这一习俗至今仍存,只不过由于公路的开通,古道的作用下降,人们也可以使用除草剂等灭草,参加人数规模不及以前。
研究表明,宗族并非一个单纯的血缘组织,宗族以祖先信仰凝聚族人,以祠堂族长形成族权,以族田公产构成经济基础,并在与官府的互动中实现宗族乡约化(组织化),与乡约、保甲等一起构成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基本组织形式⑥ 常建华: 《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科大卫将明清宗族的兴盛归因于其在商业贸易发展背景下不同程度地通过各种经济行为来控制资产,出租族田、房屋及借贷等,使得宗族具有经济运作能力,成为结合血缘关系和一定现代化商业运作机制的制度⑦ [英]科大卫: 《作为公司的宗族——中国商业发展中的庇护关系与法律》,收入其《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一书,周琳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 。平卿村地处偏远山区,家族势力虽难与平原大族相媲美,但两个家族在1949年之前皆有族田,且开展一定的经济活动,用于家族祭祀、分红、教育等公共事务。从现存民国七年(1918)张氏祠堂账簿来看,年内收入分为四部分:一是族内家户逢添丁、添妻、添儿孙媳妇,需向族内缴纳一定的银钱;二是房租、田租、卖砖和卖木板的收入;三是舞龙灯红包;四是贷款利息。支出包括购买祭祖用品(春节祭礼、清明祭扫坟墓、冬至祭礼),购买春节用品(摆祭红烛、口香饼等),立秋做戏(当地称“立秋戏”),修缮祠堂,龙灯红包① 松阳、遂昌等地春节时各村多有舞龙灯习俗,龙灯除了在本村舞以外,还要到周围村庄里舞,一般会到该村的香火堂、祠堂和部分人家。所到之处,接待者均要支付红包以作谢礼。所以,当地人称,舞龙灯尽管费时费力,但是不亏,常有一定收入。 ,松阳和遂昌完粮(税),经理② 从调研来看,经理一职责任重大,一般为族内辈分高,为人贤德又有能力的人担任,负责宗族集体经济、纠纷调解和族人教育等。 工钱以及年内可能发生的其他祠堂公事,诸如修谱、处理族际纠纷的诉讼费等。并且,因为收租和添丁收入较多,自民国十三年(1924)开始给男女丁数分丁银③ 张氏家族民国七年(1918)祠堂账簿,平卿村民存。 。
三、村落公共文化空间特征与功能
萧放通过对宋明以来城市节日民俗的分析,认为城市节日的最大特征是公共性,公众参与性与公共性的仪式表演是城市文化空间的本质特征。城市节日文化具有宗教性、娱乐性与消费性的历史文化特性① 萧放: 《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宋明以来都市节日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相比之下,作为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经济的产物,平卿村传统文化空间体现出带有一定边界的公共性,以及强烈的神圣性、实用性和规范性,并内生出一定的现代性。
动物的生存法则里有食物链,在我看来,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连锁企业就是一条经济链。管理者想要公司强大,就不可能一直只经营这一家公司止步不前,这样很容易被后来者所超越。连锁企业跨越了地域障碍,假如你的公司在上海,你想把自己的业务拓展到北京,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连锁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北京设立子公司,招纳技术和管理人才,只要选定子公司的经理,让他打理子公司的业务,就能够使自己的公司在北京有分店。同样的道理,只要你妥善经营,你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自己的连锁店。
民间文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开展被赋予了政治合法性② 高丙中: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第5期。 ,但在实际操作中,信仰层面常常是被遮蔽的内容,但平卿村的个案分析恰恰说明乡村社区以祠堂、香火堂和社庙为主体搭建的神圣空间体系是村落运行的精神轴心。
中药材是我国药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种,其类型非常多,不同药材的形状与质量也大相径庭,因此,对不同类型中药材进行鉴定成为现今中医临床工作中非常关键的一项工作。中药材鉴定工作中常用的方法有很多,传统经验鉴定法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鉴定方法[1]。本次研究主要选取一些常见中药材,分别利用现代鉴定法、传统经验鉴定法进行鉴定,对比二者鉴定的准确率,现报告如下。
[11]Nation,P.(2001a).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可以看出,祠堂年中活动包括了岁时祭祀、文化活动、经济生产和往来等,承担着一个家族的信仰支撑、社会服务、经济保障等多项功能。这些活动由祠堂总经理主持,另有四位头首配合。总经理辈分高于头首,具有较高的声望和权威,头首由族内按照家户轮值,年龄较轻,张氏家族规定不低于15岁,周氏族人没有规定,两三岁的孩童也可以做头首,实际由父亲代理。1949年以后,家族组织受到冲击,祠堂田被收,周氏家族虽有族长,但只具有象征作用,张氏家族没有族长;两姓族谱从1940年代以后均未重修;文化大革命时期祠堂均遭破坏,祠堂内原存的祖先神主牌被毁,张氏祠堂原有的牌匾和纱灯等多被毁,1980年代祠堂相继重修。现在祠堂平时多关闭,仅遇修缮、立秋戏和春节摆祭和舞龙灯等活动时开放,祭祀活动一般只在春节时进行。
显而易见,教师以这样的方式渗透德育教育能够让学生懂得礼貌待人的重要性。同时,“小题大做”式地渗透德育也能够真正实现润物无声渗透德育。
其次,社庙信仰仍存在深厚群众基础。正如村民们所说,跟社庙相关的事,人心是最齐的。这既源于传统的力量,又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不稳定有关。在平卿,男孩出生后要在社庙上香,年满18岁要是社庙上丁,去世后也要报庙告神。在村民看来,只要是平卿人,不论在哪里都离不开社神的关照。自1990年代开始,因村内资源紧缺和传统农业生产限制,村民开始陆续出外打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逐渐搬出村庄,到邻近的古市镇居住,现在古市平卿村民约有200多人。但由于人们对家乡茶叶经济的依赖,每逢春茶采摘季节,很多人要返回村庄采茶或者往返于古市与平卿村之间加工和销售茶叶。这样平卿村就被拉扯成两个主要的地理空间——“山上的平卿村”和“古市镇平卿村民聚居地”,相应的社神信仰在城镇化时期,已经随着人口的迁徙,成为超越村落界限的民俗认同。另外,当前茶叶生产和外出打工等带来的生产生活的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强化了人们对平安的祈求,激发了信仰的活力。2018年社庙重修时,村民们出钱出力,扩大了庙宇规模,合资敬奉了香炉和纸炉① 学者鞠熙对北京门头沟千军台古幡会的研究发现,幡会作为国家级非遗已经成为当地一度空心村落形成新的价值认同的重要促进因素(参见鞠熙: 《实践:民俗学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关键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而本人对于平卿村社神信仰的观察也注意到,人们关于社神的灵验传说仍在增加,信仰仍然规范着人们的世俗行为。比如,该村某村民在女儿高考前连续烧了三天香,后来女儿考中重点大学。另一个曾阻挠社庙重修的村民重病之后持续昏迷,情况危机,直到社庙烧香许愿之后,症状才有所缓解。 。
空间是叙事的物质载体,是承载村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情感依托,村落的公共空间与村民个体成长和集体生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实用性。马树华通过对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提出,文化空间也是一种创造力量,它“形塑了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参与了城市的成长”② 马树华: 《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化空间与日常生活》,《东方论坛》2009年第4期。 ,乡村文化空间亦然。以一个平卿男人为例,出生后要到祠堂和社庙注册,18岁要到社庙上丁,并有资格担任做福头首,开始参与村落公共事务,在此前后还可能会担任祠堂或者香火堂头首,参与本家族或房支事务,结婚以后要带领妻子进入祠堂和社庙拜祭,生子以后要到祠堂或者香火堂分饼,每年遇到做福、过年、舞龙、修路等都有责任参加。去世在香火堂接受祭奠,神主入祠堂。虽然现在随着人口的外流以及人们仪式的改变,个体与传统空间之间的连接在减弱,但是对于生活在村庄中的人们来说,祠堂的祭祀和戏曲娱乐、社庙的信仰功能以及香火堂的心灵依托等仍不可缺少。
3)完善城镇排水系统,努力提高污水处理程度。部分城区污水处理厂及大部分乡镇污水处理厂存在不连续运行的现象,应切实加强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工作,完善城镇排水系统,实现水的健康循环。
针对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构成及其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研究,杜赞奇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框架③ [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黄宗智也从对中国法律的研究中提出“第三领域”的说法,强调的是地方社会通过宗族、社区调解解决纠纷的非正司法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④ [美]黄宗智: 《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14—135页。 。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乡村治理体系中存在的自治元素和结构。从公共空间视角出发,相对稳定的空间架构表明平卿村的基层治理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正如国家有中央、省、县、乡、村等层级,村民们通过神圣原则建构起香火堂、祠堂、社庙、村落群中心庙(东北殿)等层级体系,对日常生活构成约束和规范,这是通过宗族、乡社形成的一套自治传统,这种“乡里自治的自我服务方式,是中国传统社会基层自我管理的方式之一”⑤ 萧放: 《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逢年过节严格的祭祀顺序,内化成对家庭、家族、村落不同的认同和归属感。同时神圣规则也成为造成冲突或解决危机的依据。比如2017年底,在民俗学者介入下,平卿村委试图利用社庙重修,结合村落传统建立起现代社团组织,激活村庄活力。但是由于实际操作中没有严格遵循召开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的机制,更由于违背了社庙只有在损坏或者村庄发生危机才能重修的神圣原则,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村庄矛盾。
而nA级的基准电流源设计大多是基于Oguey电流源结构[10]。文献[11]提出了一种能够优化Oguey电流源的温度特性的新结构,将温度系数降到了177 ppm/℃,输出电流为92 nA,消耗功耗670 nW;文献[12]也是基于Oguey电流源结构,作者在电路中应用运算放大器将电源抑制比提高到了85 dB,产生46 nA的基准电流消耗的功耗约500 nW。文献[13]采用正负温度系数的两路电流相互叠加的方法得到了温度系数为20 ppm/℃的14 nA基准电流,消耗功耗140 nW。
中国乡村并非具有严格边界的固化的村落共同体,“国家在场”一直对村庄产生影响,当前的村庄正在内生出一定的现代性,有利于国家力量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空间的公共活动为公众集体参与、具有共同建立规则、展开公共仪式表演。以社庙做福来说,全村人按照男丁人数筹米,然后均分肉米,买肉的钱均摊。修路、舞龙等也都是全体参与。这种集体参与、集体受益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正符合当代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平、公正、共享精神。而且,文化大革命以前,村里还有两个龙会以及社会(春社和秋社),社会为家庭条件较好的十来户联合起来办,社会有社田,用于春秋两次祭祀社神。龙会是过年时舞龙的组织,舞龙会有一定的资金收入,结余的部分用于社庙祭祀等。过年时还有夫人会,组织到东北殿陈十四处祭祀。这些会社是明清时期广泛存在于民间的一种信仰和利益共同体,其以宗教信仰为情感连接,以经济互动为主要目的,在基层社会发挥着一定作用。在松阳石仓,会社组织相对于宗族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其存在土地买卖等市场交易行为,但会社内部成员比较平等,达到经济互助① 章毅、冉婷婷: 《公共性的寻求:清代石仓契约中的会社组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当前的乡村人们又在召唤公共性,赵孟营的研究则认为,当前农村建设缺乏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行政强制也缺乏法理基础,他认为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方利益的介入是解决农村基层动员的有效途径② 赵孟营: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层动员》,《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而毛巧晖对北京怀柔区琉璃庙镇杨树底下村敛巧饭活动的研究发现,当地村民将原来只存在于女性做巧饭的习俗扩大化,塑造成全村共筹米、共爨同食的公共活动③ 毛巧晖: 《遗产化与民俗节日之转型:基于“2017‘敛巧饭’民俗风情节”的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段友文、卫才华对晋南乡社的研究也发现,当代社组织通过料理红白事和村落公益事业等在现代经济建设中日益彰显出社会化的活力④ 段友文、卫才华: 《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组织研究——以晋南万荣通化村、荣河村和河津西王村为例》,《民俗研究》2005年第4期。 。所以,传统会社组织在当代仍有现代性转化的意义。
结语
随着国家从乡村的逐步退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平卿村与全国很多乡村一样,空心化加剧,村民异质化增强,村民之间互动关系减弱,公共文化活动减少,基层组织活力减退,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村民与村庄产生了疏离和陌生化,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整合作用弱化。
如今,多数村民只有在春茶时节返回村庄短暂居住,但大家都忙于采茶卖茶,互动并不多。春节时,人们会再次回到村里过年,互动相对较多,比如走亲戚、商店打牌、祠堂和香火堂拜祭等,但是居留时间比春茶时节还要短暂,有的只居住几天,有的只在大年初一祠堂祭拜之后随即出村。因为对于习惯了城镇生活的人们来说,村里的居住条件较差,祠堂、社庙等神圣空间以及小卖部、村头巷尾等公共场所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聚会和娱乐需求,这都给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入提供了空间。以浙江省积极推进的文化礼堂建设为例,提出将“文化”与“礼堂”相结合的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构想,整合农村文化资源,打造集道德教化、礼仪文明、文体娱乐和知识技能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① 参见丁峰、李勇华: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长白学刊》2018年第4期;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化礼堂操作手册》(第六版),2017年发布,内部资料。 。这种现代性的改造方式“弥合了国家与民俗、大传统与小传统、名与实之间的张力与差异”② 靳浩辉: 《农村社会治理视阈下祠堂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嵌与重构——以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为例》,《理论月刊》2018年第7期。 ,但国家力量的介入又在消解固祖先信仰和地方认同,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思路有加速了传统文化空间的世俗化,加速了村落文化记忆的丧失③ 林敏霞、颜玲云: 《从宗祠到文化礼堂: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功能研究》,《民族论坛》2016年第12期。 。所以,公共文化空间如何实现国家、社会与“第三领域”的良好互动,将国家治理政策与乡村自治传统更好融合,并实现传统与现代生活接轨等仍有待讨论。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A Case Study of Pingqing Village in Southwest Zhejiang Province
HE Shao-ya
(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Management/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Abstract: Taking Pingqing Village in west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ffirms its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discusses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It is held that 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mainly based on the product of the village endogenous power, i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villagers' production, living and spiritual need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sanctity, practicability, standardization and modernity, it on the one hand conforms to the need of nation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n the other con flicts with public cultural progress.
Key words: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identity;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ublic cultural progres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9)03-0117-12
收稿日期: 2019-04-01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18@ZH011)子课题“百村社会治理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贺少雅,女,河北深州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民俗学、节庆礼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乡社会治理等研究。
责任编辑:董德英
标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论文; 空间建构论文; 文化功能论文; 基层社会治理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论文; 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