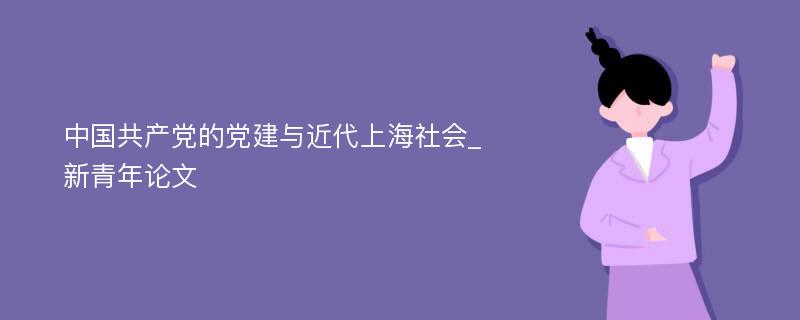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近代论文,中共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前的1921年7月,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缔造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上海,此一事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本土根源。作为当时中国的首位城市,上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中共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以及中华社会应对这种侵入而激发出来的各种因素,上海的现代性得以发展。综合了本土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来自西方的外部影响力。这种现代性汇集和包容各类新生事物,集中体现在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新社会阶级(如工人阶级)的萌生与成长,从而为历史注入新的动力。由此产生的变革观念,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建党史研究向来是史家旨趣之所在。①中共何以在上海创立,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在上海建党?本文拟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
一、上海成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国际化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对外开埠。1845年,由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共同商定的《土地章程》出台。②同年,英国人以此为法理依据设立英租界;1848年美租界建立,英、美租界于1863年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也于1849年宣告建立。两大租界在19世纪下半叶不断越界筑路、渗透扩张,完善各自的市政管理机构。这样,上海出现“一城三市(政府)”的格局,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口岸城市。开埠前的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仅第12位,人口20来万。而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人口已达200多万,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上海城市受外来经济、社会及文化冲击,最明显反映是租界的存在——它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得到二等公民待遇,又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是中西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
作为中国近代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对整个近代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外国势力掌控下,上海迅速由一座江南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从1865-1936年间,上海占全国对外贸易的45%-65%。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有46%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上海,36%集中在东北地区,剩下的18%散布在中国其他地区。中国的关内出口总额中,上海占46%,天津和广州分别占15%和7%。④
伴随外资进入,外国的企业、商业观念和商业模式亦不断输入,催生上海产生一系列新的现代产业部门。首先是制造业的发展。开埠不久,即有外资在上海兴办近代工业。1843-1859年间,共18家外资工厂开办。1860年以后发展迅速,到1864年达38家,门类扩展到10个。⑤英商1860年初率先创建拥有100部西式丝织机的怡和纺丝局,紧接着法、美、意等国商人也纷纷在沪投资设厂。⑥到1913年,外资企业在上海的总资本额达6346万元,比1894年的975万元增长5.5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0.34%。⑦
中国人自办的现代企业也逐渐发端。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创办,此后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纷纷设立。效仿外资企业的民族工业也蓬勃发展。据统计,1895-1911年上海新建的民族工业企业为112家,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资本额2799.1万元,占全国的近30%。⑧尤其是一战期间,外国资本势力因世界大战严重受挫,上海资产阶级乘机迅速崛起。以新开设工厂为例,辛亥革命当年上海新开设工厂只有9家,1914年新增26家,到1921年新增工厂数达90家。⑨以机器工业为例,甲午战前,中外资本设立的船舶与机器修造工厂共有18家,到1920年止,仅民族资本所设工厂就高达114家。⑩以华人资本于1914-1922年创办的纱厂而言,上海有16家,天津有6家,此外,无锡、武汉各2家,芜湖、济南等各1家,这期间在上海开办的纱厂,超过全国的一半。(11)
伴随现代制造业在上海的产生,新的产业类别也层出迭现。早期出现船舶修造业、印刷业等多个新型的工业门类。1895年后,又涌现11个新的工业门类。1911-1922年,上海近代工业门类从22个增加到32个。(12)这说明现代产业部门正在向纵深发展,上海日渐摆脱单纯的以港兴市的贸易城市格局,进入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产业也在外资引导下在上海逐渐产生、发展、壮大。到民国初期,上海已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以外资银行为例,到1922年,上海共有外资银行(包括中外合资银行)30余家。(13)据1936年资料,在沪外资银行达20余家,其主营业务有国外汇兑、存款、放款、抵押放款、套汇、现货与期货金银交易、外汇与黄金套利交易、经营债券本息、投机买卖等。(14)同时,中国本土的钱庄与银行业也因借鉴外国银行的管理经验而有所发展。1911年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尚不足1亿元,而到1921年,存款总额已近5亿元。(15)在金融业带动下,证券市场亦渐趋发达。1914年12月,《证券交易所法》经北洋政府颁布实施。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翌年5月,原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6)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格局变化巨大。1912年,华洋分界的城墙被拆除,代之以环城马路。1914年,分隔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洋泾浜被填平。嗣后,随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西扩,都市面积急剧膨胀。到1921年,上海城区面积比开埠时扩大10倍。公共交通也有了重大进步。1914年,无轨电车被引入,“该项电车式样系本埠电车公司工程师所特制”,“可容有二十六人之多”,且“虽最狭之街道,该车亦能通行无碍,且该车停顿之处并无一定,乘客上下可随地为之”。(17)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公园、电影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应运而生。不断涌入的移民,以及包括新社会群体在内的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着这些开放的都市新景观。在都市空间内,逐渐产生一套现代生活方式。城市上层以及中产阶级的衣着、语言和社会行为也随西风起舞,展现一个与传统乡村截然不同的城市世界。百货公司、影戏院、小家庭以及新创的社会阶级专用名词等等,均反映出1920年代一种混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面向。与亮光闪闪的现代生活相伴随的是阴暗,诸如贫富分化、社会混乱等等。
总之,上海经济之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让中国人见识一种崭新的经济样式,打开了一扇新的机遇之窗。另一方面,上海的不均衡发展,凸显这一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由此而产生一个现代与传统分立的二元格局。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是一个把各个区域编织进等级化、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延续状态被打破,不彻底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现代性便成型了,从而构筑了畸变的现代性叙述。
二、新阶层应运而生
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上海人口亦快速增长。据统计,1910-1915年间,上海新增人口达71.7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4万人。此后直到1920年代初,每年仍新增10万人左右。(18)到1920年,上海人口已达229万,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中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的人口为77.5万,尚不足上海一半。(19)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导致近代上海的社会结构出现分化,新的城市社会阶级逐渐崛起。
近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勃兴,造就包括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家集团。上海的工业资本家群体是由工业化本身所孕育的。譬如,上海纱厂承办人的出身背景与其他城市(如天津)有着显著差别。(20)上海的资本家更多来自绅商家庭。其中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曾接受新式教育的高学历人士,比如留洋的穆藕初,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以及金融界的陈光甫等,因此具有较强烈的民间色彩。而天津等地的资本家,往往官僚家庭背景浓重,导致天津的工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官僚主导型特点。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上海新兴企业家,年富力强且大多出洋留过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发展状况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因而也更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21)他们与城市其他精英阶层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较有活力的社会力量,这既指他们在捍卫自己权益方面,也指他们在对待较大公共议题方面。资产阶级本身依附性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1920年,全国工人发展到194.60万人,其中上海有近51.38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强。(22)可以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23)处在城市底层的产业工人超负荷地工作着,收入却非常微薄。1917年圣约翰大学学生对曹家渡工人聚居区的社会调查显示:“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而当地“常见男工谋10元、8元,女子做丝厂每月所入亦如此”,结论是此类工人家庭“非有一人以上在外谋生不可,仅靠男工赚钱的家庭,在曹家渡甚罕”。(24)1920年《星期评论》指出,“上海工厂劳动者的工银,平均差不多只得二角五分至三角,月收不过九十角。至少要假定有两天缺工的损失,月收就只有八十四角”。(25)作为无产者,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性。
1919年6月5日,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工人阶级立即开始行动,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首日罢工工人就达2万之多。(26)除邮政工人声明“各地救国团体相互联系”之需要而不罢工外,全市纱厂、钢铁、运输、印刷、土木、油漆行业和马车夫等都参加了罢工,涉及行业之广、行动之快前所未有。他们公开宣称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27)罢工目的是为了“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28)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29)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不下11万人,连同店员、手工业工人7万多人,共18万人。紧接着就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开始“三罢”斗争。“五四”运动的中心由此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达到高潮。上海产业工人阶级意识的萌生,为中国早已复杂万端的社会环境增添新的内容。
当时的有识之士被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诚如陈独秀在沪所言:“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此意为缺乏具有近代意识的市民——引者注)。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30)陈独秀已意识到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他在上海寻找到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
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则是上海又一大群体。据统计,在1910年代的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31)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绍兴的邵力子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的施存统,因内讧而失望,与俞秀松来到上海,原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成为《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32)而五四运动后的北京,政治气氛压抑,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出狱后南迁上海,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上海。诚如鲁迅所言:“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33)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加上文化事业发达,中外联系广泛,自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
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却面临传统士人与现代职业人双重认同的困惑乃至不安。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将其称作“在社会上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34)由于处于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制中,人们对技术性专家的需求极其有限,“无所依附的人”处境尴尬,许多读书人内心有着不小的压力。这些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工具理性的统治,放弃文化理想,将自己的智识降低到技术层面。受过教育且“无所依附”的读书人,努力在变动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在此情势下,读书人中最活跃的一部分脱出旧轨,成为最有热情推动社会变革的行动者。而恰在此时,革命为“无所依附”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项历史使命,契合了知识分子对角色的追求。
三、上海建党的文化起源:思想、主义、新文化
上海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通过上海传入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亦藉此应运而生。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业务欣欣向荣,1911-1920年间,总计出书2657种,其中占首位的社会科学类为801种。(35)而1912-1926年间,上海出版的图书占全国的70%。(36)福州路从清末起已发展成为著名的“文化街”,聚集着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37)报纸、杂志、书籍如雨后春笋,销量颇大。这些现代文化传媒组织构成芮哲非所指称的“印刷资本主义”。(38)文化的“工业化”初步奠定上海的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地位,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制造出人数可观的阅读公众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新型文化事业依循市场原则来运作。譬如,《新青年》的发行机构即是民办的群益书社。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从1916年9月1日2卷1号起,该刊改名为《新青年》。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指明建设新文化的基石:科学与人权(民主)。他号召青年们须有世界视野,声言:“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共国于危亡者,共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共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39)《新青年》杂志旗帜鲜明地宣扬求知识于世界,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一种普遍趋向,即自觉将中国之命运与世界大势联系在一起,探寻中国问题的解决。对五四一代而言,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40)依托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舆论市场的优势地位,《新青年》将思想启蒙的理念逐渐传布神州大地。譬如,《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号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省市的76家书局。(41)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最初每期1000份增加到16000份。(42)可以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新青年》等杂志的引领下,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
此后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文化精英汇聚上海。新的思想和智识风气往往首先在这里得以译介和流布。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的上海,由西洋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就首次介绍了马克思的主张,广学会的李提摩太誉之为“安民新学”,“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43)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个报道了这个重要消息,宣布“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临时政府已推翻,美克齐美党占据都城,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并指出“主谋者为里林(列宁)”。(44)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彷徨无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与视野,知识人从中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45)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阶段,西方被热切地当成一个绝对的、不容质疑、唯一可能的行为标准来接受。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的屠杀,使西洋文明顿失光泽。以至陈独秀失望地声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46)而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则被当作“一面寻找未来方向的镜子”。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日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一个以人类和谐为特征的世界性的共产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前后最早介绍宣传诸种社会主义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其中,除《新青年》编辑部一度在北京(发行部则在上海)外,其余三种都是上海的刊物。据曹聚仁回忆,“邵力子主编《觉悟》态度最为积极,和《新青年》桴鼓相应,最为青年学生所爱好。那时上海《民国日报》受了政府干涉,邮寄颇成问题,就靠日本邮局在转送,居然一纸风行。经常替《觉悟》写稿的,如陈望道、刘大白、沈定一、杨贤江、张闻天、瞿秋白,后来都是社会革命的激进者”,“张东荪主持上海《时事新报》,其副刊《学灯》创刊于1918年3月间,研究学术,介绍新知。也是《新青年》的同路人”。(47)而后人评价“宣传新文化运动最早,和最有力的报纸,是上海《时事新报》”。(48)五四时期的其他名刊如《太平洋》(上海)、《每周评论》(北京)、《国民》(北京)、《新潮》(北京)、《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国》(上海)、《解放与改造》(上海)、《科学》(上海)等,也多半位于上海。俄共代表费奥多尔报告上海之行时亦赞誉,“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49)
五四时期,《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觉悟》等上海报刊,与一度在京的《新青年》南北呼应,可称之为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近代上海发达的媒介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经由《新青年》和五四时期其他刊物(大多在上海)传入中国。而《新青年》杂志复归上海,既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转向,亦意味着上海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引介和传播的主要中心。诚如美国学者格里德尔所评价的,《新青年》“一旦置于陈独秀的独断控制之下,它就成了中国第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从《新青年》的历史和几个早期撰稿人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到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大部分历史”。(50)通过上海的印刷出版网络,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地在各地传播开来,由此培育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创建一个全国性政党。1919年9月,李汉俊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提出在中国建立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党”的设想。(51)另有作者指出,“希望各国的国际社会党,及我们中国的国际社会党,先将这国际的强权推倒,这就是我主张国际革命的意思”。(52)1920年2月中旬,在李大钊等人帮助下,陈独秀离京出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53)此次迁移意义重大,“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54)
来到上海的陈独秀,“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55)他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小沙渡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5月,陈独秀推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专刊,专论工人问题。蔡和森对此盛赞道:“中国第一个五一节,宣传很大,《新青年》发行数目多达一万份,所以当时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已普遍全国了。”(56)英国驻沪领事馆的情报显示,“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工商友谊会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它们似乎或多或少处于陈独秀的影响之下”。(57)另一份文件亦指出,“陈独秀在上海工商友谊会的组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担任该会出版的《上海伙友》周刊的编辑。他还同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有联系。由于其布尔什维克倾向,如果陈成功地确立起对这些劳工组织的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就非常可能会给当局制造很大麻烦”。(58)松沪护军使更致电北洋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59)显然,陈独秀在上海卓有成效地组织劳工运动,使得英国当局认定他已是享有很高声望、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者,并对上海的劳工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同时,陈独秀着手重组《新青年》杂志,以陈望道、李汉俊等倾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为基础,组成编辑《新青年》的上海同人群体。(60)在这一过程中,他与主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主编《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等人建立密切联系,(61)并以之为基础成立同人沙龙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频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经验。他的寓所兼《新青年》编辑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也成了革命者的中心场所。胡适在晚年曾自述,“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62)通过这样一个人际网络的构建,以《新青年》杂志(包括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刊物)为中心,陈独秀周围初步形成一个倾心马克思主义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群体,从而为共产党的建立奠定成员基础。
而苏俄与共产国际亦开始在中国大力开展工作。1919年3月,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职责为“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交换情报工作,进行口头和书面宣传”等。6月18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加蓬考虑到在东方开展革命运动的需要,提议在区委下“设一个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主要任务是“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在给俄共(布)中央的报告中也称“他们打算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联系”。(63)
随后,苏俄方面数次向中国派遣使者,试图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接触。这些使者先后有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64)共产国际频繁遣使来华,既反映莫斯科对东方问题的重视,亦表明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行动上不一致、不协调和互不通气。(65)在这种背景下,1920年4月,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所派遣维经斯基一行5人到中国,同中国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同时考察可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1920年5月,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在上海正式展开建党大业。随后经陈独秀介绍,维经斯基和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一起商谈苏俄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与会者提议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革命联盟。诚如维经斯基在该年6月的信函中所述:“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66)显然,维经斯基的到来,给予了已初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外部帮助和支持,使建党大业成为现实。维经斯基利用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沪成功展开工作,包括“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67)
1920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应当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只有5名成员: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杨明斋、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沈泽民、袁振英、林伯渠、李中、周佛海等后来参入。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进知识分子,这反映了上海都市的开放性与移民性特点。对于此事之经过,俞秀松在自传中写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68)作为早期成员之一,俞在自传中确认中共发起组与先前由陈独秀所构建的、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群聚的上海知识分子同人网络的渊源与关系。正如共产国际代表利金所指出,“上海小组具有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69)李达认为,“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70)马林也高度肯定上海发起组的中心地位:“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71)在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为了在中、朝、日等东亚国家直接进行实际活动,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东亚书记处。该处所设“中国科”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72)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便是通过《星期评论》杂志社,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5月中旬,陈望道携翻译完稿的《共产党宣言》,应邀到上海任《星期评论》社编辑。6月28日,陈望道委托俞秀松把《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交给陈独秀。是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
上海发起组充分意识到大众传媒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20年8月,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广工人运动经验的《劳动界》周刊。嗣后,《新青年》杂志脱离群益书社,另成立新青年社,从8卷1号开始独立发行,仍由陈独秀主编,主要讨论社会主义问题。陈独秀在该期《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已示与胡适等北京同人异趣,是《新青年》上海编辑部思想转向的一个信号。自此,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刊物的《新青年》便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中央机关刊物。随后,上海发起组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马克思主义常识,推动建党工作。张国焘日后总结道,“上海小组办了劳动周刊(4000份35期),伙友(2000份),共产党(6期)”。(73)依托于上海发达的文化网络以及便捷的交通条件,《新青年》、《劳动界》等影响日众,迅速传遍神州大地。譬如,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间,地处内陆的长沙文化书社共计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分别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和《新青年》(2000本)。在其读者中,“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74)维经斯基亦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75)共产主义印刷品的广泛传播,使得租界当局倍感焦虑,英国情报文件就显示,“根据法租界巡捕房提供的信息,法租界巡捕于(1921年)2月1日搜查了公馆马路283号的一家书房,查获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书籍据信是在法租界内印刷的,包括《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阶级争斗》、《工团主义》等”。(76)
为团结、教育、培养进步青年,上海发起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该组织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不久,上海发起组于9月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共第一所干部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干部。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首次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3班……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77)在杨明斋校长的领导下,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在此学习过。(78)
11月,陈独秀已明确提出中国劳动者要“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夺来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79)他与战友们正式制定中共第一个章程草案——《中国共产党宣言》,正文分三个部分:(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3)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明确昭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存的资本制度”,“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80)
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是名符其实的“临时中央”,“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81)陈独秀对建党工作颇为重视,指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82)他亲自负责武汉、广州、长沙和济南的建党工作。1920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到沪,陈独秀与他谈论了马克思主义,8月即请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包惠僧忆及武汉小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建立的,并强调“我们同上海的关系较为频繁,密切”。(83)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建立组织。各地小组以上海为中心,保持着密切联系。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在一大召开前,“计算(全国)六个小组共有57同志”。而且,“一次大会以前经费是自筹的,上海新青年社原来有2000元,营业赢利计4000元,汉俊设法筹措一些,湖南等处,每月由中央津贴二三十元。(广东不在内)北京因与俄同志接近,募了一些捐款。一次大会以后,中央则由国际津贴”。(84)可见,此时共产党之经费主要为自筹,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上海发起组开办的新青年社创收所得。陈独秀亦颇为重视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他多次表示:“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85)“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86)
在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成立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构想已在上海发起组中逐渐酝酿。陈独秀与其他同志讨论了建立全国党组织及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事宜。(87)共产国际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4月的报告中陈述:“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88)5月,上海发起组委托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请他回沪或将上海发起组迁往广州,但陈独秀认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政治环境不利,地理位置也不适合,不便于各地联系,因此仍属意上海。6月初,上海发起组与刚抵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马林商谈后,认为建党的条件业已成熟,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海发起组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以后,发函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请每地派两位代表赴上海开会。(89)
需指出的是,具有宽松、自由社会环境的法租界成为“一大”召开的合宜地点。由于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能在此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法租界客观上给革命者提供了方便。1917-1921年间,孙中山等人将法租界(新区)作为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国民党党部即设在环龙路44号。孙中山的活动得到法租界当局的默许和保护,他寓所门口甚至有巡捕站岗。(90)巡捕头目黄金荣曾长期关照孙中山。无独有偶,1919年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在法租界长期开展活动。此外,法租界还有5000名俄侨,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无形中起到掩护作用。更重要的是,上海发起组成员拥有或使用的房产多在法租界。(91)美国学者叶文心(Wen-hsin Yeh)也认为,直到1922年底,中共上海组织的活动几乎都在法租界运作。尽管巡捕房始终未曾放松对共产党的监控,但与上海租界外中国其他地区严酷的政治环境相比,法租界仍然是个较为开放、自由、讲究法治理念、能“提供政治避难”的区域。1921年10月陈独秀曾被法租界拘捕,最后判决亦不过是罚洋100元,驱逐出法租界了事即是明证。这也是上海为何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地的原因之一。(92)
1921年7月23日,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五、结语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正在经历早期工业化的国际大都会,变革的伟力横扫陈旧的传统模式,新的社会阶级重整了传统社群。在工业化引导下,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在上海等沿海城市产生。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亦开始在这些工业城市呈现。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聚集着最广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工业社会的诸种矛盾与紧张,也以阶级斗争的形式直接在上海表现出来。正如列宁所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93)随着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阶级斗争形势亦表现得愈加尖锐,这样一种阶级状况,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社会基础。
与之同时,依托于日趋发达的都市文明和大众社会,上海出现了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新型文化人逐渐在学校、出版、工商企业等现代组织中安身立命,他们自成一类,是新兴的社会力量。20世纪初的新式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们,把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现代性现象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毫无保留地把意见贡献给这些广阔得令人惊讶的问题领域。透过这样一个舆论场域,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自上海发端席卷全国,形成一个风起云涌的局面。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思想文化上的准备。
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受到这一缕现代之光的照耀,进而在中国问题中看到世界命运的影子。对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愿景主要是社会方面的,与整个国家对社会变革的渴望相一致,能够与更广泛的社会集团建立联系,并为他们提供一种全新意义的团结。马克思主义借由与历史必然性的主张产生关联,对人类历史提出普遍性的解释,对社会的公正结构提出一种规范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西方的先进思想推崇备至,进而认定共产主义是未来的历史潮流。这种集体认知的背后,揭示出一个新观念的浮现——一个超越国家、种族乃至阶级的“理想社会”,逐渐出现在人们的意识层面,越来越清晰。
作为全国文化与舆论中心,上海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中心。正如共产国际代表所指出的,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主要中心”,“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94)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上海的诸多报刊与《新青年》相呼应,不遗余力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托于上海发达的印刷资本主义网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本得以译介,广泛影响为数庞大的阅读公众,进而造成一种进步的公共舆论。周有光1923年进入圣约翰大学求学时,也从图书馆借阅了英文版《资本论》,尽管他还一知半解。(95)而次年郭沫若由日返沪,从东方图书馆借来英文版《资本论》,并制定5年翻译计划。(96)此外,随着城市间交通的改良,近代上海凭借其沿江沿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中国最大经济中心的辐射力,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其他城市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条件。
上海都市的国际性特征也为建党大业提供良好条件。凭借着近代中国面积最大、历史最久的两个租界所提供的政治庇护以及宽松、自由的舆论环境,先进知识分子可以从事革命宣传。再加上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这种四海一家的世界性特征方便共产国际使者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共商建党伟业。而且,上海地处长江口,通讯和交通便捷,工商金融服务设施优良,这些都为共产国际遣使来华联络乃至为中共建党实施经济资助,提供了便利条件。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初期的有声有色的活动(中央长期在上海活动),也构成上海历史的华彩乐章。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集聚和出发,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改造中国的时代剧。
注释:
①国内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田子渝:《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等。国外研究成果,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Alexander Pantsov,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9-1927,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 Wen-hsin Yeh,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等。
②相关内容及土地章程的历史沿革可参见Land Regulations and Bye-laws for the Foreign Settlement of Shanghai,1845-1930,U1-1-105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页。
④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⑤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⑥徐新吾、黄汉民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⑦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4页。
⑧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7页。
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第63页。
⑩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4页。
(11)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第414—415页。
(12)龚骏:《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0—32页。
(13)李一翔:《外资银行与近代上海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
(14)《旧中国外商银行调查资料》,《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
(15)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3年,第298页。
(16)张一凡、潘文安:《财政金融大词典》,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第53页。
(17)《记上海之无轨电车》,《协和报》1914年第4卷第36期。
(18)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91页。
(19)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20)1920年上海有华商纱厂19家,有资料可查的负责人18人,其中,除1人出身背景不明外,出身实业界的2人,官宦之家的3人,商人家庭的8人,另4人具有多重身份。(参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第414—415页)
(21)以上海总商会董事会成员的年龄结构为例,1920年改组前后,有明显的差异,改组后,50岁以下的会董30名,在董事会占85.3%。(参见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社会志(初稿)》上册,第419页)
(22)《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6号。事实上,这一时期上海新生的工人阶级构成相当复杂,按照英国学者史密斯的研究,上海产业工人被地缘、性别、秘密社会体系等诸多因素划分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参见Stephen Anthony Smith,Like Cattle and Horses: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1895-1927,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24)《曹家渡调查》,《约翰年刊》1921年。
(25)戴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星期评论》1920年5月劳动纪念号。
(26)《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申报》1919年6月6日,第11版。
(27)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9页。
(28)《字林西报》1919年6月12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9页。
(29)《求新机器厂工人全体罢工》,《新闻报》1919年6月7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党的创立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30)《陈独秀过沪之谈片》,《申报》1920年2月23日,第14版。
(31)Mary Louise Ninde Gamewell,The Gateway to China:Pictures of Shanghai(1916),Taibei:Cheng Wen Publishing Co.,1972,pp 106-107.
(32)参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8页。
(33)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年,第132页。
(34)参见Karl Mannheim,Louis Wirth,Bryan S.Turner,Ideology and Utop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1991,p.127.
(35)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75页。
(36)“国史馆”中华民国史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文化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166页。
(37)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p.17.
(38)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安德森说,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生为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随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美国学者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则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对近代上海文化传媒工业的分析中,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资本主义(如“文化街”)对塑造近代中国思想和精神形式有巨大作用。(参见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
(39)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陈独秀本人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青年》杂志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即法文“青年”的意思。
(40)蔡元培:《国民杂志序》,《国民》1919年第1卷第1期。
(41)《各埠代派处》,《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2号。
(42)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43)《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万国公报》1899年第123期。
(44)《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民国日报》(上海)1917年11月10日,第1版。
(45)《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8页。
(46)陈独秀:《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1919年第22号。
(47)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65-166页。
(48)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9年,第324页。
(49)《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50)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51)李汉俊:《世界思潮之方向——我有几句话要说》,《民国日报》(上海)副刊《觉悟》1919年9月7日。
(52)若愚:《国际的革命》,《每周评论》1919年第10号。
(53)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事略》,《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5月24日,第3版。
(54)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2日),《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胡适(他明确将《新青年》群体归于自由主义)在此信中对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与转向唏嘘不已,认为“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沈雁冰则认为,早在陈独秀出走上海前,他已与北大的自由派教授意见分歧,以至“陈独秀一怒之下,说《新青年》本来是他创办的,他要带到上海去”。(参见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可见,陈独秀与北大的自由派友人分道扬镳后,作为一个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寻找革命同人,并着手将新文化运动转化为走向行动的社会革命。
(55)《辩诉状》(1933年),《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5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页。
(57)Dispatch no.35 dated 4th February 1921 from the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at Shanghai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forwarding the Shanghai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ing 31st December 1920,FO 228/3291.
(58)Dossier 120C Shanghai Intelligence Bureau Minutes of Meeting,October 1920,FO 228/3214.
(59)《淞沪护军使向北洋政府发电指责陈独秀组织机器工会》,《申报》1920年10月16日,第6版。此处的“淞沪护军使”一职在政府公报中明确为“松沪护军使”。
(60)有关《新青年》上海同人之政治倾向,参见《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之二,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8页;《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2页;《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四),《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7页。
(61)关于陈独秀与戴季陶、李汉俊等上海文化人的交往,参见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第87、168—169页。荷兰学者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亦认为,以陈独秀为中心聚起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深感兴趣的上海知识分子小圈子,后来的上海发起组即从这个知识分子小群体中产生。(参见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p.59)
(62)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1、211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53—154页。
(64)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74—76页。
(65)参见《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6页。据近年来俄国学者的考证,围绕着对华工作的主导权,苏俄内部各机构有着复杂的权力斗争。参见M.Persits,"A New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1920-1922," Far Eastern Affairs,1997,no 5.
(66)《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页。
(67)《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页。
(68)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俞秀松纪念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230—231页。关于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及其性质,仍有较大的争议。参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田子渝:《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李丹阳、刘建一:《“革命局”辨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69)《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8页。
(70)《李达自传(节录)》,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页。
(71)《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
(72)《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9页。
(73)K.B.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百年潮》2002年第2期。
(74)《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3—293页。
(75)《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页。
(76)Dispatch no.236 dated 6th July 1921 from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Peking to Lord Curzon at the Foreign Office in London,forwarding the Shanghai Intelligence Report for the three months ending 31st March 1921,FO 371/6634,1921:F2200/309/10.此处被查抄的书房即新青年社。沈雁冰曾证实被查抄的地点还有承印《新青年》的又新印刷所。(参见吴少京主编:《亲历者忆——建党风云》,第183页)关于新青年社所印书籍,毛泽东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参见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周恩来对此亦有所回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页)
(77)《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9月28日,第1版。新渔阳里6号是当时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活动地点,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6月的工部局警务日报中,有大量关于该处活动的情报记载。
(78)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79)陈独秀:《短言》,《共产党》创刊号,1920年11月。
(8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81)《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摘录)》(192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86页。
(82)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6页。
(83)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9页。
(84)张国焘曾提及“在1920(年)冬汉俊曾写了一本小册卖给商务书馆,得了300元”。(参见K.B.舍维廖夫提供:《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手稿本),《百年潮》2002年第2期)此可旁证陈望道、李达等人回忆上海发起组的经费主要依靠上海的党员卖文维持这一说法确系实情。另外,新青年社原有(股本)资金2000元的来源颇可深究。譬如,1920年7月2日,正在为新青年社独立发行而招股的陈独秀致函高一涵,言辞恳切地称“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参见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可见新青年社之原始股本金中,有一半系由招外股所得,尚余1000元股款之来源因史料缺乏存疑。
(8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页。
(86)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9页。
(8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88)《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9页。
(89)包惠僧回忆,路费由马林提供,“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焘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77页。
(90)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4页。
(91)如《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位于老渔阳里2号,《星期评论》编辑部就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家里;“一大”会场亦是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望志路106、108号,即今兴业路76、78号),此楼1920年夏建成,属贝勒路树德里的一部分(今黄陂南路374弄),楼南当时尚存农田,环境颇为幽僻。
(92)Wen-hsin Yeh,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p.212-214.
(9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页。
(94)《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5页。
(95)周有光:《拾贝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0页。
(96)王训昭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标签:新青年论文; 陈独秀论文; 1920年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上海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觉悟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时事新报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