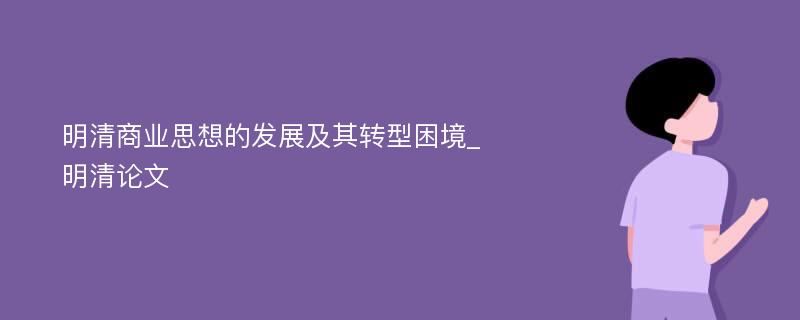
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困境论文,思想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2-0148-7
明清时期被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人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并且出于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中后期开始有商书大量刊行,反映出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为数众多的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及经营形态,也能够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①。由于大量的商书公开刊行,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这是全社会商业思想的重要体现。本文拟从明清大量公开刊行的商业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商业思想的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一、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经济活动,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协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们所难以回避的问题。
明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农从商”及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这在明清文集、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多有体现。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时期的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重信义,守然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从明代天启年间程春宇的《士商类要》,崇祯年间李晋德的《客商一览醒迷》,到清乾隆时期吴中孚的《商贾便览》,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及至清末杨树棠抄本《杂货便览》,这些训诫在明清两代一直相沿传承。吴中孚的《商贾便览·工商切要》开篇强调,“习商贾者,其仁、义、礼、智、信,皆当教之焉,则及成自然生财有道矣。苟不教焉,而又纵之其性,必改其心,则不可问矣。虽能生财,断无从道而来,君子不足尚也”。
在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富从勤得,贫系懒招”;“和能处世,俭能治家”;“为士者勤则事业成,为农者勤则衣食足,为工者勤则手艺精,为商者勤则财利富”②等训诫多有出现。
由于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士商类要》特书《戒嫖西江月》以示警;《客商一览醒迷》强调要“锐志坚持,必不堕于勾引”③。《商贾便览·工商切要》更是直接指出,“赌嫖二事,好者无不败家倾本,甚至丧命……二害非小,当自知之”。直至民国年间的《生意经络》④,仍反复训诫:“最可恨者,嫖、赌、吃、着四字。若犯了一字,即穷之根,贫之源也。看旁人穿好衣,吃好食,切不可照他行事。近来鸦片一项,尤生意中所最忌,万万不可沾染。切记切记。”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为杰士”、“倚官势,官解则倾”⑤的训诫,告诫人们,不要附炎趋势,攀援权势,屏夺人财。同时,在经营理念上,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反复强调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以义行商。程春宇的《士商类要》第四卷,辟有《人伦三教》、《起居格言》、《省心法言》、《养心穷理》、《居官莅政》等近30小节,阐述“立身持己”、“和睦宗族”、“孝顺父母”、“敬兄爱弟”、“君子知恩”、“勤劝读书”等事理。乾隆年间王秉元《贸易须知》的《序》中强调:“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诺,习勤劳,尚节俭。此四者,士农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⑥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业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意义深远。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互利和秩序等人际关系原则的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这也不利于商业长久的顺利发展。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传统社会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与经营理念,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思想遗产的局限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职业道德、经商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明清商书所倡导的经营思想方面,大多将视点着重在经商能力的培养和个人品德的要求上,强调要谨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而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各类商书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业思想,对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繁荣商业的理论创新意义便受到很大的局限⑦。
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⑧。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传统商业思想转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了。
在思想观念上,长期以来,儒家思想重义轻利的观念,加上“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的官方意识形态,无形束缚着工商业思想的发展。虽然明清时期经济思想较之前代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有丘浚、顾炎武等人反对官营工商、反对盐茶专卖、主张扩大国内商品流通、主张自由贸易,冯应京、黄宗羲等人提出“工商皆本”,颜、李学派强调重视工商业、反对轻视商人等思想的出现,但这些思想大多是零星散见于其私人著作、文集或奏疏里,并没有带来经济思想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大多仍局限于“本”“末”之争的思维框架内,对社会经济发展所涉及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则很少涉及。因此,就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其商业思想的发展水平比较而言,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像被奉为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平天下”统治要术的《大学衍义补》,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思想界也没能产生主导作用。相反,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准则仍然是“重农轻商”,一如《大清会典》所明确记载的,“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若为常经,由来已久”⑨。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西欧国家,自15世纪到17世纪中叶,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手工业逐渐扩大,商业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出现了代表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重商主义,并成为这一时期欧洲经济思想的主流,还一度成为当时欧洲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像英国,也正是在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成为当时生产的主要形式,对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引发工业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⑩。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专著。在英国,有威廉·配第的《赋税论》(11)、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12)、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3)、休谟的《休谟经济论文选》(14);在法国,则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的《法国详情》(15)、重农学派的代表作魁奈的《经济表》(16)、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等等,及至英国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9)、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20)的出版,标志着古典经济学发展至顶峰(21)。
这些经济学专著对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予以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及技术性讨论,内容涉及赋税、货币流通、地租、分工、交换、工资、外贸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像威廉·配第活动和著述的年代,正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他的著作大都是直接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写的,讨论了诸如公共经费的各种项目及增加的原因、人民不愿负担赋税的原因、货币流通、征税方法、地租、租金和利息的性质、货币价值的提高与贬低、国内消费税等一系列英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经济问题,着重研究和解决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财政税收制度以适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为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出谋划策(22)。诺思的《贸易论》则超越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国内外贸易的政策,竭力主张经济自由,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及至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的理论,则为李嘉图所继承和发展,并在马克思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改造,发展成为科学的完整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不仅内容日趋丰富、成孰,而且在不同程度上都为当时的执政者所重视,直接影响了当时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这一切是同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界所望尘莫及的。
明中叶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发展,并成为江南地区市镇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因,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提供了商业思想发展的相应土壤,但我们看到,事实并未如愿。即使是生活于当时全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江浙地区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尽管已自由发展工商业,并为商人的利益而辩护,但他们也仍然未摆脱传统的本末观的束缚,可以说,传统官方“士农工商”、“重本抑末”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已成为人们观念更新的最终桎梏。这便是明清商人所面临的“知识遗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思想上难以超越,商人们的经营理念自然也无法超越传统商业思想的藩篱。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商人们的谋利手段而言,许多商人往往不是通过创新和冒险,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以增加商品附加值,而较多地是注重从现有利润总量中占取更大的份额。对此,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的分析一针见血,“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以为理性状态大不相同。……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的可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23)。
这种“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的心态,以争得“政策性优惠”方能操持胜券的现实,成为明清经济转型时期商人们“二次创业”的重要桎梏。许多商人在凭自己的勤劳精明发家致富后,他们大多并不热衷于考虑怎样去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规模,以期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是将较多的财力花费于官场奉应,捐纳功名,“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只能进行各种方式的政治投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商人们也就难以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最终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不可避免地削减了其自身的发展潜力与动力。明清时期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盛隆一时的徽晋商帮中的诸多富商,往往藉此形式财运亨通,富甲天下。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粮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后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以票号而执金融界牛耳。但当时局变迁,当经济的发展需要其更多的技术因素及先进的理论意识时,他们便无法胜任其角色变化,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三、制度缺陷的制约
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其中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官场欺诈的诫惧与痛恨。从明代万历年间余象斗《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程春宇《士商类要》、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附悲商歌》,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感叹“宿水餐风疲岁月,争长竞短苦心肠”(24)的旅途奔波与“披星步峻”的辛苦,反映出当时经商环境的艰难。
如果说客观上的经营环境令商人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商业思想的发展。纵观中国古代,历朝政府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较之前代更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25),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业思想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的现象。《士商要览·买卖机关》有一重要训诫:“是官当敬,凡长宜尊”。并进一步解释:“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这是教育人们对官吏和年长者要尊敬,比较强调中国传统的长幼有序的伦理规范。但是,其对“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的训诫是值得关注的,它告诫人们,官吏们均属朝廷命官,尤其是得罪不起的,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商人们对官府及至官吏的一种敬畏心态。明清时期各部商书对“是官当敬”这一训诫的重视与关注(26),也说明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敬官、畏官及至崇官之倾向在明清商人中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由此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商人们始终走在权力与经济交织的钢丝绳上,他们既要忍受封建政府的政策性苛税,备受多种勒索;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必须与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虚与委蛇,不惜血本,捐官捐输,结交公卿权贵,及至附庸风雅,以期捕捉官方经济利益的动向,获取某些重要资源的“专利权”。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官商融合”,才能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27)。在某种程度上,明清商人所遭遇到的这些困境,实际上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制约。这种“国家强于社会”的政治结构特征,直接影响到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心理。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明清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也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就经济环境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从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专营专卖制度、均输平准法、政府统一铸币权等一系列政策开始,到宋代王安石的均输法、市易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之西欧封建社会各国要广泛全面得多。但是,“这种干预主要基于统治考虑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本身”。“无论是征税还是致力于公共工程,其主要目的是统治,其次则为促进或阻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8)。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同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构成绞杀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观念更新的双刃利剪,“成为阻止资本积累和独立的商人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一”(29)。就这样,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的“结构性制约”,又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藩篱(30)。因此,尽管明清时期市场经济取得很大发展,但经济上与政治上均有自主性的商业都市却未能出现,商人市民阶级也从未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政府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以官僚集团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生存、发展为目标。一种旧制度,虽然它已被证实为是无效率的,但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还是要力图加以维护。而一种新制度即使符合公众的利益、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但如果危及统治集团的存在和利益,就会被拒绝实施(31)。回顾中国古代历朝的政治经济改革,可以说,其中的诸多改革不乏有经济、政治上的新意之处,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主要缘由是改革触及了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最终当权者拒绝实施。另一方面,从先秦时代的商鞅变法,历经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到明朝的张居正,这些改革所呈现的演进轨迹是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步步加深,“从劳动力刚性管理到产业结构凝固化,从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运作,从农村金融的控制到税收改制的虚置”,莫不如此(32)。这些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其一,由于历次经济改革中政府的干预力度是累加的,要想维护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就意味着改革成本的递增,这在低效率的专制经济中越来越难以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扩大,使人们的自主经济理性得不到正常的培育(33)。因此,在中国古代,制度的调整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制度变迁总是滞后的,这一特征在社会面临转型时期的明清时代尤为明显。
在传统社会制度制约下,明清时代社会各阶层,无论是官绅、地主、商人以至一般平民百姓,他们的最终目标乃是买田置宅,或科举入宦。就商人而言,从事工商业,并不是他们最终的追求,而只是达到这些终极目标的一个有效手段而已。明清时期虽有大量的“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存在,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这“弃儒从贾”的背后,或者是家遭变故,无以为生的士子,而更多的则是那些科考无望的落拓儒生(34)。同时,在业已成名的徽晋商人、特别是徽商中,我们也看到了为数甚多的“亦贾亦儒”及至业贾致富后转而从儒的事例。在科举时代,习儒是为了入仕,徽商向儒说穿了也就是向官。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生员则更多。清代单是歙县一县(包括寄籍)取得科举功名者,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35)。仅一县即如此,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如此众多的人拼搏科场,如果没有一种浓厚的崇儒风气,是不可能形成这种局面的,徽商也因此而得名“儒商”。至此,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积淀终将构成明清商人发展的终极限制。
这对经济思想领域的直接影响便是中国古代不乏有价值的经济思想,但最终并没有转变为实际的经济体制。商业思想的发展也只能是在传统思想意识所允许的范围内,以微弱的态势而发展。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仍不可得。明清时期的商贾们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这正是商人在发财致富后热衷于捐官捐衔的根本原因。即使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式商人如张謇、周学熙也同样认为走经商谋利之路是不得已之举,多有“舍身喂虎”之感叹(36)。
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不在当时对于商人之态度与待遇”,“实在于观念上之漠视轻忽,既不重视,自难有积极鼓励,研求精进发展”。因此,“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37)。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明清商人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经营理念的商书,主要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并据此制订了各类规范法则,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38),商书的记载较之一些士人文集甚至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经营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令其陷入转型困境,最终也限制了明清时期的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39)。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也很能窥见端倪。
收稿日期:2009-09-18
注释:
①关于明清商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详见张海英《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以明清商书为中心》,载《复旦史学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4《立身持己》;(清)吴中孚:《商贾便览》卷1《江湖必读原书》。
③(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警世歌》。
④本文据民国十一年宏大善书局石印本。该书卷首序中谓此书为“句容王秉元先生原著”,但将其与乾隆五十一年汪淏所辑纂王秉元之手抄本《生意世事初阶》对照,内容大为丰富。本条“鸦片一项”即是新增。
⑤(明)李晋德:《客商一览醒迷·警世歌》。
⑥(清)王秉元:《贸易须知》卷1,光绪五年刊本《序》。
⑦详见张海英《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以明清商书为中心》,《复旦史学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日]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后江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页。
⑨光绪《大清会典》卷二三七。
⑩晏智杰主编:《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第三章《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1)[英]威廉·配第:《赋税论》,陈冬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2)[英]达德利·诺思:《贸易论》,吴衡康译,祥槐校,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英]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4)[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5)[法]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伍纯武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6)[法]魁奈:《经济表》,吴斐丹、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7)[法]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学史教研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18)[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9)[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20)[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1)详见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相关篇目介绍,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2)宋承先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2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24)(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2《陆路诗》。
(25)张海英:《明清时期“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6)此条训诫多被日后商书如《客商一览醒迷》、《商贾便览》等所注引,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清商人对此条训诫的重视。
(27)《士商类要》卷2《贸易赋》。
(28)曹沛霖:《政府与市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83页。
(29)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30)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31)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4页。
(32)(33)钟祥财:《中国古代能产生市场机制吗——兼与盛洪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34)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有许多的相关资料,黄山书社1985年版。
(35)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36)朱英:《浅谈近代中国商人的义利观》,《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7日。
(37)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38)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商人“自足”世界的呈现》,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9页。
(39)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