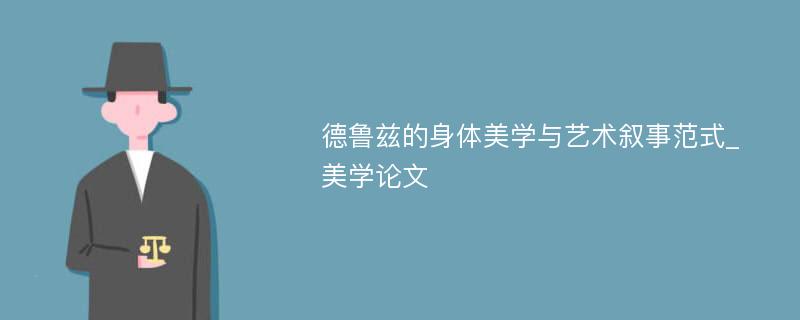
德勒兹身体美学与艺术叙事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美学论文,身体论文,德勒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5958/j.cnki.gdxbysb.2015.02.007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5)02-0040-06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涉及许多人文学科,我们在政治、精神分析、艺术等许多领域都能觅得德勒兹思想的踪迹。其中,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讨论文学和电影时,德勒兹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待开掘的叙事思想矿藏。作为一名哲学家,德勒兹当然不会“就事论事”,他在论述相关的叙事思想时,其实已经包含了对于生命本身的思考。例如,在对电影的探讨中,德勒兹将电影看作成一个“有生命的影像”[1],他从“感知”、“动情”、“行动”、“思考”等生命形态的角度来论述自己的电影哲学,从而使得电影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事实上,“身体”是德勒兹美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德勒兹在其相关的美学论述中分别讨论过“有机身体”、“无器官身体”、“充盈的身体”、“空洞的身体”等,而从这些不同的身体美学观出发实际上可以串联出一条德勒兹对于艺术的理解之线。本文便试图以德勒兹的身体美学为视角,结合他不同的身体观来阐发不同的艺术叙事范式。 一、“有机身体”与有机叙事 对德勒兹而言,理解事物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日常层面”与“纯粹层面”。而在德勒兹“皱褶”的思想下,这两个层面又始终缠绕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层面予以凸显。例如,德勒兹论述电影时所言说的“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就可以被看作为电影的“身体”在不同时段中显示出的不同生命状态。当它凸显“运动-影像”时,此时电影的“身体”构成与叙事法则都遵循日常行为的逻辑;而当它凸显“时间-影像”时,日常生活的逻辑被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本质的“感觉”之逻辑所取代。同样,我们的身体实际上也有两个层面,而当它处在“日常层面”状态时,就表现为“有机身体”。“有机身体”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身体,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由首、身、四肢、器官等部分组成,它们遵循着自然界有机化的法则,其特征通常表现为: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一定条件下部分受损后整体依旧能保持相对稳定的运作等。可见,自然界中有机体的特征显现出的是各个组成部分及身体器官之间的协调合作,其结果便是构建出一个完满的有机整体。 将叙事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整套有机叙事论的体系,将叙事与生命有机体进行了类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2]63而“完整”就意味着“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2]74如此,叙事本身俨然就成为了一个具有有机生命特征的“活物”。古罗马的贺拉斯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论,提出了“合式”的观念。《诗艺》开篇就讽刺与有机整体不相符的作品:“如果一个画家做了这样一幅画:上面是个美女的头像,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有覆盖着各种颜色的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看到这样一幅画,能不捧腹大笑吗?”[3]127他将亚氏的一元论改为质料、形式的二元论,要求叙事作品在内容上要“合理”,即要知道能写什么和该写什么,以体现古典主义的伦理观和理性原则;在形式上要“合式”,即作品要是一个有机整体,在题材的选择、性格的刻画等方面都要做到“得体”、“妥帖”、“恰到好处”及“尽善尽美”。文艺复兴时期卡斯特尔维屈洛提出了“时间整一”、“地点整一”与“情节整一”的三整一律。17世纪法国的高乃依的戏剧叙事理论同样强调有机整体的观念。时至今日,当谈论叙事时,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讲述一个故事,至于是谁在讲述、怎么讲述的问题都被故事世界本身的趣味性所代替。这个故事通常具有一个吸引人的开端、跌宕起伏的进程、惊心动魄的高潮以及一个可以让观众平复心境的结尾。这就是我们对传统叙事的理解。对于艺术叙事而言,以简·奥斯汀、巴尔扎克等为代表古典小说无疑是这类叙事的典型,而在当代它们化身为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消费性电影,继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这样一种叙事范式,其遵循的逻辑符合德勒兹所言的“感知-运动模式”。“感知-运动模式”是我们的身体在日常生活状态中展现出的一整套“刺激-反应”机制。此时,当我们遇到一个外在的刺激时,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各个器官之间的协调运作来回应这一刺激,使得事物被纳入到我们的有机身体可理解的范围中,继而促发情感、思考及其随之而来的行动。正是因为“感知-运动模式”模式的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才会显得合情合理、有条不紊,显示出一种有机化的特征。然而,在德勒兹看来,这样一种叙事范式构建出的有机整体,其实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主体的出场。德勒兹认为,有机体意味着我们被组织起来,将自己的身体连接起来,意味着我们成为能指和所指,成为解释者与被解释者,这样的一种主体化存在意味着我们被固定,成为表述的主体。有机整体论是对世界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组织,面对凌乱的世界,人类本能的认知逻辑把一切都组织起来,似乎一切发展都是按照首尾呼应的起、承、转、合来进行。申言之,有机叙事实际上深深打上了主体性哲学的特征。由于主体的确认同时意味着一个相应客体的存在,因此有机叙事从构成法则上来说总是遵循着二元对立的模式,正如格雷马斯所建立的二元对立矩阵那样。同时,主体的存在还意味着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成为可能。因此,有机叙事从目标实现上来说总是喜欢表达相对确定的观念,例如在好莱坞电影中,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美国民主的胜利这类主题作为美国文化输出策略不断冲击着我们的视听与世界观。此外,由于主体哲学体现出的是“感知-运动模式”,因此有机叙事从美学效果上来说主要表现的是我们的世俗生命,即使它呈现为科幻或魔幻题材,有机叙事深入的运作逻辑依旧是日常的、现世的。 二、“无器官身体”与非有机叙事 正如任何一个事物都至少拥有两个层面,当我们的身体摆脱了“日常层面”而凸显“纯粹层面”的状态之时,其便不再是“有机身体”,而是幻化为了“无器官身体”。“无器官身体”是德勒兹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勒兹《意义的逻辑》一书中,之后在德勒兹与加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与《千高原》中获得了进一步阐发,并被德勒兹用在《感觉的逻辑》一书中来阐释弗朗西斯·培根的现代绘画。 作为一名深刻的哲学家,德勒兹对身体的理解当然不会只停留在“有机身体”的层面。因为,在德勒兹看来,“有机身体”只是一种身体的表层状态,这种身体模式表达的只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而哲学思考显然应该比这种状态更为深入。因而,德勒兹从一种更为宏大的生命观出发,引用法国残酷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的观点认为,“身体是身体/它是独一的/而且不需要器官/身体永远也不是一个有机组织/有机组织是身体的敌人”,“有机组织不是生命,它囚禁了生命”。[4]47-48对德勒兹来说,我们的日常身体,即“有机身体”,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真正的纯粹身体的一种囚禁或者限制。换言之,正是在我们真正的身体,即“无器官身体”之上,“有机身体”才得以形成。德勒兹认为,在“无器官身体”之上,我们安睡,醒来,攻击,以及进行一切所谓的人类正常活动,“无器官身体”,“正是当你除掉一切之后仍然剩余的事物”,[5]201而那些事物,正是有机体组织好了的“幻想”,是意义和主体化妄想而出的整体。“有机身体”是一个在“无器官身体”上的层,它是对“无器官身体”的科层化;而“无器官身体”就是要打破这种科层化。换言之,打破相对确定性的束缚,而将身体的自由流动凸显出来。因而,“无器官身体”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器官的身体,它“不与器官相对立,而是与那种被称作有机体的器官的组织相对立”。[5]220因为,有机的主体束缚了我们真正的自由的生命。申言之,“无器官身体”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不确定性的方面来说,“没有器官的身体并不缺器官,它只是缺有机的组织,也就是说缺对器官的组织”;从确定性的方面来说,“没有器官的身体的定义并非是器官的缺乏,它并不仅仅因为器官不能确定而得到定义,说到底,他是通过确定的器官的暂时的、临时的在场而得到定义的”。[4]50-51这种临时的在场,意味着“无器官身体”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生成与变化之中。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是“无器官身体”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 “无器官身体”的概念可以推至叙事领域,成为叙事反叛传统有机论的哲学思想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无器官身体”的概念在德勒兹那里作为一种本体或纯粹层面的存在,并不是“一”和“多”的“分有”关系,毋宁说,它超出了“一”与“多”的对立,是融合性和多元性的。因此,它存在于各个领域,而各个领域的“无器官身体”遵循着同样的“秩序”。德勒兹认为除了有人的“无器官身体”,还存在货币的“无器官身体”、国家的“无器官身体”、军队的、工厂的、城市的、党的等等。如果说将叙事看作生命体在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那里还只是一种类比的话,那当我们说叙事的“无器官身体”时,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类比了,它就是叙事的事实。一方面,它反抗外在抽象的有机结构;另一方面,它在内部维持着各个元素的临时在场,以避免出现对某种被表现之物的图解行为。马克·伯恩塔等在《德勒兹与地理哲学》一书中指出,“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更加确切的解释其实就是“非有机组织论的身体”。[6]62-64因此,当叙事艺术幻化为“无器官身体”时就成为了一种非有机叙事。 事实上,对有机叙事的反叛一直都存在。例如,在浪漫主义时期,作家注重内在情感的表达,他们虽然仍认为艺术作品应该像自然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其内涵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新古典主义树立的金科玉律显然已经满足不了自由精灵无边的嬉戏。比如德国大文豪歌德一方面强调作品的有机整一,另一方面又强调作品自身的生命气韵。“怎么能说莫扎特构成他的乐曲《唐·璜》呢?哼,构成!仿佛这部乐曲像一块糕点饼干,用鸡蛋、面粉和糖掺合起来一搅就成了!它是一件精神创作,其中部分和整体都是从同一个熔炉中熔铸出来的,是由一种生命气息吹嘘过的。”[7]246同样,柯勒律治也一反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叙事单一性,开始强调其中的杂多与“不和”。他所推崇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这种杂多的典范,因为莎士比亚常把悲剧与喜剧、痛苦与欢乐、低俗与崇高、圣人和愚人等表面的不和谐浇铸为一个整体,从而拓展了表达的可能与界限。对传统有机整体观念的反思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德勒兹特别推崇一些所谓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叙事。以文学为例,德勒兹认为写作(叙事)就是迥异于中心和模仿的永未完成的异质性生成。迥异于中心,意味着写作(叙事)不应该成为“男人”,因为“男人”表现为一种对他人及他物的统治地位。相反,写作(叙事)应该成为女人,成为动物或者植物,成为分子,直到难以察觉的微小物质,因为“女人、动物或分子总有一种流逝的成分超越他们自身的形式化”。[8]2迥异于模仿,就是不要为过去的内容强加一种表达形式,不再去刻意寻求可辨识的部分或事先的存在,而是要找出一种邻近的,难以辨别的或未区分的区域,这就意味着异质性的生成。重要的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建立联系,哪怕是看起来最为异质的联系,于是就出现了卡夫卡笔下的不会游泳的游泳冠军和米肖(Michaux)所说的躺在床上的运动员。这样的一个异质性过程是永无完结的。“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8]1 在这样的一种叙事范式下,有机叙事的科层化势必要被逐一击破,以释放出身体最为深层的力量。如果说有机叙事是一种逻辑化的理性构成,非有机叙事就是一种体验式的感觉表现,它不再以一种严密或“完满”的整体的样貌出现,而是以一种散点式的强力而现身。贝克特的《莫洛伊》可以说就为我们展现出了有机与非有机之间的冲突。这部叙事作品由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构成:莫洛伊和莫朗。莫朗是一个体制中的人,隶属于社会、机构、历史话语等,而莫洛伊则是一个游荡在社会边缘的人物,他的无知和混乱让他从体制中逃逸,在莫朗和莫洛伊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中心与游牧之间的交锋与缠绕。非有机叙事反对任何确定的阐释,因此,在非有机叙事中我们不会发现协调运作的起、承、转、合,因为它不愿构成任何可能的整体性存在者。因果联系在这里也不再重要,因为因果观念“与其说适用于真实行为本身,不如说适用于叙事,适用于作为‘模仿’的故事—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术语对现实世界没有意义”。[9]32同样,它也不需要任何类型化或功能性的人物。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其中的妹妹形象本身就是“姐妹—侍女—妓女”等多重形象感觉般的交合,恒定的家庭三角关系的诠释只能是对这部小说的机械解读。人物在卡夫卡笔下可以变成甲虫,变成猿猴,变成鼹鼠,可以是任何“生成—动物”,但绝不是动物性与人的机械相加。“卡夫卡故意扼杀所有隐喻,所有象征,所有意指,也同样扼杀所有指称。变形是隐喻的反面。”[10]115总之,非有机叙事并不种植一棵根植于一处中心的叙事参天大树,而是创生“根茎”漫布的叙事千座高原。 三、有机、非有机、无机的叙事美学辨析 将现代叙事理解为对传统叙事的反叛,甚至认为现代叙事是“反叙事”,这样的理解显得过于极端。事实上,传统叙事和反传统叙事的关系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表面的对抗下是幽暗之中的冥冥微妙联系。对于传统与反传统,有机叙事与非有机叙事的关系,我们仍可以在德勒兹对“无器官身体”的探讨中获得启示。 德勒兹认为,“无器官身体”并不是对有机体的彻底放弃,如果只是将它抽象地与已经科层化的有机体相对立是不够的。“无器官身体”并没有先于有机体而存在,“它与有机体相邻,并不断地处于构成自身的过程中”。[5]277-278这就意味着,“无器官身体”是在对有机体的抗争中显示出自己的。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双向运动——有机的非有机化与非有机的有机化,而到达的临界点就是运动开始与结束的共在时刻。在此,非有机体与有机体之间的关系不禁让我们联系到中国哲学的“道”这一概念。事实上,德勒兹对此也有认识。“问题在于构建一个强度性的无器官的身体,道,一个内在性的场域,在其中,欲望无所缺乏……”[5]218我们知道,中国的“道”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其分化为“有”和“无”。“有”与“无”是相生相合、不可分割关系。中国道家脉络的美学传统更加强调对“无”的观照,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无器官身体”也更加强调非有机的一面。但正如“无形”要通过“有形”来彰显,“神”要通过“形”来摹写一样,“非有”也正是要在“有”中才能显现,而通过“非有”,“无”也就自然天成了。此乃“无中生有”,“有无相生”,“有显非有”,“非有显无”。那么,“无器官身体”所处的这种“有无之间”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答案就在于它时刻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方面,是被组织好了的可辨识的“层化”表面,它被遏止于其中并且要忍受上帝般裁断的煎熬;另一方面,是“解辖域化”的解构运动,在其中它努力拓展自身并趋向一种不断创新的实验性的自由。正是在这狭路相逢的左右为难之中,“无器官身体”进行着自己永恒的、激烈的战争。 那么,究竟如何在有机体中凸显出非有机体,即:怎样将“有机身体”努力朝向“无器官身体”开放?德勒兹认为,与科层化的有机体针锋相对,要成为非有机体就要对有机体进行“去连接”的实验,就是去主体化。但是,有机的非有机化过程需要格外的谨慎,因为这是剂量的艺术,过量就是危险;这里需要的不是一把疯狂挥舞的大锤,而是一把极为精致的锉刀(这也表明创生非有机叙事并非易事)。所以,“应该保留足够的有机体,以便它在每个黎明重新形成;应该保留那些意义和解释的少量储备,哪怕只是为了用它们来反抗它们自身的系统……同样,应该保留主体性的少量份额,以便能对主导性的实在作出回应。”[5]223换言之,非有机就是对有机的一点一点地“解构”,在有机体的层级之上,利用它所提供的可能性进行试验,在它之上发现一个场所,发现潜在的“解辖域化”运动和可能的“逃逸线”,但这样的运动还不至于让有机体“解体”。同理,非有机叙事也对有机叙事进行着同样的实验。例如,电影史中的新好莱坞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电影等都对传统电影有机叙事进行了反叛,这些作品都展现了有机叙事体的疲态,用难以掌控和言说的异质性成分开始了解除“领土”,还原“土地”的革命。 进一步说,非有机叙事对于有机叙事的实验或革命的极端形式是什么?换一种问法,可能存在一种无机叙事吗?无机的事物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但往往是集合整体。比如一台制造用的机床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但却不是有机整体,因为其中的部件可以随时拆去和替换,整体和部分之间并没有一股联系之“流”予以贯之。同样,一个杂货市场也是一个无机整体,因为店面与店面之间并没有一种“亲缘”关系。事实上,当我们强调拆解联系的时候,绝不是要摧毁联系。当我们进入有机体时,发现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一旦我们稍稍偏离这个(人为的)中心,就会发现情况变得很复杂。即,在生产“无器官身体”的道路上可能会出现两种身体:“充盈的身体”和“空洞的身体”。德勒兹指出:“最糟糕的并非是保持于被层化的状态——被组织、被赋予意义、被征服——而是将层置入一种自杀性的崩溃或狂乱之中,因为这会使得层重新降临到我们身上,而且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为沉重。”[5]223瓦解有机体,这绝非自杀,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丧失了的统一体相关的)碎片性的器官”。[5]228如果说非有机是有机的互补面,那这种朝向无机解体的身体就是有机身体的真正对立面。然而,只要作为人的生命还在,就永远不会达到绝对的无机。那么,对于叙事而言,情况又会怎样? 这涉及最小叙事性的问题。叙事性是用来“描述叙述世界/叙事特征并将之与非叙述世界/叙事加以区别的那组特征”。[11]150普林斯认为,对于任何非矛盾性事件的呈现(且两个事件不能在逻辑上彼此进行预先假设或彼此让对方成为必需),如至少一个发生于时间t的事件,与发生于其后的另一时间t[,1]的另一事件将构成一个叙事。[12]142安德烈·戈德罗的定义则更为详尽,他认为,一个信息被认为是传播一个叙事,只有当这一信息在任意转变的过程中表现任一主体,这一主体因而先位于一个时间t,后进入一个时间t+n,且说明与t时刻相比,这一主体的谓语在t+n时刻发生了什么。[13]62-62“发生了什么”,意味着“转变”。托多罗夫指出,“转变”体现了差别与相似的综合,它连接了两个事实,而这两个事实又非同一体;它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操作:既证实相似,又证实差别。[14]147-167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叙事至少要有一个主体,它的谓语在一段时间进程中发生了异质性的改变,其中有一个“施动者”作为变化的内在之力。如果将这个叙事的最小定义与无机的原则相对应,我们以电影为例可以推导出以下几种无机叙事。第一,它没有凸显主体,比如一组没有任何关系镜头的叠加,如雷内·克莱尔《幕间休息》中缺少“施动者”的场景转变。第二,它没有凸显谓语变化,比如定格的画面,或者拍摄主体与摄影机同时静止的镜头,就像安迪·沃霍尔长久的《沉睡》。第三,它不能生成时序,这并不是说不能打破时序,而是说其中无法还原一种时间的观念,比如以文本游戏的角度看来,《去年在马里安巴》中无法确定的时间策略就属于这种情况。从而,所谓的无机叙事其实是缺少叙事学意义上的美学内涵的“叙事”。 简言之,非有机叙事和有机叙事是一种互补关系,虽然我们将无机叙事作为有机叙事的对立面来看待,但也不会在绝对意义上剥夺它叙事的可能性。这就如同将达·芬奇、弗朗西斯·培根和波洛克三者的绘画相比较,它们虽然在绘画性上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区分,但三者首先都具有艺术性(艺术性与叙事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只是,正如德勒兹所暗示的,波洛克的行动绘画因其极端的自由和凌乱,从而有消解绘画性的倾向。在此,它与无机叙事消解叙事性的冲动不谋而合。 总之,德勒兹的身体美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叙事美学思想,尤其是“无器官身体”的概念更是成为我们串联有机叙事、非有机叙事与无机叙事的关节点。在当今对艺术叙事的研究缺少哲学、美学视角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对艺术作品叙事美学层面的探讨弥补了传统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过度强调形式的不足,是对后经典叙事学的一种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