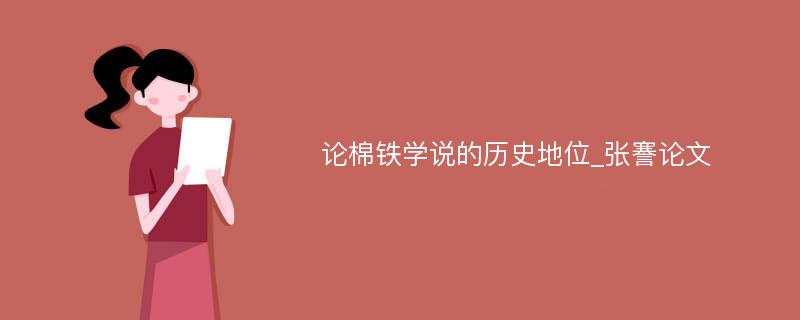
试论棉铁主义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地位论文,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6-0076-09
近十多年来,学界关于张謇及其实业活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比较而言,研究张謇政治活动、实业活动的较多,研究张謇经济思想、特别是颇有影响的棉铁主义的较少,忽略了棉铁主义在中国近代工业化中的宏观发展战略指导作用。本文试图从工业化的角度,对张謇的棉铁主义做一系统的阐述,从而对其在中国近代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新的估价。
一
张謇的棉铁主义工业化主张的提出,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心路历程。这一心路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思想理论形成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1910年4月,南洋劝业研究会在江苏南京成立。张謇是该会发起人之一。在致开幕词中,张謇首次提出棉铁主义工业化主张。遗憾的是,在现已出版的各种有关张謇的著作中,没有发现这篇文字。但庆幸的是,张謇在其日记和随后的文章中,给人们留下了他思想的足迹。在张謇日记中,尽管没有关于棉铁主义的记载,但留下了有关南洋劝业研究会1910年4月在江苏南京成立的历史记录。1910年11月28日,张謇在与友人谈话时,“反复陈说”其主张:“实业以振兴棉业之纺织为内维,扩充矿业之煤铁为外境。”(注:《张謇全集·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43页。)1911年,张謇在《海关进出口货价比较表序》中说:“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开幕,謇于各行省到会诸君子,发起联合研究会,乃裒光绪一朝之海关贸易,参考其大略,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如行深山,临悬崖,榛莽四出,披而始识无路;如泛雾海,见一岛屿,若隐若见,而始得所趋。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为预会诸君子告。……至柔惟棉,至刚惟铁”(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4~785页。)。这时张謇虽然还没有将其提升到棉铁主义的理论高度,但其中的“振兴棉业之纺织为内维,扩充矿业之煤铁为外境。”、“至柔惟棉,至刚惟铁”已经跃然纸上,棉铁主义呼之欲出。
1913年10月,张謇出任熊希龄内阁工商、农林两部部长。上任伊始,即在其《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的施政纲领中指出:“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复著奖励棉业之议,上之政府;彼时政府不之省也。今謇无以易此。”(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至此,棉铁主张上升为棉铁政策。在随后的《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张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棉铁主义。他说:“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为捍卫图存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在此,他试图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乘民国初年举国上下大兴实业之东风,将棉铁主义变成一种国家实业政策或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对此,他后半生一直向社会各界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大声呼吁,并身体力行。这一时期,有关“謇与棉铁,固向持积极主义者”、“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之说,几三十年”、“鄙人投身实业,持棉铁主义,二十余年于兹矣。”(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4页。)“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故此一种主义,敢自信为适当”,“殖产兴业,棉铁最为重要”(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中国产业普查,“调查之要在棉铁”(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环顾中国实业之当兴者,孰有大于植棉与纺织者乎!”的言论(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02~804页。),在其文章、谈话、书信中俯拾皆是,反映了他对中国工业化的不懈追求和一贯努力。
棉铁主义作为一种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其具体设想是:“集一银公司,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之棉之稻、麦,类之铁之煤为从要,其他如水利、如电、如铁路、如汽车等为次从要。如是十五年小效,三十年大效可以预言。”(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04页。)具体来说,建立国家银行,以金融业为龙头,广泛筹集国内外资金,作为发展实业的雄厚资本;优先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以发展棉纺织业带动相关的稻米、小麦等粮食产业,形成一个农工商齐头并进的大农业格局,以发展钢铁工业带动相关的水利、电力、铁路、汽车、机械等产业,形成一个以点带面、次序发展、相互促进、协调有序的大工业格局。全国通盘考虑,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地方因地制宜,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区域优势产业布局。时间上,15年初见成效,30年大见成效。
二
任何一种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天才人物空想玄思的结果,而是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反映。棉铁主义也不例外,它是时代精英张謇面对个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即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社会总危机情形下,从救亡图存、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忧患意识出发所做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从内心深处所迸发出的深沉呐喊。
第一,张謇提出棉铁主义,是出于挽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产业的需要。具体来说,就是争取利权,减少贸易逆差。张謇面对开关以来巨额的中外贸易逆差所表现的担忧和焦虑,决不是什么杞人忧天,而是忧国忧民。在张謇的言论中,有关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词句比比皆是。诸如“内忧外患,相逼而乘”、“时事之艰难极矣。謇独居深念,时而忧国计,时而忧民生”、“政局未定,民困尤深”、“然我不即治,人将有代我治治者,主权云何?国体云何?謇不忍言矣。”(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5页。)张謇以清代光、宣两朝的《海关贸易册》中的进出口货价比较表为依据,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作了系统分析。通过分析和比较,张謇惊人地发现,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中国经济落后的缘故,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逆差,而在进口货中则以棉、铁的进口所占比例为最大。张謇指出:“查前清光宣两朝海关贸易册,进口货之多,估较价格,棉纺物曾达二万万以外。次则钢铁,他货物无能及者。是以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63页。)其中,又以棉纺织品为最甚。张謇说:“披览近年海关贸易册,较其进出口之差负,岁计一万万余两,而进口大宗,断推棉织物。”(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26页。)“最多之年,值银一万八千余万两。照海关八折估价,则卖价实有二万三千万两。宣统三年,数亦一万四千四百万两,折合一万八千万两。漏卮如此,岂不可骇?”(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5页。)他指出棉纺织品和钢铁是中国进口货的最大宗商品,每年进口额高达3亿两左右,认为这是造成我国所以严重逆差的主要原因。张謇认为,要改变这种极其不利的局面,防止财富的大量外流,闭关自守、中止中外贸易不是办法,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世界工商大势及公理”,而漠视现实存在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坐视二万万两年输出之财,漠不经心,不思挽回本身气血自为养活之理”,更是大错(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0页。)。他认为,只有以棉、铁为中心来发展中国的实业,才可减少外贸的进口,从而堵塞漏卮和收回利权。张謇指出:“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至柔惟棉,至刚为铁”(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1页。)。“就各项实业而言,最为吾所主张者为棉铁二项,以其于近世界中为必不可少之物也。现时吾人所用之棉铁,皆来自外洋,今后正宜努力使此二者皆可由本国供给。”(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2~374页。)1911年6月,张謇利用摄政王载沣召见之机,斗胆进言,简要阐述了自己以发展棉铁业为中心的实业主张。他说:“朝廷一面须将农工商各实业已办者,实心保护;未办者竭力提倡,以培元气。国人但知赔款为大漏卮,不知进出口货价相抵,每年输出,以棉货一项论,已二万一千余万两。铁亦八千余万两,暗中剥削,较赔款尤甚。若不能设法,即不亡国,也要穷死。此须农工商部通盘筹划,分年进行。”(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在这里,张謇为中国的实业发展立下了坐标,即从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入手,优先发展棉铁产业,挽回利权,走出工业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第二,优先发展棉铁业,不仅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而且符合中国传统资源的实际。张謇认为:“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4~785页。)棉铁业既是国家的基本工业,又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棉制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在中国市场上一直销路最广,而要发展本国的近代工业,则更需要钢铁,故兴办这两种行业,除均可容易得到非常优厚的利润外,更能促进国家工业化的整体发展,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张謇说:“人生所需,惟衣食为必要。今以抚有四万万人口之中国,而衣食所资,事事物物,仰给外人,虽欲不贫,乌可得也。”(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5页。)“我国人民衣食所需之最缺乏者,莫如棉糖。”(注:《张謇全集·事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此外,中国是一出产棉铁原料的大国,发展棉铁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说:“吾国产棉地,在世界几占十分之三四”(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9页。)。“中国之棉,南以通海为最,北则直隶、陕西,西则湖北,均有可称。”“铁需用极大,而吾国铁产极富。以至富之矿产,应至大之需要,岁可得数千万,一出一入,相差之度,不可以道里计。赢数万万,与绌数万万,在国民生计中,当受何等影响”(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29页。)。因此,发展民族纺织业,既可以为民谋利,也可以为国库增加收入。钢铁工业不仅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是其他工业部门发展的基础,同时关系到国防安全。张謇说:“钢铁工业为各种工艺之母,而关系国防尤为重要。”(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鄙人尚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人降伏于我国旗之下之日”(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总之,张謇的棉铁主义,强调优先发展棉铁工业,对外既可抵制进口,对内又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同时可以增强国防实力。所有这些,对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具有启发意义。
第三,优先发展棉铁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张謇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加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发展实业,不可能齐头并进,全面铺开,必须选好行业,重点突破。因此,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必须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救穷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实业不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举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则须究今日如何而致穷,他日如何而可富之业”(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9页。)。“农工商业为类至多,政府人民,财力均困,若事事并营,力分而益薄。……故与其分而致薄,无宁合而可厚”(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经过仔细比较和周密权衡,张謇发现,棉纺织业和钢铁业在各种工业部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优先发展。“棉铁为国家基本工商业。”“制铁事业关系国家生存。”(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0页。)“煤铁业关系国本”(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农工商业之至大者,曰棉铁。”(注:《张謇全集·事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中国要振兴实业,必须以建立和发展棉铁工业为中心,以此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这样才“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他说:“謇尝研究海关贸易册,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38~839页。)他认为,棉铁是根本,是振兴中国实业的重中之重,必须重点发展,优先发展。而要作到这些,必须首先确定目标。张謇说:“顾所谓农工商者,犹普通之言,而非所谓的也。无的则备多而力分,无的则地广而势涣,无的则趋不一,无的则智不集,犹非计也。的何在?在棉铁。而棉尤宜先。”(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在张謇看来,只要中国大力发展棉铁工业,以棉铁工业为中心来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便“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从而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以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相抗衡。
三
张謇认为,实施棉铁方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实行“开放主义”,欢迎外国商人到中国投资,特别是发展钢铁工业。因为发展钢铁工业涉及到巨额资金和先进技术,而这两者恰恰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张举借外债,而且是大量借债,是有风险的,动辄便会招致“卖国”的罪名。对此,张謇特别声明,在他几十年的实业生涯中,从来没有“外资外股”。他说:“下走从事实业二十余年,组织各种公司,如纺织、盐垦等,以数十计,资本总额几达三千万元,是否有外资外股,彰彰共见。”(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但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实业的整体进步,必须引进外资。“吾财用缺乏,则取资于外国;人才缺乏,则取资于外国,彼以其资本、学术供吾之用,吾即利用其资本、学术以集吾事。”因些,在中外“条约正当,权限分明”的基础上,从铁矿开采到建立机械工厂,“亦可听欧美人建设”;“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0页。)具体办法有三条,即举借外债,合资、独资(注:参见章开沅、田彤著:《张謇与近代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40页。)。
第二,建立“三大保障”和“一大机制”。所谓“三大保障”,即法律保障、税则保障和金融保障;所谓“一大机制”,即奖励机制。
建立法律保障,即建立和健全法律体系,为发展实业造就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即国家通过颁布法律,鼓励私人开发此类产业。张謇看到了法律在兴办实业中的作用。他说:“法律作用,以积极言,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则有纠正制裁之力。二十年来,所见诸企业者之失败,盖不可以卒数。推原其故,则由创立之始,一至于业务进行,在在皆伏有致败之衅,则无法律之导之故也。将败之际,无法以纠正之;既败之后,又无法以制裁之。”(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
建立税则保障,即外争税权,内废“恶税”,建立公平合理的征税制度。所谓外争税权,即就近代以来中外所定条约中不平等的关税制度,通过协商,争取解决;所谓内废“恶税”,即早日废除常关、厘金税制。张謇说:“厘金与常关,皆为通过税,世界皆目之为恶税……百里一税,二百里再税,道途梗阻,节节为厉,行之愈远,则商货成本愈重,是禁制商货之流通,迫其近售,而罚其远行者。”(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内贸如此,对外贸易也同样如此。张謇说:“各国通例,出口货多无税。吾国则不然。若丝、若茶、若棉、若其他土货,有国际之竞争者,莫不有税,是抑制输出也。抑制输出,是为自敝政策。”(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6页。)
建立金融保障,即建立中国自己独立、统一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张謇认为,发展农工商的关键,取决资金的融通。中国农工商之所以一蹶不振,重要原因是国家缺少一个坚实的金融基础。对此,张謇建议:“窃以为为今之计,惟有确定中央银行,以为金融基础;又立地方银行以为之辅,例行银行条例,保持民业银行、钱庄、票号之信用,改定币值,增加通货,庶几有实业之可言。”(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
建立奖励机制,目的是“使之发展”、“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关于奖励和保护方面,张謇提出了“保息”措施和“保育主义”。他说:“故今日中国为奖励纺织计,根本计划,必先奖励植棉,必也使全国植棉之地,视今日倍之”(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为此,张謇还提出了奖励棉业的具体办法:“对于棉产,宜用奖励法。奖励之中,又分扩充、改良二法。扩充则注重大农,改良则注重小农。凡集合公司,垦辟荒地,植棉至一万亩以上者,奖一千元;五万亩以上者,奖六千元;十万亩以上者,奖一万二千元;二十万亩以上者,奖三万元。凡个人改良棉产十亩以上者,每亩奖二元。”(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第三,发展棉花生产,要有全国规划,统一组织实施。首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对中国的产棉地区进行系统调查,摸清家底,“调查之要在棉铁,其尤要在欲详知能扩张之植棉地”(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其次,系统了解外国棉花生产及棉纺织业发展现状,作到知己知彼。1912年,张謇发表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说》,对美国、印度等产棉大国的棉花产地、产量及纺织业状况做了初步分析。1923年,张謇发表了《商榷世界实业宜供求统计,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一篇长文,以文后附表的方式,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印度、日本、埃及等产棉国家的棉花产地、产量及纺锭用棉、棉量产销百分比做了系统分析,并与中国做了比较。再次,推行奖励植棉政策,颁布植棉法与纺织法。复次,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改革品种,推广良种。张謇说:“我国地处温带……无不宜棉。依完全办法,必省设一植棉试验场,以为推广改良之范。”(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这样,用十年时间,在中国适宜生产棉花的11个省份,将棉花产地由4000万亩扩大到5500万亩。其中,4000万亩满足国内需求,减少外棉进口;1500万亩用于出口,增加外汇收入。除原有纺织厂外,增加纺机160万锭,增加织机5万锭。在此基础上,争取过几年再翻一番,即纺锭达到300万,织机达到10万。“设使全国上下一致进行,岁岁增加,以五年为一期,三五期后,增至三百万锭,国庶有实业可言矣。”(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张謇认为,即便这样,比起英国的57731500余锭、南美的17864399锭、北美的10435083锭、日本的1731500余锭,尚有很大差距。中国纺织业要在短时期内缩小差距,迎头赶上,任重而道远。除了发奋图强、永不放弃外,政府的投资和奖励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朝末年,国势贫弱,民生憔悴,有人倡议设立救国储金,定额为5000万元,“有事则为国家之用,无事则为海陆军及教育之备费。”张謇对此不以为然,主张将5000万元全部用来发展棉纺织业。他说:“且吾料五千万之棉织业兴,足抵五百万兵之一战,而纺织业之人才且辈出焉。”(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第四,发展钢铁工业,应该矿冶并举,钢铁结合,形式多样。相对于不太发达的棉纺织业,中国的钢铁工业更显落后。1890年,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后改名为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钢铁工业企业。该企业开办之初,连年亏损。对此,张謇忧心忡忡。他希望依此为基础,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张謇说:“我国铁业,只一汉厂,正须借以养成后起之才,备扩充之用”(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铁业为吾华一线生机,今日为世界各国岁注目者,仅此一厂。”(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3页。)如何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张謇认为,其一,实行开放主义,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商、外资投资于钢铁企业;其二,对中国的铁矿资源进行系统普查,在此基础上做重点开发。他说:“查吾国铁矿,如湖北之大冶,如安徽之当涂、繁昌、铜陵、天长,如直隶之永平,如山西之泽潞,如河南之修武,如江苏之利国驿,皆已由本部陆续派员调查。”(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为使调查更具权威性和科学性,张謇在任农工商部长期间,先后聘请法国人梭尔格博士为地质调查员,瑞典人安特森博士为顾问,英国人卫勒博士为技术总监,全面负责调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其三,经营方式,除对外开放外,国内实行官营为主、民营为辅的开发模式。具体办法,国家主要对关乎军事、经济的铁、铜、银,实行官办,“择一二矿产富饶之区,作为官营矿业”(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民营或商办实行特许制度。其四,钢铁结合,矿冶结合,通过发展钢铁工业,带动诸如煤、油等相关产业的开发,实现矿冶同步发展。
四
张謇经历了清朝后期和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多次向当政者提出了发展棉铁的主张和设想,要求以发展棉铁为龙头,大力振兴和发展近代工业。但是,张謇这个良好的愿望落空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对此,张謇深有感慨,他不止一次说道:“是以有棉铁政策之计划。曾言于政府,惜政府不能用”,“是以謇于南洋劝业会时,即发表中国现时实业须用棉铁政策之说,复著奖励棉业之议,上之政府;彼时政府不之省也。”“下走所俯仰太息者:下走昔请公布奖励植棉条例时,我国上下之蔑如者十人而九五不止,即彼政治实业家亦尚未注意。”(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6页。)“如鄙人所持棉铁主义,倡之于二十年前,尝谓果用吾言,必能杜绝他邦宰割之谋,乃不能见用,夫复何咎”(注:《张謇全集·事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0~201页。)。张謇一直认为,“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棉铁主义能否实行,成败兴衰,“则视乎人,视乎财,视乎国力。总之,政治能趋于正轨,则百事可为,不入正轨,则自今而后,可忧方大。”(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7页。)棉铁主义作为一个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战略蓝图,没有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没有成为政府行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抹杀其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反,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棉铁主义的地位及作用给予新的评价和肯定。
第一,棉铁主义的提出,反映了张謇的世界意识,是其追赶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借鉴西方产业革命经验的一次尝试和努力。众所周知,18世纪率先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首先是在棉铁业开始的。当时,英国的棉纺织业属于新兴的但又幼弱的工业部门,市场前景不错,但同时受到内外双重压力:内部是毛纺织业的排挤和打击;外部是品质优良的印度棉布的强烈竞争。为了生存和发展,在棉纺织业领域首先开始了技术革新。飞梭、多轴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蒸汽机的相继发明和广泛使用,使纺纱和织布比翼双飞,促进了英国棉纺织业的长足进步。棉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部门机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和普遍利用,也大大推动了冶铁、采煤等重工业部门技术装备的革新。煤的开采及其在冶铁中的使用,大幅度降低了燃料消耗,形成了“煤铁革命”,使英国一跃而起,成为西方产业革命的发源地。
西方产业革命的历程,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工业自身发展的一般轨迹。关于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著名学者瓦尔斯·霍夫曼(Walther,Hoffmann)在其《工业化国家类型研究》一书中指出: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开始于纺织工业,从食品工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属于少数,只有荷兰、丹麦、新西兰及南美几个国家(注:转引自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78页、第178~180页。)。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针对一些学者贬低棉纺织业在整个工业革命中的地位的观点,郑重指出:“不可小看棉纺织业革命的意义”,并从三个方面重申了棉纺织业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一,“棉纺织业的勃兴揭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在英国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没有别的工业的重要性堪与相比”;其二,“如果说英国经济于1787年后起飞,那都是棉纺织工业的功劳”;其三,“即便棉纺织业对机械化的高涨和对大型冶金企业的兴起没有直接起到巨大作用,棉纺织工业的利润无疑为工业化支付了第一批帐单”(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662~665页。)。张謇提出棉铁主义,正好反映了西方工业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轨迹。对此,我们不能用巧合一词来解释。相反,棉铁主义的提出,是张謇“世界眼光”、“全球意识”的真实体现。张謇认为,当今时代,不仅是“列强竞争之时代”,而且是世界文明竞争之时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竞争,中国社会经济的综合改造和全盘统筹,必须以世界、全球为参照系。“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竞争之会……但有本国古代历史之观念者,不足与于列国竞争之会。即不足救我国时局之危”(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而且必须明了“世界工商大势及公理”。张謇了解世界的窗口是海关贸易册,通过这个窗口,再加上他对日本的实地考察,发现了棉铁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謇尝研究海关贸易册,知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从这个层面来讲,张謇提出棉铁主义,是具有世界眼光的。
第二,张謇提出的棉铁主义,已初步触及到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模式。优先发展棉铁业,以棉铁业为龙头,实际上已经涉及现代工业中的两大门类——重工业与轻工业。即发展重工业以钢铁工业为重点;发展轻工业以棉纺织业为核心。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它能为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动力和现代化技术装备,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没有钢铁工业的优先发展,很难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棉纺织业是轻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城乡居民消费资料的主要来源,直接关系城乡民众物质和文化生活,具有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快、积累多的特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为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同时,它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大量吸收劳动就业。关于工业化初期为什么要优先发展棉纺织业,张培刚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张培刚指出:其一,衣服的需要弹性大于食品,因而与其相关的纺织业便成为当时工业的主干,就享有特殊地位和较为有利的机会而首先经历工业转变的过程。其二,从区位的观点来看,粮食作物大都是普遍性的,而棉、丝及羊毛则大都是区位性的。具有区位性的产品之间的贸易每每较为频繁,而且数量也较大。纺织品的流动性远较食用产品为高,因其运输较便,易腐性较低。其三,从技术的观点着眼,纺织工业在生产上需要更多的技巧,因此,其所需的熟练劳动较其他许多工业为多。就内部生产结构而论,纺织工业所需要的劳动者的数量也多,这对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有好处。就张謇棉铁主义的实践来看,张謇在棉纺织业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棉纺织业的发展,也相应激活了其他相关产业,形成了部门产业间的良性互动,使地方经济趋于繁荣。张謇的这一努力,也恰好反映了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实际。著名学者吴承明曾经指出:“中国近代产业萌发时期的特征: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然而,纺织工业后来却成为中国唯一的略有发展的民族工业。”(注:《论张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考诸历史,棉纺织业在近代中国发展迅速,一枝独秀,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从另一方面引证了张謇的慧眼独识。
而发展钢铁工业,由于资金短缺,非个别人实力所能实现。张謇对此一直引为憾事。他说:“铁,吾猝未能业之者;业棉则逾二十年。”(注:《张謇全集·实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93页、第802页。)“我国铁业,只一汉厂,正须借以养成后起之才,备扩充之用”。“近年,謇在苏省,对于纺织、植棉汲汲进行,略著成效。惟铁业尚无萌芽,私心引以为撼。”(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其实,这不仅是张謇的遗憾,而是中国近代经济与社会的悲剧,并非张謇个人之力所能解决的。尽管如此,由于张謇的倡导,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1920年前后,先后以官办或中外合办的方式,创办了奉天本溪湖公司、上海浦东和兴公司、鞍山振兴公司、湖北象鼻山铁矿等钢铁企业,钢铁产量从1912年的2521吨增加到1921年的7.7万吨,“钢铁工业极一时之盛”(注: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第三,棉铁主义超越了近代中国出现的各种经济救国理论,与其比较,思路清晰,见解过人,内容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众所周知,自近代开关以来,面对西方的经济入侵,人们提出了不少救亡图存的理论和主张,经历了一个从“以农立国”到“以商立国”再到“以工立国”的演变过程。其中,刘锡鸿的农业为本论特别典型。作为当时有名的守旧者,刘锡鸿别有心裁地提出了他的经济观点,提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实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农本商末。他认为,中西国情有别,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疆域大小、土壤肥瘠等自然条件方面有差别,大工业以及火车、轮船等新式交通运输工具,在西方是行之有效的东西,但却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采用这些东西,不会带来好处,而只会把事情弄坏。他以英国的情况和中国相比较说:英国“地狭而不腴”不适合搞农业,要“养民”就只能靠“拓地通商”;中国情况相反,土地广大肥沃,“利在劝农”,所以不应效仿西方国家发展新式工业(注: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1~682页。)。对此,张謇从工业至上的角度,运用西方的现代工商理论,对之做了批评,认为西方的包括农工商的大实业观较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说要高明得多。他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注:《张謇全集·艺文上》,第151页。)张謇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仅仅依靠单方面发展传统农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说严重一点,就是单纯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也不现实。他说:“中国生齿繁而遗利,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6页。)所以应该农工商并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郑观应“商战论”的核心内容是“振兴商务”、“以商立国”,主张以商务为中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理论的提出,显然是受了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它对于反击当时守旧派的“以农立国”论,曾经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是,将经济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通商和贸易,忽视了生产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样失之偏颇,本末倒置。对于当时影响甚广的“以商立国”论,张謇同样做了批评。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注:《张謇全集·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第189页、第260页、第262页、第162页、第165页、第189页、第416页、第13页。)。“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认为“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于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张謇全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第38页、第37页、第38页。)。值得注意的是,张謇提倡:“以工立国”,并不是笼统地、漫无目的的齐头并进,而是有重点、有次序、有计划的系统工程,“生平持论,以富中国,当自营棉铁始”(注:沃丘仲子:《现代名人小传》,下卷,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8年,第168页。)。即以棉铁为突破,以银行为后盾,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从而使中国工业化有一个明晰和系统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