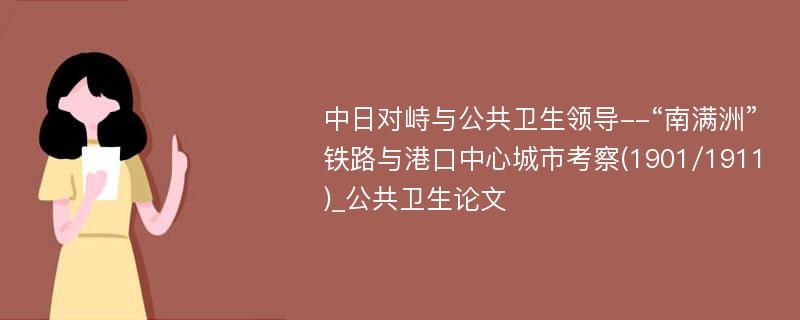
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洲论文,领导权论文,港口论文,中心城市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东清铁路的修筑和铁路附属地的开发,东北以丰富的木材、煤铁、畜类及大豆等粮食资源,从原先只有少数边屯和军事驻扎地的边远之区,一跃成为东亚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大批来自山东、直隶、山西等地的移民劳动力,春来秋去,麇集在营口、大连、奉天、长春、哈尔滨等铁路、港口中心城市。这些社会底层民众,成千上万地蜗居在城市临时搭建的贫民区及筑路工地的简陋工棚;再加上与东亚主要通商口岸(上海、香港、神户、台湾)的密切船舶往来,烈性传染病经常在该地区爆发,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①确立和加强以疾病治疗和救治为中心的公共卫生事务是当务之急。不过,此时东北主权名义上虽属中国,但俄国在1898年通过东清铁路的修筑,日本通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分别在“北满”、“南满”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时在奉天传教行医的英国传教士医生司徒阁(Dugald Christie)写道:一个不经意的旅行者如果横贯东北全境,乘西伯利亚火车穿越“北满”荒原和市镇,看到的是俄国建筑;再在“南满”铁路换乘设备和服务更好的日本火车之后,看到的都是日本建筑,会以为到了俄国和日本。“只是在乡村和边远市镇,才很少看到日本和俄国的影响。”②就此,1909年2月调任东三省总督的锡良说:东三省自甲午、甲辰以后,“受强邻之激刺,生国家之思想,人民知身家性命非合群不能自保;复目睹朝鲜亡国之惨状,甚恐三省版图首沦异域,即万劫不能自拔,其切肤之痛,较之各行省有特别之危险,不能不有特别之请求”。③此时,俄国因日俄战争失利,在该地区的侵略扩张能力被暂时削弱,取而代之的是野心勃勃、亟欲吞并东北而称霸东亚的日本。在中日尖锐对抗的态势下,当地公共卫生事业怎样开启,汇集了哪些矛盾,具有何种特性,并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是颇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些讨论涉及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务的历史特质和时代精神。国内学者目前对此类问题的探讨,还较多关注中国自身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较少论及列强干涉和中国民族主义抗争的议题,故可忽略不论。比较而言,欧美、日本学者更多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视角,讨论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④毕竟,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如果脱离了列强在华的激烈竞争和角逐,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和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背景,关于疾病、医疗和公共事业的许多研究就无法深入。东北则由于经济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此时列强争夺最为激烈的重点地区,欧美、日本学者的研究更以此为中心。⑤不过,从中国本地学者的角度来看,欧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和欠缺。就资料而言,他们虽较多利用了英文、日文资料,却没有太多注意开掘中国当地的资料。再就研究的问题来看,他们虽较多呈现了日本帝国医学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攫取中国国家主权和确立势力范围,以及西方/日本霸权文化对中国知识精英,乃至对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和控制;但对于中国方面的应对,如国家政权怎样介入地方公共卫生事务,其开创和运作的过程乃至实际效果,相关叙述都较为抽象和粗略。⑥这就带来了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即尽管这些研究者对日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由于叙述主角没有进行置换,最多也还是讨论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关的问题,这就可能会让人误以为东北公共卫生事务是由日本单方面推动或主导的,中国只是一个反应迟钝、步履蹒跚和无关紧要的被动陪衬——历史光照仍然被更多聚焦在日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边。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本稿期望从中日之间的纠结、碰撞,及其竞争和较量入手,重点探讨该地公共卫生事业与日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公共卫生事务开启和推动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
一、台湾经验移植与日本殖民医学的抢先开启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当“南满”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之时,该地区中国官方的公共卫生事务尚未真正起步。具体来看,即使是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奉天,也是街道仄狭、房屋简陋,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与二三十年前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1882年抵达奉天的司徒阁写道:该地房屋的地面不是土,就是砖块,多与屋外的地面持平。房屋的一半被砖砌的土炕占据,人们白天在这里吃饭、聊天和休息,夜里在这里睡眠。食橱和房间很少被清扫,如果炕是干净的,就足以让人满意。窗户用纸,没有玻璃,室内光线严重不足。很少房屋装有天花板,蛛网和尘土长年挂在横梁上,人们在地上随意吐痰。整个城市没有下水道,脏水任其到处流淌。城里几个大水塘汇聚了从街道流出的雨水,人们在此清洗蔬菜和衣服。街上堆放着垃圾和杂物,从来没有人清扫,狗和猪成为清道夫。1884年,奉天霍乱肆虐,整个城市没有一所医院,病人都被送到了司徒阁的诊所。司徒阁每天从早忙到晚,收留病人的简易棚屋不敷使用,只能将源源不断送来的患者安置在露天,死亡率高得惊人。司徒阁估计:在疫病蔓延的八、九两个月中,“大约两万具棺材从城门抬出”⑦。霍乱之后,1887年6月,地方绅商捐助的同善堂附设施医院,按单、双日分诊男女两科,每年施治病患约1800余人次。后来由于经费难以为继,没有多长时间就关门停诊了。⑧1901年,俄国乘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占领奉天,因霍乱流行而采取了强制性隔离措施,引起当地民众恐慌,同善堂的绅商们遂又筹款恢复施医院,不定期施行义诊,专治贫病无力求诊者。施医院无住院养病之设备,只是按日分别男女,流动施治。⑨总体上说,其时中国管辖区内的城市道路清扫、垃圾处理,以及疾病治疗和预防,都只是个人或民间行为,官府不甚过问,很少插手,故可认定尚无近代意义上制度化的公共卫生机构和设施。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要想在“南满”立足,首先遇到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驻扎该地的第四师团近10万士兵,以及数以万计迅速涌入的日本商人、文职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毕竟,让当时那些初来乍到的日本人难以适应的,是气候和环境。东北地区冬季天气严寒、空气干燥,长时间室内封闭取暖,再加上居住拥挤,通风不畅,极易罹患肺结核等疾病;夏季则气候炎热,城市没有下水和供水系统,蚊蝇肆虐,极易罹患肠胃疾病。统计显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参战178292人,伤病总数171164人次,其中枪伤7774人,占参战兵员总数的4.36%,患有脚气、痢疾、疟疾、霍乱等病的47921人,占参战兵员总数的26.88%。再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约1700名士兵罹患了各类传染病,其中旅顺战场的肠伤寒患者、赤痢患者分别约占病患总数的13%、87%;辽阳以北战场的肠伤寒患者、赤痢患者分别约占病患总数的49%、21%。⑩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很多日本人移民东北,其中不少人因不能适应当地气候而患病离开或死亡。进一步调查数据显示,移住东北的日本人患病人数较日本本土多至7倍以上,儿童死亡率较日本本土高2倍,肺结核病患者是日本本土的4倍,每年返回日本本土后死亡的人数上千。再与日本本土比较,东北日本人每万人中赤痢患者较日本本土高19倍、伤寒患者高7倍、白喉患者高5倍、猩红热患者高53倍、痘疮患者高120倍。日本职业医生总结道:“满洲以最可怕之结核为首,肺炎等呼吸器病及各种传染病极多,现今只可受不健康土地之污名。”(11)
可供参照的成功案例,是日本在台湾已经先期展开的公共卫生事务。1894年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同时也是该地殖民医学开创者的后藤新平,曾是一位职业医生。后来他自费到德国学习医学两年半,并实地考察过英国济贫法的实施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医学,返国后一度担任过内务省卫生局长。留学德国期间,后藤新平对欧洲列强殖民统治印象深刻,认为欧洲殖民政策有三大支柱,即教堂、医学和铁路;日本无法依靠宗教,只能依靠医院和文教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1901年11月,在后藤新平的大力督导之下,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重点城市设立卫生组合,建立定点鱼菜市场、屠宰场,开设排水沟、上下水道,设立隔离病院、火葬场、公共厕所、公共浴室等。同时,当局还大力推行公医制度,设立官立医院,至1904年全岛已有200名日本医生。由于台湾常遭霍乱的袭击,后藤新平大力推进饮用水的改造。至1904年,占全岛居民人口1/10的台北,所掘水井已达800余眼,公共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12)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地医学的成功,受到当时列强和中国改革精英的注意。1905年在上海出版的华文《时报》,刊登一篇转译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称:日本在该岛不遗余力地整顿卫生,“染疫死亡之数,遂大减少。当1901年上半年,染疫而死者有2619人,1903年仅600人。”(13)
1906年11月,后藤新平从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任上,调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简称“满铁”)总裁,成为日本在东北殖民事业的规划者和主持者。台湾的成功经验,让后藤新平相信依靠军事占领只是“霸道”,文明的利器应是创办学校、医院的“王道”,即参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作模式,在东北以铁道、教育、卫生和科学研究为中心,推进“文装的武备”。(14)为了得到日本内阁大佬们的鼎力支持,后藤新平撰写了《满铁总裁就任情由书》一文,提出在此后10年内日本至少要向该地移民50万,如有可能拟移入百万人以上,以确保日本的主导地位。(15)然而,不同于台湾,此时东北不是完全殖民地,日本殖民市政当局受制于列强激烈竞争和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反抗情绪。如果在台湾,日本采取的是日本“内地”延长“同化”政策,那么在东北则只能通过包括公共卫生事务在内的快速现代化成就展示,以证明其殖民事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于是,日本在其控制范围内迅速颁布了卫生行政法令,设立了制度化的卫生行政机构。1906年10月3日,日本开始在其居留民人数最为集中的大石桥、奉天、公主岭等地设立警务署,部署警察931人,1913年增至1583人,负责日常公共卫生事务,如督促民众清扫街道,在传染病蔓延期间负责管制交通,并逐屋进行检疫等。(16)1907年2月,日本关东都督府颁布了第9号令——《卫生协会规则》,成立以日本人为主,有当地华人参与的卫生协会。协会设置会长(由日人担任)1人、副会长2人(有一位中国人)、卫生委员38人,日常事务则由大连民政署选任10位常议员负责。时年53岁、经营杂货业并担任大连华商公议会会长的郭学纯,也被日本当局举为副组合长。(17)同年秋天,大连及周边地区爆发鼠疫,日本市政卫生当局除采取严格的检疫、防疫措施之外,又将住户按经济收入状况分为五等,由5角递减至1角,按月缴纳卫生费。为准确掌握各区居民住房和人口状况,卫生委员会召开了董事及书记会议,议决将全市分为10个区,每区派员2名,每日调查50户人家,报酬是4元5角。(18)再至1909年6月,在原有地方组织“会”的基础上,日本殖民当局还在金州、普兰店和貔子窝等地推行保甲,将10—20户居民编为一甲,保甲长须向当局报告传染病流行情况,并负责疾病预防和督促各家各户的消毒事务。(19)
与此同时,日本花大气力,投入巨额资金,创办了当时东亚技术设备最为先进的医院。1906年,上任满铁总裁伊始的后藤新平,在满铁尚无赢利、经费缺乏的情况下,提出要创办关东府附属大病院,向内阁要求拨款120余万日元。(20)1907年,刚创办的满铁大连医院就是当时中国境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现代化的医院,号称“东洋第一”。这一年该医院诊治病人达95726人,1908年达到180926人,1909年上升至250528人。此外,日本的“南满”铁路市政当局还在新民屯、营口、长春等地建成28所规模不等的病院,拥有1445名医生、护士,每年治疗门诊和住院病人约在100—200万之间。(21)1920年初,在华基督教会对全国医疗卫生事业进行调查,认为东北各大城市中非教会医院为数甚多,如法库、抚顺、开原、辽阳、沈阳、旅顺、铁岭、长春、吉林、六道沟等处,并称:“在中国其他省区设备最好的医院非教会医院莫属,而独在东北则为南满铁路局所设,医生皆为日本人,规模最大的一所医院设在沈阳,该医院并附设一所较大的医学院,中日学生并收,用日语教学。”(22)就此,日本官方文件也称卫生与教育是其在东北最成功的两项殖民事业,“就中医院网的建设,正因为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是此道的权威”。(23)
更让人惊愕的,是日本殖民市政当局还以大规划、大投入和大制作,彻底改善了满铁所在地大连的城市卫生景观。日俄战争之前,即在俄国人统治时期,大连市内秋天尘土遍布,开春一片泥泞,到处是筑路工人临时搭建的工棚和陋屋,卫生环境相当窳陋;1905年4月,日本辽东守备队颁布了《大连市专管地区设定规则》,规定华人入住日本人居留区内,必须登记和经过日本警察局核准。(24)此外,日本殖民市政当局严格禁止建造当地华人的矮小房屋,规定新建房屋分为二种:一是砖石,或金属建造,永久建筑的高度须在30尺以上;临时建筑虽可用木板或砖为之,然高度则须在12尺以上。1907年前后,整个城市景观已一片日式风格,2/3商店为日本人所有,地名则使用日本名,“名之在南者,曰‘大和町’、‘越后町’;在北者曰‘武藏町’、‘长门町’;在东西者曰‘土佐町’、‘朝日町’、‘美浓町’;一桥则曰‘日本桥’,一公园则必曰‘常盘公园’”。(25)再至1910年前后,鉴于城市发展日见规模,殖民市政当局又规定所有房屋必须用砖或石块建造;在店铺地区建造的房屋,高须在27尺以上,一般居民区须在24尺以上,市郊则须在12尺以上。时人说:“俄治时代,房屋尚属寥寥,且又粗恶,今则高楼栉比,焕然一新。十年进步,正可惊也。”(26)至于相应的卫生设施,日本关东厅、满铁将每年预算的10%—15%用于公共卫生事业,1905-1910年期间投入数百万日元,修筑城市供水系统。1908-1909年间,满铁不但投巨资修筑了大连的城市道路,其工程师和建筑师们还为关东厅设计了巍峨的政府大厦,于1910年建成。同年,一条新的轨道电车业已开通,号称东北最豪华的大和酒店也开始接待客人。另外还有新栽种的数千棵树木,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林荫道和种族隔离的居民区。(27)1910年11月,在哈尔滨发行、具有俄国背景的《远东报》谈及日本人在医院、卫生、供水、道路、下水管道等项目的投入时,评论道:“日人占据南满以来,全副精神经营一切事业,观其沿线之设备费,殊令人警骇。”(28)
二、中国为对抗日本而快速推进公共卫生事务
中国方面最早意识到卫生事务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是在1900年7月俄国借义和团起事之机发兵攻占东北全境期间。1902年4月8日,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自条约签订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分三期从东北撤军。1903年4月18日(此时已超过第二期撤军限期10天),俄国驻北京代办柏兰孙突然向清政府提出所谓“俄国政府七条照会”,称俄军从奉天、吉林撤军的前提是清政府必须正式保证接受俄国的要求,包括中国政府承认其在东北的卫生行政权力,即当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爆发时,允许由俄国负责营口等港口的检疫、防疫事务。对此,清政府予以拒绝,回复说防疫一事,中国极欲讲求,天津、上海等地均已制定严格的防疫章程,营口关道将依法办理,并会同该地海关税务司,与各国领事妥为筹议,禀报外务部核定。(29)
清政府与日本在公共卫生事务方面最先发生正面冲突的时间,是在1905年3月日军攻陷俄国占据的奉天之后。经历了城市争夺的激烈酣战,奉天城内难民麇集,满目尸体和瓦砾,日本军政署随即下设卫生局,负责清扫街道,搬运各街区的垃圾,并着手进行检疫、防疫。盛京将军增祺当即向日占领军提出严正抗议,与之进行了反复交涉,强调奉天公共卫生清扫事务应归中国市政当局负责,日军不得擅自行动。北京外务部闻讯后也紧急召见日本公使,促其电饬日军立即停止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但“日本公使不允,答以卫生局实为免疫,彼此兵民两有裨益,实于地方无碍”。(30)作为应对之举,盛京将军增祺匆忙成立奉天卫生所,不顾战争刚刚结束,人工车辆异常昂贵(每个小工一天需银洋7角,大车一辆需银洋9元),每天动用小工200余人,“大车一百三四十辆”,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将城内近百年来积聚的垃圾全部运走。此外,当局还规定每家门口贮水一缸,以备洒街,并出示严禁人家积秽。进入五月之后,工价稍减,奉天卫生所仍以“常车三四十辆”,随时清理街道。(31)在给北京中央政府的奏折中,东北地方行政长官忧心忡忡地称:“值师旅饥馑之余,深恐疫气流传,至为民害。客军未撤,尤宜先事防范。惟现应饬将医官病药等项,赶即筹办,期敷查疫治疫之用。商约内业已订明奉将自开商埠,将来外商萃集,尤应将工巡事宜赶为筹办妥善,以保主权。”(32)
当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挟战胜俄国之余威,占据原本为俄国攫取的大连、旅顺、奉天等地,并以此强迫中国谈判日本在“南满”的权益和地位。1905年11月17日至12月22日,在中日双方的谈判过程中,日方蛮横坚持索取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卫生执法权,即由日本领事负责铁路附属区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务;与之毗邻的中国管区的公共卫生事务,则由日本与中国地方官员共同负责;当再有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爆发,日本可以动用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各战略要地的守备部队。(33)最终结果是中国被迫签署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不得已将“南满洲”划为日本势力范围,至于公共卫生事务方面,虽没有明确将权利让给日本,但参与此次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议定,中国方面即刻在该地区推进公共卫生事业,以防止发生外交纠纷和日本侵犯中国主权事件。他们的想法是:“和议既成,须早图抵制,略占先着。如省城之马路,新沈之铁路、电灯、电话,营口、大连湾、安东之商务,榨房、碾房、店栈之类,各处卫生、巡警、建筑、矿产等类,皆须筹办。不能普办,亦须择办;不能立办,亦须先图兴办之基,不能将来全入人握。”(34)
此时正值中国朝野视日本为东亚国家快速现代化的成功范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均以日本为师,公共卫生事业也不例外。1902年由袁世凯创办、1906年改隶陆军部军医司的北洋陆军医学堂,教学语言是中文和日语,英语不是必修课。除讲授中国经典和教日本语的中国教师外,讲授生物、化学、药理、解剖、生理和外科者都是日本教授,其中有一位还参加过1900年联军攻占天津和北京的军事行动,是拥有日军上校军衔的资深教授。(35)尤其相对于中国其他省区,日本在东北影响最大,交通最为方便,从大连乘船三两天即可抵达日本,地方官员和商董赴日游历成为一时风气。1906年11月,东北地方当局讨论如何推行卫生新政时,提学使张鹤龄上书盛京将军赵尔巽,称:医学卫生急宜振也,“拟特聘东西医专家(日本旧日医法多用中国古书,尤为改良我国医学为便),设立学堂,宽其时期,养成专门术业,别就地方情形,编制卫生浅说,设所传习翻译报章,俾于生活程度稍稍进步,且于开通风气有绝大影响(日本变法之初,最得医学家之力)”。(36)1907年1月19日,赵尔巽致函军机处,奏请将创办公共卫生事务当作此时东北各地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赵尔巽称:奉省迭经兵战,情形与内地稍有不同,必须悉力整饬,一切修路、卫生、防疫、去秽,以及菜场、屠宰场、停车场等项均已粗具规模。赵尔巽的担心是:“盖以客军逼处,事事须争先着,倘办法稍不完备,必致啧言。而日领事荻原到奉以来,时攘我警权,其领事馆内均于警察卫生有专员专科。初次晤面,即以为请。经尔巽严词据理峻拒,又思设法破坏。经局员格外防备,未留罅漏,现仍于商埠巡警争执甚力。”(37)
为了与日本方面竞争,中国成立了制度化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大力改善以前破烂不堪、也常让日本借机找碴的城市卫生景观。1906-1907年前后,按照赵尔巽的指令,各地纷纷创办了卫生局,负责街道清扫、垃圾处理。如1907年1月成立的铁岭卫生局,很快就让市镇的卫生景观得以改善。时人说,该地“不第到处洁净可观,即前日新雪初晴,各家门前街道均扫除一空,而无积雪碍路之处,至夜则各区路灯齐炯炯,然如寒星,大有文明气象”。两年之后,即1909年10月,又有报道称:“铁岭城厢内外,近来秽污不堪,日昨见卫生队挨户传知打扫洁净,翌日即进行检查,如再有堆积污秽,将进行惩罚。”(38)当然,改善最明显的城市,还是作为东北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奉天。1907年前后,当局投入经费100余万元,将以往只是泥水路的主要街道铺设了碎石。至1908年7月,省城巡警总局每月拨洋1000元,用于常年维护这些马路的工料费用,“而一切人员仍由工程局另行每月开支”。(39)以往每到夜晚,市内街道没有路灯,整个城市漆黑一团,此时当局规定,入夜时分,住户各在门前点一盏灯,以供夜间出行之用。接着,官府出资在城区主要街道架设了路灯,并在交通要道和重点地段设置了监管治安和卫生的深蓝色警亭,雇备人夫车辆,修建厕所,日事扫除,致使城内一些重点地段渐臻洁净,夜晚灯火通明。改革精英们认为这是“新奉天”对“旧奉天”的“起义”,即“旧奉天”是城郭不完、宫室苟简、民质朴素、交易露市,负贩鸣金击鼓、吹笳鼓号,何一非古时部落之蜕迹;“新奉天”则是有了公共卫生事业,城市景观得到较大改变,“是故衣服不新则污垢,饮食不新则溃败,空气不新则恶浊,宫室不新则倾圮,器用不新则窳败,人物不新则笃固,国家不新则老大。新者若旭日,旧者若夕照;新者若源泉,旧者若枯海;新者若乳虎,旧者若腐鼠;新者富进取之思想,旧者多保存之性质。”(40)
与之相应,当局在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中国辖区内还创办了若干官办医疗设施,负责疾病救治和预防。早在1905年3月,盛京将军增祺以“东西洋各国,均讲卫生之道”为由,奏准设立奉天官立医院,医生均为中医,分内外两科,按月施诊,春、秋布种牛痘,“常年经费大洋两万元”。(41)此后,赵尔巽接任盛京将军,对公共卫生事务更加重视,上任之初颁布政令,声称要聘请中外医生,研究医学治疗,并准备开设医学堂,教授学生。1906年12月,奉天大北关卫生医院正式挂牌运营,聘请了日本医生2名、英国医生数名,每天接待患者100多人,所有医药悉由官府施予。后由于病人太多,奉天市政当局又“出示招考医官30名,报名有60多人”。(42)此外,比较重要的官府医院还有长春、安东等地的医院。如吉林民政司筹款创办了长春医学研究施医所,最初不过一二十人前来就医,半个月后增至每日五六十人或六七十人,“日见增多,有加无已”。(43)不久,医学研究施医所增设官药局一处,“由官拨款五千吊,以为提倡”。(44)同时,当局承诺还将及时成立西医院,“不致偏废”。(45)1910年,安东地方行政当局创办广仁医院,聘请华人和日本医官按方施治。一个月内,华人、日本医生施药诊治男女患者分别为330余人、160余人,总计690余人。(46)此外,当局还加大了对恶性传染病蔓延的预防和监控。1907年夏秋,营口等地爆发霍乱,并蔓延至盖平、安东等地,在奉天巡警当局特派专员的督办下,这些县镇的检疫、防疫委员自晨到晚巡察各街道,发现疑似病人,即送隔离病院。(47)有些重点地区还成立了相应的卫生管理机构,委派专人进行日常督促和管理。
为表明官府推进卫生事务现代化的决心和力度,地方行政当局还对众多传统医疗从业人员进行了业务考核和甄别。1907年,东北地方行政部门规定,凡省埠及各县城地方,须由警察官署下令组织医学研究会,“各县城镇医生在十名以上者,得组成一会,不及十名者,可附入就近县区研究会。研究会定期三年毕业,以资深之医生为会长,选定后由警察厅局或各县加给委任。”(48)地方舆论也呼吁:国家之安危系于良相,而国民之生命赖乎良医,所谓“全国之人,皆为病夫,中国之医学可想矣。今夫言变法者,莫不曰强种,夫强种当自改良医学始。”(49)就具体执行情况来看,这项法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在奉天,据警务局调查,1909年计有注册内、外、齿、眼等科西医195人,没有注册的医疗从业人员都被取缔。1910年7月,警务局开始调查旧式产婆人数,宣称俟调查完竣后,一律传齐考试,“须合格方准行业”。(50)同年11月,警务局在大东关创办医院研究所,规定中医业者均须入所研究,以重生命。“开学数日,报名者虽有三百余名,而能通医理者仅有三分之一,类皆一知半解,售卖成方之人,警务局拟令其改营别业,以免庸医杀人之害云。”(51)同样的考试也在各地推行。1908年7月31日,吉林省民政司对申请医学研究所的报名者进行考试,题目是:“类伤寒有几症,同伤寒有几症,是何病症,如何治法,或详言之?瘫疽有五善七恶,试分析言之?疮疡未成,宜消已成,宜托施治,以何为难,试举其说,并陈治法?”现存的档案资料也表明,有人由此被剥夺了在城市行医的资格。一位考生的试卷上就被考官红笔批道:“披阅禀词,讹字、谬句,不一而足;似此文理欠通,辄以儒医自称,无乃谬妄。行医为民命所关,未便滥竽充数,所请着不准行。”(52)再如1910年10月,铁岭“悬壶问世医生不下百家,医术良善者有之,当遵命创办医学研究所”。(53)
三、创设巡警和在“万国防疫会”上的成就比拼
中国当局在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城市创办巡警,是针对日本扩张最具冲突性和竞争性的一项日常举措。早在1902年,奉天就已创办规模80人的巡警队,但职责只是与保甲相辅而行,稽查户口,并不负责清扫城市街道、搬运垃圾等公共卫生市政事务。1905年,北京中央政府设立兼管卫生事务的巡警部,添设卫生局及官医局,负责全国卫生事务。(54)1905年底,奉天巡警总局成立,内设卫生科,兼管省城卫生事宜,以及防疫、清道、检查食物和药品,还负责医院管理等事项。按照《奉天警务公所清洁规定》,全城按东西走向划分为内城、外城,划分清道队清扫范围和责任,卫生弁长和巡警按规定进行监督。巡警章程规定警察对于卫生的责任如下:一是建设,即警察为保持公共健康及一般清洁秩序起见,协商市政机关及劝导督促指挥人民从事建设;二是管理,即无论官民经办卫生事项,警察均须切实管理。(55)至1910年前后,奉天各属巡警达两万余人,省城6个警察署共有巡警1400余人,市内平均每126人配有1名巡警。“省城岁需银三十三万余两,各属岁需银共二百一十五万余两。”(56)此外,辽阳、营口、新民、铁岭等地也设立“工巡卫生总局,或名巡警卫生总局,主管防疫、清道、检查饮食物品之地方卫生事务”。(57)
需要稍作引申的是,这种冲突性和竞争性还体现在中国方面筹办巡警,不只是为了城市治安和公共卫生事业,暗地里还是作为扩军练兵之准备。1909年7月15日,兵部一份秘密报告称:俄军沿东清铁路沿线屯扎,兵员总数不下二三十万;日本于鸭绿江左岸,宪兵数逾5000,韩国境内驻屯军增至1个师团以上,俄军在西伯利亚之地不下20万,一旦有事,均可恃其铁道之运输力,不数日而奉吉江三省之日俄兵力达百数十万。至于中国在东北的军事力量,1910年10月8日,陆军一等咨议官、东三省陆军教练处总办陆开先的报告中说只有陆军两镇,再加上奉、吉两省五路、黑龙江省三路巡防营,共两万余人。1911年4月,陆军第三镇二等参谋官孙兵、三等参谋官王承斌等人上书兵部,提出东三省中国军队数量太少,不足以抵抗外侮,宜假托巡警名目,潜练短期陆军,建议巡警训练课目以战时最紧要者,严行教授,“并于学课之余,演说时危国耻,以激发其爱国之天良”。这份报告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陆军大臣荫昌致东三省总督的密函中写道:“东省办事棘手,添练军队不易。闻现正筹办预备巡警,用意深远,似可假托巡警名目,暗练短期陆军,以期多得有用兵士。预备巡警,原定两月毕业,今宜增四个月为一期,马队则八个月为一期,拟由本部派遣各镇候差学生赴奉,或由尊处在第三镇候差生内选派。今担任此项巡警军事教育,其课程择最紧要者教授,庶暗增兵力于无形,而托名教练巡警,而不致别国干涉,是应可行。”(58)
由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当局没有相应的资金准备,整个中国也缺乏一个近代意义上的财政税收体系,因扩充警察数量和骤然推行的各项公共卫生事业而产生的巨额开支不得不强行摊派到当地商民身上,从而引发了强烈不满和抗议。20世纪之前,奉天城市管理基本上由绅董组成公议会负责,官府不直接插手。当时,绅董公议会将城市分为城关内外,街道分为16个会所,遇有支办官差、庙会、水会、本街等一应杂费,均按商铺大小摊派,然后统由各会首承办。1900年,俄国以镇压义和团为由出兵攻占奉天,及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占领期间,占领者需要供应军需、保持市面,都由公议会首出面,按照铺房摊派,收齐后交由俄、日占领当局。1905年3月,奉天市政当局为防止日本占领军插手奉天卫生事务,紧急设立卫生所,清扫街道搬运垃圾,所用一万余两经费借自商会。不久,当局深感临时成立的卫生所只能办理清道、路灯,一切医务病房仅能略具规模,而无法进行公共卫生执法,遂于1905年底将警察局升格为能够负责整个城市公共卫生事务的巡警总局,所需每月11000元费用仍由商会设法代收。商会则将之分摊到十六街会首,然后再由他们分摊各街铺户,按月收齐,解交警察局。1906年,赵尔巽将巡警扩充至1000余名,年支经费增加到40余万,其中大部分又摊派到商人头上,致使以往只纳铺捐而不纳房捐者,此时既要纳铺捐又要纳房捐,负担骤然加重,“商众不加体察,私相聚议”(59),最终决定罢市抗议。
正是由于经费支绌,中国官府在公共卫生事务方面,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与“南满”铁路沿线日本控制区无法相比,也不如俄国控制的“北满”铁路沿线城镇。官方的秘密报告称,与哈尔滨俄国铁路附属区毗邻的傅家甸,本是双城所属的一个小村屯,自从修筑东清铁路以来,商贾骈集,始成一贸易商场。1907年设滨江厅厅治,居民客籍居多,商业多小本生意,无巨资营业之家。官府没钱投入公共卫生事务,不得已将之交给一位名叫齐长庚的商人纠集股本办理。商人办理此事,本为赢利,难免浮冒虚縻。后来官府接手,改办卫生警察,设局长一员,专司其事,每年需要经费15600余吊。这笔钱虽规划来自铺捐,及卫生局所收妓捐各项,但起动时须由地方官筹垫。当地官员报告称:“惟办理伊始,招募夫役,并购置车马等样,需款较巨,拟由卑职先行设法借垫,俟收有款项,陆续归还。”(60)当新创办的卫生局运转之后,1910年地方官报告说,该地“一举一动均为外人观瞻所系,或借口街道不洁,有碍卫生;寓窃道铁,有碍路政。每欲借箸代筹,以侵犯我主权,因应一有不慎,即滋交涉。此地方之实在情形。设立卫生警察,专司检查疫疠,平治街道疏通沟渠及一切卫生事宜,两年来路无坑坎,人无染疫,颇着成效。”(61)不过,当吉林省民政司随后派出警政巡查人员进行巡视时,却发现该城除十字街稍为清洁外,其余各处粪土终日拥积,臭气恶熏,妨害卫生,莫此为甚。原因就在于经费支绌,警察自己购买服装,故多破烂不堪,且人恒有凄凉饥色。这份官方调查报告强调:“且巡警有表率之责,为人民所瞻仰,亦即为盗贼所畏惮,故一切军装,虽不必遇事华饰,究不宜致形腐败。况双城当俄轨冲要,巡警尤为外人瞻目。观城局派有交际员率带巡警十名,分驻租界,俄人问资,协助保护,不失主权,幸赖有此。倘令该城巡警,一般严肃整齐,庶与租界警察不至相形见绌,亦可免外人姗笑、轻视之心。”(62)
让中国方面稍感扬眉吐气的,是1911年春东北肺鼠疫逐渐平息之后,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防疫会”。1911年初,当此次鼠疫开始在东北大规模蔓延之时,俄国担心疫情可能会由中东铁路和来往西伯利亚的华工传播至俄国境内,曾联络在华列强外交使团,试图召开以俄国为首的万国鼠疫会议,邀请各主要国家专家学者,研究协同防疫事宜,“惟日本反对此事,美国亦以组织万国会议之事,甚为延缓,非所以救急之道,以致俄外交界之目的未达”。(63)1911年2月4日,在东京的日本众议员山根正次等三人向众议院提出“预防百斯笃事请开国际防疫会议案”,谓:“现今欲讲求百斯笃预防扑灭之方法,究竟非一国政府之力所可得而济事,是以该国政府为此应行通牒于清、俄、英、德、美、法等各国政府,请择地在上海或在东京召集一大国际防疫会议,更缔结一切防疫条约。”(64)为了不让日本反客为主,中国急忙与英国外交使团的外科医生道格拉斯·格雷(Douglas Gray)和美国公使进行多次接触和交谈。据伍连德回忆,由于日、俄都想插手东北防疫事务,因而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宗旨、召开时间和出席人数等事项,颇让中国官方费了一番心思。就举办此类学术会议的惯例而言,地点应在鼠疫肆虐最严重的哈尔滨召开,但那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担心产生外交纠纷而予以否定。后经过各方商议,会议地点定在奉天,中国方面考虑到该地作为东三省总督驻节地,是中国在东北的政治中心,日、俄势力较为有限,中国能在会议场所、接待规格、议程设定和出席人员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避免横生枝节。此外,在与各国协商时,中国特意强调会议宗旨纯为学术之研究,“种族及政治议题与之无关”。(65)
得知中国决定主办此次大会,日本当局担心在东北的主导地位和领导形象会被削弱,故对会议邀请持消极态度,迟迟不予回复,只是得知欧美列强肯定派代表参加后,日本才公布了5人代表团名单。由于日本向来认为自己居于亚洲科学研究前列,此次会议的学术领导权自然在其必争之列,故派出师从德国著名细菌学家科赫、并于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时率先发现鼠疫杆菌而享有世界声誉的北里柴三郎博士。此时,北里柴三郎博士年近60岁,日本当局抬出他的目的,无非是想在名望和声誉上压倒中国方面负责此次会议的伍连德,伍时年32岁,且没有太大的世界影响。(66)3月19日,北里柴三郎乘火车从东京新桥站启程,21日在门司埠换乘“喜义丸”海轮,23日抵达大连。在接受《满洲日日新闻》(Manchuria Daily News)记者采访时,北里柴三郎声称,日本处在鼠疫研究的世界前列,中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权为此次会议设置议题和炫耀自己的防疫成就。他警告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日本代表将予以坚决抵制。(67)就此,一位美国代表的印象是:“北里柴三郎看上去好像是被日本用来实现政治目的的。”(68)
除了学术议题和会议日程之外,中国、日本和俄国的竞争还体现在其所控制区域的现代化成就的比拼上。3月15日是星期六,会议休会两天,日本不失时机地邀请与会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大连、旅顺参观访问。去大连时,日本当局特意安排代表们乘坐只有在美国才能见到的豪华列车。列车车厢装饰得豪华气派,墙壁上镶嵌着绘画和照片,宽大沙发上铺有长毛绒垫子,餐车上的用具银光闪闪。抵达大连后,代表们下榻在按照纽约现代风格建造、当时东北最豪华的大和酒店。作为一个刚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新兴港口城市,当时大连没有什么名胜可供游览,但东道主还是安排代表们环游埠内各处。对“南满”铁路所属大连医院,各位代表“尤详观于其规模完备齐全,咸深称赞”。(69)当晚,满铁总裁在大和酒店可容纳500—600名客人的宴会大厅里,举办欧洲风格的豪华酒宴,宴请各位代表。翌日,代表们分乘30辆汽车前往海边,在四周长满柏树的楼阁式餐馆里,品尝了生鱼片、寿司等各种日本美味。下午,代表们乘车参观了旅顺港,当晚则是关东厅总督举行的盛大欢送酒宴。第二天,代表们乘豪华列车返回奉天。(70)俄国东清铁路当局也邀请代表们访问哈尔滨,参观俄国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各种现代化市政设施,并设盛宴予以款待。(71)
作为东道国,中国方面竭尽全力保证会议的学术研究水平。3月22日,即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莅临奉天,亲自坐镇督办会议筹备事宜,尤其注意学术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代表中有34位来自英、美、日、俄、德、法等11个国家,5位中国代表来自检疫、防疫第一线,有丰富的临床救治经验,学术水准毫不逊色。(72)会议工作语言是英语,中文、法语、德语、俄语、日语则需要译成英文。奉天交涉司的英语翻译不够,就从奉天中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巡警学堂、中东铁路公司等处借调熟悉英语、俄语和法语的教师、文办、打字员数人,报酬是每人车马费50两银子。尽管此时中国财政极为紧张,但由于事关政府形象和国家主权,北京和东北地方官员还是为办好此次会议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73)代表们下榻的宾馆和会场被修缮得富丽堂皇,客房除摆放舒适的家具之外,还特意装设电灯、供水系统和一个大洋铁炉;女宾和代表夫人们的客房装饰得更为别致和精心,并修建了足够数量的私人厕所和浴室。考虑到有来自欧美的代表,会议膳食由奉天著名的华富饭店(Astor Housr Hotel)操办。此外,会议还准备了英国式的下午茶、点心,雇佣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侍者。奉天交涉司特向东三省陆军兵备处借了马夫和20匹马,并从天津搭克马车行以一个月的租期为限,以每辆车月租金120块银元的价格,租用了15辆马车。为了方便代表们购物和邮寄信件,大清银行派出两名职员在会场专门为各国代表兑换钱币,奉天邮政局设置了邮箱。此外,省城警务局挑选了10名武装骑警,日夜巡逻,消防队也时刻待命,并在会场附近增派士兵作为警卫。按照伍连德的说法,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让代表们切实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好客之情”。(74)
此次会议闭幕之时,围绕中日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治理能力,各方在评论中流露出不同心态。在大连出版的日文报刊《满洲日日新闻》刊出题为《研究会终了》的报道,寥寥数十字中最誉美的言词不过是与会各国专家称赞“清国成功地举办了此次会议”。(75)上海的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刊发的一篇通讯员评论也只是说:以往日本总是不放过使中国蒙受耻辱的机会,中国政府也常被外国批评而没有机会洗刷恶名,“此次会议的召开,中国履行了国际责任。作为会议东道主,努力在满洲阻止鼠疫的蔓延,应该得到列强的体谅。”(76)然而,中文报刊则充溢着某种扬眉吐气之感。此次会议召开之时,华人舆论称,1909年,上海虽召开过万国禁烟大会,但那是美国提倡的,中国只居客位,不免有所缺憾。“此次防疫之设则不然,首由中国主催,各国实赞同之。故为此次防疫会,乃中国开催万国会之嚆矢云尔,谓中国一大名誉事可也。”当会议闭幕时,华人舆论又称:“以中国为主人,而名曰开万国会,说者谓,此从古义未有之事也。而其会所研究者,则皆系世界人类之祸福事。与社会秩序之安否又相关。若即能收其成功,以造福中国,并令世界医学之史,大开一光明异彩,为二十世纪一新时代,又谁曰不可者。然又为此进而思,以中国医学失败之期,而忽获兹开防疫会之大利益,且将推其功能于全世界,此非中国独具之能力所可为也。”(77)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在以往欧美、日本学者较多关注日本在东北推进殖民医学的基础之上,重点讲述了中日双方在公共卫生事务方面的角逐和对抗,以及对各自公共卫生现代化能力的展示和证明,除在叙事上希望扩充关于日本殖民市政当局与中国地方官府、改革精英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以及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卫生行政机构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细节之外,也期望由此修正或改写以往关于中国官府和社会在推进包括公共卫生事务在内的各项现代发展中的愚顽不化、落后消极的呆板形象。毕竟,中国官府和改革精英为应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确也较为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敢向日本叫板和抗衡的“自强卫生”、“救国医学”的话语体系,以及官府奋力推进的公共卫生行政体制。
其时,广泛见诸于报刊的是所谓“欲强其国,务强其民;欲强其民,务强其身,请自卫生始”。(78)东北地方更以反侵略和扩张为主题,强调官府和改革精英的政治主导性。1906年由绅商为主成立的奉天保卫公所声称:无论所举何事,皆有公议之责任,其中包括“禁止赌博、偷窃、游惰、污秽及一切妨害治理之发达者;修治街道、桥梁、沟渠及一切洁净卫生诸事宜”。(79)同一时期,法库门绅商成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和善会的章程也强调:“凡兴学卫生防疫诸事,会中应设法筹办。”(80)1911年4月奉天“万国防疫会”闭幕之后,清政府成立了由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直属行政效率较高、大部分官员都有留学经历的外务部,而非旧官僚成堆的民政部。(81)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增加对当地公共卫生事务的财政投入。1911年7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从海关税中特批5万两银子,用于哈尔滨时疫医院的建设。不久,赵尔巽又从海关税中拨款2万卢布(相当于银14760两),用于在满洲里、同江、大黑河等地建立防疫医院。1911年9月,哈尔滨防疫医院开工建设,1912年12月交付使用,医院主体大楼投入银7万两修建,有能够容纳400人的检疫观察病房、30名疑似病人和40名鼠疫确诊患者的隔离区。(82)至此,东北也成为中国“自强卫生”、“救国医学”搞得最好、近代医疗设施最完备的地区。此后,日本尽管也蓄意染指东北事务,“却无法再将传染病蔓延作为指责中国政府无能的借口”。(83)
面对中国社会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国官府的积极应对,日本在争夺东北地区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侵略和扩张的柔性和老谋深算的一面。与在先期殖民的台湾和朝鲜采取的措施不同,日本在东北采行了更具柔性的文治行政体系。在《满洲经营策梗概》等文件中,后藤新平设定日本在东北的扩张策略,是利用铁路、自来水、汽船、电信及医院等文明利器,以确立能够在该地凌驾各方的“学术霸权”,并获得殖民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84)1906年5月22日,日本元老阁僚召开会议,接纳了后藤新平的建议,决定撤销日俄战争时期在“南满”各地成立的军政署,将行政权力移交中国当局,以及文治的关东厅和满铁。接着,后藤新平及其后继者在“南满”铁路附属地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景观和公共卫生事务中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取得的实际成就和展示性效果,受到了欧洲各国乃至中国改革精英的赞誉,使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当局颇为自得,称这“都是满铁可引以为傲的”。(85)
不过,历史的吊诡又在于,作为一种扩张/反扩张的矛盾和冲突模式,尽管中日双方都颁布卫生法令,创办医院和卫生巡警,清除城市垃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区域的卫生环境。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举措有些只是为了争夺东北地区的公共卫生事务领导权,以证明自己才是最有效和最合法的治理者、统治者,从而忽略或搁置了本应对最贫穷人群、卫生环境最恶劣街区的重点关注和重点投入。这也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交通便利,外来人口众多,该地区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仍然是中国境内疾病丛生、烈性传染病最为频繁的传播地和蔓延地。究其原因,从日本方面而言,殖民医学本来就是为了保证在该地区的日本人的卫生健康,故医疗设施主要设置在日本居留民、官员和士兵数量最多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86)就中国方面来看,在与日本殖民医学竞逐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模仿和复制了其运作逻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公共卫生事务推进方式。例如,中国官府和改革精英倡办的公共卫生事业也集中在中心城市的主要街区;军人和政府官员在官办医院支付半价医疗费用,得到优先治疗和照顾;一些与日本殖民当局较劲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地方基层的实际运作中,很多只是表面文章。(87)与之相应,广大农村一直缺医少药,悬壶行医之人“率皆医理粗通,为谋衣食计耳”。(88)最具反讽意义的是,尽管日本居民区的卫生医疗设施,在先进性、舒适性、便捷性和展示性方面,不少都可被标榜为“东亚第一”,但由于日本居留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生活服务高度依赖华人苦力,在彼此频繁的日常接触之中,日本居留民无法避免来自贫苦华人区的霍乱、鼠疫、肺结核等烈性传染病的传染,并不时波及日本侨民社区,乃至日本本土。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在该地区以巩固和扩张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公共卫生事务,又有着殖民医学或帝国医学损人利己,或损人也不利己的内在品性。
*本稿曾于2009年6月28日在日本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会报告,得到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岛涉、东京大学日本史教授野岛(加藤)阳子等与会者的评论指正,特此致谢。
注释:
①相关的研究,请参见拙稿《现代经济扩张与疫病的跨区域蔓延:以上海、东北铁路港口中心城市为中心的观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1期,2006年3月,第91—129页。
②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14),p.279.
③《奉天全省各界绅民因时局迫不及待呈请代奏明年即开国会以救危亡折》(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六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9页。
④Ka-che Yip,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1928-1937(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5);B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按:此书已有中文版,即罗芙芸著《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最早的研究是美国学者Carl F.Nathan的《满洲的防疫和政治,1910-1931》(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Mass:Th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67)。本书利用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的领事报告(consular reports)、一些英文报刊剪报(press clippings),以及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North Manchurian Plague)的资料。作者试图揭示公共卫生如何成为满洲现代化的核心,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焦点和美国所扮演的仲裁角色。其后则有美国学者Carol Benedict的《19世纪的肺鼠疫》(Bubonic Plague in Ninetieth-Century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0—164)。此外还有日本学者饭岛涉的《ぺ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东京,研文出版社2000年版)。最近的研究则有美国学者Robert John Perrins的"Doctors,Diseases,and Development:Engineering Colonial Public Health in Southern Manchuris,1905-1026," in Morris Low(ed).,Building a Modern Japan: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in the Meiji Era and Beyond(N.Y.:Palgrave MacMillan,2005,pp.101—123)。按:此文献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哲嘉先生提供,特此致谢;日本学者江田いづみ《满洲医科大学と“开拓卫生”》(庆应义塾经济学会:《三田学会杂志》第97卷第2号,2004年7月,第109—122页),又见市雅俊、斋藤修、胁村孝平、饭岛涉编《疾病·开发·帝国医疗:アジアにおける病气と医疗の历史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第91—93页);饭岛涉、胁村孝平《衛生と帝國——日英殖民地主义の比较史的考察に向けて》(东京《日本史研究》第462号,2001年2月,第3—4页)。另外,也可参见1990年以来欧美、日本一些学者倡导的新东北史研究,如Yoshihisa Tak Matsusaka,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1904-1932(Cambridge,Mas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江夏由树、中见见夫、西村成雄、山本有造编《近代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の新视角》,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
⑥初步研究请参见拙稿《东北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1910.11-1911.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8年第3期,第213—231页,该文已由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译成英文刊出。
⑦Du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pp.45—46,48; Inglis Christie,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The Story of a Life with a Purpose(London:J.Clarke &Company Ltd.,1932),p.133.
⑧赵恭寅修,曾有翼纂:《沈阳县志·慈善·医院》卷14,1917年铅印本,第2—3页;饭岛涉:《近代中国におけゐ“卫生”の展开——20世纪初期“满洲”を中心》,东京《历史学研究》增刊号,1997年10月25日,第124—126页。
⑨《杂录》,王家勋:《奉天全省警察报告书》第4编,1920年刊印,第7页。
⑩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p.158;饭岛涉、胁村孝平:《卫生と帝国——日英殖民地主义の比较史的考察に向けて》,东京《日本史研究》第462号,2001年2月,第3—4页。
(11)三浦运一著,郭文宗译:《满洲之住居卫生》,《东方医学杂志》第13卷第1号,1935年1月20日,第6页。
(12)Liu,Shi-Yung,Medical Reform in Colonial Taiwan(Ph.D.Dissertation,Pittsburgh University,2000);范燕秋:《新医学在台湾的实践(1898-1906):从后藤新平〈国家卫生原理〉谈起》,台北《新史学》第9卷第3期,1998年9月,第49—85页;范燕秋:《疫病、医学与殖民现代性:日治台湾医学史》,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
(13)《论日本殖民能力》(译自伦敦《泰晤士报》),《时报》,1905年1月23日,第2版第2张;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编:《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卫生》(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参考资料),1934年印行,第13页。
(14)小林道彦:《后藤新平の大陆政策》,御厨贵:《时代の先觉者:后藤新平,1857—1929》,东京,藤原书店2004年版,第125—133页。
(15)鹤见佐辅:《后藤新平传:满铁时代(1906—1908)》,东京,藤原书店2005年版,第17—18页;黄福庆:《论后藤新平的满洲殖民政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上册,1986年6月,第371—387页。
(16)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9页。
(17)傅立鱼编:《大连要览》,大连泰东日本社1918年版,第83页。
(18)《民政署拟开验疫所》、《注重卫生》、《时疫全消》、《开卫生讲话幻灯会》、《民政署饬立之卫生会开会》,《盛京时报》,1907年9月11、12日,10月10日,均为第5版。
(19)市雅俊、斎藤修、胁村孝平、饭岛涉编:《疾病·开发·帝国医疗:アジアにおける病气と医疗の史学》,第91—93页。
(20)《医术を以て南满统治》,《满洲日报》第479号,明治40年3月17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日),第2版。
(21)鹤见佐辅:《后藤新平传:满铁时代(1906-1908)》,第259页;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第178页。
(22)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第280页;中册,第520页。
(23)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0页。
(24)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第177—178页。
(25)《省商务汇志》,《东方杂志》第4卷第11期,1907年12月,第172页。
(26)傅立鱼编:《大连要览》,第9—12页。
(27)Robert John Perrins,"Doctors,Diseases,and Development:Engineering Colonial Public Health in Southern Manchuria,1905-1926," in Morris Low(ed.),Building a Modern Japan: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in the Meiji Era and Beyond,pp.101—114.
(28)《日人南满统计一览表》,《远东报》,宣统二年十月三十日,附张之一。
(29)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Japan,1868-1945(Washington D.C:The Library of Congress,Photo Duplication Service,1954),缩微胶片,MT21214,1012。
(30)《记外部与日使馆议阻设卫生局及军政署事》,《时报》,1905年4月17、19日,均为第2版第1张。
(31)《兵部咨查卫生所清理街道雇用车辆工夫系何项用款及车辆工夫数目事及盛京将军的札》(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辽宁省档案馆藏,JC10/12282/000269—00271。
(32)《奉天省城内外拟修马路将警察局改为巡警总局归并办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馆”)藏,巡警部档案,150。
(33)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片,MT11242,00037。
(34)《赵尔巽、盛宣怀、吕海寰、岑春煊等人筹议日俄战争对策、日俄议和善后事宜之奏折》,一档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缩微胶片第24卷。
(35)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1995),pp.274—275
(36)《提学司张鹤龄为呈请事照》(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一档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缩微胶片第29卷。
(37)《盛京将军致军机处》,一档馆藏,赵尔巽档案全宗,缩微胶片第21卷。
(38)《巡警卫生之进步》,《盛京时报》,1907年1月1日,第3版;《注重卫生》,《盛京时报》,1909年10月20日,第5版。
(39)《奉天民政司呈为裁并警务处马路科归卫生科管理及奉天行省札》,辽宁省档案馆藏,JC10/23669/001944—001948。
(40)《新奉天》,《盛京时报》,1908年6月26日,第2版。
(41)该医院聘院长(1人)、医官(2人)、药剂师(2人)、看护长(1人)、产科女医生(1人)、雇员(3人)、看护生(4人)、看护妇(1人)、看护夫(6人)。《奉天民政司呈为裁并警务处马路科归卫生科管理及奉天行省札》,辽宁省档案馆藏,JC10/23669/001944—001948;赵恭寅修,曾有翼纂:《沈阳县志·慈善·医院》卷14,第2—3页。
(42)《论奉省宜整顿医学考究卫生》,《盛京时报》,1906年12月4日,第2版;《卫生医院》,《盛京时报》,1906年12月9日,第3版。
(43)《医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本仁回籍守制的呈文及吉林民政司的批文》(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0102。
(44)《吉林民政司奉宪札关于医学研究会拟设官药局等情的移文》(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十八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0023。
(45)《吉林民政司奉宪札为成立省官立西医院等事项的呈札文》(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一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0008。
(46)《医院施治之人数》,《盛京时报》,1910年6月11日,第5版。
(47)《医员搜访染病实数》、《防疫所报告》、《查验渔船时疫》、《病灾已减》、《日益蔓延》、《时疫消除之病院》、《防疫员之报告》,《盛京时报》,1907年9月13、22日,10月2、4、11、19日,12月4日,均为第5版。
(48)《奉天全省警察厅局所管理卫生章程施行细则》,王家勋:《奉天全省警察报告书》第2编,第20—21页。
(49)《论改良医学之不可缓》,《盛京时报》,1908年10月9日,第2版。
(50)《调查产婆》,《盛京时报》,1910年7月15日,第5版。
(51)《庸医何多》,《盛京时报》,1910年11月29日,第5版。
(52)《吉林民政司关于王子新等人愿入医学研究科及补考情形的批示》(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一十月四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1221。
(53)《筹设医学研究所》,《盛京时报》,1910年9月26日,第5版。
(54)《巡警部拟聘卫生顾问官》,《时报》,1906年1月3日,第1版第1张。
(55)《奉天全省警察厅局所管理卫生章程》,王家勋:《奉天全省警察报告书》第2编,第3页。
(56)《遵旨并案议覆陈明奉省行政经费折》(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第1249页;赵恭寅修,曾有翼纂:《沈阳县志·民治·户口》卷3,第31—43页;饭岛涉:《近代中国におけゐ「卫生」の展开——20世纪初期「满洲」を中心》,东京《历史学研究》增刊号,1997年10月25日,第125页。
(57)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第78页;饭岛涉:《近代中国におけゐ「卫生」の展开——20世纪初期「满洲」を中心》,东京《历史学研究》增刊号,1997年10月25日,第125页;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沈阳市志·卫生》第13卷,第191页。
(58)《对于驻屯东省日俄兵力报告书》、《陆开先报告日俄军队在东情形》、《为急救东三省之危亡,谨就管见所及缮具》、《陆军大臣荫昌致东三省总督函》、《陆军部与直隶总督陈夔龙、东三省总督锡良洽商假托巡警名目,暗练陆军防范日俄侵略有关函件》,一档馆藏,兵部—陆军部档案,1504。
(59)《为拟在奉天开办房捐补助警事费》(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辽宁省档案馆藏,JC10/120/002600—002625。
(60)《吉林民政司关于滨江厅详报净街事宜归并巡警局办理的札文》,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1221。
(61)《滨江厅关于地方情形及任内筹备宪政奉办各项事宜成绩清册的详文及民政司的批文》(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三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0377。
(62)这份调查报告具体写道:该城马巡待遇,不过月薪串钱30吊,步巡不过月薪串钱18吊,而伙食昂贵,每日小米饭两顿,啖以咸菜,恒有凄凉饥色,“兼须自备靴履,余钱已寥寥无几,马巡稍有资本者无论矣,至步巡,或有家室,其何以堪?”《吉林民政司关于派员分赴各属考核警政等情的呈札文》(宣统元年十一月六日),吉林省档案馆藏,J029/01/1232。
(63)《各国对于中国之瘟疫》,《远东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附张之二。
(64)《国际防疫会议之议案》,《远东报》,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附张之二;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39; "The Plague," The North China Herald,Feb.17,1911,p.352。
(65)The Confidential Report of Dr.Richard P.Strong,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War,Aug.10,1911,p.19,NA,158.931/181,p.36.转引自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pp.36,37;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15,1911,pp.144—145;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41—42;《北方防疫汇纪》,《申报》,1911年3月3日,第1张第4版;杜山佳:《万国防疫会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第16页。
(66)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46.
(67)《日政府派员来东考察鼠疫》,《盛京时报》,1911年2月20日,第5版;《北里博士行程》,《盛京时报》,1911年3月21日,第5版。
(68)The Confidential Report of Dr.Richard P.Strong,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War,Aug.10,1911,p.19,NA,158.931/181,p.36.转引自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pp.36,37;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15,1911,p.137;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42,62—69。
(69)《各国委员会之来连》,《泰东日报》第679号,1911年4月16日;《大连医院の观览》,《满洲日日新闻》,1911年4月17日,第2版。
(70)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62—63,68—69.
(71)Imperial Russian Embassy,Washington,Feb.19,1911,NA,158.931/89a; Minister Calhoun's Dispatch No.196 from Peking,Mar.5,1911,p.3,NA,158.931/162.转引自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p.24;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68—69。
(72)杜山佳:《万国防疫会议》,《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第16页。
(73)财政极为紧张体现在当时正进行的北运河工程,原计划经费80万两,其中40万两由直隶地方自行筹措,另外40万两由中央政府从京奉铁路行车,以及山海、东海两关关税进款中拨解。由于肺鼠疫肆虐,京奉铁路因检疫而停运,各港口厉行检疫带来巨额开销和花费,致使中央政府欠款达151000余两。1911年2月初,当东北疫情快速蔓延之时,奉天行政当局准备添设医院,实施检疫,锡良致电北京中央政府,请求拨款。据说,摄政王览毕电报,恻然于怀,旋降旨着度支部暂将大连税关项下拨银15万两,以充该省检疫之需,“并着锡良迅速认真筹办,俾早日消除,毋任传染”。3月中旬,锡良又奏请向各国银行借银200万两,以济急需,度支部即行议准。《度支部议覆直督奏北运河工程,请饬另行拨款项由》,一档馆藏,会议政务处档案,35/3/2,993;《北京防疫记》,《时报》,1911年2月10日,第2版;《议覆吉抚电奏疫症猝发灾情异常,饬部筹议折》,一档馆藏,会议政务处档案,35/3/2,995。
(74)"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15,1911,p.137;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45; "A Banquet," 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 6,1911,pp.349—340;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73—74.
(75)《研究会终了》,《满洲日日新闻》,1911年4月28日,第2版。
(76)"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The North China Herald,Apr.15,1911,pp.144—145.
(77)《论研究防疫会重在实行》,《顺天时报》第2747号,1911年4月12日,第4版;《万国鼠疫会各疫员来京颂叙》,《顺天时报》第2765号,1911年5月3日,第2版。
(78)海蠖:《医学与社会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4号,1904年5月,第7—10页;谷音:《论中国前途与医学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1904年7月,第107—114页。
(79)《奉天保卫公所实行章程》,《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1906年2月,第10页。
(80)《法库门和善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年第1期,1906年2月,第11页。
(81)为了与世界同行便利交流或被列强认可,防疫事务总处的领导层多为留学生,并聘有一大批德国、奥地利、俄国的医学专家。早在1911年,美国驻哈尔滨领事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就认定:外国人虽然控制着中国海关和邮政,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则为中国政府自行设置和管理,“这标志着中国在该地区的统治进入一个新时代”。1915年10月,美国驻北京公使的一份报告称:与混浊的中国政治相比,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节约、效率和克制堪称楷模,并说:“一般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最优秀的机构。”Consul-General’s Dispatch No.165 from Harbin,Jul.29,1911,NA,158.931/184; Minister P.S.Reinsch's Dispatch No.795 from Peking,Oct.23,1915,NA,158.931/209.转引自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pp.42,43—53;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1—6。
(82)1919年霍乱侵入哈尔滨,该医院接收了1962名患者。除此之外,中国官府还在松花江的三姓(1913年)、大黑河(1914年)、牛庄(1918年)及安东等地陆续建成了9所规模不等的防疫隔离病院。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p.42,43—53; Wu Lien-Teh,Plague Fighter: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pp.45—48.
(83)Carl F.Nathan,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1931,pp.64,77.
(84)后藤新平:《满洲经营策梗概》,《后藤新平文书·满铁总裁时期》第3卷(缩微胶片),水沢市后藤新平纪念馆发行。
(85)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340页。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关东军用武力占领东北之后,后藤新平还被一些主张文治的日本精英当作成功扩张“南满洲”的一面旗帜和象征,用来批评军部的嗜血好武倾向。如1933年5月,时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的松本重治从上海抵达大连,特意拜谒了矗立在星浦海难公园的后藤新平铜像。他写道:“我感觉他的堂堂风采正象征了以往日本‘大陆经营’的理想。同时,又想到后藤先生提倡尽可能和平地开发满洲经济,而关东军用刺刀炮制出‘满洲国’,后藤先生的伟大理想会不会因此而破灭了呢?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译:《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86)入住设备最先进的日本“南满医院”者多是日本人,住院费昂贵,“闻至少亦需日洋一元二角,惟中国人减半,以示优待,但未经长春病院医士许可者,不得送入。”《优待病人》,《吉长日报》,宣统二年四月初六日,第10版。此外,就诊人数也多为日本人,1907、1908、1909、1910、191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该医院就医的日本人分别是92134、175057、241777、286151、213678人,中国人就医人数相同年份则分别是3592、5869、8751、10925、13906人,远远少于日本人就医人数。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卫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变容》,第178页。
(87)例如,时人批评奉天城内设置公共厕所,原为清洁免生污秽起见,实际上便溺甚为艰难,原因在于厕所便溺之处,仅有“四人设置”,而日间同时如厕者“往往不下十数余人”,不乏便溺于裤内者,“故此怨恨之人不可胜数,况厕内须得勤掬秽物,方保卫生,而今亦不见勤掬,又不敷用”。再如长春卫生局开办多日,各街衢并未整饬,臭秽等物仍然沿街堆垛,厕所亦未修齐,时人批评道:“现有霍乱之症,而贩卖臭烂瓜果食物及卫生有碍者,亦不禁止。”《厕所现状》,《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第3版;《办理卫生尚未实行》,《盛京时报》,1906年10月4日,第5版。
(88)邢麟章修,王瀛杰续修,李耦纂:《东丰县志·商业》,1925年修,1931年续修,出版地点不详,第1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