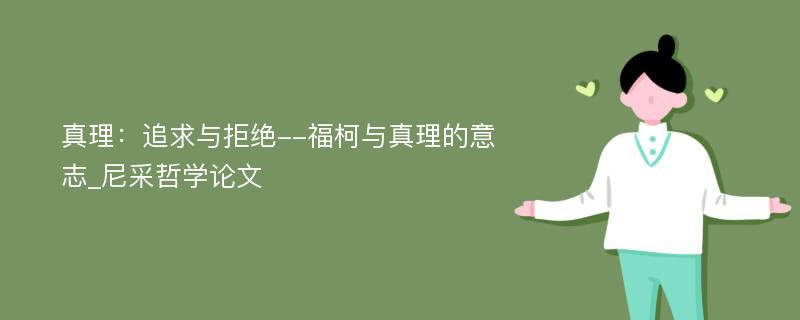
真理:追寻与拒绝——福柯与真理意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意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真理意志的质疑
从柏拉图开始,真理的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如何追寻真理?真理在哪里?怎样找到真理而不会犯错误?而康德在认识论上的革命则换了一种提问题的方法:真理是如何可能的?人怎么可能获得知识?我们看到虽然康德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前面的问题,我们在大多数时候对自己和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还是怎样才能获得真理。问题虽然是两种,其实背后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真理是应当被人所追求的,人虽然是因为吃智慧树的果子,具有了获得知识和真理的能力才被逐出伊甸园,承受原罪所带来的责罚,但是人们似乎痴心不改,不断地探求真理并以此为荣。人类对于知识的自豪在帕斯卡尔这一段著名的话中得到了最好体现:“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注:帕斯卡尔:《思想录——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64-391(347),121-219,157-158页。)
但是,有这么一天,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它转换了问题的方向,把to be的问题转向了ought to be。它是致命的,因为在前面的认识体系中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这就意味着它对这个问题缺乏免疫力,无法从这个体系自身推导出来。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才具有如此强烈的颠覆性,以至于人们对它所做的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尽可能地绕过。然而,问题一旦提出,在没有解决以前就不太可能悄无声息的溜过,总是会在人类的精神上重重地刻下一笔。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福柯与真理意志(volonté de vérité),然而实际上,首先提出真理意志问题的是尼采。他首先提出真理的虚妄和真理意志的虚妄。他说:“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辞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注:尼采:《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载《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106页。)尼采从真理和人生的关系出发来质疑真理意志的合理性。真理在他那里仅仅只是一个人类用以生存的工具,一旦这个工具反过来束缚了人的生存和创造能力,那么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它扔到一边去。
福柯继承了尼采的衣钵,以其独特的方法对真理意志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提出,求真,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具有历史性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尼采几乎是相同的,福柯认为把话语划分为真的和假的,这是在从赫西俄德(Hésiode)到柏拉图的古希腊时期所完成的一个历史事件,(注:尼采则把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作为关键性的人物,并把他当作自己的敌人加以猛烈的批判,事实上对苏格拉底的批判贯穿尼采的全部思想。)真理意志在那时才被建构起来并在话语体系中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注:M.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1971,p.17.)但是,福柯就是福柯,而不是尼采,虽然他们都对真理意志提出了批判,在精神的谱系上可以说血脉相连,但是福柯的批判与尼采的批判走的是不同的路径,如果说尼采的批判是一门轰响的巨炮,要炸毁阻挡强力意志(注:Volonté de puissance,通常译为权力意志,但胡其鼎先生认为强力意志也许更为妥当,权力意志这个词的政治色彩可能过于浓烈了。笔者赞同其观点。)的障碍,那么福柯则更像医生的手术刀,对时代的症候进行解剖和诊断。他认为真理意志在话语的运作中起着一种区分和排斥的作用,它在使一部分话语享受无上荣光的时候,使另一部分话语永远地落入黑暗之中,例如疯子的话语、非理性的话语,这是一种稀少化的作用(raréfaction),损害了话语的多样性。实际上,福柯认为作为真理意志之顶峰的启蒙“使整个社会实体石化和固化、停滞不前,从而维持社会秩序”,(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3-74,10,26,11-12,4页。)那么福柯对真理,对作为真理的知识的批判是如何进行的呢?在这一批判中,福柯的立场是什么?他的方法是什么?他所遇到的障碍和难解的困境是什么?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这种批判的第一步是打碎知识进化论的链条。认识进化论认为我们的认识总是不断进步的,连续的,人类的知识可以不断向真理迈进,即使如康德所说,绝对知识是无法获得的,物自体在人类的认识能力之外,但对于科学家来说,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却毋庸置疑,虽然有时会有偏离和干扰(例如某些政治运动或战争),但是方向是不变的,这种思想最悲观的表述是: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获得永恒不变的真理,但只要人类存在,我们就会认识到更多的真理,永远进步。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知识的历史图景就成为这样一幅宏大的战斗场面:人或者抽象出来的人类智慧与妨碍人进行认识的种种障碍(愚昧、弱点、某些错误、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手段的欠缺等等)进行战斗,最终人类智慧将不断前进,并将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在福柯的谱系学分析和描述中,关于知识的大叙事(grand récit)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叙事,也就是说那些在知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偶然因素,一些历史的碎片浮出水面,它们在知识和学科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福柯就在图书馆的角落中追索这些知识的形成过程,它们如何获得自己的对象,如何使自己成为有用的、可以被投资的、有价值的,最终是如何自我合法化的。
二、对精神病学的具体分析
在福柯的学科史研究中,精神病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注:福柯对精神病学或在整体上说对“关于人的科学”的兴趣与其自身的经验应当是密切相关的,其父亲是外科医生,他自己有同性恋倾向,而且获得过心理学学位,并且在心理诊所中工作过,还教授过心理学。参见《福柯年表》,载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对疯癫这个领域和精神病学这门学科之形成进行研究的《疯癫与文明》(注: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37页。)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福柯着力回答了如下问题:疯子在历史上,在社会的话语和想象图景中是如何变化的?精神病学是如何产生的?它如何把疯子建构为需要它来进行治疗的对象?精神病学的产生和政治权力有什么关系?精神病学产生之后对政治权力有什么影响?精神病学对于我们构建“人”这个概念起到了什么作用?
首先,在中世纪,人们对待疯子如同对待麻风病人,排斥是最主要的反应。这种排斥行为的典型就是所谓“愚人船”,把疯子放到船上带到远方。文艺复兴使疯子开始发话,疯子因为其激情被认为更接近真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无理性和怪诞使他具有某种吸引力。在这个时期,疯癫是活跃的,个性化的,他们形态各异,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理性的世界进行交流。到古典时期,人们用一种方式使疯子归于沉寂,这就是历史上的“大禁闭”(grand enfermement)。1656年,发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它虽然名为医院,但并非一个医疗机构,并不进行任何治疗活动,而是一个半司法和行政机构,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这是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机构,用来保证公共安全。它所要对付的威胁来自穷人、失业者和疯子。很明显,直到这时,疯子并没有被当作一个需要特殊对待的群体,针对社会来说,他的首要特征并不是大脑出了毛病,而是穷,并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从当时的道德图景上看,这些人所犯的罪行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而工作的伦理在资产阶级兴起时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伦理。总医院的任务就是“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注: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43页。)这时对疯癫的排斥根据的是劳动伦理原则。
在总医院和类似的机构中为了消灭游手好闲这种最大的罪恶就必须强迫这些囚犯干活,让他们服从工作的义务,无论这种工作有没有经济价值。但是在这个时候,疯子就逐渐显现出他与其他穷人的不同之处,那就是疯子不是不愿意工作,而是根本无法工作。这“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注: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57页。)此时,疯癫开始以独立的角色,伴随着它的各种独特性质出场了。
后来,疯癫主要表现在一种话语之中,人们通过这种话语来确认和把握疯癫,这种话语就是谵妄(délire)。一种话语形式决定了某种存在形式或者说某种非存在的形式。之所以说非存在,是因为在古典时期的体验中,疯癫意味着某种缺席的状态,理性的缺席,人性的缺席。疯癫以一种类似的方式立于理性的对面,成为理性的一面镜子。
最终,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体验:非理性。它既逃避理性,又有理性所熟悉的某种结构。既处身理性之外,又可能为理性所认识和把握。在这个时候,开始把人分为有理性的人和无理性的人。理性在确定非理性并把它推入到虚无之中的时候,理性也划定了自己的范围。人通常是以自己所不是的东西进行反思的。
在16世纪的医学观念中,精神和肉体基本是一个统一体,这实际上有一点类似中国的中医。肉体的变化与性质和精神的变化与性质是互为因果的。躁狂症和忧郁症是与类似体液、干燥、阴冷、粘稠一类的词和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而歇斯底里的起因多半在子宫,疑病症的原因则在胃肠。但它们进入疯癫领域是在肉体空间中的病因学被道德病因学取代以后才发生的。由于歇斯底里是一种有害的元气渗透的结果,那么体质的密度就决定了犯病的可能性。这样当一个人生活舒适、闲散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心灵的松懈患上歇斯底里。
神经疾病开始被赋予道德意义,他们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之中: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炽烈过分的结果,疯癫开始成为某种道德过失的效果。人之所以变疯是由于道德过失受到责罚。至此,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病学就快要出现了。
疯癫的非理性表现瓦解之后,完全被划归道德领域之后,就仅仅成为一种疾病。心理学诞生了,而疯癫将成为它的对象,某种无声的客体。它不再是一种体验的表达,不再是理性的之外的某种知识的可能性,而仅仅是一个可以得到分析的对象。
人们以前认为有罪的,现在无罪,而在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并非“良心的发现”,也不是道德水准的提高,其实这只是由于知识的图景发生了变化,而其中的敏感者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
在18世纪和19世纪都有人抱怨把疯子和罪犯关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然而出发点却恰好相反。18世纪的抱怨是犯人在禁闭所里受到了疯子的折磨,而18世纪的抱怨则是疯子理应得到比犯人更好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抱怨都来自同情心,也就是说都是人道主义的,但却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现实至少说明解放疯子,把他们从监狱中放出来并置于治疗他们的医院之中的运动与人道主义无关,不过是这个运动给自己加上的人道主义幻影。
那么这种意识转变的原因在哪里呢?
18世纪,把疯人和囚犯放到一起,实际上是对囚犯的一种惩罚,疯子既是被压迫的,又是压迫的,既体现了禁闭的可怕,自己又同时是禁闭权力的对象。他有双重的身份。
与此同时,穷人随着经济危机从被禁闭的人中间独立出来。因为经济危机证明了贫穷与道德无关,它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由于穷人的存在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因此他们不仅是无辜的而且是有用的。这样禁闭本身就成为一个错误,必须结束禁闭。问题出现了:如果不禁闭的话,疯子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精神病院诞生了。精神病院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病学的发展是政治的结果,是禁闭以及解除禁闭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并非科学的进步和人道主义的胜利。也就是说,以疯子作为自己的对象领域的精神病学之出现不是人类认识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一个偶然的结果。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偶然和突变,而不是任何必然性。
既然认为精神病的病因在于道德上的缺陷,那么精神病院的首要责任就是恢复或者说建立一种道德体系。这种道德的特征是权威、服从、悔悟。这种道德效应的形成所依赖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使自身客体化。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对话,甚至进行辩论。古典时代的禁闭使这种语言控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在精神病院中这种对话完全消失了,通过用沉默来对付谵妄,使谵妄本身陷入沉默之中。此外,精神病院通过强迫病人自我审视,并且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审判和惩罚。疯子最终不得不使自己对象化,而且这个对象不是自我反思的对象,而是借用他人的目光审视自我所造成的对象化。如果说疯癫就意味着异化,(注:在法文中,精神错乱和异化是一个词aliénation。)那么这种自我对象化意味着双重异化。通过这种道德的强行灌输,精神病院“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注: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253页。)精神病学这门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
在对精神病学学科史的考察中,福柯不是把精神病学的源头放在某一个遥远的过去,他坚决地抛弃了那种追溯源头的历史学。他认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起点上,事物是完美的;它们出自造物主之手,流光溢彩,沐浴着黎明时分无阴影的光照。”(注: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载《福柯集》,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149页。)人们用这种遥远的高贵的源头来为现状进行辩护,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而已。在福柯眼中,精神病学诞生于它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文心理条件,特别是与各式各样的权力相互作用的关系,(注:“精神病学(在19世纪初也许几乎直到19世纪中叶)不是作为医学知识或理论的一个专业而毋宁说是作为公共卫生的一个专门分支来运转的。在成为医学的一个专业以前,精神病学被制度化为社会防护的一个特殊领域,针对的是一切由于疾病或由于所有可以直接或间接当作疾病的东西而进入社会的危险。正是作为社会的预防措施,作为社会整体的卫生学,精神病学才得以制度化的(永远不要忘记法国精神病学专业的第一种杂志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M.Foucault,Les Anormaux,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4-1975,Paris,Seuil/Gallimard,1999.)而不是来自某个遥远的过去,也不是伟大理性运行到这一阶段所必然产生的果实,而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造成的。谱系学就是要恢复精神病学诞生的那一刻它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它决不愿意忽略细枝末节,不在偶然的事件中寻找“历史的必然性”,相反它致力于为一切金碧辉煌的真理大厦建立起其并不那么光明的谱系,如果说达尔文把一只猴子放到了人的起源处,那么福柯就是把依靠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的巴黎总医院放到了精神病学的起源处。这种恢复最让人触目惊心或者说最有批判意义的地方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赖所依靠的知识的根本的历史性,认识到知识与具体政治环境的结合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而这正是对知识本身进行批判的起点,福柯所做的就是找到这个起点,为后来者的批判建立基础。
这本书出版两年以后,在福柯1974-1975年法兰西学院的授课《不正常的人》(注:“精神病学(在19世纪初也许几乎直到19世纪中叶)不是作为医学知识或理论的一个专业而毋宁说是作为公共卫生的一个专门分支来运转的。在成为医学的一个专业以前,精神病学被制度化为社会防护的一个特殊领域,针对的是一切由于疾病或由于所有可以直接或间接当作疾病的东西而进入社会的危险。正是作为社会的预防措施,作为社会整体的卫生学,精神病学才得以制度化的(永远不要忘记法国精神病学专业的第一种杂志可以说是《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M.Foucault,Les Anormaux,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4-1975,Paris,Seuil/Gallimard,1999.)中,他分析了精神病学的变迁以及精神病学在司法和公共卫生领域中所起的作用。精神病学逐步地把畸形的人、所谓不可救药的坏蛋和手淫的儿童建构为“不正常的人”这样一个危险的领域,而自己作为对这个领域进行监视和治疗的手段,从而一方面让自己服务于刑法体系,另一方面让自己利用刑法体系,获取更大的空间和权力。在这样的领域中,精神病学一边建构自己的方法论、分析和学科纪律,构造自己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另一方面,使自己与权力铰接起来,在现代社会中进行运转。
三、福柯的策略
这里,我们所说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一种主要从否定的方面来说的界限。第一点,不直接攻击在学科中得到合法化的知识。福柯几乎从不说精神病学和其他学科说的是谎言或偏离了客观事实,他在其分析的过程中坚持一种外部分析的角度,决不对某种知识的真或不真进行判断。这是福柯的底线,也是其精妙的克制术,因为如果他对某一种学科的知识真或不真进行判断,那么他就会落入这门学科的陷阱,因为无论说真还是不真,都必须假设出一个真的存在,以其为参照系才能进行评判,这无疑会使他不知不觉掉到他自己所批判的学科的窠臼中去。所以福柯才在为自己规定的方法原则中说:“外部性:不是走向话语隐藏着的内部核心,走向在其自身表现出来的一种思想或意义的核心;而是要从话语自身出发,从其表面和合法性出发,走向其外部的可能条件,走向引起这些偶然事件的系列并确定其边界的东西。”(注:M.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Gallimard,1971,p.55.)
第二点,不否认知识也许会进步。福柯的意见是:我们会生产出更多更有效的知识,但是这一点与我的问题无关。对这一问题的回避体现了他对自己的方法的局限性有明确的自觉。实际上,福柯在某些场合还是承认认识论水平是有高低之分的,(注:参见M.Foucault,Les Anormaux,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4-1975,ibid,1975年1月15日和1月22日的授课。)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个问题被他的论述排斥在外。而且福柯批驳了那种认为权力和知识的结合必然会压抑知识和歪曲真理的说法,他认为权力经常是生产性的。在《疯癫与文明》(注: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权力的运用使精神病学的产生成为可能;在《规训与惩罚》中,刑罚权力的运用生产出一系列对肉体进行训练的技术,并运用到军队、学校和工厂等社会各个方面;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历史知识的生产更是权力争夺中的重要赌注之一。
第三点,用权力的小战略代替真理意志的大战略。如前面所说,真理意志的大战略是把知识的整个发展过程纳入一个连续的、从古到今到未来的人类自身发展的战略部署,这个战略的目标就是征服谬误,达到真理。福柯则把知识线索打碎,观察它是如何在与它同时代的权力关系中发挥作用的,而权力关系又是如何作用于它,这样他就用共时的断层研究取代历史的连续性。(注:据此,有人认为福柯是结构主义者,皮亚杰(J.Piaget)在《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中就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讨论。但是福柯自己对此予以否认,而且在这一点学界尚有不少争议。参见莫伟民:《福柯与结构主义》,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年6月。)而在福柯的假设之中权力是一个不存在超历史战略的力量关系,这样,为知识创造条件的,促使某一类知识产生的,不是所谓人类的真理意志,人类永恒的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在某个具体环境中运转着的权力。然而正是在这个地方福柯的思想被误读了,有人提出福柯的命题是“知识就是权力”,(注:参见王冶河:《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载《读书》1997年2月。另参见旷新年:《从界外思想》,载《读书》,1997年6月。)其实福柯的工作就是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它们是同一的东西,研究就是不可能的了。(注:参见福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载《福柯集》,同上书。)
第四点,放弃理论的重建。中国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老话,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它简明扼要地表达了我们赋予思想批判工作的期待和任务,一般来说,当我们批判或看到别人批判一种思想或者体系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取而代之。然而福柯的战略却不是这样,他放弃了理论的重建,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福柯式的对整体知识进行解释的体系,不存在福柯主义。他对思想的任何体系化和系统化倾向保持警惕,“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局部知识……的复兴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权力,这就是无序的、片断的谱系学的计划。”(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3-74,10,26,11-12,4页。)这是一种“游击队”式的风格,他不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话语问题,也决不归纳出他所研究的对象的规律。对福柯而言,社会规律是不存在的,对未来的预见是不可能的,它不过是一种束缚话语并进而束缚人的没有根基的幻想。福柯的工作是“知识的造反”,而且这种造反是永恒的,它并不企图推翻那个旧体系,树立起自己的体系,而是不断地造反,在知识的密林中永远只当一名游击队员。
福柯通过这一系列方法,使知识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知识从匿名的变成具名的,这个具名并不是强调这个知识的所谓发明者,而是强调它自己具体的历史身份,强调它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与权力相互作用时在空间和时间上所处的位置。它是有一个地方的(local),而不是普遍的,笼罩一切的。它总是在生活中,在世界中,对实在的肉体的人发生影响的知识,而不是超然世外,从世界的外部对世界进行观照的知识,这样知识自己的出发点便重新被拉回到生活的世界之中,那种从某个圣洁的地方发出的照亮世界的光束(知识过去的形象)不见了,从而恢复了知识真正的“在人间”的性质。
四、对福柯的质疑
首先,虽然福柯反对知识的自我合法化,反对认为有某种连续的、普遍的知识发展的链条,他要“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3-74,10,26,11-12,4页。)但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在强调知识的局部、不连贯这些特征的时候,作为知识的背景的权力却又反过来变成一个普遍的、连贯的整体,成为某种无意识(注:这里的无意识不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而是黑格尔的无意识的整体理性精神的运动意义上的。)的过程。在福柯对儿童手淫问题以及对后来的乱伦问题的研究中,知识-权力的共谋是这样进行的:权力需要解决大家庭混乱不清的关系,使父母真正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于是就策动一场针对儿童手淫的运动,医生不断地宣称手淫对身体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把各种各样的疾病的病因归之于手淫,对于健康来说手淫成了万恶之首。这样社会就要求父母取消他们与孩子之间的中介(保姆、祖父母、各种亲戚等等)并直接对孩子进行照料和监视。这样,单细胞的小家庭就建立起来了。然而,过于紧密地监视会造成父母对乱伦的担心,并对此产生负罪感。为了打消父母的疑虑,解除他们的负罪感,从而让他们更好地承担起照料和监视孩子的职责,精神分析出笼了,它宣布乱伦的危险不是来自父母,而是来自孩子,孩子对父母的欲望才是乱伦的根源,因此父母可以继续对孩子进行紧密地监视和细致的照料。(注:M.Foucault,les Anormaux,ibid,cours du 5 mars 1975 et du 12 mars 1975.)我们看到在这里,没有以真理意志为基础的“大叙事”,但是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大叙事:“权力的大叙事”,权力成为另一种大叙事的内容和主题,它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福柯在他的论述中说得非常清楚:无论说手淫是万恶之首的人,还是精神分析的发明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是用来让父母与孩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意识到的是相反的东西,他们认为手淫有害是因,父母监视和照料是果。福柯把因果链条颠倒过来,这样就解除了科学知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就制造出了那个无所不能的权力之网,它能够让知识在不知不觉之中,在无意识中为其服务。然而,对这个权力的无意识福柯却没有任何交代,这个不断生产知识的机器的运转机制在他的分析中仅仅只是作为一个隐含的背景存在,这个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连续的,整体性的。虽然他也说要“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进行研究”,(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3-74,10,26,11-12,4页。)但是,权力自己的形态虽然可能是局部的,不规则的,但是它对知识的作用却几乎是规则的和普遍的,而且是无意识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认为人类知识的生产是受着统一理性的运动指引而向前迈进是掉进了知识自我合法化的陷阱,那么认为知识的生产都是在无所不在的权力指引下左冲右突是否也会落入另一个过分强调权力的陷阱呢?
其次,福柯虽然自己小心翼翼,不愿意把自己的谱系学碎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而甘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给它们,强加给它们统一起来的理论的王冠”,(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3-74,10,26,11-12,4页。)但是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统一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但是统一的背景,或者说统一的关系,即知识-权力无所不在的关系是存在的,那么福柯自己的分析话语、自己的某种充满战斗气息的知识话语是与何种权力铰接在一起的呢?因为福柯的话语也是一种知识,一种关于学科诞生和发展史的知识,它来自图书馆、档案、附注、积满灰尘的书、从来无人过目的文章和印数极少躺在书架上直至几个世纪以后才有人拿出来的书。(注: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3-74,10,26,11-12,4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在讲述真理(也许不是大写的真理,而是小写的碎片式的真理),谈论知识,那么福柯与权力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共谋关系之中呢?他所进行的颠覆和批判工作有没有可能在无意识之中为另一种权力技术开辟道路或提供工具呢?既然权力无所不在,而且可以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福柯采取的所有对权力技术保持警惕、对合法化的知识和真理进行质疑的做法都可能同时被另一种权力技术殖民和投资利用,在这里福柯遇到了不可解的问题:对一种普遍的关系进行批判之后,这个关系马上就可以反过来把批判者纳入其中,尤其是在这种关系可以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福柯能够强调自己的策略和谱系学方法可以避免被现存的某种权力利用从而形成对话语的奴役,但是他不可能证明自己可以逃离这个普遍的权力网络,不在这个网络的节点之上。
我们看到福柯在这里进入了一个悖论。他试图以知识来解救知识,以对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和批判来摆脱某种宰制和束缚。然而,在指出知识-权力这张大网是如何无处不在并对它发动攻击的时候,他自己却无法证明自己可以挣脱这张网。这个悖论正好构成了一个对真理和知识追寻和拒绝的游戏,当他追寻的时候,他说,我正是为了拒绝,可是当他拒绝的时候,是否这又成为另一种追寻的一部分呢?
标签:尼采哲学论文; 福柯论文; 疯癫与文明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刘北成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