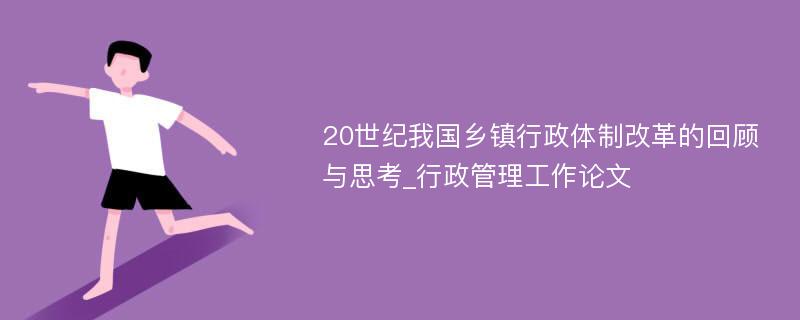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乡镇论文,管理体制改革论文,行政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980(2006)05-0052-09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相继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的矛盾、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的对立,最终导致我国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一百年来乡镇行政体制管理改革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启示。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倡导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
一般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第3页)。但到了清朝末年,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小势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开始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特别是到1850年,中国总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1亿人陡增至4.3亿人[2](第452-471页),这对传统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国家行政权逐渐下移,进一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成为晚清政府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二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统治者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3](第724-741页)于是在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其中府、州、县所在地10万人口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5万人口以上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分别建立“自治公所”,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公共事务[4](第724-741页)。但是,“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5](第463页),“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稀矣”[6](第184页)。而到1915年,袁世凯执政期间即宣布取消“乡镇自治”,开始实行区、村二级制。“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村”名义上仍保留自治性质,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同时,袁世凯还首次把现代的警察制度推向地方基层社会,
“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7](第43-150页)。这表明了晚清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蒋介石执政以后,一方面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了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体系,即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形成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8];另一方面,“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9](第67页),如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10](第612页),“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11](第98-99页)。可见,此时的保甲长们已经被完全警察化和特务化了。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12](第56页)。因此,“民国时期的乡只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13](第297页)。但是,这种“现代官僚制度”与“乡绅经纪体制”相混合的政治怪物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 [8]。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但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区一级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约需686721人,保甲约需 12140908人,三项合计为12992241人”[14](第574-587页)。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12](第50-52页)(即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能力远远低于其经济榨取能力),最终吞噬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总之,不管是晚清政府推行的“乡镇自治”,还是民国时期推行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整合,“代表国家权力的管辖权和规则既没有建立,也没有通过机构的设置贯彻下去,国家并没有改造地方权威的管制原则或取代它的管制权力,从而将地方社会纳入国家规则的治理范围之中”[15](第31页)。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乡苏维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乡苏维埃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的“议行合一制”,是指“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16](第439页),“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以防止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17](第414页)。正如列宁所指出:“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18](第103页)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19](第59页)但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第789页)。
解放战争时期,各大解放区逐步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以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也相继建立,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庞大的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中国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21](第213页),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22]。因此,“从1951年土改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23](第49页),把国家行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制度型权力”的支配体系,从而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
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的《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中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截止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但在这一时期,农民协会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发挥着相当独特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土地改革,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24](第364-365页)。正因为这样,“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底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底层”[25](第86页)。但是,“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26](第231页)。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又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起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27]。总之,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21](第220页)。
三、“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与瓦解
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全国12万多个乡镇和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改组成了2.6万个人民公社,同时还建立了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5亿多农民群众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28](第51页)。这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堪称为一大“奇迹”。从理论上看,“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29](第541页);从实践上看,“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29](第537-538页);从组织形式看,“共产党塑造公社,支配和领导着公社”[30](第237页)。但是,这种规模空前、涉及面极广、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却让世代沿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民群众感到了极度恐慌和无所适从。因此,“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31](第618页)。于是,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农民让步,全国人民公社数量由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正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此后的20多年里,“公社对农民进行以基层政权为中心、为主导的重新组织,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及迁徙活动都掌握在基层政权手里,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也由基层政权支配”[15](第35页),尤其是“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30](第377页)。直到1982年底,全国人民公社数量为54352个,生产大队719438个,生产队597.7万个[32](第366页)。可以说,从1958年公社的建立到1984公社的解体,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或停滞,农民的希望或苦难,都与人民公社制度相关。但迄今为止,“或许是因为一边倒的否定人民公社的舆论已经把公社时期判定为一个错误的时代,学者们很难意识到研究这一时代有什么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30] (第12页)
正如有的学者提出,“人民公社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下去,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去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中国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2]。也有的学者提出,“正是这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利用行政管理的力量,广泛组织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与兴建,填补了旧中国水利设施建设的两大空白:一是兼防洪、灌溉、养殖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大中型水库的修建;二是提水工程的兴修和提水机械的广泛使用。这段时期,农田水利设施兴建的力度是非常大的,20世纪末的中国农村运作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修建的” [33](第170页)。可见,“它单靠人力就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全国建起了上万座水库、几千座小型水电站、几百英里的铁路线,在大江大河上建起了一座座桥梁,开拓隧道,修筑马路,开发了更多的矿藏,灌溉了更多的土地。……以前由多为当地大户人家出身的举人秀才发起修庙、修桥、办学和赈济之类的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领导带头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照顾孤老、改善地方医疗条件、引进水泵或新式犁具乃至组织扫盲活动等等”[31](第610-617页)。
但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30](第200页)。譬如,“截止1978年底,全国人民公社6.5万多个,拥有国家干部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三项合计为4250万人。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却只占全国的5%左右[34](第161页)。总之,“人民公社是一个特别强调原则的时代,其核心是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的教导办事”[31](第435页)。然而,“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而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导致出现了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的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最终使人民公社制度的经济基础发生严重的危机”[34]。直到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11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长年搞饭吃,但国家每年仍需要进口大批的粮食和棉花来弥补缺口。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29](第832页)。因此,“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25](第508页)。
四、“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的确立与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彻底动摇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权威基础,“它甚至无法容忍新兴的社会力量,无法协调和统帅社会”[35](第 211页),“以至造成了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29](第853页)。1982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10条规定:“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截止1985年底,全国共建立了79306个乡, 3144个民族乡,9140个镇和948628个村民委员会、 588多万个村民组[32](第366页)。
最近20多年来,这种“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逐渐暴露出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首先是“旧庙刚拆又添新庙,旧人未走又添新人”。譬如,1983年至1985年的“社改乡”期间,全国增加了36786个乡镇,增加了23万多个村民委员会。若按平均每个乡镇配备20名干部,需要新增加国家干部735720人;若按平均每个行政村配备7名干部,需要新增加村干部161万人。这与当时我国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村级集体经济正走下坡路的现实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于是,从1986年到1996年,全国乡镇数量共减少了19617个,行政村数量也减少了接近10万个。尤其是1998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天撤并乡镇4个,照此发展下去,预计到2010年全国乡镇将减少至3万个左右[36]。“如此大规模的乡镇精简并没有产生激烈的社会震荡,乡镇改革可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并称为农村改革的三大奇迹”[37](第609页)。但随着乡镇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人员共有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1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经济负担占40%左右”[38]。其次是乡镇“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事实上,“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区)、乡(镇)5级政府构成的行政体系,到了最低一级的乡镇时,政府任务和目标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这就使得乡镇一级成为面对上级,且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官僚机构”[39]。从乡镇一级的“财权”看,“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全国的71%。尤其是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只承担2%,省级财政只承担11%,县级财政只承担8%,乡镇财政竟然承担了78%”[40]。因此,我国不少乡镇目前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据农业部199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乡镇一级负债总额为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08万元;村一级负债总额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21万元,农民人均负债374元”[41]。据专家估计,目前这一数字可能已增至6000~8000亿元甚至更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法制和政治体制的不健全,使得各种权力机关和部门‘寻租’行为增多了;乡镇机关和干部在办公设备和经费方面的攀比风气、个人收入方面的‘钢性’原则以及职务和升迁方面的‘棘轮效应’也都表现出来了”[42]。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有无数双“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第三只手”(乡村基层干部)齐刷刷地伸向农民,“有些地区的农村人口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43](第1页)。再次是乡镇“条条”与“块块”分割现象严重。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都把“捞油水”的乡镇站所(如公安、司法、工商、财政、税务、金融、邮电、通讯、电力、医药、烟草、粮食、供销社、盐业、城建、土地等)人权、财权、物权收归上级业务部门管理,而把“花钱不得利”的站所(如农技、农机、水利、畜牧兽医、林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甩给乡镇管理,这样就使乡镇一级政府几乎变成了“空架子”。最后是乡镇“党政一体化运作”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目前,我国乡镇仍未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而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25](第637页)。因此,村民自治既受到地方行政权扩张的压缩,又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基本处于一种行政与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总之,我国下一步如何把乡镇建设成为有“活力、有权威、有效能”的地方基层政府仍是一大难题。
五、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整个20世纪,就是国家行政权不断下沉,并将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39]。但在这一时期,“农业财政来源和财政能力决定和制约着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和走向,也决定着传统国家对乡村治理格局的特性”[39],徐勇教授将其称之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乡村治理体制[44],(第4页)。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儒家的行政体系中特有的反官僚制倾向和行政的疏放性,亦即每个行政单位仅有少数现职的官吏,是由于国家财政上的限制所致”[45](第162页)。因此,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建构的四种新型乡镇行政管理模式都不可能超越“以农养政”时代的两大规律:一是所谓的“帕金森定律”,即“官僚机构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一般规律性。因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是官僚机构发展过程中惯有的通病”[46](第87页);二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即“历代中国的税费改革都是将杂费归并到正税中一起征收,但每次取消杂费后,又会孳生出新的杂费,反而会加重农民的负担,最终形成了‘积累莫返之害’”[47]。正如马克思所提出:“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发展。”[48](第305页)
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为此, 2005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整合事业站所,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49]。这是我国下一步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新定位,也预示着一场规模浩大、波澜壮阔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序幕拉开了。那么,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历史演变的基本经验与教训有哪些呢?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中国的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却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过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50](第166-167页)。实际上,早在1940年代,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中国要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51](第168页)。因此,“20世纪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丢掉了中国!”[21](第213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从当初 50多名党员且处在秘密状态的小党,发展到现在成为一个拥有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7000多万名党员且在13亿人口大国执政的大党,关键就在于通过“制度型权力”重新建构了当代中国农村的权威结构。可见,“我国现代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在彻底打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国家机器之后,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乡镇组织。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9](第88页)。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可能对我国下一步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认识不清或产生误解。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是“弱化”还是“强化”、是“自治化”还是“行政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的基本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因此,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国家角度,从中国的国情特点出发,积极探索如何建设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使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与乡村治理结构实现有效的对接,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根据西方政治学中的公共治理理论,实行地方基层政府的“善治”,是建立现代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制度保障。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一般都是从便于行政和便于居民参与本地管理出发,综合考虑了历史、地理、民族诸因素,根据一个基层行政单位能否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确定的” [52](第341页)。这是因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得越深坏处越多,将使基层活力泯灭,甚至发展停滞;而地方行政区划规模过大,又将导致政令不通,行政效率低下。而保持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适度规模,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满足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制度基础” [53](第164页)。因此,“乡镇”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政府运作程序的规范性1541。尤其是目前我国总人口的63%、劳动年龄人口的60%、老年人口的66%、少儿人口的70%都居住在农村,如果急于撤销乡镇的行政建制,那么势必将给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麻烦。总之,我国下一步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本乡镇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地方基层政府”[55]。
其次,要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综观世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56]。为此,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57](第23-24页);“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57](第131页)。关于这一点是绝不能含糊的。因此,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必须克服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否定党的领导,使村民自治工作放任自流;二是党的组织不尊重法律规定的村民的民主权利和村委会的职权,包办代替”[57](第132页)。其实,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与扩大基层民主并不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使之成为统筹协调各方和整合乡村社会政治力量的“龙头组织”。应当认识到,“村庄是生产性的和建设性的”,只要真正体现了“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即让农民自由、自主、自治的活动),善于把分散的个体农民自愿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就能使基层党组织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
最后,目前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是“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进入20世纪的一百年,我国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之所以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其根源就在于:一方面缺少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法律法规,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对所有上级部门交办的事情,哪怕人力、财力不够也要勉为其难(即“对上负责”);另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是靠农民自己解决,而乡镇一级政府自身又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根本无法履行其应有的职能(“即对下负责”)。因此,我国下一步更多涉及的是对整个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财税制度、户籍制度、农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诸多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有可能将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再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历史经验和现实存在的问题都说明了,中国农民并不需要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组织,但是需要他们可以进退自由的互助性、服务性组织,如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联系全国的专业组织,能够反映农民诉求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农民自己的组织或有社会各团体和志愿者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可以填补政府职能的某些空白,有的可以为农民提供成本更低、更优质的服务。这是我们在改造、规范各级政府职能同时所要进行的另一项长远和重大的举措。”[42]也就是说,通过“第三部门”可以弥补“政府失灵”的制度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机制缺陷,“而目前我国发育新的农民中介组织资源和促进传统组织与新发育组织两种资源有效对接的最大限制因素是,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尚未解决,各级政府决策层在组织创新方面的政策供给严重不足”[58]。一言以蔽之,我国迄今尚未建立起“民主化、法治化的现代农村政治制度;开放、公平的现代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科学、文明的现代农村文化制度;赋予农民各种权利的规范的现代农村社会制度”[59](第8页)。这是“十一·五”期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收稿日期:2006-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