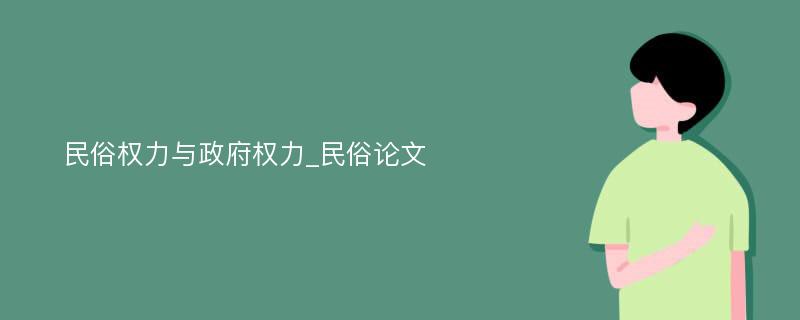
民俗的力量与政府权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论文,权力论文,力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俗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俗努力将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观念纳入规范的维度之中;另一方面,是以传统的力量捍卫传统。在现代社会,这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一
民俗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关于“应该做什么”,举一例子:现代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工业已很发达,月饼随时可做、可售、可吃。但是,平时人们很少吃月饼,市场上也很难见到月饼,临近八月中秋,人们便蜂涌至商店争购月饼。只有在中秋的月色下,人们才能充分享受到月饼的美味和过节的乐趣。在民俗的维度之中,人们的生活在不断重复,延续成模式化的生活,这使得人们对未来的日子有了预见和期待,生活变得更有规律和意义,社会趋于安定和祥和。关于“不应该做什么”,可以人的“欲望”加以说明。欲望是人的本能要求,但作为“社会的人”,又必须对欲望进行某种抑制。这种对欲望的抑制,便是禁忌。如果没有欲望,也就无所谓禁忌;而有了禁忌,并不意味着欲望的消失。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看来,“这些禁制可能和具有某种强烈意愿的活动相互关联。它们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随着禁忌的维持,那种原始的,想从事禁忌事物的欲望依然继续存在着。他们对禁忌事物必然采取某一种矛盾的态度。在潜意识中,他们极想去触犯它,可是,却又害怕这么做;他们恐惧,正因为他们想做,只是恐惧战胜了欲望”[1]。人们很可能已经觉察不到与禁忌相对应的欲望,因为它们已被深深地嵌入潜意识当中。一旦禁忌瓦解,那么欲望就会穿破意识层次而付诸行动。
一些传统民俗在今天社会中还有力量,或者说,现代人有时不得不随俗而行,主要是受到民俗规范力量的惯性冲击。传统民俗的规范力量对社会较多的人来说,更多是无清晰意识效应的惯性,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2]民俗的规范性是一种与法律并存但不一定一致的惯性形式,它不是靠明确的条文,而是靠人们的习惯心理和群体力量来维系的,具有一种威力很强的惯性动力。民俗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一般不属于命令式的强行指派,它也要求一统,但这一统,是潜移默化、循循诱导式的。
民俗是一种民众中传承的文化传统,其核心就是传统,其传播又是在复制、更新和强化文化传统。对传统的依附和眷恋是人类的本性,一旦有人肆意破坏传统,便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詹姆士·O·罗伯逊(James Oliver Robertson)曾对神话这样界说:“没有经过任何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考,我们就接受了许多意象、观点、行为模式、象征、英雄、故事、隐喻、类比和解释,简而言之,即神话——这一切是存在的,使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符合逻辑,易于理解。”[3]显然,这里的神话可以置换为民俗,因为神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接触、感受到的人类最早的民俗形态之一。在人类文化意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神话作为一种原生态的文化意识,演化并构成了人类文化意识的意象原型。这些意象原型反复出现,奠定了人类文化意识的理性基调和现实的倾向性。
二
民俗作为一种传统的力量,总是作用于一定的民众群体,或者说,一定的民众群体总是建构、流行自己特色的民俗惯习,或行为模式。这使得民俗带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色彩。然而,民俗的“民”即一定的民众群体并没有将“俗”当作某种权力资源,或有意识地使用民俗固有的规范力量,只是一味地顺应这种规范力量。因此,自然状态的民俗规范力量不是对生活的强加,而是被融入生活模式之中,在特定的时空里营造生活范型。
民俗要进入现代社会的控制系统,必须走出民间,突破“一定的民众群体”的边界,成为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异在。远古时期对大自然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对图腾的禁忌等等,曾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现今社会早已转化为相关的法律、政令。可以说,法律、政令以及种种的乡规民约,都是禁忌在文明社会的变异存在。在整个社会控制管理系统中,禁忌和法律、政令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禁止”的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要求得稳定和安全,首先是要确定和告诫人们“不能做什么”,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宣扬该有的行为。法律和政令显然是继承了禁忌的结构模式,只不过将口承范式置换为书面范式。传统是结构,是符号,是思维和阐述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禁忌本身的结构形态“禁令—违禁—惩罚”从民间传统延续到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它使得人们的行为和思想越来越理性化。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系、法律体系、思想体系、行政体系和教育体系其实都是在演变或深化禁忌的结构形态。只不过这些“禁令”不再来自民间自控又自动的系统,而主要由上层权力话语系统发布。
远古社会,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主要诉诸于民俗的浇铸。家庭、学校乃至监狱出现后,这些组织和机构以建立社会规范和规范社会为己任,尽力使社会规范功能得到发挥和扩张。社会规范由于得到这些规范机构的推行和强化,便变得强硬起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学校、工厂等机构“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却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4]。民俗滞留于民间,对群体中人一视同仁,意义和作用是共享的;对群体外人而言,亦无任何损害,是一种牢固的文化边界。这种自然状态的民俗,便远离了权力话语系统。而一旦被政府部门所利用,即成为被转化的权力。
同时,过去许多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民俗礼仪,也逐渐为上层社会所利用,甚至被一些权力机构所操纵和管辖,民俗的规范力量由民间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及行政机关。
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农耕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早期的农业生产,一是依赖“天公作美”,二是依赖有生产经验的人的传授与管理。为使农业生产取得硕果和生产技艺得到传授,老人被人尊重并逐渐习俗化,加上人们对血统和家族集体利益的重视,孝的观念和行为不断强化,孝俗形成了。这种深入人心的孝敬老人的习俗,统治者或精英们不会让其永远停留于民间或者说是“俗”的层面。于是,孔子在创建儒家学说时,将孝俗加以理性的概述和礼仪的控制,构成了儒家思想孝悌的核心之一。1949年以后,孝敬老人尤其是孤寡老人又成为国家民政部门的职能。民政部门运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向需要救助的老年人提供帮助。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成为政府的行为。
按照米歇尔·福柯的现代权力观,知识与权力有关,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5]。民俗作为模式化的行为规范,其展示的过程显然也是在实施权力。然而,拥有民俗的民众从来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并不认为民俗知识与权力有瓜葛,从来没有把民俗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否则,民俗就不是民俗,而是妨碍人们正常生活的桎梏。而民俗一旦进入权力机关,便拥有权力力量。于是,原本在家族内进行的孝敬长辈的各种民俗仪式活动,演化为民政部门和上级领导对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问寒问暖。家族成员的孝敬行为转化为政府行为,政府变得更有亲和力,提高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仪式空间突破了家族或家庭的范围而得到急剧扩张,孝与被孝的亲情之间的关系延展至一般的人际关系。一方面,政府吸纳民俗知识而使自己的权力话语更能为民众所接受,权力的展示更具渗透度;另一方面,民俗进入主流话语系统,获得政府权力的支撑,便超越了原本的民间生存空间,大大扩展了势力范围,加快了传播速度。
三
任何民俗活动都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具有强烈的展示性。过去,民俗表演和民俗力量的释放主要集中在神庙、祭祀场、竞技场等公共场所。人们常常在这些公共场所所表演、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等,举行场面宏大的公共仪式,所有的人都是仪式的参加者。此时,所有的能量在瞬间聚集、释放,人们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民俗的规范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似乎威力也更为强大。民俗的集体性又表现在人们互相监视民俗的实施情况,每一个人的民俗行为都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违背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大家都会将他拽回民俗的轨道上。
现代社会,民俗的展示性的仪式过程已经被权力机构所掌握,群众性的仪式场合变成了政治集会和各种宣传活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外交话语等在集会仪式上被反复宣讲,并通过各种传媒瞬间输入千家万户。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远古时期规范社会的特征是,“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到少数对象”,但是,现代社会的机制恰恰颠倒过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6]。在主流话语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民俗行为的自愿、自主与自在变成了人为的规训。民俗的规范力量被权力机构所利用而更为强大,形成为严密的规训机制。“一定的民众群体”为全民所取代,特定群体的规范演化为全民的规训。所谓的民俗的“民”正急速地被分化和被肢解,传统的民间群体所剩无几,群体与群体的壁垒已经坍塌,群体中人随时可能变成“流民”。散落在各地的人们每天睁着眼,看电视里面一大群人的集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会大多在建有主席台的封闭式的特定空间里进行。民间集体仪式则大多在露天举行,显示出官方集会所无的开放性特征。
即便如此,民间仪式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正在发生转换,甚至在急剧萎缩。“有着强烈狂欢精神的庙会和娱神活动,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7]。这是前近代时期法律规定相对放宽的情况。经受所谓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原先盛行于民间的带有潜在颠覆性和破坏性的集体民俗活动,被权力话语系统所颠覆和破坏。与此同时,民间娱神的狂欢名正言顺地转换为国家政治狂欢,民众的狂欢精神早已被国家权力所巧取和利用。一部分民俗的力量便被权力机构挪移过去,得到前所未有的合理利用。现代人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依附于传统的民俗空间,易于达到全新的张扬。
四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社会行动区分为四种类型:(1)目标合理的行动,即能够达到目标,取得成效的行动;(2)价值合理的行动,即按照自己信奉的价值所进行的行动,不管有无成效;(3)激情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4)传统的行动,即按照习惯而进行的活动[8]。在传统社会中,后两种行动占主导地位。而在工业社会中,前两种行动占主导地位,而且只有这两种行动才属于合理的行动。相反,“严格的传统举止——正如纯粹的反应性模仿一样——完全处于边缘状态,而且往往是超然于可以称之为‘有意义的’取向的行为之外。因为它往往是一种对于习以为常的刺激的迟钝的、在约定俗成的态度方向上进行的反应”[9]。民俗行为自然属于传统的处于边缘状态的行为,肯定要被合理的行为所左右。而且,“目标”和“价值”皆由权力系统所定性和把握,传统的民俗行为为了变成合理的行为,争取生存的空间,有时便不得不迎合这些“目标”和“价值”,甚至有意纳入到“大传统”的范畴之中。有一些民俗已然失去了自我,如对青少年的教养习俗,在内容和形式上已为权力系统所控制。现在中小学教科书已很少采用民俗的内容,课堂上引进了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授课方式离传统民间的口传心授越来越远。在现代社会,有些民俗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它们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和自由,其规范力量自然难于充分展示出来。
对民俗事象活动过程的干预和介入,是相关权力机构的权力。传统所构筑的可以吸纳广大民众参与的活动空间,历代统治者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加以控制和利用。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民俗发展本身的需要,民俗一旦形成,即成为自控又自动的运动系统,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其规范力量同样可以得到充分释放。仍以禁忌为例,利奇说:“人体的排泄物或分泌物普遍地构成严格禁忌的对象,尤其是粪便、尿、精液、经血、剪下的头发、指甲屑、体垢、唾液、母乳等。这是符合这一禁忌理论的。这些物质在最根本的方面是模棱两可的。……既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由此形成的禁忌极为强烈。”“人形化的神灵、圣母、超自然的半人半兽妖怪,这些边缘性的、模棱两可的东西被赋予介乎神人之间的力量。有关他们的禁忌最为强烈,甚至超过了神灵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范畴引起人们给以极大的关注,并抱以最强烈的禁忌情感。”[10]英国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也认为凡处于模棱两可状态的动物便是不洁的、禁忌的;属于禁忌范围的物体都是带有两义性的因而无法明确归类的东西[11]。但她在这种“两义性 = 禁忌”的基础上再向前深入了一步,力图考察人类分类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所禁忌之物并非在于它们本身是污秽的或圣洁的,而在于它们的“位置”。它们是混淆了人类采取分类体系或与之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说禁忌物是社会分类系统的产物。
任何分类体系都不能将所有的事物涵盖进去,总有一些事物处于边缘的模棱两可的状态。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就人本身而言,比如说,中性人或说阴阳人、同性恋者、心理变态者、艾滋病人等皆属于分类体系中的另类,他们是人,可又不是完全“正常”的人,是介于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怪人”。尽管这些“怪人”不具有“神”性,由于受宣传和传说的影响,他们也被赋予某种邪异的力量,在许多人的心里产生恐惧之感。故而他们便成为禁忌的对象。
这些禁忌的对象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背离了传统的关于“人”的标准和看法。对“怪人”的禁忌,是要努力维护人的正常性。试想,如果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禁忌之人,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些禁忌之人似乎与法律、道德无涉,也就是说,法律和道德并不排斥和诋毁他们的存在,而禁忌的存在,却使人们和他们保持距离,惟恐自己与他们为伍。尽管我们提倡同情与关爱,但禁忌则迫使他们竭力隐瞒自己的身分,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生存的空间。禁忌的力量似乎在维护人类的所谓“纯洁”。
尽管民俗发展的“动势”本身就有自我调整的本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价值观念的更新,一些具有悠久历史且传播惯性极强的民俗事象很难及时自我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生成环境。这样,民俗的规范力量便与时代要求相抵触,政府权力机构的干预势在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