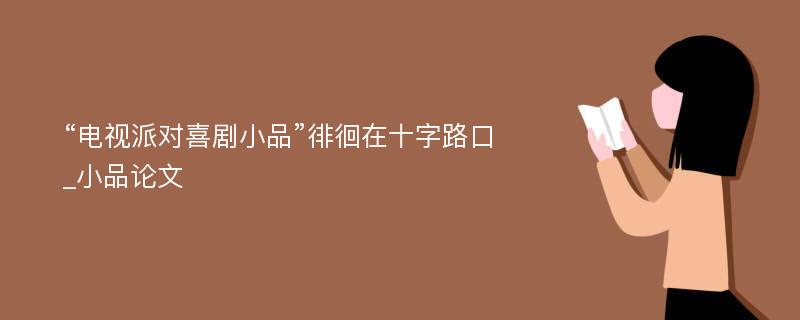
徘徊于十字路口的“电视晚会喜剧小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口论文,小品论文,喜剧论文,晚会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短暂辉煌小品史
八十年代,是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大模大样地登上中国的艺术殿堂,舒展身姿,写下第一页独立历史的年代。
早在六十年代之初,当时还相当年轻的两位导演王扶林、俞玮就试图将戏剧院校用于教学和考核的“小品”搬上年轻的中国荧屏。1964年,由《球迷》等十多个喜剧小品组成的《笑的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举轰动京华,可惜,人民欢畅的笑声并未使它幸免于大批判的厄运,中国最初的表演性小品的寿命竟然与其名称同样短促。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当小品再一次冲出考场和讲台,登上荧屏和舞台时,早已淡忘了历史的观众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它欢呼致意。
如果说文革前的昙花一现是中国“电视晚会喜剧小品”的“史前史”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上半期则可以说是它真正的“启蒙期”。
八十年代初,王景愚、游本昌将西方传统的哑剧与中国传统杂技中的小丑表演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哑剧小品”,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屏幕,揭开了新时期“电视晚会哑剧小品”的序幕。
紧接着,夏钧寅、澹台仁慧和陈佩斯、朱时茂分别将王景愚等人的独人哑剧小品变成多人话剧小品,将话剧教学小品从考场和课堂搬上表演的舞台,首开新时期话剧小品之先河。特别是陈佩斯、朱时茂的系列小品,从1984年的《吃面条》到1985年的《拍电影》,再到1986年的《卖羊肉串》,通过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走进千家万户,最早将“喜剧小品”这一名称响亮地提到全国观众面前。
以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晚会喜剧小品”进入了红极一时、恣肆汪洋的“繁荣期”。1986年9月是一个巧合的月份,在这同一个月里,陕西和天津两地不约而同地举办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两场喜剧小品比赛:“陕西省首届喜剧小品电视表演赛”和“天津市青年幽默喜剧小品大奖赛”。两场比赛都是采用现场打分和电视播出的办法,不同的仅在于,陕西是现场直播,天津是录像转播。天津一连搞了两届,陕西则抓住不放,每年一届,一直延续到1992年10月的第七届。自此,陕西、天津以及东北继北京之后,成为新时期中国小品艺术重要的创作和表演基地。
在上述各地的推动下,1987年6月,中央电视台主办了“全国首届专业戏剧小品电视比赛”。1989年11月,文化部群文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举办了“‘南开杯’全国业余话剧小品邀请赛”。1990年10月,全国总工会、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全国首届职工话剧小品比赛”。1990年,北京和上海也分别开展了“首届业余戏剧小品电视比赛”和“全国戏剧小品征稿评奖活动”。至此,“电视晚会喜剧小品”的创作和比赛从几个基地迅速推向全国各地。晚会小品一经电视媒介传播,立刻出现万人空巷、争相观赏、街谈巷议的热潮。对戏曲、话剧,甚至电影、相声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厌倦情绪的中国当代观众,用慷慨的掌声、笑声、赞词和选票对晚会小品表现出久违了的热情,从而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小品热”。
大约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电视晚会喜剧小品”进入了一个艺术上的“徘徊期”。尽管先后涌现出《吃鸡》、《吃面条》、《超生游击队》、《相亲》、《大米与红高粱》、《张三其人》、《追星族》、《延安情》、《如此包装》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和王景愚、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黄宏、赵本山、巩汉林、潘长江、赵丽蓉、郭达、杨蕾等一批知名度相当高的小品明星,但广大观众对近年来晚会小品的艺术质量缺乏创新的状况已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有的甚至发出了种种使人瞠目的呼声:
——喜剧小品压根儿就称不上艺术;
——喜剧小品走红是中国戏剧甚至整个文艺的悲哀;
——喜剧小品毁了一批演员;
——喜剧小品好景不长,马上就会消亡……
站在这股舆论潮头的弄潮儿,不但有一群以“高雅艺术”卫道士自诩的评论者,而且居然还有那么几位恰恰是靠喜剧小品红遍全国的影视剧演员,他(她)们的现身说法不仅增强了讨伐喜剧小品的力度,而且似乎也加强了其感染力和可信度。
然而,奇怪的是,弄潮儿、卫道士和现身说法者的征讨不仅没有使“喜剧小品热”降温,反而使喜剧小品越炒越热,成为众望所归的喜坛盟主,成为一台电视晚会不可或缺的主角,甚至开始形成一种独立的喜剧艺术样式。
从历史长河来看,任何一种艺术样式都有可能经过形成、发展、兴旺到衰落以至灭绝的整个生命历程。对口词、三句半已经大体走完了这一过程,昆曲则正在依靠人工输氧,艰难竭厥地维持生命。喜剧小品将来也许有一天同样会面临这种悲剧命运,但至少今天人们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或衰亡都有其自身的基本规律,这就是看它是否能够顺应当代观众的大众审美心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喜剧小品之所以至今仍不降温,正是因为它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凝练性、瞬间性或片断性、精巧性、喜剧性)消解了中国观众对熟悉的艺术样式和僵硬的艺术模式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疲劳,顺应了种种大众审美心理和审美趋势(例如求新求异、追求快节奏、寻求娱乐、要求倾吐心声等),成为中国当代戏剧革命(市场化、现代化)和喜剧启蒙(本体化、现代化)的一名马前卒。
因此,我以为,“电视晚会喜剧小品”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目前恐怕不是如何为之送终的问题,而是怎样丰富、完善,使之持续兴旺、再领风骚的问题。
二、前方四股冲击波
声言喜剧小品“好景不长”,有可能“自行消亡”的观点,尽管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但却从一个侧面向少年得志的喜剧小品发出了警报:前方有四股冲击波,谨防触礁!
第一股冲击波来自喜剧小品本身。
喜剧小品自从由教学小品的母体脱颖而出之后,便开始了复杂化和异化的过程。
所谓“复杂化”,主要是指其内容。教学小品一般选取生活瞬间的某种情绪,而喜剧小品则往往发展为某种情节,篇幅也有所扩展。
所谓“异化”,主要是指其形式。教学小品一般仅选用话剧本身的某些基本表现手段(如语言、动作),而喜剧小品则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各种姊妹艺术形形色色的表现手段(如曲艺、影视、歌舞、杂技等),逐渐形成自己所特有的复合性表现手段体系。
正是这种复杂化和异化使教学小品迅速地脱离母体,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然而,九十年代以来,这两种趋势出现愈演愈烈的苗头。
首先是小品的凝练性和片断性受到挑战。一部分喜剧小品篇幅越拉越长,情节越搞越复杂,“小品”开始大踏步地向“小戏”靠拢,小品原本具有的独立的样式规律、美学特征和巨大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有鉴于此,我以为应对“小品”与“小戏”加以明确区分,比如说,能否从以下四个角度对“小品”所进行的规范来对二者加以基本的划分:
其一,从选材上讲,小品一般选取比较小的题材,即凡人小事,力求以小见大。
其二,从结构上讲,小品注重展示情绪、性格的某个侧面以及性格之间的撞击,而不刻意追求性格、情节、冲突以及起承转合的完整性。
其三,从构想上讲,小品力求截取生活流中符合小品要求的瞬间或片断,注重提出问题,不注意解决问题,注意写情绪的大起大落,不注重写性格的大起大落。
其四,无论是就剧本创作还是就表导演的二度创作而言,喜剧小品比较靠近生活,忌讳“编”和“演”的明显痕迹。
在有些喜剧小品向小戏靠拢的同时,另一些则在向相声以及其它曲艺形式(例如二人转)靠拢,这同样有可能抹煞小品自身的特质,从而取消小品继续独立存在下去的价值。
喜剧小品和相声确实具有一些彼此渗透的相似之处,如喜剧性、袖珍性、通俗性、交流性(指与观众的默契合作、情感交流)等。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从而使它们成为两种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的艺术样式:
其一,在结构上,相声呈现出明显的松散性,喜剧小品则具有较强的凝聚性。
其二,在表现方法上,相声以叙事性为主要特征,喜剧小品则以动作性为主要特征。
其三,在艺术手段上,相声已出现明显的程式化倾向,而喜剧小品则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喜剧小品向小戏、相声、二人转的大幅度靠拢是喜剧小品迷失自我、丧失优势的表现,这就不能不使其部分痴迷者发出失望的悲鸣。
第二股冲击波同样来自喜剧小品本身。
对喜剧小品来说,娱乐性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不仅是通向目标之桥,而且是安身立命之本。八十年代,在斩断时时悬在中国喜剧头顶上的“纯娱乐论”这柄“达摩克利斯剑”方面,在为喜剧艺术以至整个艺术的娱乐功能正名方面,喜剧小品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大约也是从九十年代起,这位常胜的暴发户开始骄傲起来,它片面地总结了自己成功的经验,企图以一俊遮百丑,似乎只要能让观众发出笑声,不管是什么样的笑声,便是成功。于是,庸俗、粗俗、低俗之风迅速蔓延,低级趣味和无聊之作趁虚而入。连有些知名度相当高的喜剧艺术家也不例外。前些年,他们曾经以自己生气勃勃的小品艺术征服了十几亿苛刻的中国观众,为华夏喜剧创造了笑的频率和电视收视率的吉尼斯纪录。然而,近年来,为了让观众发出廉价的笑声,他们不惜“赤膊上阵”,从硝烟滚滚的炮筒中钻进钻出,甚至恨不得走下台去胳肢观众。其结果,观众在发出生理性的笑声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告别了艺术性的喜剧。
第三股冲击波来自其它姊妹艺术。
正当喜剧小品沉醉于胜利的喜悦高枕无忧的时候,其它姊妹艺术却怀着深深的危机感,认真借鉴喜剧小品的成功经验,纷纷与现代传媒之娇子——电视联手,创造出“相声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以及“情景喜剧”等崭新的复合性艺术样式。如果说前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声电视小品”、“音乐电视小品”、“舞蹈电视小品”有所探索(尽管其探索未必就一定成功)的话,那么,梁左、英达联袂创作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则是对“电视系列小品”(仍指用电视进行传播的小品)的一种新尝试。
与此同时,一种真正电视艺术化了的,即以电视镜头语言进行创作的“电视喜剧小品”也应运而生。我在本文中称之为“电视晚会喜剧小品”的那些作品,尽管由于它们是整台电视晚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具有重要结构意义的组成部分,因此不能说完全不具备电视艺术的因素,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应该说只是借助于电视这一媒体进行传播的舞台喜剧小品。而从八十年代末以来,以天津电视台导演俞玮的《哈哈集》栏目为发端,中央电视台以及广西、江西、陕西、西安等省市电视台相继推出一批有一定质量的电视艺术化的“电视喜剧小品”,如《烟》、《安琪帽》、《有一个青年》、《孤岛》、《怪圈》、《礼尚往来》、《中国历代笑话系列短剧小品选》等。尽管由于喜剧小品的电视艺术化难度较大,实践时间尚短,又缺乏大型晚会、特别是春节晚会的高收视率效应,因而至今尚未出现象《大米与红高粱》、《超生游击队》、《吃面条》这样为广大观众认可的代表作,但鉴于它拥有电视所独具的众多艺术和技术手段,其崛起与发展,同其它博采众长、励精图治的姊妹艺术一样,对晚会小品实现了不容轻视的冲击和超越。这与晚会小品的原地踏步、自我重复甚至陷入模式(赵本山也许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第四股冲击波来自广大观赏者。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观赏者,就总体而言都是“喜新厌旧”的。现代的观赏者在艺术审美中往往有一种带一定盲目成分的求新求异欲望。中国大陆上多年的政治封闭和文化禁锢造成了几个作家、几个样板戏和几种模式统治了十亿人十年的荒唐历史。一旦开禁,多年积累起来的审美疲劳便驱使人们以近于疯狂的逆反心理,抵制一切陈旧的、钦定的、灌输性的、模式化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这种厌旧厌同的普遍心态同现代人的求新求异心理一拍即合,成为新时期大多数观赏者的一种重要审美趋向。
当年,喜剧小品第一次冲出地平线时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这种观赏心理。喜剧小品至少在两个方面吻合了这种需求。一方面,它以一种与人们谙熟的多种艺术样式有所不同的形式出现,使人耳目一新,于是观赏者面对过分熟悉的艺术样式不由得产生的审美疲劳顿时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每一个小品不过十分钟左右,还没等观赏者产生疲惫感和厌倦感,另一个小品又以全新的场景、形象和风格呈现在他的面前,于是,新鲜感立时重新攫住了他。
而今天,这种喜新厌旧的观赏心理又成为一种不利因素,对坐吃老本、缺乏新招的喜剧小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喜剧小品走红的时间持续得越长,观众的期望值就越高,这种负效应就越大。因此,喜剧小品想要不失去自己的观众群,至少保住那些比较稳定的喜剧小品迷,就决不能滥用他们的偏爱和信任,过分寄希望于他们欣赏的惯性,而应正视自己近年来自我陶醉所造成的停滞不前局面,恢复当年第一次冲出地平线时的那种“突围意识”和爆发力,对自己、对姊妹艺术、对广大观赏者,勇敢地实现第二次冲刺。
三、“喜剧小品”何处去?
喜剧小品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它曾经给予相声及其它姊妹艺术所造成的挑战和威胁,就像是杂技演员甩出去的“飞去来器”一样,绕场一圈之后,今天又落到了它自己头上。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次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登上新高峰的机遇。
声言喜剧小品即将寿终正寝,是对大众审美心理的误断;而不承认喜剧小品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看不到若处理不好则有可能出现危机,同样也是对大众审美心理的漠视。无论误断还是漠视,都不利于喜剧小品这一新兴艺术样式的健康发展。
喜剧小品将会向何处去?其主动权归根结底掌握在喜剧小品自己手里,具体来说,掌握在喜剧小品的各位创造者手里,其中既包括实践者(第一创造者)——编导演,也包括评论者(第二创造者),甚至还有观赏者(第三创造者)。因此,喜剧小品的新生和繁荣,将仰赖于这三个方面军友好的、理智的、有效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