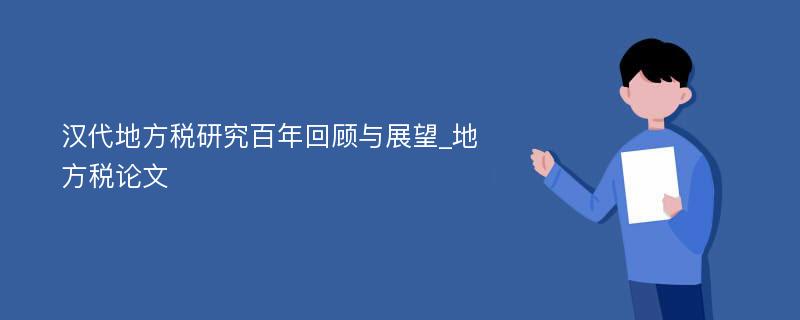
近百年来汉代地方税研究的追溯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税论文,汉代论文,近百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5)02-0084-08 地方税作为地方政府行使职责,中央或地方根据一国税收管理制度规范,地方司职征收管理的税,收入全部由地方政府管理使用。 汉代刚成立时,诸侯国的税收管理权限独立自主。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可知,中央授予诸侯国征税权,诸侯王国在向中央缴纳献费以外,所有收入皆由诸侯王自行安排使用。表明汉代早期有地方税的存在。 地方税的制度及施行状况,影响着对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社会阶层关系。汉代的许多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主张轻徭薄赋。《汉书·西域传》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农本①。晁错称,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工②。但囿于时代局限,传统史学未能全面深入探讨地方税的外延与内涵。20世纪之后,国内外学者就汉代地方税展开深入分析,取得累累硕果。此处就汉代地方税史的研究文献展开评述,供诸位学者探讨。 一、汉代地方税史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及主要特征 回首汉代地方税的百年研究历史,可归纳出所经历的3个特色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乃1920-1949年。 此阶段乃中国传统地方税史学向近代地方史学衍变的时期。学者运用传统地方税史学的研究方法,关注考据历史文献,辨识制度规定之时,也逐步导入西方财政学理论,对汉代地方税展开全新评判。胡钧③、徐式圭④、常乃德⑤、刘秉麟⑥、杨志濂⑦、刘不同⑧在考据古代文献之时运用近代财政学理论,阐释汉代地方税的税种、税制要素、地方税收征管机构、地方税收监督,但专门研究汉代地方税的学者较少,援引文献多取自古典书籍,欠缺实地考证与出土文物的印证。但也有一些别具一格的研究,周筠溪认为,汉代地方税税收收入乃专款专用,存在一定的流用,为实现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地方财政会使用准备金、开源、增税、专卖收入、募捐、发行货币、流用。地方税收管理机构中,封君乃地方税收管理者,诸侯王的税收管理机构为少府,税收管理者为郎中令,丞相对地方实施税收监管。存在财政收支法定、官员自给、横向转移支付、税收监管不力、官员职责不清,地方税权日益扩张⑨。 马非百提出,汉代地方税中,地租有田赋、藳税、假税,人口税(丁税)有算赋、口钱、献费,更赋(免役税),杂税有财产税(訾算、牲口税)、所得税(息租)、鱼税(海租、鱼税,水官负责征收),工税、关税,市租、车船税、酒税⑩。 加藤繁指出,汉初,地方可自主征税,后地方征税只可用于诸侯王衣食(11)。 许宏然归结汉代吸取秦灭亡经验教训,实施轻税,征收地方税赋依照量出为入原则,不以敛财为目的(12)。 黄君默依税负的转嫁与否把汉代地方税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有田赋、户赋、口赋、算赋、军赋、更赋、杂税。间接税有算缗钱、六畜税、算车钱、关税、杂税、權酤、盐铁(13)。 罗振玉、王国维(14)引发了研究简牍的风尚。学者不断考证敦煌汉晋木简,如张凤(15)等。到1930年间中瑞西北科考团挖掘出居延汉简后,更丰富了研究证据。为汉代地方税研究供应了珍贵史料。劳干更从汉简中论证汉代地方税,取得了卓越成就(16)。 此阶段对汉代地方税的专题研究较少,多散见于汉代税收制度研究之中,但内容还是十分丰厚,从汉代经济社会、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地方税关联层层展开,视野开阔,观点鲜明,且将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研究方法运用其中,其研究理念为后来新中国汉代地方税的研究者继往开来,发展成汉代地方税研究的主导潮流。 第二阶段乃1950-1978年。 此阶段的研究具有3个特质。 第一,汉代地方税作为专门的研究主题较少,多数研究乃在探讨朝代更迭、农民战争、土地所有制、户籍制度、田赋制度时提及地方税。这主要是因为地方税的产生、发展和衍变是与其时的政局、经济社会结构紧密关联。同时,学者多使用马克思主义创新史学展开研究,多探讨地方税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关联,对汉代地方税的研究较为浅显。 第二,对重要的汉代地方税收制度展开创新的理论探索,研究汉代地方税时注重动态化、关联性。李剑农指出,汉初诸侯王与诸侯对辖区内居民有征税权,彻侯有领地,但无权征税,从公赋税中领取奉养,关内侯不拥有领地,无权征税,并阐释了地方的主要赋役制度(17)。韩连琪认为,田租与刍藳税作为不同的税种,通常一道征收,共同减免,田租定额征收,征税形式是货币、布帛或谷物。封君食邑不是依照户数征收,而是依田亩数征收。还探讨了算赋、献费、算赀、算缗钱、徭役的征收范围、纳税时间、税收征管(18)。 丘少伟、郭焕珍直指盐铁专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补充地方军事资金,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便利地方人民生产生活(19)。 卢南乔探讨秦汉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爆发原因乃苛重的赋役,严厉的刑法,具有反抗封建地主剥削的性质,又有反抗农奴压迫的性质(20)。 裘锡圭就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展开考释,对汉初算赋、口钱、刍藳税等的征收范围、计税依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方式进行重新审视(21)。 其他学者也就汉代地方税及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专卖制度的关联展开分析,所探讨议题在1980年代以后依然为研究热点。但仍欠缺汉代地方税的专门论述,对地方徭役制度、商税制度、山川园池之税的研究也较为少见。 第三,学者对汉代地方税展开广泛的资料搜索和深入细致的思量,成果正处于厚积薄发之势。此阶段的学术研究,引发改革开放之后的专业研究层出不穷。 第三阶段乃1979年至今。 此阶段汉代地方税研究兴旺发展,在4个方面有着明显的突破。 第一,发掘与运用大量的新资料和新方法,汉代地方税研究的日益兴旺。虽然在古代文献与官方官修正史就汉代地方税的论述不少,但很多相互抵触,挂一漏万,特别是汉代地方税具体运作的史料更稀缺,造成汉代地方税研究的混杂,真伪难辨。学者体会到新资料对汉代地方税研究的重要价值。1970年代末后,伴随汉代文物、古迹的大量发现,官方记录的公布,民间文献诸如地契、族谱、家谱的面世,汉代地方税研究的新资料不断挖掘,汉代地方税研究日新月异。 陈直考释居延汉简,论证居延屯田采取包租制,纳税人为个人,税收管理官员有农都尉、护田校尉、别田令史、候农令、农府佐、仓长、仓佐等。管理代田的官员有代田长、部农长、都垂、农亭亭长(22)。 伍德熙考释简牍,对汉代口赋的纳税人加以界定。地方啬夫负责征税(23)。 李恒全对张家山汉简进行考证,得出刍藳税与田税为不同的税种,田税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课征,刍藳税按顷课征(24)。 杨志贤考证张家山汉简,地方诸侯国税收管理组织比照中央,由丞相和御史大夫分管政务和监察大权。丞相之下设一内史,掌管地方谷帛财货,凡地方内赋税皆上报内史。又设一少府,掌管诸侯财政,收山海池泽之税,以为诸侯私藏。以法律形式确定租税管理。各种会计簿籍,分类登记田租、户赋、盐税、矿产税及工商税等。下级政府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经济收支情况及各种财政文书(25)。 黄今言从张家山竹简看两汉初期的税赋,认为户赋与赀赋的用途都是供给军费的开支。户赋为人口税,赀赋为家庭财产税(26)。 于振波从简牍考证,户赋乃独立税种,按户征收,缴纳形式为实物与货币,刍藳税依田亩面积课征,以交纳实物饲草为主,供给本地需求(27)。 陈伟将松柏47号木牍《南郡卒更簿》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相对照考证,推断西汉前期普通卒更曾施行三更制,一般民众要担当卒更,属于地方税赋的一种(28)。 朱德贵就长沙走马楼吴简推断,僦钱为转运税,乃政府定期征收的税种,地僦钱账簿为记载临湘侯封地转运税征收情况的总账簿(29)。 张荣强从《二年律令》推论傅包括正卒兵役和徭役,皆为地方税。(30)。 贾鸿经《二年律令》推断,西汉时期户赋不涵盖口算钱,也不涵盖刍藳税,乃独立于田租、刍藳税的税种。户赋与刍藳税的征收对象不一,户赋征收对象为户籍,刍藳税征收对象为授田。征收范围不一,卿以上不征收田租、刍藳税,卿以下交户赋。征收标准不一,户赋1年31钱,刍藳一顷1年55钱。征收形式不一。户赋以钱和刍作为征收形式,刍藳税以刍和藳为征收形式(31)。 第二,不断从更多层面、更多视角践行研究,拓展了汉代地方税研究的内涵外延,推断出汉代地方税的衍变发展规律和格局。 1.汉代地方税内容的见微知著。 由于各史料详简不同,真伪难辨,汉代地方税研究中有不少困顿,汉代地方税内容乃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周伯棣诠释西汉的列侯封君有权在封邑内课征租税,来为其生活提供费用。列侯封君课征的租税中,有户赋,依照户来征收(32)。劳干(33)认为户赋、军赋、献赋是与口赋、算赋乃并列税种。孙翊刚、李渭清(1984)提出汉代封国的地方税有辖区内征收的田租、户赋、市租与山海园林池泽税。田租有按田亩数量课征,也有按田亩产量定率课征。户赋乃封国对辖区内民户课征的一种税,是封君的食租。市租是对市肆中商贩取得的商品营业额课征的一种流转税。封君封地里的市肆,对商人课征市租(34)。付志宇(2011)认为山海园林池泽税是对山、海、江河、湖泊、草原、池塘、园圃等的产物为征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山川园池市肆的税收收入,为封君的私奉养(35)。陈锋指出汉代有临时性田赋的附加税,受灾时有按受灾程度给予的田赋减免(36)。李恒全、季鹏考证汉代刍槀税乃以实际田亩数量为计税依据征收(37)。晋文认为刍税优于藳税,更赋的关键乃在于出钱代役(38)。王彦辉指出汉代财产税征收对象为正常税目之外的动产、不动产,征收范围持续扩张,财产税逐渐常态性征收,以平赀为基础定额课征(39)。马怡认为,汉代的小徭役乃地方政府征用的规模较小的力役(40)。温乐平对徭役类型、服役对象及减免进行考释(41)。张荣强主张,汉代税收征管时间中的“计断九月”,乃依照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粟的成熟时间而定(42)。上述文献多从微观视域展开汉代地方税史的求证,推动着汉代地方税的细致化研究。 2.汉代地方税的动态研究。 高敏分析汉初、文景时期刍、藳税制度的变动,刍、藳税也可用货币形式缴纳,刍税从依田亩的好坏征收,发展为按户征收(43)。 臧知非论述西汉田税征收方式承袭于秦朝,实施定额征收,按顷计算、按户课征,从实物缴纳转变成实物、货币皆可且以货币为主的缴纳形式,刺激了汉初商品经济进步,也使个体农民加速破产(44)。 丁光勋指出,傅乃正卒兵役,汉初承袭秦制15岁起傅;汉景帝2年,改为20岁起傅;汉昭帝时,改为23岁起傅,56岁免傅。但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会调整始傅、终役的年龄(45)。 李梦泽指出汉初地方有监郡御史,监管地方税。但监郡御史对地方税监督力量不断弱化,后重新设置刺史与司隶校尉,强化了对汉代地方税的监督(46)。 上述研究多局限于某一方面,需要增补研究内容,但从动态视域探讨汉代地方税还是值得嘉许的研究视域。此类研究文献帮助人们更深刻地把握汉代地方税萌动、发展规律。 3.汉代地方税和经济发展、社会衍变的交互作用。 此乃更广博的研究视域,此视域偏重汉代地方税变动与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联,理论思辨特征较为浓厚。 朱德贵指出,封君财政管理中,汉初,诸侯王、列侯各有封地。封君可在封区征税、役使刑徒劳动。中央政府逐渐限制诸王、列侯的财政权限。剥夺了诸侯王的治民权、财权。授予封国征税权,但武帝将盐铁收归官营后,禁止王国铸造钱币,防范封君私奉养的规模。封国的继承由中央决定,还限制王国擅兴徭役、侵占公地等。汉代封君的财政权限逐渐萎缩,最后封君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只能够衣食租税,地方税逐渐减少(47)。 袁秀华、周长山认为,中央派出朝廷使者——刺史对郡国守、相进行监督,致力于户口增殖、流民防止,从而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有效地获取(48)。 刘华祝指出,汉代土地私有制盛行,地主向佃农征收的地租按田亩产量的50%征收,具有产品直接分配性质,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征收地税,税率乃三十税一,计税依据按照历年田亩面积、贫瘠肥沃程度、产量的常量而定,以实物谷米为征收形式,还兼征刍藳税,具有产品再分配性质(49)。 臧知非考释,西汉前期工商业主经由授田制度取得山川林泽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以“占租”的方式自行申报缴纳定额税,农民的租、质、户赋、园池税实施按户按顷定额缴纳,且以货币缴纳为主,表明汉代矿产资源丰富,开采活动发达(50)。 姚澄宇认为,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兼有国有土地,因而农民在面临重税赋的情况下,难以保有其土地,土地兼并严重(51)。 张信通指出汉代为保证赋役制度的实行,汉代政府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凡政府控制的户口皆由乡官里吏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记录在户籍,具体涵盖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5个部分,被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称作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相应赋税和徭役、兵役(52)。 上述文献从政治、工商业与户籍制度的视角研究地方税,论证了地方税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关联,有助于全面认识汉代地方税。 4.汉代地方税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汉代地方税反映了地方政府同编户齐民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关系,汉代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法律与经济地位。汉代征收地方税之时,怎样对待不同的社会阶层?纳税人、负税人分别是哪个社会阶层?实际税负如何?地方税的经济效应怎样?社会效应如何?公平与否?效率如何? 臧知非提出,汉代土地私有化,农民实有土地数不同于应纳税土地数,政府向农民征税的数量标准相同,而农民实纳税额看地方官员的征管景况,实际征管程序相当繁复。井田制的十一而藉与十税一的税收负担率大致相同(53)。 朱德贵指出,汉代的田租税律少缴、漏缴田税者施以惩处,以儆效尤;田税征收中对达到一定爵位等级者有减免(54)。 饭尾秀幸认为西汉初期,地方税收益丰厚,在西汉后半期,中央逐渐削弱地方税权(55)。 胡寄窗、谈敏指出,汉代地方采取清静无为的课税原则,着力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56)。 杜树章认为汉代田租轻、人头税与徭役重,人头税税率日益提高,徭役让民众不堪承受(57)。 陈登原以为汉代坚持田税税负低,但豪强尽享低税好处,平民百姓税负依然沉重,不仅要缴纳谷税、藳税,还要负担税官的乱收费(58)。 渡边信一郎提出,更徭作为地方力役乃服役者在县内从事劳动。社会性劳动编制与租税的征收相同。编户百姓缴纳的田租、算赋、口赋、过更钱等租税,由地方征收、保管,以献费形式上交中央财政(59)。 孙文学坚持汉代地方税对农业重视力度大,相机减免农业的田租和赋税,对商人课以重税(60)。魏莹发现,商人若不如实申报收入和财产,会被罚没财产,检举人则被奖励给一半的罚款(61)。 可以发现,虽说汉代地方对农业施以轻税,但农民依然负担了多数税负。对商业施以重税,但商人可经由购买爵位的方式享受税收优待,未达成税收公平。为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强化地方税收监督,但带来经济滑坡。汉代地方税未实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但地方政府还是使用一定手段,缓和社会阶层对立,维护政权稳定。 第三,研究议题日益开阔,不仅对汉代地方税和土地制度、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户籍制度展开相关探讨,还开展了很多补漏之作,更加深了对汉代地方户赋、徭役、市租的归总。有关户赋、刍槀税、口钱、地方税征管、地方税收监督的研究,在1979年以前较少,但1979年后,这方面的研究拓展不少。高敏经由张家山汉墓竹简考证户赋乃将口钱、算赋的按人头收的“赋税”改成按户出税、把按顷亩入刍的刍税改按户征收,改变了征收方式,是对有爵位的人的优惠,以户赋入钱为中央税收,不属于私奉养的经费;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租、质、户赋、池入钱属于中央税收,山川矿产税包括煮盐、采银、铁、铅、金、丹等矿产税,从价或从量比例征收(62)。李伟认为,口钱同于吏奉、缮兵、传送、给转费,乃地方政府运作资金来源(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吏奉是发给百石以下小官的工资,传送是用于运输物资的徭役,缮兵用于地方军队建设维护,给转费作为运输费用有着特定用途(63)。钟一鸣主张,诸侯王有租赋收入权,可征收口赋、算赋,用于诸侯王领地的公务开支,山川园池市井租税收入作为诸侯王私人开支的来源,诸侯王有权征发兵役、力役。中央对诸侯王施行规范的上计制度监管其税收征管,严肃惩处随意调整税负的诸侯王,诸侯王要向中央上交献费。诸侯国有权任命内史、司农、少府、长史,管理本领地的税收征收管理(64)。黄今言指出,汉代地方税收主要监督赋钱、粮谷、守御器、兵械,有按月、按年、按季度或不定期的监督(65)。 这些研究丰富了汉代地方税研究内容与研究领域,有助于明确认识汉代地方税的税种,税制要素、征收管理与收入去向。 第四,在不断学术研究累积基石之上,出现了一批标志性学术成果,汉代地方税研究步入鼎盛时期。陈梦家的《汉简缀述》(66),详细论述了汉代地方税务官员的职位职责,学术价值非凡。马大英的《汉代财政史》(67),对汉代地方税收收入、税收管理论述全面。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68)对戍卒、屯田、赀产税、上计制度、名籍制度展开细致归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撰的《居延汉简甲乙编》(69)、谢桂华等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70)为汉代地方税研究供应了丰富的考证史料。钱剑夫的《秦汉赋役制度考略》(71)、高敏的《秦汉赋役制度的考释》(72)、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73)对汉代地方税进行了深入阐释。 二、前瞻与思忖 20世纪以来汉代地方税发展曲折,经由多层面、广方法的探讨,体现了汉代地方税的丰富内涵和宽泛外延,取得了显著的突破,但汉代地方税依旧需要学者的持续研究,要不断搜寻并使用新的研究资料,加强有关工作探寻。 (一)继续使用经济学与财政学理论探索汉代地方税 恰当的理论运用关联着汉代地方税研究价值,就汉代地方税研究的百余年历程来看,需进一步采用当代的经济学与财政学理论展开探讨。已有研究涉及汉代地方税到底存在与否的争辩,地方税乃地方具备管理权限的地方性收入,有学者以为汉代乃中央集权型国家,地方税征收机构乃中央直属机构,没有地方税,无视汉代成立之初郡国皆有,诸侯国有征税权,存在地方税。吴王辖区有铜山,可铸造钱币,汲取海水煮盐,财政收入丰厚,无需征税,表明诸侯国也有免税决定权。汉武帝后,诸侯国依然有权征管衣食租,存在地方税,只是地方税收收入绝对值下降。就算在郡县,地方政府征税后,在发生特殊情况时如灾荒,仍有权安排支出,具有对税收一定程度的支配权,表明郡县仍对地方税有一定管理权限,只是管理权限较小而已。另外,汉代地方政府间还有转移支付,汉代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会向地方政府拨付资金、物资,为纵向转移支付。郡国之间还存在资金、物资的横向流转,为横向转移支付。若否认汉代地方税的存在,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也不会存在,这就会隔断汉代地方税与近现代国家地方税间的历史关联,也无法诠释近现代国家地方税的合理性。如采用理性姿态,认可汉代地方税的存在,则又需应对新的疑难:汉代地方税涵盖哪些税种?在汉代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地方税的合理规模多大?地方政府如何对经济社会地位各异的社会各阶层拟定合理税负?汉代地方税中哪些税种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哪些税种劳民伤财、激化社会矛盾?汉代地方税负如何,在汉代地方生产收入中的相对规模怎样?这些疑难皆需潜心测度考证。有学者认为汉代地方税收负担小,有学者以为汉代地方税收负担大,到底大还是小?需严密论证,不能随意下定论。深入研究此类疑难,会使汉代地方税研究更科学、合理,对当代更有借鉴价值。又如,汉代地方政府实施重本抑末的税收政策,但征收的结果却是商人富有,农民贫困,竞相舍本逐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从商品经济的供求关系入手,也表明对商人、商业实施重税更多是出于财政目的,而调整经济结构目的并未达成。需要进一步探讨汉代地方政府对商人、商业征税的目的及征税的经济影响。 (二)需强化实证量化分析 学者一直都在关注汉代地方税史的量化研究,研究成果颇丰。于琨齐论证汉代地方田租采用分成制为基础的定额征收,计税依据乃平均亩产量,考证了汉代地方田租税率有什五税一、三十税一,但对地主为官者的实际税率仅为1%,对普通农民则高达50%(74)。周国林测算了汉代的田租标准,以为汉代亩租额为通常为1斗5升(75)。汉代地方税有按人头、按户、按田亩征税,怎样比较不同征税方式的税负,对农民生活影响怎样,经如何市税推测汉代地方商品经济水平,这些疑难学者皆有论述,但观点各异。地方税作为一种地方政府与辖区民众间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乃数量关系,需加强实证量化分析,才能对汉代地方税的规模、税种、税制与地方社会生产力、地方民众生活等重要议题展开科学合理的探讨。但实证量化分析需大量的数据,税率、计税依据、度量衡、亩产量、物价、生活成本等,各地皆有异,因此要坚持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尽力从史料中攫取符合汉代地方社会生产力、地方生活境况的真实数据资料。 (三)踊跃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 汉代地方税作为实实在在的社会活动,涉及地方所有民众,但以往研究多侧重于考证地方政府税收制度,较少再现地方税实际缴纳流程,特别是基层乡一级社会的税款缴纳、服役的具体情状再现。未来此方面的探索,期盼有新资料、新线索的补充,也要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吴天颖就汉代买地券考证汉代地租率乃见税十五,即50%,让人们对汉代地方的地租、地价有所了解(76)。钟一鸣提出,汉代存在地方税收竞争,诸侯王国有权自行征发兵役与徭役,徭役负担低于郡县,诸侯王国在财力充沛之时,可不征税或少征税,甚至在民众践更时提供补贴,郡国的人为逃避重税,转而移居到低税的诸侯国,郡国要抓捕移居者,诸侯国还会与郡国对抗,表明地方政府间有税收竞争,税收竞争的结果是低税地吸引了更多劳动力,地方综合竞争力提高,威胁到中央统治的稳定性(77)。吴世明、王勇由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中出土的夫人玉印及家啬夫印封泥,推墓主可能生前乃外诸侯国南越国分封于桂林郡的相当于侯一级官员的妻子,且外诸侯可获取相应地方税收收入(78)。袁延胜考证汉代县级算赋文书天长纪庄木牍《算簿》中的事算,发现徭役和算赋的纳税人相同;《算簿》中复算数目在算赋总额占比为1/10,显示汉代地方复算人员众多;《算簿》和《户口簿》的统计表明,汉代算赋纳税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1/2;《算簿》中8月份和9月份的算赋数额,分别为八月户口核查与地方税征管期限截止于九月的计量结果(79)。此类论著虽不多,但反映了如进一步采用新史料、新视野、新理论与新方法展开汉代地方税研究,一定能让汉代地方税所体现的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生动如灵。 ①(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28页。 ②(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5页。 ③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63-89页。 ④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46-59页。 ⑤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纪书局1930年版,第79-96页。 ⑥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5-158页。 ⑦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第167-196页。 ⑧刘不同:《中国财政史》,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版,第187-204页。 ⑨周筠溪:《西汉财政制度之一斑》,《食货》,1936年第3卷第8期,第8-36页。 ⑩马非百:《秦汉经济史资料(七)租税制度》,《食货》,1936年第3卷第9期,第9-33页。 (11)加藤繁著、萧正谊译:《中国社会史概述(一)》,《食货》,1936年第5卷第2期,第12-24页。 (12)许宏然:《秦汉社会的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第10-29页。 (13)黄君默:《两汉的租税制度》,《食货》,1936年第3卷第7期,第30-35页。 (14)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日本京都东山书社1914年版,第26-49页。 (15)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二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版,第135-146页。 (16)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213-224页。 (17)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145页。 (18)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繇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第49-67页。 (19)丘少伟、郭焕珍:《桑弘羊舌战群儒——读〈盐铁论〉》,《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3期,第47-51页。 (20)卢南乔:《从秦汉农民起义、农民战事的特点来看历代农民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诸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第51-62页。 (21)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第49-63页。 (22)陈直:《居延第一批汉简与汉史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34-38,51页。 (23)伍德熙:《居延出土〈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简牍考释》,《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第19-28页。 (24)李恒全:《汉初限田制和田税征收方式——对张家山汉简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2-131页。 (25)杨志贤:《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初会计管理制度的发展状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12页。 (26)黄今言:《从张家山竹简看汉初的赋税征课制度》,《史学辑刊》,2007年第2期,第3-10页。 (27)于振波:《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槀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2期,第151-155页。 (28)陈伟:《简牍资料所见西汉前期的“卒更”》,《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23-35页。 (29)朱德贵:《长沙走马楼吴简“僦钱”、“地僦钱”献疑》,《商业研究》,2008年第12期,第192-194页。 (30)张荣强:《〈二年律令〉与汉代课役身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5-41页。 (31)贾鸿:《〈二年律令〉所见西汉“户赋”制度》,《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52-54页。 (32)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98页。 (33)劳干:《秦汉史》,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6年版,第36页。 (34)孙翊刚、李渭清:《中国财政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35)付志宇:《中国财政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3页。 (36)陈锋:《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4期,第5-13页。 (37)李恒全、季鹏:《秦汉刍槀税征收方式再探》,《财贸研究》,2007年第2期,第79-84页。 (38)晋文:《商鞅变法与秦国田租的征课——兼论秦汉“纳粟拜爵”与“更赋”的起源》,《秦文化论丛》第十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9页。 (39)王彦辉:《论汉代的“訾算”与“以訾征赋”》,《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57-75页。 (40)马怡:《汉代的戍役》,载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24-725页。 (41)温乐平:《西汉初期徭役制度新证》,《学术交流与动态》,2004年第6期,第53-56页。 (42)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0-93页。 (43)高敏:《论两汉前期刍藳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14-116页。 (44)臧知非:《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论——对张家山汉简的初步研究》,《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第143-151页。 (45)丁光勋:《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第51-55页。 (46)李梦泽:《两汉地方监察制度研究概览》,《中学历史教学》,2008年第4期,第80页。 (47)朱德贵:《地方财政管理》,《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7页。 (48)袁秀华、周长山:《西汉刺史设置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分析》,《政府与经济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49)刘华祝:《关于两汉的地租与地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52-56页。 (50)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释析——兼谈西汉前期“弛山泽之禁”及商人兼并农民问题》,《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26-33页。 (51)姚澄宇:《论秦汉土地所有制形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第50-53页。 (52)张信通:《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籍》,《安顺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58-61页。 (53)臧知非:《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兼答李恒全同志》,《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63-70页。 (54)朱德贵:《〈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田租税律”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96-99页。 (55)宫宅洁:《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战国秦汉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6期,第26-21页。 (56)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192页。 (57)杜树章:《中国皇权社会的赋税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58)陈登原:《中国田赋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59)渡边信一郎:《汉代国家的社会性劳动的编制》,载于(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7-312页。 (60)孙文学:《中国财政思想史(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113页。 (61)魏莹:《中国古代赋税徭役(上)》,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62)高敏:《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21-122页。 (63)李伟:《从凤凰山汉简看地方财政税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第83-87页。 (64)钟一鸣:《西汉诸侯王之财权考述》,《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9-13页。 (65)黄今言:《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第18-24页。 (66)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67)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68)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 (70)谢桂华、李均民、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71)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72)高敏:《秦汉赋役制度的考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67页。 (73)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74)于琨奇:《两汉田租征收方法与数量探析》,《安徽史学》,1995年第1期,第1-5页。 (75)周国林:《汉代亩租额稽核》,《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5-102页。 (76)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15-34页。 (77)钟一鸣:《西汉诸侯王之财权考述》,《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9-13页。 (78)吴世明、王勇:《论西汉初年的外诸侯》,《求索》,2007年第8期,第215-216页。 (79)袁延胜:《天长纪庄木牍〈算簿〉与汉代算赋问题》,《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5-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