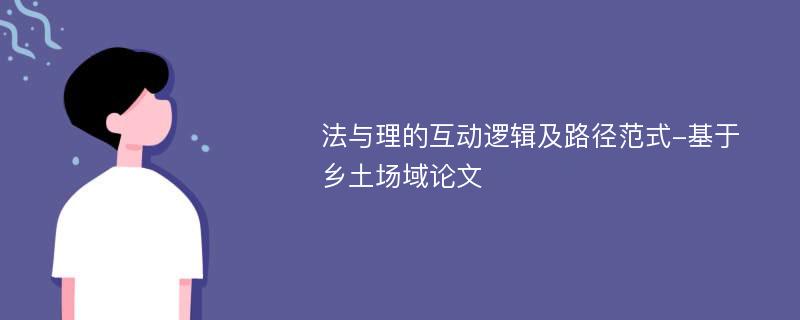
法与理的互动逻辑及路径范式
——基于乡土场域
刘 俊*
内容提要: 法理是由法到理解决社会诉求的应然路径,凸显对国家法的扩充性解释,属于由上至下的模式;理法则是先理后法地调适乡土场域纠纷矛盾的地方思维模式,旨在强调民间情、理、法的逻辑关联,彰显由下至上的习惯与国法的有机整合。国家在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时,乡土场域下的村规民约等习惯法也应纳入法治的系统范畴。国家的法理思维与地方的理法知识应抹去博弈态势,彼此尊重,取长补短,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 法理 理法 国家法 民间法 乡土场域
法理与理法在本文的研究中既有概念的指涉,更侧重于由法到理与由理至法的路径解析,立足于静态的词义分析和动态的路径构建,在静与动的样态结合中离不开两大场域,即国家场域与乡土空间。在国家的层面,法理系国家制定法思维,围绕正义、民主、公平、效率等法理学学科视野下的社会性法理,凸显国家法中 “理”的层面属性。一般的运行逻辑是先法后理,当法难以阐释社会问题时,再将与法精神相关的 “理”的诸元素作为裁判的考量,在西方部分国家即判例,在我国主要表征为司法解释。在乡土场域,“理”有别于国家法伴生的社会之理,与国家场域下的理的话语阐释体系差异较大,其彰显的是乡土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独具的话语体系和规则。同样,与国家法由法官或司法职员、律师队伍的专业解读不同,乡土之 “理”由地方法杰或精英人物、权威人士进行灵活运用。乡土之 “理”既有村规民约的涵义也囊括习惯法或民间法的约束性规范。从法对社会秩序进行控制的价值层面上,期望能对社会的任何场域都能进行调适。事实上,由于社会秩序的多元,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存在多维样态。法并非万能之策,只是不可或缺之国器,特别是在特殊的具有不同民族习惯习俗和历史传统的乡土社会,“理”反而比法的适用更为亲切、更为灵活,演绎的是先理后法的适用路径。但无论是哪一种路径范式,都以公平公正解决社会问题、保障社会主体合法权益为逻辑旨归。国家法既要尊重地方性知识的 “理”性元素,乡土场域解决社会问题的“理”的方法运用也不能以违反国家法为前提,两者应发挥各自优势,除却路径适用的 “范式位阶”之争,合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法理思维与自下而上的理法模式助推国家的良性之治,实为良策。
一、二元范式的 “理”描
范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框架中,率先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后逐步被社会科学重视。在不同领域的学界研究中,范式既作为一种技术分析路线,也指无论是理论探寻还是实证研究中运用的规范方式。本文关于法理与理法的逻辑分析,其实就是两种技术路线的范式研究,既有动态的路径梳理,也有静态的面向阐释。
(一)法理的路径范式
法理的范式研究主要立足于法理学的学科维度下进行,无论是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等都在探寻法理的真谛。什么是法理,或法中有无理,是理性之维还是道理、情理之径,学界至今仍旧在争论中。张文显教授认为:法理,指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在一定意义上是法的渊源。法理作为法的渊源,目的在于弥补法律规范的空隙。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即: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从词源或语法结构上,法理即对法的条文、规则进行扩展性解释,将法的知其然进行知其所以然的深描。在研究的维度上,有对宪法体制、司法体制、立法体制展开宏观论述,也从价值法则、政治法则、程序法则等横截面阐释,最终都离不开关于如何保障人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辩论。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宪政还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从法的概念、理论、体系、运行方式、惩罚手段等都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广泛宣示、表征和凸显法的权威性、普遍性及强制性。尽管从孟德斯鸠、卢梭、洛克、霍布斯等到后来的哈特、德沃金、富勒、哈耶克等从法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功能等层面进行辩护,特别是卢梭从契约论的角度论证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即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只是人民为实现最大福祉的公共载体,国家自身没有权力。国家通过人民的授权制定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然国家制定法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社会现象,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秩序的多样性决定了国家法对社会控制的有限性。卢梭指出:除了根本法、公民法和刑事法以外,还存在第四种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法——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们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①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基于此,需要从判例、司法解释、学界理论甚至抽象的法的精神高度进行法的 “理性”说明或理论补救,从而保障国家法在自上而下适用中的权威。在这样的语境中,法理之 “理”与民间的道理和情理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畴。前者基于强大的组织机构和行政资源对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分配,标榜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在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法治系统中彰显法是治国利器;后者相对国家法的刚性而言渲染更多的是非法的思维下的 “道理”和 “情理”,重于从特殊的民间场域规避国家法的介入进行社会秩序的调适,在国家法可以包容的空间内融情于理,将民间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国家法干预之前。然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乡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中依赖的是民族习惯习俗或习惯法、民间法,国家的法理话语在地方性的复杂民族知识体系中没有太多的 “救济市场”。
法理除了在国家的政治性宣示外,特别重要的是司法中的扩张性解释及裁判中的弹性考量。夏勇认为:人们总是习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结构方式来思维。社会规则特别是法律,是要靠语言来阐明的,而语言又具有模糊诡异的特性。这样,法律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语言与逻辑的艺术。法理说理既是法官自我认同的表现,也是当事人和公众认同裁判所必须的,更是司法裁判在法律框架秩序内回应民意的重要手段。法官运用法理说理,可将法理融于法律方法之中,对得出裁判规范的过程进行解释、考量和论证,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法理说理应辅以修辞学方法,充分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心灵、情绪和情感因素,以增强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和可接受性。② 夏勇:《什么是法理学?》,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156.html,2018年10月28日访问。
(二)理法的认同逻辑
关于为何和如何将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HPM基础理论探讨有两场报告.报告10“有关如何在数学教育中运用数学史的分类框架:一项实证研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20个中学HPM课例,建构了将数学史融入数学课堂教学方式的分类框架,报告2“以巴赫金的对话视角置身及研究历史和数学教育”是一种对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研究的元分析,用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论点支持对数学教育研究的反思,从对话的视角来思考研究者、参与者及数学史之间的对话互动.
在乡村社会,有很多繁杂琐碎的村民事务或纠纷是法律难以调整的,即便通过诉讼的方式,抽象的条文和法官话语抹去了关键问题的复杂背景,条文的适用与具体案例的背景有很大的差距,仅仅依靠法的是与非难以达到村民对诉求期许的内心平衡,法始终代替不了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的 “理”的阐释只有通过精英人物才能解读,便于执行。因为精英人物属于乡土知识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具有解决纠纷的双重思维,既可以运用国家法的乡土话语解读和说服纠纷当事人,满足国家法在乡土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和空间,也尊重乡村民间的习俗。换言之,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人物运用 “理”的思维有效润滑了上到国家法权,下对乡土地方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的传统规则,灵活运用了法理与理法的双重标准和原则,⑧ 李庆真:《变迁中的乡村知识群体与乡村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尽管更多的是扬 “理”抑 “法”。村民宁可信任 “理”的解说,也不完全走国家法介入的救济程序。在特定的乡土场域,“理”具有 “法性”,理代替了法的调适功能,法却难以发挥理的润滑作用。因此,无论是法还是理,关键是公平的解决问题,法的刚性也许解决了形式上的诉求,但村民内心是不服的,即没有理的部分介入,这样的方式依然隐含诉的瑕疵。而在理的话语场域,当事人会顾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尊严、社会舆论、利害关系等,这些元素国家法不会纳入分析,其适用的固化甚至死板,与理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形成鲜明反差。但法的强制性和权利义务分配的权威性是 “理”不能媲美的,法的公正抹去了与法无关的要素,更为纯粹;“理”通过法外的要素 “威胁”当事人的调解或妥协就范,牺牲了一定的公平性。因此,法与理在各自的话语中都有其优点,各美其美。“国家法”与 “乡村理”应有机融合,兼顾权威与地方性知识,尊重习惯法的适用空间,共同发挥两者的合力,美美与共。
1、积极推进国土资源“一张图”建设。我们要加强第二次土地调查等专项调查和数据库建设,并按照统一标准来加强数据的整合、分析和提炼。同时,建立数据更新制度,不断增加信息数量、提高信息质量,做到资源状况“一览无余”,做到资源家底“心中有数”。对于支撑监测监管、决策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各类数据必须集中汇交,并一定要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及时进行数据更新和记录。
惟实干方可书写青年担当。青年人身上所富含的拼搏精神、挑战意识、创新因子等特质,必将对国之重器施与生生不息的动力,也必将深刻地影响新时代的进程与走向。
(三)法理与理法中 “理”的差异性解释
法理与理法是 “一体”的,一体性特质表现在两者的渊源区别,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权利义务为中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法有其产生的依据、主体、程序。法通过草案提出、审议、表决与通过、公布等路径生效,提供社会主体行使行为的参考,而且附属权利义务。在法产生过程中,蕴含其中的理主要起到解释或阐释的作用,以原则性、规则性、灵活性进行相应的调适。理的产生不需要国家制定,也不借助于国家机构的载体,不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理是人们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积淀,是在社会中逐渐形塑的地方话语规则。除却权力要素和公共属性的社会之理外,乡土社会的理有地方性 “法”的属性。由于两者都产生于国家话语下的场域,前提是一样的,因此具有 “一体”的特性。而差异的隐喻凸显法与理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同质性的特征体现在两者都发挥共同治理社会的功能,都以利益调整的公平化为其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但 “一体”并非完全相同,也有异质的特点,法产生于国家严格的立法程序,适用的范围更广,具有强制性;理针对不同的地域体现不同的特点,具有适用的差异性,没有强制性,更注重伦理道德的融入。
二、法理的应然路径——防止国家法的绝对一元化
不少不法商人受利益的驱动,利用餐饮废弃油脂进行非法提炼,加工制成地沟油,低价卖给饭店、宾馆作为食用油回流到餐桌。餐饮废弃油脂发酵变质后含黄曲霉素、苯等有害化学物质,长期食用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引起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致使癌症患病率大幅度提高。有些饭店、宾馆、单位餐厨垃圾被畜禽养殖户收运后未经消毒、灭菌等无害化处理直接作为饲养畜禽的饲料,这样容易引起畜禽感染病毒产生,再通过食物链的传递作用,使人体感染口蹄疫、肝炎等疾病[1]。
法理从语法构成或逻辑顺位上是先法后理,由于关涉了秩序、利益、权力、权利、效率等的价值,因此,无论是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包括了法理领域的论述,贯穿于社会活动和多元主体的行为中;无论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体公民都在利益的博弈中寻求法理的支撑。法理甚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演绎为一条基本的适用原则,在法律具体规范脱域时,遵循法理成为基本的援引规则。法理的构成路径首先体现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实践中,以纯粹国家法的样态规制社会主体行为,理成为辅助的补充。可以说,理的部分是法领域的延伸,彰显法隐含的精神、原则。法理出场于与法相关的法域和法缺场的其他非法域,但其逻辑路径是先法后理,国家法的遵循和适用是前提,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法的位阶宣示了法适用的权威、强制、范围等。法理辐射更多的是国家法在全社会的适用,强调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的普遍性、强制性、阶级性,传递守法的基本义务和违法的责任承担,法理在空间上紧扣国家场域。但法的刚性和固化条款难以阐释所有的社会行为,法不是治理社会的唯一工具。因此,蕴含于道德层面的理相对法而言具有更多的柔性、弹性和灵活性,法理的身份为法的调适孱弱预留足够的 “理”的空间。基于基本的社会法则和人伦常情,法理深刻阐释了国家法与社会、地方性知识的共性,侧重的是法的先入为主,自上而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法的治理手段促进社会发展、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在这一目的的践行过程中,有很多场域或空间仅仅依靠法是不能够解决的,国家法应规避自身天然的权威自傲,尊重蕴含于地方性知识中丰富的 “理”的元素,尊重地方 “理”的特殊治理价值,何况在地方特别是蕴含民族习惯法的偏远乡村的某些社会行为难以通过法进行调适,法弘扬的宗旨在这样的场域中是不能完成法自我解释的。法的使命有赖于地方多元的 “理”的要素市场,即 “理”根据法的适用效度顺势而为,伺机而动,与法共同促进社会良治。
有学者认为,“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应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四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⑥ 谢晖:《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载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 情感并非只能是任性的和不公正的,并非不能作为法律价值的终极来源。⑦ 郭忠:《法理和情理》,载 《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
三、理法的实然思维——凸显 “扬理抑法”地方性逻辑
与法理的应然适用路径相反,理法是自下而上的逆向思维。先理后法,首先凸显的是更具地方性知识的 “理”,法并非首选的要素。在前文提到,法理的应然路径中国家法适用要注意地方性知识中的各种 “理”,村规民约、习惯习俗以及其他非文本的 “理”的要素。在乡村场域,村民遇到纠纷或矛盾时首先用到的高频词是 “讲理”,在 “你太不讲道理了”或 “简直是无法无天”的语境中阐释 “理”的地方性权威。在他们能理解的视野中,合法并不一定有理,但有理是否合法不置可否,即重心在于 “理”。先理后法,除非是众所周知的如故意杀人罪等的法域理解。在乡村之所以扬 “理”抑 “法”,主要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村民法律意识的普遍薄弱,法律术语的欠缺导致他们通过地方性语言融入到 “理”的语境中;二是乡村熟人社会在能规避法介入的情况下,除非是较大刑事案件,其他斗殴、民事纠纷等尽量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解决,预留双方的 “面子空间”,所谓 “抬头不见低头见”,自身回避了法的干预;三是通过诉讼的渠道成本高,参与的成本是确定的,即便胜诉,是否执行到位尚不确定,因此利益存在于法的应然阶段;四是在法庭的特殊空间中,法官、当事人、旁听者、代理人等庭审要素的严肃性、权威性带有略微的恐吓感、压抑感,增添心理负担;五是村寨乡土法杰或精英人物可以帮忙协调解决,这样的 “非法话语”更适应当事方的思维逻辑,相对于法的 “专业性条款”更入耳;六是通过中间人的 “讲理”融入了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将习惯习俗、村规民约、个体品性、村寨社会舆论、左邻右舍评价、今后的和睦共处等进行深度加工,通过良好的协调处理,这样不成文的地方性 “讲理”系统 “胜”于国家 “权威话语”。扬 “理”抑 “法”,国家法条被地方习惯 “知识化”,国家的法律在自下而上的乡村治理路径中反而被边缘化了。当乡村矛盾演绎到必须由国家法干预的时候,“讲理”的逻辑被弱化,因为国家法同样蕴含了更大的 “理”,国家法不是唯一,即便在乡村繁琐的纠纷中脱域,但也不会 “临阵退场”。
在乡土场域的很多矛盾和纠纷解决上,国家法并不绝对具有优先性。除了诉求成本以及法庭隐含的权威和严肃阻隔了利害关系的亲和性外,主张权利的话语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充分的表达,特别是在国家法的语境下,民间 “理”的阐述解读受限。而情、理、法的阐释离不开特殊的乡土环境,亦不能脱离村规民约或其他民族习惯法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深描。理法之理即蕴藏在习惯法的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当纠纷发生后,村民首选的民间法或习惯法的解决方式,更接地气、规则相宜,因灵活性强,弹性大,寓法入情,再由理到法进行解读。因此,理法的路径范式往往能将看似复杂的诉求解决好,更重要的是效率高,当事人心理认同。什么叫民间法?梁治平认为: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与 “官府”相对的是 “民间”,因而在国家法之外,可以用 “民间法”一词来作区别,故民间法是指国家法之外存在的具有法的属性的社会规范。③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谢晖避开民间法的具体定义,而是从其价值进行阐释。他认为:“对熟人而言,以利益关系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反倒是不能接受或不容易被接受的规范,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不可接受性。而以情感为原则与核心的民间法,反而是容易接受的规范,具有更多的可接受性。”④ 谢晖:《论民间法与纠纷解决》,载 《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即使一个国家因为种种原因,可以改造既有的以习惯法为主的民间规范,但民间规范作为人们交往行为规范的事实不可能被消灭,纵使旧的民间规范被淘汰了,新的民间规范也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迁应运而生。”⑤ 谢晖:《论民间规则与司法能动》,载 《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
四、法与理的辩证关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理”既有伦理、常理的解释,也有道理、理论等的分析,暗含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某种路径、规则或规律。但无论基于何种认识,“理”的本真意义都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解决事物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事事要在理,事事要循理,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探寻路径。正因如此,理与法发生了关联,构成了法理或理法的价值。但在本文的研究中,第一个法理的 “理”与第二个概念理法的 “理”范畴不同,前者指国家话语下结合法的精神、原则,并在一定的政治语境和法律脉络中筛选或浓缩出来,体现具有法治精神性质的 “理”的国家公权性。而后者的范畴并非在国家话语和社会权威语境下,即不是法延伸的理,也非政策、文件等的精神映射,剥离了与国家公权力染指的社会原则、规则甚至政治语境演绎的 “理”,而是民间特别是乡村视野下的习惯、习俗、村规明约、人伦道德等熟人社会中生存的独具地方性知识的 “理”,植根于浓厚的地方人文土壤。与法理层面的 “理”比较而言,缺乏公权力的文本表述,更多的是通过乡村精英或乡土法杰、权威人士、知识分子群体的威信、个人魅力等进行阐释。理法之 “理”是乡土村民的交流方式和解决工具。通俗而言,蕴含法理性质的国家大道理他们不懂,但是特殊历史空间下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和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更适合自下而上的理法场域。因此,笔者的 “理”的研究半径脱离国家法理的“理”域,而专指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一切地方性话语体系和规则,即理法中的乡土之 “理”。为了不引起后文论述的逻辑混乱,特作为一个部分进行说明。
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家法还是习惯法和民间法,都是一种调控社会秩序的规则。社会控制的方式有多种,法只是其中的一种控制手段。法律作为规则的一种,都是为了更好地确保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保障国家机器部件的正常运转。不可回避的是国家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国家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以权利义务为中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在强大的政治语境和权力谱系中功能被无限放大,尽管也的确需要这样的放大。但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对乡土秩序的调适价值却被社会所弱视或忽略。如果没有民族地方习惯法的规制,国家法仅凭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是很难对地方社会秩序进行最佳控制的。
五、力求法与理的互融共治
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因素,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笔者以 “矛”比喻为社会问题或社会纠纷,“盾”比喻为解决问题或纠纷的方法,“矛”具有侵益性和主动性,同样,社会问题或社会纠纷具体破坏性和延伸性。对此,就需要 “盾”的防范和化解,笔者认为,“法”和 “理”共同构筑了防范和解决社会纠纷的 “盾”,即 “法”之盾或 “理”之盾。一般而言,法代表国家意志率先对社会问题或纠纷进行评价,以决定是否介入,在对社会治理中凸显 “法”先行的路径,法于国家和社会是解决 “矛”问题的首要方式,在诸多解决方式或解决路径中具有首要的 “价值位阶”。强大的立法、司法、行政、仲裁等机构或组织与立法者、执法者、律师队伍、科研工作者等主体共同构筑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严密体系。法的权威性、广泛性、公平性等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权威之道,演绎了先法后理的 “法理”路径;然此 “法道”并非唯一性,除了国家权力场域中 “理”的补充,还有乡土场域的地方之 “理”,蕴含在习惯习俗、村规民约、地方性话语规则和体系中,在熟人社会的乡村 “治理市场”更大,效果更好。国家层面的法与理只有在必须介入的情况下,村民才不得已而选择之或被动选择 (如被提起公诉)。国家法理的话语权被乡土农村 “地方性知识”裹挟的 “说理”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在我国数以万计的乡村中,依靠乡土之“理”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不胜枚举,村民在很多琐事纠纷中一般首先找寨老、头人、村委会、村中权威人物等进行调解,无论是刑事、行政还是民事领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首选调解,而利用国家法的诉讼程序是在说理解决不了时才考虑,即国家法理的适用在 “路径位阶”被边缘化,乡土调解之 “说理”率先登场,“说理”的话语具有解决乡土问题的 “准司法性”作用,张扬的是由理到法的理法逻辑。
在城镇,国家法理解决问题和纠纷的市场要广阔一些。在乡土农村,“说理”性质的理法维系一方社会秩序的作用更为明显,不是说国家法不重要,而是在占据绝对权威和统治力的社会场域中,法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日益提升,治理体系愈加完善,法理不可或缺,难以替代,是国家 “法盾”的重要 “防火墙”。无法难以国治,弱法更难良治。因此,由法到理有其应然的逻辑解释;然仅仅依法之治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乡土农村繁杂的琐事和其他特殊的社会问题,需要独具地方特点的 “说理”论道,通过柔性的伦理道德和村规民约等进行解决问题的试探性尝试,彰显国家法理的 “君子气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方面为国家节约了司法成本,一定程度上契合“村民自治”的语境意义;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法理层面的枯燥条文或判决依据,当事人的心态是 “不得不接受”,迫于国家法强大的威慑力,法理层面的公平未必延伸到当事人内心的平衡,何况法律的审判过程根据严格的程序和严谨的法律语言进行,忽略了当事人经历的特殊背景和利害关系。伦理道德等的因素被排挤或弱化,当事人有限的法律知识不足以通过法理的思维进行自我安慰和评判;相反,独具地方性知识的 “说理”因蕴含了更多的道德因素、社会舆论、熟人看法等 “法外”元素,加之彼此心领神会的地方性语言和表达习惯,使得当事人不是迫于接受,而是心甘情愿地找其他理由让自己主动接受,自己给自己找地方性的 “理”性阐释。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先法后理还是先理入法,都应除却这样的 “价值位阶”路径之争,应遵循法适用的规律,违法犯罪不适用调解的,地方性知识再丰富也只能通过国家法理解决,法不能脱域;当民事案件或者可以调解的其他案件在当事人合意的情况下,不经过诉讼,可以进行非诉调解,凸显理法的适用路径。法与理均是我国 “君子之治”,都尽其能事窥探最适合的公平之道,最大化的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国法中应细探和重视乡土之理,乡土之理应参照国法之魂,方能实现美美与共的 “君子之治”,助推乡村之治。
六、结语
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征程中,依法治国是重要的命题。从法制体系的层面,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都在对国家法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实践。对于法律执行中的缺憾也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跟进和学术界的理论解读,即国家法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等的绝对法制话语权,这无可置疑。但如果将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维护、纠纷解决等置于法治思维的语境,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国家法并非唯一的治理手段。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依法治国也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等的保护。除了法制的元素外,乡土场域的诸多道理特别是蕴含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的乡村,理与情、理与法、理与面子、理与尊严等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性知识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下,民间规则、习惯习俗因其权利义务的内嵌及处罚的内容而被赋予习惯法或民间法或村规民约的内涵。乡土场域中的很多矛盾纠纷其实都是因琐事缘起,然琐事解决的思维路径恰好需要理的渗透。尽管我国的法制教育和法治宣传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依然不够,很多偏远地方的村民法律意识薄弱,法治思维有限。因此,根据习惯习俗及生活道理来解读和判断纠纷中的是与非成为常态。毕竟,在乡村,除了日常遵守国家法的应然思维外,人们很少通过诉讼的程序解决矛盾,即国家法在乡土场域中的纠纷解决存在的交集暂时无法与地方性知识的道理系统相比拟。
当然,在司法实践特别是民间矛盾调解的非诉程序中,合法性是首要考虑的要素,地方性的理论系统不能跃出国家法包容的底线。国家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知识系统。因此,理的解释不能超出法的精神。同理,国家法也应在法治的思维中尊重乡土场域的纠纷解决方式,将习惯法与国家法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实现乡村的良治和振兴。由法到理与由理至法的不同路径并非两条平行线,从渊源上,国家法的产生也缘于原始的习惯,与民间的习惯之理有共同的土壤,只是国家法的专业性、系统性、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浓缩了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而民间之理则根据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场域有多元的存在样态,对人们的生活纠纷和琐事矛盾起到重要的调适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法理与情理有统一调适的空间。如果固执否定习惯法、民间之理的路径作用,强行适用国家法,不但造成后者的水土不服,甚至不符合整体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国家在倡导乡村振兴,但如何实现乡村的发展,从法治治理的方式上而言,法理与理法的融合、国家法律文化与民族文化习俗的包容、国家法权威性与地方知识特殊性的互补是重要的关系考量,国家法适用路径的刚性与乡土场域道理的柔性有机嵌入乡村法治的思维模式中,将法理情进行辩证的司法适用,方为良策。
兽面纹广泛出现在各种玉器上,有的素面无底纹;有的充填着各种底纹;有的较为抽象,有的较为具象,均具有一定的骇异性。如瑶山10号墓出土的玉三叉形器,见图2,器上的兽面纹,眼睛、鼻、嘴部位鲜明。
Abstract: Legal principle is the necessary path from law to reason to meet the social demands,which highlights the expanded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law and belongs to the top-down mode.Reason principle is the local thinking mode of resolving social disput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local field, which aims to emphasize the logical connection of folk feelings, theories and laws and to show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customs with the national law from the bottom up.When the state promotes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governance, customary laws such as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local field shall also be brought into the system of rule of law.The legal thinking of the state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local laws shall erase the situation of competition, respect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Legal Principle; Reason Principle; National Law; Local Law; Local Field
DOI: 10.19350/j.cnki.fzsh.2019.01.003
*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课题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JJD850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卢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