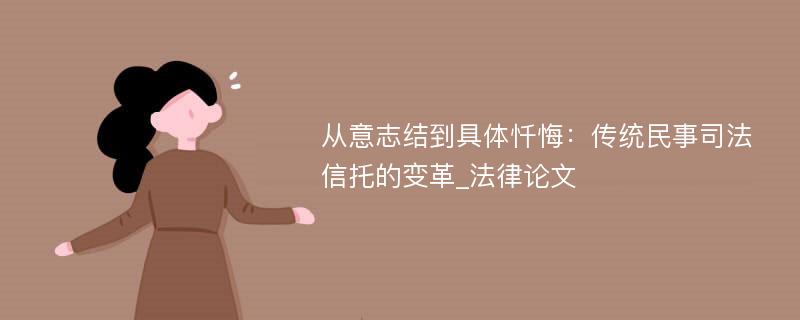
从甘结到具结悔过:传统民事司法信任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结论文,民事论文,司法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3-0128-09
一、问题之提出
刑法学界对非刑罚处罚的研究并不太多,主要的论点集中于非刑罚处罚方式的存废与否,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探讨尚付阙如。我们在本文中将针对当前非刑罚处罚方式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当代刑法中具结悔过作为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实际上展现了刑法的宽容性,即不仅体现了对轻微犯罪人的宽容,也展现了对刑法自身的宽容——刑法的谦抑性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动辄使用刑法或者刑法万能的思维得到弱化。更为重要的是,具结悔过等非刑罚处罚方法也体现了对犯罪人的信任,社会相信依靠犯罪人自身的能力能够消弭罪行,恢复稳定的秩序。非刑罚处罚方法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司法信任之意。就中国传统司法而言,使用具结的情形十分多。由于民事和刑事案件不同的审判程序,具结的使用也不大相同,主要的不同是在民事司法中是否使用“甘结”。而对于民事和刑事中都要使用证据或者需要担保时,具结则普遍采用。由于民事司法中使用的“甘结”有着更为不同的含义,更能体现对诉讼当事人的信任,因此,本文主要使用“甘结”来比对现在刑法中的“具结悔过”,试图链接古代司法传统与现代刑法,借此说明“具结悔过”可能展现给我们的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意义同非刑法处罚的内涵具有密切关系,非刑罚化是刑法民法化的直接要求,表现了对违法犯罪者的人文关怀。①诚信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民法化的过程中,对诚信原则的体现则成了刑法民法化成败的关键。“具结悔过”等非刑罚处罚方法正是体现着意义重大的诚信价值观,对“具结”这一意义的揭示,不仅对刑事立法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民法典的编撰也具有警示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民法典和刑法典的传统化与现代化进行沟通的尝试。
二、清代民事司法中的甘结
“结”字从连接、聚合等义引申为判决、治罪,所以后来也将那种表明保证负责或承认了结的司法文书称作“结”。“具”做动词用,如具状(备办词状;写状子)、具结检验(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出具保证,以免对尸体、现场等进行检验)等等。因此,"具结"是指对自己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表示。同时,“具结”也可作名词,此时“具结”也叫“执结”、“甘结”、“保结”、“检结”、“切结”等。此类表示负责或承认了结的经过签押的字据很大程度上包含着担保的意思,并且也可以看作是古代愿意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普遍的意思表示形式。“结”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一是“甘结”,“甘”表示自愿、乐意之意,如甘伏(甘心降伏)、甘罪(自愿承担罪过)等。由具结者为保证自己的身份、行为而出具的结,称为甘结,又称自具甘结、具结。二是“保结”,“保”有担保之意。由具结者为担保他人的身份、行为而出具的结,称为保结,亦即为他人担保,其担保方式又有联保、互保、连环保等。出具甘结或保结,是由传统社会中注重信用的心理和文化因素演化而来的传统管理方式。
(一)甘结的形式与内容
清代州县的自理案件包括民间细故和律例规定的只处笞杖刑的轻微刑案。在清代的司法程序中,对这类“自理词讼”案件的结案形式,并没有统一的规定。通常的结案的形式分为两种:责惩及训诫和息。责惩方式包括笞、杖、枷号。训诫和息大体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堂审,州县把两造各自训诫一番,让他们出具甘结、遵依等保证书,有的还需乡保亲谊写保状;第二种是在经过调停后由原告或中间人撤诉销案;第三种形式是经过审理以乡里调节,州县官在审理后责令乡保亲谊调处或加派差役协同调处。这三种方式经常交织使用。一般在民事案件审理终结时,由当事人或其监护人、调解人出具甘结、保状、禀呈,表示悔过、服输或和解,州县官作出批示,即可结案。民事判决大多数表现为在当事人或监护人、调解人的呈状、保状以及甘结上作出批示的形式,“甘结或保状加批示”“就是自理案件的基本结案形式。甘结的内容多样,主要是表达当事人(尤其是败诉一方)通过诉讼,心甘情愿地接受司法审判机构作出的裁判结果,并保证不再争讼滋事,愿意切实履行,大致上有表示悔过、服输、和解三种甘结。
我们从南部档案中找到一份完整的甘结,涉案双方当事人都有甘结(具结),据此可以看到甘结的真实面貌:
(原告)具结状
民妇杨邓氏,今于爷台前为结状事情:氏具告杨天富等一案。沐恩集讯,查氏夫外出,向夫兄杨天富滋衅。凭娘家胞弟邓元恺叙议,以氏出钱九千文,邓元恺书约领归,事后与杨狗儿角口滋衅,不应捏词将伊控案,恳免深究沐断,杨天富与杨狗儿再给氏钱四串度活,永断葛藤,俟后再向杨姓滋非,自甘坐罪,今氏遵断具结是实。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具结状妇杨邓氏(画押)
批:准结后再寻衅定予重处
(被告)具结状
民杨天富,今于爷台前为结状事情:杨邓氏告民一案。沐恩集讯,查杨邓氏向民寻衅,凭伊娘家胞弟邓元恺等议给钱九串,书约领归。事后杨邓氏与杨狗儿角口滋衅,将民一并控案,讯明断民同杨狗儿从出钱四串文,永断葛藤。今民遵断具结是实。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具结状民杨天富(画押)
批:准结②
从中我们知道,甘结的格式内容包括:具甘结人,因何案而具,最后是固定格式"所具甘结是实"或者“遵判和息”等等,当然也有口语化词语来表达甘心接受的意思,如“再不敢妄为了”。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都申明自己是“以依奉结得”,是遵照州县官的审断结论才具结的,是遵命和息。在州县“甘结”的案件中,不仅败诉方必须具结保证不再滋事,胜诉一方也应当具结,双方都承认官府审理的结果。州县官的民事判决经常是在当事人的“甘结”上作出的批示,③这在以上甘结的具体形式中可以得到证明,此种批示被称为审语。“审语乃本县自准告词,因情判狱,叙其两造之是非,而断以己者”。这种“审语”因为是“以主惟在我,直决之以为定案,而更书其判狱之词以昭示之也”。案件经原、被告签字画押,便可归入卷宗,以备上司不时或定期检查,每月都要造册上报。因此,“审语之难,不在合式,在原被之匿情肤诉,两证之左坦饰虚,而我能折之,使彼此输心允服,因笔之以为不可移易之为难也”。因为如果诉讼双方有不服的,可以上控,乃至到中央去京控,这对州县官的前程影响甚大。④“使彼此输心允服”是上级审查民事案件“月报”制度的主要标准,而“彼此输心允服”的形式表现则是双方当事人的“甘结”。这是“甘结”的制度性意义,既有实体性(当事人服判息讼的标志),也有程序性(案件审结和月报程序要求)。
(二)甘结与调处
清代民事司法中普遍采用调处,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论息讼”中曾说:“词讼之应审者十无四五。其里邻口角、骨肉参商细故,不过一时意气,冒昧启讼,或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乎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⑤根据现存不完整的档案记载,嘉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0年间宝坻县244件自理案件中,责惩结案的,不过二十几件,其余均系调处结案。⑥诉讼内发生和解、撤诉等情形时,州县官通常会给以批示“准”或“不准”,批令调解时也会责令调解人将结果禀复,并且予以确认执行或者确认违法无效。在官府确认之下的调解结案当事人往往碍于公权力大多自觉执行,若有少数不遵从者,官府有责任保障其执行。
乾隆二十四年(1769年)九月杨梅控周凤章掘挖古堰案即是一例。州县官受理后,批“约保邻证查理复”。乡约刘朝君等人查明杨梅控状中的古堰经过杨梅的田产和周凤章的产业,以前并没有争端。周凤章的弟弟周国章未经周凤章许可将田地卖与杨梅后导致周凤章挟怨拆毁此堰。刘朝君等人向周凤章理剖,让其赔偿修复梅堰,而周凤章不肯,于是刘向州县官禀复案情。三个月后,八月初三州县官又让刘朝君去调解,然而仍然未果。八月十八州县官差原差役协同刘朝君等人查复梅堰是否是古堰。此案在调解与裁判中交相进行,乡约地保的查证调解与州县官的批令互为作用。后来差役讯问熊启疆等人,他们承认杨梅的堰只是个水沟,而被告、原告都供认梅堰并非古堰,是个水沟而已。此案明晰后,州县官写下判词:“讯得杨梅口质之中证喻凤祥等称系水沟,并无古堰,始行具控。将杨梅责嘴十五下。喻凤祥、王思政、陈伯山各责嘴十下。生员熊启疆掌手五下。仍将杨梅、喻凤祥、王思政、熊启疆押候。仍令息事人等照谕具息,取具遵依甘结和息立案。”⑦州县官在裁判责惩杨梅、喻凤祥等人之后,仍然押候,让相关人写下和息状,遵依甘结立案,是裁判与和息相结合的典型。从中可以看到,甘结与和息(和平息讼)相连,可以认为甘结的性质与和息同一,即使得双方当事人“自愿”了结案子。但是在此案中官方还使用了教育式的“责嘴”惩罚,从而迫使双方当事人接受“甘结”。
当然,也有当事人利用“具结”这样一种制度来迫使官方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淡新档案中有一例便是。当事人之一的被告刘琴五(73岁)被其族人刘桂春告上法庭,桂春的祖父曾让刘琴五的父亲耕种一块田面权归他的土地,无需向他交田面小租,田地大租则付给拥有该地田底权的另一位地主,这样过了约20年,到1875年,当初立契双方均亡故,桂春要求琴五付给他小租,过去6年他确实交了620石租米。到1880年,桂春家道中落,想卖掉土地,却又无法使琴五放弃租种权,于是桂春向知县呈控。琴五立即呈词,辩称他父亲的耕作权是以900元的借贷代价换来的。1880年11月29日第一次堂讯,双方各执一词,知县只好传唤其他族人作证,到12月5日第二次堂讯时,知县已经觉察到琴五的说辞纯属捏造,故断令:桂春的祖父确有田面权,桂春自当有权随意处置,另一方面,由于琴五的父亲已交付大租20多年,这笔租米实应由田面所有人承担,所以琴五应该得到补偿。因此断定桂春先给琴五450元,然后才能要回土地。但琴五坚称他应得900元。翌日,知县重申自己的判决,但琴五抗称“不敢遵断”,不然全家将无地可种。
由于清代法律规定要当事人甘结,所以只要琴五不让步,这件案子就不能算正式销结。当月21日,知县再次堂讯,这次他指出他判给琴五的补偿费要比当初族人调解时所定的300元高出150元,但琴五仍拒绝接受,知县终于动怒,责斥琴五“侍老不允”,并下令扣押,等候下次堂审。3个月后,知县再次决定将补偿额提高到500元,但琴五仍嫌不足,他情愿坐牢,也不肯甘结。这样,琴五凭借一股顽强劲,迫使知县将补偿费一步一步提高到650元,到1881年8月13日,他才接受衙门的条件。后来又另加堂讯四次方才结案,直到12月中旬,亦即衙门受理15个月后,涉案各方均具结接受,情愿了结争端。⑧据此不难发现,“甘结”是被严格当作民事司法裁判的最终程序,因为官府并不作出正式的判决书,只是作出批语或者审语,刘老汉才得以使用了民事司法以“甘结”为结案标志这一程序性规定。官府的让步一则因为当事人为老人,二则也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官方表达,即县官并不判案,而只促成案子的解决。因此,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它所引申出的一个相应的要求是,当事人出具甘结,自愿接受官府裁决。⑨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甘结是清代州县民事案件的最后程序而且是必经程序;二是官府可以使用各种权力资源迫使当事人接受裁判,并出具甘结,因此甘结丧失了其当事人自愿的本意;三是甘结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民事调处功能的发挥,其本意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调解结案的大幅比率即可推测),这种效果的实现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和官方都真心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此为大圆满;另一种是当事人一方利用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使自己的诉愿得到满足,官方反而被“胁迫”。据此,甘结的形成可能存在当事人和官府都会被彼此“胁迫”的假“甘结”,也有双方意愿都能得到满足的真“甘结”。当事人可以利用“甘结”制度作为同官府和另一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砝码,官府同样会利用教化或者强权迫使当事人接受“甘结”。
三、甘结在当代法律中的转变:具结悔过
(一)刑事司法中的“具结悔过”
1950年公布的《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规定,县(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有权逮捕、拘禁并判决被告死刑、没收财产、劳役、当众悔过或者宣告无罪。可见,当众悔过在建国初期是一种刑罚方法,它是以判决书的形式来表达的惩罚方式,并不具有立即执行的性质。直到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才取消了这种刑罚方法。自清末刑法改制确立了以教育刑为主导的刑罚体系和制度以来,我国逐渐在刑罚的裁量和执行方面引入惩罚教育制度,主张在行刑过程中施行感化教育,注重刑罚的轻缓和对人权的保障。1979年的刑法或多或少受到世界范围内刑法改革运动的影响,非刑罚化思想有所渗入。其中,《刑法》第3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可见,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这既不是行政处分,也不是刑事处分,而是人民法院对其采取的一种教育措施。所以,当人民法院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被告人,予以当庭口头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赔礼道歉处理后,就没有必要再用刑事判决的形式予以判处。以刑罚之外的教育、民事和行政措施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是非刑罚化思想渗入中国刑法的一大表现。除此之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同时做了配套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基本上没有对相对不起诉人采取训诫、具结悔过等相关教育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在刑罚制度之外还存在着众多的惩罚制裁方式,其中的责令具结悔过便包含有道德声讨的意味。道德教育的思想贯彻其中,这是对古代德化乃至德治的一种回归,但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其作用。在刑法中规定道德的和法律的(民事行政等等)惩罚方式,实际上是在刑法条文中引入了社会行刑的意思表示,在表达上至少是主张多元化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造理念。这也是对古代司法的一种回归。
关于责令具结悔过的适用方式,刑法无明文规定。根据司法实践,既可以在宣告有罪判决后要求犯罪人在一定时期内写出不再犯罪的书面保证,也可以事先写好悔罪书,在宣告有罪判决时当庭宣读,还可以将悔罪书印成多份,交给有关单位或基层组织。该处罚方法大多与训诫并用,或者两种方法均用口头形式(但具结悔过口头表述的,应制作笔录并交被告人签字);或者前者口头形式,后者书面形式;或者两者均用书面形式。一般的做法是,训诫由书记员记入笔录,另外让犯罪人再写一份具结悔过书附卷。从中可以看出,具结悔过并不制作判决书,只在案件档案中留存,与权威性的判决书大为不同。这种形式并不代表具结悔过微不足道,它除了表达社会危害性相较于通过判决的犯罪行为较小以外,在法律上至少表达了教育轻微犯罪的意思。
中国行政(民事)诉讼中也有责令具结悔过的做法,但与刑事诉讼中的具结悔过性质不同。在行政(民事)诉讼中,责令具结悔过是指人民法院对具有妨害行政(民事)诉讼行为情节轻微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后,责令其以书面形式承认错误、认识错误,并保证不再进行妨害行政(民事)诉讼行为的一种强制措施。一般适用于经训诫后仍继续进行妨害诉讼的行为但情节相对较轻的人。显然,行政(民事)诉讼中的具结悔过不同于刑事诉讼中的具结悔过。
当然,由于我国目前对于非刑罚方法不够重视,在司法上也较少使用,而且也没有对非刑罚方法的执行作出相应的监督制约性规定,致使在一些情况下,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非刑罚方法处理的决定后,当非刑罚方法被犯罪人拒绝执行时,司法机关会因法律无相关规定而无法对拒绝执行非刑罚方法的犯罪人采取相应措施强制其执行。
(二)其他法律中的“具结悔过”
1979年和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第56条均规定了具结悔过的适用情形:“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取保候审是危害性较小或者判刑较轻的犯罪人所适用的制度,均反映了国家或者社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一种信任。
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1994年的修订本第30条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其中就规定了具结悔过。但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本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此处的“强制性教育措施”目前是指劳动教养。⑩该法所规定的轻微处罚方式有警告和罚款,将具结悔过取消,一则可能是因为具结悔过的意义已经包含在警告中;二则可能因为具结悔过的作用不大,干脆使用“强制性的教育措施”。
四、具结与司法信任
从世界化刑罚发展和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讲,非刑罚惩罚方式必须在中国刑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下面讨论信任关系与具结的关联。
(一)信任在古代民事司法“甘结”实践中的强化
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11)法律作为社会秩序调整的手段之一(并非主要手段之一),并非经常使用。州县官员对于影响百姓生计利益的民事案件采取的根本策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2)权利的分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破坏的秩序重归于好。“解铃还须系铃人”,官府深知要恢复正常的人际秩序并非靠官方的一纸判决便能达到,它还是需要纠纷双方自我的秩序回归,这也是民事司法多没有判决出现的原因。纸面化的判决背后所包含的真正意义是修复秩序,当判决本身只具有形式意义的时候,判决便不再重要,因此,甘结的出现正是在秩序自我恢复的意义上才具有强大的功能。甘结所传达的信任关系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即互相作出甘结,对双方能自愿履行裁判表示信任,这是双方出具甘结的基本要求,若是一方不信任,一方便不会作出甘结。二是民与官的相互信任。此处的信任又具有两层意思:其一,表现在涉案当事人信任官方所作出的裁断是公平合理的,否则可以拒绝接受。进而,信任官方能够确保裁断的执行。其二,表现在官方对涉案当事人的信任,一旦当事人作出甘结,官方便有理由认为此案处理得十分正确,并有理由信任双方当事人能够当场或者事后自觉履行。可见,信任关系对于纠纷解决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的作用,包括审判拖延的成本和执行判决的成本。(13)当然,由于作出甘结的人不同,甘结所具有的作用也不同,监护人、调解人或者乡保等作出的甘结则更多的带有保证的意思。此种保证与古代中国早有的保甲制度和连带制度密切相关。由于古代尚未有官方的“公证”制度,“私证”畅行,除了在商业私行为领域外,在公行为如诉讼中也经常使用。在诉讼中对证据等作出担保的制度是民与官之间信任关系的具体写照,担保所包含的信任消弭了由于古代侦查技术的缺失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同时也将百姓网罗在帝国政权控制的大网之下,在熟人与伦理社会的古代中国,此种制度能大为盛行也实属必然。我们以往的研究始终局限在帝国对民众的控制和教育的层面,对民众与官府之间的信任缺乏研究。
同时,在清代民事司法中将甘结作为诉讼的最终程序,实际上与官府在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官方被视为百姓之父母,因此可借用滋贺秀三的“教谕式审判”(14)这一概念。官方不知疲倦地反复使用调处,甚至还靠责打等强力方式教育当事人,从而促使当事人自愿或者被迫作出甘结,用心可谓良苦。一方面是为了寓教于讼,教化“愚民”;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彻底化解纷争,恢复以往的秩序,维持社会的和谐安定。审判的过程实际上是官方和民众不断互动的过程,没有现代法官中立的价值理念,官方实际上在诉讼中主动承担了行政职责——维护社会安定。这是古代行政与司法合一的表现,这里我们称作“行政司法”。在这样一个语词中我们更能明白诚信机制的重要。当代行政法理倡导依法、透明、公正的行政原则,提倡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对违法行政依法予以处理。在依法行政中不断强化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关系,为政府行政提供民意支持。清代的民事司法中广泛使用调处,官方并不中立,将司法行为看作行政行为,实际上也是在构建官民相互信赖机制。从审判的过程中,我们能深刻体会到纠纷的化解是官与民相互协作的结果,缺少了任何一方的合作或者信赖,案件就有可能被拖延,秩序的恢复便成问题。信赖中虽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暂时的信赖是案件得以了结和秩序得以恢复的关键。因此,官方在司法行为中参与了同民众的信任构建,使得官方在此后的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中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资源。
(二)信任在近现代刑事司法“具结”实践中的弱化
回到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的法律,立法司法中有关“具结”制度的“具结悔过”依然在法律中使用。虽然使用效果差强人意,但无论是制度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乃至道德意义都值得关注。制度意义表现在非刑罚处罚方式是刑罚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文化意义在于传统中国刑法一贯强调教育感化的作用,道德的意义体现在同中国不断倡导的德治理念相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具结悔过,还是警告以及训诫或者赔礼道歉,都仅具有心理或者道德上的意义,是犯罪人心灵的忏悔和自我救赎。这同古代的“甘结”大为不同。以上论述表明,甘结在制度意义上不仅是一种必经的诉讼程序,也是一种实体法意义上对判决的补充,同时更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服判息讼的举措。二者之所以能联系起来,是因为在官与民和民与民的信任关系上找到了契合点。
训诫或者警告在当代法律中均有规定,其实无论是在审判中还是在行政执法中,口头的说教不可避免,即使法律没有规定,在实践中对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也依然十分普遍。训诫、警告和赔礼道歉与“具结悔过”有密切关系。实践中具结悔过主要以书面形式表现,它是在官方有形无形的说教训诫后形成的自我罪感认知,因此,在悔过书中赔礼道歉是常有的,“决心以后不再犯事,保证重新做人”也是经常的话语书写。话语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官方对涉案人“真心”反悔、“立志”改过的信任。否则,为何仅仅通过一个相对刑罚来说十分简单的“悔过”就让当事人免除处罚?当然,使用“具结悔过”毕竟是少数,针对的是可以不处以刑罚的轻微犯罪。官方对这种犯罪的信任通过“以观后效”的方式来强调。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取消了“具结悔过”,而将其改为“强制性教育”。可见,“以观后效”并不令人乐观,“具结悔过”这一相对松散的教育方式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强制性的收容教育便势在必行了。通过这一立法上的改动,我们感受到官方对民众(违法者)信任程度的降低。立法代表了官方的立场,由于它所针对的是不确定的适用主体,因此立法的规制对象是不确定的民,当然也规制官本身,一旦官员与民众均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人之后便均是民。具结悔过适用范围的不断削弱正说明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在立法时被打了折扣。同时,它还从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刑法现代化中的自身悖论。随着1981年以后我国死刑适用范围和对象的扩大,自由刑的幅度提高,并使我国过去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重刑化色彩,因而防止重刑化成为1997年刑法修订时刑法学界的强烈要求,但是在修订后的现行刑法中,死刑的罪名仍有60多个,无期徒刑的罪名多达99个,而且几乎每个罪行条款都规定了自由刑,而没有只规定财产刑或资格刑的犯罪,(15)这使我国刑法仍呈重刑结构。非刑罚惩处措施在现行刑法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使得迎合世界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成了泡影。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刑法学界在刑事立法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上也争论不休。(16)但从现行刑法看,犯罪化是主要特色,(17)犯罪圈被适度扩大,因此非刑罚处罚方法在刑法中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使得刑罚的功能被无限夸大,社会生活中一旦出现失范行为,人们不是向民法、经济法、行政法求助,而是首先要求用刑法规定,殊不知立法者应该确信社会改良在预防犯罪浪潮方面比刑法典更有益,树立人们的自尊和培养兴趣比威慑和限制所取得的收效还要大。(18)从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看出《刑法》第32条规定具结悔过等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社会治理需要综合的手段,所以该条文才不厌其详地罗列了道德的法律的多重处理方式。但仅此一条,与刑法典的全部条文极不相称。刑罚万能的背后是立法万能的立场,立法万能实际上是否认民众的理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对民众自我治理的不信任。(19)
五、具结之难:原因及结论
我国虽然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取消了具结悔过的使用,代之以“强制性教育”,但并未取消在刑事诉讼法中对作为违反“取保候审”的后果之一的“具结悔过”的规定。原因何在?
上述诉讼法中规定的具结悔过使用的情形主要是针对妨害司法审判的行为,是对程序进行中的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20)而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具结悔过则针对的是对刑法等实体法违反的后果。我们虽不能据此得出针对扰乱司法程序的惩处要轻于对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但至少可以看出,针对扰乱司法审判程序的行为要迅速处理,以免妨碍程序的顺利进行,毕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程序性审判而最终得到的审判结果。因此,简单易行的训诫或者具结悔过变成了上好的惩处措施。一旦训诫或具结悔过不能了事,便需要另案处理,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这与清代司法中的“甘结”大不相同,“甘结”作为民事审判的最后一环,既是实体要求,也是程序要求,而且甘结不是作为一种惩处措施,它成为判决的一部分,更是执行判决的保障。
更进一步分析,近现代中国法律在使用“具结悔过”的惩处方式时多偏向于轻微犯罪和程序性制裁领域,主要在公法领域适用,这同行政性和政治性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检查”相类似,使得具结这种方式在私法领域完全丧失使用价值,民事责任中与具结悔过稍有联系的只是“赔礼道歉”。虽然可以认为赔礼道歉中也包含了具结悔过,但是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在民事责任中没有使用“具结悔过”这一词。
早在周秦之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担保制度,秦代的连坐之法被视为公法领域使用连带制度的先例,到明清之际更为盛行。同时,民商事诸经济行为中担保制度也被广泛使用,宋代是一个标志。(21)纵观整个古代中国,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对“结”和“保”的使用大致上可以平分秋色,不论在司法审判还是在行政管理中。到了近现代乃至当代,在西方司法行政理念的影响下,司法或者审判与行政完全分离,分离的后果使得对官民信任的重视重点放在政府行政中。法院的独立性和消极性被强调,这种强调则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审判公平、公正,从而进一步强化民对判决的信任,因此,在司法领域,中立性本身即代表了信任的全部。
古代司法行政合一,强调法官的中立性,法官作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同行政官员毫无区分,但随着近现代司法独立的要求,法官不仅仅作为官僚,更是代表社会正义和良心的一部分而被看重,法官本身便代表了信任,因此不再有判决之后的“甘结”出现,只是发给判决书,送达之后签字或者按手印来表示接受审判。反思当前的执行难问题,我们又不得不对判决表示极大的不信任,对法官也抱有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当前司法中尤其是民事审判中对调解制度的倡导(刑事司法中对和解制度的重视也是一部分)和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推广在某种程度上均是为了重建法官的声誉和社会信任感。
治安管理处罚法删除了“具结悔过”,代之以“强制性教育”,实际上是对诚信缺失的无奈之举,而当下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强制性教育)的呼声也甚嚣尘上。这似乎是一种讽刺。当前公法领域中“具结悔过”制度适用领域的缩小与清代民事司法中“甘结”制度的广泛使用形成鲜明对照,或许当前对调解制度的强调和群众路线式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倡导是一种补救私法审判领域信任缺失的尝试和努力,刑罚的严厉背后或许该有某种温情,像具结悔过在实体法中便不应删去,因为它蕴藏了诸多的“信任”。
注释:
①所谓刑法民法化,指的是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过程中,刑法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变化的现象。参见李冠煜《试论中国的非刑罚化改革》,《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63页。
②《南部县档案》(全宗号101,目录号17,案件号581),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此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吴佩林为我们提供一些南部档案中的甘结原件并允许我们使用。
③张晋藩:《中国古代民事诉讼制度通论》,《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第58页。
④(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二《刑名部·看审赘说》。
⑤(清)汪辉祖:《佐治药言·论息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⑥张晋藩:《清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315~317页。
⑦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⑧《淡新档案》(编号22418),转引自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
⑨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159页。
⑩参见《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11)[美]D·布迪、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12)徐忠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第8~10页。
(13)参见张维迎《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03~112页。
(14)[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15)刘艳红:《新刑法调控范围之理性思考与启示》,《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第60页。
(16)当时的论争大致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非犯罪化”说、“犯罪化”说和“折中”说,具体参见马克昌《借鉴刑法立法例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法学评论》1989年第 2期,第49页;高格《刑法思想与刑法修改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4年第 4期,第45页;赵秉志《刑法改革问题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17)田宏杰:《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18)[意大利]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第93页。
(19)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阐释,详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0)该措施不同于程序性制裁,程序性制裁是通过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宣告为无效、使其不再产生所预期的法律后果的方式,来惩罚和遏制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其主体是负有刑事执法和司法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534~535页。
(21)参见季怀银《中国传统民商法兴衰之鉴》,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该书第二编“契约与信用——传统民商法的辉煌”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